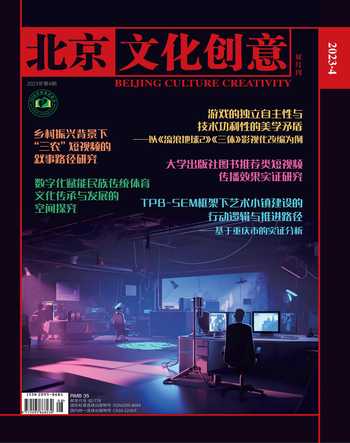游戏的独立自主性与技术功利性的美学矛盾
2023-04-29杜钊远焦仕刚
杜钊远 焦仕刚
摘要:2022年末以来,随着由《流浪地球2》《三体》改编的影视作品面世,中国科幻文艺的产出初显声势。然而,科幻题材背后的技术功利性与文艺作品的无功利趋势却矛盾凸显,形成了美学意义上的冲突。而游戏,作为一种历史久远、不断发展的文化现象,契合科幻文艺特性的同时,又保持着独立自主性,能够同时进入技术哲学与艺术美学的语境,成为有效转译信息的中介,以期构建可供对话、缓解美学冲突的平台。当科幻文艺背后的精神指向借助游戏现象的理论,介入、分析并找寻新的方向时,便有助于解决中国当代科幻文艺由美学冲突而展露的内在矛盾。
关键词:科幻 文艺 游戏美学
一、中国科幻文艺影视化改编的矛盾与指向
科幻一词,全称科学幻想(science fiction),从诞生之初便与小说等文艺形式呈现强绑定状态。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其表现形式逐渐从文字转码为影像,再从影像升维为虚拟现实,内涵愈发丰富。伴随我国经济的发展,“科幻”这种文艺范式也愈发为大众所接受。从早年间老舍《猫城记》到近年来的《三体》,无不说明科幻作为一种文艺类型能达到极高的创作水准与生命活力。
2022年末,以《流浪地球2》为首的一众作品将中国科幻文艺推向了一个小高潮,中国的科幻文艺在形式上也出现了电子游戏和电影双枝并茂的景象。纵观科幻文艺的发展史,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电影与电子游戏无疑是科幻题材最具广泛性的表现形式。相比于电影,电子游戏对于科幻题材而言更有一种内嵌的自洽性,更适于科幻文艺的特征表现。诞生于电子信息时代的电子游戏,其本身暗含着与科技概念间的结构性隐喻。在科幻文艺作品中,强调的往往是“科学技术”与“虚构世界”两大要素,其设想的未来世界背景构建、新兴科学技术展示,在电子游戏所营造的虚拟现实中往往得以通过3D立体建模的形式具象化呈现。游戏本体所具备的规则性质,与电子计算机编程语言及其背后的科技化指向也产生了直接联系。
因此,一旦将视角从平面文字的科幻小说拉入影视屏幕背后的虚构世界,中国当代科幻文艺产出便遭遇新的诘问:科幻文艺的美学追求究竟落脚何处?无论如何追寻,一种矛盾都总是若隐若现,即文艺形式背后的无功利性倾向与科幻技术主题的功利性之间的直接冲突。这一冲突实际上具备多元生成路径,需要找到一种总揽且规律性的答案以勘破这种矛盾及其身后的社会文化隐喻。
本文聚焦文艺理论及美学层面的厘清,从这一点出发,矛盾的具象表现是一众科幻影视作品的视觉效果与其剧情文本乃至整体美学风格不相符。举例说明,在《三体》电视剧中,由于经费与技术的客观限制,布景与画面美术呈现出的未来感在现有视觉欣赏习惯下显得廉价并刻意,其画面质感与原作中相对写实的时代描述呈现出一种外在不和谐;再比如《流浪地球2》的剧本编排,被强行插入了一部分亲情戏码,缺乏编剧逻辑上的前后铺垫,从而在文本层面呈现出内在不和谐。这样的倾向使得文艺作品本身的审美性与趣味性被削弱了,取而代之的是高科技展示的视觉奇观与功能性建构的剧情营造。然而,精妙绝伦的科技奇观在实际的影像演出中并不一定与科幻文艺形式本身所提供的氛围或风格相契合,功能化的剧本设置也使得叙事变得突兀。因此,廉价化的科技奇观、僵化的剧本创作等问题背后,乃是创作时的考虑不周、精神指向匮乏等带来的连锁反应,这种连锁反应所制造的外在冲突,直指题材与文艺形式本体的内部失协。这是文艺形式背后的无功利性倾向与科幻技术主题的功利性之间的直接冲突一众多元化成因中表现最为凸显、迫切的矛盾,也是本文尝试寻求突破的重点所在。
游戏作为电子信息时代的综合性艺术手段,极大丰富了科幻作品的表现形式,并且极大限度弥补了艺术表达中“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固有问题。游戏与科幻之间的相性契合,使其成为科幻文艺背后美学追求的合适载体。将游戏带入科幻文艺的语境,催生出“语-图”中介,从而创造出一种可能的窗口,以达到本文所思考的“艺术美”指向。由此,游戏的本体及其衍生概念,究竟有着何种性质,能够成为通往科幻文艺美学的路径呢?
二、游戏,科幻文艺的隐喻
荷兰语言学家、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在《游戏的人——文化的游戏要素研究》一书中,将游戏的本体精准地描述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并附带了诸多文化子体对游戏的考察和观照。①在这考察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承认,游戏行为伴随着人类有记载的历史成为某种“有意味”的聚合。之所以借用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的“形式”与“意味”理论,正是因为其符合游戏艺术独立自主与无法适应简单内容形式两种性质。这证明了它不再是一种直觉认知上的“玩物丧志”,也不是简单的人类活动状态,而是开始进入人文社科研究的概念范畴。以此为基础,游戏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方法,通过理论去解析其他概念。
这种独立自主,从本质上辨析,是一种自发性、产生于游戏本体性质的无功利自觉。它在一定程度上与现实生活拉开了距离,验证了游戏自身所处的虚拟状态。这种状态却又无法彻底脱离现实生活的观照:游戏更类似于柏拉图所认为的现实世界——依存真正的理式世界而存在。科幻文艺确实营造出了一个虚构的世界,但从艺术生产的角度来说,由于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无法脱离自身所处的环境,自然也无法与现实生活脱钩。在这一点上,科幻文艺与游戏不谋而合。约翰·维特根斯坦(Johann Wittgenstein)在《哲学研究》②中更是坦诚“语言游戏”无法被详细分类,呈现出一种“家族式的聚集”,因此,游戏的群聚形式可以被形容为具备着相似特征,但细究之下绝不相同的一群事物。事实上,从他的“语言游戏”出发,此种无功利的独立性依然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它是生活的经验性总结,映照着人类在生活中的一切细微发现。但“语言游戏”仍然不是生活,它是生活化的,是映照着生活的倒影。至此,“语言游戏”与科幻文艺之间在这种虚拟性上仍然互通。
而游戏的独立自主性,在德国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那里也获得了同等的验证。其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首当其冲地确立了游戏本体所具备的学科性独立,即游戏的主体为游戏本身。沿袭康德的观念,游戏可以说是一种无目的的行为,却又具备合乎自身存在意义的目的③——以自身来观照自身存在的意义。同时,伽达默尔还以德语词根中“游戏”,即“Spiel”的另一释义“无规则目的的反复运动”来对游戏进行分析。正是由于无规则目的的反复运动,揭示了游戏这种运动所具备的自主重复性,也印证了艺术创作及其效果的不确定性。此外,游戏行为本身成了游戏的最终目的,因而便不存在其他背后核心指向。就如同吉尔·德勒兹(Gilles Louis Réné Deleuze)的“根茎”,聚集在一起,却又不围绕着一个核心进行结构构建——它本身就是一个较为完备的自主结构,与框架下的去中心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存在着某种“结构-反结构”的奇妙和谐。而最重要的是,伽达默尔将游戏的特性与艺术作对比,从《真理与方法》的第二章起便依据相同的性质将两者归纳为同一类事物。这为游戏与科幻文艺的连接提供了直接锚定性的证明,其内在独立的无功利性与科幻艺术形式的无功利性由此对照起来,形成了语义媒介上的互通,具备了沟通的可能。
不难得出,如果将游戏视作广义上的文化现象,便会与科幻文艺的艺术具象形成对应,乃至于切实的隐喻。科幻文艺以不同的艺术形式构成了表达,无论是文学、电影还是游戏,均无法被一概而论,却又切实生成了独属于科幻文艺自身的系统。然而,它们并非围绕着一个实际的旨意或核心(这是后现代的特征),却又默认地形成了自身结构。如同伽达默尔论游戏之于游戏,科幻文艺也之于科幻文艺,通过自身存在印证了自身指向。
师从赵毅衡的宗争在《游戏学:符号叙述学研究》中对游戏作出了如下定义:“游戏是受规则制约,拥有不确定结局,具有竞争性,虚而非伪的人类活动。”①我们以此作为基础对科幻文艺作出对照:第一,科幻文艺的创作会将叙述内容放置在科学技术及近未来或未来的背景规则下,这是规则的制约。第二,科幻文艺审美过程的最终指向会根据接受主体的变化而变化,无法确定,这便是不确定结局。第三,科幻文艺将不可避免地涉及技术宰制的探讨,其为人类竞争意识的潜在体现。第四,科幻文艺的想象世界构建是一种建立在现实世界观照下的虚而非伪。
综上所述,我们将科幻文艺在创作与审美鉴赏进程中形成的系统称为一种“游戏”。这样“游戏”系统的比喻,标注着科幻文艺的精神所归,具备科幻文艺的根本特征。这种系统将带入影视改编的工业“游戏”之中,为科幻作品寻找一种精神所归。后文将对游戏理论进行解析,进而锚定科幻文艺影视化改编的美学矛盾。
三、中国当代科幻文艺影视改编的美学难题
游戏的性质决定了其可代指科幻文艺的系统性,尤其是两者之间艺术无功利性质的遥相呼应。其审美过程中有两种参与形式,其一是直接进行游戏的主体,其二是对于游戏的观看。伽达默尔着重陈述了游戏观看者对游戏的重要性。被观赏是一种明确的审美过程,它不仅仅印证于游戏,也几乎印证于所有艺术门类、艺术形式。因此,游戏的观看者逐渐变成了审美主体,这种观看不仅仅是旁观,更是观赏。观赏代表着审美主体催动着自身的确切经验,尝试去分辨、赏析,进而完成对于艺术作品的情感共鸣。而当下的中国科幻文艺作品,无论是文学、电影还是电子游戏,均可以通过“观看”这一形式完成审美进程。
可一旦我们将中国科幻文艺的审美观赏视作游戏的观看时,游戏观看者必定会进入无功利自觉的语境——即艺术与游戏的无功利趋向。自康德以来,美被认为是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让人想起一种拥有中心化倾向的德勒兹逃逸,其内在有着一种存在且并不凸显的根本矛盾。当下多元化后的美感虽然已经无法达到德国古典美学理想中的那种纯粹——它是被边缘碎片化的,但仍保留着部分主体性的美。
中国当代科幻文艺在影视化改编时所提供的审美感受便是其美学难题所在。任何文艺形式都无法逃离其无功利性的趣味所在。从这一点来说,诗意与韵味的缺位是中国当代科幻文艺影视化所面临的直接问题。当下中国科幻文艺的代表作品无疑是《流浪地球》系列电影及《三体》的相关影视化改编。《流浪地球》和《三体》从其文学原著来看,无论是语言特点还是文本诗意,均难以被称为足够“美”。它具备文化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精彩,却在美学中失语,也就是在“游戏”的趣味中失语。而相似的问题仍然在科幻文学改编而来的影像中存续着。《流浪地球2》镜头语言与电影工业美术设计是合格的,但在整体观感上却很难谈得上足够“美”。其镜头美术风格表达出的艺术特征,结合其文本部分的剧情设定,缺乏统一和谐之感。电影内的部分视觉场景处理,例如MOSS人工智能出场的工业化场景,过于简单干净。这虽然符合高科技的观感逻辑,但在整个末世背景下,却是反直觉的。这种反直觉引发的便是视觉风格的不统一,缺乏美学逻辑上的考量。
科幻文艺对于科学技术的描绘与思考是其兼顾技术与人文的立身之本,如何达成两者间微妙的平衡是其诞生以来就存在的重要命题。然而,沉迷技术前景的描绘,抑或假借科学之名表达立场,这是科幻文艺经常出现的状况。在《流浪地球2》中,无论是人机伦理关系的探讨,还是在巨大灾难面前对于人性表现的描绘,其社会学与伦理学意义都十分深厚。一个直观的问题是,《流浪地球2》非常精彩,却难以被界定拥有一种直观且全面的“美”。电影工业的合格化可以让其被大众舆论满足,却无法以一个文艺类型的标准被满足,让艺术及美学被满足。美、丑、优美、崇高等传统审美范畴,鲜少能在中国当代科幻文艺的表达中找到相似对应。
事实上,愈加繁复的科学技术与飞速发展的科学概念,都是以信息的方式将文本原存的诗意挤兑了出去。小说是文本,电影也是文本,游戏自然也是文本。在文本的容量内,诗意与韵味依存,但文本的容量是有限的,当新概念、新技术以信息形式充斥进入时,诗意的消失是必然的。作为游戏的科幻文艺失去了乐趣,游戏用以关照自身且得以成立的目的也就随之失去了。中国科幻文艺在影视化改编进程中的矛盾在于,用一种技术性的崇拜覆写了对艺术之美的重视。艺术美并非消失了,只是此间的艺术美远远没有达到一件合格艺术作品的标准,使得呈现效果参差不齐。但事实上,又不得不将其纳入科幻文艺作品的范畴之内。它体现的根本问题在于中国科幻美学的荒芜,没有指向,也无从下手,这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迷失:无所适从却又没有系统的重新建立,呈现出一种意义的消弭。如果借用游戏的比喻,那就是游戏内虽然建立有规则,却缺乏目标;游戏可以前往结局,却没有意志所向;游戏可以被观察,却只有机械式乐趣,缺乏观看的情趣。
四、技术性崇拜——科幻影视化改编的原旨
我们将科幻文艺代入广义游戏的视域,根本动因在于游戏同时兼顾了科幻与艺术的双重特点,游离其中,以中间态的趋势保证了语义的连接。然而,中国科幻文艺的美学难题背后究竟由何而起?这是寻找矛盾背后答案的必经之路。而游戏作为科幻文艺可依赖的直接隐喻,跳脱着映射出矛盾的另一种对照:游戏自身功能性与乐趣的冲突。
游戏是一个动态的游玩或审美过程。因此,有两种情况会使游戏丧失效力。其一,游戏者停止了游戏进程,游戏被中断了,功能性不复存在;其二,游戏失去了趣味,其本身的目的也随之失去。如果放在科幻文艺上进行分析,第一种情况就是审美进程由于艺术作品本身的原因被强制中断了,因此美学风格发生断裂,不再连贯;第二种情况便是艺术作品自身的诗意与韵味不够,趣味消失了,游戏自然也就失去游玩与被观看的意义。在这里,趣味是无功利的趣味,而游戏是“有意味”的聚合。克莱夫·贝尔认为美是“有意味的形式”,但这里的“有意味”更加注重形式内容间的关系,同时暗示了科幻文艺系统的处境:它与现实生活的感受会有距离,这是先天的题材范围所决定的;同时,与科技问题的结合也预示了其欣赏旨趣独立于其他文艺形式。但这就代表着科幻文艺的独有乐趣能够凌驾于传统审美感受之上吗?事实并非如此。
在《三体》的电视剧乃至动画剧集中,其彰显科幻文艺独特旨趣的表达最为明显。科幻文艺的旨趣之一便是对新科技、新世界乃至新概念的想象与渴望。影视剧因其传播媒介具有视觉化与听觉化的优势,自然会以具象化的艺术形象去表现这种对于虚构世界及科技的想象。例如《三体》电视剧中对于“古筝行动”这一事件的描绘,利用视觉特效营造出令人瞠目结舌的效果,将纳米技术巨大的摧毁作用展现了出来。然而,过于渲染或强调此种技术性的想象,会不自觉地将本应具有的诗意挤兑。此外,影视工业及商业的规律会进一步将这种空间压缩。这与构建关于科技的视觉奇观同理,它吸引了受众,却没有吸引游戏的观看者。换言之,只有游戏观看者,才是实际进入艺术欣赏领域的艺术接受者。而这种轻视了艺术欣赏者的创作表现,究其根本是一种变相的技术崇拜。
技术性崇拜并非一种显性的弊病,却导致了科幻文艺的创作缺乏对美的追求,反而将注意力放置在技术想象当中,顾此失彼。这种倾向可以追溯到两点:其一是科幻文艺美学的主题特征,一旦谈及科幻,就不可避免地涉及技术概念;其二是一种中国传统的实用主义。这都是中国科幻文艺的原生问题,前者来源于科幻文艺本身,后者则来自中国式的发展语境。这实际上是中国科幻文艺背后的社会性隐喻。
杨庆堃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中总结了一种弥散型传统,在这种呈现主流趋势的社会结构传统中,是与“偶像”做出交易,从而获得直接利益性的回报——这种诉求直接的功利性传统被镌刻在文化基因中不断前行。①
从此,技术成为新的“偶像”,新的交易对象。而从中提炼出的这种功利性传统无疑也直接影响了中国当代科幻文艺的发展。因此,技术崇拜顺遂着深厚的历史社会原因,沿袭了这种一如既往的功利性传统,为中国科幻文艺打上了烙印。即便如此,在中国美学史上仍然有着诸多针对美韵与诗意的论述,无论是北禅宗对于本我世界的探索,还是东晋玄学美学的诸多意见,均建立在超脱世间功利的基础之上。这些美学观念往往来源于宗教或文化体系,在世界美学史上都是独树一帜的。因此,中国科幻文艺的美学矛盾没有理由用技术崇拜将诗意和美韵挤兑出去。从中国美学史的多种意义生发,我们依然能够找到提倡无功利的痕迹。换而言之,中国科幻文艺美学理应考虑到更综合的美学表现——对于诗意和美韵的探寻是一种源自中国本土文化的传统,甚至是本能。
为何《流浪地球2》《三体》的影视化改编仍然看不见此种精神指向?以致于在《三体》动漫剧集中,出现用大量过往动画素材等现象,这实质上就映射出科幻文艺对于技术崇拜的单一表达,以及面对“游戏”观看者的某种有意忽视,其在不自知之中,联合着艺术工业资本将诗意与美韵拒之门外。这种态度上对于美学的漠视,不仅代表了现有作品的问题,也拉低了中国科幻文艺的发展上限。
五、游戏的乐趣,科幻美学的指向
综上所述,如何明晰中国当代科幻文艺的美学矛盾?我们借由游戏(艺术)理论所创造窗口进行详细论述:科幻文艺的系统性可以被表达为游戏,游戏的游玩与观看即为文艺作品的审美鉴赏进程。无论是游戏的游玩观赏,抑或艺术的审美鉴赏,实质上都是具备无功利趋向的。然而,来源于客观历史原因的技术崇拜明确标榜着一种实用的功利工具性。这两者间的冲突无疑在科幻文艺的内部产生了矛盾,游戏的过程被中断,审美的意义随之逝去,进而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科幻文艺应该如何具有诗意,科幻文艺的创作指向应往何处?
在中国科幻文艺的美学系统中,技术由于变成了功利性的化身,一个新兴且有用的“偶像”,那么自然便要寻求消解矛盾的方法,以求得其美学上的自由,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指向。这是中国当代科幻文艺必须跨越的一步,以期通过游戏理论的辨析获得科幻文艺在美学上的救赎。
这一步必须从游戏的娱乐性质及技术祛魅两点入手。首先,科技的功利工具性是针对现实世界的,是严肃的。而与严肃构成反义的正是轻松的娱乐。运用游戏理论对科幻文艺进行分析的一大优势是,游戏本身的娱乐性质将技术功利主义的严肃解构了。我们将通过游戏的娱乐舒缓自身,与现实保持距离,从而不再沉迷于对技术“偶像”的崇拜。需要明晰在科幻文艺作品中崇尚技术“偶像”无法获得直接的利好交换,甚至使得文艺本身的美育功能遭到破坏。
其次,“技术的祛魅”是需要从根本上摆脱技术崇拜,即通过游戏审美与技术哲学的双重作用,引发诗意的纾解与对崇拜的警醒。因此,具备无功利趋向的玩乐,是达成这一目非常直接且有效的手段。游戏在这些过程中全程在场,其存在成为必然。同时,可供玩乐(技术操作)且观看(审美)的“游戏”成了调解技术与艺术之间矛盾的中介。从这一点来说,游戏所能提供的,不仅仅是连接两者,更是培养了一种意识,即把游玩观看(审美)的过程养成一种乐趣。为了重视这一过程,必须从游戏的指向中厘清。一旦游玩中断,观看的乐趣随之消失,其本身作为文艺类型的必要性也就随之不复存在。培养游玩乐趣的过程实际上是培养审美趣味的过程。需要明晰的是,游玩与审美始终同在。
“游戏”的自我独立性预示了科幻文艺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使其脱离于其他文艺类型。也就是说,科幻文艺的研究需要区别于纯粹的艺术无功利性,在两者间寻找一种精神指向的平衡。这种精神指向并非社会文化意义上的,而是必须在表现意义上的。同时,也需要在克莱夫·贝尔的有关艺术自身独立完整性的“意味”上进一步深入探讨。游戏作为“有意味”的“聚合”,理应强调这种美学上的整体性——它强调的是审美的整体,而非文学性,也非由文学性所引发的人文关怀。因此,中国当代科幻文艺的一个显著误区,是将人文精神或人文理想混淆成美的主体,由此疏忽了艺术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也忽略了“游戏”游玩与观赏应具备的旨趣。
游戏的重要性不只是连接,更在于其本身不断变换的身份特质。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救赎”,正是因为它的流动性具备模糊技术与艺术间边界的能力。对于技术的工具性而言,它是弱功利的,而面对艺术时,它又成为弱审美的象征。无论是艺术创作者还是艺术接受者,均可在游戏的美学指向和乐趣中获得片刻的喘息与慰藉。游戏的玩乐态度所带来的无功利区别于纯艺术或纯美学的无功利,为科幻文艺寻找到一个为一定功能性寻求合理性的缓冲地带。它既允许技术探讨所带来的功能主义,也强调与无功利间的非直接联系,因为游戏的目的从来不直接对应现实意义,却有着暗中联系——它对于矛盾双方都保持着距离。从理论的角度而言,游戏已经具备了切实的美学基础。游戏观看者相对于艺术接受的审美主体而言,更适应科幻文艺作品的语境,也就更容易超脱于科幻美学的内在矛盾。
六、从游戏出发:科幻文艺影视改编的可能路径
单从影视化改编的中国科幻文艺作品来看,以游戏理论作为指导,趋向一种文艺创作的理想状态是具备可行性的。
我们将科幻文艺的创作过程视作游戏的制作过程,其规则的制定、游戏目的指向,以及最终通往无目的的合目的性,都是为了将技术的探讨与美学的意蕴视作一个整体。游戏需要游玩与观看来证明自身存在,因此科幻文艺需要在创作和审美的全过程综合考量。游戏观看者是一个不可绕过的审美主体,它同时连接着技术思考与美感两端。技术思考代表着需要从技术的功利性跳脱出来,不能局限于技术所带来的工具利好及文化社会性的反思。美感又是对艺术作品及游戏旨趣的直接要求。
如何做到兼顾技术思考与美感呢?技术思考毫无疑问需要依照文本原型中对于技术概念的设想及反思,这种反思依据于虚构的社会架构,是对人类命运的关心。此外,应该考虑到这种虚构的情境下,人们如何看待美的本体。美感则是依赖于创作者对于文本原著及影视本体的理解,具体表现为合理杜撰人物的行动,深思熟虑地编排合乎作品内在逻辑的戏剧性表达。虚构世界中的观点、思潮以何种方式进一步构建了影视化中的具象视觉表现,即建筑、人物造型等。这些在艺术形式上的具体操作无异于构建一个“游戏”的世界,即构建一套规则与目的。这些构建最终仍是为观众服务,为审美的主体服务,为游戏的游玩者及观看者服务。
以1982年上映的经典科幻电影《银翼杀手》为例,其改编自菲利普·K·迪克(Philip K. Dick)的原著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电影制作者深入考察了原著文本中对于近未来洛杉矶的情景描述,根据其中的设定详细构想出了一套被后世称之为“赛博朋克”的科幻美学风格。这一美学风格涉及具体的技术哲学反思,科技发展下人类生存处境等问题,呈现出一种颓废的末世观感。无论如何,这种通过模型建构、美术设计、人文考量的综合美学风格奠定了一个根本性的本体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其用反派复制人头目关于宇宙星河的自白当作结尾,意味深长。总结来说,《银翼杀手》是在社会性、文化性、技术性反思之上统筹的美学创造,它发明了新的游戏体系:无论是虚构世界规则的构建,游戏者(主人翁)的结局设定,还是游戏那无功利性的终极审美目的,配合着对于未来社会生态的臆想,都为游戏的观看提供了足够的意趣。通过一个整体化的美学考量,将统一和谐的后现代风格呈现在观众面前,以此游离在电影商业、工业和人文理想的终极追求之间,达到了一定的审美高度。
为此,中国科幻文艺作品在创作时必须将其当作一部整体的游戏进行设计,这种设计不仅仅是技术性的,也是美学上的。举例来说,《流浪地球2》就是一次弱审美的电影工业进步,科技场景的搭建自然非常吸睛,但就其中的生活化场景来说,充斥着一股都市电视剧的质感,无法参与支撑宏大的主题。因此,在影视改编的剧本设计阶段,一旦原著的细节描述较为孱弱,则必须通过银幕编剧及艺术设计丰富薄弱处,构建完整的艺术风格,以达成美学上的追求。电影是极为综合的艺术形式,它结合了建筑、美术、音乐、戏剧等多种艺术门类。具象化的表达需要视觉设计的支撑,例如场景环境、服化道、剧本、故事主旨、设定背景、人物性格互相贴合,从而完成具体且完整的美学风格建构。
这与一场完整的游戏建构如出一辙,且游戏还需要对观看者的感受进行关照,从而完成艺术传播与艺术接受间的互动。将创作的过程视作一场游戏的“嬉戏”,减弱功利主义对于影视改编的影响。相关的艺术创作者需要树立这一前置意识,才能进入科幻文艺创作的佳境。当游戏于科幻视域中在场时,技术崇拜便不再是唯一可表达的要素。因此,以游戏理论代入,会将科幻文艺作品的艺术寿命进一步延长,扩展其意义边界,形成艺术思潮,从而解决美学追求上的矛盾,化解无处下手的精神迷惑。
七、结语
中国科幻文艺的影视化改编是当代中国科幻文艺的典型现象,典型现象的背后自然有着复杂的成因。本文试图聚焦并辨析其隐含的内在美学矛盾。这一矛盾表面上是科幻文艺的实际性表达与形式内容的美学要求无法相匹配,而究其根本则是艺术无功利与技术功利性之间的直接冲突。科幻文艺本身具备双重属性,它既需要技术的直接描绘,又需要作为艺术作品为观者提供审美支持。所以,技术性功利与艺术无功利间的调和便成为当代中国科幻文艺的难题。
通过美学、哲学及文化学对于游戏本体的圈定,从而认定游戏可以成为调和这两者间问题的桥梁。之所以将游戏作为方法,是因为游戏既作为一种艺术的近似物,又与技术保持着距离。一方面,游戏就此构成了中介,增大了可解释的空间,扩容了科幻文艺的意义。另一方面,游戏包含着更为完整的精神指向与审美过程,它能够帮助科幻文艺创作者确立艺术风格,明晰方向。因此,游戏的观看者变成比审美接受者或审美鉴赏者更为全面的概念。利用游戏观看者所蕴含的审美诉求,可以精准定位中国科幻文艺的内在矛盾,也能够实验性地指导科幻文艺美学的旗帜所向。
在以科幻文学影视化改编的详细操作中,游戏成了具体艺术表达的精神性指导,具备两个方面:其一,是在艺术表达上的统一性,需要艺术创作的各个部分达成共识,更为详细且用心地运用各艺术门类的知识,创造出一个风格统一的艺术世界。这样的艺术世界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游戏”,满足游戏观看者的需求。其二,是在统一的艺术世界外,还需要具备游戏的乐趣,产生一个充斥美感与意韵的世界。这就需要在文本层面产生诗意,并利用高超的表达手段将其转译到视听语言当中。这样的方法指引,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美学指向上的燃眉之急,明确科幻文艺出产的最终目的。
作者:
杜钊远,广西艺术学院人文学院艺术理论与批评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艺术理论与批评
焦仕刚,广西艺术学院影视传媒学院,副教授,电影学博士,研究方向:影视史论与影视文献学
(责任编辑:齐月)
Abstract: Since the end of 2022, the production of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literature and art has shown some momentum with the release of film and television adaptations such as “Wandering Earth 2” and “Three-Body” However,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utilitarian nature of technology behind science fiction themes and the non utilitarian trend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is prominent. Digital games, as a cultural phenomenon of humanity since ancient times, align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cience fiction and literature while maintaining independence and autonomy. They can simultaneously enter the context of technological philosophy and artistic aesthetics, becoming an effective intermediary to construct systems for translating information. Therefore, the spiritual direction behind science fiction literature and art requires the theoretical intervention and analysis of game phenomena to find new methods, in order to solve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revealed by the adapt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aesthetics from film and television.
Key Words: Science Fiction, Art, Digital Game Aesthe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