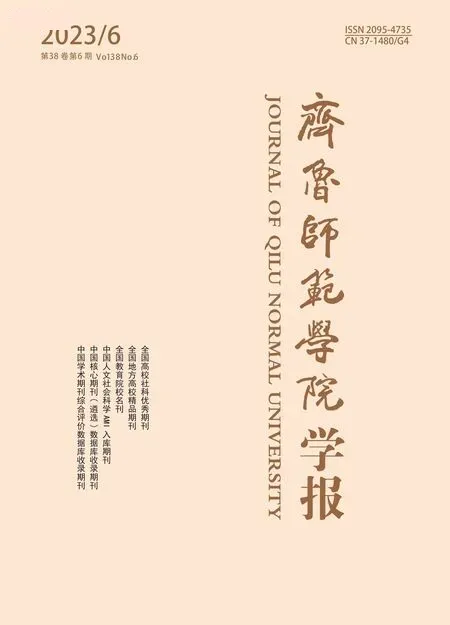新媒介语境下一流课程教学的新路径与新方法
——以文学概论课程为例
2023-04-25杜智芳
杜智芳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新世纪以来,以互联网、计算机、智能手机、影视动漫等为载体的“新媒介”冲击了现代生活的诸多方面,也引发了生活、工作、学习上的一系列变革。在新媒介、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浪潮下,自2018年起,教育部围绕“一流本科、一流专业、一流人才培养”,持续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全面开展一流本科课程建设,树立课程建设新理念,推进课程改革创新”[1]45。就文学概论而言(又称文学理论),它属于文艺学的分支之一,是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该课程对于夯实专业基础,培养辩证思维和人文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新媒介推动了文学概论教学方式与手段的革新,如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在线课程教学、网络直播教学、视频会议教学,等等。事实上,新媒介带来的不只是“表层景象”的改变,还包括与其同步变化的“结构框架”,即教育教学的“整个肌体”。换言之,新媒介需要教学理念、教材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的全方位变革,以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内涵式、高质量发展。
然而,已往文学概论教学存在诸多问题。教学理念较为陈旧、落后,本质主义、教条主义突出;教材体系偏于抽象、僵化,板块化、界限化分明;教学内容侧重理论说教,同现实语境、接受主体脱节;教学方式热衷新技术、新花样,但“新瓶装旧酒”,难以实现基础文艺理论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总之,文学概论教学已跟不上时代发展,需探索与之相应的新路径、新方法——建立融合马列文论、基础理论、前沿问题的“文艺学大理论”课程体系,综合文本细读、多媒体、对话交流的教学方式与手段,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激活基础文艺理论“旧话语”,展开基础理论与前沿问题的对话,让理论贴近现实、指导文艺发展。文学概论教学要充分发挥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中作为“火车头”的“牵引力”作用,积极响应“新文科”建设需求,培养具有爱国情怀、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文科人才。
一、立足文本细读,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新媒介需要一种交叉式、整合式思维,电子时代的人应是感知整合、整体思维、整体把握世界的人[2]4。文学概论教学在新媒介语境中应变、求变,迫切需要建构融合马列文论、基础理论、前沿问题的“文艺学大理论”课程体系,在综合思维和宏观研究中,“创立大文艺学、宏观文艺学和战略文艺学的构想”[3]11。在此过程中,如何处理马列文论与文学概论的关系?如何避免“知识填鸭”和“强行灌输”的不利倾向?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4]377-378。因此,马列文论在文学概论中不能作为纯粹的“知识拼图”,而是作为科学的指导思想与方法理论,尤其要立足“文本细读”,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被实践检验和证明了的指导文艺工作的正确理论和经验总结[5]1。对文艺研究而言,“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文艺理论的一些问题就很难理解到位”[6]19。随着新媒介语境的变化,对图像时代、景观社会、虚拟现实、网络文艺、人工智能美学等新文艺话语的分析,依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与判断,也必须坚持“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框架,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
(二)立足“文本细读”与把握“三组关系”
当文学概论教学涉及马列文论时,应思考如何让马克思主义理论入脑、入心,让学生真懂、真信、真用。出路在于两点:一方面,立足“文本细读”,即深入领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经典作品中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述,理解并掌握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具体产生过程。另一方面,把握“三组关系”,是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文学概论、马克思主义文艺范畴与经典文本、马克思主义批评实践与新媒介语境之间的关系。
1.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文学概论
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是文学概论的指导思想,但要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的“零散论述”进行文艺学知识范畴的转换。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专门的文学和文艺批评著作,其文艺思想散见于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等著述之中,“但是,绝不能由此就断定它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7]5。如何将那些零散的文艺见解,理论化、系统化为关于文学本质、文学创作、文学文本、文学接受、文学发展等各方面的整体知识。
同时,还要尽力避免两种倾向:其一,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零散论述,直接当作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如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8]162,不能直接等同于马克思提出了“文艺活动论”。其二,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生硬地嵌套进文学概论的知识体系。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发“意识和存在”的关系时,曾将意识形态比作照相机中的“倒立成像”和“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8]525,但不能据此简单地认为,他们就是在专门探讨“艺术反映论”问题。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原典中的一些并非文艺观的阐述,需要经过必要的学理演绎和引申,使之转化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并贯彻到文学理论的阐释中,让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更具严密的学理逻辑[9]54。
2.马克思主义文艺范畴与经典文本
马克思主义文艺范畴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但需要立足后者的“细读”,具体完整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范畴的产生、发展过程。就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创立者和奠基者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吸收借鉴了自古希腊至19 世纪的人类优秀文明和文化成果,创立了以现实主义为核心,以真实性、倾向性、典型性为理论支柱,涵盖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文艺的现实主义、文艺的生产和消费、文艺的继承和发展、文艺批评的方式与标准、文艺的内容与形式等一系列有关文艺的思想、原则和方法。文学概论在讲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思想和范畴时,需要返回“历史语境”,对经典作品展开深入扎实的细读。
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范畴和经典命题的把握,离不开细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作品。如《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它们主要涉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①、文艺的社会意识形式属性、文艺的社会作用和发展规律。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悲剧创作、现实主义、艺术倾向性、艺术典型、文艺批评的原则和标准等基本文艺观念的阐发,主要体现在他们写给斐迪南·拉萨尔、敏·考茨基、玛格丽特·哈克奈斯等人的一系列书信中[7]12-13。
3.马克思主义批评实践与新媒介语境
文学概论教学讲授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时,不能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要切入社会现实与文艺现状,阐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媒介文艺。虽然新媒介文艺是一种时代潮流、全球化现象,但是必须以“中国本土”的文艺经验和实践为对象,凸显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精神,让马克思主义批评真正做到“接地气”“显活力”。教师要教会学生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念,剖析网络小说、影视动漫、电子游戏、科幻文学等文艺现象,让学生真切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剖析现实的可行性、科学性、深刻性。
以河南卫视“唐宫夜宴”系列节目为例,教师可从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的生产与消费”展开分析。该节目关注“艺术生产力”要素,借助数字技术(5G+AR),实现虚拟空间的具象化生产,既为受众带来身临其境的视觉享受,也赋予了更多的想象力。在技术赋能下,传统以符合年轻人审美趣味的形式呈现;年轻人以身穿汉服、旅游打卡、创作表情包等方式参与其中,形成了良性的文化生产与消费的产业链条[10]32-33。“唐宫夜宴”系列节目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也是新媒介文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展现中国形象的典范之作。
二、善用多媒体,激活基础理论“旧话语”
(一)新媒介及其对文学艺术的影响
建设适应新时代发展的一流本科课程,急需深化课堂教学革命,改革传统的“教与学”形态,全面推动现代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的深度融合。新时代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关键任务之一,就是“主动适应和引领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11]53。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是新媒介语境下文学概论建构“文艺学大理论”课程体系的指导思想和科学观念,那么,基础文艺理论则是其整体框架的“主体部分”。文学概论教学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介技术手段,激活基础文论话语的“丰富潜能”与“内在张力”,使之适应当下的社会现实与文艺现状,实现基础理论“旧话语”的创造性利用和创新性发展。
新媒介是数字化、互动式的复合媒体,具有超时空、整合性、移动性、参与性、沉浸感等特点。金惠敏在《媒介的后果——文学终结点上的批判理论》一书中,曾将新媒介的后果概括为“趋零距离、图像增值、球域互动的全球化”,并阐发了新媒介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他从两个方面重新理解了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对于文学的意义:其一,新媒介通过改变文学赖以生存的外部条件而间接地改变文学,其二,新媒介直接地重组了文学的诸种审美要素[12]32。的确,新媒介改变了文学艺术的存在环境、关系网络,也必然带来文艺面貌和存在方式的转变。欧阳友权指出,新媒介的“数字化语境”给文艺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变化,即语言艺术日渐被音像艺术所挤占,文学存在方式从书面转向电脑网络,艺术从单媒介向多媒介延伸[13]79-80。
(二)多媒体与基础理论的现代转化
不可否认,新媒介对文学及其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文学概论教学要在危机之下应变、求变,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综合运用多媒体技术,激活文学理论已有知识体系所蕴藏的潜能和张力,实现基础理论“旧话语”向现实语境的迁移、利用、发展、创造。事实上,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传统文论话语在理论形态、思想内容、讲授方式、批评实践上都较为落后于时代,也普遍脱离了学生生活和学习实际。如典型、意境、意象、象征、模仿、风格、流派、现实主义等,诸多理论范畴都有其诞生的历史语境,且已形成相对固定的知识体系。因此,文学概论基于历史和实践所形成的概念、原理、方法、标准等,需要借助多媒体技术,结合社会现实和文艺现状进行重新阐发。然而,新方法的本质不是“新瓶装旧酒”,而是“老树发新枝”。换言之,中西文论的传统话语都面临一个“现代转化”的问题。那么,如何让旧的文论话语重新活起来,这需要从教学手段和教学内容两个方面尝试突破。
1.融合多种教学手段
文学概论要充分利用各种新媒介,使其相互融合、彼此互渗,让学生在丰富多彩的课堂上乐知、好知。从内在构成讲,“‘新媒介’既是单数,也是复数……新媒介指的既是一个本质不同的新型媒介,也是许多媒介,甚至是每一种媒介”[14]138。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指出,在思考多媒体时,“它必须能从一种媒介流动到另一种媒介;它必须能以不同的方式述说同一件事情;它必须能触动各种不同的人类感官经验”[15]67。文学概论教学的新方法在于教师熟练掌握新媒体技术,巧用善用文本、图像、视频、音乐等多媒体手段,“把沉默单向的课堂变成碰撞思想、启迪智慧的互动场所”[16]8。
以中国古典美学范畴“意境”为例,除了借助语言、文字对其进行概念史梳理和构成分析之外,还可展示体现意境之美的图片、影像、视频等,让学生对意境的“玄妙之思”得以具象化、视觉化,并在各种媒介的相融相交之下,体会意境美学的“可见”与“不可见”。此外,还可从当下生活和新媒介文艺现象出发,寻找激活基础理论“旧话语”的突破口。以叙事理论为例,教师可选取一些社会关注度高、反响强烈的网络小说、影视作品进行分析。如近年来热播的影视作品《长月烬明》《漫长的季节》《流浪地球》《三体》等,皆可从叙事结构展开剖析,而神魔叙事、悬疑叙事、科幻叙事都是激活当下叙事研究的理论入口。
2.拓展创新教学内容
文学概论要跳出知识传授的视野局限,思考新媒介对文艺学知识体系和理论话语的影响。媒介因素打破了传统文学研究的“四要素”(世界、作家、作品、读者)范式,将其重塑为包含“媒介”的“五要素”范式。美国学者阿瑟·阿萨·伯杰较早从大众传播和叙事的角度提出了“五要素”(或“五焦点”)的理论范式。他指出,大众传媒存在“五个焦点”的基本领域:艺术作品(文本)、艺术家(创作者)、观众、美国(社会)、媒介;而且,人们不能忽视其中的任何一个焦点,必须根据它们的相互关系进行考量,尤其需要关注“媒介”对其他要素带来的深刻影响[17]17。
伯杰的“五焦点”模式对于建构新媒介时代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李玉臣认为,构成艺术整体活动的基本因素有五个:世界、作者、媒介、作品、读者,而“艺术媒介”是艺术过程中的“最为根本的要素”,若将其除去,其他四个要素就无法存在于艺术系统之中[18]12。单小曦结合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模型,将李玉臣归纳的“艺术五要素”结构进行调整,提出了电子传媒时代文学理论的“五要素”范式:作品、世界、作家、传媒、读者,而“作品是其中的本质性要素”,正是它构成了文学活动的关键环节[19]166。由此可见,“新的媒介塑造了新的文学”[20]34,也塑造新的文学理论,而“只有开放文学理论才能发展文学理论”[21]63。
在新媒介的影响下,传统文艺学话语急需拓展理论边界,深入考察“媒介与文学”的相互影响与作用,开辟文学载体转向新媒介后的新格局和新样态。已有部分文学理论教材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如王一川的《文学理论》、南帆的《文学理论:新读本》,两者在结构安排上分别增加了“文学媒介”“传播媒介”的章节;“马工程”的教材《文学理论》在第十章“文学活动的当代发展”中补充了一节“现代传媒与文学发展”,增加了图像文化、网络文学的相关内容。
当媒介与文学交融互渗,文学的存在形态、性质特点、研究方法都要放置到“媒介文艺学”②的整体框架之中,而“文学与媒介”“文学与图像”“文学与传播”也成为较为热门的新文艺话语。以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的插图本为例③,可分别从文学图像、文学传播两个角度入手分析。首先,从文学与图像出发,文学语象和文学插图的融合,使得不同媒介之间的“统觉”在人的心理层面实现共享,而“‘统觉共享’就是语言艺术和图像艺术相互交汇的‘公共空间’”[22]25,正是它们让《野草》的“言说”与“图说”相互促动、彼此生发,由此打开了隐藏其中的深广生活和丰厚意蕴。其次,从文学与传播出发,大学生吴一凡对《野草》的创意改编,以Rap 的形式将其中16 篇作品改编成一首节奏感很强的说唱歌曲,在B 站上的播放量超过1000 万次,让经典又晦涩难懂的鲁迅文本拥有了贴近时代的“新形式”,也由此获得了“新生命”。
三、对话前沿问题,从文艺学走向“新文科”
(一)展开基础理论与前沿问题的对话
在新媒介的促动下,文学概论的跨学科性得以凸显,而如何运用文艺学方法解决现实问题,充分发挥一流本科课程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作用,这也是文学概论教学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2019 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着重强调了提升课程的高阶性、突出创新性,倡导“教学内容体现前沿性与时代性,及时将学术研究、科技发展前沿成果引入课程”,运用先进、互动的教学方法,“积极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式与个性化学习”[1]45-46。
因此,文学概论教学在筑牢专业基础的前提下,迫切需要与“前沿问题”展开对话,让学生深切感受到基础理论的学以致用,让文艺学在多学科的交叉中不断拓展边界,实现从文艺学向“新文科”的跨越式发展。在文学概论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安排上,前沿问题可作为实践环节展开。“前沿问题”主要指关于国内外文艺理论的最新发展和成果,涵盖文艺学学科中较为领先、前卫、突出的理论、美学、批评等问题。
(二)突出培养学生的“两种能力”
在文学概论教学中讲授一些文艺学前沿问题,可以帮助学生获得国际性、前瞻性的学术视野,提高运用理论知识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关于前沿问题的筛选,可选择贴合生活现实与学生实际的文艺学热点,如视觉文化、消费文化、粉丝文化、二次元美学、生态美学、人工智能美学、空间批评、生态批评、科幻批评,等等。简单说来,文学概论教学中的文艺学前沿问题讲授,应突出学生“两种能力”的培养:实践能力与对话能力。
1.培养实践能力
所谓培养实践能力,是指培养学生理论联系现实、分析现实、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8]500文学概论所讲授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可以帮助学生在关注当下社会的文艺现象时,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笔者的经验为例④,教师要注重选取人们普遍关注的文学艺术和文化问题,将学生感兴趣、接触多的文艺话题作为分析对象,揭示其背后的思想观念和学理逻辑。学生也会依据所学知识,挑选感兴趣的话题进行研究。如选秀节目与消费文化、偶像崇拜与粉丝文化、躺平现象与青年亚文化、电子游戏与二次元美学、耽美网文与女性主义、同人小说与叙事结构,等等。
2.培养对话能力
所谓培养对话能力,是指培养学生在基础理论与前沿问题、个人与团队成员之间的交流对话能力。因为,无论在“理论与理论”还是“人与人”之间对话,两者都能在沟通交流中拓展认知、更新观念,最终形成一种“视界融合”。英国学者戴维·伯姆认为,“对话仿佛是一种流淌于人们之间的意义溪流,它使所有对话者都能够参与和分享这一意义之溪,并因此能够在群体中萌生新的理解和共识”[23]6。当学生选定所研究的前沿问题后,教师要启发学生开展基础理论与前沿问题的对话。
其实,“基础理论与前沿问题”并非彼此分离,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两者是“源与流”“根与枝”的关系。如对视觉文化、消费文化、粉丝文化的学习,需要掌握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哲学美学,以及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教师可引导学生从基础理论中探寻思想源流与学理依据,做好概念史、问题史的梳理。同时,教师要遵循“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原则,实施小班化、翻转课堂式的智慧教学,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小组讨论、分工协作、课堂汇报的形式开展教学,提升学生之间的交流对话与团队合作能力。
(三)从文艺学向“新文科”的跨越
整体看来,新媒介语境下文学概论教学注重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与信息技术,突出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共生,将新知识、新理论加载到既有学科体系和知识结构中,让文艺学学科“升级迭代”,适应新时代的发展。应该说,这些变革发展之路,与“新文科”建设的理念不谋而合。我国的新文科建设发端于2018 年,正式启动于2019 年。新文科的实质在于文科教育的创新发展,其任务和使命是“培养知中国、爱中国、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文科人才;培育优秀的新时代社会科学家;构建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学派;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24]8。
新文科建设的目标要求,即建成以精品课程为核心、以创新方法为突破口、以评价体系为保证的与时俱进的学科体系和课程体系[25]173。因此,探索新媒介语境下文学概论教学的新路径与新方法,符合我国“新文科”的建设需求,有利于加快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尤其是对于建构中国特色的文艺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也有学者指出:“‘新文科’建设的要义在于引领学科方向,回应社会关切,坚持问题导向,打破学科壁垒,以解决新时代提出的新问题为指归,重点工作则在于新专业或新方向、新模式、新课程、新理论等方面的探索与实践。”[26]7据此讲来,新媒介语境下文学概论着力建构的“文艺学大理论”课程体系与“新文科”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也恰好证明了两者之间的“学理耦合”。首先,在内涵特色上,它们都重视多科学、跨学科的交叉、交流、交融,倡导各学科之间的协同共创,打造“学科共同体”与“学科集成体”。其次,在思维方式上,两者都强调复杂性、关联性、整体性的思维,因为任何学科的创新都以既有知识的整体性、体系性为基础,任何学科“都不是各个学者学术研究的简单集合,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体系”[27]22。再次,在培养方式上,它们都是对原有培养模式、课程体系与内容的升级改造,尤其突出“人文与科技”的融合。
当然,新文科是一艘融合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关联学科的“三元结构”[25]168式的“学科航母”,其内涵范围远远大于文艺学学科。但是,从新文科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实现途径看,文艺学可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走向新文科的“尖刀连”和“排头兵”。或者说,新媒介语境下对文学概论教学新路径与新方法的探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从文艺学走向“新文科”的一次尝试性跨越。
四、结语
总之,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已经步入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在教育部“以本为本”“四个回归”的原则指引下,一流本科教育的关键在于一流课程。新媒介语境下对文学概论教学的新探索,是高等教育应对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建设“新文科”的有益尝试。如何利用文学概论教学的新路径与新方法,有效实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新文科”重塑,这也是今后的文学概论教学需要不断深入研究的问题。
注:
①恩格斯晚年有一系列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主要有:《致保尔·恩斯特》(1890 年6 月5 日)、《致康拉德·施密特》(1890 年8 月5 日、10 月27 日)、《致约瑟夫·布洛赫》(1890 年9 月21—22 日)、《致弗兰茨·梅林》(1893 年7 月14 日)、《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 年1 月25 日)等。
②关于“媒介文艺学”或“媒介诗学”的研究专著,可参看欧阳友权的《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2005)、张邦卫的《媒介诗学:传媒视野下的文学与文学理论》(2006)、单小曦的《媒介与文学:媒介文艺学引论》(2015)等。
③流传较广的《野草》插图本,可参看鲁迅:《野草:插图本》,裘沙、王伟君、裘大力插图,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年。
④2020 年11 月,河南大学的“文学概论”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下一流课程)。在负责人张清民的带领下,课程团队在文艺学前沿问题、马列文论、文艺理论经典选读方面积极开展教学研究与实践,并以选修课的形式拓展文学概论教学,形成了“文学概论+”的课程集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