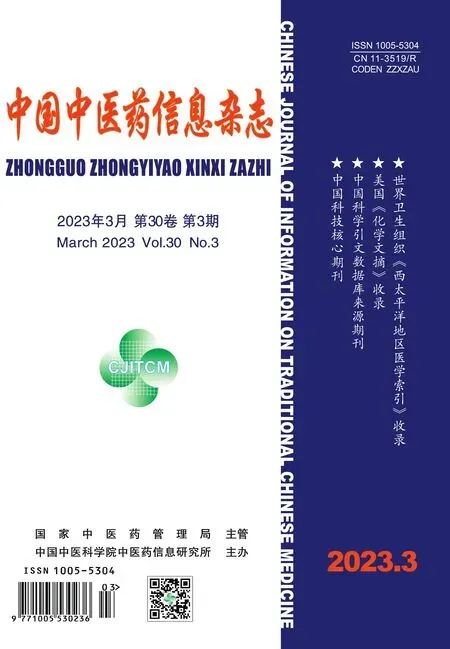基于“内风”理论辨治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
2023-04-06李思成史扬宿家铭柳红芳
李思成 ,史扬 ,宿家铭 ,柳红芳
1.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北京 100029; 2.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北京 100700
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Graves disease,GD)属器官特异性自身免疫病之一,是因甲状腺激素产生过多,导致神经、循环、消化等系统兴奋性增高和代谢亢进为主要表现的一组临床综合征。若不及时治疗可引起甲状腺危象甚至死亡。目前现代医学一般采用抗甲状腺药物、碘131、手术治疗等,使用相关药物常伴有不良反应。根据一项系统评价及Meta分析显示,应用抗甲状腺药物治疗后的复发率达52.7%[1],而碘131和手术治疗均需终身维持使用甲状腺素。GD属中医学“瘿病”范畴,是由情志内伤、饮食及水土失宜等,致气滞、痰凝、血瘀壅结颈前,发而成瘿。其证型主要为肝郁化火、气阴两虚、阴虚阳亢[2]。笔者临证发现,GD表现的眼突、心悸、多汗、手足震颤等,以及发病特点、病机、治法,与“风气内动”相关,因此基于内风理论可补充概括GD的临床特点与表现。兹结合临床经验与相关文献,就内风与火、热、痰等不同病理产物夹杂的复合病机进行阐释,为GD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1 理论溯源
内风是指风起于内,“内”是体内,“风”是病态,其与外感风邪相对而称,特指内伤杂病具有震颤、麻木、抽搐等“风的特象”的疾病病机[3]。风本为自然界之气候,《素问·金匮真言论篇》有“天有八风”,因其“触五脏”故“邪气发病”。又《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风气藏于皮肤之间”,“在脏为肝,其志为怒”,“风气通于肝”,概括了内风与肝的关系甚为密切。《素问·至真要大论篇》“诸暴强直,皆属于风;诸风掉眩,皆属于肝”阐述震颤、眩晕、动摇等与风邪为病同类。随着对疾病认识逐渐深入,后世医家发现一些内伤杂病表现特点与“外感风邪”相似,从而提出“其有不由外感而亦为风者”(《景岳全书》),即“内风”理论。
金元时期,医家们更全面认识到“内风”是人体内部阴阳、气血等不协调产生并引起疾病。刘完素首先提出“热极生风”,所谓“风本生于热,以热为本”(《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因烦劳五志过极,卒而动风,治疗重视“先服祛风涤热之剂,辛凉之药,治内外邪”。李东垣认为元气不足是“内风”引发的关键。朱丹溪则立论“痰热生风”,认为东南气温多湿,由湿生痰,痰生热,热生风,故“风主乎湿”(《医学三字经·中风第二》)。至清代叶天士在前人基础上,阐发“内风”皆“乃身中阳气之变动”,“肝为风木之脏,倘精液有亏,肝阴不足,血燥生热,热则风阳上升”(《临证指南医案》),进一步说明肝精血不足,阴虚阳亢而产生内风,治当滋液熄风、濡养营络、补阴潜阳。
现代医家对“内风”理论有了更丰富的完善。如李大鹏[4]认为,“内风”不应简单归纳为身体内阳气亢逆变动生成的病变状态,还应当有气血虚实变化等;吴建林[5]也认为,内风病证的病机形式不仅有一般认为的肝风内动、阴虚生风、热极生风等,还有血瘀生风、气虚生风、痰浊生风,其病性也是寒热错杂,虚实交接。这些观点拓宽了中医内风病机的形成机理。
2 病因病机
《诸病源候论·瘿》有“瘿病者,忧恚思虑……又诸山州县人,饮沙水多者,沙搏于气,结颈下,亦成瘿也”,认为“瘿”的发病与饮食结构、情志不畅相关。《外科正宗·瘿瘤论》“夫人生瘿瘤之症,非阴阳正气结肿,乃五脏瘀血、浊气、痰滞而成”,提出瘿瘤主要病机是气、痰、瘀壅结。现代医学认为,GD与遗传因素、自身免疫、环境影响等有关。相关研究表明,30%GD患者有家族病史[6]。另外,高碘饮食、压力、妊娠等均可诱发本病。目前对碘盐的推广及摄碘知识普及,一定程度减少了食源性甲状腺功能亢进的发生[7-8],因而GD发病因素越来越趋于自身免疫、环境诱发等[9]。
3 发病特点与内风相关性
3.1 起病于春,循经于肝
GD起病时间、部位等都与内风相关。有学者使用圆形分布法分析GD收治的时间规律发现,其发病存在季节分布,以3-5月为高峰[10]。此时恰好为春夏之交,六气中“风”较为亢盛。所谓“春气正,风乃来”,“东风生于春,病在肝,俞在颈项”(《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同气相求,人与天地升发、生长之气相应,故春季为人体脏腑阳气升发最旺之时,若阳动过亢,则化为内风。又《灵枢·经脉》提到“肝足厥阴之脉……上贯膈,布胁肋,循喉咙之后,上入颃颡”,GD发病部位在颈部,与足厥阴肝经循行部位重合。肝本为风脏,肝气亢动生风,循经上袭,发为瘿病。
3.2 素体阴虚,阳亢化风
瘿病多与素体阴虚有关,病变涉及肝、心、肾等脏腑[11]。在中医证候学相关研究中,肝肾阴虚证占甲状腺亢进的证型比例高达44%[12],而心肝阴虚证比例亦较高[13]。《证治汇补·惊悸怔忡》“有阴气内虚,虚火妄动,心悸体瘦,五心烦热”,若阴液不足,阳气亢动而为风,内风反煎灼津液,更致阴虚加重,二者相互影响,循环往复。肝为风木之脏,体阴用阳,而乙癸同源,水不涵木,肝阴不足,肝阳无以为制,则发为内风。又《素问·风论篇》提到心风,“多汗恶风,焦绝善怒吓,赤色”。心为神明之府,若阴虚不能濡养心脉,难以制约阳气,也会产生虚风内动,扰乱心神[14]。GD患者多见口干喜饮、恶热多汗,乃阴虚阳亢化风,风火合邪,津血耗伤,是以燥渴;风火行于体表,迫阴外出,是以汗出。
3.3 情志不遂,气郁化风
《诸病源候论·瘿候》有“瘿者,由忧恚气结所生”,可见瘿病亦与情志不遂有关。其中社会节奏快、生活压力大是其重要诱因[15]。瘿瘤乃本于七情,情之所至,气则随之,或上而下,或结而不散于颈前。《类证治裁》有“风依于木,木郁则化风”,木郁日久,则肝气郁勃生风,风性善动,故瘿者轻症见性情急躁、咽喉不利,中则心悸、消谷善饥,重则筋脉失养、手足震颤。
3.4 饮食不当,痰聚生风
饮食不当是GD潜在因素之一。有报道,GD患者对海产品的消费频次较健康人高[16]。《丹溪心法·瘿气》有“瘿气先须断厚味”。脾胃为后天之本、生化之源,若过食海鲜等生冷咸鲜之品,食气入胃而不能散,脾失健运,水湿停而化痰,痰聚生风,风挟痰阻扰肝经循行,则见眼珠突出不纳、颈部甲状腺肿大等。
3.5 其他
另外,风邪与免疫性疾病密切相关[17]。GD属器官特异性自身免疫病,有特征性自身抗体,并发症繁多,临床表现不一,与中医风邪“善行数变”特性相符。
4 主要临床表现与内风相关性
风者善行而数变。《伊尹汤液经》:“有为风寒湿痹者,有为癥瘕坚结者,有为消渴温疟者,有为结胸心悸者,有为呕吐下利者,有为发黄发狂者,有为诸惊,有为诸痫,有为诸痛,有为诸疮,诸般杂症,万不同之证象,皆由风作。”说明风邪致病,具有多变和多动特点,证候变化繁杂,且可在人体内外各个部位发病。GD证候群复杂,累及多个系统,符合中医“风”的致病表现,因此对GD的认识不能忽视“风”这一要素。
4.1 上肢震颤
GD的典型临床表现为手部震颤。《儒门事亲》有“曲直动摇,风之用也”,风为阳邪,性主动,善走窜,上攻于头面则口眼歪斜,游于四肢则见四肢不收、抽搐软蠕等。《金匮翼》云:“颤振,手足动摇,不能自主,乃肝之病,风之象。”所谓木气鼓动,风淫末疾者是也。《医碥》云:“颤,摇也。振,战动也。亦风火摇撼之象。”GD常见上肢震颤,不能自主,或为肝经郁热化风,或阴液亏虚不能敛养阳气,导致阳亢化风,内风走窜筋脉,摇动四肢。
4.2 眼突不纳
GD患者常伴有不同程度的甲状腺相关性眼病,其临床表现包括眼目胀痛、干涩、夜不能闭,甚者畏光、流泪伴刺痛。现代医学认为,甲状腺眼病与眶后组织的特异性自身抗体有关,其病理基础为眶后淋巴细胞浸润,成纤维细胞分泌大量黏多糖和糖胺聚糖在组织沉积,导致眼外肌和脂肪肿胀损伤引起突眼。中医认为,内风扰动是甲状腺眼突病机之一,且眼睛局部病理改变涉及痰、热、瘀等多种病理产物[18],亦有医家从肝风内动论治甲状腺相关眼病取得一定疗效[19]。《素问·金匮真言论篇》有“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肝风内动,风邪上扰,则眼球震颤,夜不能寐”,《目经大成》认为“愁瞳子瞠瞠不转头,阳邪亢风热又相投”。GD患者寐不能闭眼,犹如“花缸变鱼之目,凸而定凝”,故被称为鱼睛不夜,乃阳邪亢害,风热壅阻之故。内风挟火热上攻于目,风火相煽,痰瘀互结,鼓动眼球外凸。
4.3 心悸失眠
GD对心脏具有一定刺激作用,患者常出现心动过速、心悸等表现,甚者有心房颤动和心力衰竭[20]。《诸病源候论》有“惊悸者,是风乘于心故也”。心为神明之府、藏神,若心阴不足,心失所养,虚风内动,心虚怔忡,则失眠不安;亦或火热实邪扰心,热极生风,神魂易动,可见惊悸不宁、失眠亢奋。且心包与肝同属厥阴,《金匮悬解》言“厥阴之经,以风木而孕君火。风木不舒,奔腾击撞,故气上冲心,心中疼热”,《外台秘要》有“风邪入脏,梦寤惊恐,心悸诸病”。由此可见,GD心悸失眠等与内风扰心相关。
4.4 口渴消食
GD患者常见口渴、多食、多便等类似消渴症状。《伤寒论·辨厥阴病脉证并治》言“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撞心”,《儒门事亲》有“风消者,二阳之病,火伏于内,久而不已,为风所鼓,消渴肠胃,其状口干,虽饮水而不咽,此风热格拒于贲门也”,《医理真传》“消症生于厥阴,风木主气,盖以厥阴下木而上火,风火相煽,故生消渴诸症”。风热内扰,风可销津,热能耗液,中焦动戈,则见消谷善饥;风火上烁肺金,津液不足,欲饮水自救,故见口渴、多饮。
4.5 其他
GD患者也会出现自汗、大便增多、消瘦、甲状腺肿大等症状。因风为阳邪,性开泄,风行于营卫,营卫失司,表气疏泄,而见自汗不止;内风鼓扰大肠,大肠为传导之腑,主传化糟粕,大肠失司,风热内扰而无出泄,故见大便泄泻、频次增多。总之,GD虽然证候复杂多变,但万变不离风、火(热)、痰等病机。
5 风药的运用
风药具有升、散、透、窜、通、动之性,配伍应用可起到宣散透邪、发散郁热、辛散通络、升举清阳、通阳畅气等功效[21]。《素问·至真要大论篇》言:“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以甘缓之,以辛散之。”治疗GD应紧扣“风”在诸多病机中的枢纽位置,认识到内风鼓动盘旋,夹杂火(热)、痰等其他病理因素引起的一系列病症。因此治疗GD当以熄风、潜阳、滋液等为主。
5.1 熄风清热
适用风热实邪亢盛病机。根据风热火邪涉及脏腑不同,选用不同清肝、清心药物,如夏枯草、柴胡、栀子、蒺藜等。其中夏枯草味苦、辛,性寒,入肝经,“祛肝风,行经络,行肝气,开肝郁,止筋骨疼痛,目珠痛,散瘿”(《滇南本草》)。叶天士总结夏枯草“遇火令而枯,禀金水之气独全,水制火,金平木,故专主少阳相火,风木肝胆经之证”(《本草经解》)。风热上攻眼目,致目凸肿胀、目痉,夏枯草可疏风明目、清肝解热、散结消肿。柴胡味苦、辛,性微寒,归心、肝、胆经,“用其凉散,平肝之热”(《本草正义》),对肝火横逆损伤脾土具有清散作用;加之柴胡入少阳经,少阳厥阴相表里,少阳主枢,内寄相火,柴胡清解少阳郁火而助肝气疏泄,以清肝泻火。
5.2 熄风潜阳
若情志不舒,五志过极,加之素体阴虚,导致火热亢盛,阳化过极而生风,出现上肢震颤、心悸房颤等,需加用熄风潜阳药物,如牡蛎、珍珠母、代赭石、龙骨等。若肝阳亢动,可以镇肝风法,方选镇肝熄风汤,其中代赭石“主鬼疰,贼风,腹中毒邪气”(《神农本草经》),性凉而质重,归肝、心经,功用平肝潜阳熄风,又能凉血降逆,《医学衷中参西录》认为其“性甚和平,随降逆气而不伤正气”。对GD患者肝阳失制,阳亢化风,内风扰动心神,惊悸不安,怔忡失神,代赭石色赤而入心经,质重而降肝逆,有熄风潜阳、镇心安神之妙。
5.3 滋阴熄风
叶天士总结治疗内风,需用“肾水以涵之,血液以濡之,肺金清肃下降以平之,中宫之土以培之”(《临证指南医案》)。GD患者津液亏虚,风邪内动,上至肺阴,风火销烁,则咽干口渴;心阴不足,心风扰动,则心悸不安;胃阴消中,则消谷消瘦;肝阴不足,阳亢生风,则目涩不清、手臂颤抖。肾藏五脏之精,为全身阴液之本,故可重用地黄、山萸肉等滋养肾阴;加麦冬、五味子养心肺之阴;白芍、知母养肝阴、育心血。其中地黄味甘、苦,入心、肝、肾经,滋肾水而补益真阴,GD病程延绵难愈,易反复,久病入肾,伤及先天之本,故当滋肾阴固本。
5.4 熄风通络
风邪内扰,风胜则动,可见手臂颤动、心慌惊悸等,加之经络不通,导致甲状腺肿大、眼突不纳,临床可选用钩藤、僵蚕、全蝎等熄风通络之品。有报道,使用小剂量全蝎、僵蚕等治疗甲状腺功能亢进震颤取得一定疗效[21-22]。《本草纲目》载:“蝎,足厥阴经药也,故治厥阴诸病。诸风掉眩搐掣,疟疾寒热,皆属厥阴风木。故乃治风之要药。”全蝎性善走窜,循表入里,能祛风止痉,尤善治疗惊风抽搐、中风、癫痫等。但值得注意的是,该类药有一定毒性,且性烈而易伤正气,临床不可过用、久用。针对眼突、眼睑退缩,有医家使用搜风剔络止痉法,运用钩藤、全蝎、僵蚕等取得较好疗效[23]。
6 结语
临床上,GD病情迁延,伴随系统躯体症状多,且易反复发作。上述结合相关文献,梳理“内风”理论关联的GD起病特点、病因、躯体症状、病机及治疗等,阐述“内风”在GD发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临床应结合内风论治GD,理清风与火(热)、痰、郁等其他病理产物的关系,根据患者虚实情况,灵活辨证,为以熄风、清热、潜阳、补阴为核心治法施治提供充分依据。当然,临证切忌死守一方一法,需知常达变,方可获得更佳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