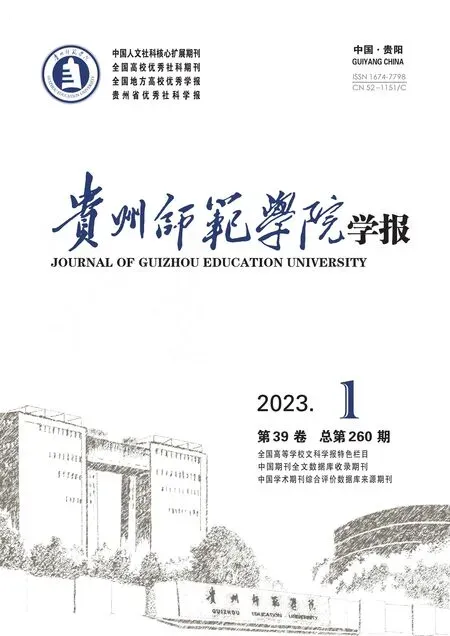唐赋京都书写之思想意蕴研究
——以长安为创作中心的考察
2023-04-05陈巧燕
陈巧燕
(华侨大学文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引言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云:“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1]此番言论很好地解释了中国京都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京都,作为统治者的政权所在地,既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又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自汉代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崛兴以后,措辞富丽的赋体文学便与京都文化的兴起与演进缔结了不可分割的关系。刘勰在《文心雕龙》一书中,曾就班、张二人的写作特色进行比较,并作了中肯且精确的评价。他认为:“孟坚《两都》,明绚以雅瞻;张衡《二京》,迅发以宏伟。”[2]尽管班、张二人的写作特色有所不同,但在他们的笔下,汉代京都的自然景观与人文风采依然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至唐代,辞赋能手如李庾、李华、杜甫、乔潭、徐彦伯等对帝都长安的描摹与颂扬,可视为这一文学传统的延续。从赋家的生平、赋文的序论以及赋作中的内容进行分析与判断,发现唐赋中的长安书写有着众多篇幅,如李庾的《西都赋》,李华的《含元殿赋》,杜甫的“三大礼赋”,刘公舆的《太常观四夷乐赋》,达奚珣的《太常观乐器赋》,乔潭的《裴将军剑舞赋》,谢偃的《观舞赋》《听歌赋》《东郊迎春赋》,王邕的《勤政楼花竿赋》,钱起的《千秋节勤政楼下观舞马赋》,虞世南的《狮子赋》,徐彦伯的《南郊赋》,元稹的《郊天日五色祥云赋》,王起的《东郊迎气赋》《北郊迎冬赋》,还有张复元、李绛的《太清宫观紫极舞赋》,张甫、陶举、高盖、敬括等的《花萼楼赋》,以及沈郎、陈嘏、无名氏等的《霓裳羽衣曲赋》,白行简、钱众仲的《舞中成八卦赋》等等。更重要的是,唐代赋家以开放的胸襟气魄、深厚的人文修养、激切的政治道德关怀与宏阔的写作精神共同累积与形成了唐赋长安书写之思想意蕴的丰富与深邃。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唐赋书写长安之思想意蕴加以探讨,以体现其丰富性与深邃性。
一、王权意识
王权意识即王权主义,其主要内涵是王权至上和王权崇拜。作为我国古代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它不仅直接表现为理论形态,还贯彻到政治制度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刘泽华先生在《中国的王权主义》一书中认为:“王权主义,是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其特点是宣扬君权至上;君主是全社会的最高主宰,神圣不可侵犯。王权主义的形成是中国古代社会君主政治的需要;反过来,王权主义又巩固和强化了君主专制统治。”[3]此番论述,诚谓卓见。王权意识不仅肯定了君主的崇高地位,也赋予了君主巨大的权威。因而,王权意识为历代君主所关切。如秦始皇横扫六国,统一华夏后有言:“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4]再如汉高祖刘邦建立大汉王朝后亦即宣布天下为己业。
京都绝非一座普通的城市。作为君主政权的所在地,京都已然成为君王权威与王朝气势的重要表征,其所承载的政治内涵是非常深刻的。因此,在汉朝时期,赋家便常在赋作中以京都之人文、形胜来颂美王权意识,以表现他们对当朝君主的信服与崇拜。司马相如的《上林赋》铺陈京都上林苑之壮丽和天子游猎之盛况,歌颂了大一统时期帝王的气魄和声威。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在比较西都长安与东都洛阳的过程中,均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歌咏了前后汉君王的荣耀与威力。唐代赋家秉承这一写作精神,在以长安的地理山川、宫殿建筑、乐舞艺术、皇家祭祀等为主题的篇章中,对王权意识进行了热烈的赞颂。这又集中体现在以下三点:
其一,天赋君权论。在古代中国,天赋君权是历史最悠久的王权观念之一,是论证君权绝对性的各种理论中最具有信仰色彩的部分。何谓天赋君权?即君主的权力与地位是由上天或者天道赋予的,君主的权威等同于天的权威,以不可违逆的“天命”来解释君权的获得与更替,这就是天赋君权论。《尚书·泰誓》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5]404孔安国言:“天佑助下民,为立君以政之,为立师以教之。当能助天,宠安天下。”[5]404《诗经·大雅·文王》毛亨传:“《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6]530郑玄笺:“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6]530自殷周以来,天赋君权论一直占据着王权观念的主流位置,在唐代天赋君权论依然影响深远。
陆贽在《冬至日陪位听太和乐赋》一文中认为是上天赋予了君主制定历法的权力:“乐自上古兮和洽是闻,日至南极兮阴阳肇分。名太和而顺气,取初阳而配君。则知天授圣而正历,圣应天而放勋。惟至也去阴就阳,惟乐也偃武修文。”[7]4696这就为君主制度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提供了哲理性依据。李程的《大合乐赋》亦颂之曰:“诚夫天祚我皇,恩历遐昌。掩邃古之嘉乐,轶三代之圣王。窃贺声明之巨丽,敢联雅颂之遗章”[7]6378,强调了君王地位的至高无上。由对天赋君权论的坚信与维护,推衍出的是对上天的畏惧与敬重。如贾餗的《至日园丘祀昊天上帝赋》写唐代君主敬天尊神、希冀受福:“惟天为大,惟圣奉天。所以就阳位,郊上元。礼高明之覆育,答生植之陶甄。告太一以衹敬,拥神休而吉蠲。”[7]7535再如赋家张余庆在《祀后土赋》中将大唐的繁盛与富足归因于上天的庇佑:“粤若盛唐,勃承天光,礼乐克备,典谟允臧。固以辚轹轩昊,跨蹑尧汤,豚鱼信行于寓县,鹓鹭才擢于岩廊”[7]9883,显示了唐人对上天的尊崇。
天赋君权、君承天运,一直是古代世人普遍接受的一种政治观念。此观念一直是帝王权威神圣性与绝对性的重要依据,故为历代君主所重视。赋家命意宏博、运笔古雅,在辞赋中对天赋君权论的阐述,表明赋家在意识形态方面愿与现实的政治和官方的思想保持一致性,体现了赋家对君主的忠诚之心。
其二,帝王煌煌功业之彪炳。“文韬武略”“气吞山河”“开疆拓土”“天下大治”等词汇,历来被视为帝王圣明的标志。古代帝王多有建功立业的强烈欲望,因为功与业是证明与支撑自己君临天下、教化众生的重要依据。此外,古代帝王还常以刻石、封禅以及著书立说等多种方式来圣化自己,希望自己的政治风范能根植于民心甚至流传万世。而赋家“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在辞赋中对帝王千秋功业的颂赞与君主之希冀正相统一。
高祖李渊在隋末大乱和群雄逐鹿中胜出,建立了强大的唐王朝。后历经太宗、高宗、武后等多位帝王的励精图治,国家也迎来了繁荣与强盛的新局面。辉煌的功业刺激了文人的创作体验,遂唐代赋家载言载笔时多以自豪之情来歌颂当朝君主的非凡成就。如李庾在《西都赋》中对大唐君主的文治武功予以大力宣扬:“外则国子招徒,疏馆开轩。左立太学,前惇广文。膳丰中厨,就教九年。稽以博士,总之成均。秘书典籍,品命校郎。……采摭轩昊,牢笼虞夏。辟孔子之学堂,敷一代之风雅。此王者之文教也。”[7]7644“亲兵百万,制以神策。紫身豹首,金腰火额。猎霞张旆,剥犀缀革。……依榆关以作镇,拒柳营而开壁。逐虏则出塞飞尘,伐叛则救晹作泽。此王者之武威也。”[7]7644杜甫的《三大礼赋》以饱满的情感和激昂的文字一展大唐帝王之崇高功业。“初高祖、太宗之栉风沐雨,劳身焦思,用黄钺白旗者五年,而天下始一。历三朝而戮力,今庶绩之大备,上方采庞俗之谣,稽正统之类,盖王者盛事。”[7]3640(《朝享太庙赋》)“今王巨唐,帝之苗裔,坤之纪纲。土配君服,宫尊臣商;起数得统,特立中央。”[7]3640(《朝献太清宫赋》)“盖九五之后,人人自以遭唐虞;四十年来,家家自以为稷契。王纲近古而不轨,天听贞观以高揭。”[7]3643(《有事于南郊赋》)李华在《含元殿赋》亦对大唐君主的功绩进行了热烈的讴歌:“其或蛮夷不至,帝用兴戎;降元帅于天上,发神谋于禁中。皇灵震燿,殄厥渠凶;矫矫武臣,此焉献功;操俘虏而陈器械,恢莫大之威容。”[7]3187
中国古代的政治思维历来强调君主的功与业,因此君主继承大统后都会多方面论证自己的辉煌成就,以此圣化自己,表明自己有资格永享绝对的权力与地位。唐代赋家发挥赋体之“颂赞”功能,在行文中极力夸耀大唐君主的丰功伟绩。这种将君主形象英雄化与理想化方式的书写,既显示了赋家对最高统治者的信服与崇拜,也强化了帝王的称圣意识与政治需求。
其三,大一统观念之宣扬。大一统政治思想要求人们统一于“华夏”,统一于“中国”,统一于“君主”。古代书籍对此多有论证。《尚书·盘庚》篇:“各长于厥居,勉出乃力,听予一人之作猷。”[5]347《礼记·曲礼下》:“君天下曰‘天子’,朝诸侯,分职授政任功,曰‘予一人’。”[8]《诗·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6]443《左传·昭公七年》载:“一国两君,其谁堪之?”[9]大一统理论强调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具有专属性,该理论赋予并强化了君主的无上权力,同时也为君主的绝对权威提供了合理性保证。
赋家王起与穆寂的同题之文《南蛮北狄同日朝见赋》明显贯穿着大一统的盛世格局与统治思想,表明赋家对大唐正统皇权的支持与拥护。王赋云:“圣上惟北辰之位是缵。匪南面之尊是满。穷发斯服。雕题无算。仰天威以怀柔,化夷德为悃款。”[7]6483穆篇记:“我皇道叶神化,功高睿算。万国之光斯临,八圣之业是纂。遐哉辫发之俗,既竭赤诚;逷尔椎髻之人,亦输丹款。岂不以阴阳焕乎金镜,律吕谐乎玉琯。德该动植,而以信以宽;仁及飞走,而不麛不卵。故得殊方述职,异俗来庭。归我元造,沐我皇灵。晓逾赤坂以向日,夕过白登以占星。碛路诚遥,委毳幕氊裘之质;山梯虽险,致穿胸儋耳之形。”[7]6981刘公舆的《太常观四夷乐赋》通篇洋溢着赋家对大唐君王泽披远方、外夷宾服的自豪之情,亦具有鲜明的大一统观念。赋篇有云:“我圣君文明立极,化本雍熙,太和克同于天地,贡乐不假于蛮夷。所以司于太常,奏于丹墀,俾华夷之风不隔。羁縻之义在兹。”[7]7324“夫其始也,伊四部之爰来,辟九门而并入。水火之位,雕题衣毛以相向;金木之方,皮服左衽以对立。于以彰四夷之咸宾,于以表五兵之载戢。”[7]7324乔潭的《裴将军剑舞赋》将裴旻将军出神入化的剑舞与其积极用世、建功立业的英雄气结合起来,诉诸于赋篇,表现了赋家对大一统王朝蓬勃气势的热情礼赞——“将军以幽燕劲卒,耀武穷发。俘海夷,虏山羯,左执律,右秉钺。振旅阗阗,献功于魏阙。……岂若将军为百夫之特,宝剑有千金之饰,奋紫髯之白刃,发帝庭之光色。所以象大君之功,亦以宣忠臣之力。”[7]4610-4611
强大和统一的唐王朝,不仅经济富庶、国家安定,而且兼收并蓄、善交友邦,极为重视与四方异域的和睦相处。在这样的历史大环境中,唐代赋家敏锐地把握到时代的脉搏,在赋作中对于大一统观念的热切宣扬,展示了大唐帝国版图的弘远与大唐国祚的蒸蒸日上,可以视为赋家维护王权尊严、塑造王朝气势的庄严颂歌。
行文至此,读者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唐代赋家在书写长安之地理形胜与人文活动的赋作时,对王权主义的极度关注与重视,而且这种风气一直贯穿于整个长安赋篇的创作中,甚至对宋代京都赋的写作产生深远影响。虽然赋家对王权至上这一政治理念的热烈赞颂可能带有顺情虚饰的一面,并非全部出于真心实意,但从特定的角度去考察,反能理解赋家渴望参与帝国政治而积极进取的用世心态。
二、仁德意识
“仁德意识”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理念之一,历来都被大力提倡。在古代,君主应当以“仁德”为标准来约己修身、治理天下、协和万邦,唯有如此,方能获得天地、神祗与百姓等的支持与拥护。正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5]662“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0]90“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11]51又赋这一文体,“雍容揄扬”,自汉代起对于仁德意识的理念和实践,都有集中且明确的反映,唐代的赋亦是如此。其中,唐代辞赋中的长安书写就仁德理念的反映,主要有以下几种呈现。
首先,对君主个人品德的直接赞扬,以表现赋家对仁德意识的肯定和重视。彭朝曦的《勤政楼视朔观云物赋》云:“‘云者运也’,陛下观之,所以广运明德。人既苏而宁靖,德乃运而充塞,犹储精而谷神,尚克己而作则,方将扬耿光于五圣,布深仁于万国。”[7]9899李华《含元殿赋》记:“今吾子之文明,昭乎累圣之耿光,美于大君之孝德。”[7]3189陆贽《东郊朝日赋》有“日为炎精,君实阳德,明至乃照临下土,德盛则光被四国。天垂象,圣作则,候春分之节,时则罔愆。顺《周官》之仪,事乃不忒”[7]4695之言。韦充《郊特牲赋》有“惟吾君之德也,与天地之巍乎”[7]7564之语。元稹《郊天日五色祥云赋》有“今陛下德至天地,恩覃草莽,当翠辇黄屋之方行,见金枝玉叶之可数。陋泰山之触石方出,鄙高唐之举袂如舞。昭布于公侯卿士,莫不称万岁者三;并美于麟凤龟龙,可以与四灵而五”[7]6548-6549之言。从上述例子可见,“仁德”在唐朝时期,是赋家对君主品行最重要的评价之一。因为只有君主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拥有仁德精神,才能成为百官与万民的表率,才能让百官与万民心甘情愿地诚服。诚如孟子所言:“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11]23
其次,对君主施行仁德之政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的赞颂。如谢观的《东郊迎春赋》:“故乃布德施政,远达幽通。高卑咸沐,贵贱攸同。始振蛰虫,在好生恶杀;遂行庆赐,可灭私徇公。乃得化洽方隅,恩光岐雍。遵古典以立则,授人时而敬用。愿迎乎千春万春,与夷夏之所共。”[7]7872杜甫的《有事于南郊赋》:“伏惟陛下勃然愤激之际,天阙不敢旅拒,鬼神为之呜咽;高衢腾尘,长剑吼血。尊卑配宇县刷,插紫极之将颓,拾清芬于已缺。炉之以仁义,锻之以贤哲;联祖宗之耿光,卷夷狄之彯撇。盖九五之后,人人自以遭唐虞;四十年来,家家自以为稷契。王纲近古而不轨,天听贞观以高揭。蠢尔差僭,粲然优劣;宜其课密于空积忽微,刊定于兴废继绝。而后睹数统从首,八音六律而惟新;日起算外,一字千金而不灭。”[7]3643审乐可以知政,唐代赋家亦通过长安之乐风与舞容来赞扬君主的仁政与德治。陆贽《冬至日陪位听太和乐赋》云:“既而筍簴齐列,笙竽互传,偕肃肃而合雅,亦啾啾而同元。备以四夷,识四海之无外;成于九土,知九德之咸宣。崇易简岂同于濮水,务德化宁比于钧天。既损之而又损,盖斯焉而取焉。”[7]4697李绛的《太清宫观紫极舞赋》记:“美乎!冠之象以峨峨,舞其容以傞傞。合九变之节,动四气之和。散元风以条畅,洽皇化之宏多。是时也,天地泰,人神会。舞有容,歌无外。故曰作乐以象德,有功而可大。”[7]6525钱仲众的《舞中成八卦赋》曰:“我后惟明,旧章爰制,以嗣以续,不陵不替。和乐且孺,每立象以化人;德音不忘,故体乾而称帝。是知卦之设也。八方正,四序和,彼象功以明德,安可与兹舞而同科?”[7]9859-9860另李蒙与石贯的同题之文《藉田赋》,均表现了大唐君主亲行躬耕之礼,以示君主施仁德于百姓,愿百姓丰衣足食的美好希冀。李赋开篇即云:“揉为耒,剡为耜,取其象也远矣。农为本,食为天,惟其利也大焉。圣人利器致丰,躬亲莫重于稼穑;轨物励俗,敦劝克厚乎率先。于以奉神衹,昭报之诚达;于以祈社稷,孝享之德宣。则躬耕之义也,从古以然。皇帝勤惟国本,钦若人天。所务惟农,顺动而取诸豫;所宝惟谷,时行而应乎乾。洎正月之吉日,将有事乎昊天;列千官于近甸,屯万骑于遐阡。”[7]3664石赋亦有“大皞御辰,勾芒定位。天子率躬耕之礼,有司谨亲载之事。以为帝籍斯阙,皇猷久坠。不修耒耜之功,是堕粢盛之义。……礼乐既备,人神告休。事虽兆于东作,稔以见其秋收。岂独亲耕于甸内,实亦种德于道周”[7]7915之语。由以上例子可知,唐代赋家对君主所践行的仁德之政,多有详细的描述与赞扬。从这些描述与赞扬中,读者可以清晰地洞察到唐代赋家对仁德之治与太平之世的期望与企盼。
再者,赋家的仁德意识还表现在对尧舜二君的标榜。相传,尧舜是我国古代社会部落联盟中最具有“仁德”美名的两位首领。他们勤政爱民、以德辅政、制礼作乐、万邦和睦,深得万千民众的尊敬与爱戴。随着时代的发展,后世常将“尧舜”作为明君圣主的代表与象征。因此,在以长安为书写对象的辞赋中,唐代文人也多以尧舜之治世形象来表现自己对仁德意识的重视与推崇。如刘公舆的《太常观四夷乐赋》开篇云:“圣皇穷天覆以张宇,极地载以光宅。端拱协有虞陶唐,献乐奏戎夷蛮貊。岂不以浃洽元化,沐浴圣泽。”[7]7324周存的《太常新复乐悬冬至日荐之园丘赋》记:“尔其金石具陈,鼗鼓间出,和其戛击,节以徐疾。五色不乱以成文,八风不奸而从律。大章彰之,已合陶唐之代。韶尽美矣,不惟有虞之日。”[7]5196无名氏的《霓裳羽衣曲赋》曰:“今我皇绍唐尧之业,继圣祖之德,制礼作乐,而和兆人,端拱垂衣,而朝万国。”[7]9986又崔立之的《南至郊坛有司书云物赋》载:“懿夫宇宙氛氲,晴郊景曛。宗伯司礼,保章辨云。荣光烛于九野,佳气覆于六军。飘飘飖飖,郁郁纷纷。足以昭上帝,瑞吾君。时谓唐时,歌卿云之五色;德称虞德,咏南风之再薰。”[7]6191王起的《虔禋六宗赋》云:“然后一德不二,三皇可四。地发嘉生,天呈上瑞。致百神之职,兴兆人之利。君子谓大舜之克禋,惟我皇之能备。”[7]6494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唐代赋家之仁德意识实与儒家义理息息相关。仁德观念,不仅是儒家的一种社会理想,也是儒家的一种政治策略。《论语·为政》篇记:“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0]91《孟子·公孙丑上》云:“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11]19《荀子·王霸》篇亦有“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12]之言。又李唐王朝自立国起,便十分重视儒学的教育作用,追求以儒学教化百姓。比如唐太宗奉行儒学优先、三教并重的政策。他曾宣称:“朕今所好者,唯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13]君主以儒学为正宗,并以相应的措施扶植儒学,为儒学的繁荣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环境。在这样的氛围中,儒家之仁德义理遂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社会的各个群体和各个方面。所以,唐代赋家在辞赋创作中宣扬仁德意识,实在情理之中。
三、生命意识
“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14]“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长。”[15]生死问题,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古老的问题之一,也是人类对自我,对世界的观照中所面对的最本原与最朴素的问题之一。与先秦相比,唐朝时期的人们已经能够较为正确地认识生命的现实状态。但唐赋,作为一种颂赞文体,在对长安之景、长安之物和长安之事进行赞颂时,却很少对生命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作深入的思考与探索,也很少对生命的衰落与灭亡表现出深沉的感伤与哀悼。就具体情境而言,唐赋中的长安书写所蕴含的生命意识主要包括两大类型:一个是祝愿君上圣寿无穷;另一个是肯定君主的享乐意识。
首先,祝愿君上圣寿无穷。中国古代的人们很早就意识到人的生命在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转瞬即逝的存在,再流光四溢的生命,再辉煌耀眼的成绩,也终会有如烟消亡的时候。于是,依恋人世,祈求长生便成了中国古人最普遍的一种世俗欲望。余英时先生在《东汉生死观》一书中,曾这样总结汉代人对生死问题的看法:“一般来讲,那时人们对人世具有强烈的依恋感,他们渴望长寿而害怕死亡。此外,他们关心世俗的事物并受世俗道德的约束。”[16]这种忧生惧死的生死观,在唐朝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随着专制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君主大都希望自己能永久地拥有不可撼动的权利与权威,因此,他们渴望万寿无疆的想法就变得异常强烈。长安作为首善之都,已然成为君主权势的外化之一,遂在辞赋中,唐代赋家就长安书写向君主祝颂长寿,便成了一种普遍的表达。
陈嘏的《霓裳羽衣曲赋》即在一片歌舞升平中表现了自己祝愿君上圣寿无极的企盼。“懿乎乐洽人和,曲含仙意。杂弦管之繁节,澹君臣之元思。清凄满听,无非冲穆之音;飒沓盈庭,尽是云霄之事。吾君所以凝清虑,慕元风。无更旧曲,用纂成功。既心将道合,乃乐与仙同。悦康平于有截,延圣寿于无穷。”[7]7896高盖的《花萼楼赋》亦有相似的祝愿之语:“岁如何其岁之首,花萼楼兮对仙酒,愿比华封兮祝我圣君千万寿。”[7]4033另大唐的君主常常在皇家祭祀的典礼中寄托他们祈愿长生的想法,所以唐赋中与长安祭祀相关的篇章中会频繁出现一些祝寿之词。如萧颖士的《至日园丘祀昊天上帝赋》篇中有云:“是以神降我福,人怀我惠;时罔凶荒,物无疵疠。致洪化于仁寿,岂不由肃敬于大祭?”[7]3260徐彦伯的《南郊赋》篇末颂赞道:“煌煌灵台,告成功兮。我君孝享,亚坤宫兮。纯嘏布濩,延皇穹兮。惟策代表,霭升中兮。享寿千亿,传无穷兮。”[7]2715王堙的《南至云物赋》记:“于时帝在旸谷,风后陪骖;会玉帛而涂山有愧,朝公卿而汾水怀惭。佳气从龙,遥连渭北;非烟拂日,俯对终南。懿圣诞之与万,美皇道而超三。”[7]3376类似的祝寿赋篇还有崔立之的《南至郊坛有司书云物赋》、陆贽的《东郊朝日赋》等作品。
对生命短暂的不舍与感叹,对挽留生命的强烈追求,促使人们萌生了“长生”与“长寿”的想法。但“长生”或者“长寿”只是一种理想图景,是人类文明对于生命永恒的一种美好企盼。伴随着生命意识的逐渐觉醒,唐朝时期的人们已经较为清楚地知晓生命进程之不可逆。所以,唐代赋家在辞赋中向君上祝颂长寿,更像是一种恭敬之语,就深层次心理来说,它反映的是臣子对君主所拥有的政治身份与政治权利的认同与敬重。
其次,肯定君主的享乐意识。生命的消逝,是无法回避的一个客观事实,是人类个体无能为力的必然结局。于是,注重世俗生活,尽情地享受生命的美好与欢乐,亦是对生命别样的热爱与珍惜。唐朝是开放性的时代,唐人的生活情态是活泼的、鲜明的。《开元天宝遗事》中曾有这样的记载:“都市男女,每至正月半夜,各乘马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游。”[17]诗人李白亦有诗云:“五陵少年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18]
唐代赋家的长安书写,虽受到了雅正纲常与礼乐交欢的定向规范,但仍详尽地铺陈与极力地渲染宫殿之富丽、乐舞之繁会和百戏之精彩等,以此顽强地肯定着君主的世俗享乐意识,充分地彰显了世俗欲望的合理性。如张甫的《花萼楼赋》既描写了花萼楼的华丽与精致,又铺叙了君民同乐的盛况。“厉丹凤,陵白鹤;浮纲玲珑,流光灼烁。阴移翠仗,影碧潭之清泠;日上金题,照锦林之花萼。”[7]4031“帝曰惟休,顺豫而游;跻攀初极,眺览还周。登万乐或歌或舞,列千品乃公乃侯。莫不倾赤县,竭神州;士女都集,衣冠尽留;悉观圣旨,共仰皇猷。掩宫扉则闻箫声之下汉,卷珠箔则睹天人之在楼。”[7]4031乔潭的《裴将军剑舞赋》不单描绘了“为天下壮观”的裴旻剑舞,也刻画了裴将军献戎捷于长安后,君臣开怀畅饮、其乐融融的和谐场面。其词曰:“将军以幽燕劲卒,耀武穷发。俘海夷,虏山羯,左执律,右秉钺。振旅阗阗,献功于魏阙。上享之,则钟以悍簴,鼓以灵鼍。千伎度舞,万人高歌。秦云动色,渭水跃波。有肉如山,有酒如河。君臣乐饮而一醉,夷夏薰薰而载和。”[7]4610郑锡的《正月一日含元殿观百兽率舞赋》写的是元日大朝会上君王偕同百官一起欣赏百戏表演。赋中有云:“皇上端拱穆清。法春秋五始之要,酌礼乐三代之英。赫帝典,含元正。衡纪允叶,摄提为贞。疏龙首以抗殿,靡鱼须而建旌。开彤庭执玉帛者万国,发金奏韵《箫韶》而九成。祥风应律,庆云夹日。华夷会同,车书混一。羽卫宿设,乘舆晓出。陈八佾象钧天之仪,舞百兽备充庭之实。彼毛群与羽族,感盛德而呈质。”[7]4601
肯定君上赏心娱情、适当享受生活乐趣的篇什还有陶举的《花萼楼赋》、李华的《含元殿赋》、沈郎和陈嘏等的同题之文《霓裳羽衣曲赋》、王邕的《勤政楼花杆赋》、钱起的《千秋节勤政楼下观舞马赋》、敬括的《季秋朝宴观内人马伎赋》等等。在这些赋作中,赋家对于宫室之华丽、乐舞之多彩与百戏之丰富的描绘是不厌其烦的,有时甚至连篇累牍地堆砌辞藻,而这些繁复细索的句子与词汇,流露出的是赋家对世俗欲望的执着与不懈追求。不盲目地奢求生命的长度,提倡充分地享受富有世俗乐趣的生活,这也是生命意识的另一种体现。
四、结语
自秦汉大一统形成以后,京都建设与制度渐趋完善。唐长安城地处关中平原中部,依山带水,南对终南山、北临渭水,且总体地形东南高、西北低,易守难攻,地理位置优越。不仅如此,作为京都,在政治上,长安代表着帝王、国家和权力;在经济上,长安代表着繁荣、富庶和财富。故唐代赋家殚精毕思,承汉散体大赋之遗绪,在赋作中以铺陈之手法绘声绘色地描摹了长安的纷呈物态与丰繁事象,如地理山川、园林风景、宫殿建筑、乐舞艺术、百艺表演、校猎情景、天子祭祀、商业贸易等,无不透露着京都长安的庄严与繁华,彰显着帝王身份的尊贵与显赫。因此,以唐赋中的长安书写之思想意蕴为切入点,有助于我们去解读唐代辞赋创作与京都文化的深层关系。此外,唐赋与长安之关联,还可以引发我们作进一步的思考,即作为表现中国唐代文化的重要文学载体之一——唐赋,它与唐朝国家的运行又有怎样的具体性联系,而我们又该如何搜集资料、查阅文献、解读作品,才能对其进行有效性地、学理性地研究与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