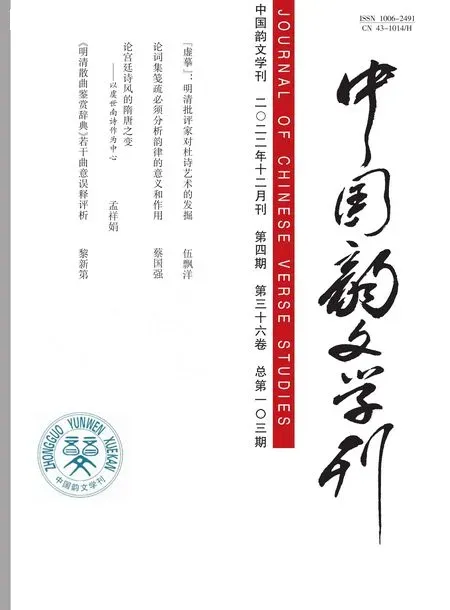“赋家”称谓谫论
2022-02-09王泽华
王泽华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9)
作家称谓表面上只是一个称呼、代号,实际上其背后不仅流露出显而易见的身份批评、创作价值评判,亦有兀自蕴藏的文体认知、创作逻辑等。古人或许早就意识到了该问题。王充在《论衡·超奇》篇云:“杼其义旨,损益其文句,而以上书奏记,或兴论立说、结连篇章者,文人鸿儒也。”[1](P211)较为宏观地定义了“文人”之职能。而具体到各体文学领域,对作家称谓的思考虽间或有之,然鲜有成系统的专论,且视野多局限于批评理论昌明的诗、文领域(1)如宋玉《九辩》:“窃慕诗人之遗风,愿托志乎素餐。”白居易《读邓鲂诗》:“诗人多蹇厄,近日诚有之。”茅坤:“荆川批‘断、续’两字,是文家血脉三昧处,非荆川不能道。”。近年来,我国学者开始关注作家称谓问题,围绕“文人”“诗人”“曲家”“小说家”展开了一系列的思考(2)如对“文人”称谓的研究,有吴承学、沙红兵的《身份的焦虑——中国古代对于“文人”的认同与期待》,《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对“诗人”称谓的讨论有李舜臣的《何谓诗人:中国古代“诗人”观念的演变》,《学术研究》2021年第9期,赵强、陈向春的《从群体到个体:“诗人”一词的传统涵义及诗学内蕴》,《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10期,等等;讨论“曲家”的如汪超、谭帆所撰《古代曲家的身份认同与观念阐释》,《文艺研究》2015年第5期;“小说家”称谓的研究有高华平的《先秦的“小说家”与楚国的“小说”》,《文学评论》2016年第1期,等等。。具体到赋学范畴,相关研究则略为沉寂,唯许结在《赋学讲演录(二编)》中,以赋体文学发展过程为线索,讨论了“赋家”社会身份或曰政治身份的变迁,并借此窥察赋的创作问题。其实,退一步看,单纯意义上的“赋家”称谓,也涵摄着赋体源流、创作观念、诗赋之别等重要命题。为何辞赋作品产生很早,而作家称谓的使用却很晚才出现?为何“辞人”称谓在很长一段时间流传比“赋家”更为广泛?为何称辞赋作者为“赋家”,而不是“赋人”?“赋家”称谓到底意味着什么,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一 由“辞人”到“赋家”
辞赋作家之称谓,最早当追溯到扬雄自“诗人”析出的“辞人”。《法言·吾子》云:“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2](P49-50)这里的“辞人”有着明确的指向,即指景差、唐勒、宋玉、枚乘、贾谊、司马相如等人,同时扬雄还指出了辞赋“丽”的特质,批评当时不加节制的“丽”的辞赋创作趋向,认为作品带有“丽以淫”特点的作家,就是“辞人”。从赋体文学的源头来看,扬雄对“辞人”的定义应当析自“传《诗》之人”或者说“赋《诗》之人”。班固对其论曾做过深入的解读。《汉书·艺文志》云:“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3](P1756)“学《诗》之士”最早作“贤人失志之赋”,扬、班虽然承认荀子、屈原的作品是赋,却不肯称其为“辞人”,而仍将他们归为“诗人”。由此可以看出,作品依循“古诗之义”的辞赋作家,在当时仍可称“诗人”,而作品坠失“古诗之义”的辞赋作家,被称作“辞人”。彼时“辞人”尚不是通用称谓,辞赋作家的称谓仍然模糊不清。
扬雄将“诗人”与“辞人”对举,使得“辞人”一词带有贬义色彩,但无形之中也拔高了“辞人”。可是,“辞人”称谓并未因此广泛流传,两汉至魏晋,“辞人”都未能成为辞赋作家的专属称谓。尽管班固《汉书》一再申述扬雄之论,然亦有如王符《潜夫论·爱日》云:“百姓废农桑而趋府庭者,非朝晡不得通,非意气不得见,讼不讼辄连月日,举室释作,以相瞻视。辞人之家,辄请邻里应对送饷。”[4](P214)这里的“辞人”就显然是指涉及诉讼之人。
直至刘勰《文心雕龙》撰成,辞赋作家的“辞人”称谓才再次回归人们的视野。《文心雕龙》提及“辞人”多达十四次,基本上固定了“辞人”的含义,成为后世“辞人”称谓使用的范本。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十四个范例中,有三次作“词人”,考察其内涵与“辞人”无异,且“词人”一词最早即见诸《文心雕龙》,后世亦常将“辞人”与“词人”混用,故亦将其一并讨论。刘勰使用“辞人”,与扬、班之论主要有两点不同。一是“辞人”涵盖范围的变化。《文心雕龙》称“辞人”,凡半数是指辞赋作家。如《辨骚》篇云:“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5](P162)《时序》篇云:“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5](P1677)可以看出,这里的“辞人”已不是特指作品淫丽的作家,而是涵盖了整个辞赋创作群体。不仅如此,“辞人”泛指文学家的情况也较多见。如《指瑕》篇载:“近代辞人,率多猜忌,至乃比语求蚩,反音取瑕。”[5](P1545)《物色》篇云:“古来辞人,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5](P1758)前者是批评当时特重音韵的创作风气,后者是谈论古今作家文风的变化,二者都没有专指辞赋作家的意思。此外,《明诗》篇还有:“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5](P185)竟以“辞人”代指“诗人”。出现这样的情况,意味着“辞人”之内涵或许已不同于两汉,词语的感情色彩发生了游移。这是刘勰区别于扬、班之论的第二个方面。魏晋以降,经学根本松动,“古诗之义”渐不再是评判文学作品价值的最高标准,“辞人”的贬义色彩也逐渐消褪。尽管刘勰在部分篇章中还是批判“辞人”作品的诡巧淫丽,但其持论总体上是中立客观的。更何况,当时以“辞人”代指“诗人”的情况并非个例,如钟嵘《诗品》:“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故词人作者,罔不爱好。”[6](P47、54)颜之推《颜氏家训·名实》:“竟日欢谐,辞人满席,属音赋韵,命笔为诗,彼造次即成,了非向韵。”[7](P374)这些都说明,至迟在南北朝时期,“辞人”称谓已逐渐走向中性化。
刘勰《文心雕龙》前后,亦有沈约《宋书》、魏收《魏书》等间或提及“辞人”,大抵不出刘勰所论。此不赘叙。
由“诗人”完全凌驾“辞人”,到“辞人”可以包纳“诗人”,从赋体文学演进的角度来看,反映了赋的创作主流由“铺采摛文”的骋辞大赋,转向“体物写志”的抒情小赋。同时,从文学接受上说,也体现了由“雕虫俳优”之作到“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的认知转变过程。许结有论:“辞赋的‘明体’理论至魏晋及南朝而展开。”[8](P804)或许正是这种明体、辨体意识的增强,使赋体文学在观念上愈加独立,方才有辞赋作家专属称谓之需求与可能。
但“辞人”称谓终究没能为辞赋作家所独享。唐宋以降,“辞人”的使用频率虽日益繁多,但词义却进一步泛化,泛指文学家的情况要远远多于专指辞赋作家。如唐代白居易有诗云:“辞人命薄多无位,战将功高少有文。”[9](P530-531)将“辞人”与“战将”对举,泛指文人。又宋代姚铉云:“世谓贞元、元和之间,辞人咳唾,皆成珠玉,岂诬也哉!”[10]姚氏在文章中全面品评了贞元、元和之间文人的诗、文、赋,随后发出上述感叹,可见,其所称“辞人”亦是泛指文人。踪凡云:“唐宋(含辽金),是中国赋体文学史上的又一关键时期。”[11](P277)律赋郁勃,文赋肇兴,这个时期的辞赋创作可以说是远超前代,直逼炎汉,而辞赋作家却迟迟没有得到专有的称谓。“辞人”的多义已不符合赋体文学创作、批评、传播的发展要求,于是,“赋家”称谓被唤醒,终于成为辞赋作家的专指独称。
“赋家”称谓复苏,更深层次的原因当是唐宋的“古律之争”。清人陆葇在《历朝赋格·凡例》中说:“古赋之名始乎唐,所以别乎律也。”[12]可知唐人将律赋产生之前的赋体文学,即骚体赋、诗体赋、散体赋、骈体赋、赋体之文等,统称为古赋。这阐明了两点文学动向,一是在唐宋,律赋成为创作主流,且持续兴盛不衰,因此后世才有“复古”之可能。许结有论:“律赋在唐代出现,元、明赋学复古,是针对律赋而言的。”[13](P162)正是说明这一点。而先唐多称“辞人”,恰正指古赋作家,为区别古赋与新兴律赋,将“赋家”称谓推出,自有其内在机理。二是要注意此一“别”字,律赋作为考试文体,虽与献赋有一定关联,但其创作程式、创作心态、创作题材乃至创作环境与古赋都完全不同。先唐称“赋家”,是受经学和子学影响,有学术化和职业化的原因。而科举试赋制度下的“赋家”,又有着全新的学术路径与职业要求,唐宋大量出现的律赋技法文献,如《赋要》《赋谱》《赋格》等,恰好说明了这一点。那么,“赋家”称谓究竟有何内涵?其在不同时代的指向有何不同?这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
二 历代“赋家”称谓指向
据《西京杂记》所载,“赋家”称谓最早似当出自司马相如之论:“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14](P65)而周勋初通过用词用语、文艺观念等,考订此语不可能出自西汉,而应是魏晋之间伪托。[15]许结亦云:“尤其是‘赋家’之称,汉人指称家数即学派,而无及个人者……汉代文献无此指称,而其所指却多轻贱语……”[8](P259)不过,《西京杂记》一语虽为伪托,但也并非毫无价值,元明论赋“祖骚宗汉”,就常奉其为不刊之论。又四库馆臣亦云:“其中所述,虽多为小说家言,而摭采繁富,取材不竭。李善注《文选》、徐坚作《初学记》,已引其文,杜甫诗用事谨严,亦多采其语,词人沿用数百年,久成故实,固有不可遽废者焉。”[16](P49)据此看,即便《西京杂记》“赋家”之语系伪作,亦当出于唐代以前,并且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西京杂记》论“赋家”,具有三点开创性意义。一是首倡“赋家”,为后世辞赋作家称谓的确立提供参考;二是不以乖离《诗》义而批评,客观看待甚至有褒扬辞赋作家与辞赋创作之意味;三是提出了“赋家”的创作要求,即在创作方法上要语言精工华美、内容丰富有序、音韵和谐自然,在创作心态或者说创作思想上,要察览万物,领悟“道”之奥妙(3)参见陶慧《“赋迹”“赋心”说涵义新探》,《文艺理论研究》2017年第4期。。
《西京杂记》之后,又有刘勰《文心雕龙》谈及“赋家”。在《诠赋》篇中,刘勰列举了荀卿、宋玉等十位辞赋作家加以品评:“凡此十家,并辞赋之英杰也。”[5](P289)并点评了王粲、左思等近世辞赋家代表。刘勰此论,是针对个人创作展开的,他说的“家”乃指大家、名家,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统称,更接近于量词,而并非辞赋作家的专有称谓。如《诗品》云:“观斯数家,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6](P186)“二汉为五言者,不过数家,而妇人居二。”[6](P197)亦同此理。六朝品评风气甚炽,不仅对人物加以品评,甚至有《书品》《画品》等,把刘勰此语放在这样的语境下理解,就不难发现这一点。
迄于唐宋,“赋家”称谓开始广泛流播。这个时期的“赋家”称谓有两点异于前代。一是广作褒扬语,以称当世作家,乃至自称。陈师道《贺关彦长生日》诗云:“经术宜传世,清明正得秋。德优高士传,名重赋家流。”[17]关彦长为陈氏密友,陈赞其在士人群体中德高望重、在当世辞赋作家中有很高名望。此处“赋家”与“高士”相对,此诗又是一首贺诗,可以肯定,“赋家”称谓在这里乃是褒赞之辞。再如,晚唐律赋名家黄滔,二十余年不第,登科后赋诗云:“贾谊才承宣室召,左思唯预秘书流。赋家达者无过此,翰苑今朝是独游。”[18]得意地自期显达能够超越前代赋家,在当今文坛也是独占鳌头。黄氏显然也把自己归为“赋家”,且结合全诗用语,他对自己的“赋家”身份也不无称褒之意。二是唐宋“赋家”称谓主要指称律赋作家。如宋人李廌《师友谈记》曾记载秦观的一段论述:“少游言:‘赋家句脉,自与杂文不同。杂文语句或长或短,一在于人;至于赋,则一言一字,必要声律。凡所言语,须当用意屈折斫磨,须令协于调格,然后用之。不协律,义理虽是,无益也。’”[19](P20)秦观认为,作赋首重声律,用词用语必须严加推敲琢磨,甚至将“调格”置于“义理”之上。秦氏所论之赋,当指律赋。唐宋科举试赋,首重韵律,一旦错韵失律,当即黜落,重律为先乃是律赋的铁则。由此看,秦观所言“赋家”,即主要指律赋作家。再如林希逸《李君瑞奇正赋格序》称:“今集赋家大小诸试,自兰省三舍、诸郡鹿鸣,以至堂补巍缀者,皆在焉。”[20]所谓“大小诸试”当指大大小小的试赋活动。王士祥称:“凡符合科场试赋文体要求的赋皆应称为试赋。”[21](P144)而“兰省三舍”即指秘书省与太学内、外、上三舍,与“诸郡鹿鸣”并指中央及地方的试赋活动。至于“堂补巍缀”,当是文人举子的平日练习之作。林氏此语紧密围绕科举试赋展开,他所称的“赋家”自然专指律赋作家。
唐宋以“赋家”称律赋作家,其背景乃是律赋为唐宋时期赋体文学的主流。踪凡称:“现存1700篇唐赋,1400篇宋赋,皆以律赋为大宗。”[11](P277)律赋受到文人士子的追捧,不仅在于其作为考试文体,更在于作赋对才学提出的极高要求。对此,宋人沈作喆曾引孙何汉论云:
唐有天下,科试愈盛,自武德、贞观之后,至贞元、元和以还,名儒巨贤比比而出。……惟诗赋之制,非学优才高不能当也。破巨题期于百中,压强韵示有余地;驱驾典故混然无迹,引用经籍若己有之;咏轻近之物则托兴雅重、命词峻整,述朴素之事则立言遒丽、析理明白。其或气焰飞动而语无孟浪,藻绘交错而体不卑弱。颂国政,则金石之奏间发;歌物瑞,则云日之华相照。观其命句,可以见学植之深浅;即其构思,可以觇器业之大小。穷体物之妙,极缘情之旨。识《春秋》之富艳,洞《诗》人之丽则。能从事于斯者,始可以言赋家流也。[22]
做律赋要破题准确、用韵严整、语言华美、结构精巧,运用典故要自如有度,咏物描写要有所寄托,还要做到与君国时事相联系,何其难也!孙氏认为,只有达到了这些标准,才可称得上是“赋家”。有需求就会有市场,唐宋不仅诞生了一大批律赋创作的名家圣手,还出现了一批教人作赋的教材、参考书。如当时有名的律赋作家范传正、张仲素、白行简等,都著有关于律赋创作要领、心得的专书,史志见载的就有《赋枢》《赋诀》《赋门》《左传类对赋》《赋门鱼钥》等数种。此外还有官方颁布的试赋韵书《礼部韵略》、用于补充和解读官韵的《增修校正押韵释疑》等等。唐宋时期,辞赋别集也开始大量编纂。据踪凡《中国赋学文献考》统计,现知先唐辞赋别集总共才有6种,元明清三代凡64种,而唐宋(含辽金)时期就有60种。以上所论,不仅说明律赋在唐宋时期十分兴盛,更可以看出,彼世围绕律赋创作活动,产生了一批专业化的人才。由于律赋创作需极富才学,相比一般的诗文创作有一定的门槛,故而时人赋予这些专业化人才“赋家”的称号,其中的褒赞之意,不言自明。要之,“赋家”称谓在唐宋不仅指一般的辞赋作家,更多的是指从事律赋创作活动的专家。“赋家”称谓在唐宋被叫响,其根本原因在于辞赋作家乃至辞赋产业的专业化、职业化。这也标志着赋体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两汉之后经历再度革新,走向成熟与复苏。
迨元及明清,“赋家”称谓渐指代一般意义上的辞赋作家。《古赋辩体》用十九次,并《雨村赋话》《历朝赋格》等称“赋家”,皆作泛指之意。可以说,唐宋以后,“赋家”称谓逐渐稳定,作为辞赋作家的通用称号沿用至今。
所可考者,唯金、元科考有“词赋”一科,遂有“词赋家”之称。据《金史·选举志》载:“其后南北通选,止设词赋科,不过取六七十人。”[23](P1136)又《元史·选举志》载:“以论及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作三日程,专治一科,能兼者听,但以不失文义为中选。”[24](P2017)“词赋家”最早当专指科举试赋作者,这是沿用唐宋称“赋家”之传统。如程钜夫《赵仪可墓志铭》称:“余自弱冠闻江右诸儒,先称词赋家,必及赵仪可。”[25]此语前先论及试赋制度,后又言赵仪可年逾七十参加科举事,可知这里的“词赋家”当专指试赋作家。明代科考废考赋之制,然仍称“赋家”“词赋家”,用作称呼一般意义上的辞赋作家。如胡应麟《诗薮》云:“《志》之于《略》仅三之一,则西汉诸词赋家,亦仅半存而已。”[26](P252)入清已还,虽曾短暂考赋,亦有“馆阁赋”盛行,然“赋家”“辞人”“词赋家”及“辞赋家”并用,再无特称。唯段玉裁注《说文解字》,常言“辞赋家作”“赋家所谓”“词赋家或言”等,当是上承大赋、律赋盛行之世,字书、韵书之写作传统也,同时,这也反映出辞赋创作在清代的再度兴盛。
三 “赋家”与“诗人”
诗、赋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在产生、发展、鼎革等环节保持紧密的联系。《汉书·艺文志》合论二者为“诗赋略”,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等都将诗赋并举,充分说明古人对此已有深刻认知。钱志熙亦称:“‘诗赋’并非简单的目录学分类的一对组合性名词,而是凝结着诗歌与辞赋之间复杂关系的汉魏文学的核心概念,它所指向的是以诗赋为核心的一个纯文学的共同体。”[27](P38)在此语境下,诗赋二体作家称谓作为同样紧密相连的两个概念,具有明显的比照意义和价值。考察“赋家”与“诗人”称谓演变之异同,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赋家”称谓的内涵,从而管窥诸多赋体文学发展的关键性问题。
一曰辞赋作家称谓产生相比于“诗人”的迟滞。战国末,宋玉《九辩》首次提到“诗人”之称:“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28](P192)然而直到大约两百五十年后,扬雄才揭橥了“辞人”之称。为何从辞赋文学产生到辞赋作家称谓出现,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岁月?这大概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辞赋作者具名明确。韩晖说:“与诗歌散文相比,辞赋是一种产生晚而自觉早的文学样式。”[29](P1)不同于早期诗歌的集体创作以及“《诗》人”身份的模糊,辞赋作者从一开始就是较为明晰的,从荀子《赋篇》到宋玉《高唐赋》《神女赋》,从枚乘《七发赋》到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不仅作者署名基本清晰可考,赋家的生平事迹、文才声名更是为人所熟识,甚至作品的创作背景也有清晰的记录。因此无论在史志目录、批评论著还是在日常交流中,时人常径称为某某(作家名)赋、某某作,而少用作家称谓称呼。第二,“辞人”称谓在早期带有贬义色彩,辞赋作者往往不愿被贴上这样的标签。《汉书·贾邹枚路传》载:“皋赋辞中自言为赋不如相如,又言为赋乃俳,见视如倡,自悔类倡也。”[3](P2367)又扬雄《法言·吾子》称:“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2](P45)枚、扬本意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辞赋乃是他们获得天子关注的手段,不料却弄巧成拙,被“俳优畜之”,是故他们不仅痛恶自己的“辞人”身份,甚至有悔赋之思。第三,据踪凡《中国赋学文献考》稽考,尚未见唐代以前有赋学批评专书。先唐赋学批评多依赖文本,表现为选本、赋注、作家事迹评论等模式,即便是偶见赋论,也是寥寥数语、极为简略。少数例外如《文心雕龙》义旨遥深,也正是辞赋作家称谓广泛使用之渊府。由于赋学批评的不发达,少有对赋家群体的反思,因而“辞人”“赋家”等称谓也极少被使用。
二曰“赋家”称谓演变对“诗人”的依附与独立。“赋家”对“诗人”的依附,上文论扬雄、班固语时已有所提及,前人亦多有考论(4)参见冷卫国《“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论扬雄的赋学批评》,《齐鲁学刊》2013年第3期;曾祥波《“诗人之赋丽以则”发微——兼论〈汉志·诗赋略〉赋史观的渊源与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不待赘言。关键是从称谓演变的角度来讨论二者之关系。李舜臣说:“战国末期至六朝,‘诗人’主要专指《诗经》的作者;从唐代特别是中唐之后,则普遍用指一切写诗之人。”[30](P176)可以看出,“诗人”称谓与“赋家”称谓相似,其指代对象总体是扩大趋势,隐含着一条创作群体下移的线索。由“辞人”到“赋家”与由“诗人”到“诗家”路径基本一致,这种趋同性当然是由文学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但彼时经学虽不复至高无上之地位,其影响亦不可忽视。谭德兴就说:“(魏晋南北朝)文学从对经的依附中获得发展的养分,并通过对经学理论话语的直接转化,构筑文学独立发展的理论、方法与范畴。”[31](P13)其次,上述“迟滞性”与此论“趋同性”还表现出,赋体文学不仅长期“依经立义”,对诗体也有着依附关系。进一步看,这或许说明迟至“赋家”称谓确立前,赋体文学虽在文体上获得独立,但并未在创作观念和批评观念上真正独立。迨至唐宋,诗赋二体作家称谓皆得以确立,“诗人”又派生出“诗客”“诗翁”等称谓,而“赋家”以下虽有“词赋家”“辞赋家”等,然终不及诗人之称流衍广布。这一方面反映了赋体文学确实不如诗体兴盛,另一方面或许也说明赋的创作群体虽亦下移,然较诗而论,其速率极缓,赋的创作仍有着较高的门槛。向上溯源,最早“赋家”称“家”或许是解释这一现象的密钥。
三曰为何称“赋家”而不是“赋人”。既然“赋家”称谓的演变与“诗人”有诸多趋同,那么为什么没有仿照“诗人”直接称“赋人”?况且“文人”“词人”等都沿用了称“人”的称谓模式,为何独赋称“家”?需要说明的是,早期“辞人”确实曾指代辞赋作家,但一来多含贬义而没有被广泛接受,更重要的是,“辞人”称谓不能旗帜鲜明地说明作家专长于“赋”。从文体学角度看,“辞”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文体,曹丕、陆机、刘勰等在论述文体时都没有提出“辞”一类。不过,倒是有不少先例表明,古人在论述甲骨卜辞、祝词、颂词、讼词、楚辞、辞赋等概念时,都曾称它们为“辞”。由此来看,“辞”或许是一个更高层级涵摄诸多文体的复杂概念。那么,就不难理解后世“辞人”称谓指向芜蔓的问题了,因为“辞”本身就指向多种文体。至于“赋家”称“家”,则大抵有两条线索可供考察。一是“赋家”称谓依托学术之“家”。许结称:“无论赋含学理,抑或赋写学术,赋的学术化倾向之明显,亦非它体所及。”[32](P82)先秦两汉学术百家争鸣,经学、子学影响巨大,辞赋的产生与发展自然亦受其沾溉。彼时的赋家,如王褒、扬雄、班固、张衡等,皆具有良好的学术背景。简宗梧即认为:“儒家泰半兼赋家,而赋家兼为诸子十家者,几乎全是儒家。”[33](P119)这正是从作家身份角度点明了辞赋与学术关联紧密。唐宋逮清,科举试赋重经史之义,辞赋创作对学术水平的要求借由科举制度不断提高,不少作品具有很强的学理性,甚至可径视作学术著作,如《述书赋》《事类赋》《文者贯道之器赋》《四书类典赋》等等。刘熙载《艺概·赋概》称“赋兼才学”[34](P101),“才”自然指作家的天赋才气,“学”即指学问、学术,亦说明“学”是构成辞赋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二是“赋家”称谓昭示职业之“家”。辞赋创作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作,不仅要求作者学殖深厚、拥有慧心巧思,还要在此基础上精工钻研、苦心经营。司马相如作赋冥思数百日乃成,扬雄竭智至于暴病一年,梦到“五脏出地”,张衡《二京赋》更是穷十年之功才作成。正是因此,魏收才称:“会须能作赋,始成大才士。”[35](P2034-2035)这些都说明,辞赋创作有着较高的门槛,“赋家”作为一种身份、一种职业,确非常人可以达到,理应受到世人钦服。而再从文化学的视域中考察“赋家”之身份,早期天子听政之瞍赋、外交揖让的行人之赋、科举制度下围绕试赋产生的专门化人才等,更是无不透露出辞赋创作职业化的因革线索。
“赋家”称谓之演变,从独特的角度反映了辞赋文学源起、鼎新的发展路径,体现了辞赋文学传播、流布的接受过程,揭示了辞赋文学文体批评的厘革动向,在辞赋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