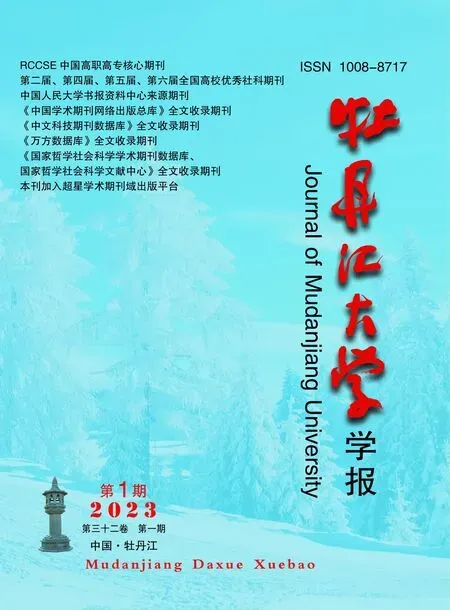《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的被凝视与反凝视
2023-03-21朱冰娴
朱冰娴
(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引言
《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是福克纳最负盛名的短篇小说,小说以倒叙、打乱时序的方式展现了南方贵族小姐爱米丽被美国南方社会、父权社会全方位凝视的悲惨的一生。小说叙事视角多变,主要以“我们”这个第一人称复数叙述为主要叙事视角,故事的内容主要是通过“我们”来凝视爱米丽进行的,因此,对于“我们”是谁,作者为何以“我们”的视角叙述爱米丽的一生以及凝视爱米丽的过程是值得探讨的。首先,需要确定“我们”的范畴。小说的五部分都提到了这一主体,显而易见,“我们”包括了全镇的每一个人,无论是政治当局、所有的妇女们,还是爱米丽的父亲都是南方社会的成员,而“我们”的一举一动正是南方社会对爱米丽“监视”的缩影。“美国著名的‘非自然叙事学家’布莱恩·里查森(Brian Richardson)指出第一人称复数叙述‘是表达集体意识的绝佳工具’”[1]88,因此需要看到小说中作为集体意识的凝视对爱米丽悲剧命运的影响。
“凝视”(gaze) 是当代视觉文化研究的关键词,字面意思指“注视”“长时间看”,“是一个双边术语,同时凸显凝视的人和被凝视的人”[2]5,也就是涉及主体和他者的关系。在《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明显地存在主体与他者,即爱米丽与“我们”的互动关系以及两者互相建构的关系。爱米丽的一生不仅作为欲望的投射对象被南方社会的主体“我们”凝视,还被作为南方贵族权威的父亲建构自我,从而永远失去自我。虽然她曾对这样的凝视进行反抗,以爱上工头荷默·伯隆的方式反抗父亲生前对她婚姻的束缚以及“我们”对身为贵族的她的门当户对的婚姻的期待,然而这样的反抗依然是在南方社会的注视之下,最终也是失败的,甚至于在死后也被凝视,永远禁锢在南方社会的文明之中,成为一朵被社会全方位凝视的凋零的玫瑰花。可以说,凝视的行为贯穿全篇小说,无论是被凝视还是反凝视都值得探讨,本文即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借鉴后结构主义大师米歇尔·福柯和精神分析学的代表拉康等的凝视理论对福克纳《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爱米丽的被凝视与反凝视进行解读。
一、“我们”的凝视——欲望的投射与规训
故事背景发生在美国南北内战之后,北方资本入侵南方社会,南方种植园经济崩溃的时刻。传统的南方社会构建出了“骑士”和“淑女”的文化道德体系,在奴隶制种植园经济体系之中,“骑士”是守护“淑女”的,“淑女”则成为“骑士”的精神力量,依附于男性得以生存。这样的文化不仅被南方贵族所认可,还内化于普通平民的精神世界之中。“骑士”们天然地认为自己有保护“淑女”的义务,更应该确保“淑女”的高贵与纯洁。南方的失败让“我们”沉湎于过去的贵族时代,因而将保持南方传统的希望寄托在出生于没落贵族家庭的爱米丽身上,小说开始即说爱米丽是杰斐逊全镇的“纪念碑”,而这种荣耀捆绑了爱米丽的一生。
小说第一节提到“爱米丽小姐在世时,始终是一个传统的化身,是义务的象征,也是人们关注的对象”[3]41,开篇就点明了爱米丽作为南方传统的代表被全镇的人“我们”所凝视,因而她的一举一动被“我们”监视。凝视是带有欲望的,拉康认为凝视背后蕴含对欲望的投射[4]95,因此,凝视是充满着欲望与幻象的,看的过程中匮乏与欲望不可分割,观看主体通过观看希望获得欲望的满足。[4]95可以说,“我们”不仅是被南方社会凝视的他者,也是凝视爱米丽的他者,作为他者,不只是从属于主体,还建构了主体,“我们”将重建南方传统的欲望通过“凝视”建立在“淑女”爱米丽身上,所以说,不难理解当几个人向法官斯蒂芬斯申诉爱米丽家中飘出难闻的气味时,四位参议员为确保爱米丽“淑女”的高贵,在午夜时分像夜盗一样潜入爱米丽家的地窖处,在地窖和所有的外屋撒上石灰以去除臭味,从而保护“淑女”的名节,建构他们理想当中的“淑女”形象。而这样的欲望投射也必然隐含着对爱米丽的监视,从而达到建构他者的目的。
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为讨论凝视提供了关键性的空间意象。“他以英国哲学家边沁(Bentham)设计的‘全景敞视监狱’作为现代社会建制的隐喻来说明现代社会是如何运用无所不在的注视/监视以实施对身体和心灵的规训的”[5]9,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处于无形地被他人凝视的处境,而这样的凝视背后是一种监视,这种持久的、无所不在的监视规训着现代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从而构成一个监视社会。可以说,南方社会就是这样一个“全景敞视监狱”,而“我们”中不论是全镇的男人或妇女,对爱米丽从小到大的关注,小到穿着、仪态、纳税、房屋的气味,大到婚姻,这种持久的、无所不在的凝视正是代表着南方社会对爱米丽的监视和规训,其中最能体现出“我们”对爱米丽规训的事件即是对其婚姻的干涉。
爱米丽爱上荷默·伯隆这件事对于“我们”来说非同小可。荷默只是建筑公司的工头,在身份上与爱米丽相差悬殊,况且只是一个拿日工资的不同于贵族的没有遗产的人,加上他又是一个北方人,因此,“我们”认为这对于贵族小姐来说并不是什么“贵人举止”,深信这段爱情使她堕落。基于南北战争中因南方损失惨重而导致的对北方的仇恨,和荷默喜欢与男人来往的同性倾向以及无意于成家的态度,后两者都被受清教传统影响的重视婚姻、反对同性恋的南方社会所不认可,男子汉不想干涉,因此,“我们”中的妇女迫使浸礼会牧师拜访爱米丽,然而爱米丽和荷默在下个礼拜又驾车出现在街上,这一切说明宗教力量的失败。第二天牧师夫人又写信告知爱米丽的近亲,借用家族力量干涉爱米丽的婚姻,这不仅是南方社会对爱米丽的凝视,也包含了男权社会下女性对爱米丽的凝视。而这些凝视,寄托着“我们”对南方社会贵族的希望,因而除了把这样的欲望投射到爱米丽身上外,也通过不断地规训爱米丽的行为、生活来实现,这一切导致了爱米丽这朵玫瑰花的渐趋凋零。
二、父亲的凝视——隐在的权威与主体建构
同样的,作为南方贵族的一家之主,爱米丽父亲的主体行为及形象是通过“我们”的凝视才得以建构的。爱米丽的父亲不仅是家中的权威,更是南方社会权威的代表,他的权威由作为他者的“我们”建构,他则将这种权威投射到爱米丽的身上,以这种权威强制、干涉着爱米丽的婚姻和全部人生。
小说提到,在我们的“凝视”下,这家人就是一幅画中的人物:身段苗条、穿着白衣的爱米丽立在背后,她父亲岔开双脚的侧影在前面,背对爱米丽,手执一根马鞭,一扇向后开的前门恰好嵌住了他们俩的身影。[3]45这里“马鞭”就是权威的象征,代表着父亲对爱米丽从小的规训与凝视,“凝视是直接的观看主体的构建”[2]9,父亲的凝视不仅建构了爱米丽的主体,也成为爱米丽悲剧人生的成因。
在我们眼中,父亲的性格三番五次地使爱米丽作为女性的一生平添波折,而这种性格仿佛太恶毒,太狂暴,还不肯消失似的,[3]49即使在父亲死后,其在生前所建构的权威依然化为隐在的权威凝视着爱米丽。正如父亲在生前赶跑了所有的青年男子的行为一样,爱米丽也赶走了一切来拜望她的人,父亲的离去意味着建构其主体的他者的消失,为了确证自我,她只能死死地拖住这给予她一切又抢走一切的人。
然而父亲的死亡并不代表父亲凝视的消亡,爱米丽依然处于被凝视的话语之中,父亲作为南方社会的成员也包括在“我们”之内,在世的“我们”的凝视仿佛也是对爱米丽父亲凝视的延续。父亲留给爱米丽的遗产仅仅是这座与周遭格格不入的带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特征的房子,荷默死后,爱米丽将自己永久地困在这座房屋里,它不仅是父亲隐在权威的代表,更是意味着父亲对爱米丽剩余人生的凝视。更可悲的是,在爱米丽的丧礼上,“停尸架上方悬挂着她父亲的炭笔画像,一脸深刻沉思的表情”[3]50,父亲的炭笔画像在第一节参议员们拜访爱米丽时即已出现,而它又出现在爱米丽的丧礼上则意味着女主人公从出生到死亡都注定逃脱不了父亲的凝视和权威。
在父亲这样一种隐在权威的凝视背后,是如米歇尔·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指出的:“毋宁说,正是凝视建构了具有不可化约性的个人,因此我们才有可能围绕着它组建一种理性语言”。[2]7爱米丽父亲生前对她的凝视与规训是由南方传统社会或者说代表着南方传统社会的“我们”的凝视所构成的,那么,围绕着凝视对象所组建的理性语言和理性力量支配着看和被看的主体,因此,不论是爱米丽、爱米丽的父亲或者“我们”都是被南方社会所凝视、建构的,其中,最大的受害者则是爱米丽。
三、反凝视的失败——理想自我与主体的消亡
“如果说人一出生就受到多层凝视——他人、社会、权力,那么两性中女性不仅仅和男性承受同样以上凝视,还受到男性和其他女性的凝视,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女性在凝视中受到更多的约束。”[4]95由上可知,爱米丽的一生是一直被父亲、全镇的“我们”以及南方社会凝视的,她的主体也是由我们所建构,在这种凝视之下,爱米丽虚构了理想自我,即南方社会的纪念碑。她一直生活在这样的话语体系之中,因而她拒绝了交税,拒绝了在门口钉上一个金属门牌号和邮件箱等等这些被北方资本主义入侵的痕迹,与时代隔绝、活在过去,显得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
直到她遇见了荷默,内心的自我意识才被逐渐唤醒。这个与她有着天壤之别的男子,性格开朗,全镇的人他都认识。他活在人群的中心,身上具备北方工业文明的包容与开放的特征。爱上荷默成为爱米莉一生中唯一一次叛逆父亲、“我们”和南方社会的机会,她不顾宗教、家族和社会力量的干涉,以这样一种自由恋爱的方式反抗“我们”对她的凝视、父亲对她的规训,这更是主人公现实自我对理想自我的摧毁。
然而荷默的存在却使得爱米丽在理想自我的凝视之下摧毁了现实自我。在小说里,在“我们”的凝视下,见证了每逢礼拜天下午爱米丽和荷默乘着漂亮的轻便马车驰过的场景,她昂着头,荷默歪戴着帽子,嘴里叼着雪茄烟,戴着黄手套的手握着马缰和马鞭。文本第二次提到的“马鞭”就是荷默手中所握的,可以说它代表了他对爱米丽的凝视和规训,而这种凝视是从爱米丽出生起即有的。当她的爱情被“我们”凝视,被近亲干涉,被荷默背叛,最终她被这一切激化了。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指出:“在任何凝视中都有一个对象——他人作为我的知觉领域中具体的、或然的在场。这个在场使我产生羞耻、焦虑等情绪,我凭借此类情绪把握到自身‘被凝视的存在’”[2]6,理想自我的死亡使得爱米丽牢牢抓住荷默这个能够建构她主体的他者,然而在这个身上寄托着爱米丽唯一的希望的人却无意与她成婚,爱米丽为了把握到自己的存在,为了反抗这种从一出生以来就有的凝视与规训,她选择了以砒霜毒死荷默的方式将他永远留在身边。
总体来看,爱米丽的反抗是失败的。拉康认为凝视中的视觉行为会影响到主体的自我身份和认同。实际上,在爱米丽被凝视以及建构自我的同时,也是她自己认同这样的身份与主体的过程,因而,在荷默被杀害的背后,她仍然离不开这种身份认同,即南方贵族多年养成的传统中那种极端自私、高傲、偏执,为达到某种目的不择手段的残忍,因对这样一种传统与身份的认同,她杀害了荷默又与其尸体同床共枕多年,以一种近乎变态的方式留住自己的爱情和反抗“我们”对她婚姻的凝视与期待。可以说,爱米丽是用她所认同的方式,即自己所反抗的传统来反抗“我们”的凝视,这种反抗的方式和对象在本质上并没有改变,从这一方面来说她依然被禁锢在“我们”的凝视之下。从另一层面来说,当主体自我中的某些东西不符合理想自我时会出现挫败感、负罪感,“而负罪感又会衍生出自我惩罚的需要,从而导致以自身为对象的施虐和自我毁灭等病态现象。”[6]91被视为是纪念碑的爱米丽一向是“怪癖乖张”“冷酷高傲”“像是一尊偶像”,荷默的死意味着她现实自我和主体的死亡,荷默死后,她又回归到被“我们”凝视的境地。她虽然把作为对凝视反抗的产物荷默永远锁在楼上的房间,但最终她也将自己永远封闭在了象征着父亲权威、被“我们”凝视的四方形大木屋中,“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3]49。
凝视他人就是被他人凝视,在“我们”的凝视中,“不时我们在楼底下的一个窗口——她显然是把楼上封闭起来了——见到她的身影,像神龛中的一个偶像的雕塑躯干,我们说不上她是不是在看着我们”。[3]50由此可见,被“我们”凝视的爱米丽在余后的日子中也通过窗口凝视“我们”。正如齐泽克在《斜目而视》中分析的投向窗外的视线与监视是主体唯一感到安心的地方。需要指出的是,监视并非就是凝视,凝视是监视之下的隐形结构,此凝视穿透了表面的监视或者说窥视行为,既使欲望现身(“这是‘我’要的”),又破坏了它(“‘我’到底想干什么”)[2]11,爱米丽在反凝视失败后退回到父亲遗留的房子里,她的欲望只能通过窗口来实现,而这样的欲望却恰恰意味着她理想自我和主体的死亡。或许让爱米丽能够安心的唯有这个“全景敞视监狱”本身,因此在最后,她自愿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慢慢凋谢,慢慢死亡。
四、结语
福克纳的短篇小说《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以倒叙、打乱时序的叙事模式刻画出一位被美国南方社会、父权社会全方位凝视和规训的女性形象。南方贵族小姐爱米丽的一生不仅被寄托着重建南方的欲望的南方社会的主体“我们”凝视与规训,还被作为南方贵族权威的父亲建构理想自我,从而永远失去自我。直到遇见荷默·伯隆,才逐渐唤醒女主人公内心的自我意识,开始对这种从小到大的被凝视进行反抗,以爱上工头荷默·伯隆这种自由恋爱的方式反抗父亲生前对她婚姻的束缚以及“我们”对身为贵族的她的门当户对的婚姻的期待。然而这样的反抗依然是在南方社会的注视之下进行的,最终也是失败的,杀害荷默的背后依旧是爱米丽对南方贵族多年养成的传统中那种极端自私、高傲、迫害别人的残忍手段的认同。直到最后她依然被囿于“我们”的凝视之下,将自己永远封闭在象征着父亲权威、被“我们”凝视的四方形大木屋中,甚至于在死后尸体也被父亲的画像凝视。爱米丽最终被禁锢在南方社会的传统文明之中,成为一朵在南方社会凝视下的凋零的玫瑰花。作者正是借爱米丽悲剧的一生,给予读者以对女性、对美国社会传统与现代等各方面问题的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