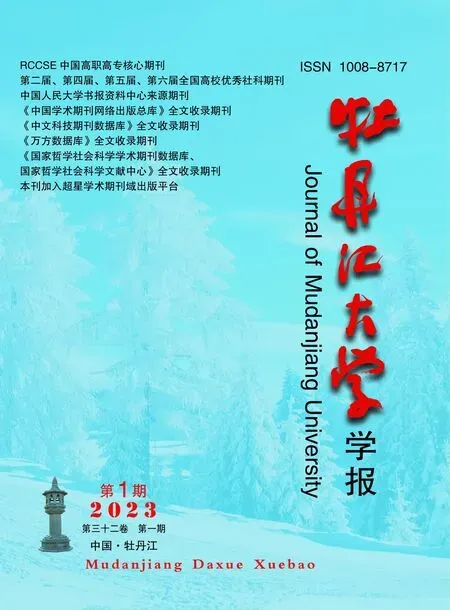语言演化视角下的象似性与任意性
2023-03-21马军
马 军
(新疆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一、引言
语言学中的象似性(iconicity)传统上只限于拟声词(onomatopoeia)这一概念。由于拟声词在各语言的词汇中所占比例很小,因此很难引起学者的注意,其研究往往也处于一种边缘状态。近年来,随着功能和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对象似性的研究又重新兴起,并扩展到语法层面(Haiman 1985; Langendonck 2007)。这给语言的任意性(arbitrariness)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后者自Saussure(1916/2002)提出以来,一直被认为是语言的本质特征之一,与象似性形成了一组对立的概念。
围绕语言的象似性和任意性问题,国内学界也一直存在争议:有的赞同象似说(理据说),有的坚持任意性的观点,有的则主张两者并存(具体争论见章柏成 2012;张延飞、刘振前2015)。与此同时,随着对语言事实理解的进一步加深以及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深层次的认知和文化机制来理解语言中形式和意义映射的本质。形式和意义之间简单的任意和非任意性划分正逐渐发展成为更加完善的多样关系(Dingemanseetal. 2015)。尽管如此,目前的研究大多是基于共时的视角,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对于探讨人类语言特征这类宏观话题而言,需要有更加宽阔的视野。鉴于此,本文拟从语言演化的视角出发,探讨语言中象似性和任意性产生的缘由、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其背后的认知机制,希望不仅能加深对语言象似性和任意性的认识,同时能促进语言和心智的相关研究。①
二、概念的澄清
在语言研究过程中,概念理解的不同往往会导致混乱和争议。因此,在展开讨论之前,有必要澄清一些概念。
1.进化与演化②
英语evolution一词本身就具有多重含义,译成中文可以是“进化”也可以是“演化”。因此,evolutionoflanguage可以译成“语言进化”也可以译成“语言演化”。然而,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聚焦于生物学角度,后者更多的是关注文化因素,因此在研究范式上相去甚远。Berwick & Chomsky(2016: 83)指出:“遗憾的是,有时存在将字面意义上的进化(基因组)变化与历史变化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现象混为一谈的倾向。”他们认为可以用更为准确的表述消除这种混乱。前者是“使用语言的有机体的进化”,后者则是“有机体语言使用方式的变化”(Berwick & Chomsky 2016: 83)。也就是说,语言能力的出现涉及进化,而一直持续的历史变化不涉及进化。
但是,并非所有的研究者都赞同这种二分法。Tallerman & Gibson(2012: 14)指出,仅依赖最近的几个基因的变异这种简单的语言进化无法解释语言能力的复杂性,文化传递(cultural transmission)在某种程度上也塑造了语言能力。Fitch(2017: 4)也认为没有必要将两者截然分开,并指出在语言进化(演化)领域存在一种不好的倾向:把某个特性挑出来作为语言的关键,认为其他特性都无关。事实上,要解决语言进化(演化)问题,需要考虑各种因素,包括文化、基因、语言变异、大脑网络构成语言语法机制的本质等(Progovac 2019)。
为了将上述两种观点区分开,本文把只涉及基因变异的生物学意义上的语言起源和发展观称为“语言进化观”,把凡是涉及到文化变化(不管是否涉及基因变异或自然选择)的统称为“语言演化观”。本文是在后者的框架内展开讨论的。
2.突变与渐变③
和进化与演化密切相关的另一组概念是“突变(saltationist)”与“渐变(gradualist)”。语言突变论中最具影响力的是Berwick & Chomsky提出的“全有或全无(All or Nothing)”观点(Progovac 2019)。他们认为,从没有语言到拥有复杂的现代语言是由于单一的小的基因变异而突然出现的(Berwick & Chomsky 2011, 2016)。也就是说,不存在所谓的前语言(pre-language)或处于没有成分结合和完全自然之间的“中间状态”的句法(Berwick 1998; Chomsky 2005; Moro 2008)。也正是因为如此,这种方法无法根据语言活化石或语言变异形成关于语言发生的具体假说(Progovac 2019)。从根本上讲,突变论认为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人类语言能力和其他物种身上所发现的任何事物之间是非连续的,完全割裂的。
相反,渐变论认为语言的出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不断的发展变化,一步步演变成为成熟、复杂的现代语言。渐变论者认为目前的语言结构对过去的语言变化和阶段有所启示,基于现在的某种更迭可以重构早期没有更迭的状态,如借助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构建原始词汇(Heine & Kuteva 2007)以及利用语言“活化石(living fossils )”构建原始句法(语法)(Brickerton 1990, 1998; Jackendoff 1999, 2002; Progovac 2015, 2016)。需要注意的是,渐变论中有的只关注语言的历史变化,不考虑基因变化或自然选择。事实上,无论是突变论还是渐变论,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人类对语言的掌控至少有一定的基因基础(Progovac 2019)。因此,要解释语言有必要把生物进化和文化演化都考虑进去。
基于语言演化的渐变论,本文认为,人类语言经历了从象似性到任意性这样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下面做详细论述。
三、语言演化视角下的象似性
Tallerman(2012: 479)指出,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早期的人类使用某种前语言(pre-language)或原始语言(proto-language)的方式交流。这种语言比完整的语言更为简单,或许含有发声(vocal)、手势(gestural)和模仿(mimed)成分。也就是说,无论语言是否起源于发声、手势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语言最初都具有模仿的性质。所谓模仿(mimesis),就是对感知的外部世界事件结构的类比呈现,它与视觉和听觉特征密切相关,是象似性的一种体现。因此,这里的象似性是指“语言(或交际)形式中的某些特征和相应的所指对象在某些感觉运动和(或)情感特征之间的任何相似性”(Perniss & Vigliocco 2014: 2)。语言的象似性起源研究主要围绕着听觉和视觉两个方面展开。
1.象似性与语言听觉起源
语言的听觉象似性体现在发声上,即语音层面,因而发声起源的象似性研究主要针对表音文字的语言。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源远流长。古希腊斯多葛(Stoic)学派为了表明语言的自然基础,认为至少语言中最初的词汇是通过拟声词或“发音模仿”来模拟自然的(Langendonck 2007: 395)。到了现代,丹麦语言学家Jesperson(1922/1968)提出语言起源的摹声说(the bow-wow theory),认为语言源自对自然界声音的模仿,例如英语中“布谷鸟(cuckoo)”就是模仿布谷鸟的叫声,“狗(bow-wow)”模仿狗的叫声,而“重击(bang)”模仿的是击打的声音。这些词传统上被称之为拟声词,通常被认为在语言中占有很少比例,因此处于边缘状态。事实上,拟声词只是在语言中广泛分布的语音象征(sound-symbolism)词的一种。④Jackendoff(2002: 131)指出,现代语言的词汇中存在一些“缺陷”词,它们的共同点就是有语音和语义,但缺乏句法。英语中的例子包括yes/no(是/否)、hello(喂)、ouch(哎呦)和shh(嘘)等,也包括动物的叫声如bow-wow和oink(猪的叫声)等。Jackendoff(2002)把这些“缺陷”词看做是“语言的活化石(living linguistic fossils)”,即语言演化早期阶段(原始语言)的残留。Cuskleyetal.(2010:389)指出,在探讨语言演化的过程中,摹声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或遭到排斥,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认为自然语言是任意的,不是象似的;二是我们使用听觉进行交际,因此只能象似性地表达和声音有关的意义。对此,他们提出不同的观点:几乎所有的语言都利用某种形式的象似性,象似性更适合较小的原始语言系统,而且手势同样可以有象似的表达。此外,与语言相关的跨模块倾向实验也支持象似性的原始口语(Cuskleyetal. 2010: 389-390)。
2.象似性与语言视觉起源
语言的视觉象似性主要体现在手势(gesture)上。⑤Armstrong & Wilcox (2007: 5)指出,认为手语可能是最初真正的语言这个观点并不新鲜。早在柏拉图的《对话录》(Cratylus)中,苏格拉底就根据词语的起源思考了聋哑人使用的手语本质,认为手势比发声更具象似性。从现代语言演化理论的角度看,语言学家们认为语言最初是源于手势,随着发声成分的逐渐增加,只是在后来人类演化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Armstrong & Wilcox 2007; Corballis 2012, 2017)。Corballis (2017: 154)指出,也许早期的语言很大程度上是由模仿的手势构成,同时伴随有无意识的咕哝声,但是我们的祖先逐步有意识地控制了这些咕哝声并逐渐规约化。随着这些咕哝声变得越来越精细,最终取代了手势,尽管手仍旧起着协调配合的作用。Armstrong & Wilcox(2007: 30)认为,在原始人类进化过程中,远远早于上呼吸道包括声道,手和上肢就具备了现代人的构造。从这点来看,有理由相信,原始人类最早的类似语言的行为涉及可见的,尤其是象似性和标示性的手势符号,尽管发声可能也是原始人交流的重要部分。象似性的手势经过仪式化(ritualization)被约定下来,逐渐形成语言(手语)。而人类的文化(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共同进化的基因)成就找到了如何将世界的视觉呈现能力转变为经济、有效的言语(Armstrong & Wilcox 2007: 133)。
这里需要注意两点:第一,手势不同于手语,但是两者有着密切的关联。手势和手语符号在手语者的话语中可同时或交替出现。通过词汇化或语法化手势也会随时间进入到手语的语言系统中(Wilcox 2019: 261)。第二,手语也是语言。长期以来,人们并不认为手语是一种语言,而是描绘性的手势,缺乏语言的特征,如语音、构词和句法(Wilcox 2019: 251)。事实上,这是一种长期形成的偏见。随着研究的不断发展,现在普遍认为手语和口语有着重要的共同特征。与口语不同的是,对于手语符号源自象似性和指示性这一点很少有人提出质疑(Armstrong & Wilcox 2007),因此象似性被认为是手语的重要特征。
值得一提的是,除手语外,语言的视觉象似性还体现在表意文字的语言中。表意文字是一种用象征性书写符号记录信息的文字体系,不直接或不单纯表示语音,例如汉字。⑥从汉字的演化发展来看,最初的象形文字或更早的图画文字就是对事物形状的描摹或直接刻画,具有很强的象似性。尽管经过数千年的演变,现代汉字跟最初的形象相去甚远,但依然留有象形文字的痕迹,如“山”“水”“日”等等。也许有人会指出,汉字是文字,不能把文字混同于语言。事实上,无论是表音文字还是表意文字,它们都属于书写系统,只不过前者是用来记录发音,所以常常就把记录的文字(词)和口语乃至语言混为一谈了。正如Chafe (2018)所指出的那样,主流语言学的研究实际上大多都是基于声音和书写的。因此,严格地讲,前面所说的基于听觉的“语言”的演化实际上就是记录语音的“文字”的演化。当然,这并非本文关注的重点,在此不做进一步讨论。
3.为什么是象似性?
从以上有关语言象似性起源的讨论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假设:早期的语言形式或原始语言,无论是口语或手语,都具有显著的象似性特征。那么,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语言源于象似性?Perniss & Vigliocco(2014)认为,象似性是人类语言三个基本特征的根基:即语言演化过程中的位移性(displacement,即描述非当前事物的语言能力)能力,语言习得过程中建立指称性(referentiality, 即学会把语言标识映射到物体或事件上)的能力以及成人语言处理的体验性(embodiment,基于我们的感觉和运动系统)。
换句话说,象似性与人类的认知密切相关。象似性的事物形象直观,容易被识别和理解,便于大脑的处理和加工。这也与人类早期的原始语言系统相适应。从语言演化的角度看,早期人类借助某种肢体的或发声的符号形式来表达概念、交流思想。在指称事物,尤其是非当前的事物时,就会通过模仿来激活相关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以牺牲外在的相似或象似性为代价,模仿被逐渐修正或被更加流线、高效的形式所取代(Corballis 2017)。此外,对儿童语言早期习得,即个体发生(ontogenesis)的研究表明,象似性在这一阶段发挥着重要作用(Monaghanetal. 2014;Perniss & Vigliocco 2014;Dingemanseetal. 2015)。当然,这并不是说象似性只存在于认知的初期阶段。作为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认知模式的反映,它自始至终伴随着我们,并发挥着重要作用。Donald(2012: 183)指出,“大量的现代文化残留证明了模仿作为一种表达模式的重要性和持久性。模仿在很多非言语的文化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如戏剧、舞蹈、歌曲、视觉艺术和肢体语言。它出现在流行文化、群体行为、广告、政治宣传和媒体之中。它是人类表现力最古老和最深厚的基础。”
如果说语言中的象似性本质上是人类认知的一种体现,那么不妨说象似性也是语言的基本特征之一。既然如此,为什么语言还具有任意性?这是因为,随着人类认知水平不断的提高,语言也会相应地随之发生变化,而任意性就是这一发展变化的结果。
四、语言演化视角下的任意性
所谓任意性,就是指语言符号的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换句话说,语言符号的形式、声音和语义之间没有任何自然的、内在的或逻辑上的必然联系。任意性的概念自Saussure(1916/2002)提出以来不仅仅被看成是语言的基本特征之一,而且成为了语言学研究的基本假设。但需要注意的是,Saussure同时还区分了语言研究的历时性(diachrony)和共时性(synchrony),并强调共时研究的主导作用。⑦这就意味着,任意性很大程度上是在共时视角下观察语言而得出的结果。但是,从历时或语言演化的角度看,语言从一开始并不是任意性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变化过程。对于任意性的产生,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加以考察。
1.对比动物行为视角
在其《言语起源》(TheOriginofSpeech)一文中,Hockett(1960)对比了人类语言和其他生物交际系统的相同和不同之处,提出了人类语言所具有的13个设计特征,任意性就是其中之一。Hockett(1960)认为这些特征是一级一级逐步演化出来的,处在上一层级的生物交际方式具有下面所有生物层级交际方式的特征或是从中演化而来。这就是说其他生物的交际方式可能具备了某些特征,但只有人类的语言具备所有13个特征,⑧例如灵长类动物的交际方式具有任意性、语义性和专门性等特征,但是缺乏人类语言的二层性、能产性和移位性等特征。Gibson(2012)梳理了前人对类人猿类似语言行为的研究,指出很多手势和大多数符号字(lexigrams)可以充当非象似、任意的符号,用来指具体的物品或动作,符合典型的象征定义。⑨但是,Deacon(1997)认为,真正的象征不仅体现在孤立的标记语境中,而且还表现在与其他象征的关系上。因此,至少有三个类人猿,即Kanzi、Sherman和Austin在使用他所定义的象征。尽管如此,由于这些类人猿的研究基本上是在人工驯养的环境下实施的,接受了相关的语言训练,而且所掌握的任意性符号也是非常有限的,与人类语言灵活的任意性相去甚远。
2.生物学视角
Brandon & Hornstein(1986)在心理学和生物学框架内对传统的象似(icons)和象征(symbols)概念重新做了界定,认为从象似到象征构成了一个连续统:一端是感知象似(perceptual icons),另一端是象征,中间为系统发生象似(phylogenetic icons)。从演化的视角看,绝大多数已知的动物交际方式处于感知象似和系统发生象似之间,而人类语言是系统发生象似过渡到象征的产物。这是因为动物的象似交际系统满足不了表型遗传机制(phenotypic inheritance mechanism),而人类语言具备了表型遗传机制的3个显著特征:传递信息、表达各类无限信息以及非刺激性信息的能力(Brandon & Hornstein 1986: 184)。可以看出,与Hockett强调动物交际系统和人类语言之间的连续性不同,Brandon & Hornstein认为动物的交际方式只限于象似性,而人类的语言跨越了象似性,具备了任意性(象征性),因此任意性(象征)是人类语言所特有的。当然,任意性的产生除了自然选择的因素之外,文化演化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3.文化演化视角
从文化演化的视角来看,规约化(conventionalization)在任意性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这里的规约化是指通过惯例而不是外在的相似将符号(手势或言语)与概念相连并维持的过程 (Corballis2017: 173)。可以想象,随着人类认知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一方面抽象事物和复杂概念的表达仅仅依靠象似性的模仿是难以胜任的;另一方面,交际过程中的经济、快捷要求也对象似性形成挤压,而规约化则使得符号简化,象似性成分逐渐减少,同时任意性日益凸显。Darwin(1872/2009:300)在《人与动物的情感表达》(TheExpressionoftheEmotionsinManandAnimals)中说到:“出于快速的原因,聋哑人和原始人在实践中尽可能压缩他们的符号。因此,它们的自然来源或起源常常变得模糊或完全消失。发出的言语也是如此。”
Burling(1999)指出,理据性符号的透明性似乎赋予它们超越任意性符号的明显优势,但规约性和任意性最终总是胜出,这说明它们一定有重要的优势,来弥补理据的丧失。那么,那些优势是什么呢?
4.任意性优势
Dingemanseetal.(2015)的研究表明,尽管非任意性(象似性和系统性)在学习、交际和范畴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是任意性对交际而言具有关键优势。第一,一定程度的任意性对信号的灵活传递而言似乎是必不可少的。任意性摆脱了形式和意义之间的一一对应,开始把信号或信号的一部分当做离散的结构单元来使用,使二层性(duality of patterning)成为可能(Hockett 1960; Nowak 1999);第二,任意性能够表达凭借直接感知所无法表达的概念(Clark 1998);第三,在完全是象似性和系统性(systematicity)的语言里,相似的形式表达相似的意义会造成很大的混乱。实验研究表明,系统性会妨碍不同所指对象的区分,而任意性则能起到促进的作用(Monaghan et al. 2011)。对任意性和象似性进行比较的一项最新研究认为,任意性具有适应性因为它使语言信号变得高效且容易辨别(Perniss & Vigliocco 2014);第四,对语言认知功能的研究表明,任意性标识有利于类与符(type/token)差别的学习,可能是因为象似形式会激活更为具体的实例,而任意形式激活更加广泛和抽象的呈现(Edmiston & Lupyan 2015)。另一方面,从语言习得的角度来看,研究表明,系统性在语言习得早期阶段的词汇学习中作用显著。随着词汇的发展,系统性减少,同时任意性增强以促进交际的表达性和有效性(Monaghanetal. 2014)。
任意性所具有的这些优势有助于人类在语言使用的过程中能够突破象似性的局限,使语言更具创造性,在交际过程中能更加灵活地表达思想。也许正是因为任意性和象似性之间存在的明显差异,往往使得语言学家认为任意性是人类语言的基本特征,而不是象似性。比如,Pinker(1999: 2)指出,“拟声词和语音象征当然存在,但它们只是更为重要的符号任意性原则的特例。否则,我们从直觉上就能理解每一门外语的词汇,永远不会需要一部词典!”同样,Goldberg(2006: 217)说道:“除了相对罕见的联觉音组的情况外,......一门语言选择表达特定概念的特定语音形式......通常来说是完全任意的。”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专注于共时的语言现象,但忽视了历时演化的因素;二是只注意到了语言中典型的象似现象,但却忽略了从象似性到任意性之间的连续性,或者说以不同形式广泛地存在于语言之中的象似性。当然,如果旨在强调人类语言与动物交际方式的不同,可以把任意性视为是人类语言的设计特征之一。
五、语言符号的连续性
既然任意性是由象似性逐渐演化而来,这就涉及到语言的连续性问题。这就如同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中某一语言项A向B转化时不是瞬间完成的,中间还有A和B长期共存的状态。同理,从象似性到任意性的转变过程中,一端是象似性,另一端是任意性,中间则是具有不同抽象程度的象似性。Peirce(1931/1974)关于符号的划分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他区分了三种符号:象征(symbol)符号、指示(index)符号和象似(icon)符号。“象征符号依据规定,通常是一般概念上的联系来指某个客体,象征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是指这一客体。”(Peirce 1974: 2.249)自然语言中的大多数词汇都是象征符号,或“规约”符号,也就是Saussure所说的“任意性”符号;“指示符号依据是否受到了某个客体的影响来指这一客体。”(Peirce 1974: 2.248)在指示和客体之间存在一种因果关系,如烟就是火的指示。火灭了,残留的烟不再具有指示作用。自然语言中“这”“那”“这里”等指示词就属于此类。但是,由于它们都是约定的符号,因此这些指示词也是象征符号(Langendonck 2007: 397);“象似符号只根据符号所拥有的与某个客体一样的特征来指这一客体,不管此类客体是否存在。”(Peirce 1974: 2.247)需要强调的是,这三类符号很难以纯粹的形式出现,大多数符号都是这三类的混合(Langendonck 2007)。
聚焦于象似符号,Peirce (1974)又划分出形象(image)、隐喻(metaphor)和图样(diagram)这三个次类。形象属于典型的象似,作为符号它通常在感觉特征上与所指对象相似。感觉特征可以是视觉上的如相片、雕像或绘画等,也可以是听觉上的如音乐。在自然语言中形象象似的突出例子是拟声词;隐喻象似通过在另一事物中的对应特点来呈现某一符号的代表性特征,例如狮子代表勇敢的人;图样象似是指符号本身并不一定与所指对象相似,但是符号系统排列的关系反映出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例如,在凯撒的名言“我来,我见,我征服”(veni, vidi, vici)中,三个谓语动词的顺序就体现了动作发生的时间顺序。同样,这里需要再次强调连续性的问题。Langendonck(2007: 398)认为,从几乎纯粹的形象象似到“纯粹”的图样象似存在一个渐变过程。
Christiansen & Chater (2016: 138)指出,除二十世纪外西方学者们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的焦点是形式和意义之间映射的系统性(systematic)程度,而不是任意性。系统关系可以体现为绝对象似性(absolute iconicity),即语言特征直接模仿语义的某一方面,如拟声词;同时也可以表现为相对象似性(relative iconicity),即在没有模仿的情况下相似的音和义之间存在统计规律,如bouba和kiki效应。⑩Perniss & Vigliocco(2014)认为,象似性映射存在不同程度的抽象性(abstractions),也就是说,象似形式和其所指对象在相似性上存在程度差异(从更直接到更间接)。例如英语中拟声词meow(猫叫声)或者是和厨师这个词相伴随的“搅动”动作就是对意义或所指对象的直接模仿。因此,这些形式和意义的映射显示了较低的抽象性。但是,其他类型的象似性映射则更加的间接,因而更抽象或图式化(Meir 2010)。进一步说,任意性实质就是象似性的极端体现。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象似性表达具体,任意性表达抽象,从象似性到任意性也是隐喻延伸的结果,因为抽象的概念通常是借助隐喻延伸来表达的(Lakoff & Johnson 1980)。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自然语言符号中,从象似性到任意性构成了一个连续统。当然,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共时状态下呈现出来的特征。事实上,这种连续性显然是在语言逐渐演化过程中形成的。Brandon & Hornstein(1986: 171)指出,“从共时的角度看,符号与所指的关系似乎是完全任意的,也就是纯粹象征式的。然而,从历时的角度看,总是能追踪到符号和其所指的演化关系。”语言的这种演化与人的认知发展密切相关,如果说象似性体现了人类的认知水平的初期阶段,那么任意性则是高级阶段的认知体现。当然,它也是人类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或者说文化演化过程中选择性压力的结果(Christiansen & Chater 2016)。
六、结语
共时视角下的人类语言特征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盲人摸象,每个人只关注于自己看到的一面,但忽视了对事物整体的把握。因此,有必要跳出共时的框架,从更加宏观语言演化的视角来审视象似性和任意性问题。从考察的结果看,人类语言经历了一个从象似性到任意性的发展变化过程。早期的人类语言,无论是口语还是手语,应该以象似性为主,之后象似性逐渐削弱,任意性日益增强。这种转变实际上是人类认知水平不断发展的反映。人类早期的语言系统简单,表达的概念具体而形象,象似性在这个时候发挥着关键作用;随着人类认知水平的不断提高,语言越来越复杂,表达的概念也更加抽象,任意性的优势日益凸显。有关儿童语言发展(个体发生)的研究也证明了象似性和任意性在儿童语言学习的不同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因此,可以说象似性和任意性都是人类语言的基本特征。但是,如果要把人类的语言特征与动物的交际方式作比较,应该说只有任意性才是人类语言所具有的特征。因为从语言生物演化的角度看,只有人类的语言突破了象似性的限制,过渡到了任意性。需要注意的是,强调当前语言的任意性特征,并不意味着象似性不再起作用或者就此消失。正如前文所述,从象似性到任意性演化的结果就是形成了一个连续统,甚至可以把任意性看做是象似性演化所产生的的极端形式。因此,作为人类的基本认知方式之一,象似性依然以不同的形式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生活(包括语言)之中,并积极地发挥着作用。
Dingemanseetal.(2015)指出,当前关于语言符号任意性的思考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长期以来所持的词汇形式和意义之间的任意观正逐渐发生改变,开始认识到语言中任意性和非任意性两者都具有的重要性。本文就是朝着这一方向所做的努力。注释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象似性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既包含语言符号(能指)与外部事物(所指)之间的关系,也包含语言系统本身所具有的理据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前者是具体的象似性,后者是抽象的象似性。具体论述见正文。国内学者杨烈祥、伍雅清(2019)区分“演化”和“演变”,“演化”相当于本文的“进化”,“演变”相当于本文的“演化”。关于突变论和渐变论的详细论述见Progovac(2019)和杨烈祥、伍雅清(2019)。Akita & Pardeshi(2019: 1)指出,典型的象似性的语音象征词在非洲语或普通语言学中被称为摹拟词(ideophones)、在日本语言学中被称为仿音词(mimetics或giongo/gitaigo)、在南亚和东南亚语言学被称 为表达词(expressives)。他们把拟声词(onomatopoeia)归入摹拟词。gesture通常被翻译成“手势”,事实上,它不仅包含手势还包括脸部表情、姿势以及其他肢体动作。对手势的定义和讨论见Wilcox(2007)。对于汉字的性质,国内外学者也存在一定的争论,但没有大的矛盾,具体见李运富、张素凤(2006)。Stawarska(2015: 93)指出,从Saussure的手稿看,他既反对语言研究的完全共性性,也反对完全的历时性。而是《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编辑者们把共时性研究视为唯一的科学客观方法。 Evans(2014)认为Hockett提出的这13个特征,包括后来补充的3个特征都不是人类语言特有的。这里的象征是指Peirce(1931/1974)对符号的定义,他所说的象征(symbol)就是指符号的任意性,不同于前文谈到的语音象征。相关研究表明,bouba更容易和圆形物联系在一起,而kiki更容易和尖刺物联系在一起。
注释:
①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象似性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既包含语言符号(能指)与外部事物(所指)之间的关系,也包含语言系统本身所具有的理据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前者是具体的象似性,后者是抽象的象似性。具体论述见正文。
②国内学者杨烈祥、伍雅清(2019)区分“演化”和“演变”,“演化”相当于本文的“进化”,“演变”相当于本文的“演化”。
③关于突变论和渐变论的详细论述见Progovac(2019)和杨烈祥、伍雅清(2019)。
④Akita & Pardeshi(2019: 1)指出,典型的象似性的语音象征词在非洲语或普通语言学中被称为摹拟词(ideophones)、在日本语言学中被称为仿音词(mimetics或giongo/gitaigo)、在南亚和东南亚语言学被称 为表达词(expressives)。他们把拟声词(onomatopoeia)归入摹拟词。
⑤gesture通常被翻译成“手势”,事实上,它不仅包含手势还包括脸部表情、姿势以及其他肢体动作。对手势的定义和讨论见Wilcox(2007)。
⑥对于汉字的性质,国内外学者也存在一定的争论,但没有大的矛盾,具体见李运富、张素凤(2006)。
⑦Stawarska(2015: 93)指出,从Saussure的手稿看,他既反对语言研究的完全共性性,也反对完全的历时性。而是《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编辑者们把共时性研究视为唯一的科学客观方法。
⑧Evans(2014)认为Hockett提出的这13个特征,包括后来补充的3个特征都不是人类语言特有的。
⑨这里的象征是指Peirce(1931/1974)对符号的定义,他所说的象征(symbol)就是指符号的任意性,不同于前文谈到的语音象征。
⑩相关研究表明,bouba更容易和圆形物联系在一起,而kiki更容易和尖刺物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