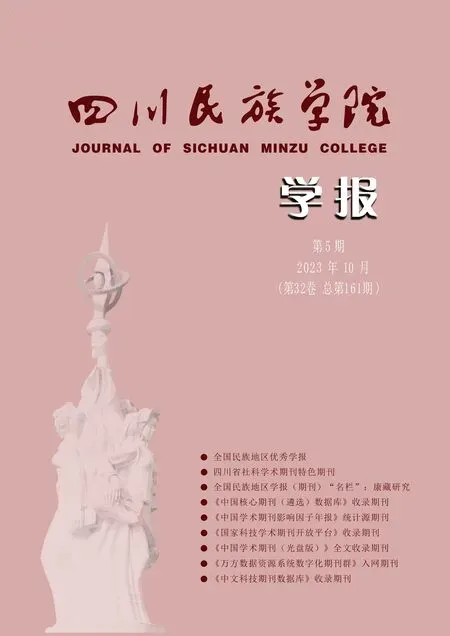清末驻藏大臣之选任困境
——以联豫赴藏为中心的考察
2023-03-15何文华
何文华
(四川师范大学,四川 成都 610064)
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初一(1905年4月5日),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在巴塘遭戕害,十八日后雅州知府联豫由四川总督锡良转上谕,获授副都统衔,调任驻藏帮办大臣。现有研究多关注联豫驻藏新政,且相较于同期受任赴巴塘平乱的赵尔丰、与英协商藏事的张荫棠,联豫筹藏成效又为后世肯定不足,还有观点认为张、赵二人短期离藏和未能入藏都与联豫刻意排挤有关。(1)如吴丰培先生在《联豫驻藏奏稿》“跋”中写道,“(联豫)因忌张荫棠之娴于外交,才出其上,构于那桐,挤之出藏”。车明怀在《晚清变局中的驻藏大臣》一文中,认为“赵尔丰做事操切,加之驻藏大臣联豫极力阻挠,赵尔丰未到藏就被朝廷调回。”(见《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3 年第 1 期,第43 页。)本文主要考察联豫受任至光绪三十二年底(1906年)升任驻藏大臣兼帮办大臣的赴藏早期经历,认为联豫的出身、宦历川边的条件符合清朝选任驻藏大臣的传统标准,其洋务经历又满足清末藏事革新的基本需求,以联豫赴藏是清中央在藏事危机下的合理抉择。然而,面对新任,联豫从一开始就多显无奈,赴藏途中也多延宕。这是清末川藏道途梗阻、驻藏大臣筹藏缺乏人力、物力支持的客观限制,也是同期赴藏群体的普遍心理。至清末,从驻藏大臣选任为始,由其入藏布展的西藏施政实已陷入困境。
一、清廷以联豫赴藏的传统选任路径
藏地边疆稳定对清王朝统治意义重大,作为古代最后一个集权王朝,清政府在汲取前朝治藏经验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系统的治藏方略,其中遣大臣驻藏是清政府经不断调试而独创的方略之一。驻藏大臣从最初防备准噶尔,监控藏情,到“总揽事权,主持藏政”,至清末在藏事危机中维护中央主权,始终是代中央“职掌”西藏人事、军事、外交等事务的关键人物。
驻藏大臣须全面客观地将西藏信息传至北京,供中央遥控决断藏事,但西藏距北京有万里之遥,至清末都未完全开通直达邮电系统(2)“川康电线清光绪末年架设。系沿官道逾相岭至打箭炉,由打箭炉沿南路经理塘巴塘至昌都,由昌都循官道至拉萨,拉萨至江孜一段尚未修通,全藏乱已作。时理塘以西之电线,概被乱番割毁。”(见任乃强著《川康交通考》,第129、139页。),遇紧急事件往往来不及先行奏明再请旨执行,因此在清朝地方大吏“一面具奏,一面实行”制度下,无论为清中枢提供可靠信息,或代中央紧急处理藏事,清廷对驻藏大臣“除了以勤政爱民这一标准衡量外,更大程度上是看其是否对清中央忠诚”。[1]由于旗籍子弟与清朝统治休戚与共,以旗籍人员赴藏是清朝选任驻藏大臣的重要标准之一,“清廷奉派驻藏的大臣,主要出自满族、蒙古族和汉族;就人数而言,满族人最多,其次为蒙古人,汉人则极少”“任官用人具有种族与旗籍上的差别,是清朝官制的一大特色。驻藏大臣是钦派的重要官职,自然亦具有此项特色”,[2]清朝选任一百四十余位驻藏大臣,仅联豫之后短期入藏的张荫棠、温宗尧为非旗籍汉人,[3]驻藏大臣的旗籍占比明显高于其他同级官员。
联豫属内务府正白旗人,以恩荫入选笔帖式。受任驻藏帮办大臣时,联豫就在谢恩折中感怀身世,“伏念奴才汉军世仆,浙水微员,渥蒙天高地厚之恩,绝无息让涓埃之报”。[4]1抵藏不久,驻藏大臣有泰在日记中也记载了联豫的“满汉”之见,“午后惠臣由联大人处来,亦为交代事,似稍明代,然满汉之意见,仍未镕化,可不必也。”[5]675有泰离藏途中又记拉萨流传张荫棠被称为“康党”的俚语,“弁兵接藏内来信,不知为谁所发,乃俚歌一纸,大骂张憩伯(按,即荫棠),钞存以作笑话观可也”,[5]713并在写给其表弟度支部尚书溥颋的家书中特别提及,“建侯(按,即联豫)对兄言,死一康广仁,欲令八旗人均给其偿命耶?”[6]由于满汉畛域经常作为清末革命派用以宣传革命排满的重要依据,有泰因张荫棠参劾得罪,其称张为“康党”并提及联豫对“康党”的不满,均可见驻藏大臣群体在旗籍身份认同下对清朝统治的维护。得知联豫受任,更有报刊公开吁请,“闻政府以驻藏大臣均用满员,现值满汉不分畛域之际,拟参用汉员简任以资得力云。”[7]
清朝西藏与西南各省关系密切,外来势力侵藏的危机也更早被西南各省感知,从西南各省遴选驻藏人员遂成为清朝中后期的常见途径。驻藏大臣文海进藏前为贵州按察使,庆善从四川候补道赏副都统擢任驻藏办事大臣,裕钢则从四川雅州知府调任西藏粮务委员,后赏副都统衔为驻藏帮办大臣,两年后擢任办事大臣。帮办大臣桂霖由贵州贵西道赏副都统衔擢任,安成由四川候补道赏副都统衔擢任,凤全为四川候补道员。因“西藏为川蜀藩篱,与强邻逼处”,[8]四川对清朝治藏影响尤重,傅嵩炑在《西康建省记》中感叹,“夫川之东南北皆有行省以为屏藩,四方瞻望,惟此西顾之忧。故藏虽距川六千余里,舍友驻藏大臣粮员,夷情章京一员,廉俸则由川解矣,驿站则系川设矣;且藏地之拉里粮员、前藏粮员、后藏粮员、靖西同知,以及驻藏游记、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外委、兵丁亦由川省委任遣戍发给薪饷矣。是西藏对于川省有关系,故川省对于西藏负责任。”[9]
联豫赴藏前任雅州知府,处藏事最前沿。“雅处蜀之偏陬,东接邛嘉,西抚番藏南襟六诏,北控诸羌”,[10]11雅州府辖域在川省与西藏联结处,长期承担着调查藏情、管辖川边藏族民众、设汛驻防等治藏职责。《雅州府志》序即载明,“志必先列图,所以上观天文以验灾详,下察地理而知险易,雅幅员广远,直通西藏,绘图可不详乎?兹先绘星图,次刻总图,府州县各绘一图,口内土司各刻一图,巴塘、理塘、西藏慧远庙,暨夷人装束住房器械各图,其形以备参考”,[10]21其志专列西藏、川边土司等篇,明确“西域分前藏后藏,非独边塞,且属绝徼,我朝德威远播,四夷归心,是以前后藏均隶职方,咸遵正朔,故亦另列一类,详载疆域形势户口贡赋以明一统,无外之模”,[10]23并绘制前后藏地形、寺庙及由川至藏沿途山川、里程等详情。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于打箭炉新设雅州同知,职在辖关外各土司,知悉巴、里二塘直通西藏一路案情,并设塘汛于要隘处,置重兵镇守。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川督锡良奏准改打箭炉(今康定市)为直隶厅,进一步加强川边经营以援藏。雅州知府职任为联豫奠定了解藏情的基础,他在为随员张其勤著《炉藏道里最新考》作序时指出,“关内之地,虽极险阻,固人所共知而常经者,如其记也,应自关外始”,[11]387清政府以联豫赴藏也建立在其知悉一定藏情的基础上。
二、清廷以联豫赴藏的藏事改革诉求
十九世纪后期英印势力向藏地扩张,哲孟雄(锡金)、廓尔喀(尼泊尔)、布鲁克巴(不丹)、拉达克等清朝“外藩属国”逐渐被瓦解蚕食,一种“唇亡齿寒”的危机迫使比邻藏地的西南疆臣们较早参透西方以游历、通商、开矿为借口,实以侵占西藏土地和人民,并由西藏门户入侵西南的殖民本质,于是相继提出振兴藏事的意见。以丁宝桢、鹿传霖等为代表的川督,以长庚、文硕等为代表的驻藏(帮办)大臣,以陈炽为代表的京官等,对清末的西藏政策以及驻藏大臣制度都提出了建议与对策,但基于清末应接不暇的统治危机,中央与地方以及川、边、藏地方之间的差异认知,改革藏事经历了长期的讨论阶段。
庚子事变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慈禧以自己与光绪帝名义发布上谕,宣布实行“新政”,要求各级官员应“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学,军政财政”等拿出具体改革办法,后专事“新政”的督办政务处成立,由此从中央到地方的新政正式拉开帷幕,东北三省、新疆和蒙古、西藏等边疆改革被提上日程。文硕驻藏时就提出,“方今藏中急务,莫切于洋人游历通商。而一则英吉利求望甚殷,一则唐古忒拒绝尤峻”,建议“于现任章京暨曾经随往出使外洋之学生内,拣选人品端方,事宜熟练,文理通顺,字画整齐者拣选二三员,派往随同办事,以收指臂之效”。[12]驻藏大臣作为清中央派驻藏地的“钦差”,清末又承载着振兴藏事的期望,社会上更急切呼吁要员入藏,“滋悉实为商议藏事并拟派亲王出镇,一切官制悉如行省。亲王之外另派两大员以辅助之:一管理外交各事,一专司地方应办之政”。[13]
联豫生于清朝“同光中兴”时期,自幼“随侍广东”,于而立之年随洋务派干员薛福成出使英、法等国,归国后历任浙江、湖北等省,主要经办洋务事业。吴丰培在《联豫驻藏奏牍》跋中记,“联豫曾随薛福成出使欧洲,以通晓洋务称”。[4]207薛福成出使在光绪十五(1889年)至二十年(1894年)年间,期间驻德大使洪钧的随员张德彝在卸任途中与联豫有过少许交集,其光绪十六年(1890年)日记内载:3月8日,“新任驻扎英、法大臣薛叔耘星使福成驾法公司‘伊拉瓦’的轮船于前日抵马赛,明日到巴黎”;10月1日,联豫约张德彝“在凯歌路之智慧阁看圆画,即前于同治丙寅所看之涨眼画”;10 月3日,联豫又约张登艾菲尔铁塔,“余等驾至第二层”等。[14]出洋的阅历对联豫产生了重要影响,有泰初见联豫就记其会数句法语,并载“联豫云,人非出洋,不能阅历。皇太后、皇上、军机大臣不知何时出洋,可发一笑”。[5]668回国后,联豫在清末政坛中留下了持办洋务的痕迹。《中华报》刊文《记驻藏大臣联豫奉命驻藏后情形》道:“联豫,满洲汉军旗人,以笔帖式援例候选同知,随薛钦使福成出使英法三年,循例保举以知府用分发浙江。未到浙江之先,鄂督张制军调湖北练目强军,不受制于张彪,毅然辞去,在浙江练武卫新军颇有声,其后得诚中丞保荐放四川”,[15]记联豫在浙江编练新军。驻藏后联豫在奏请重铸乾隆“宝藏银”折中,又述及自己“前在湖北,浙江均经办理银圆局务”。[4]18在选任联豫赴藏的上谕中,清廷强调藏事紧急,要求其直接由蜀入藏,联豫持办洋务的经验,同样满足了清末拟改革藏事的诉求。
联豫受任后,深知清廷改革藏事意图,“况朝廷注意于西藏者久,急欲经营,以时势论之,则今日之两张,其重要为何如哉”,[11]388由此提出“务实”的筹藏基本路径,“方今朝廷惩积弱之弊,废科举,讲实学,汲汲求新法,以图富强。西藏之地,为我西南数省之屏藩,俄觊觎于北方,英要挟于西方,已成岌岌可危之势,今日者使一任其腐败,而不兴实业,不施我国家保护之实权,则虽日恃口舌之辩论,文牍之往还,虚与委蛇,无益也。”[4]191抵藏之初,联豫就提出改革税制、铸造银币等财政改革计划,并编撰《新学抄本》等学务改革内容,还向噶厦政府提出“新政十条”等方案,为此,相对保守的前驻藏大臣有泰还多次讥笑联豫,认为其改革办法“系财迷之事”“可谓下乔木入幽谷办法,亦可怜可叹矣”(3)“下乔木入幽谷”典出《孟子·滕文公上》,原文为:“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幽谷者”;表面意思为从高树上下来钻进幽深的坑谷里,说明的是从良好处境转为恶劣处境的情形。引用此典,有泰主要认为联豫在藏推行新政的想法不顾及西藏现实,毫无意义。。[5]669-671后有泰因被张荫棠参劾,得到了联豫帮助,于是对联豫拟行的改革又多了几分同情,在离藏途中感叹,“谈及建侯在藏,八九月间因番间反对,诸事不成,因著急大病,回忆建侯初到,何等气焰”,[5]764可见联豫赴藏确也带来了明显的改革风气。
三、联豫对赴藏任命的应对与原因
联豫受任之际,内有西藏地方势力深涉巴塘、理塘叛乱,外有英印军队第二次侵藏正于曲米新谷大屠杀后急速向拉萨进军。《中华报》刊文载联豫受任情形,“西藏今日为英俄交伺之地,中外得之枢纽关系重大,人所共知。方意朝廷简派驻藏大臣必妙选贤君后以期巩固边疆,辑和民人”,后详文描述道:“上谕简联豫为驻藏帮办大臣颇出锡制军意外。联以疾苦之雅州府忽得肥美之成都府,欣然不知所措,徘徊于幕室中。忽一夕,家人呈电报进,口称恭喜。联不暇辨识电封所书何字,即向幕友笑言,大帅如此性急,不待我布置就忙赴任。幕友在旁瞥见电封有钦宪字样,促令开封近烛开视,则为上谕帮办驻藏大臣着联豫去。钦此。目瞪口呆、立如木鸡半晌始能言,意甚怅怨,扶掖进上房见妻妾儿女抱头痛哭。”[15]如是,联豫本以为经周璇能调任成都,却突然被告知赴藏,可谓十分悲切。
在奏谢朝廷授予驻藏帮办大臣折中,联豫两次表示惊惶,“奴才跪聆之下,感悚莫名”“才疏专对,节随四国以遄征,学愧临民,符秉一麾而出守。兹复钦承鸾命,典属乌斯,荷倚畀之自天,实悚惶于无地”。[4]1联豫还试作周旋,望清廷撤销其赴藏任职,“昔见锡制军长跪不起,乞求代奏开去差使,仍守成都。锡制军答以此次出自特恩,非疆臣所擅敢奏请,请好自为之,无多言。又欲乞将军司道代求,据诸人相见时均贺以简,在帝心指日必有大用,以塞其口。更觉局促不安。”[15]至联豫入藏三年后,《新闻报》仍刊文忆其不愿入藏情形,“联初闻恩命,惊惧丧魄,长跪于锡总督之前痛苦乞哀。求锡为奏请收回成命,锡辞以无能为力始怏怏绝望而出”,[16]最终联豫将家人留置成都,只身赴藏,但途中又多延宕。
从雅安返回成都与锡良商讨藏事期间,清廷多次催联豫就道赴任。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九月初三,上谕令“联豫即着仍行驻藏,迅速驰往,会同有泰将应办事务,悉心经理,毋失机宜”,九月二十二日,军机大臣又寄锡良上谕,令联豫“迅速驰往等”,直到十一月初十联豫才从成都启程,耗时八个月,从年中入藏较佳时节迁延至寒冬。十一月二十七日,联豫抵打箭炉,又以奏调随员丁勇、赶备乌拉和道途中断等为由,在炉关滞留百余日。“奴才抵炉以来,详查关外情形,一时断难就道,理塘巴塘一带,经大兵剿办之后,土司头人逃亡殆尽,关塞萧条,元气未复。刻下建昌道赵尔丰办理一起善后事宜,即转运军粮电杆电线乌拉,犹觉不敷,奴才随带员弁丁勇,人数既多,乌拉更难措备。设使中途阻滞,转觉进退维艰。”[4]7按清朝章程,凡出关大差在炉关购置包裹行李,采办米粮,具备夫马只有四十天期限,期间“照章由炉厅预办供给,每日伙食折钱五千文,小菜折钱两千文,马料折钱四百文,牛油烛二十斤,菜籽油二十斤,以四十天为率。扣到正月初二日期满,后仍照常索取供应,炉厅不堪其扰。”[17]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正月初九,联豫突然又向清廷奏请改走海路入藏,“西藏艰危之状,久在圣明洞鉴之中,自宜迅速驰往,查看情形,以期设法补救。思维至再,惟有改走海道,较为妥速。”[4]7由川藏路入藏是清朝边臣赴藏任职惯例,行程中也能调查沿途边情,此前有报刊谈到,“巴乱炽之时,锡制军即谓变乱肃清不知何时,不如航海以较稳妥,况有稽志文成案可援。联对以跳梁小丑,仗大帅神威,刻期可荡平,宁稍待。若改航海,万万不可,凤大臣甫经被戕,后来者即便改途,番民必笑钦差胆怯且虑,一举成例,此道遂废,锡制军深然其言”。[15]联豫从坚持陆路入藏宣誓权威,到突然奏改海道,遭到清廷谴责,朱批“仍着驰驿前进,并沿途察看一切情形,毋得藉此延宕。”[4]7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四月初五,联豫才又从打箭炉启程,于七月二十日抵达拉萨,从接受任命至抵拉萨,历时共一年又四个月。
联豫赴藏费时尤长遭到了弹劾,“帮办大臣联豫奉命将及一年,尚故意逗留,延不到任。近闻有御史递封奏,以西藏门户既已开放,将来交涉日繁,非得通达时务之才不能胜任。联豫以庸碌之才,怀畏缩之念,即到任后亦不足镇慑番族,转启外人轻视之心,请另简贤员等语。”[7]然而,联豫不仅未被撤职,短期内竟获连续升迁: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月二十三日,联豫抵藏仅三个多月就升任驻藏大臣,时有泰未遭弹劾,意味着清政府以联豫领副职入藏或已有该计划;十一月初三,因张荫棠辞任驻藏帮办大臣,联豫再兼驻藏帮办大臣,说明联豫赴藏初期表现基本符合清中央预期。
虽后世对联豫赴藏及迅速升迁多有诟病,认为是其凭借与军机大臣兼外务部负责人那桐的姑舅关系(4)《清史稿》载:“那桐,字琴轩,叶赫那拉氏,内务府满洲镶黄旗人。光绪十一年举人,由户部主事历保四品京堂,授鸿胪寺卿,迁内阁学士。二十六年,兼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晋理藩院侍郎。……二十九年,擢户部尚书,调外务部,……三十一年,晋大学士,仍充外务部会办大臣”;《辛壬春秋·西康篇》载:“驻藏大臣联豫者,军机大臣那桐之戚也。”;何藻翔《藏语》载:“(那桐云)帮办大臣联豫是舍亲,人亦明达,惜体太弱。”,但从联豫对赴藏新任的反映及其旅途行思,结合清末藏事环境当有更理性解读。西藏苦寒高远,赴藏任职属高危职业,联豫畏惧入藏在情理之中。有研究统计清朝实际赴藏的驻藏大臣,因病故、殉难和回京后因藏事赐死、自杀者达32人,死亡率超过26%。[18]联豫赴藏已年近五十,且凤全刚遭杀害,其赴藏可谓生命冒险,如其所言,“我今方欲向天西,风雪漫天冻马摔,北人不畏风霜苦,但愁病体难支持,难支持,何日抵乌斯”。[4]200
清末川藏道途梗阻,赴藏费时、多险也是客观限制。昔凤全途经巴塘时感叹,“二百年钦差往来通衢,乃竟若此,可胜浩叹。无怪得此差者,皆视谓畏途耶!”[19]118联豫长期滞留炉关,与乡城、桑披构兵直接相关,“奴才抵炉以来,详查关外情形,一时断难就道,理塘巴塘一带,经大兵剿办之后,土司头人逃亡殆尽,关塞萧条,元气未复。”[4]7至于联豫突然奏改海道,有泰推测是因番人劫掠,“因里、巴塘平后,马军门、赵观察已饬知番众各安本业,不意忽然复行杀起,穷番只得逃往小路,凡聪本所贩茶叶,均行抢尽。刻下来信即为此节,恐茶叶未克即时到藏,亦阻此地商人著往东路,不知是否的确,然联建侯不能振策,拟欲乘槎,或为此也。”[5]624行至拉里,联豫随员张其勤更叹,“大臣过境,尚且如此抗玩,他人可知矣。闻从前安星使过此,行未数里,其番官喝令众民抛掷石块,将纤夫明亮等一律截回……该番官又复如是,且始终未来一见。”[11]404联豫旅途的无奈,如其诗曰:“以此行为难,安知不更有难于此者,顾以予半生所历,江海之阔,轮蹄之苦,罔不备尝,盖自总角迄于今,垂五十年,无日不驰驱于道路中也,从未有如蜀道之难者”。[11]387
清末驻藏大臣职权旁落,筹藏缺乏应有支持,更是受任者不愿履职的重要原因。道光以后,驻藏大臣权力旁落,朝野均言藏政须整治,但筹藏长期缺乏有力支持。联豫在成都就奏陈,“奴才此次进藏,本欲随带三两营以壮声威而资震慑;到藏后扼要驻扎,并将各台制兵,剔退老弱,更补精壮,庶几缓急可恃。惟通年核计饷项,实属不资……实系无款可筹。现仅招募勇丁一百名随带入藏。”[4]6联豫虽深知,“藏卫多事,政务殷繁,需才孔亟”,[4]4然随员周荣和(5)周荣和冒大兴藉土人,蒙捐四川遇缺,先县丞,小有才,善逢迎,在雅州府听差,为联豫赏识,又因通蕃语,熟夷情奏调通往。委派前站文巡捕(向无此名),事无巨细皆由其一手经理,致启贪腐。沿途索夫马陋规,在荥经清溪县遭告发,行至炉关获罪,后许承宝、余陵等皆逃散。面对“(前随员)或因事撤退,或因病请假,均已销差回省”,联豫只能再奏调四川拔贡知县陈启昌、县丞齐东源等革员。齐东源后回忆,“予于丙午春蒙联建候星使驰书相召,同赴西招。四月始抵炉,而星使已先出关矣。当是时也,闻星使前调随员八人,以道途艰险,兵事未靖,遂俱求去,同行者惟慎庵一人”;[20]有泰日记也记,“闻联大人路上颇难行,驿马皆老弱,兵丁竟有背鞍步行者,狼狈可知矣”;[5]657联豫则作诗言,“天阙难翱翔,立马四顾心茫茫”,[4]200从中颇能见联豫赴藏囧途。
至清末,大臣不愿赴藏已是普遍心态,其入藏后的筹藏布展更深陷困境。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受任驻藏帮办大臣的桂霖,在成都迁延一年多,最后以眼疾为由辞不入藏;凤全在家书中坦言,“彼时诸事皆有头绪,再行奏请开缺,就近回川调理……大约此事行止,总在明年春夏之交方能定居。如有意外更动,则听天位置耳。如再到前藏,虽封侯亦不敢应命也”,[19]38-39将帮办大臣驻地由察木多改至巴塘;有泰在藏也急盼内调,他在家书中写道:“联大人本月廿二日到任……张大人听说八月可进藏,如藏内规模早定妥,今年腊月任满,盼早回内地”。[5]665联豫在五十岁高龄赴高远苦寒藏地,虽深知中央锐意改革藏事并有一定洋务经验,但其“忧时愤世,难落言诠,二三君子,乐知天命,升沉荣辱,各有姻缘……明日之事,事且置焉”[4]199的心理,已成为清末大臣赴藏的真实写照。最终,以驻藏大臣为核心进行的筹藏布展,如联豫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底奏陈,“夫时至今日,急起直追,已嫌太晚,若再因循,后患何堪设想……值此人才缺乏,库款拮据之际,日夜焦思,难安寝馈”“奴才惟有酌其缓急,权其轻重,不敢因循坐误,亦不敢卤莽图功”,[4]14-16处于“须行”又“难行”的困境。
四、结语
对于清朝驻藏大臣的选任,有观点认为清代均限用满人,满人中庸碌者多,末年尤多贪佞,贻误国家。[21]甚至有国外学者指出,“中华帝国主要是由有劣迹的官员代表它在西藏供职,他们曾被撤职或降职”。[22]然而,从王朝统治角度出发,无论正常职务调动或选用革臣,绝无向藏地派遣“庸才”可能,也不会单纯把官员“因过遣藏”,在清朝“因俗治藏”政策下驻藏大臣筹藏在于维护边疆稳定。清末藏事内忧外患,清廷选任联豫赴藏,既符合清朝长期从八旗子弟和西南各省选官入藏的传统路径,其出洋与经办洋务的经验又符合西藏新政改革的需求,联豫在赴藏费时尤长且遭弹劾的情况下又获迅速升迁,都表明了清朝驻藏大臣选任的中央意志。联豫对驻藏新任的应对与赴藏早期行思,是清末藏事环境客观限制及驻藏群体普遍心态的反映,说明以驻藏大臣为核心展开的筹藏施政至清末实已深陷困境,在以简单“人才论”评价驻藏人物之外,更应结合清朝藏事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