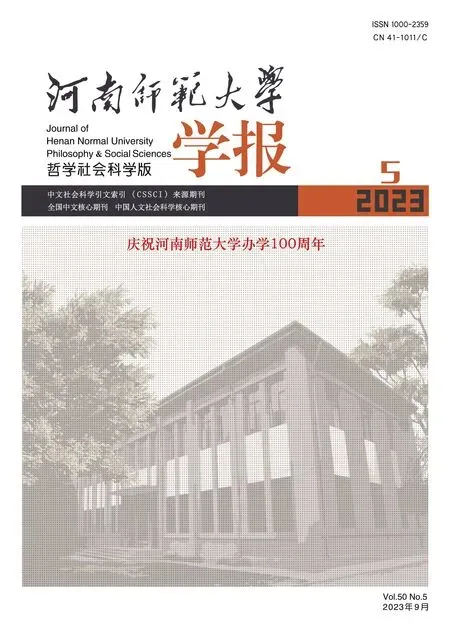论冯友兰对儒家伦理的转化创新
2023-03-09柴文华
柴文华,张 收
(1.黑龙江大学 哲学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2.哈尔滨工程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儒学在中国历史上有过长期的“独尊”,然而在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近现代,社会制度的革新和西方文明的冲击使作为中国传统伦理主体的儒家伦理受到严峻挑战,引发广泛的质疑批判并陷入深重的伦理认同危机。需要思考的是,中国现代伦理秩序的建构是否能够摆脱儒家伦理基因?进言之,儒家伦理如何参与新时代的伦理建设?研究冯友兰的伦理观,对解答以上问题具有重要启示。
一、对儒家伦理的态度
冯友兰对待儒家伦理的基本态度,是在同情理解的基础上肯定其内在价值。晚清以降,中国社会变革在“器物”和“制度”层面相继遇挫之后,先进知识分子将突破点聚焦到“文化”层面,传统伦理道德成为首当其冲的革命对象之一。梁启超在1902年前后就喊出“道德革命”的口号,提倡发明一种新道德以取代中国传统旧道德。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打倒孔家店”成为一时潮流,为在中国传播自由、平等、民主等西方思想,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吴虞等人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儒学进行过批判,“三纲”“五伦”“忠孝节义”等尤其受到猛烈抨击。冯友兰对儒家伦理的思考很大一部分正是回应所谓“民初人”对儒家伦理的批判,亦即是对热衷于取法西方现代伦理的“道德革命”的回应。
冯友兰从“共”“殊”来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每一个体或者说“殊相”内部都存在“主要底性质”与“偶然底性质”,事物的主要性质可学而偶然性质不可学。比如学习孔子以成圣人,孔子的“圣德”是其主要性质,可以学习,而孔子是鲁人、做过鲁司寇、活七十多岁等都是其偶然性质,不可学习。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均是个体的、特殊的“殊相”,内部充斥许许多多的无可模仿套用的偶然性质,单纯从个体的角度讲西方化或现代化都只是从一个“殊相”变为另一个“殊相”,这样的主张既说不通也行不通。而从事物的“类”或“共相”的角度来看,则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原因在于它们是不同类型的文化,比如可以看作是家庭本位和社会本位的区别,其间差距需要中国进行工业革命以改变社会制度方能弥补。基于这种理解,冯友兰提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思路:第一,从类型上讲要全盘改变,即从一个旧的类型转变为另一个全新的类型;第二,从内容上讲只需要部分改变,在将旧的文化转为新的文化类型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可以有选择地扬弃取舍,继往开来;第三,从民族性上讲要坚持中国本位,“此改变又是中国本位底”,“我们只是将我们的文化,自一类转入另一类,并不是将我们的一个特殊底文化,改变为另一个特殊底文化”(1)冯友兰:《贞元六书》,中华书局,2014年,第252页。。综合起来看,冯友兰主张中国文化应该大变但非全变,在变革中适当保持中国本位,防止全盘西化,中国传统文化需要继承和发扬。
就儒家伦理而言,冯友兰首先驳斥“民初人”对儒学的肆意攻击。他在《原忠孝》中指出,“清末人注重实业,民初人注重玄谈”(2)冯友兰:《贞元六书》,中华书局,2014年,第302页。,民初人大谈西方的“精神文明”,包括西学中的纯粹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等,可是不知不觉中轻视了工业发展。引进西学而不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会造成水土不服,那些先进的理论也就无法落实。如果不优先解决所引进的西方先进思想理论与落后的中国现实之间的矛盾,好比“先请了英雄,而不为设‘用武之地’”(3)冯友兰:《贞元六书》,中华书局,2014年,第275页。。同时,冯友兰还认为“打倒孔家店”、视礼教为“吃人”以及将“万恶淫为首”改成“万恶孝为首”等等言论乃“偏激之辞”,可当作社会转型期的一种独特社会现象来看待,但其观点本身错误,因为发表这些言论的人没有以正确的历史观评价儒家伦理。儒家伦理并非孔子、朱子等人凭空捏造,它与历史中特定时代的生产工具、生产方法、社会制度相适应,是社会的产物而非某些人的随意规定。批评儒家的礼教及其缔造者们迂腐、愚昧、残酷、无人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评价标准没有考虑时代的限制,好比用围棋的规矩批评下象棋的人,自然动辄得咎。为避免这种混乱,冯友兰在《新理学》中对道德评价标准作出设定:“一种社会内之分子之行为,只能以其社会之理所规定之基本规律为标准,以批评之。其合乎此标准者,是道德底。如是道德底,即永远是道德底。”(4)冯友兰:《贞元六书》,中华书局,2014年,第132页。以此为准鹄来回应新文化派对儒家伦理的抨击,体现冯友兰对儒家伦理的深切同情。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2014年,第891页。,是谓同情的理解。钱穆也主张要以同情的理解对待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正是由于冯友兰对儒家伦理同情的理解,使得他成为文化上的保守派。激进与保守的二元对峙构成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张力。熊十力在《读经示要》中说道:“后生游海外者……乃妄为一切破坏之谈。则首受攻击者,厥为经籍与孔子。北庠诸青年教授及学生,始掀动新潮,而以打倒孔家店,号召一世。”(6)熊十力:《熊十力全集》(第3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68页。保守派在文化攻防中处于弱势地位,主张中西互济调和,对中西方文化之优劣得失,一般都能加以客观的看待和评价。
在同情理解的基础上,冯友兰肯定儒家伦理的内在价值。从过去来看,儒家伦理已经证明了它的价值所在。中国古代有“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将道德看作评价个人价值的最高标准,维系一个社会存在和稳定的法则。冯友兰指出,中国历史上尊重道德的传统和中国社会组织的坚固以及中华民族的永久存续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由此观之,如不考虑它对社会现代变革造成的障碍,儒家伦理在促进民族团结、维持社会稳固方面确实拥有无可比拟的强大力量。而放眼未来,冯友兰坚信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旧邦新命”“继往开来”。他认为道德分“常”“变”,即不变的道德和可变的道德。依托“共相”之社会,凡有社会存在即存在的道德为不变的道德,而依托某种社会而存在的道德为可变的道德。就可变的道德而言,当一个旧社会转变成新社会,其道德需从旧道德转变成新道德,此即旧道德与新道德的分野。冯友兰指出,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就是“常德”,即不变的道德。“此五常是无论什么种底社会都需要底。这是不变底道德,无所谓新旧,无所谓古今,无所谓中外。”(7)冯友兰:《贞元六书》,中华书局,2014年,第394页。不变的道德可以说是一切类型社会所必具的基本道德。冯友兰说:“某种社会制度是可变底,而基本道德则是不可变底。”(8)冯友兰:《贞元六书》,中华书局,2014年,第399页。他认为现代化是社会制度的变化,而不是基本道德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看,儒家伦理的某些价值元素具有普遍性,儒家伦理的一些基本道德准则与现代社会生活之间并非完全割裂。冯友兰认为可以借“中体西用”来说明传统伦理道德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如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是说:组织社会的道德是中国人所本有底,现代所须添加者是西洋的知识、技术、工业,则此话是可说底。”(9)冯友兰:《贞元六书》,中华书局,2014年,第399页。这一提法乍看与洋务派的说辞别无二致,其实是经过了他经常使用的“正”“反”“合”的辩证过程,其中“中学”的范围缩小到道德层面,而“西学”也特指现代化意义而非地域意义上的西学。总结自清末至20世纪30年代期间中国社会发展的状况,冯友兰指出:“若把中国近五十年底活动,作一整个看,则在道德方面是继往;在知识、技术、工业方面是开来。”(10)冯友兰:《贞元六书》,中华书局,2014年,第400页。按照冯友兰的观点,中国人所欠缺的是知识而非道德,在基本道德方面可以继承和发扬我们的道德传统,这就充分肯定了儒家伦理的内在价值。
冯友兰的上述观点在今天看来大多是正确的。第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派人物对儒家伦理的批判确有偏激之处,如“打倒孔家店”“废除汉字”“吃人”等。如果说他们的批判有“片面的深刻”,最终导致的则是“深刻的片面”;他们持绝对主义的方式,好的一切皆好,坏的一切皆坏;他们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自卑和自贱心理,陷入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而难以自拔。第二,与第一点相关,他们对包括儒家伦理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持的是“冷酷拒绝”的态度,与冯友兰等提倡“同情理解”恰恰相反。立足于“知人论世”的历史主义态度和文化自觉以及文化自信的立场,我们对包括儒家伦理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必须抱着“同情理解”的态度,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中“掘井及泉”,为当代的社会发展、文化建设、伦理建构提供优质的本土思想资源,为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提供古代智慧和文化基因。第三,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逐步展开的,作为在古代产生和发展的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这是当时的知识精英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激进的西化派认为儒家伦理已经过时,而且还是现代化强大的阻滞力量,应该彻底抛弃;而包括冯友兰在内的现代新儒家的代表则在冷静反思的基础上,指出并弘扬了儒家伦理的内在价值。今天,如果有人再提出儒家伦理有没有现代价值的问题显然已经过时了,因为儒家伦理对当代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影响已经成为实实在在的事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荣辱观等与儒家伦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冯友兰在大约80年前对包括“五常”在内的儒家伦理的弘扬虽生不逢时却高瞻远瞩。第四,我们也应该看到,冯友兰对儒家伦理的探讨有“中体西用”的影子,虽然“中体西用”有历史的合理性,但在今天已不合时宜。我们思考儒家伦理的转化创新问题,应该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把马克思主义伦理精神、西方伦理精神和儒家伦理精神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构建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伦理精神,摆脱仅仅用体用范式思考伦理精神建构的局限。
二、对儒家伦理的创新
冯友兰的伦理观在创造性上有三方面的表现:一是以“新理学”体系为其伦理观的形上学基础;二是结合逻辑分析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提出道德层次论;三是通过辨名析理、抽象继承等方法论探索创造性转化的具体方式或途径。
“新理学”作为现代哲学意义上的形上学体系,它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将传统儒学中的一些概念和命题加以澄清,使其超乎形象、“不着实际”。在此基础上,冯友兰对儒家伦理的许多观点都带着“新理学”本体论的逻辑分析色彩。按照“新理学”的看法,“有物必有则(理)”,“理”是对一类事物的属性的抽象,事物之理与实际的事物之间,是共相与殊相的关系。因此,有社会必有社会之理,有道德必有道德之理。在《新理学》第五章中,冯友兰对“道德之理”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所谓“道德之理”,即“一社会内之分子,依照其所属于之社会所依照之理所规定之基本底规律以行动,以维持其社会之存在”(11)冯友兰:《贞元六书》,中华书局,2014年,第128页。。道德之理的这种规定,“剔除了伦理道德所赖以依附生存的现实社会制度、纲常结构”(12)柴文华:《冯友兰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6页。,使道德变成与实际社会现实无涉的纯哲学概念。在道德与社会的关系上,决定一种行为道德与否的标准与具体是什么类型的社会无关,而是与这种行为是否“合乎其社会之理所规定之规律”有关,这实际上构成了道德评判的参照系统。冯友兰特别指出:“一种社会内之分子之行为,只能以其社会之理所规定之基本规律为标准,以批评之。其合乎此标准者,是道德底。如是道德底,即永远是道德底。”(13)冯友兰:《贞元六书》,中华书局,2014年,第132页。举例来讲,以中国古代社会作为参照系统,产自古代社会的“忠孝”就是最大的道德,哪怕古代社会的制度已经被推翻,但“忠孝”依然是道德的,因为“忠孝”的参照系统是固定的。通过这种设定,儒家伦理道德的价值就得到最大限度的肯定,不能以现代社会的进步就批评它落后过时,进而通过不变的道德与可变的道德的区分,为儒家伦理适应现代社会和现代性转化找到通路。
“新理学”的人生境界说,则以划分精神境界的方式使儒家伦理的思想价值得到保留和提升。四境界中,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的人对宇宙人生的觉解程度比较低,是“自然的礼物”,人顺其自然地发展就可以达到。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是“精神的创造”,必须通过一种工夫修养以“尽人之性”方能实现。显然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才是“新理学”所主张的人生境界。道德境界中的人,其行为的根本特征是“行义”,即自觉地追求社会公利,其行为可以概括为“尽职尽伦”。冯友兰指出,道德境界的人,有较高的觉解去做选择,也就是儒家所谓的自做主宰;他尽职尽伦以尽性,能够“不顾毁誉,不顾刑赏”,甚至做到孟子的“舍生取义”;“他忧常是为天下忧,他乐常是为天下乐”(14)冯友兰:《贞元六书》,中华书局,2014年,第670页。,在古代社会能够尽忠尽孝,在现代社会也能爱国救民而不计利害得失。可以看出,在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说中,“儒家的伦理价值观念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公与否成为判断道德与否的标尺”(15)柴文华:《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哲学史省思》,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55页。,这昭示着重义轻利、公而忘私、心忧天下、舍生取义等儒家伦理思想在现代伦理的构建中不仅没有被去除或边缘化,反而有种复兴或重返伦理价值中心的倾向。
冯友兰对社会和道德进行逻辑分析,提出道德层次论。他说:“不但逻辑中有层次论,即道德学中亦应有层次论。”(16)冯友兰:《贞元六书》,中华书局,2014年,第255页。冯友兰在道德伦理中引入“层次”的概念,目的是解决道德认知中经常出现的逻辑混乱,他举《庄子·胠箧》篇“盗亦有道”的典故以说明。盗跖认为,即使偷盗也需“圣”“勇”“义”“智”“仁”五德兼备才可成功。道德本来要禁止做不道德的事情,但在这个故事里,有些不道德的事情反而需要通过道德来实现,如此一来构成“不道德底道德”,容易引起人们对道德认知的误解。冯友兰解释,盗跖所率领的团体,本身是一个小型社会,但其又属于一个较高层次的社会,低层次社会中的道德要求与高层次社会中的道德要求,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因此判断一种行为道德与否,需要站在“其所属于之社会之观点看”(17)冯友兰:《贞元六书》,中华书局,2014年,第134页。,采取单个社会视角而不是多个(或多层次)社会视角,也就是前面所说的道德评判的参照系统。冯友兰的道德层次论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向。在近现代,中华民族长期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压迫,随着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在国内传播以及一些国际公约的签订,致使一些人产生可以用道德和法规来维持国与国之间秩序从而实现国家和平的幻想。道德层次论从理论上打破这一幻想,它揭示了西方的精神文明只能在一个国家的内部发生作用,而各个国家之上,并未形成有效的更高层次的社会组织,国与国之间处于野蛮状态,国际公约和国际舆论不足以对西方国家形成多强的道德约束力。所以国家民族的独立不能寄希望于国际互助和道德制裁,只能靠自己武装自己来争取,这种认识无疑是非常清醒明智的。
上面所述可以说是空间范围的道德层次论,除此之外,冯友兰还讲了社会性质的道德层次论。社会性质的道德层次论,受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深刻影响。从1935年发表《秦汉历史哲学》开始,冯友兰的历史观开始认同唯物史观的一些观点。在《新事论》中,冯友兰根据他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来分析社会和历史问题,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横向地看待历史。在冯友兰看来,当时的西方社会是“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当时的中国是“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中西方的经济基础不同,其社会性质存在根本差异。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要将生产家庭化的社会转变成生产社会化的社会。冯友兰指出,生产工具决定生产方法,生产方法决定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决定伦理道德,即道德随着社会组织而定,在生产家庭化的社会里,“一切道德,皆以家为出发点,为集中点”(18)冯友兰:《贞元六书》,中华书局,2014年,第286页。。这并不是中国人的短处和弊端,而是客观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由此推论,到了生产社会化的阶段,以家为中心的伦理道德会让步于以社会为中心的伦理道德,比如爱国的观念会变成“活底道德”,为中国大众所接受。
以上两种道德层次论,前者说明了道德适用的空间范围问题,后者说明了道德适用的社会性质问题,综合来看,它们共同揭示了社会道德必须与社会现实相适应的规律,显然汲取了唯物史观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内容。
冯友兰虽然肯定儒家伦理的内在价值,但它毕竟是君主专制制度下的产物,具有历史局限性。传统儒家伦理如何转化创新,在理论和现实中仍需克服障碍寻找出路。冯友兰的探索是:第一,辨名析理。辨名析理是魏晋思想家玄谈时常用的方法,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将其概括出来,表示在本体论探讨中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在“新理学”中,冯友兰进一步提升辨名析理的理论内涵,他表示“逻辑分析法,就是辨名析理的方法”,并且提出“析理必表示于辨名,而辨名必归极于析理”(19)冯友兰:《贞元六书》,中华书局,2014年,第1007页。。如前面所述,冯友兰运用逻辑分析方法使“社会”“道德”等变成纯形式化的概念,皆可以看作辨名析理的结果。又比如对“仁”的分析,冯友兰用“利他”“爱人”的共同点将各种关于“仁”的说法综合起来,表述为朱熹提出的“仁”是“爱之理”这一规定。“所谓仁,如作一德看,是‘爱之理’。爱是事,其所依照之理是仁。”(20)冯友兰:《贞元六书》,中华书局,2014年,第140页。不难看出,通过辨名析理,“仁”的含义表述得更加准确、简洁、明晰。第二,抽象继承。1957年,冯友兰在《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一文中提出“抽象继承法”,这个方法对儒家伦理的转化创新同样有启发。冯友兰指出,如果全面了解中国哲学思想,应该注意到中国哲学的一些命题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个是抽象的意义,一个是具体的意义。比如《论语·学而》中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它的具体意义是孔子让人学习诗、书、礼、乐等传统的东西,这对我们今天的用处不大,不必去继承。可是从抽象的意义来看,这句话是说无论学什么东西,学了之后都要及时、经常地温习和实习,这是件很快乐的事,这句话到现在还是正确的。拿孔子的“爱人”来讲,从具体的意义来看,儒家主张亲亲、爱有差等,孔子所说的“爱人”有其特定范围,从孔子所处的社会阶层来看,其“爱人”实际上“爱贵族”的成分居多。而从抽象的意义说,孔子所说的“人”与现代所谓“人”的意义差不多。同样,“天下为公”“节用而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哲学命题的抽象意义,都是可以拿到今天来用的。冯友兰提出的“抽象继承法”,其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说白了还是“新理学”中的“共相”和“殊相”,这也导致“抽象继承法”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判。但从今天的视域来看,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自有其合理之处,因为不论是古人还是今人都是人,他们所面临和思考的对象世界大致相同,其思维成果自有其相同之处,这就是反映人的类价值的普遍性元素。既然我们承认这种普遍性元素的存在,事实上也就承认了“抽象继承法”的合理性。因此,对于儒家伦理的转化创新来说,“抽象继承法”不失为一种可供选择的正确方法。
三、以“忠孝”为中心的考察
“忠孝”是儒家伦理的核心内容,冯友兰说:“在旧日,最重底伦常是君父,最大底道德是忠孝。”(21)冯友兰:《贞元六书》,中华书局,2014年,第287页。因为“忠孝”是儒家伦理中重要的精神文化遗产,所以冯友兰对“忠孝”的问题展开集中的阐发,这也是他对儒家伦理转化创新的一个个案分析。
冯友兰分析了“忠孝”产生的根源。他认为道德不是任意的人为规定,而是由社会制度所决定的。近代以前的中国是“生产家庭化”的社会,家就是一个经济单位,一切社会组织都以家为中心,一切人和人的关系也都能套进家庭关系。比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有三伦是有关家庭的,君臣、朋友二伦的内容也能从家庭关系中类推出来。在生产家庭化的社会里,一切道德都是以家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其中“孝”是一切道德的中心。中国古代宗法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家国同构”, 君臣关系可以比拟父子关系推出来,因此“忠”和“孝”在含义上也极相似,冯友兰说“孝”实质上就是“忠”于家,说明“孝”和“忠”的差别仅仅在于作用对象不同。
冯友兰考察了“忠孝”冲突的情况。“忠孝”都是最大的道德,二者发生冲突时往往难以抉择。“忠孝”冲突有普通和极端两种。普通情况的“忠孝”不能两全,是在外忙于“王事”和在家侍奉父母之间的矛盾,严重一些可能会牺牲自己导致无法奉养父母,这时都应该“移孝作忠”。极端情况的“忠孝”不能两全,是不仅因尽忠而导致不能尽孝,甚至会给父母招来杀身之祸。孟子和程颐都认为,在这类极端情形下,应该辞去官职以挽救父母。冯友兰指出,孟子和程颐的观点不论现实中是否可行,至少在理论上说明了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中“孝在忠先”。在这个基础上,移孝作忠也不是真正的忠比孝优先,因为移孝作忠可以使父母获得美名,归根究底是“孝”的行为,这也表明社会制度是道德原则的决定性因素。冯友兰进一步分析了现代社会即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中的“忠孝”冲突。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在经济上是生产社会化,人的全部生活与社会融为一体。在这种社会,“孝”的含义没有发生变化,而“忠”的含义却发生很大变化。古代社会的“忠”,按《论语·学而》“为人谋而不忠乎”来理解,有“为他人”的含义。在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一分子,“人替社会做事,并不是替人家做事,而是替自己做事;不是‘为人谋’,而是为己谋”(22)冯友兰:《贞元六书》,中华书局,2014年,第300-301页。。如果还用“忠”来表示的话,其含义(“为己谋”)与古代社会的“忠”(“为人谋”)的含义迥然有别。在这个意义上,古代的忠君不能直接转化为爱国。因为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中,忠君是替他人做事,而在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中,爱国是替自己做事。有了这种觉悟而谈爱国,爱国才不是空洞的理想,而是一种“活底道德”。在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也有家庭,只是家庭不再是经济单位而已。巩固家庭不再是人们的第一义务,因此“孝”也不再是“百行先”。冯友兰说“在此等社会中,孝虽亦是一种道德,而只是一种道德,并不是一切道德的中心及根本”(23)冯友兰:《贞元六书》,中华书局,2014年,第300页。。冯友兰认为以上意义的“忠孝”和传统的“忠孝”意义不同,因此可以说是新道德,可见旧道德可以转化成新道德。
冯友兰在《新世训》第二篇《行忠恕》中还着力讨论了“忠恕”等问题。《论语·里仁》中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朱熹在《集注》中解释:“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冯友兰指出朱熹的解释不够精确,应该补充为“尽己为人”。“尽己”,可能是为别人做事,也可能是为自己做事,只有“照己之所欲以待人”才是“忠”的意义。冯友兰指出,宋明道学家所讲的“道德”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任何社会都需要的道德,如仁义礼智信;一类是某种特殊社会所需要的道德,如“忠孝”;还有一类是不违反道德规律的生活方法,如勤俭等。他认为“忠恕”一方面是实行道德的方法,是为仁之方,所以忠恕之道是任何社会都需要的道德。忠恕之道是“以一个人自己的欲或不欲为待人的标准”(24)冯友兰:《贞元六书》,中华书局,2014年,第435页。,这个标准在每个人的心中,简单平易,不必外求,易于践行。另一方面“忠恕”又是普通的待人接物的方法。日常生活中有些礼义往来和人情世故,可以按照忠恕之道来办,但是和道德与否关系不大。总之,冯友兰认为“忠恕之道,是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可以行底”(25)冯友兰:《贞元六书》,中华书局,2014年,第449页。。
通过分析冯友兰对“忠孝”和“忠恕”的阐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儒家伦理和现代伦理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跨越的鸿沟,属于常德的伦理道德可以古今通用,专属于古代社会的一些伦理概念,经过重新阐发和释义也可以转化为新道德。综上我们还可以看出,在现代伦理的展望中,冯友兰认为社会与个人之间是“大我”和“小我”的关系,个人寓于集体之中,反映了其伦理观具有群体至上的理论倾向,这种价值观与儒家的重义轻利、公而忘私的价值取向一致,体现出对儒家伦理的继承和发扬。儒家伦理是种美德伦理,道德的元素在儒家文化中占据极大的比重,强调群体、责任、义务使历史长河中的中华民族团结稳固,源远流长,同时个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的淡薄也导致儒家伦理难以完全适应民主、自由、个人权利为主流价值的现代社会,后者是冯友兰所缺少关注的。尽管如此,冯友兰对儒家伦理价值的肯定以及在儒家伦理的转化创新中所开辟的道路,对于我们进一步思考儒家伦理的转化创新和构建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伦理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