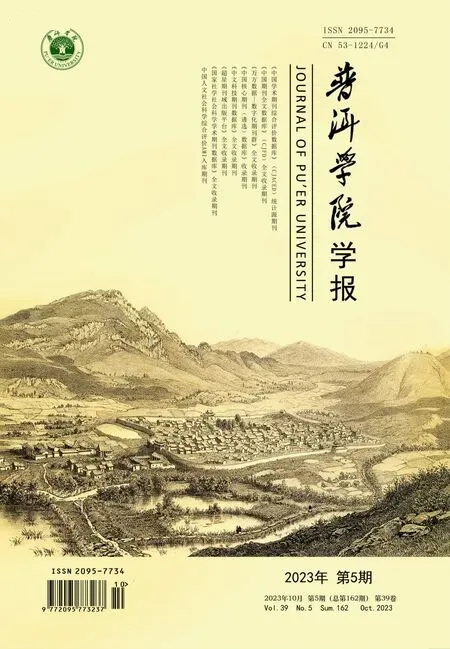文化多样性与文化整合:以历史上傣族农耕稻作文化为中心
2023-02-19李莲
李 莲
普洱学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云南 普洱 665000
历史以来,云南始终保持着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显著特征。学界通常认为这是云南具有地域环境多样性、族群多样性和经济文化类型多样性使然。其中,傣族作为一个古老的稻作民族,其农耕稻作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汉魏时期西南地区就居住着“夷越”“滇越”“骆越”等越人,过着“饭稻羹鱼”“食物常足”的生活。远在两千多年前,傣族地区就有种植水稻的灌溉农业出现。除了傣族和壮族外,布依族、水族、仡佬族、侗族等也是百越民族的后裔,都是古老的稻作民族。在云南,还有氐羌系的白族、哈尼族等都较早从事水稻栽培。古滇国主体民族为越人,是稻作文化的开创者。稻作文化是历史上的傣族先民及后裔得以世世代代繁衍生息、自身文化不断整合而薪火传承的不竭动力,也是其文化传播力所及并使周边其他民族受到浸润而产生文化整合的重要驱力。
一、云南各民族的稻作文化
中国是原生稻作文化的发祥地,尽管云南地区已发现的栽培稻遗存年代较为晚近,从考古上看,先后在昆明、呈贡、晋宁、安宁、元谋、宾川、江川、剑川、曲靖等二十多处出土文物中,发现有碳化稻粒、稻穗凝块或陶制器具上的穂芒压痕。在宾川白羊村遗址发现的碳化稻粉末,为公元前3770 年左右的遗物。据此推断,云南的稻作历史至少在四千年以上[1]。这说明中国作为稻作文化的起源地,其自发轫之时即呈现多“元”一体的特征。由于包括云南在内的中国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是古代民族(族群)迁徙的大通道及其聚集的大舞台,加之云南古代民族(族群)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在作为农业文明重要标识的稻作文化的持有者的民族中,傣族先民的稻作历史和文化较为凸显,傣族聚居区逐渐成为了云南的主要栽培稻地区。
稻作文化又分为水田稻作文化和陆地旱谷文化,但它一般是指以水田稻作为主的经济形态所产生的文化,包括稻作生产活动及其与之相关联的社会生活和习尚,如生产生活方式、信仰、习俗,以及稻作民族的性格、爱好与文化心态等。云南历史上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的关系,稻作民族的种植或耕作形式不尽一致。例如,傣族、壮族、白族等从事的主要是坝区水田稻作;哈尼族由畜牧文化转型为坝区稻作文化,然后又转型为梯田稻作文化;景颇族、怒族、傈僳族、彝族、独龙族、纳西族、拉祜族、布朗族、佤族、德昂族等由畜牧文化转型为陆地旱作文化后有旱稻种植(其中部分居住在坝区、河谷的有水田稻作,如彝族等);苗族、瑶族等游耕民族,据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或陆地旱作或水田稻作。20 世纪50 年代以前,景颇族、佤族、纳西族等以种植旱稻为主,少量水田的开辟是向汉族或傣族学来的。总之,山居民族“分别以轮作、杂粮栽培、游耕的形式从事旱稻种植,并与居于坝区、河谷的傣、壮、汉、白、哈尼等水田、梯田稻作民族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1]。云南各民族在各自相对封闭而又相互依存的“文化——地理单元”之中,所创制的稻作文化特色是多样并存又相互联系的。
在云南的各稻作民族之中,傣族的水田稻作较为突出,它是傣族文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及各民族稻作历史的具体情况,可以看到,尽管杂粮栽培中有旱稻栽培,但旱稻只是杂粮栽培的一个品种之一,而对水稻栽培民族而言,水稻是其主要的生产作物,也是其主要的生活资料,稻谷成为经济生活的中心,并影响和构造了以水稻生产为特色的文化形态”[1]。在云南各民族农耕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大致经历三个阶段,即前农耕阶段、以杂谷为主的刀耕火种阶段和以稻作为主的阶段。有的民族经历了前两个阶段,直到20 世纪中叶之后实现了直接过渡;而傣族、壮族等在古代就发展到以稻作为主的阶段。相较于其他山居民族而言,傣族择水田而耕,居多傍水,是古老的稻作民族。
通过对上述云南各民族稻作文化的起源及其比较分析后认为,农耕稻作文化显然为傣族带来了文化上的优势地位。即水稻因富含人体所需优质蛋白质、粗纤维少易消化吸收、易储存和加工、产量较高,使傣族人口得以大量繁衍生长;水稻单作利于生产技能和生产力的提高,利于定居生活,利于傣族形成以稻作为主的经济生活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稻作文化在傣族农耕文化体系中逐渐居于主导的地位。除傣族之外,白族、哈尼族等氐羌系族群由畜牧文化转型为稻作文化,稻作文化也逐渐在其农耕文化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稻作文化的传播致使傣族与周边各族之间的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得到加强,产生了文化整合,形成了一定区域内的民族共同体文化。
二、 稻作文化是傣族文化转化、整合的推动力
(一)文化整合既是一个历时性的过程,也是一个共时性的结果
文化整合是指构成文化的诸文化事象或诸文化元素的相互吸纳、融合, 并使之趋于一体化的过程。亦指不同文化经交汇、选择后,积淀、转化为一种多元和谐的文化体系。文化整合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经济因素有密切关系。就傣族而言,政治因素是外因,经济因素是内因。笔者认为,政治上的整合自元代在云南设置路府州开始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直到明清时期最终完成。元代傣族的世居之地“夷方”与中央王朝的政治归属性得以强化,到明清时傣族地区继续成为中央王朝西南边疆经略的重要地区之一。而在特定区域上的“夷民”及相应的地理空间就被逐渐整合为一体,并使傣族先民的文化心理发生了变化,对中央王朝产生了较为稳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清代的傣族,其分布基本承袭明末,靠内地区则范围有所扩大,省内十五府皆有之。但总体上仍以普洱府(今宁洱)、顺宁府(今凤庆)、景东厅(今景东)、镇沅厅(今镇沅)、腾越厅(今腾冲)、元江州等地为其传统的主要聚居区[2]。
以上元明清时期逐渐整合形成的云南境内的傣族辖地空间,其后虽有所分散或分化,但现在傣族及相应的地理空间分布格局基本上是延续下来了的。当然,政治归属性的强化并非意味着中央王朝对傣族地区的治理从此就强化起来。如“勐卯果占璧”政权于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 年)始受封为麓川路,傣族土司政权从此趁元王朝初期对其统治无暇顾及之机悄然强大起来,到元惠宗至元六年(1340 年)思可法继任“勐卯王”时,已经建立了强大的“麓川政权”。明朝时,继任麓川主思伦法、思任法继续向四周扩张,甚至威胁到云南腹地,致使朝野震惊,最终于1441 年至1448 年间,明朝廷三次派王骥率大军征讨,史称“三征麓川”。此后,中央王朝治理渐成守势,甚至部分靠外而“白夷”较集中的孟养、木邦、孟艮、八百、老挝等土司地区先后被缅甸洞吾王朝攻占而脱离云南[2]。傣族地区并非像云南(昆明)、楚雄、曲靖、临安、大理等靠内地区是中央王朝在云南统治的核心区。《西园闻见录》记载:“今云南、楚雄、临安、大理等府设置如内地,而更以元江、永昌之外麓川、车里等处为西南夷,亦犹汉时自成都而视滇池也”[3]。《南中杂说》亦云:“明朝旧制,两迤列郡二十有一,然流官分治不过云南、大理、曲靖、临安、楚雄、澄江而已,余皆土司归命,而授之号,曰土府”[4]。说明政治上的整合属于外部因素而非傣族文化整合的内生动力。
上述历史上所形成的人文地理空间是傣族先民的活动区或傣族文化传播、辐射的核心区。傣族文化圈是云南的栽培稻地区,在傣族文化圈内作为农业文明重要标识的稻作文化占有非常突显的地位,是傣族文化转化、整合的内生动力。所以,傣族自身在历史上因早已产生了以稻作文化为核心的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交流,至迟在明代以后,就从单向的“纵向发展”转向与异质文化交流互动的“横向发展”,乃至转型发展,形成了新的文化模式,实现了文化整合。
(二)傣族以稻作文化为核心的文化整合表现
1.傣族的共同体文化基因
从稻作文化发轫时起,久远的原始观念和文化形态与之相整合,形成了以稻作文化为核心的原生文化,奠定了傣族的共同体文化基因。首先,流传久远的谷种起源神话在傣族起源类神话体系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犹如水之源木之本,获取谷种是稻作农业的源头活水,谷种起源神话便是农耕稻作文化开始出现的表征。傣族谷种起源神话的类型多样,主要有飞来稻型、动物取来型、英雄盗来型、穗落型、神人给(授)型等。这些作为傣族原生文化重要标识的谷种起源神话都与傣族特定的地域环境、特定的经济文化类型、特定的原始(民间)信仰、相关的祭仪,以及稻作民俗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其中,不仅反映出人们对已被神圣化了的谷种一直保持着某种敬畏、崇拜心理,甚至将谷种视为是“谷魂”的载体,尊称它为“谷魂奶奶”。其次,傣族的原生文化的主体是以稻作文化为中心而展开的,其文化活动也都围绕着稻作生产而展开。传承至今的稻作生产中的祭祀活动保留了许多傣族的原始文化,特别是对谷神、水神、山神、龙神和鱼神的崇拜。
2.傣族原生文化与边际文化相整合
傣族原生文化与滇文化、南诏文化、大理文化、汉儒文化、东南亚文化等边际文化相整合,形成了具有鲜明的原生文化标识以及边际文化共同特征的特色文化。
首先,从不同历史时期的汉文献记载对傣族先民的称谓变化当中,可以看出傣族在这方面文化整合的轨迹之一斑。例如:先秦时称为“濮人”“越裳”,说明还存在与其他族群相混称的情况;秦汉魏晋时称“滇越”“掸”“鸠僚”,此时与其他族群有了较明显的区别;唐宋时称为“金齿”“黑齿”“银齿”“茫蛮”“绣脚蛮”“绣面蛮”等,说明傣族居住的地域较广阔,历史上因为战争等因素迁徙流动频仍,地域分割突出,有的与其他民族间隔错杂聚居,由此导致傣族各地的文化风貌各有不同,也因此而出现了不同的分支(部落)称谓。但从另一方面又证明各方傣族先民壮大起来后分支(部落)繁多的同时,还与南诏文化、大理文化等有密切接触,傣族先民及其文化与周边其他民族及其文化的区分度更加明显,具备了较为显著的傣族共同体文化特征。元代时对傣族先民统称为“金齿百夷”或分别称为“金齿”“百夷”(或“白夷”),表明伴随着傣族的悄然崛起,文化整合进一步加强,具有鲜明的人文地理风貌和社会文化特征的傣族文化圈开始产生;明代时傣族先民的族名有了一个比较同一的称谓即“百夷”(或“白夷”、“伯夷”),只不过因各地风俗的殊异区分为“大百夷”和“小百夷”,但共同点是他们此时都因佛教文化的渗入并居主导地位而使得傣族文化实现了佛教化转型,以他们的聚居地为代表的傣族文化圈正式形成;清代及民国时期称为“摆衣”或“摆夷”,其中又分为“旱摆衣”和“水摆衣”两个支系,大致为“傣那”和“傣泐”的区别,延续了元明以来所形成的傣族文化圈内的文化风貌和特征。
其次,傣族原生文化在吸纳、融入了边际文化之后整合为特色文化的一些基本情况。例如傣族古风俗诸相:“乘象国”(滇越)[5]“漆齿”“养象以耕田”[6]“槟榔致礼……凡遇亲友及往来宾客,辄奉啖之,以礼之敬”[7]等。又例如经济模式和经济行为文化的嬗变:“交易五日一集……以毡、布、茶、盐互相贸易”,“地多桑柘,四时皆蚕”[7],已与当时中国内地的农桑无异;“一岁两收,春种则夏收,夏种则冬收”[8],“地产五谷……输纳粮税”[9],“其谷则稻、黍、稷、粱、麻、豆、荞、稗”等[10]。又例如语言文字方面从“记识无文字,刻木为约”[11],到“其文字,进上者用金叶写之,次用纸,次用槟榔叶,谓之缅书”[12]。又例如文化教育方面也受到了儒学的浸润:元明清时期傣族地方先后办起了庙学、社学、义学、府州县学和书院等,建学以祀先圣,学习儒学,出现“昔惟缅字,今有书史;民风地宜,日改月化”的局面[13]。
上述记载,无不体现着傣族以稻作文化为核心的鲜明的区域文化特色。稻作文化使傣族先民变得安土重迁,无大故不肯轻去其乡,利于傣族文化与异质文化的交流、吸纳与整合。史载傣族主要聚居地的德宏、保山、腾冲、永平等地山川秀丽,号称西南富庶之地。在这些地方“正统间始建学,选卫子弟之秀者而立师以教之,于是士风渐振,以读书自励而举于乡试者,科不乏人”[14]。这些地区,一方面崇佛教,以米蒸熟斋供缅佛,听僧诵经,顶礼膜拜;另一方面,自元明设卫分屯,驻军镇守多江南人,“遂沿用江南风俗”,加之“声教涵濡,风气日上,民勤耕织,士重诗书,汉夷相安”[15]。
3.傣族文化转型发展为具有鲜明佛教化色彩的傣族文化模式
南传上座部佛教传入傣族地区并居于支配地位之后,傣族原生文化、特色文化与佛教文化相整合,转型发展为具有鲜明佛教化色彩的傣族文化模式,其间是稻作文化起到了耦合作用。景谷地区流传的召西塔(佛祖释迦牟尼在未悟道成佛以前称为召西塔)的传说讲道:菩提树下苦修了6 年之久的召西塔,直到最后不饮不食整整49 天,不省人事。就在召西塔生与死的紧要时刻,天神叭雅英下凡来施救,只见他变成一个娜哨(姑娘),小心翼翼地往召西塔的嘴里足足喂了49 个“好麻途”(傣语一种糯米饭团),使召西塔慢慢地苏醒过来。现在傣族群众“赕帕召”(“帕召”新雕塑的佛像),要备上49 个“好麻途”去佛寺告赕,以此来纪念召西塔再次获生[16]。又例如傣族神话传说谷魂奶奶就是谷神,人类要敬奉她并得到她的保护,才可能有收获。因此,森林中的诸神都很敬佩她,称她为“至高的谷王”。但佛来到森林之后,不尊敬她,她也看不起佛,见到佛不肯下跪,并且气冲冲地飞走了。于是,田地里的谷物干枯,谷仓里的谷种全都飞走,人类没有粮食吃。人类无法活下去了,要求佛到天上把谷魂奶奶请回来。从此,人们更加尊敬谷魂,不敢得罪谷魂,每当播种收获时节都要祭谷魂[17]。
但是,稻作文化在转型以后的傣族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在傣族人民文化心理结构中的重要作用始终没有动摇。而佛教文化在和原生文化、特色文化经历了最初的冲突、碰撞之下选择了与后者相互包容吸纳,发生联系互动,从而产生了原生文化、特色文化和佛教文化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联动效应,相互调适、融合。这些原先不同质的、有差异的文化在傣族共同体的框架之下走向整合,这是稻作文化在其间起到了耦合作用的结果。正如有学者指出:“正是在发达的稻作文化基础上,才为上座部佛教的传播提供了温床,才有了傣族繁荣的民间文学和丰富的历史文献,才使傣族在哲学、艺术、科学、宗教、医学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宏富的成果和一系列独创性成就”[18]。
三、傣族稻作文化的向外传播及文化整合
傣族历史上与其他民族最重要的文化交流互动,就是稻作文化的传播。傣族稻作文化在其传播过程中使与之接触较密切的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发生了变化,从而形成了本民族的特色文化。
云南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是古代四大族群百越、百濮、氐羌、槃瓠迁徙流转繁衍融合之地,种族的杂交、文化的交流极为频繁。这些历史悠久的古族群,在古代都创造了相当发达的文明,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与其他民族交往联系,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用于丰富自己。吸收最多的应该是较为先进的农业文化,其中就包括百越系统的稻作文化。因为作为农业文明的重要标识,稻作文化在农耕文化体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随着民族迁徙及文化传播,傣族稻作文化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力和带动力是比较突出的,甚至对某些民族而言,如果引入了傣族先进的农耕技术,如果吸纳了傣族的水田稻作文化,即可视为走向了农耕文明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从传播路径上看,首先,世居于或活动于傣族文化圈内及其周边的与傣族交往较为密切的一些民族(族群),应该是傣族稻作文化传播的重要吸纳者(如景颇族、纳西族、布朗族等)。其次,随着傣族的迁徙,又将稻作文化传播到新的定居点上,带动起当地的土著民族学会水田稻作(如佤族、拉祜族等)。纳西族以种植旱稻为主,少量水田的开辟早年传习于傣族。史载纳西族先民男女皆刀耕火种,“稻有黑背子、老乌谷、罗罗谷、水长谷、糯谷数种”,又载“麓川稻,种自麓川来”[19],在引入了水稻谷种的同时势必也引进了傣族的种植方式;于16 世纪以后迁徙到德宏地区定居下来的景颇族,学会了傣族的水田稻作,稻谷成为了他们的主粮;历史上居住在傣族周边的芒景(今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惠民乡境内)布朗族学会了傣族的水田稻作。芒景布朗族由于长期受到傣族文化的浸润,在保留本族原生文化以及原始信仰的同时,也积极吸纳傣族文化,其中就包括傣族的文字及其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信仰。迁徙到普洱地区景谷、孟连等地的傣族先民,一方面融入了原住民的某些习俗和文化,另一方面也传播了先进的稻作技术和文化,带动了原住民生产力的提高和文化的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哈尼族由畜牧文化转型为稻作文化,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傣族的影响。这在迁徙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意为“哈尼族祖先的搬迁史”中有清晰的描述。史诗叙述了哈尼族先民从祖先诞生的“虎尼虎那”高山南迁到哀牢山的历程,较全面地反映了哈尼族历史文化形成、演变及发展的轨迹。其中讲到了“惹罗普楚”与文化转型的事象:因森林大火,哈尼祖先继续南迁到住着稻作民族阿撮(傣族)的嘎鲁嘎则之地,向阿撮人学习了农耕稻作文化,接着南迁到雨量充沛的惹罗普楚。在这里正式成为稻作农耕民族,并安寨定居(产生了选寨基习俗,发明建造蘑菇房),建立起社会组织制度(推选了西斗做头人,头人兼有祭司的职责),逐渐形成南方强大的部落民族。以后无论如何迁徙、分支,惹罗普楚的生活模式一直伴随着他们[20]。这当中传递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信息,就是吸纳了傣族的农耕稻作文化对哈尼族早期的文化转型、文化整合起到了较大的影响作用,哈尼族迁徙中向傣族学会了稻作生产是该族群走向农耕文明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在古代,先进的生产技术包含着相关的信仰、神话传说、祭祀仪礼等,具有浓厚的复合文化的性质。因此,水田稻作作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它的传播很可能伴随着各种相关的文化和信仰习俗。相邻的地区或相邻的民族间类似的共同性的民俗文化多数是因直接传播而引起的;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口大规模移动,造成不同文化的碰撞、交流和整合,形成各民族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的和合相通。这些情形通常表现出先进文化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带动力,在文化传播、整合中能发挥巨大的作用。以西双版纳为例,历史上就是多民族地区,除坝区居住着傣族外,山区还有布朗、佤、哈尼、拉祜、基诺等民族。相较而言,稻作文化能够提供比较充裕的粮食,支撑着傣族在经济上成为先进民族,同时作为经济基础,支撑着傣族在政治上成为统治民族。傣族文化以稻作文化作支撑,向山区民族广泛传播,使得众多山区民族学会了傣族语言,有的还接受了傣族的服饰,布朗族则在傣族影响下信奉了南传上座部佛教[21]。在西双版纳区域内,稻作文化以及与稻作相关的民间信仰与习俗等诸文化事象在坝区和山区交融,逐步整合成为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为各个民族所共同拥有的体系文化。
历史上云南是多民族(族群)迁徙、交汇、融合的大舞台,各民族的文化都具有其顽强的生命力和独特性,各民族的文化既有共性,也有互补性。这样,历史上以傣族稻作文化为核心的文化整合,其形式是一定区域内的松散的诸民族共同体文化,其关系是整体性文化之中彰显、包容着民族特色文化,整体性文化通过诸民族对它的认同获得发展与传承,其文化风貌是呈现一定区域内的具有多元、包容、互补、和谐特质的诸民族共同体文化。
四、结语
傣族所具有的稻作民族的文化特质和信仰体系是经过长期的历史形成的结果,也是傣族在历史上以稻作文化为核心与外来文化碰撞、交流、整合,获得文化转型、文化再造的结果。傣族的原生文化、特色文化以稻作文化作为的重要支撑,从而没有被佛教文化所完全覆盖或替代;稻作文化在不同文化系统之间起到了耦合作用,而使不同系统的文化在稻作文化共同体的框架之下走向整合。文化整合与文化多样性并行不悖,受到傣族稻作文化长期浸润的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在既保持着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的同时,又融入了傣族文化的因子,从而形成了本民族的特色文化。这些民族的特色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外来文化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也是文化整合的体现。稻作文化以及与稻作相关的民间信仰与习俗是一定区域内的具有多元、包容、互补、和谐特质的诸民族共同体文化的主要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