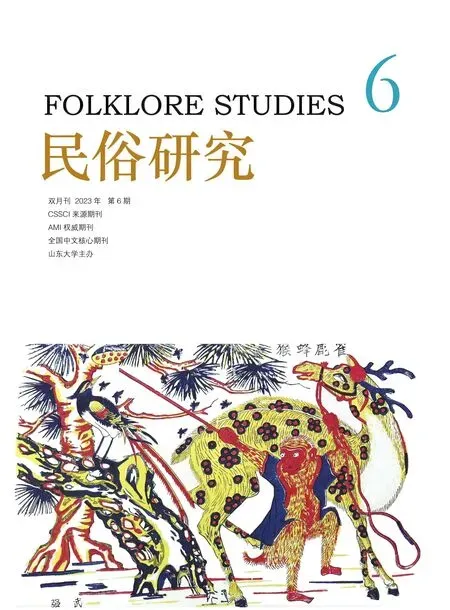论葛兰西的民俗观
2023-02-19李正宇
色 音 李正宇
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是著名的意大利思想家,意大利共产党(Partito Comunista Italiano)创始人之一。1926年,葛兰西被捕入狱,1929年被允许写作,此后共留下了33卷笔记。(1)葛兰西的狱中笔记共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Einaudi出版社于1948-1951年间陆续出版的葛兰西作品集(Le opere di Antonio Gramsci)中的6卷,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分别为:《历史唯物主义与贝奈德托·克罗齐的哲学》(Il materialismo storico e la filosofia di Benedetto Croce,初版于1948年,下同)、《知识分子与文化建设》(Gli intellettuali e l’organizzazione della cultura,1949)、《民族复兴运动》(Il Risorgimento,1949)、《关于马基雅维利、政治和现代国家的笔记》(Note sul Machiavelli, sulla politica e sullo Stato moderno,1949)、《文学与民族生活》(Letteratura e vita nazionale,1950)、《过去与现在》(Passato e presente,1951)。然而,这6卷并不是Einaudi出版葛兰西文本系列的全部。这个系列还有囊括葛兰西其他文本的《新秩序(1919-1920)》(L’Ordine nuovo 1919-1920,1958)、《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新秩序(1921-1922)》(Socialismo e facismo, L’Ordine nuovo 1921-1922,1966)等卷。但这一版本,按照吕同六先生的说法,是“按内容分门别类,整理和编辑”(参见[意]安东尼奥·葛兰西:《论文学》,吕同六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5页)的,并不完整,且未按时间顺序排列。直到1975年,由盖拉塔纳(Valentino Gerratana)校勘的版本(Antonio Gramsci, Valentino Gerratana (a cura di): Quaderni del carcere. Torino, Einaudi, 1975)才问世。该版本共4卷本,包括29个笔记本,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是葛兰西狱中笔记的第二个版本。本文的指代和引用皆来自后者。此外,有关葛兰西狱中笔记的数量一直存在着争议。葛兰西研究会(Fondazione Gramsci)会长瓦卡(Giuseppe Vacca)认为共有33卷笔记,属于较为权威的说法。参见Giuseppe Vacca, “Antonio Gramsci,” in Istituto della Enciclopedia Italiana,Dizionario Biografico degli Italiani. volume 58, Roma, 2002. Disponibile su https://www.treccani.it/enciclopedia/antonio-gramsci_%28Dizionario-Biografico%29/ (data di accesso: 10/10/2022).其中,他集中论述民俗的一节对意大利学界影响深远。意大利著名民族学家、宗教史学家德马蒂诺(Ernesto de Martino)受他启发,创造性地提出了“进步性民俗”(folklore progressivo)的概念。意大利著名人类学家奇雷塞(Alberto M. Cirese)编写的影响深远的人类学教材《统领文化与从属文化》(Culturaegemonicaeculturesubalterne)则以葛兰西的egemonia概念命名。美国民俗学者桑德斯(George R. Saunders)认为,葛兰西对意大利的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三个学科而言都是影响力极大的人物。(2)参见George R. Saunders, “Contemporary Italian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13(1984), pp.447-466.意大利民俗学者德伊(Fabio Dei)认为,葛兰西狱中笔记中关于民俗的论述给意大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人类学研究带来了根本性的创新。(3)参见Fabio Dei, Cultura popolare in Italia: Da Gramsci all’Unesco. Bologna, il Mulino, 2018.美国民俗学者乔兰(DiarmuidGiolláin)认为,葛兰西对民俗的社会性定义指明了欧洲民俗学研究的另一种性质——“对进步的叙述”(narrative of progress)。(4)参见Diarmuid Giolláin, “Narratives of Nation or of Progress? Genealogies of European Folklore Studies,” Narrative Culture, vol.1, no.1(2014), pp.71-84.
在意大利,有关葛兰西民俗观的研究已十分丰富,但在意大利之外,他却很少被民俗学者所提及。美国民俗学者伯恩(Moyra Byrne)率先将葛兰西对意大利民俗学的贡献介绍到英文学界。(5)参见Moyra Byrne, “Antonio Gramsci’s Contributions to Italian Folklore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lklore Review, vol.2(1982), pp.70-75.美国民俗学者金卡莱拉(Stephen O. Gencarella)则受奇雷塞的启发,将葛兰西的“民俗”和他的“自发哲学”(filosofia spontanea)相联系,延伸了葛兰西的民俗观,并将之应用于批判民俗学(critical folklore)当中。(6)参见Stephen O. Gencarella, “Gramsci, Good Sense, and Critical Folklore Studies,” 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 vol.47, no.3(2010), pp.221-252.刘奕伶认为,葛兰西的思想基础是实践哲学,批判旧文化、创造新文化是其主要任务。沿着金卡莱拉的思路,刘奕伶将民俗阐发为“自发哲学”,在葛兰西的其他文本中寻找其民俗观与其思想整体的联系。(7)参见刘奕伶:《民俗的批判与批判民俗学——葛兰西论民俗》,《文化遗产》2018年第3期。但她缺乏对意大利学界观点的考察,行文中虽然提到了“文化领导权”,但只说“民俗是文化霸权斗争中重要的一环”,并没有进一步揭示葛兰西使用的“民俗”和“egemonia”这两个概念的内在联系。总的来说,中文学界中有关葛兰西的民俗观还需进一步研究和讨论。
一、葛兰西之前的意大利民俗学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民俗学整体上是浪漫主义、实证主义的,主要以材料收集为方法,以构建民族形象和精神为目的。浪漫主义时期和实证主义时期的意大利也有着十分丰富的民俗学研究积累,对此科基雅拉(Giuseppe Cocchiara)的记述最为详细和全面。(8)参见Giuseppe Cocchiara, Storia degli studi delle tradizioni popolari in Italia. Palermo, Palumbo, 1947(后再版为Giuseppe Cocchiara, Storia del folklore in Italia. Palermo, Sellerio, 1981);Giuseppe Cocchiara, Storia del folklore in Europa. Torino, Einaudi, 1952.科基雅拉认为,意大利的浪漫主义时期以维柯(Giovanni B. Vico)为起始,意大利学者对民间文化的研究兴趣从穆拉托利(Ludovico A. Muratori)的《中世纪意大利古风物》(AntiquitatesItalicaeMediiAevi)和卡尔梅利(Michelangelo Carmeli)的《神圣及异教风俗史》(Storiadivaricostumisacrieprofanifinoanoipervenuti),到普拉库奇(Michele Placucci)的《罗马涅农民的风俗与偏见》(UsiepregiudizideicontadinidiRomagna)(9)科基雅拉中原文的援引有误,将《罗马涅农民的风俗与偏见》(Usi e pregiudizi dei contadini di Romagna)误记为“《罗马涅农民的风俗与习惯》”(Usi e costumi dei contadini di Romagna)。,发生了从过去到现在的转变。在科基雅拉看来,贝尔谢(Giovanni Berchet)的《格里索斯托莫给小儿半严肃的信》(LetterasemiseriadiGrisostomoalsuofigliuolo)率先关注民间诗歌,认为意大利的新诗歌应该反映现实的情感和信仰,因为它们呈现了具体的现实。(10)参见Giuseppe Cocchiara, Storia del folklore in Europa. Torino, Bollati Boringhieri, 1971, pp.278-284.
在实证主义时期,科基雅拉认为,罗曼语族的语文学(filologia romanza)与民俗学研究联系最为紧密,并作为研究方法越来越受到民俗学者的关注,尼格拉(Constantino Nigra)是他们的代表。尼格拉凭借语文学的基础,创新了收集民间歌谣的方法,并率先将历史演绎的方法引入民间歌谣的研究,其代表作为《皮埃蒙特的民间歌谣》(CantipopolaridelPiemonte)。卢比埃里(Ermolao Rubbieri)收集了许多口头传承的民间诗歌,收集在《意大利民间诗歌史》(Storiadellapoesiapopolareitaliana)中;丹科那(Alessandro D’Ancona)的《意大利民间诗歌》(Lapoesiapopolareitaliana)则专注于对文本的语文学式的研究;同样专注语文学研究方法的还有曾与丹科那合作的孔帕雷蒂(Domenico Comparetti)。(11)参见Giuseppe Cocchiara, Storia del folklore in Europa. Torino, Bollati Boringhieri, 1971, pp.363-381.
在葛兰西之前的意大利民俗学研究领域,享誉最高、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当属皮特雷(Giuseppe Pitrè)。皮特雷于1841年出生于意大利西西里自治区首府巴勒莫(Palermo),在高中和大学阶段先后学习古典学和医学,后成为医生,得以与更多的当地民众接触。1871年,皮特雷出版了《西西里民间传承丛书》(Bibliotecadelletradizionipopolarisiciliane,以下简称《丛书》)的第一卷《西西里民间歌谣》(Cantipopolarisiciliane),至1913年,《丛书》共出版了25卷,内容包括民间歌谣、传说、谚语、戏剧、节日、偏见、信仰、风俗、医疗等。在每一个主题的序言中,皮特雷都会与此前意大利或欧洲的相关研究和争论对话,科基雅拉认为,《丛书》的所有序言集合在一起就是民俗学的一部理论性著作。(12)参见Giuseppe Cocchiara, Storia del folklore in Europa. Torino, Bollati Boringhieri, 1971, pp.386.《丛书》的最初几卷侧重19世纪民俗学研究的主题,如歌谣、传说、谚语等,但自19世纪80年代起,他更多地关注日常生活的实践领域,而这些内容常常并不像此前的研究对象一样被认为是“优美的”,而是普通和肤浅的,有时甚至被认为是古旧的、“原始的”。(13)参见Raffaele Corso, “Giuseppe Pitrè,” in Istituto della Enciclopedia Italiana, Enciclopedia Italiana, Roma, 1935. Disponibile su https://www.treccani.it/enciclopedia/giuseppe-pitre_%28Enciclopedia-Italiana%29/ (data di accesso 3/11/2022).1882年,皮特雷创立了《民间传承研究档案》(Archivioperlostudiodelletradizionipopolari);1891至1892年,举办了西西里民族志展览(Mostra etnografica siciliana);1894年出版《意大利民间传承书目提要》(Bibliografiadelletradizionipopolarid’Italia);1910年在巴勒莫大学文哲学院(Facoltà di Lettere e Filosofia, Università di Palermo)获得意大利民俗学研究领域(14)folklore和demologia是意大利民俗学稍晚一些的名称。皮特雷当时将其研究称为“民众心理学”(demopsicologia)。的第一个教席。
在浪漫主义时期和实证主义时期,意大利的民俗学研究经历了由兴趣到学术、由业余到专业的转变;虽然皮特雷的《丛书》中出现了日常生活领域转向的势头,但总的来说其研究对象主要还是民间诗歌、歌谣等文本;研究者也更多的是以语文学式的研究方法对这些文本进行收集、分类、整理、阐释、评论;研究成果则以构建民族形象、满足人们对本民族的想象为主,很少反映民众的实际生活境况和其遭受的苦难。因此,葛兰西认为这些研究只完成了学术性的收集工作,而在这些研究中,民俗是被当作“如画般的要素”(elemento pittoresco)被研究的。
二、葛兰西的民俗观
葛兰西并不以民俗学者身份自居,他本人也没有系统地从事民俗学研究。对意大利民俗学影响较大的是他狱中笔记中关于民俗的论述,能集中体现民俗观的部分位于该笔记第27卷《对民俗的评论》(Osservazionisulfolclore)一节。(15)folclore系英文单词folklore的意大利语化。葛兰西在笔记其他部分也有关于民俗的论述,参见Antonio Gramsci, Valentino Gerratana (a cura di): Quaderni del carcere. Torino, Einaudi, 1975, p.1105, pp.679-680.
在第27卷开篇,葛兰西从克罗乔尼(Giovanni Crocioni)对皮特雷的民俗材料分类的批评谈起:
克罗乔尼……批评Pitrè于1897年在《民间传承书目提要》导言中给出的对民俗材料的分类,认为此分类是混乱的、不精确的,并给出了自己的分类:艺术、文学、科学、民众的道德。但这个分类也被批评为不准确的、定义糟糕的、过于宽泛的。齐亚皮尼(Raffaele Ciampini)……问道:“这样的分类科学吗?举例来讲,如果这样分类,如何将迷信纳入?‘民众的道德’又指什么?如何科学地研究‘民众的道德’?并且,如果这样分类,为什么不(同样)讨论一种‘民间的宗教’?”(16)克罗乔尼(Giovanni Crocioni,1870-1954),意大利哲学家、语文学家、教育家。齐亚皮尼(Raffaele Ciampini,1895-1976),意大利历史学家。引文中提到的《民间传承书目提要》,即《意大利民间传承书目提要》(详见Antonio Gramsci, Valentino Gerratana (a cura di): Quaderni del carcere. Torino, Einaudi, 1975, p.2311)。尽管葛兰西的狱中笔记已有多个中译本,但它们多是英文或俄文版选编、节译版本的再选编与再节译,内容不完整。目前,葛兰西笔记中论述民俗的部分只有一篇名为《民俗学》的中文译稿,由吕同六翻译,收于他编译的《论文学》中。但该译文的着眼点是葛兰西的“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实践”,没有将民俗和葛兰西的思想核心产生关联,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葛兰西的独特用意。此外,该版本还存在一些漏译、误译的情况。综上,为了理解葛兰西的真实用意,本文主要参考1975年校勘本,选文皆由李正宇翻译。原文整理自葛兰西的手稿,其行文习惯也更多地体现他本人的思维过程,使得一些句子冗长且复杂难懂。译文尽可能呈现原文的思维逻辑关系而不擅自调整语序等表达方式,以求最大限度保留葛兰西的文风。
葛兰西认为,以皮特雷为代表的民俗学者的贡献在于两方面,一是材料收集,二是对材料收集方法的探索:
事实上,至今只做了一些学术性的材料收集工作,而民俗的科学也主要在于对这些材料的收集、挑选、分类方法的研究,即为了有益地开展某一方面的学问所需要的实践中的谨慎和经验性的原则。但不应该因此不承认研究一些伟大民俗学者的重要性和历史意义。(17)Antonio Gramsci, Valentino Gerratana (a cura di): Quaderni del carcere. Torino, Einaudi, 1975, p.2311.
但他们的工作存在着一个严肃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民俗主要是作为一种“如画的”要素被研究的。(18)Antonio Gramsci, Valentino Gerratana (a cura di): Quaderni del carcere. Torino, Einaudi, 1975, p.2311.
“如画的”(pittoresco)是十分恰当、传神的表达,意大利民俗学在浪漫主义和实证主义时期的积累就像画作一样被挂在墙上供读者欣赏,就连研究者自身也极少和当地人互动,他们的研究对象是文本而非人。由此,葛兰西表达了自己关于民俗的见解:
应该将民俗作为相当程度暗含的、社会特定(时间和空间)阶层的、和历史发展中出现的“官方”(或者更广泛一些,在历史上,社会中文化程度更高的部分)对世界的观念相对立的(这种对立也主要是暗含的、机械的、客观的)“对世界和生命的观念”来研究。(19)Antonio Gramsci, Valentino Gerratana (a cura di): Quaderni del carcere. Torino, Einaudi, 1975, p.2311.
这里,葛兰西阐释了民俗之“俗”的含义。不同于浪漫主义时期和实证主义时期的意大利民俗学者,葛兰西创造性地将民俗之“俗”定义为“对世界和生命的观念”,即世界观和人生观。在之前的研究中,“人”,或者说“民”,只是文本的载体,民俗学者重视的是他们承载的文本以及这些文本在他们之间传播的过程。一旦文本被采集完毕,他们与研究者的关联就结束了,接下来的工作是研究者对文本的分析。不仅如此,这些文本对现实的反映有一定迟滞,它被创造出来以反映过去的某个事件、某种情感、某种生活,但始终与当下有着一层分隔。但世界观、人生观是依托人而存在的,作为人的观念、认识,它是不断更新、变化的。如果将民俗之“俗”定义为世界观、人生观,民俗学研究的重点就在于认识和理解“民”不断更新、变化的世界观、人生观。这样一来,“民”就从被动的、提供文本的载体,成为主动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叙述者。之前实证主义的、语文学式的研究方法显然无法达到这样的目标,研究者需要深入“民”间,与“民”同吃同住才能做到对“民”之“俗”一定程度的理解和描述。
葛兰西不仅对“俗”有着清晰的描述,在对“民俗”的整体描述中,也给“民”下了确切的定义:
这种观念不仅是不精细、非系统性的,因为根据民众(即至今为止社会的所有形式的从属和工具性阶层的集合)的定义,他们在发展(尽管这种发展是自相矛盾的)中无法拥有精细的、系统性的、政治上有组织的、中心化的观念;而且是多样的、复杂的(不仅指不同的或相似的,也指从最粗鄙的到最不粗鄙的分层),如果我们甚至不能说它是一堆由历史上出现的所有对世界和生命的观念的碎片堆成的难以消化的混合物的话。这些碎片的大部分,或干脆说残缺的、受污染的材料只残存于民俗中。(20)Antonio Gramsci, Valentino Gerratana (a cura di): Quaderni del carcere. Torino, Einaudi, 1975, pp.2311-2312. 引文提到的“这种观念”是指民众的世界观、人生观,即“民俗”。
在葛兰西看来,“民”是“至今为止社会所有形式的从属和工具性阶层的集合”(l’insieme delle classi subalterne e strumentali di ogni forma di società finora esistita)。因为是“从属和工具性阶层的集合”,“民”的世界观、人生观缺少政治上的组织性和中心化,“不仅是不精细、非系统性的”,“而且是多样的、复杂的”,或许可以将之描述为“一堆由历史上出现的所有世界观、人生观的碎片堆成的难以消化的混合物”。在前文中,葛兰西也提到,民俗是“和历史发展中出现的‘官方’对世界的观念相对立的”。这里的“官方”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葛兰西将其阐释为“在历史上,社会中文化程度更高的部分”。显然,这种“官”性与“民”性的区分并非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或者,我们也可以将这种“官方”与“民间”直接理解为相对文化程度的高低,即一种势能差。
这种文化程度的势能差,会导致处于高位的文化的碎片自然地落入民众的认知当中,被拼凑成新的“难以消化的混合物”。同样不断坠入民众认知中的还有现代思想和科学:
现代思想和科学也持续赋予“现代民俗”新的要素,包括一些科学的概念和看法。这些概念和看法从它们的语境中脱离且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变形,不断落入民众的领地,并被“插入”传统的马赛克中……民俗只有作为民众文化生活状况的反映才能被理解,尽管民俗的一些观念在文化生活状况改变(或看起来改变)或给奇怪的组合以空间后仍然保持着。(21)Antonio Gramsci, Valentino Gerratana (a cura di): Quaderni del carcere. Torino, Einaudi, 1975, p.2312. 所谓的“马赛克”,喻指由各种文化碎片组成的混合物,亦即民俗。
综上,葛兰西对民俗总体上持消极态度。按照他的论述,民俗在官方的世界观面前,在更高程度的文化面前,在现代思想和科学面前都是处于低位的;民众不是文化的生产者,而是前述文化的接受、裁剪、拼接、缝合者。这种低位既是政治的、经济的,也是科学、思想方面的。若熟悉葛兰西,我们不难看出这样的民俗观背后是他的egemonia思想。
三、葛兰西民俗观的egemonia视角
1951年6月,在葛兰西研究会的推动下,罗马艺术剧院(Teatro delle Arti di Roma)举办了三场关于葛兰西《文学与民族生活》(22)《文学与民族生活》为葛兰西狱中笔记第一个版本的六卷之一,具体出版信息详见本文开头部分注释①。的讨论。其中,第二场讨论的主题是“葛兰西与民俗”(Gramsci e il folklore),参与学者有德马蒂诺、桑托利(Vittorio Santoli)、托斯齐(Paolo Toschi)。桑托利证实了葛兰西关于意大利文学自文艺复兴后脱离人民的观点;托斯齐一方面展现了葛兰西对故乡撒丁岛民间传承的热爱,一方面批评了葛兰西对民众主观能动性的忽略。(23)参见Paolo Toschi, “Dibattito su Gramsci e il Folklore,” Lares, vol.17(1951), pp.153-154. 桑托利的观点发表为 Vittorio Santoli, “Tre osservazioni su Gramsci e il folklore,” Società, n. 3(1951), 后收录于Vittorio Santoli, I canti popolari italiani. Ricerche e questioni. Firenze, Sansoni, 1979, pp.219-228.德马蒂诺在讨论中指出,葛兰西民俗观中的“民”是政治、经济方面的从属阶级(classi subalterne),而资产阶级则具有统领地位(posizione egemonica)。(24)Ernesto de Martino, “Gramsci e il folklore nella cultura italiana,” Il de Martino. Bollettino dell’Istituto Ernesto de Martino, 5-6(1996), pp.87-90.
德马蒂诺使用的形容词subalterno和egemonico,分别指“下级的、部下的、次要的”(25)北京外国语学院《意汉词典》组:《意汉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796页。和“掌握霸权的、统治的、支配的”(26)北京外国语学院《意汉词典》组:《意汉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68页。,它们清晰地指向了葛兰西的egemonia思想。奇雷塞持同样观点,认为虽然葛兰西并没有在对民俗的论述中直接使用egemonia相关表达,但实际上明显地表现了统领与从属的对立。(27)参见Alberto M. Cirese, “Concezioni del mondo, filosofia spontanea e istinto di classe nelle ‘Osservazioni sul folclore’ di Antonio Gramsci [1969-1970] ,” Lares, vol.74, no.2(2008), pp.467-498.可见,意大利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葛兰西的民俗观具有egemonia思想的视角。英文学术界也发现了意大利学界对葛兰西民俗观中“统领”与“从属”的强调。(28)参见Christie Davi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Folkloristics: Classic Contribution by the Founders of Folklore,” Alan Dundes (ed.), Folklore, vol.112, no.1(2001), pp.114-116. 本文转引自Stephen O. Gencarella, “Gramsci, Good Sense, and Critical Folklore Studies,” 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 vol.47, no.3(2010), pp.221-252.意大利文单词egemonia可以直接对应英文单词hegemony,但在中文语境中却面临着翻译的挑战。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其译名展开论述。有的学者认为应译为“霸权”,有的学者则认为应该译为“领导权”,还有观点认为egemonia主要指文化的方面,因而应该称之为“文化霸权”或“文化领导权”。(29)参见徐洁、戴雪红:《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近40年研究综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1期。
通过对葛兰西狱中笔记校勘本原文的考察,我们发现,葛兰西的egemonia有两种使用场景。第一种较为广泛,包括一国之内或不同国家之间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常常和表示限定的形容词并列,如“国际的”“政治的”等等。第二种则特指与政治社会(società politica)相对的市民社会(società civile)。葛兰西的确强调市民社会中的统治与政治社会中暴力的统治不同,强调文化的方面。但这种语境的特指只是葛兰西egemonia含义的一部分,不能因此以偏概全,认定它就是文化方面的。
事实上,egemonia本身指的是一种地位和权力的差异:它由地位高的向地位低的行使,由拥有权力的向该权力的对象行使。虽然只有一个单词,但它暗含的其实是一对相对的概念,在意大利语中是egemonia-subalternità。egemonia的占有或行使以这种地位和权力的延续为标志。换言之,地位高的继续保持高地位,拥有权力的继续拥有权力,并在一切相关方面保持这种首要性、优先性,继续拥有最终决定权和一票否决权,说明egemonia在被占有、被行使。相反,如果失去了原有的高地位和权力,不再拥有这种首要性和优先性,便说明失去了egemonia。
“霸权”和“领导权”的译法各有侧重,但在葛兰西民俗观的语境下,似乎都和葛兰西的原意有所出入。首先,霸权和领导权的区别在于是否存在着“同意”。葛兰西论述民俗时并没有直接表明民众对官方、对更高程度的文化、对现代思想和科学的接受是否存在着“同意”。事实上,葛兰西民俗观的语境并不强调霸权和领导权的区别,并不强调民众是主动处于低位(尽管这种“主动”本质上可能也是被动的)还是被动处于低位,它强调的只是民众处于低位这件事本身。其次,从“与官方相对立”“社会的所有形式的从属和工具性阶层的集合”等表达中,我们看到的不是葛兰西对文化方面的限定,而是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的混合。因此,egemonia在葛兰西的民俗论述中或可采取“统领”/“统领权”的译法,它兼有“统治”和“领导”的含义,也与原指更为契合。(30)我们曾就葛兰西使用的egemonia一词的内涵与译法就教于高丙中教授,他认为,egemonia实际上是一种具有霸权性的领导权,应采取“统领”/“统领权”的译法,既准确又显得温和。本文亦采用该译法。
四、葛兰西民俗观的传承和应用:德马蒂诺的“进步性民俗”
发现葛兰西民俗观中的统领权视角,使后来学者传承他的民俗观时与其思想的整体产生联系,尤为侧重于在无产阶级运动中的应用。葛兰西认为,民俗的教育的目的在于:
使广大人民群众的一个新文化诞生,现代文化和民间文化或民俗之间的分离将会消失。(31)Antonio Gramsci, Valentino Gerratana (a cura di): Quaderni del carcere. Torino, Einaudi, 1975, p.2314.
德马蒂诺指出,葛兰西谈到的“新文化”与无产阶级运动的推进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紧紧相连,其目的在于国家文化的统一;如果将葛兰西的民俗观放进其思想的整体和其讨论的根本问题中看待,就会发现葛兰西的民俗观与他的思想有着有机的、本质的联系。(32)参见Ernesto de Martino, Stefania Cannarsa (a cura di), “Due inediti su Gramsci ‘Postille a Gramsci’ e ‘Gramsci e il Folklore’,” La ricerca folklorica, no.25(1992), pp.73-79.事实上,作为共产主义者的德马蒂诺也正是葛兰西民俗观的直接传承者和应用者。
德马蒂诺于1908年生于意大利南部城市那不勒斯,父亲是铁路工程师,母亲是教师;大学期间参军,在间歇中完成了大学的学业,曾参加反法西斯活动;先后加入意大利社会党(Partito Socialista Italiano)和意大利共产党,在匈牙利十月事件后与意大利共产党逐渐疏远。他的学术和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意大利的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被誉为这三个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1949年,德马蒂诺发表《朝向下层民众世界的历史》(Intornoaunastoriadelmondopopolaresubalterno)(33)参见Ernesto de Martino, “Intorno a una storia del mondo popolare subalterno,” Società, 5, n.3(1949), pp.411-435.,在意大利学界引发了广泛的争论。德马蒂诺受葛兰西统领权视角的启发,强调对下层民众世界的关注,对到当时为止西方民族学研究的族群中心主义作了批判。他开篇明确指出,下层民众世界指的不仅仅是一国之内,而是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以及统领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工人与农民。显然,他是用葛兰西的统领权视角来思考的,他的下层民众世界指的正是被统领的群体。德氏提到,当时在世界范围内的下层民众为了进入历史而战斗。他们带着既有的文化习俗、对待世界的方式、千年轮回的信仰等等一同冲进了历史,必然会导致文化的“野蛮化”。他随即引用了葛兰西的观点,即需要创建一种新的文化来克服文化的这个民间阶段,这就在于从政治站位上进步性地利用下层民众世界的文化传统。
1951年,德马蒂诺发表《进步性民俗》(Ilfolkloreprogressivo),指出:
在工人运动及其最高理论意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推动下,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下层和工具阶级的民间文化生化传统迎来了真正的解冻……民众开始构建一种进步性民俗,用来对抗其下层社会地位,或用文化性的话来评论、表达使从其下层社会地位中获得解放的斗争。(34)Ernesto de Martino, “Il folklore progressivo (note lucane),” L’Unità, 28/6/1951.
德马蒂诺谈到,战争笼罩之时,不仅先锋作家和画家被动员起来,连卢卡尼亚(35)卢卡尼亚(Lucania),系意大利南部的历史区域。的农民都有他们的表达。其中一首具有当地传统旋律、由农家乐器伴奏的歌曲这样唱道:
他们给我们送了明信片,就好像是面包和酒一样。(36)Ernesto de Martino, “Il folklore progressivo (note lucane),” L’Unità, 28/6/1951.
这样的民歌民谣就是德马蒂诺鼓励发现和收集的进步性民俗。随后,德马蒂诺在杂志《人民日历》上向读者发出邀请,收集此类文本,并对征集文本的范围作了五点限定:(1)流行于民间,有一定传播范围;(2)过去和当下的皆可;(3)需要具有进步的内容,即政治、社会的内容;(4)方言和意大利语皆可;(5)投稿人应当提供有关稿件尽量多的信息。(37)参见Ernesto de Martino, “Il folklore. Un invito ai lettori del Calendario, ” Il Calendario del Popolo, n.7(1951), p.989.
不难看出,德马蒂诺强调进步性民俗的目的在于政治动员,鼓励下层民众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自身下层地位的反抗,推动无产阶级运动。因此,德马蒂诺对葛兰西的继承是多层次的,他用葛兰西的统领权视角看待民俗,提出进步性民俗的概念以期实现葛兰西的目标——创造新的文化,实现国家文化的统一。但德马蒂诺进步性民俗的主张与葛兰西在对民俗的论述中表达的观点有所不同。葛兰西认为:
国家并非不可知论的,而是有着它自己的人生观,并有着传播它的义务,同时教育国家大众……教育活动,并非凭空产生或开展:事实上,这种活动是和其他在明或在暗的观念相竞争和斗争的,而民俗在这些观念中并不占少数,其坚韧程度也不逊色,因此是需要“被克服的”。由此,认识民俗对于老师来说,意味着了解哪些其他世界观、人生观在更年轻一代的知识和道德实际形成中发挥着作用,以便用被认为是更优等的观念根除和取代它们……显然,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不仅要深化和扩展民俗的研究(ricerche folcloriche),还需要转变其本义。民俗不应被视为稀奇古怪的东西或一个如画般的要素,而应被当作一种十分严肃且应当被严肃对待的事物。只有这样,教育才会更加有效并真正使一种新的文化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诞生,现代文化和民间文化或民俗之间的分离将会消失。这种活动若进行彻底,或将在知识层面与新教国家中的宗教改革意义相一致。(38)Antonio Gramsci, Valentino Gerratana (a cura di): Quaderni del carcere. Torino, Einaudi, 1975, p.2314.
可见,葛兰西对民俗的态度是消极的,认为研究和教授民俗的目的在于了解它,并创造出能够联合不同阶级的新文化来取代它。德马蒂诺则没有对民俗全盘否定,而是发现了民俗中具有进步性的部分,并主张利用进步性民俗实现向新文化的过渡。
德马蒂诺的主张无疑发展了葛兰西的民俗观,并使之真正应用到了无产阶级运动当中。尽管坎纳尔萨(Stefania Cannarsa)通过对德马蒂诺进步性民俗概念产生过程的梳理,发现德马蒂诺此概念的提出更多地受到前苏联民族学的启发(39)参见Stefania Cannarsa, “Genesi del concetto di folklore progressivo in De Martino,” La ricerca folklorica, no.25(1992), pp.81-87.,但事实上,这其实与葛兰西的影响并不冲突。葛兰西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在监狱中的写作也一直围绕着共产主义事业展开,其目的是创造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而前苏联正是这样一个范本,他沿着葛兰西的思想和主张发现了前苏联民族学研究实践中的先进经验,并用它回答了葛兰西设下悬而未决的难题,这是自然而然的。
五、结语:葛兰西民俗观的现今延续与影响
20世纪50年代后期,作为葛兰西民俗观应用的“进步性民俗”概念随着德马蒂诺与意大利共产党关系的疏远逐渐被舍弃(40)参见Stefania Cannarsa, “Genesi del concetto di folklore progressivo in De Martino,”La ricerca folklorica, no.25(1992), pp.81-87.;20世纪80年代开始,奇雷塞等民俗学者也不再将葛兰西作为思考的重点。(41)参见Fabio Dei, “Gramsci, Cirese e la tradizione demologica italiana,” Lares, vol.77, no.3(2011), pp.501-518.表面上看,葛兰西的民俗观似乎已不是意大利民俗学界直接关注和讨论的核心话题,但实际上今天意大利的民俗学研究正是以葛兰西的民俗论述为基础的。葛兰西的民俗观使意大利民俗学发生了从研究文本到研究生活,从只关注“俗”到将“民”与“俗”结合,从以搜集、分类、整理为主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到以注重实地调查的社会科学的调查研究的多重转变。这样的转变使意大利民俗学与文学疏离,逐渐接近民族学和人类学。由此,奇雷塞在《统领文化与从属文化》中将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国内的文化差异(dislivelli interni di cultura),将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国外的文化差异(dislivelli esterni di cultura)。(42)参见Alberto M. Cirese, Cultura egemonica e culture subalterne. Palermo, Palumbo, 1973, p.10.现在,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在意大利已不再是彼此独立的学科,而是合并为“民俗-民族-人类学学科”(M-DEA/01)(43)经过学科设置的改革,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在意大利被合为一体,称为“民俗-民族-人类学学科”(le discipline demo-etno-antropologiche),简称“M-DEA/01”。。因此,可以说今天意大利的民俗学、民族学和人类学格局的基础是受葛兰西的影响而逐步形成的。
此外,由葛兰西的民俗观衍生出的“进步性民俗”与现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着内在的一致性。高丙中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把人民日常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发现出来,以文化遗产的名义让它们永远传承下去,代代乐享”(44)高丙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中国属性》,《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0年第1期。。德马蒂诺主张从下层民众世界的文化中选取具有进步性的内容,使下层民众的声音被听到,使他们的文化被欣赏,甚至使之成为动员他们反抗自身下层地位的号角。这种对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的关注源于葛兰西。
葛兰西一直对意大利南部人民有着深深的同情和关切,他认为意大利的南方问题是由意大利的历史决定的,对此他在狱中笔记里有着多处论述。(45)意大利北方与南方在经济发展、现代化程度等各个方面有着显著差异。人们通常认为,北方更为开放、现代、发达,而南方则更为保守、传统、落后,今天依然如此。意大利南方的这种情况被称为“南方问题”(la questione meridionale)。相关论述,参见Antonio Gramsci, Valentino Gerratana (a cura di): Quaderni del carcere. Torino, Einaudi, 1975, pp.47, 82 &2021.尽管他在具体论述中对民俗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但他却深深热爱自己的家乡撒丁岛,并在狱中和妹妹的通信里表达了对孩子学习撒丁语的坚持,并认为撒丁语不是方言,而是一门语言。(46)[意]葛兰西:《狱中书简》,田时纲译,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9页。事实上,他对民俗复杂的感情在他对民俗的论述中也有所体现。在谈到民众的道德时,他认为:
(民众的道德)一些是僵化的,反映过去生活的情况,并因此是保守的、反动的;一些则是一系列的创新,常常是创造性的和进步性的,由发展过程中生活的方式和情况自然形成的,和统治阶级的道德相左或仅仅是相异的。(47)Antonio Gramsci, Valentino Gerratana (a cura di): Quaderni del carcere. Torino, Einaudi, 1975, p.2313.
这种对意大利南部人民的同情还影响了来自那不勒斯的德马蒂诺。尽管德马蒂诺逐渐放弃了“进步性民俗”的主张,但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写就的几部著作(48)即《古代世界的死亡与仪式性哭丧》(Morte e pianto rituale del mondo antico)、《南方与巫术》(Sud e magia)、《回咬之地》(La terra del rimorso)。都聚焦于意大利南部。特别是在研究塔兰托现象(tarantismo)的《回咬之地》中,他认为南部人民的巫术与宗教实际是在面对现代思想和文化的一种存在主义的挣扎。(49)Ernesto de Martino, La terra del rimorso. Milano, Il Saggiatore, 1961, pp.44-45.
现在,葛兰西和德马蒂诺这种同情、关切和尊重的文化态度在意大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中得以延续和发展。意大利政府十分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更名后的该国文化部(50)意大利文化部(Ministero della cultura)1974年初创时名为“文化和环境财产部”(Ministero per i Beni Culturali e Ambientali),先后于1998年和2013年更名为“文化财产和活动部”(Ministero per i Beni e le Attività Culturali)和“文化财产和活动及旅游部”(Ministero dei beni e delle attività culturali e del turismo),2021年起更至现名。从意大利文化部曾用名可以看出,文化财产保护一直是意大利文化部的主要工作内容。下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办公室(Ufficio UNESCO),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其主要职责之一。目前意大利共有16个项目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其中包括葛兰西家乡撒丁岛的“多声部民歌”(canto a tenore sardo)在内的8个遗产项目由意大利政府独立申报。在意大利,不仅各级政府部门重视非遗保护工作,民间也积极参与其中。受塔兰托现象启发,致力于发扬传统音乐的“塔兰托之夜”(Notte della Taranta)音乐节于1998年开始每年举办一届,至今已26届。由此可见,葛兰西对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的同情和关注正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下去,普通人越来越受到尊重,普通人的文化也越来越为人们所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