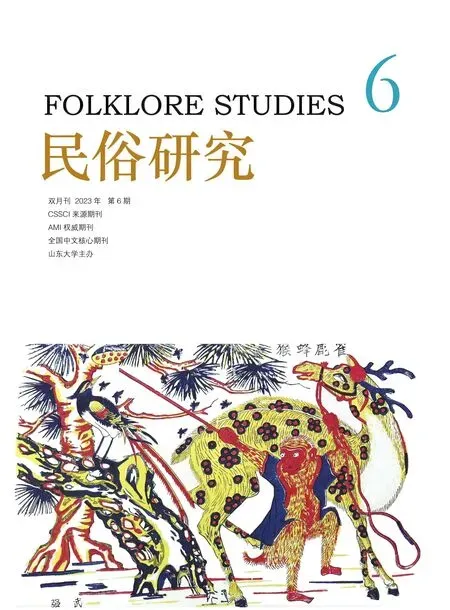从平面社会到垂直整体
——费孝通与马林诺夫斯基思想的中国转化
2023-10-25王燕彬
王燕彬
一、导言:文化科学与超社会的文明
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人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一生追求建立一种“文化的科学”。他认为这种科学并非自然科学的从属,而是真正的、对人的科学研究。(1)Bronislaw Malinowski, A Scientific Theory of Culture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与之不可分割的是他对文明的思考,他试图通过参与观察式田野工作进行彻底的方法论革命和理论范式更新,以实现对世界文明的整全理解。为此,他主张对孤岛式的文化整体(the integral whole)进行个案民族志研究(2)虽然费孝通等人的“社区”一词直接翻译自派克(Robert Park)的“community”,但马林诺夫斯基功能主义人类学对20世纪早期“社区研究”之形成有重要影响。费孝通在总结中国社区研究的历史时指出,社区研究诞生于对社会分析完整性的需求,而马氏基于特罗布里恩岛调查的孤岛式文化整体研究正符合这种需求,于是“这种人类学的社区研究方法介绍到中国,形成了中国社区研究的主流”(费孝通:《二十年来之中国社区研究》,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5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531页)。他晚年回顾早期实地调查时也说:“我们自动地,并非有意识地跟着马老师当时正在构思的《文化论》和‘文化表格’所指导的方向行动了。”见费孝通:《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3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420页;另见丁元竹:《中文“社区”的由来与发展及其启示——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110周年》,《民族研究》2020年第4期。,通过长期深入调查单个小型社区,将其物质、精神、社会组织、语言等各文化方面作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进行考察。(3)参见王铭铭:《小地方与大社会——中国社会的社区观察》,《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1期。进而,他强调文化要素的功能性和情境性,每个文化都特殊而不可公约,只有在具体语境中才能真正理解文化现象,这是参与观察方法的基石。基于此,他展开了对特罗布里恩岛的研究。但同时,其视野并不局限于特定的小型孤立社区,而是试图把握更宽广的文明。一方面,他的文化科学理论依赖一种“普遍人性假设”,即人共通的生理-心理需求及其满足是文化和社会构建的基本前提和动力机制。这导向了文化普遍论,即每个文化的构成方式和逻辑是相同的,特罗布里恩岛部落与欧洲社会并无实质不同。(4)参见[英]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美拉尼西亚新几内亚群岛土著人之事业及冒险活动的报告》,弓秀英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6-27、48页。另一方面,马氏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非洲研究和《文化动态论》(TheDynamicsofCultureChange)中也超出了封闭社区的文化想象,试图考察高度复杂的文化变迁与文明互动,可惜的是,他在孤岛式个案民族志方法和普遍开阔的文明视野间陷入了徘徊。
在此背景下,马林诺夫斯基特别关心如何使其方法论跨越“文野之别”,也期待着来自东方的声音,并积极与中国学者合作,将其文化科学探究从简单社会投向广阔而复杂的文明。于是,不仅功能主义传入了中国,中国文明的经验也反哺着马氏的思想。1936年,吴文藻离开伦敦之际,马氏将《文化论》文稿赠与他,后由费孝通翻译连载,并作为《社会学丛刊》甲集之首出版,以图“促使社会学之中国化”(5)参见吴文藻:《〈社会学丛刊〉总序》,吴文藻:《论社会学中国化》,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7页;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6-32页。。《文化论》是马氏文化科学理论的纲领性著作,不仅系统论述了马氏的功能主义学说,所附的方法论性的《文化表格》也特别为吴文藻所看重,吴氏对其加以详述,以帮助中国学者进行田野工作。(6)参见吴文藻:《论文化表格》,吴文藻:《论社会学中国化》,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69-332页。《文化论》揭示了马氏文化科学理论的两大支柱:功能论和整体论。在理论上,以文化的整体和功能反对文化形式论、文化实体论;在方法上,借实地观察进行社区文化之整体、文化要素之功能的研究。(7)参见费孝通:《〈文化论〉译序》,费孝通译:《费孝通译文集》上册,群言出版社,2002年,第293-296页。而费孝通作为马氏的学生深受其影响,直至晚年仍在研读马氏的《文化论》《文化动态论》等著作。可见,马氏功能主义理论与个案民族志研究方法在中国影响甚大。与此同时,马林诺夫斯基也极为关心中国问题。在费孝通留英时,马氏亲自担任他的导师,在课上逐章讨论他的博士论文。在《〈江村经济〉序》中,他写道:研究人的科学、未来的人类学不仅要对原始人有兴趣,而且要关注有重要政治经济地位的民族的文化研究,中国正承担着作为文化科学之人类学的“未来”理想。(8)参见[英]布·马林诺斯基:《〈江村经济〉序》,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2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216页。留英归国后,费孝通也谈道:“我必须在建立一门研究人的科学以及在使一切文明之间真正合作上分担他那沉重的负担。”(9)费孝通:《江村经济》(修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页。关于费孝通赴英时与马林诺夫斯基的详细交往,参见张冠生:《费孝通传》,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133-172页。
马氏所面临的个案方法与广阔视野间的张力及其对中国文明的关切可以进一步纳入到“文化”与“文明”的概念分野中,尽管他在使用上不太区分二者的语义。社会人类学中的“文化”概念发端于19世纪德语传统的“民俗心理学”,并由博厄斯(Franz Boas)带入美国人类学传统,在英国人类学界则因拉德克里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影响深远。“文化”概念与18世纪以来的欧洲国族主义有密切关系,强调一个群体明确的自我认同与清晰的社会边界,将这个社会和文化的内部与外部强烈地区分开。受此观念支配,“文化”人类学研究聚焦于单一的、孤立的社会内部的社会和文化现象。沃尔夫(Eric R. Wolf)指出,这种研究方式本身是西方自身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投射。(10)参见[美]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赵丙祥、刘传珠、杨玉静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15页。与之相对,“文明”的概念源于英法传统,并在莫斯(Marcel Mauss)的讨论中发扬光大。它强调社会现象没有清晰的边界,也并非孤立存在,文明是一个超出个别社会的、多层次的、具有广泛内外关系的文明复合体,或者说“超社会体系”。中国社会正是一个典型的“超社会体系”,为复合的文明体观念提供了可贵的例证。(11)参见王铭铭:《超社会体系:文明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68-70页。
在这个脉络下,马氏的心态可被更深入地理解。他的文化科学奠基于单一社区的动力学机制,即一个完整的社会如何在普遍的人性需求上根据特殊化的情境条件生成,强调通过个案民族志进行参与观察式的田野工作,这无疑处在“文化”概念的范围之内。(12)Bronislaw Malinowski, “The Group and the Individual in Function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no.6(May, 1939), pp.938-964. Bronislaw Malinowski, A Scientific Theory of Culture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同时,他并不止步于此,而是希望进一步探讨超社会的文明关系。这亦是费孝通的关怀。他说:“我们必须记住整体还有层次,没有和周围隔绝的系统,也没有真正自给自足的社区。在现实中社区的最高层应包含整个世界。一切概念上的整体是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13)费孝通:《经历·见解·反思——费孝通教授答客问》,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1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203页。因而,费孝通对于马氏理论与社区研究方法的继承和发展,体现出他如何在后者基础上实现对于整全的、超个体社会的中国文明的理解,解决马氏未竟的难题。
有学者指出,费孝通早期的《江村经济》和晚年的“利奇-费孝通之辩”作为关键文本构成了连续的问题线索,即马林诺夫斯基以微型社区作为调查研究的基本单位,主要适用于微型、封闭、同质性强的原始部落社区,而费孝通通过类型比较等方法将其推广到中国研究中,实现了人类学从简单文明到复杂文明的重要转折,跨越了文野之别,将研究对象从异域社会转向本土社会。(14)参见谢立中:《从马林诺斯基到费孝通:一种另类的功能主义》,谢立中主编:《从马林诺斯基到费孝通:另类的功能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53-358页;[美]大卫·阿古什:《费孝通传》,董天民译,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7-68页;邱泽奇:《费孝通与江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3页。其次,马氏强调的“参与观察”调查方法是费孝通晚年重视人的观念和心态的线索之一。(15)参见周飞舟:《将心比心:论中国社会学的田野调查》,《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他晚年探讨的“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与马氏在《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中总结的田野中的“不可测度”遥相呼应。第三,费孝通受到马氏文化变迁研究的启发,将“无历史”的功能主义发展为可以认识文明之历史的历史功能主义,将文化的历史性纳入功能主义研究。(16)参见杨清媚:《最后的绅士: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9年,第58-61页;乔健:《试说费孝通的历史功能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本文将进一步探讨为什么费孝通凭借上述对马氏功能主义的发展能够把握复合的中国文明整体,以及他为什么能实现这些发展。下文将从三个方面进行讨论:第一,从空间到时间,费孝通在两个维度上拓展了马氏方法。空间上的类型比较法未能完全把握中国文明整体,他从时间历史的角度进行了开创性尝试。第二,费孝通从单一的文化和社区研究开始,逐步将研究拓展到复合的文明体系,再到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第三,这背后是费孝通与马林诺夫斯基在科学观念上的差异,费孝通的实在论观念使其能够超出马氏基于单一社区的功能主义研究的界限,进行类型比较,以逼近中国社会之整体。同时,他根据马氏文化科学的思路,将历史维度还原于个体的自然本性之上,进而贯通中国文明整体,促成了马氏文化科学的历史化,开创了历史功能主义。
二、空间性完整:中国实地研究之方法
费孝通首先试图以“类型比较法”在空间上拓展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方法,从而通过对小型单一社区的深入研究,逐步逼近复合的中国文明整体。他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一突破,是因为他和马林诺夫斯基的学说建立在不同的科学观念基础之上。
(一)两种“社会整体性”:孤岛式文化整体与文明复合体
马林诺夫斯基个案民族志方法的理论基础是文化“整体性”学说。他将“文化”界定为人类出于自身基本或衍生需求进行的创造,人因此进行协作和组织,所以文化将个体转变为团体。一个文化的各个方面或制度组织都满足着人的不同需求,知识、巫术、宗教、艺术等则填补这些制度组织之间的空隙,并消除内在矛盾和社会混乱。(17)参见[英]马林诺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费孝通译文集》上册,群言出版社,2002年,第275、285页。因此,一个文化整体必然对应着一个完整的社会。特罗布里恩岛社会之所以有一个完整的文化,正是因为在这个社区中人们的各种需求能够被完整地满足。费先生精辟地指出,根据马氏理论,像江村或特罗布里恩岛这样小型社区中的居民“生活在这社区的人文世界里,他们所生活在其中的人文世界却是个整体,因为它满足了这个村子居民的全部生活。它包括了马老师所讲到的文化的诸方面和所有的社会制度。这些方面,和这些制度又是密切地有机联系成一个体系”(18)费孝通:《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3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422页。。故而,马氏认为,一个分立小型社区的文化对于其中的个体而言是充分而自足的,通过深入的参与观察能获得对其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的整全理解。
但费孝通和马氏的研究对象在规模上有根本不同。马氏考察的文化整体是小型单一社会(19)弗斯(Raymond Firth)将此发展成“微型社会学”的概念,试图以一个小型社区或较大社会的一部分为对象进行研究,要求研究者亲自参与其中并进行密切的观察。参见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4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13-49页。,而费孝通始终关心更为宏大的中国社会整体。无论江村还是禄村,这些马氏文化整体标准上的小型社区只是费孝通试图理解的中国社会整体的一部分。利奇(Edmund Leach)指出,这必然导致马氏功能主义的方法论无法适应费孝通的研究需要。(20)Edmund Leach, Social Anthropology. London: Fontana Paperbacks, 1982, p.127.详细讨论见梁永佳:《本土人类学与多重普遍性:重新思考“利奇-费孝通之辩”》,《民俗研究》2022年第6期。1990年费孝通阅读到利奇的评论时说:“如果我学人类学的志愿是了解中国,最终目的是改造中国,我们采取在个别小社区里进行深入的微型观察和调查的方法,果真能达到这个目的么?个别入手果真能获得概括性的了解么?”参见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缺席的对话》,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2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45页。实际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观念是燕京学派的共识,这是吴文藻等人在20世纪30年代引介功能主义的关键原因。(21)参见费孝通:《〈文化论〉译序》,费孝通译:《费孝通译文集》上册,群言出版社,2002年,第293页。燕京学派将马氏功能理论及社区调查方法与布朗的社会比较研究法、派克的人文区位学结合,力图把握中国社会的普遍原则和基本结构,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深入认识。(22)参见吴文藻:《社区的意义与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吴文藻:《论社会学中国化》,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39-461页。
如何从小型社区到中国整体,费孝通的经典解决方案是“类型比较法”,他试图以此从单个社区研究的“点”到多个社区的“面”,从特殊到一般,通过空间上的拓展逐步接近中国社会整体。类型比较法的三个步骤为:首先,研究者将单个社区作为某一社区类型的代表进行深入研究;其次,确定研究的代表性类型后,根据此类型关涉的普遍意义问题决定如何记录和研究社区中的具体信息;最后,对不同类型进行比较以获得普遍的概括。(23)参见费孝通:《禄村农田》,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2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411-413页。费孝通晚年在回顾禄村的研究时更系统地论述了这种方法,即先对一个具体社区进行解剖,掌握其社会结构的内部联系和产生条件,然后观察其他社区,与之比较,进行归纳,产生不同类型和模式,再进一步扩大实地观察的范围,由点到面,由局部接近整体。(24)参见费孝通:《〈云南三村〉序》,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1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138页。
表面上,费孝通和马林诺夫斯基的分岔仅仅在于马氏主张对单一小型社区的文化整体进行深入的考察,而费孝通试图在其基础上用类型比较法超出小型社区的界限,以对复合庞大的中国社会整体展开探究。但实际上,二者有着更为深层的、思想脉络上的分别,费孝通在空间上拓展马氏社区研究方法的关键是二者不同的科学观念。
(二)实在论与经验批判主义:方法论的科学观念基础
马林诺夫斯基并不反对“比较”本身,但对比较的基础和限度十分警惕。这个态度源自他的思想立场:排斥一切形而上学的假设,进行彻底的经验主义研究。马氏认为,不能假设任何文化和社会中的要素是自在自存的实体,更不能基于这一“假设”进行文化研究,因为一切社会文化要素的意义都存在于关系中,即它们必然直接或间接地满足着这个社会文化中个体的需求。研究者不能脱离文化要素在具体情境中的关系来抽象地研究它们,否则就会陷入古典人类学进化论和播化论的窠臼。马氏认为,同一个东西在不同文化中所起的作用和承担的角色是不同的。比如,同样的木杖,在一个文化中被用来撑船,而在另一个文化中被用作武器,所以不能谈论木杖的形式意义本身,只能考察它在各个文化中的功能。(25)参见[英]马林诺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费孝通译文集》上册,群言出版社,2002年,第209-212页。
马氏这一认知有哲学与科学观念的基础。在到英国之前,他在波兰学习物理学和哲学,深受马赫主义的影响。马赫(Ernst Mach)认为,一切事实或真理都基于经验而建立,每个现象都不是独立自存的,任一现象都应当被描述为关于其他现象的函数。(26)参见[奥]恩斯特·马赫:《能量守恒原理的历史和根源》,李醒民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75-76页;李醒民:《激动人心的年代: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的历史考察和哲学探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1-42页;[美]卡尔·门格:《1960年美国第六版引言》,[奥]恩斯特·马赫:《力学及其发展的批判历史概论》,李醒民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7-8页。因此,科学的目标在于经验的系统化,而不是探寻现象背后是否有一个真实的世界。与之相对的是牛顿式的经典物理学,基于一种“实在论”的世界观,主张现象背后有客观的物理世界和实体。(27)参见[美]P.G.伯格曼:《马赫和现代物理学》,[美]R.S.科恩等编著:《马赫:物理学家和哲学家》,董光璧等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90-91页。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彻底取消了实体与表象、精神与物质、自我与对象、主体与客体等传统二元对立的命题,颠覆了西方思想中认为现象之后有客观实在世界的长久观念。(28)参见[奥]马赫:《感觉的分析》,洪谦、唐钺、梁志学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29页。他主张一种“非实在论”,即一切事物都不是独立、实在、自存的,只能相对于观察者而存在,即所谓的函数性。“我”所感受到的某个“对象”,其本身并不存在,只是在具体的环境中被“我”感受到了。

而费孝通类型比较法的本质与马赫主义截然不同,其所依据的是“实在论”和经典物理学式的科学观与世界观。因为它必然要探讨一种客观的、可度量的社会结构及社会法则,要将其抽离出具体的现实环境而当作一种客观的“物”进行比较。费孝通自述,他的类型比较法最早源自同史禄国(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v)学习的生物学和体质人类学。(33)参见费孝通:《人不知而不愠——缅怀史禄国老师》,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3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82页;费孝通:《从史禄国老师学体质人类学》,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4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116-117页。这些学科强调比较生物体客观的、可测量的解剖学特征,无疑是一种经典的实在论科学。进一步,这种方法在弗斯和布朗的“比较社会学”理论中得到印证。(34)参见费孝通:《〈人文类型〉重版前言》,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1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293-297页。1944年,为在云南大学的授课提供比较社会学的教学参考书,费孝通翻译了弗斯的《人文类型》,作为《社会学丛刊》甲集第三种在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参见费孝通:《〈人文类型〉译者的话》,费孝通译:《费孝通译文集》上册,群言出版社,2002年,第471-472页。虽然布朗来华讲课时费孝通在广西瑶山工作,二人擦肩而过,但是费孝通对其学说极为熟稔。参见费孝通:《经历·见解·反思——费孝通教授答客问》,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1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191页。布朗来华对当时燕京大学学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35)参见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社区与功能:派克、布朗社会学文集及学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39-448页。相对于马赫和马林诺夫斯基,布朗无疑是个实在论者。他依据库尔诺(Antoine Augustin Cournot)的讨论指出科学方法论问题的关键是区分历史的方法与归纳、通则的方法,前者是古典人类学的方法基础,后者则是比较社会学的根基。(36)参见[英]拉德克利夫-布朗:《社会人类学方法》,夏建中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43-68页。他认为,比较社会学“将自然科学的通则方法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现象,以及文化或文明这个术语所包辖的一切东西”(37)[英]拉德克利夫-布朗:《社会人类学方法》,夏建中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51页。。而社会人类学作为一门科学所追求的规律、通则,只有通过对不同形式的文化比较才能获得。相比马林诺夫斯基学说,显然布朗认为文化要素和田野信息本身包含一种客观的社会现实。因此,比较社会学可以将特殊的社会现象从其所处环境中剥离出来,而获得对实在的、一般性的普遍社会法则的把握。
燕大学人普遍认为布朗的实在论观念是一种科学的观念。吴文藻就强调,布朗受过严格的自然科学和实验科学训练,又经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和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科学方法论陶冶,“追求一般的社会学法则”,以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社会学的实地研究。进而,社会比较方法实际上类似于自然科学中的实验方法。(38)参见吴文藻:《布朗教授的思想背景与其在学术上的贡献》,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社区与功能:派克、布朗社会学文集及学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48-249、255-256页。相较之下,马氏的方法反而不够“科学”。(39)吴文藻认为布朗的一大贡献就是认识到了关系论,即在一个社区中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相互关联而成为一个整体,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脱离其在这个整体中的关系来看。参见吴文藻:《布朗教授的思想背景与其在学术上的贡献》,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社区与功能:派克、布朗社会学文集及学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54-255页。此观点看似和马氏的函数关系论相似,实则有根本的差别。布朗和吴文藻强调的是文化要素之间相互关联,但并不否认文化要素及其背后的社会法则的客观实在性和普遍性。而马氏则认为文化要素之间不仅是相互关联的,还是互相依存的。“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的实验式的工作方法才是科学的社会学研究方式。费孝通也将这种方法称为“实验社会学”。(40)参见吴文藻:《〈社会学丛刊〉总序》,吴文藻:《论社会学中国化》,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4页;费孝通:《伦市寄言》,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400页。因而,吴文藻、费孝通等学者在接受布朗的社会比较方法时,已有实在论的观念基础,试图通过布朗式的“科学”方法去把握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背后客观的、实在的一般社会法则与真理。
费孝通虽然不了解马林诺夫斯基的思想根源来自马赫,但他捕捉到了不同认识论基础带来的不同理论与方法效果;他对马氏方法论的改造,正以费孝通本人的实在论、认识论思想为前提。费孝通曾多次批评马氏缺乏普遍性,比如在1948年的《二十年来之中国社区研究》中,他在叙述了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的人类学方法能够深入、系统地探讨一个社区之后,笔锋一转指出,“但有一个问题发生了,社区研究只是限止在较小范围的个别社区上,每个社区有每个社区的特性,如何综合不同的社区研究,形成对于一个社会的普遍了解呢?应看这种需要,遂有比较社区研究出现,就是在不同的社区研究间总得预先规定一个理论,或一个主题、一个现象,看它在不同社区中,有什么表现方式、不同形态、不同发展,在这些不同中,加以比较参照,归纳出一个较为普遍的东西,这就是type。这比单纯的社区研究就更进一层了”(41)费孝通:《二十年来之中国社区研究》,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5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531页。。他意识到马氏学说本身不能真正达到一种普遍的社会法则,而中国当前社区研究的进展正在于通过比较研究实现这种普遍性。在马氏看来,这种脱离具体情境的普遍客观性是虚妄的,但普遍、客观的社会法则正是费孝通的实在论立场所追求的知识形态。事实上,如果不是实在论的思想基础让不同社会间的比较研究成为可能,费孝通也无法指出马氏“孤岛式文化整体”研究将社区研究限定在小型、孤立、单一社会的藩篱之中的问题,并通过比较方法改造和拓展马氏方法。
不仅如此,在费孝通看来,参与观察方法存在内在困难和“整体性”把握的危机。在40年代的《禄村农田》中,他含蓄地指出,根据马氏的方法论,“要完整地研究社区生活,调查者必须把他的观察领域限制在一个很小的区域,这样他自己才能完全地参与进去。于是问题就出现了:对每一个社区做深入研究的可能性有多大?何况,观察中的深入度是没有极限的”(42)费孝通:《禄村农田》,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2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409页。。单一社区的研究无法从自身内部提供整体性的判断标准,只能不断陷入田野信息的汪洋大海之中,永无尽头。而费孝通的“类型”为社区信息的完整性提供了判断标准,只要满足类型所需求的信息,对于相关单个社区信息的记录就是完整的。
因此,费孝通之所以不完全同意马氏桎梏于社区边界之内,并试图在马氏的研究基础上进行空间上的拓展以把握中国社会之整体,其在思想上的关键原因之一是费孝通等人的一种实在论式的科学观念和世界观,这一观念使得他们认为可以通过类型比较方法来获取掩藏在繁杂社会现象背后的中国社会的一般性事实与法则。
(三)空间拓展方法论:微积分的几何图景
此种科学观念和思想背景是费孝通将类型比较方法运用于理论与田野工作的重要原因,由此他建立起从微型社区到中外文明间的系统性比较体系。首先,费孝通强调在中国社会内部的各个社区之间进行比较,建立起“类型”,并对这些不同类型进行比较。早在1936年的《伦市寄言》中,费孝通就指出应当在当时分头探索的各个社区研究之间进行“比较”。(43)参见费孝通:《伦市寄言》,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400页。40年代《禄村农田》等工作正是按照这个路线进行的。在《江村经济》中,他提出从传统手工业崩溃与现代工商业入侵的角度来解释土地制度,但仅有江村一个社区无法充分证实这个观点,于是在《禄村农田》的研究中,他试图通过考察一个受现代工商业影响较小的农村,来和江村进行类型比较,考察它们的土地制度的异同及其因果。(44)参见费孝通:《〈云南三村〉序》,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1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137页。其次,比较的范围甚至应当超出中国社会的界限,对比中国研究和国外相关研究。费孝通指出在此之后,“我们可以逐渐介绍国外社区研究的结果。好像澳洲Trobriand岛土人中父子之爱和母系制度的冲突正可用来和我们父系制度中父母对儿女的感情和婚姻礼俗的关系之相对照”(45)费孝通:《伦市寄言》,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400页。。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将西方世界的团体格局与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进行对照,这也是比较思路的实践。50年代以后,费孝通更将比较方法拓展到对中国各民族的研究上。他主张以直接访问的方式了解各民族情况,再对其进行分类比较,以此掌握各民族历史和发展的革新性和共性,从而逐步形成全面宏观的认识。(46)参见费孝通:《谈民族调查工作的微型研究》,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8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277页;费孝通:《〈盘村瑶族〉序》,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9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92-93页;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4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88-105页。
为什么类型比较法能够实现对中国社会的完整考察?这个方法分为两个相互依赖的层面。第一个层面可称为“逐步寻找一般规则”,第二个层面为“微积分式的加和”。
对于前者,费孝通基于实在性观念,期待从个别的社区研究中逐步发现中国社会的一般性规则或社会事实,从而实现对中国社会普遍、客观、完整的描述。类型比较法正是从个别通向一般的方法,是在“社会调查和普遍的概括之间建造一座桥梁”(47)费孝通:《禄村农田》,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2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411页。。它能够实现理解中国社会之完整性的必然前提是:中国社会尽管多元而复杂,但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一般性和普遍性,能够对各社区根据其条件结构进行分类。(48)参见费孝通:《〈云南三村〉序》,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1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132-139页。因而,中国社会的类型及其条件与社会结构是有限的、可穷尽的。进一步,各个类型背后有着一套客观实在、普遍有效的社会事实或社会法则。在不同类型之间进行比较,就是试图寻找其背后的社会普遍性。
为此,费孝通在运用类型比较法时使用了布朗式的“假设-检验方法”。根据假设-检验方法,社区研究的出发点是一套已有的理论及由此发生的关联问题,再根据问题去考察事实。如果理论无法解释事实,就继续在实地观察中寻求新的解释、新的理论。(49)参见费孝通:《〈昆厂劳工〉书后》,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3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164页。进一步,引入假设-检验方法的目的在于与类型比较法结合起来,获得普遍性描述。费孝通引用布朗在燕京大学的演讲指出,“社会学调查或研究乃是要依据某一部分事实的考察,来证验一套社会学理论或‘试用的假设’的”(50)费孝通:《禄村农田》,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2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225页。。他的禄村研究在《江村经济》中关于土地制度的认识的基础上,通过对四种类型的农村社区土地体制的比较,对后者进行检验和修正,获得一个中国土地所有权和租赁关系的发展如何受到工业革命下农民收入下降的影响的普遍性陈述。(51)参见费孝通:《〈云南三村〉序》,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1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132-139页。
“逐步寻找一般规则”作为寻求中国社会之完整性理解的方法,奠基在一种更朴素、更底层的逻辑上,即“微积分式的加和”。在通过类型比较法和假设-检验法逐步从微观的单个社区认知宏观的中国整体的过程中,要积累对不同类型的社区的比较和认识,以逐步逼近中国之整体,费孝通将这个过程称为“微积分”。他晚年回应利奇时指出,中国农村虽然千千万万,但可以分为有限的若干类型,通过类型比较法是可以“从个别逐步接近整体的。Edmund喜欢用数学概念来表述事物,我这里所说的‘接近’也就是微积分里的基本概念”(52)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缺席的对话》,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2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46-47页。。按照微积分的原理,一个个单独的社区或类型经过加和可以在地理空间的意义上逐渐接近中国的整体,因此对不同类型和社区的研究越充分,对于中国社会的完整认识也就越本真。尽管他提出人文世界的“整体”不应当是数学上的加总,但是这与其终身试图通过积累类型的方法逼近中国文明整体并不冲突,而是互相补充的。(53)参见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4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34页。
三、活历史:功能主义的时间维度
类型比较法有其优势,但也有内在困境。类型比较法的空间进路能否完全实现从单一小型社区研究通达对中国社会整体性的认识?费孝通意识到这一方法仍不充分。中华文明不仅是一个空间上广阔复合的文明,亦是一个历时性的整体。他在马林诺夫斯基的“活历史”和文化动态论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对中华文明进行发展和转化。他将历史性奠基在人性之上,发展出一种“历史功能主义”,以此把握历史性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整体。
(一)社会的横向与纵向
费孝通虽然反驳了利奇的观点,但明确承认微型社会学和类型比较法这条路径的困难,即“整个‘中国文化和社会’却不等于这许多农村所加在一起的总数”(54)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4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34页。。中国农村或基层社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世界,在这些微型社区之上,城乡关系把它们联系了起来,形成一种更高层次的、有别于农村的市镇社区。甚至在微型社区内部,个体生活与社会体系也往往受到更高层次社会或外部世界的辐射,处在一个更为广泛的关系体系中。甚至作为局部村落的关系网络远远超出世界的一时一隅,而处在人-人、人-物、人-神的复合关系和社区上下内外双向流动的广义人文关系之中。(55)参见王铭铭:《局部作为整体——从一个案例看社区研究的视野拓展》,《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4期;[美]马歇尔·萨林斯:《整体即部分:秩序与变迁的跨文化政治》,刘永华译,王铭铭主编:《中国人类学评论》第9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9年,第127-139页。因而,必须承认这些“微型”资料不可能综合起来说明高一层次的社会情况。(56)参见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4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36页。空间上类型比较法和微积分式的加和方式不足以真正描述中国社会整体的完整性。
在此,费孝通耐人寻味地转向了“时间”(历史)的讨论。他回顾了马氏和自己在功能主义框架中对于时间和历史的理解,“历史”的本质不是简单客观的过去、现在、未来的结合体,而在于在“当下”发生作用的功能。他引用马氏《〈江村经济〉序》,“正因为那个国家有着最悠久的没有断过的传统,要理解中国历史还必须从认识中国的今天开始”(57)[英]布·马林诺斯基:《〈江村经济〉序》,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2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217页。,设想一种历史学和社会人类学合作的可能研究方式。马氏对此并没有展开详述,费孝通则认为这是能否从微型社会学全面研究中国的关键问题,即通过历史或时间维度的讨论是否能够达到中国之整体和完整性。费孝通提出要多记录微型社区研究在不同时期的历史资料,然后将其串起来形成一个动态的“活历史”之流。(58)参见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4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40页。
但这并没有解决能否从时间角度研究中国整体的问题。实际上,费孝通在晚年思考利奇之问时意识到微型社会学在解决“多维一刻”等问题上的局限,直到《试谈拓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中才以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将心比心”予以完整解答。(59)参见周飞舟:《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社会》2017年第2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晚年经历了一个突然的历史性研究转向。事实上,把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整体,是贯穿费孝通一生的认知,他在实际研究中也很重视历史性的要素。1987年,他在回忆自己的思想历程时说:
当我特别被涂尔干的“集体意识”概念吸引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发觉有必要把他的概念转成垂直的。他的概念像是一个平面的人际关系;而中国的整合观念是垂直的,是代际关系。在我们的传统观点里,个人只是构成过去的人和未来的人之间的一个环节。当前是过去和未来之间的环节。中国人的心目中总是上有祖先下有子孙,因此一个人的责任是光宗耀祖,香火绵绵,那是社会成员的正当职责。那是代际的整合。在那个意义上我们看到社会整体是垂直的而不是平面的。(60)费孝通:《经历·见解·反思——费孝通教授答客问》,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1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191页。
借鉴涂尔干的观点,费孝通从集体性文化心理意识的角度出发,将中国视为一个历史性的垂直的实体。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和实体,其完整性不等于小型社区的加和,因为这种加和无法充分地展现将中国社会整合起来的力量和实质。在涂尔干那里,社会实体的实质是精神性的、集体性的道德观念,这些观念将社会横向地、共时性地整合起来。而在费孝通这里,对社会具有整合性力量的是历时性的、纵向的文化观念。中国人的文化观念不仅仅维系着一个人口庞大、地域辽阔的当下的共同体,也塑造了一个当下的我们与过去祖先和未来子孙所构成的历时性共同体。因此,中国社会是一个历史性整体,这是类型比较法没有揭示的方面。本文将进一步探讨费孝通对这个垂直的社会整体的思考。
(二)“反历史”的功能主义的历史化
历史悠久的中国文明是费孝通进行功能主义中国转化的思想资源和现实基础,直接促成了“历史功能主义”的提出。(61)参见乔健:《试说费孝通的历史功能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这种历史性功能主义与马林诺夫斯基“反历史”的功能主义有着鲜明的不同,是费孝通对于功能主义理论的独特贡献。(62)参见乔健:《试说费孝通的历史功能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朱小田:《论费孝通的历史观》,《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2期。关于马林诺夫斯基理论中的历史性问题的讨论,参见Ernest Gellner, “Sociology and social anthropology,” in Ernest Gellner, Selected Philosophical Themes: Volume I Cause and Meaning in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73, pp.109-140.他继承了马氏对历史问题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但又在根本上突破和发展了马氏的理论。
费孝通指出,马氏并非排斥历史,而是受限于特罗布里恩岛社会在他田野工作期间变化不大的现实,岛民也没有可靠的文字记录来准确地记述本地历史,他们的历史讲述主要服务于当前的需要。因此,马氏民族志之所以缺乏历史性分析,本质上是因为其研究对象本身没有可信的历史材料。(63)参见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4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37-38页。
费孝通总结了马林诺夫斯基的两种显著的历史研究方法。其一是马氏针对正在发生巨大变迁的社会的“三项法”(three-column approach),以其遗著《文化动态论》为代表。根据费孝通在20世纪90年代的记述,1937年夏天,马氏访问了英国在非洲南部和东部的殖民地,亲眼见证了非洲民族文化在殖民主义影响和摧残下发生的巨大变迁。于是他在秋季讨论课上开始尝试使用“三项法”来研究这种动态的文化现象,将所考察的文化现象分为三类:白人影响、文化接触与变迁、土人文化。在1938年马氏讨论课上,他在这个三项法上又增加了两项,即土人文化的重构和土人自发的新力量。(64)参见费孝通:《读马老师遗著〈文化动态论〉书后》,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4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358-362页。
通过这样的分类,马氏试图刻画非洲文明如何在欧洲文明的侵入下发生剧烈的变化。这一方法之所以是历史性的,是因为它能让一个当下的、静态的民族志研究展现出非洲文明变迁的动态过程,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非洲文明的历史变动过程。同时,这也让马氏的研究超出了早年孤岛式社区研究的范式,转向考察一种高度互动、变迁的社会。(65)参见王铭铭:《超社会体系:文明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18页。早在伦敦时,费孝通就积极尝试将马氏的方法应用到对中国社会变迁的研究之中。在《从社会变迁到人口研究》中,他针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将马氏三项法发展成包含四大项二十三小项的表格。(66)参见费孝通:《从社会变迁到人口研究》,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520-521页。其中四大项为动变势力、抗变势力、变迁事实和变迁估值,在马氏的前三项之外增加了一个伦理性的价值评估,并对每一项都予以细化。类似的方法也被费孝通运用到《江村经济》中,对江村蚕丝业变动和改革进行分析。(67)参见费孝通:《江村经济》(修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54-156页。
其二,马氏三项法指向了他的第二种历史方法理论,即“活历史”。在马氏的田野工作中,特罗布里恩岛人的历史叙述“只能看作是昔时在今时的投影,而且受到叙述者对后时的期待的影响”(68)费孝通:《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3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411页。,是文化集体在当下的需求和心理基础上重构过去,以此反过来塑造当下的个体和社会。费孝通认同这一“活历史”方法。1937年,他指出功能主义不应当着眼于在剧变的环境中去重构过去的历史,而应当追寻当下还具有现实功能的传统,即“还活着的历史”。在功能主义的视角中,重构历史来理解当下、预测未来是缘木求鱼,田野研究需要考察的是文化传统在当下发挥的功能。(69)参见费孝通:《再论社会变迁》,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501-503页。
必须指出的是,如果要通过历史性维度把握中国整体,上述历史研究方法仍有三个根本困难。首先,无论是三项法,还是“活历史”方法,都着眼于历史变迁,试图在动态变化中把握历史和现实。然而历史不仅有变迁,还有绵延。实际上,马林诺夫斯基在《〈江村经济〉序》中便谈到,理解中国历史要从认识中国今天开始,同时,可以把现状作为“活历史”来追溯过去。(70)参见[英]布·马林诺斯基:《〈江村经济〉序》,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2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217页。马氏暗示了中国的情形与特罗布里恩岛的情形不同,是一个有着严谨整饬的历史记载和丰富考古遗迹的文明。因此,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不可或缺,应与人类学方法相互补充。
其次,三项法和目前版本的“活历史”方法本质上都是“当下的”而非“历史的”,它们的工作方式都是研究一种在当下时刻、对当下的人或社会起作用的力量。其结果是,具有时间深度的历史性被压缩到当下的共时性平面之上,因而根本上仍然是“反历史”。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从马氏社区研究方法出发,可靠的信息必须来自深入的参与式调查,不可能超出调查者和田野对象直接的经验范围,从而其视野被牢牢地束缚在当下社区的经验性边界之内。
最后,前两重困难导致了第三个问题。如果费孝通没有突破这些困境,那么他实际上无法在对一个微型社会的直接经验性研究基础上描述中国社会之垂直整体,因为三项法和目前的活历史方法本质上仍然属于社区研究的范畴。
(三)历史文明体系:“活历史”与“多元一体”
马氏的活历史方法既不是费孝通思考历史问题的起点,亦不是终点。他通过对“活历史”的重新阐释,解决了功能主义的历史缺席之困境,由此实现了马氏功能主义在历史性问题上的中国转化。他将历史性奠定在人性论的基础上,最终建立了从微观的个体、家庭与社会,到民族与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通贯一体,从而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把握中国社会之整体。
尽管费孝通在前引自述中将中国社会之垂直实体的观念追溯至涂尔干的理论(71)参见费孝通:《经历·见解·反思——费孝通教授答客问》,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1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191页。,但他对中国社会整体的历史性分析仍深受马林诺夫斯基思考路径的影响。马氏强调,文化之生成和对文化的剖析,只能建立在人的生理-心理事实之上。文化和社会的存在根源于人普遍的自然本性。(72)Bronislaw Malinowski, A Scientific Theory of Culture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15-42.因此,马氏的文化科学可被称为是一种人性的科学。费孝通对马氏“活历史”学说的重塑也奠定在人性的基础之上,由此展开“历史化的文化科学”的进路。具体来说,他的起点在于人的自然本性和能力,即人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者:“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是在他是生活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三度时间中。人不能没有计划地生活。在他决定现在的行为时,他眼睛望着将来。”(73)费孝通:《生育制度》,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4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98页。
人不仅向着未来生活,同时当下也包含着过去,因为人能够闭上眼睛沉浸于“昔日”情境。(74)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5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328页。这也就是所谓“活历史”的本质意涵。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访美时所写的《鬼的消灭》中,费孝通对人的历史性生存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叙述了“活历史”的两个时刻。第一个时刻是他到芝加哥大学时,碰巧被分配到了派克的旧办公室。“我”置身于他的办公室,感觉到了他的门牌、墙壁上的旧书架、架上的书,甚至屋内的空气,回忆起了“我们”的师生交往情谊。这种交织回忆和具体情境的体验,使得“我”过去的记忆仿佛存活在这门牌、书架和书中,这就是具体的、生动的、活着的历史。第二个“活历史”的案例发生在他的祖母过世之后不久。午饭时刻,当“我”习惯性地往祖母房间望去时,“我”看到祖母的鬼影仿佛跟往常一样朝厨房走去,而这是因为他和祖母曾“在同一情境中久长的和反复的相互生活,使这些情境成为似乎是不可变的自然秩序”。(75)费孝通:《鬼的消灭》,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3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300页。实际上,祖母的记忆虽发生在过去,但是却在“我”当下的情景中活生生地展开。“我”每日生活在其中的历史,就是活生生的历史,是“活历史”。
人的这种生存方式,使得当下的人打开了历史的深度。这使人可以通过接纳历史经验满足自身生存需求。费孝通指出,“历史对于个人并不是点缀的饰物,而是实用的,不能或缺的生活基础”(76)费孝通:《乡土中国》,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5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329页。,因为人必须靠记忆和经验才能活下去。进一步,这样的历史经验与记忆必然突破个体的层面,进入到代代继替的社会之中。因为人不能仅靠自己的经验过活,还须依赖于他人的经验,“人靠了他的抽象能力和象征体系,不但累积了自己的经验,而且可以累积别人的经验。上边所谓那套传下来的办法,就是社会共同的经验的累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77)费孝通:《乡土中国》,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5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328-329页。。因此,正如马氏所指出的,人必须要在社会中才能实现自己的需求,费孝通认为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得到足够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承,从而得以生存。
鉴于功能主义强调具体环境与具体文化现象之间互相依赖和制约的关系,不同环境势必在不同社会中造成不同的传递经验和历史记忆的模式。特别地,中国乡土社会长久以来处在一个稳定、少变、绵延的状态,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积累传递经验的方式就是礼治秩序。在乡土社会中,礼规范着人的行为,使人们能够在社会中合作,完成社会任务,从而满足各个社会成员的生活需要。因而,礼的核心在于社会合作的方式和经验,礼的训诫使得这套历史性经验能够在一代代人之间传递,实现社会的长久整合与稳定。因而,个体只需要遵循乡土社会的礼法,就能获得其文化与经验。(78)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5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370-371页。乡土社会之所以能够维持这种礼法秩序的历史传承,关键之处在于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继替。在《生育制度》中,费孝通对此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其中乡土社会的代际间“反馈”模式已经受到了学者的广泛讨论。(79)吴柳财:《论中国社会的垂直代际整合——孝道与代际伦理的社会学研究》,《社会发展研究》2022年第2期。事实上,社会存续的需求使得乡土社会以家庭三角关系为核心形成了稳固的结构,以此完成社会新陈代谢的过程。在家庭中,父母将孩子视为自我的一部分,试图按照自我的理想来塑造下一代,而这种自我的理想正是合乎礼法的社会标准。(80)参见费孝通:《生育制度》,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4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99-102页。因而,凭此过程,乡土社会赋予了个体强烈的观念以维系稳固的社会继替,让社会结构在历史中基本保持着稳定的延续,实现文化的绵延不绝。
以此,中国人形成了一种历史的共同体,即垂直的整体,“中国人是一个上有祖宗、下有子孙的社会,个人生命只是长江中的一滴水,一个人的生命总是要结束的,但有一个不死的东西,那就是人们共同创造的人文世界”(81)费孝通:《完成“文化自觉”使命 创造现代中华文化》,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4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342页。。在这样的世界中,人的历史性得到了极大的展开,远远超出个体的直接经验范围,沿着时间的河流一直追溯到共同体的起点。同时,社会经验代代延续,持续地塑造着每一代个体的生存经验,使“每个人的‘当前’,不但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且是整个民族的‘过去’的投影”(82)费孝通:《乡土中国》,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5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329页。。因而,不仅“过去是当下的投影”,反过来当下也是过去的投影。
最后,既然每个人都承载着“整个民族过去的投影”,那么费孝通的历史共同体显然已经不是一个单一小型社区意义上完整的人文世界,而是一个更为宏大广阔的民族历史共同体。这样分布极为辽阔、人口繁密的民族形成的自然不是马林诺夫斯基经典理论中依靠互相之间需求关系而形成的孤岛式的文化整体。费孝通指出,“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83)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民族的整体所依靠的是共同的文化,对在各个社区中绵延的经验与观念的认同构成了民族整体的关键。更进一步,在此之上,各个民族实体在漫长的历史中互相交流、渗透、融合,“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最终形成了各民族在其中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84)参见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四、总 结
对于20世纪初的吴文藻、费孝通等人而言,马氏功能主义是解救时弊、理解中国的良方。但在引入其学说的同时,面对多元一体的中国文明现实,费孝通对其孤岛式文化整体的个案民族志方法进行了时间-空间的重组,以实现对中国作为复合的、超社会的文明的整体把握。费孝通首先尝试从空间方面通过类型比较法进行拓展,以期如微积分一样逐渐接近中国社会整体的现实。他之所以能实现这一点,是因为马氏微型社区的研究方法根基在于马赫式的经验批判主义,而费孝通通过和马氏不同的实在论观念克服了社区研究的空间界限。进一步,空间上的扩展仍然不足以充分实现对中国文明整体的把握,因为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社会必然大于其中每个微型社会之总和。费孝通尝试通过在历史维度上拓展马氏的社区研究方法,以理解作为垂直的整体的中国社会。他重新阐发了“活历史”,将历史性奠定在了对人性的理解和人的生存分析之上,再一步步地拓展到家庭、社会、民族,直至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由此将马氏功能主义改造为“历史功能主义”,实现了功能主义的中国转化。
现在可以回到最初的问题:费孝通为何能通过这种历史功能主义突破马氏孤岛式社区研究的限制,刻画复合的中国文明体。马氏功能主义就其研究方法和进路的本质而言,奠基在一种小型单一社会足以构成一个完整自足的人文世界的观念之上。这种文化想象是一种文化普遍论:每个个体虽然处境不同,但都有高度抽象而同质的普遍人性;每个社会虽然文化各异,但其生成逻辑和动力机制却完全普同。不过对费孝通来说,中国社会作为一个宏大的文明整体,它不仅在平面上是一个广阔的、相互关联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还是一个垂直的、历史的整体。一方面,个体所承载的经验和文化超出了个体的范围,深入到了从祖先到子孙的无垠历史中,中华民族因此成为历史性的多元一体共同体;另一方面,超出个体自身界限的“前后关系”(即人与祖先、亲子间的关系)、“左右关系”(联姻关系)、“上下关系”(地位差别),构成了人活生生的存在方式,进而成为文明作为关系复合体的基础。(85)参见王铭铭:《超社会体系:文明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28-29页。这使得在费孝通的历史功能主义中,每个文化都因其所承载的具体历史差异而有了不可磨灭的实质性不同。由此,文明间之所以平等,不是因为它们在形式上有着共同的生成机制和普同性的基础,而恰恰是因为它们在根本上都不相同,都是在各自的历史中以自己的方式绵延发展。
这或许正是费孝通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的基础之一。他说,“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86)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4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166页。,然后中国文明才能经过自主的适应,寻找到与世界诸文明和平共处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