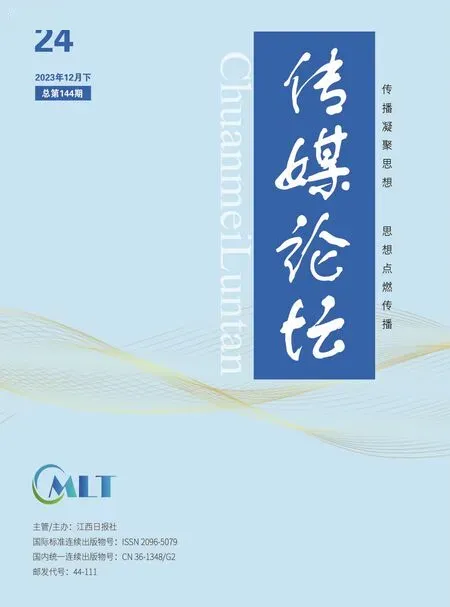影片《在路上》中的多元文化主义表达
2023-02-10郁敏
郁 敏
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被奉为“垮掉的一代”的“圣经”,真实记录了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美国“垮掉的一代”青年对美国主流文化的反叛与对多元文化的推崇。《在路上》的出版让凯鲁亚克一夜成名,同时让美国掀起“在路上”的背包革命热潮。小说中的主人公萨尔和迪恩成为美国青年,乃至世界青年的偶像。凯鲁亚克也据此在美国后现代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2019年10月21日是凯鲁亚克逝世50周年的纪念日,2022年3月12日,是凯鲁亚克100周年诞辰的日子,国内外都用不同的形式来纪念这位美国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美国旧金山的“城市之光”书店和凯鲁亚克的家乡洛威尔等地举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在国内,出版界通过集中推出《在路上》一系列的中文重译版本来重温象征着自由与反叛的“在路上”精神。而在2012年,巴西导演沃尔特·塞勒斯(Walter Salles)则在电影版《在路上》中用镜头语言对小说中的多元文化主义进行跨媒介表达,以致敬“垮掉之王”凯鲁亚克。影片中对流浪者文化、少数族裔文化、女性文化等的影像符号再现,引发了观众对于小说《在路上》中多元文化现象的再思考。
一、流浪者文化
流浪一直是中外文学中重要的表现主题之一。历史上,流浪是人们迫于生计及环境改变时做出的无奈选择。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流浪逐渐演变成为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主观选择。他们因为精神迷茫或为寻求文学与艺术自由而主动出走,为作品的创作与新思想的形成提供丰富素材与源泉。在文学发展进程中,流浪者形象成为一种留存于文学史的重要传统。文学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影响文化的发展,因此,流浪者文化也逐渐发展成为亚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
流浪者文化在美国具有其特有的历史性。如美国早期的流浪汉通过他们的流浪和徒步旅行发现了加州。五六十年代,由于《在路上》的一书的流行,流浪再度成为一种美国青年所崇尚的生存方式,是他们的追求自由、丰富自己生命内涵的途径和目的。然而,他们落魄的外表、放浪的行为与当时美国的主流精英文化格格不入。这也是白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一种体现,需要社会全体成员遵守约定俗成的白人中产阶级精致的生活标准和行为规范,不允许有影响发达国家社会风貌的异端现象存在——不管是真正影响治安的流浪汉,还是只是选择一种异于常规的生活方式的流浪者。
主流社会对于亚文化群体的不理解和不支持导致了两种文化的碰撞,引发了以“垮掉的一代”为代表的亚文化群体的反抗。“垮掉”的流浪者们喜欢自由、喜欢旷野,他们宣称“自我是最伟大的流浪汉”。[1]凯鲁亚克在《孤独旅者》中列举了一些历史上伟大的流浪者的例子,比如贝多芬、爱因斯坦、叶赛宁,李白,甚至基督与佛陀。他们不仅无害于他人、无害于社会,反而给人类历史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他和他的伙伴们也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当代流浪者的生命追求和文化价值。
影片中表现了以凯鲁亚克为原型的叙述者萨尔六次在路上的流浪生活。为了响应迪恩的召唤,萨尔第一次踏上流浪之旅,从纽约出发前往丹佛。电影镜头快速掠过林立的高楼、钢铁的桥梁、宽阔的哈德逊河,然后逐渐转向荒凉的田野,并给了正在行走的双脚一个长长的特写。这样的镜头语言象征着对于充满欲望与迷茫的纽约城的远离。萨尔背着背包、头发凌乱、面容憔悴、眼神坚定,时而步行,时而搭顺风车,向着未知的远方前进,这一画面致敬美国青年们曾经为之疯狂并努力效仿的经典形象。躺在平板卡车上的萨尔与一群打零工的人一起歌唱,一起疯狂,掏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记录下脑中不停闪现的灵感……这一切给了萨尔丰富的创作素材,原本文思枯竭的萨尔感受到了内心真正的快乐,摆脱了城市束缚的灵魂得到了真正的自由。
接下来的五次流浪分别是从丹佛到旧金山,从旧金山到纽约,从佛罗里达到纽约,从新奥尔良到旧金山,从纽约再到墨西哥……场景随着萨尔的足迹不停地转换——阳光明媚的加州、白雪皑皑的纽约、布满高大仙人掌的墨西哥;西部黄色的沙砾路、纽约黑色的柏油路、墨西哥灰色的马路;飞驰的过路车、空寂的大巴车、哈德森的自驾之旅……萨尔、迪恩、玛丽露等人在各个场景间闪现,用放浪形骸的行为将流浪的生活演绎得酣畅淋漓。最终,每个人的流浪都终结于孤寂与落寞,又回到各自生活的原点。但回归后的他们都已经不再是最初出发时的他们,而是重生后的他们。正如影片结尾处,萨尔在纽约的家中收到卡罗(即艾伦·金斯堡)的诗集《忧郁的丹佛》(Denver Doldrums),扉页上写着“献给这些诗歌的秘密英雄萨尔和迪恩”(For SP and DM,the secret heroes of these poems)。影片中借卡罗之口朗读出的诗句正是对他们流浪的轨迹和心声的华丽总结:宁可让身体在路上颠簸,用自己的身体献祭路过的地方,宁可伤痕累累,宁可死在路上,复活在路上!
二、少数族裔文化
在《多元文化主义》一书中,C.W.沃特森(Conrad William Watson)从文化观、历史观和政治观等方面对多元文化主义进行了界定。他认为所有人在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上机会平等,禁止任何以种族、民族或民族文化起源、肤色、宗教和其他因素为理由的歧视,多元文化主义的核心是承认文化的多样性,承认文化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影响。“多元文化主义强调种族平等和宗教宽容,其最终目的并非文化平等而是社会平等。在这个意义上,多元文化主义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价值观,其功能在于动员社会力量,推动社会改革,追求不同群体在文化和物质上的繁荣以及人类本身的自由和尊严。”[2]
凯鲁亚克等“垮掉的一代”不认同“白人优越论”的主流价值观,对自己的白人文化身份产生了怀疑。他们试图从黑人以及其他少数族裔身上找到文化归属,实现认同。他们愿意舍弃白人身份,“舍弃主流文化,主动走向边缘,变成边缘化的‘他者’,试图在边缘地带追寻新的文化身份,创造一个理想的精神家园。为此,他们走向少数族裔群体,在那里寻找天堂和乐园。他们希望自己变成黑人或墨西哥人,实现不同文化身份的融合和认同。”[3]在凯鲁亚克的作品中可以经常读到他对于黑人的赞美,对于印第安人的同情以及对于墨西哥人和亚洲人生活的客观描述。
在电影中,导演塞勒斯选取了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族裔进行表现,一是以演奏爵士乐的萨克斯演奏家为代表的黑人,二是以萨尔在路上偶遇的姑娘泰丽为代表的墨西哥人。
以黑人为主体的爵士乐群体是萨尔和迪恩所崇拜的对象。萨尔和迪恩在影片中与演奏爵士乐的黑人萨克斯手两度相遇,他们为他神奇的演奏水平所折服,与他喝酒,跟他回家,随着他的音乐节奏一起疯狂舞动,视他为神一般的存在。现实中,凯鲁亚克、卡萨迪和金斯堡等垮掉成员都非常迷恋爵士乐,认为爵士乐无拘无束、自由发挥、激情澎湃、酣畅淋漓的即兴演奏特征正好与“垮掉派”的特质相符。他们推崇一些著名的爵士乐手,比如绰号“大鸟”的中音萨克斯演奏家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被认为是美国音乐史上的一位伟人的爵士乐钢琴家和作曲家塞隆尼斯·蒙克(Thelonious Monk)、爵士乐小号手、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音乐人之一迈尔斯·戴维斯(Miles Davis)、爵士乐高音萨克斯管演奏家沃戴尔·格雷(Wardell Gray)等都是黑人。影片中表现的这位萨克斯手就是以演奏家查理·帕克为原型而塑造的。
《在路上》中还记录了一段萨尔与墨西哥姑娘泰丽的浪漫爱情,这段爱情也在凯鲁亚克的另一部小说《特丽丝苔莎》进行了更为细腻的刻画。凯鲁亚克真心赞美墨西哥女性,对于墨西哥的农业文明也是一片向往之情。影片中,萨尔与泰丽在公共汽车上相遇并一见钟情。他跟着泰丽来到她的家乡,与她一起摘棉花,试图融入他们的生活。在书中,萨尔说道:“他们以为我是墨西哥人,当然,在某种意义上我确实是。”[4]
虽然萨尔最后又回归到了他一直逃避的“白人梦想”中:坐着凯迪拉克轿车,带着女朋友劳拉去大都会歌剧院听音乐会,但是书中所传递的平等意识唤醒了人们对处于“他者”地位的少数族裔文化的关注,促使人们对种族问题和文化问题进行关注和思考。对“垮掉的一代”颇有研究的著名学者文楚安曾评价道:“四五十年代,美国的种族歧视仍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路上》所表达的这种对白人(实际上是白人统治者)优越性的鞭挞以及呼唤种族平等的呐喊无疑是进步的,具有极大的感召力。”[5]
三、女性文化
自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写就的第一本启迪女权运动的著作《为女权辩护》(1792)以来,女性主义发展经过了三次主要浪潮,演变出了不同的流派。但女性的地位,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社会上,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仍在曲折中浮浮沉沉。在白人男性主导的美国文化中,白人女性的地位与少数族裔的地位具有相似之处,他们在“机会平等、平权运动(affirmative action)、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te representation)和教育不平等等问题上有共同的语言。”[6]白人女性在父权制的社会中成为男性视角下的“他者”,而少数族裔的女性则面临着双重“他者”的身份。
作为美国社会中的白人男性,凯鲁亚克对女性有着同样的注视视角。有学者认为:“杰克·凯鲁亚克对于女性的态度是褒贬不一的,但是从整体来说,他对待女性的态度仍然是比较负面的……凯鲁亚克无法冷静地处理好自己的感情,也自然无法用客观的眼光来观察女性”[7]。这样的评价相对比较客观,凯鲁亚克对于他妻子的逃避和对女儿的弃养从一定程度上佐证了这一观点。《在路上》一书中,凯鲁亚克塑造了不同的女性形象,或尊重有加,或弃如敝屣,体现了其对于女性主义文化的矛盾态度。
而在影片中,塞勒斯主要表现了四个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萨尔的母亲、迪恩的第一任妻子玛丽露、第二任妻子卡米尔和萨尔偶遇的墨西哥女孩泰丽。母亲代表着无私、高尚、为家庭牺牲的“房间里的天使”形象,她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家庭。在萨尔将要远行时,镜头同时展现两个房间的画面,左边是萨尔在兴奋地收拾背包,右边是母亲在隔壁的房间中默默不语。母亲虽不舍,但没有阻止。在萨尔风尘仆仆回归之时,她也只是带着嗔怪的喜悦将其紧紧搂入怀中。萨尔没有固定工作,依靠母亲生活,母亲是他物质与精神的港湾,是他心目中的天使,也是白人男性视野中的“完美女性”,却是女性主义文化所批判的对象。
玛丽露则代表着追求自由、具有垮掉特质的反叛女性形象。只有十六岁的她不顾一切地与迪恩结婚,与他一起流浪、一起疯狂。影片中玛丽露年轻漂亮,但抽大麻、性解放、偷东西……她一样不落,用放荡不羁的行为来对抗保守的社会主流文化,寻求心灵的解脱与安慰,她的行为与男性无异。从这一层面来讲,玛丽露可以被视作“激进女性主义”的代表,追求与男性的同质化。
卡米尔是自信、独立、坚强的新生代女性代表。认识迪恩时,她是一个舞台设计专业的女大学生,金发碧眼,意气风发,为尤金·奥尼尔创作的“美国第一部伟大的悲剧”《榆树下的欲望》做过舞台设计。她接受过高等教育,经济独立,在旧金山有着自己的房子。在迪恩背叛她的时候,她有勇气和底气将其扫地出门。在迪恩离开后,她独自抚养两个孩子。她的形象贴合“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定义,这一类型的女性有主见,有自己的工作,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并不选择与男性同质,而是凸显自己作为与男性平等的另一性别的气质与魅力,她们不愿被男性“他者”化,也不把男性“他者”化。
而泰丽则代表着受到双重边缘化的少数族裔女性。作为一位生活在加州的墨西哥女性,她早早地嫁人生子,面对丈夫的家暴不敢反抗,只能选择逃避。由于缺乏教育,加之有色人种的身份,她只能从事摘棉花等体力劳动。一天的辛劳也只能从白人雇主手中换来微薄的薪水,晚上也只能住在简陋的帐篷里。与萨尔的“婚外情”,是她反抗自己双重“他者”身份的一种方式。虽然不能剥离有色女性的身份,但她主导了一次自己的爱情,而这爱情的对象还是一名白人男性。虽然这样的反抗是短暂的,却体现了“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所倡导的女性精神,对于同为少数族裔的女性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
这四位女性分别代表四种不同的女性形象,对应着女性主义文化中的不同侧面。但她们却落入了同样的悲剧性的结局:回归家庭,生儿育女,相夫教子,成为“房间里的天使”——母亲一直在纽约的家中等待着不知归期的儿子萨尔;玛丽露最终被迪恩抛弃,嫁给了一个水手,过上平淡的生活;卡米尔在遭受迪恩一次次的背叛中崩溃痛哭,失去自我,但最终却不得不以两个女儿的名义邀请迪恩回归家庭;泰丽也只能在短暂的激情后与萨尔分手,回到她丈夫的身边,在恐惧中等待下一次家暴的来临。经过几百年的抗争,无论哪一种类型的女性基本难以摆脱父权制文化的控制,最终成为男性文化附属品与牺牲品。这样的命运似乎成为女性的一种宿命,即使在21世纪的现在也是如此,要实现男性和女性在政治、教育、经济,尤其是文化意义上的真正平等,仍然在路上。
四、结语
多元文化主义是对美国主流文化话语霸权的一种挑战,以“垮掉的一代”为代表的亚文化群体通过文化反叛和文化革命实现对于白人精英文化的逃离。流浪、性解放、爵士乐,甚至偷窃、吸毒等均成为反叛的手段。凯鲁亚克在《在路上》中对这些反叛与革命用文字进行了艺术地表现,而影片的编剧约瑟·里维拉(Jose Rivera)则通过选取书中的一些经典片段进行改编,指涉不同的文化维度。导演塞勒斯则用丰富的镜头语言将美国的田野风光、城市风情与演员的精湛演技相结合,展现里维拉所精心选取的文化侧面,诠释不同文化对于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与改变,促进人们对于文化、历史、政治进行反思。经典小说滋养了电影的发展,而电影则让经典小说在不同的时空再次流行,两者共同作用,对世界文化产生长远而鲜明的影响。[8]在20世纪70至90年代期间,族裔研究、女性主义研究和性别研究等学科在美国高校纷纷开设,对于消解“白人中心论”、为社会弱势群体确立话语权力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当代,这些学科也在世界范围越来越得到重视与发展,研究成果丰硕,相关著作汗牛充栋。尊重文化差异,促进多元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旋律。一个所有文化平等相待、和谐共处的社会,应该也是凯鲁亚克与塞勒斯的共同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