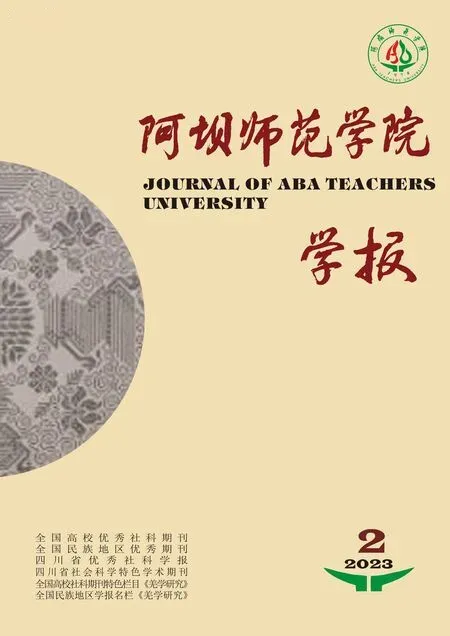民族记忆与身份认同
——路易丝·厄德里克“正义三部曲”中的景观书写
2023-02-08崔姗
崔 姗
路易丝·厄德里克(Louise Erdrich,1954—)是当代美国极富景观意识和想象力的本土裔作家。她出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儿时常去龟山保留地的外祖父家。龟山保留地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深深地印刻在她的脑海中,为她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素材。“正义三部曲”——《鸽灾》《圆屋》《拉罗斯》——中的景观描写独具印第安民族特色和文化意义,是对印第安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象征性书写,记载了印第安民族的被殖民历史和身份建构的过程。厄德里克将景观书写与印第安的民族历史、民族性格和民族身份并置,以此激发印第安民族的认同感。研究厄德里克小说中的景观,可以“使沉默的风景意象发出声音”①达比.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M].张箭飞,赵红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9.。
“景观”一词最早在文献中出现是在希伯来文本的《圣经》中,德语为“landschaft”,英语为“landscape”,同汉语的“风景”“景致”“景色”的意思相一致。“景观”一词最初是绘画领域的术语,19 世纪在自然地理学领域得到应用。到20 世纪中叶,西方学界的“空间转向”研究把“景观”扩展到新的研究领域,注重其主体性和建构性的内涵,视景观为一种文化实践活动,重视景观的“观看方式”,使景观研究进入文学、艺术等多种学科,并发展成一种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景观”一词包含了“景”(风景)和“观”(观看)两个方面的内涵,不仅是一种客观的、纯物质形态的自然物象,更承载了丰富的人文意义,且与文化、政治等紧密相关,具有区域独特性。本文以“正义三部曲”中景观与民族记忆、民族性格和民族身份的关系为切入点,分析小说中的景观如何唤醒印第安人的民族记忆,如何凸显印第安人的民族性格,印第安人如何在与风景的融合中建构民族身份,并强化自己的民族身份与归属。
一、消失的部落景观与民族记忆
英国文化地理学家迈克·克朗(Mike Crang)在《文化地理学》一书中对地理景观进行了界定,他认为:“地理景观指的是不同时期土地形态的集合。地理景观不是一种个体特征,它们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或者说是一种文化的——信仰、时间和技术”①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19.。兰开斯特大学历史地理学教授伊恩·D.怀特(Ian D.Whyte)认为景观可以构成记忆,他在《16世纪以来的景观与历史》一书中指出: “景观(landscapes)是多面向的,构成一种记忆形式,这种形式储存着人类于时间延绵中在地球上活动的历史”②Ian D.Whyte.Landscape and History Since 1500[M].London: Reaktion Books Ltd,2002: 7.。英国地理学家阿兰·R·H.贝克(Alan R.H.Baker)也指出了景观与记忆的内在联系,他认为:“往日景观的形成与意义,反映了建构人们工作、生活于其中并加以创造、经历与表现的社会。但就其留存至今而言,往日景观作为文化记忆与特性的组成部分之一,具有延续的意义”③贝克.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M].阙维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50 -151.。由此可见,文学作品中的地理景观不仅是地貌风景图,更是可解读的“文本”。它们向读者展示的是关于某个民族的故事、观念信仰和民族特征。
作为美国本土裔文学的代表作家,路易丝·厄德里克作品中的景观描写承载了作者的文化立场和价值判断。小说中的景观既是印第安人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也是在建立他们与自然界的联系下传承民族文化、建构民族身份的精神源泉。厄德里克对景观的编码体现了印第安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精神联系,展现了印第安人对部落景观的依赖和眷恋,也实现了对印第安民族历史的重述。小说中对消失的印第安部落景观的刻写是厄德里克笔下一道独特的风景,是反映印第安部落历史的重要载体。在印第安民族历史上,水牛曾是一道独特的部落景观,然而随着白人殖民者的入侵,水牛成为人们记忆中的景观。在小说《鸽灾》(The Plague of Dove,2008)中,作者通过穆夏姆的讲述,回忆了白人猎杀水牛的历史:“穆夏姆告诉我捕猎水牛的老猎人看到地上满是水牛的尸体”④厄德里克.鸽灾[M].张廷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252.,成群的水牛不断迁移。在小说《圆屋》(The Round House,2012)中,穆夏姆再次讲述了水牛消失的那段历史: 在他们祖先生活的年代,“到处都是水牛……它们遍布大地,数不胜数。可现在它们去哪儿了呢……有人看见,白人跳下火车,开枪打死了几千头水牛,然后任它们腐烂。无论如何,它们不复存在”⑤厄德里克.圆屋[M].张廷佺,秦方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189.。印第安部落水牛灭绝的历史烙印在印第安人的集体记忆中,成为民族记忆的一部分。正如芭芭拉·本德(Barbara Bender)所说: “景观包含了过去活动的痕迹,人们通过讲述过去的故事来唤起曾经的记忆和历史,从而推动他们的现在与未来。”⑥Barbara Bender.Landscape: Politics and Perspectives[M].Oxford: Berg Publishers,1993: 4.穆夏姆对消失的水牛的怅惘和愤懑表达出印第安人对白人殖民主义的控诉。水牛的景观描写反映了印第安人生活方式的变迁,印第安历史的影像在景观的书写中渐渐展开。
美洲水牛(又称美洲野牛)与印第安人一样,是北美大陆的“原住民”,美洲大陆是他们共同的家园。生活在大平原地区的水牛“以其肉供人食,以其皮供人衣……人们的生命和孩子的成长全靠野牛……”⑦李剑鸣.美国印第安人保留地制度的形成与作用[J].历史研究,1993,(2):163.正如小说中纳纳普什描述的那样,“水牛会把美味的大蜱虫抖进湖里、河里,给鱼吃,而且它们的粪便能引来其他昆虫,鱼儿也很喜欢……水牛过去常常翻土,那样草长得更好,兔子就吃得好。所有的动物都想念水牛”⑧厄德里克.圆屋:186.。水牛不仅是印第安人的主要食物来源,也是印第安人制作衣服、装饰品、工具的重要原料。可以说,水牛既是印第安人生活的物质基础,也是印第安人力量和团结的象征。然而,随着美国建国后西部领土扩张运动的开展,水牛在印第安人的生活中逐渐消失。美国政府颁布的政策法案是导致水牛灭绝的历史根源。1830 年,美国时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签署了《印第安人迁移法》(Indian Removal Act),该法案授予联邦政府权力,将印第安人从密西西比河以东迁移至密西西比河以西的荒芜地带。美国政府采取了多种强制手段逼迫印第安人搬迁。为了加快印第安人搬迁的速度,政府通过灭绝水牛的手段使印第安人失去生存的物质基础,“从19 世纪70 年代起,美国联邦政府雇佣大批猎手杀戮野牛”①张红.美国的崛起史就是一部侵略扩张史[N].人民日报海外版,2021 -09 -16.。据文献记载,美国境内的野牛最多时大约有六千万头。②Bryan Liz.The Buffalo People: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on the Canadian Plains[M].Edmonton: University of Albert Press,1991:32.“1865 年内战结束时,在大平原漫游的野牛约有1500 万头;但随着联合太平洋铁路的修建,野牛遭到大量捕杀;到1878 年,南部的野牛几近灭绝”③比林顿.向西部扩张(下册)[M].周小松,周帆,周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43.。5 年后北部野牛群也销声匿迹了。④李剑鸣.美国印第安人保留地制度的形成与作用[J].历史研究,1993,(2):164.然而,美国政府的杀戮行为不仅针对水牛,也发生在印第安人身上。在西进运动的过程中,大批印第安人遭到屠杀,美国印第安人的数量急剧下降,“15 世纪90 年代,美洲印第安人口超过欧洲,占全球总数的20%,而经过一个世纪的屠杀后降到3%”⑤冯克诚,田晓娜.世界通史全编[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841.。“到19 世纪末美国只剩24 万印第安人,几乎濒临灭绝”⑥冯克诚,田晓娜.世界通史全编:1396.。印第安人的西迁使密西西比河东部的肥沃土地落入白人之手,而印第安人却被困在密西西比河以西荒芜的草原上。许多印第安人在西迁的路上死于饥饿、寒冷和疾病。印第安人在保留地的活动范围受到严格的限制,原始的游猎生存方式受到了威胁。小说《圆屋》通过穆夏姆的讲述呈现了这一时期的保留地景观: 印第安人被赶到边界线上,还没到12 月,族人就“已经猎杀完所有动物,连只兔子也没剩……我们离开美加边境,北上加拿大,漫无目的地寻找食物,但驯鹿早就死光,河狸一只不剩,甚至连麝鼠也没有”⑦厄德里克.圆屋:184.。
在印第安民族的历史上,水牛的命运与印第安人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小说中水牛消失的景观描写是美国印第安人多舛命运的真实写照,是美国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罪恶的血证,揭露了白人殖民者剥夺印第安民族栖息地和自然资源的历史。从文化的角度来说,白人殖民者对水牛的屠杀给印第安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民族创伤。水牛是印第安人的衣食父母,是部落传统典仪的主要内容,承载着印第安民族的文化,增强了印第安民族的凝聚力。水牛的灭绝给印第安文化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德拉布尔(Drabble)曾说:“我们喜爱的景观被改变,难以识别,我们感到深切、明显、巨大的痛苦。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场所,而是我们自己及我们生命中不断变化的阶段之间的连续性”⑧转引自杨琳.景观与记忆:艾丽丝·门罗《石堡远眺》之历史书写[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22,(2):270.。厄德里克笔下的部落景观超越了自然环境,将历史与当下建立起联系,成为民族身份的象征。作者一方面通过呈现消失的水牛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景观意象来唤起印第安人的集体记忆,将个体记忆与民族记忆串联,使作品充满了厚重的历史感; 另一方面通过记忆重新编织破碎的历史景观,建构时间维度上的景观,赋予当代印第安人完整的地方感。尽管部落景观已经隐退为过去,但印第安人对历史的记忆却不断膨胀,演绎出动人的故事,反映了厄德里克对历史书写的深刻思考。通过挖掘“官方历史”背后的真相,颠覆官方的宏大叙事,作者表达出对印第安部落家园的热爱以及对印第安民族身份的认同和归属。
二、保留地自然景观与民族性格
风景是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的表征,也是塑造民族身份、唤起地方感和民族意识的重要介质。风景在人类的凝视之下转化为文学作品中的文化,而人类对风景的选择是“借助某种智力上的‘取景’,才给予‘无形式’的自然环境以形式”⑨Martin Lefebvre.Landscape and Film[M].London: Routledge,2006: 19.。人类对风景的凝视、选择和再现的过程必然打上选择者的文化烙印,使自然风景变成一种表达某种文化意义和意识形态诉求的中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W.J.T.米切尔(W.J.T.Mitchell)指出,“风景可以通过绘画、绘图、雕刻、摄影、电影、戏剧场景来再现。然而,在所有这些再现之前,风景本身是一个物质的、多重感受的媒介,在其中文化意义和价值被编码”;同时,其主张“把风景理解为一种文化表述的媒介”,并且进一步指出,“风景是含义最丰富的媒介”①W.J.T.Mitchell.Landscape and Power[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 15.。因此,风景可以通过文学作品的描写被编码。同米切尔一样,蒂姆·克雷斯维尔(Tim Cresswell)也把空间、风景和地方关联在一起,指出风景和地方是某一区域的自然和文化,是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②Tim Cresswell.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M].Malden,MA: Blackwell,2004: 12.
风景具有地域的独特性,不仅可以体现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政治观念,还可以反映出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正如肯尼斯·奥维格(Kenneth Olwig)所说:“一个民族文化的本质或性格与其栖居地区的本质或性格之间,具有一种恒久的联系”③Kenneth Olwig.“Sexual Cosmology: Nation and landscape at the Conceptual Interstices of Nature and Culture; or What Does Landscape Really Mean?”in Landscape: Politics and Perspectives.Ed.Barbara Bender[M].Oxford: Berg,1993: 310 -312.。在这个意义上,风景成为反映民族文化或性格的载体,通过文学文本呈现出来,进而成为建构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的方式。印第安人被迫迁移的经历导致民族身份与地方归属的联系受到冲击,许多印第安人失去归属感,而厄德里克在印第安保留地的自然中找到了能够代表印第安民族特征,凝聚民族历史的重要媒介——景观。作为美国本土裔文学的代表人物,厄德里克始终将书写民族历史、建构民族身份作为自己的创作动力。她小说中的景观成为建构印第安民族身份,塑造民族性格,表征民族精神的重要媒介。她将美国印第安保留地的景观生动形象地再现到作品中。她笔下的保留地景观充满了淳朴、浓厚的原始部落气息。通过她的描述,我们感受到了印第安传统文化的魅力。同时,这些景观描写也提供了美国本土裔保留地景观的历史语境,赋予风景一种怀旧之感。
小说《圆屋》开篇对1988 年保留地自然景观的描写凸显了印第安人的民族性格,强化了印第安人的民族意识和情感。故事的主人公小安东·巴兹尔·库茨的家门口长了好几棵树:白蜡树、榆树、枫树、羽叶槭和梓树,这些树虽然长得不高,却已侵入了房子的地基,“细长的树苗刚长出一两片肥厚结实叶子,就已硬生生地钻入棕色木瓦间的缝隙……树苗在看不见的墙里扎根,很难撬出来”④厄德里克.圆屋:1.。叙述者乔不禁在心里感叹: “在北达科他这种地方,这些树苗能熬过冬天真是奇迹。它们不一定缺水,但光照不足,土壤有限。然而,每粒种子生根后都钻得很深,还生出卷须探到外面。”⑤厄德里克.圆屋:1.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认为,“叙事中的任何一个细节都具有功能性,哪怕最微小的细节也都具有意义”⑥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M]//张寅德.叙述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11.。作者在小说开篇描写的印第安保留地景观,不仅是小说故事发生的背景,也为故事情节的发展埋下伏笔。这些生长在保留地的小树是一道被人格化的风景。
美国人类学家温迪·J.达比(Wendy J.Darby)在其著作《风景与认同: 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中指出,风景是“在意识形态的语境中被创造被毁灭。因此,恢复与特定地方相关的意识形态的历史,是理解风景的基础”⑦达比.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108.。作者用树苗熬过寒冬喻指印第安人被殖民的遭遇,以保留地寒冷的“冬天”作为印第安人历经劫难的隐喻。这一隐喻抨击了白人统治者制定的保留地制度的历史不公。美国联邦政府1850年针对印第安人制定的划分保留地的计划,1853 年起开始全面实施。计划的目的是通过划分保留地,缩小印第安人的活动范围,并且使印第安人远离白人定居地。在联邦政府的暴力、欺诈和威逼利诱之下,印第安人不得不离开世代生息的部落,迁入保留地。保留地的划分限制了印第安人的活动范围,导致印第安人无法再继续游猎生活。保留地的土地零零散散,有的地“小得连盖栋房子都不够”①厄德里克.圆屋:15.。他们对保留地的生活充满了担忧和恐惧:“如果用我们的土地与别人交换,恐怕会发生与移植一棵老树相同的后果:它会枯萎和死去”②转引自李剑鸣.美国印第安人保留地制度的形成与作用[J].历史研究,1993,(2):160.。小说中保留地树苗的顽强生命力回应了印第安人祖先的担忧,面对毁灭性打击,他们没有彻底消沉,也没有丧失希望。
厄德里克在小说中对保留地景观的描写出于她对这片土地的感情,这种感情源于她对印第安历史的了解。美国的西进运动和保留地政策迫使印第安人迁往贫瘠荒芜之地,动物绝迹,食物短缺,疾病肆虐,导致众多印第安人在饥饿、寒冷和疾病中死去。然而印第安人依然在灾难中顽强地生存,正如小说中的树苗,克服重重困难,扎根在这片土地,它们的“树根抓得那样牢! 也许它们已经破坏了支撑屋子的空心砖。多么有趣,又多么奇怪,一棵小树苗即使种在错误的地方也能长得如此强壮”③厄德里克.圆屋:302.。小树苗在艰难的生存环境能够顽强地生存,对于当代面临生活困境的印第安人极具现实意义。印第安人原本是北美大陆的主人,在白人殖民者的驱逐下来到保留地这个“错误的地方”。不仅如此,保留地在联邦政府的调整和改组的过程中面积不断缩小,甚至被撤销。保留地的印第安人几经迁徙,不断为白人让出土地。在保留地的狭小地域,印第安人加强了部落间的联系,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最终将保留地建成新的家园,将“错误的地方”转变为代表印第安民族身份之地。虽然屡经打击,印第安人却依然保持坚韧不屈的精神,正如小说主人公对树苗的描述:“要想把树根从它们顽强生长的角落里完好无损地扯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④厄德里克.圆屋:2.。这些品质显示出印第安人的民族精神和凝聚力。历经百年的沧桑,印第安人依然坚守在他们最后的家园——保留地。
三、典仪景观与民族身份认同
除了重温民族记忆,表征民族性格,“正义三部曲”中的景观对于建构印第安人的民族身份认同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小说中的典仪景观帮助印第安人团结部族成员,回忆民族历史,融入民族文化,进而唤起当代印第安人的族裔认同。我国著名的文化地理学专家王恩涌在其著作《文化地理学导论》中指出,“景观可以分为两大类——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⑤王恩涌.文化地理学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30.。随着西方学界把景观研究扩展到新的研究领域,景观研究逐渐发展成一种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景观研究的主题也趋于多元化,例如:“风景与权力、政治风景、作为帝国话语的风景、作为身份认同的风景、作为历史的风景、作为意识形态的风景、作为财富的风景、作为道德的风景、作为居住地的风景等”⑥周丹丹.论简·奥斯丁的风景叙事[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8.。
厄德里克通过部落典仪中的圆屋和汗屋等人文景观展现了印第安民族的文化特征,让印第安人在传统文化中建构民族身份,为小说的文字叙述增添了叙事的活力。圆屋和汗屋是印第安传统典仪的重要场所,而典仪在印第安文化传统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有助于传承部落文化、增强部落成员的归属感,是印第安人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印第安人通过典仪祈祷粮食丰收、战争胜利、疾病痊愈。作为举行典仪的重要场所,圆屋和汗屋两个文化景观是典型的印第安文化符号。
圆屋是小说《圆屋》中的重要景观,也是小说情节发展的重要线索。厄德里克选用圆屋这一景观作为小说标题有着深刻的含义。圆屋是印第安人举行典仪的神圣场所。印第安女性杰拉尔丁在这一神圣之地遭受白人侵犯喻指了“美国政府对整个部落权力的侵犯、对印第安人传统信仰的亵渎”⑦杨恒.罪恶·正义·救赎——评路易丝·厄德里克的获奖作品《圆屋》[J].芒种,2013,(17):129.。犯下罪行的白人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反映了当代印第安人的生存困境——司法上的不公平待遇。联邦、州及部落三级司法权力的重叠为白人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机,大量印第安人的权利受到损害。作者通过作品反映当初的社会现实,表达了对美国司法制度的强烈批判。此外,圆屋的形状体现了印第安人宇宙观的时空循环观念,即“时间往往被体验为循环的、反复的,而不是线形的、向前发展的,世界自身的运行模式也被认为是环形的,人的生命、其他任何表现形式和生物亦是如此”①Brown Joseph Epes.The Spiritual Legacy of the American Indian[M].New York: Crossroad,1982: 49.,“世界和整个宇宙是一种无尽的循环”②Richard Erdoes,Alfonso Ortiz.American Indian Myths & Legends[M].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1984: 5.。宇宙由无数环形构成,印第安民族的生存能力也“来自一个神圣的环形,只要这个环形不遭到破坏,民族就会兴旺发达”③Black Elk,John Gneisenau Neihardt.Black Elk Speaks[M].Lincoln Neb.: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61: 198.。基于这一观念,印第安人将举行典仪的场所建成圆形,并将这个圆形场视为环形宇宙的缩影、时间与空间的中心。“他们相信,以这个轴心为基点举行的典仪将会使他们重新融入‘伟大的神秘’的和谐整体,获取把握神圣力量的能力”④邹惠玲.典仪——印第安宇宙观的重要载体——印第安传统文化初探[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4,(4):55.。
法国社会学家爱弥儿· 涂尔干(Emile Durkheim)曾论述过典仪对培养集体情感和强化集体意识的重要性。他认为,定期地强化集体情感和集体意识才能使社会获得同一性,“这种精神的重铸只有通过聚合、聚集和聚会等手段才能实现,在这些场合个体被紧密地联系起来,进而一道加深他们的共同情感:于是就产生了仪典”⑤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仪式[M].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406.。北美大陆的印第安部落众多,且部落文化各异,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典仪文化。然而,白人殖民者对印第安人实行了的宗教同化和宗教迫害。尽管许多“传统的印第安人偷偷保留了古老的仪式”⑥厄德里克.圆屋:257.,依然有许多印第安传统仪式消失或发生了改变。直到1934 年,《印第安人重组法》颁布,这一法案试图保护印第安人的传统文化,承认印第安文化的差异。20 世纪60—70 年代美国兴起的“红种人权力”运动激发了印第安人的民族身份认同感,唤起了印第安人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典仪在印第安部落中再次兴起,成为印第安人复兴民族文化、建构民族身份的重要方式。小说《圆屋》的故事背景正是“红种人权力”运动,小说中的印第安人为了躲避神父或印第安事务管理局的管制,以跳舞为由在圆屋中秘密举行摇晃帐篷仪式、汗屋仪式等救赎仪式。在这个意义上,圆屋不仅是印第安民族文化的符号,也是实现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圆屋》和《拉罗斯》两部小说中有一个共同的典仪景观——汗屋。汗屋具有教育后辈、疗愈创伤、传承文化、民族认同的作用,是印第安人向祖先祈祷,与祖先的灵魂交流的地方。汗屋中的摆设反映了印第安人的宇宙观。屋子中央的“火坑象征着宇宙的中心”⑦曲悦.北美印第安人的仪式与礼仪[J].英语知识,2012,(12):8.,被烧得滚烫的石头被称为“石祖”,扔进火里的烟草“象征着特殊的祈祷或请求”⑧厄德里克.圆屋:38.。兰德尔在两部小说中都负责经营汗屋,通过主持汗屋仪式为印第安人祈福,帮助印第安人减轻身体和精神的痛苦。兰德尔对汗屋仪式的传承象征了对民族文化的守护。《圆屋》中的小安东·巴兹尔·库茨在兰德尔的汗屋仪式中加深了对部落传统文化的了解,在成长的过程中对民族文化和民族身份充满自信,加强了自己对族裔身份的认同。面对白人对其印第安身份的询问,他的回答是:“哥伦布搞错啦,真正的印第安人在印度,我是纯正的齐佩瓦人”⑨厄德里克.圆屋:283.。小说《拉罗斯》中的汗屋是犯错的朗德罗忏悔过错和祈祷的救赎之地,也是疗愈精神伤痛之地。朗德罗因误杀好友的儿子导致两家人精神上受到巨大打击,朗德罗在自责和痛苦中去汗屋祈求神灵的帮助。朗德罗唱着动物神灵和风神的颂歌,妻子艾玛琳一边将草药倒入火中,一边唱着召唤神灵玛尼图格和阿迪祖卡纳格的颂歌。他们在汗屋中呼唤祖先的亡灵,祈求得到帮助,最终从幻象呈现的景象中得到启示,获得内心的安宁和精神的疗愈。厄德里克通过部落典仪景观展示了印第安文化传统的魅力,帮助当代印第安人铭记历史,加深对文化传统的认识和联系,巩固印第安文化身份。
四、结语
在厄德里克的笔下,景观不仅是可视的地貌和历史的记忆,也是可读的地形学文本和符号。印第安部落和保留地的每一个景观都有独特的意义,他们勾勒了文本的背景图,记录了人物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塑造并强化了他们的民族身份,在叙事的过程中凸显了其内在价值。正是这特有的民族景观,以及与景观联系在一起的记忆,帮助当代印第安人加强民族身份认同,找到回归精神家园之路。就此而论,景观作为一个能够反映民族历史、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载体,是印第安人反抗殖民主义、弘扬民族文化、增强民族意识和实现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