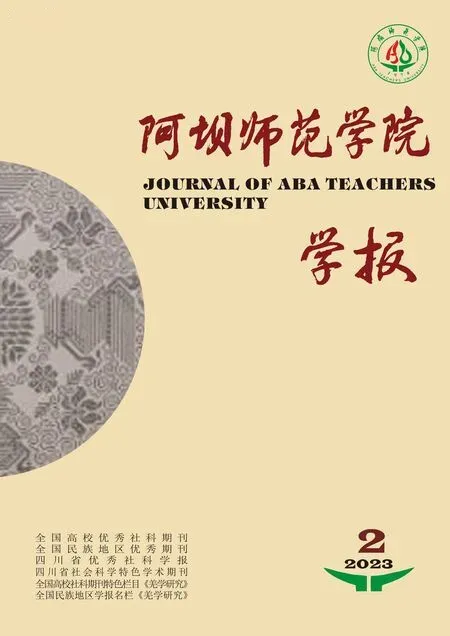现实主义的三重变奏
——论冯良《西南边》的边地书写及其意义
2023-02-08孔许友
孔许友
冯良小说《西南边》是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作品,作为一部少数民族题材长篇新作,该作一经问世就引起评论界关注。在已有评论中,两种似乎相反的声音值得注意:一种视其为“一部厚重的彝族现代史诗”①王春林.彝人“现代史”——论冯良长篇小说《西南边》[J].扬子江评论,2019,(3):78.,因为它“在民族碰撞与交融的过程中透视表现彝人现代历史命运变迁”②王春林.彝人“现代史”——论冯良长篇小说《西南边》:82.;另一种则批评它“既要通过‘历史’结构出长篇小说‘史诗性’的宏大意义,又试图‘发覆’大历史中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两者之间形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③李哲.“边地”历史书写中的“自我”想象及其限度——以冯良《西南边》为例[J].民族文学研究,2021,(1):31.。不难看出,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更加深刻和敏锐的洞察,因为前者只关注到《西南边》表现宏大意义的一面,而忽视了其“发覆日常生活”的另一面。不过,这两种意见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比较单纯地根据现实主义文学标准来理解或要求这部作品。依此标准,小说中很多日常生活描摹就容易被视为缺乏内在深度和意义的“自我”想象,它干扰、削弱了作品对现实历史主题的表现。在笔者看来,恰恰有必要重审上述批评所包含的两个层面问题: 其一,作品所呈现的日常生活只是琐碎无聊的想象,以至于不值一写? 其二,这些日常生活描写真的与作品的历史主题缺乏关联,甚至形成难以调和的矛盾?本文认为答案总体上都是否定的。事实上,《西南边》是一部内涵相当复杂的作品,不能以单纯的现实主义标准加以衡量。作者尝试在现实历史意识的基础上调取浪漫主义、新历史小说以及寻根文学的思想质素,并对其进行变造或整合,从而组成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三重变奏。这些变奏性旋律主要就体现在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之中,它们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作品的“史诗”品格,但也使作品的思想旨趣在多个维度呈现出新意。
一、彝汉关系与浪漫之爱
说《西南边》具有现实主义底色,不仅因为它的内容完全写实,也不仅因为它在政治的层面上以从民改平叛到改革开放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为线性时间坐标,表面上呼应了进化论的历史观,还因为它确有一个建构性的历史主题,即彝汉交融。小说大体呈现了20 世纪40 至80 年代四川凉山地区彝汉关系从对立、碰撞走向互动、融合的过程。小说中参差错落的故事或多或少都与该主题有关,但直接承载该主题的恰恰是属于日常生活领域的婚恋故事。它以夏觉仁和曲尼阿果这两个人物为中心,相关情节线索在整部小说中最为突出。以日常婚恋故事承载历史主题的根本依据在于自然爱欲具有政治性的功能。人类共同体的内在和谐需要落实在人的自然本性之中,并通过个体生命之间的互动来完成,而作为对美之渴望的爱欲是人的自然本性中最能达成个体生命相互吸引的冲动,“是通过激情所能到达的一种人类社会性的完满”①布鲁姆.爱的设计——卢梭与浪漫派[M].胡辛凯,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11.。
通过跨民族婚恋故事表现彝汉关系主题在已有的彝族小说中十分罕见,因此,客观上说,冯良开拓了一片新的文学表现空间。但更重要的是,《西南边》中爱欲与时代、传统之间的关联形式有别于以往彝族小说。在这些小说中,爱欲的自然性即便是剧情的缘起,即便被描绘得强烈而动人,但从来不会成为对抗意识形态的根本力量,因为爱欲本身被赋予了或鲜明或抽象的历史和阶级属性,进而,爱情的成就总是取决于爱欲附着其上的时代集体观念,也就是说,戏剧矛盾的关键部分始终建构在由不同社会存在决定的不同社会意识之间,而不是在自然爱欲与社会意识之间。唯其如此,历史意识的历史批判才能够成立。例如阿蕾的很多短篇小说,抒写彝族传统礼法强加给彝族女性的生命压抑,在揭露落后传统的同时,呼唤的是现代爱情观念和婚姻制度。在马德清的长篇小说《厚墙裂痕》中,黑彝头人施拉与奴隶阿娓的爱情以悲剧收场,原因是施拉不可能克服自己的阶级本性,而白彝阿且与阿卓的爱情能够经受考验并圆满实现,是因为他们向往平等,没有阶级观念的束缚。《西南边》中的情感叙事则不同,小说中爱欲关系演化经历的初定、沉沦、升华三个阶段,虽然约略对应民主改革、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市场经济冲击三个时期,但后者主要作为彝汉关系的历史背景,其中的时代话语不构成爱欲演化的决定因素。表面上矛盾冲突既在不同的社会意识之间,也在自然爱欲与社会意识之间,但前者被证明只是虚晃的招数,没有真正展开,后者才是作者施展手脚的场域,并且最终是自然爱欲通过自我超越影响了社会意识(民族隔阂观念),而非社会意识压制了自然爱欲。正是在这里,《西南边》完成了现实主义的第一重变奏。这一变奏具有浪漫主义的质感,因为小说所表现的自然爱欲不能被约简为一般情欲,而是隐隐之中与更高的灵魂部分相关,只有这样的自然爱欲才可能在危机的洗礼中升华,这样的自然爱欲所对应的生活日常即便琐碎亦是诗意的琐碎。
小说开头数章的时空场景是20 世纪50 年代凉山民改时期的平叛剿匪战事。平叛战事看起来紧张激烈,但作者不经意间透露,实际上我方胜券在握,没有什么悬念。所以,在木略劝降事件发生之前,它只是叙事的背景而非前台。前台上演的是一场看似“狗血”的多角恋爱剧,人物关系几分神似金庸小说《天龙八部》:出身上海资产阶级家庭的汉族军医夏觉仁对美丽娇羞又高傲倔强的黑彝姑娘曲尼阿果一见钟情,遂借军医身份的便利当起了不讨好的护花使者——不讨好是因为那时曲尼阿果心里装着她的表哥古侯乌牛。与此同时,爽利泼辣的白彝姑娘沙马依葛又对夏觉仁穷追不舍。当然并不真的“狗血”,而是为了表现夏觉仁和曲尼阿果爱欲关系的初定阶段。冯良笔底有春风,将爱欲互动刻画得活灵活现、意趣横生,对少女阿果“害羞”的描摹尤为动人,如写她不要夏觉仁给她挑脚板上的刺,只因夏觉仁是男军医,“这位犹疑不定,点头,摇头,泪光盈盈,脸面茸茸,上翘的下巴颏掬着的小肉坑,圆润、柔弱”。②冯良.西南边[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文中所引该作品原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正是这娇羞的神态令夏觉仁“眼迷心蒙”,一见倾心。阿果的性情还具有丰富微妙的矛盾统一性:她高傲冷峭,“说话不看人,鼻子高翘,傲兮兮”;却又敏感纯真,夏觉仁扶她骑马时不小心摔倒蹭破皮,她“哭得止不住,两只手从里到外横揩着眼泪,脸都花了”,夏觉仁以为她在担心自己,其实她大概只是见不得别人受伤。
上述内容读来恍惚间有脱离时代之感,细读之下则不然。其一,平叛战事中的恋爱故事关联着彝汉关系主题,并非纯然脱离时代的小历史。夏觉仁追求阿果的过程曲折不顺不仅仅因为阿果太慢热或心有所属,小说同时突出了舆论压力,首先便是彝汉不通婚的彝族传统观念。精通世故的锅庄娃子木略和汉人俘虏俞昌富都郑重其事地告诫夏觉仁:“我们彝人是不和外人开亲的……大家不分里外,乱开亲,成啥规矩!”“她家妈宁肯拉上她去跳河上吊,也不会把她嫁给你。她家的骨头硬呢,黑彝……有那么多汉姑娘,干啥喜欢彝姑娘!”事后证明,他们不完全是危言耸听。其二,平叛战事虽仅充作背景,但并非与恋情无关。平叛是民改运动的一部分,而民改运动意味着人民政治伦理在彝区的强势进入。这不仅造成彝族社会本身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深刻影响了彝汉关系。假如没有民改,夏觉仁与曲尼阿果的跨民族婚恋无疑更难以想象。面对木略和俞昌富的告诫,夏觉仁也相信自己可以依靠“和旧势力斗争”的“勇气”:“什么不和汉人开亲、娃娃亲,一概视为封建陋俗,打定主意要把曲尼阿果带动起来勇敢地加以破坏”。从中可见革命的政治话语对时代青年夏觉仁想象空间的界定。
尽管如此,这里叙事的侧重点不在于写时代变革和政治话语如何帮助夏觉仁破除彝人传统观念,让曲尼家人接受他这个汉女婿。换言之,夏觉仁心中的新观念与彝汉不通婚这种“封建陋俗”并没有真正形成交锋。了解了后情再回看此处,才明白所谓“和旧势力斗争”云云不过是冯良一贯的轻幽默。夏觉仁自己都不会料到他的勇气只来自对阿果的爱欲,因为他完全是靠着软磨硬泡,“跑去给阿果家当娃子,夜里睡柴火堆,白天放羊放猪,兜里揣几个烤洋芋,荞粑粑都吃不上”,如此吃尽苦头,才生生把阿果的家人给感化了。这一情节所传达的思想是: 社会意识的转变并不全赖宏观时势的变迁,人性和人情的底层逻辑永远是有效的力量,在具体的人生处境中,其作用可能比伴随宏观时势的话语观念更加真切。
婚恋线索最大的转折是,痴情如段誉,在婚后依旧“爱老婆爱得神魂颠倒”的夏觉仁和沙马依葛这个“坏女人”出轨。从情节发展的角度说,出轨事件是一个高潮,但就爱欲关系的逻辑而言,出轨事件无疑是低谷。追溯其有些扑朔迷离的前因后果将有助于理解这部小说的关键内涵。夏觉仁为何出轨,已有论者注意且说法不一。有的认为:“在夏觉仁自己的本心,他的出轨,也是为了爱妻曲尼阿果”。①王春林.彝人“现代史”——论冯良长篇小说《西南边》:82.也就是说,夏觉仁是在利用沙马依葛的权力给阿果续假。有夏觉仁自己的心里话为证: “他的牺牲很大,包括和沙马依葛的苟且,完全不是为了享乐。这是根生在他心底的想法,虽然愧疚,无以面对阿果。”还有的说:“对夏觉仁来说,阿果是他灵的向往,沙马依葛是他欲的承载;阿果代表了他出世的追求,沙马依葛则意味着现世的幸福”②岳雯.爱的分析——读冯良的《西南边》[J].当代作家评论,2018,(5):95 -96.,“沙马依葛牢牢占据了他的身体领域,那是位于精神一极的阿果进不去的疆域”③岳雯.爱的分析——读冯良的《西南边》:98.。以上两种说法即便不是全无道理,也都未能点出要害。为阿果续假之说显然不合情理。作者把出轨与续假相关联虽然有突显情感故事的时代背景之意,但主要是为了表明夏觉仁自己也不清楚或不愿面对出轨的潜意识真相,他坚信自己是爱阿果的,所以需要一个表面的理性解释来自我暗示。阿果之于夏觉仁也绝非只是灵的对象而无欲的承载,他们的爱情作为一种自然爱欲关系从一开始就不是只有精神一极。
情感线的这一变故其实是多方埋了伏笔的。首先,民改平叛时期,沙马依葛对夏觉仁的追求并非没有触动夏觉仁心底的波澜,只不过这层波澜被仙女般的阿果强大的吸引力掩盖了。“偶然,沙马依葛的形象会岔进来,打乱他专一的情思。奇怪,只要沙马依葛的大脸盘和杏子般的眼睛一出现,他再要想念曲尼阿果,就要费点神”。有了这一层铺垫,“再续前缘”就不显得突兀。这是出自爱欲本身的原因,爱欲的自然性使爱欲天生带有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第二处伏笔出现在夏觉仁对阿侯沙则家人做派的联想那里:“他们这种植根于血液里的顽固、傲慢刹那间刺痛了夏觉仁,曲尼阿果神情、言语、举手投足间也全是这一套”。夏觉仁从阿侯沙则家人的傲慢联想到阿果的傲慢。阿果当然不会不关心自己娘家人,但是不够在意他。“夏觉仁觉得自己的性情像狗,记吃不记打,主人家拿根骨头,哪怕光秃秃的,在他面前稍一晃悠,又能把他哄驯服”。夏觉仁与阿果的爱欲关系一直不对等,仿佛夏觉仁一直充当爱人者,而阿果永远是高不可及的被爱者。“他爱老婆爱得神魂颠倒,老婆呢,未必”。正如阿兰·布鲁姆所言: “每一个爱人者都要求被爱作为回报,只有通过爱的回报他才能占有被爱者。”①布鲁姆,雅法.莎士比亚的政治[M].潘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45.如果缺乏回报,最先承受不住的就是爱人者的自尊。不难推想,沙马依葛的第三者介入正好补偿了夏觉仁这种被爱的自尊需求。同时要注意,夏觉仁的怨恨暗示他与阿果之间不对等爱欲关系的形成不完全由于爱欲的自然偶然性。阿果不够爱夏觉仁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是阿果对汉人有一种传统的偏见,阿果的社会意识干扰了她的自然爱欲。作者多次交代过阿果的这种偏见,如阿果第一次和夏觉仁打交道时骂他的话就是“烂汉人”,古侯乌牛曾劝她为方便起见取个汉名,她坚决不干。婚后夏觉仁对她奉若至宝,她却“与俞秀只说死后绝对不和夏家那些汉人埋在一起”。但问题往往是相互的,夏觉仁的问题在于不能感同身受地理解阿果的另一种传统意识,即对本族同胞的手足相惜之情。“石哈在他眼里只是一个又傻又脏的山里人,不足挂齿。除了曲尼阿果,还有他的家人,他并不觉得和彝人有什么瓜葛,人家提到他时,总强调他是彝胞的女婿,真让他奇怪,好像这么一来,他得特别对彝人友好”。此时的夏觉仁尚未真正融入阿果的精神世界,他的浪漫之眼还是目光狭隘的,他的爱欲想象只扩展到了阿果的家人,而不能完全爱阿果之所爱。两方面的病灶不断累积,爱欲关系必定向下行。变故的导火线是“新叛”事件中夏觉仁三次“背信弃义”的表现:没有料理阿果二姐的后事,没有为阿果父亲奔丧以及告发石哈。这三次表现显然被阿果认作夏觉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明证,直接导致她对夏觉仁的情感疏离。尽管所谓“背信弃义”不无内情,但在阿果心中,夏觉仁和宁愿放弃政治前途也要为舅舅奔丧的表哥比起来,简直差得太远。
婚恋线索后半程的情节是爱欲关系经历沉沦洗礼后的回升。按照彝人传统观念,夏觉仁的行为是对阿果整个家族的羞辱,阿果的彝人性格又如此鲜明,她会如何对待背叛过她的夏觉仁? 出乎读者和小说中很多人物意料的是,阿果顶住家族压力,选择了回归家庭。阿果的本意是为担负家庭责任,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属于她的社会责任。如夏觉仁所言,阿果“保有了他们的家庭,甚至从经济上,维系着包括他的亲人在内的人际关系,最主要的是两个孩子值得依赖的母亲”。阿果的行为选择表明她“接受了人的不完美,同时实现了自己的成长”②岳雯.爱的分析——读冯良的《西南边》:99 -100.。这是内在灵魂层面的成长,其中包含对民族传统偏见的克服。尽管与夏觉仁关系的回暖要缓慢和困难得多,但成熟了的阿果毕竟没有将爱欲之路堵死,至少是重新接受了夏觉仁的仰望。最后一章写夏觉仁留在乌尔山上,指导彝族护林员种植草药增加收入,给阿果母亲、石哈以及其他彝胞看病,这些内容看似无关紧要,其实正是为了表示夏觉仁的浪漫之眼终于睁开,看到了更高更远的所在,开始升华到了精神的视域。因此,小说最后以夫妻之间投桃报李收尾是合乎爱欲逻辑的,同时也象征性地证实了彝汉交融的曲折道路和可期前景。
二、时代话语的弱解构与非典型的欲望化叙事
《西南边》现实主义的第二重变奏体现在对新历史小说写法的借鉴和调整上,在作品中主要对应与木略和沙马依葛相关的故事。新历史小说兴起于20世纪80 年代后期和90 年代,其直接理论渊源是格林·布拉特等人的新历史主义批评(亦称为文化诗学),同时也与解构主义一脉的西方哲学和文论思潮有内在关系。这一创作思潮在中国文坛掀起的尘烟已渐渐远去,学界的评价也基本盖棺论定,概而言之,一方面肯定它对传统历史小说中那些空洞失真的宏大叙事的大胆反叛,另一方面否定其游戏历史、滑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应该说这种评价是客观公允的,问题在于“后新历史”的小说道路应该怎么走,是否有可能在新历史小说与其解构的“前文本”之间寻求一种叙事策略的中间道路,既化解“控构现实主义”的沉疴,又避免新历史主义的虚无化陷阱?笔者认为,《西南边》边地书写的意义之一就是在这方面作了一次有益尝试。
就所反映的社会历史而言,《西南边》与以往多部彝族长篇小说皆有重合之处。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尤其是第二部《早来的春天》)和《破晓的山野》、阿凉子者的《血染的索玛花》以及马德清的《厚墙裂痕》等都描写了解放初期凉山彝族的民改和建政,也涉及民族团结的话题。这几部长篇都属于比较典型的传统革命历史小说,突出当时政治话语主导的宏大叙事,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西南边》的“前文本”。那么,《西南边》是如何以新历史小说的手法反讽和解构此类宏大叙事呢? 作者采用的策略主要有三:披露正史“内情”,英雄人物“非英雄化”以及政治话语工具化。
木略劝降事件是一个典型例子,同时涉及上述三种策略。这原本是一个有宏大意义的平叛故事,但作者通过披露“内情”的手法将大写历史小写化了。木略本是吉黑家的奴隶娃子,他的发迹就始于此事件。事情的关键点是木略利用政治语汇的模糊性达成了自己的私人目的。吉黑哈则被鼓动参与作乱只是一时糊涂,且他主动捉拿了叛乱主谋马海双布,原本有可能被定性为“起义”,但木略给吉黑哈则下套,骗他向解放军承认自己是“投降”,从而暗中操控了事件的性质。吉黑哈则后半生的好日子就此断送,木略则被组织安排赴全国各地作宣讲,一举成为“砸碎万恶的奴隶制枷锁的英雄”,不仅新娶了媳妇,还从此当上了官。
开场戏中一个描写恋爱互动的细节也值得注意:曲尼阿果因为脚受伤无法上马,夏觉仁“爬跪在地”充当上马石。此情此景激起了暗恋夏觉仁的沙马依葛的愤怒,她斥责阿果: “关键是你的旧思想根本没得到改造,你们黑彝家的、奴隶主家的本性还在作怪,你以为自己还是主子家的小姐,夏军医是你家的娃子啊!”夏觉仁甘当上马石确实暗示他与阿果的爱欲关系不对等,但夏觉仁是追求者,所以这里的不对等出于自然,根本不能以等级和权力关系来衡量。显然,彝区民主改革中“平等”的政治话语成了沙马依葛发泄嫉妒的幌子。小说中描写沙马依葛、木略以及俞秀拿政策语言作矛作盾的例子还有不少,既为表现人物的狡猾或机智,也暗中揭示了当时宏大话语的空洞能指。
再如,那时的政治话语很快促成木略和俞秀、沙马依葛和吴升的婚姻,他们的婚事还成了359 团宣传“民族团结的盛事”,夏觉仁遭遇的却是“不许和民族同志谈情说爱”的命令以及“违反民族政策,和彝姑娘勾搭”的指责。如此双标并非由于夏觉仁的阶级出身,因为吴升的出身和夏觉仁类似,而是由于那两对都是直奔主题,几乎没有“谈情说爱”的过程。“谈情说爱”违反“命令”,一旦结婚却很符合政策,需要鼓励,哪怕动机可疑。木略和俞秀的结婚动机就很可疑,木略娶俞秀是因为嫌弃吉黑家配给他的又老又丑的乌孜,俞秀选择同样又老又丑的木略则是为了给自己找依靠,无非利益交换而已。这又是通过内情的披露反讽那时的政治话语只在意表面结果,而忽视过程和动机。
新历史小说的另一大特点是欲望化叙事,常常将权欲、性欲、物欲等当作恒常人性的本质,如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中对权力斗争的暴力美学展示,陈忠实的《白鹿原》中以田小娥为中心的情欲大戏,苏童的《米》和余华《活着》中分别对生存欲望的积极面相和消极面相的历史化演绎等等。此类欲望叙事的意图往往与挑战、颠覆当时的宏大话语相关。《西南边》对木略和沙马依葛这两个人物的塑造同样侧重于他们的欲望化表演,尤其是在权欲方面。木略与沙马依葛之间的戏主要是他们为了各自的仕途相互利用又彼此算计。对木略的刻画尤为深入。“新叛”事件中,读者很容易以为石哈之事的责任在夏觉仁,因为是夏觉仁向木略“告发”了石哈假装带队追捕黑彝奴隶主的把戏,但起关键作用的其实是木略。夏觉仁只是希望引起木略对曲尼拉博的同情,不是真想告发石哈。他没料到木略会拿石哈这个和“新叛”没有直接关系的彝人娃子开刀。木略这么做固然是恼恨石哈的欺骗,但更主要的是急于找个替罪羊好向上表功。他要向王副政委表明自己没有“陷在要命的民族感情里”,没有“消极抗命”,因为他害怕自己与“新叛”起因的关联——曲尼阿呷是他派盘加护送的——暴露出来。这种没有当小偷却自认作贼的微妙心理,想必是红卫兵批斗给他留下的后遗症。为了在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风浪中保住官位,他必须绷紧神经,紧跟时势,绝不心慈手软。沙马依葛也是一个官迷。木略当县长后,她经常巴结木略一家。红卫兵闹事时,她却投靠红卫兵小蓝为批斗木略添油加醋,不料小蓝是个冒充高干女儿的假红卫兵,她借机捞取政治资本的企图落了空。但她并不就此偃旗息鼓,“新叛”事件中,是她向木略举报阿果回娘家奔丧,为了重新巴结木略,不惜给木略擦洗灌了猪屎的鞋子。再后来,她靠着和王副政委的暧昧关系终于正式步入仕途。
但是,与新历史小说惯常的无底线解构以及将人物欲望表现得非常极端乃至畸形不同,《西南边》对当时的政治话语的解构属于有限度、有节制的“弱解构”,其欲望化叙事亦不超出普通人的行为逻辑,相对于新历史小说反而显得非典型。整部小说没有激烈的爱恨情仇,也没有高蹈的愤世嫉俗,而是凡事皆有波澜,又终归波澜不惊。“弱解构”的体现如童年的木略当奴隶娃子受苦受难并非虚假,尽管他有时能够机智地暗中收拾主子。劝降事件中木略虽动了手脚,但有功劳也是事实。冯良让我们瞥见了真实历史进程的复杂性,避免了对历史的简单化认识,没有将政治变革本身(如彝区民改)的历史意义虚无化、荒诞化。木略和俞秀虽然似乎只是结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但两口子能同享福亦能共患难,日子过得有烟火气,比起阿果和夏觉仁飘在云端的爱情,倒有几分实在感。冯良没有把对他们婚姻动机的揭露无限制地上升到对民族团结政策的否定和批判。欲望化叙事的非典型则体现在: 木略和沙马依葛固然贪恋官位,但没有明显渎职行径,相反,在工作上都还算尽职尽责,尤其是沙马依葛,做事干练果断、处变不惊。她当公安局副局长,为了不错过时机,仅带着忠诚度尚存疑的几几嫫和一个没多少经验的年轻干部,就敢进山抓捕逃匿数十年的悍匪马布尔子,并且成功击毙了他。她和王副政委虽有些许暧昧,但二人并无越界之实,很难说王副政委提拔她全是因为被她色诱。在情欲方面,沙马依葛利用俞秀对阿果的嫉妒心理撺掇俞秀一起煽风点火,试图迫使阿果和夏觉仁离婚,但未达目的便也不了了之。
更重要的是,冯良不像很多新历史小说作家那样将复杂多重的人性约简为人性中的低级欲望——这是他们把历史进程等同于欲望表演过程的根源。冯良对人性的理解要深刻得多,她不对笔下人物作生硬的非善即恶的道德判断,但看似超然、平和的叙述中亦能见出具体行为的品质差别。所以,出轨之后的沙马依葛在阿果面前是自惭形秽的,夏觉仁的怯懦与古侯乌牛的勇气在阿果眼中形成了鲜明反差,夏觉仁一家的淡泊名利与木略、沙马依葛的贪恋权位也构成对比。
《西南边》的弱解构策略和非典型的欲望化叙事看似中庸,其实恰恰能够同时在历史和人性两个层面保有回旋和探索的空间:就历史层面而言,既延续了新历史主义对宏大话语的深刻反思,又在现实主义的本位上坚持了历史逻辑的严肃性; 就人性层面而言,既对历史洪流中普通人的真实境遇和生存选择给予同情理解,又不遮蔽或抹平这些选择所伴随的灵魂品质的高低差异。
《西南边》对历史创伤的表现也与新历史小说有相通之处。新历史小说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善于“将古今伤痛揉为一体,在历史简单化的循环之中,人们可以发现当代中国所经历的难以解脱的灾难和伤痛”①史鸣威.1990 年代“新历史主义”小说论[J].百家评论,2020,(5):33.。对历史创伤的表现是反思宏大话语的题中之义,《西南边》中红卫兵对钱书记的批斗,曲尼阿呷和曲尼拉博的死和石哈的受迫害,游泳比赛事件中的溺亡事故,以及凉山彝族社会在自由市场经济冲击下暴露出的深重危机等皆属此类。不过,有时为了刻意体现面对历史的平和态度和叙事策略的中间性,《西南边》的一些情节设计也存在令人遗憾之处,如曲尼阿呷的死是与造反派有关联的,她是被造反派驱赶才不得不离开妹妹家,但直接的死因却是回家路上遭遇山洪,实属偶然;游泳比赛事件中溺亡事故的直接原因也是意外。新历史小说放大历史偶然性通常有两种意图,一是拆解历史的理性逻辑,二是表达造化弄人、世事无常的生存感觉。《西南边》中偶然性笔法的使用大抵符合后者,但无形中削弱了创伤书写的力度和历史反思的深度。
此外,《西南边》叙事立场的中间性决定了整部作品温和、含蓄的基调,一如小说封面配图上土地的颜色——用的是介于明亮和灰白之间的赭色。在审美效果上它没有现实主义“史诗”的波澜壮阔,也不可能如新历史小说那般传奇魅惑,却也别有一番景致,如飞鸟隐没晚山,喧闹复归宁静。
三、民族文化“寻根”:风情与温情
《西南边》现实主义的第三重变奏是民族文化“寻根”意识的融入。我们知道,寻根小说亦兴起于20 世纪80 年代,而且一开始便与少数民族文学相关。1983 年,达斡尔族作家李陀在写给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信中称赞乌热尔图创作出了“地地道道的鄂温克族文学”①李陀,乌热尔图.创作通信[J].人民文学,1984,(3):121.,并说自己“多年来远离故乡,远离达斡尔族的民族生活……很想有机会回老家去看看,去‘寻根’……去体验达斡尔文化给我的激动”②李陀,乌热尔图.创作通信:124.。这被广泛认为是“寻根”文学概念出现的重要标志。寻根小说作为一种处于“中心”地位的创作潮流,在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棋王》、王安忆的《小鲍庄》、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郑万隆的《老棒子酒馆》等一批公认的代表作品问世之后逐渐为新历史主义思潮所取代,但并没有真的在实践上归于沉寂。沉寂的主要是基于文化启蒙和救世旨归的寻根写作,这种寻根将目光投向地理和族群意义上的边缘,试图寻找在边缘地带以“非规范”形式保存的文化传统。少数民族文学的“寻根”其实一直在延续并在本世纪初渐成勃兴之势,尽管“寻根”这一说法不再流行。其旨趣更多地体现在少数民族作家对自身族性文化的认同重构方面。无论是其源还是其流,寻根文学都是以文学的名义寻民族文化之根,都需要回答诸如民族文化的“根”是什么,是否可能寻得,是否需要取舍,如何取舍,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二难,如何面对后殖民主义批评的质疑等一系列问题。20 世纪80 年代寻根文学思潮的没落,主要原因就是未能很好地回答这些问题,而对于方兴未艾的少数民族“寻根”文学而言,这些问题依然隐含在认同重构的逻辑之中。以彝族文学为例,传统与现代的“二难情结”在纳张元、罗庆春、英布草心等彝族当代知名作家的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体现。他们感叹、惋惜民族传统生活方式的日益式微,试图重新皈依和张扬本民族文化的内在精神,但对现代文明及其价值观的接受又是这种皈依的前提。相比之下,《西南边》中的民族文化“寻根”之路没有表现出强烈的焦虑和困惑感,甚至表面上有些浅显和散淡,但其中或许包含了回应上述问题的新的可能性。
寻根作家通常“对民风、民俗、野史、逸闻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与兴趣”③刘忠.寻根文学的精神谱系与现代视野[J].河北学刊,2006,(3):135.。《西南边》对彝族文化的书写也有类似之处,只不过更侧重在民俗和民风方面。小说行文中间杂着大量有关彝族服饰打扮、礼俗、日常饮食乃至自然风物等民俗物象的生动描绘,诸如少女的瓦盖、美丽的百褶裙,男子不可触碰的天菩萨、多用途的披风察尔瓦; 毕摩唱的送魂指路经,给阿果作的招魂法事; 穷人吃的烤洋芋、荞粑粑,乌孜酿的桃子酒;百色的索玛花,清香的桃花,飞舞的群蜂,种类繁多的草药、野菌等等。这些内容构成了作品日常生活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是对彝族民风的刻画。《彝娘汉老子》中有一篇散文《害羞的民族》,把彝人的气质特点归结为“害羞”二字,这种气质在《西南边》女主人公之一的曲尼阿果身上得到了更为细腻、丰满的诠释。除此之外,《西南边》表现的彝人群体性格还有好勇、抱团、重情义等等,如马海双布、阿侯沙则、马布尔子都好勇斗狠,石哈、古侯乌牛等皆重情义,“新叛”事件中黑彝家支不惜烧掉房子,集体逃亡,则是抱团的典型体现。对彝族民俗民风的描绘或作为情节桥段之间的过渡衔接,或融入主要情节设计和人物塑造之中,如同浇洒在一盘大菜中的丰富佐料,使整部小说充满民族乡土风情。
在一篇简短的创作谈中,冯良曾自述: “《西南边》于作者我,是一部自我亲近的作品”④冯良.创作谈——自我亲近[EB/OL].http: //www.chinawriter.com.cn/n1/2016/0929/c404032 -28749102.html,2016 -09-29/2022 -05 -01.。这是创作动机的直白,某种意义上也是文化寻根意识的自白。如果把她的散文集《彝娘汉老子》和《西南边》放在一起读,我们不难感受到《西南边》或隐或显地融入了她个人的文化记忆和情感经验。作为一种多少带有女性气质的创作动机,“自我亲近”与一般寻根作家的“文化宏愿”有所不同,后者如韩少功曾说的:“‘寻根’……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①韩少功.文学的“根”[C]//谢尚发.寻根文学研究资料.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78.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文化拯救意向的导引下,一般寻根文学往往试图将某种抽象的超越理性、世俗的神秘精神内核认作民族文化的不变之“根”,以此实现民族文化的复魅,而《西南边》的创作动机和书写方式则表明,冯良不再抱持启蒙或救世的文化想象和情结,无论这种拯救的对象是整体意念还是少数民族自身。根据学界对寻根文学的复盘和追问,那种寻求绝对特异且一成不变的文化之“根”的思路恰恰是可疑的,也不可能真正达成,因为它不符合文化的历史逻辑,从而必然陷入启蒙与反启蒙、反抗与献媚之类动机与效果的悖论。诚如论者所言: “面对祖先和历史,寻根作家表现出的类似宗教祭祀般的虔诚行为,以及再造一个有关民族文化的乌托邦冲动……注定是一场凌虚高蹈的话语狂欢,任何回到文化原初形态的构想都不能不是历史神话的一个苍凉手势。”②刘忠.寻根文学的精神谱系与现代视野:136.
《西南边》所呈现的彝族民俗民风本质上是历史性的。这种历史性与民族文化“如何置身于政治制度、经济体系的庞大运转系统”③南帆.“寻根”文学的理论后缀[J].文艺争鸣,2014,(11):18.有关,同时也“显现于各种对话制造的周边关系”④南帆.“寻根”文学的理论后缀:18.中。烤洋芋和荞粑粑所昭示的不是恒常的饮食习惯,而是当时贫穷和贫穷背后的社会经济制度。外出求学的古侯乌牛穿起了西装,还给自己取了汉名,这当然是“对话”的结果。“文革”期间毕摩受到批斗,偷偷作法事都“被鬼欺”,而病人家属请毕摩作了法事之后也开始懂得再请医生来治疗。可见民间信仰是被裹挟在社会演化的激流中的。至于更深一层的民族群体性格,冯良也不再像写《彝娘汉老子》时那样将其归结为似乎在彝人中绝对普遍的“害羞”,如在时代弄潮儿沙马依葛身上就完全不见曲尼阿果式的“害羞”。至于抱团、好勇斗狠,显然也与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彝汉关系状况以及彝族家支伦理制度有内在关联。
进一步说,任何习传的文化传统正是因为具有历史性才有可能接受批判性的检验和反思,才有可能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和更新。真正有意义的文学“寻根”本身就应该是一个进行批判性反思并将反思成果加以审美化展现的过程。如果说《西南边》的彝族文化书写正是这种类型,那么冯良所寻到的有意义的文化之“根”到底是什么呢? 笔者以为恰恰是现世或甚至是俗世层面的人伦温情,包含友情、亲情乃至同胞之情。《西南边》实际上是一部温情脉脉的小说,对彝族民俗民风的描写也往往围绕温情、表现温情。举例言之,小说中有一段对毕摩招魂的描述:“他见过那样的场景,当时毕摩在为一个生病昏迷的孩子招魂。羊皮纸上写满了招魂的经文,内容并不特别,甚至家常,‘回来吧,回来,你家妈在阳光暖和的南坡上、在煮得有鸡肉炖得有猪肉的火塘边、在结了果子的桃树樱桃树下等着你盼着你’,婉转,顿挫,余音袅然,他听着当即泪下。”对此类有关彝族民间信仰的内容,冯良的写法既不同于《欢笑的金沙江》等早期彝族长篇那样站在科学主义的立场上简单批判其为“干迷信”,也不像英布草心的《虚野》那样以文化主义的目光渲染其中神秘、灵性的诗意,而是几乎纯然地将其当作俗世亲情的动人表达。其他表现人伦温情的情节亦俯拾皆是: 写亲情如阿果因为亲人的离世而“魂飘三处”,古侯乌牛宁可自毁“前程”也要为舅舅奔丧,曲尼阿呷把妹妹妹夫的儿女视如己出,被木略抛弃的乌孜愿意和俞秀以姐妹相称,还送来自己酿的桃子酒; 表现友情如石哈假装追捕曲尼拉博,阿果则一直挂念石哈平反之事,还有那个被管制的毕摩因为曲尼拉博生前对自己有恩,“死也要给他指路回祖灵地”;写同胞之情则如阿果和彝族基干队员同情因叛乱被击毙的对手,帮助其家属打点后事。此外,小说对彝人俗世温情的强调与对彝族传统社会伦理的批判性反思并行不悖。如作者显然反对彝族传统中父母对子女的生杀予夺之权; 家支伦理也被一分为二地看待,对“新叛”事件中那种盲目的跟随以及“老辈子”对家庭生活的干预,作者是不认同的,但她也肯定家支在彝区强制戒毒活动中起到的作用。在很多寻根作家那里,复魅和脱俗是为了抵抗现代工具理性,《西南边》则提示我们,能够抵抗工具理性,克服自我与他者间自然对立的恰恰是经过道德理性反思的俗世温情。
小说中俗世温情的表达是与彝汉交融的现实主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冯良来说,“自我亲近”并不单纯是重新确认民族文化身份的过程。冯良本人是彝汉“混血”,在散文《彝娘汉老子》中,她对自己曾经的身份焦虑有过述说。该文最后一句话(同时也是同名文集的最后一句)就是:“所以说呢,当彝族还是汉族,这是个问题!”①冯良.彝娘汉老子[M].成都:天地出版社,2005:207.此问题看来在《西南边》中得到了某种解决。我们注意到,与冯良以往的作品不同,《西南边》长江文艺版封底的作者简介中没有出现“彝族”这一身份标识,取而代之的是“四川凉山人”。这多半不是编辑的疏忽,其中透露的意味当然并非放弃彝族身份,而是从彝族人到凉山人的转换或升华。它似乎暗示“自我亲近”的背后仍然有着某种宏大的现实关怀,其旨趣超越了彝族文化本位,指向的是彝汉交融。这一宏大关怀显然不能单靠浪漫之爱所构建的连接来实现。《西南边》的文化温情主义某种意义上是浪漫之爱的自然延伸,一种从爱情直到同胞之情的跨民族的人伦温情体系由此得以建构。民族交融的推进除了要平等对话之外,更需要彼此亲近,情意相通,两个民族之间“文化公约数”的重要性由此突显出来。对人伦温情的格外珍视恰恰起到了“文化公约数”的作用,因为它既被审美地表现为彝族文化的一种精神特质,同时也是汉族文化的悠久传统,甚至还具有人类文化的普世性。温情的本质无非同情的想象,所以在小说中,人伦温情为彝人和汉人的相互接近提供了彼此想象的基础,如上文所引对毕摩招魂的描述是借汉人夏觉仁的视角来写的,民族文化的区隔在一句“当即泪下”中瞬间消弭。在“游泳比赛”善后事宜的处理中,阿果力排众议,同意溺死的汉族知青叶童和为救他而牺牲的古侯乌牛一起作烈士,理由也是人伦温情共通的想象: “阿果表妹说,……他家爸爸妈妈更造孽,多标致的一个儿子化入空气影影都不见了,他们想要儿子是烈士就由着他们吧”。作者还有意识地把友情描写放在彝族人物和汉族人物之间,如俞秀与阿果,夏觉仁与木略,虽然存在“朋友间的毒”,但没有哪一次毒到了底,更多时候是相互关照,彼此谅解。
将彝族文化和彝汉交融之“根”体认为俗世温情的倾向还有助于回应后殖民批评的审视。后殖民批评对寻根文学的质疑要点在于,寻根写作在客观效果(而非主观动机)上存在以民族“奇观”向他者献媚从而陷入霸权话语规训的嫌疑。首先需要澄清的是,不应将独特民族风情的展现简单理解为献媚。任何文化之间要沟通和靠近,都需要展示不同于他者、具有吸引力的文化审美景观。献媚的实质是对本民族文化进行刻意的神秘化加工以迎合他者目光,进而“充当其认可与评判的坐标”②刘忠.寻根文学的精神谱系与现代视野:135.,在这种情况下,“奇观”展示者真正认同的只是霸权话语未经批判性检验的文化价值观。俗世人伦温情显然不属于此类价值观范畴。其次,后殖民批评的主要关切点在于不同民族之间甚至是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对抗关系,但相对忽视了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参照、相互启发的重要性。而且,这种理论视角不能完全挪用于认识和处理统一国家内部的民族关系问题。对于后者而言,既要保持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鼓励和发展民族个性,同时更应注重挖掘和发扬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在基本价值观层面的相通性。由是观之,《西南边》的边地书写对俗世人伦温情的审美表现无疑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最后说说《西南边》的语言。从《西藏物语》到《秦娥》再到《西南边》,冯良驾驭长篇小说语言的能力以可见的速度增长,逐渐达到了教科书级的老到。《西南边》不以大开大合、跌宕起伏的传奇情节取胜,而多少带有“散文化小说”的色彩,其美学效果一定程度上倚仗了语言的精致和传神。冯良自己在一篇访谈中也曾自信地说: “如果说我有哪一点故意要‘炫’的话,我会炫小说的语言,语调和节奏都会注意,虽然川音感十足,但我们四川人可以读出声来,如果愿意的话。后一句话特指《西南边》。”①吴越,冯良.多元文化碰撞、为凉山人塑像——对话《西南边》[J].当代文坛,2017,(1):89.音调节奏与方言俚语的巧妙搭配确实是《西南边》语言上的一大特点。无论是人物语言还是叙述语言,无论是描写景色还是刻画人物,满是“川音沙沙、彝音混成”(皮皮评语)的边地韵味,加上富有女性气质的幽默、灵动和柔软,产生了一种通俗与雅致并存的形式美感。
总之,《西南边》是一部具有内在思想深度和审美气质的佳作,不仅在语言上代表了四川彝族长篇小说的发展成就,更重要的是它在持守现实主义本位的同时将浪漫主义、新历史小说和寻根小说等文学思潮的精华融汇于一炉,创造性地将日常生活叙事与严肃历史主题以牵丝挂藤的方式巧妙勾连在一起,既在写实维度上破解了僵化的传统现实主义写法模式,又有效克服了新历史小说和寻根文学等的既有困境。这是《西南边》边地书写的要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