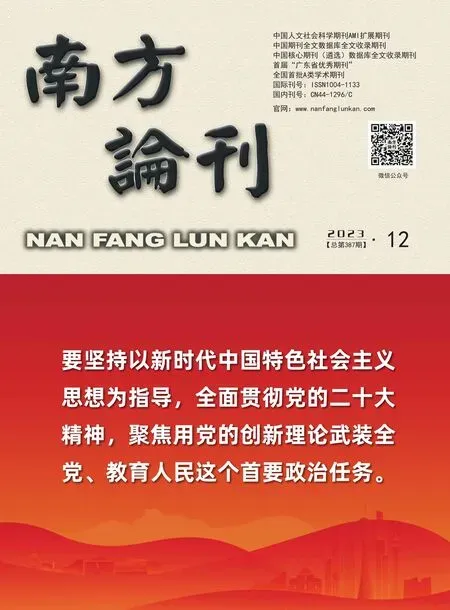城市化进程中宗族文化的复兴
——深圳大芬油画村的个案研究
2023-02-05黄壮钊
黄壮钊
(深圳大学 广东深圳 518060)
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的大芬村,以其油画产业闻名于世,有“中国油画第一村”和“世界艺术工厂”等美称,习惯上也称之为大芬油画村。随着油画产业的发展和知名度的提升,许多媒体纷纷对大芬油画村进行报道与宣传,不少学者也对大芬油画村的油画产业和文化产业展开研究。这些研究概述了大芬村油画产业的发展历程,讨论了2008 年金融危机后大芬油画产业所经历的从复制行画为主到逐渐增加原创的转型过程。[1][2][3]最近也有研究开始关注从事油画产业的画商和画工,讨论在产业升级和城中村改造背景下这些油画从业者的生活状态。[4]上述研究主要着眼于油画产业和从业者,而少有关注到油画产业的发展对大芬油画村及原居民的影响。本文将研究视角转移到大芬村的原居民,讨论油画产业在大芬油画村得到发展后,大芬村宗族文化的复兴和礼仪重建的过程,进而思考城市化进程中宗族文化复兴的意义。
一、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芬村
大芬村洪氏宗祠里挂着一张上世纪七十年代拍摄的村落景观照。照片里的大芬村建于低矮的山丘之下,村民居住在一栋栋白色的单层平房里,周边是种上庄稼的农田。可见,这时大芬村的原居民主要以务农为业。邬婆婆于1970 年20 岁的时候嫁入大芬村,她回忆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主要就是种田,同时还需要从事诸如砍柴、割草、养猪、养牛等农活(根据2020 和2021 年的田野考察和访谈记录,后续不再一一注明)。1989 年的“大芬村只有0.4 平方公里,随处可以看到芦苇丛,村里还有臭水沟,路是沙土路,一派荒芜景象,在我们的眼中,它是深圳的‘西伯利亚’。村里的交通工具还是三轮车,‘咯咯咯’地响,车一过,满街尘土飞扬。……全村只有300 多个人,基本是农民,每户一年的收入才几百块。最富裕的人家才有黑白电视机,而那时深圳关内已经很多人家买了彩电。”[5]P74可见那时的大芬村仅是一个山脚下的贫穷小乡村。
仅靠农业生产并不能让村民过上好日子,有时甚至难以保证温饱。60 多岁的邬先生说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村里有很多人去了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六七十年代则有很多人逃去香港。洪先生也从长辈那里听说,1979年村里大部分人都准备逃港,只不过估计只有20%的人最后成功逃港。1979 年前后的“逃港”风潮,在深圳地区具有普遍性[6][7],如1978 年到1980 年10 月宝安县万丰村“逃港”的村民多达1200 人。[8]P10
由于人口少,村里并没有学校,上学需到几公里外的布吉。布吉是附近的大墟镇,人口相比大芬村多许多。考虑到当时从大芬到布吉需要走一两公里的山路,上世纪八十年代,村里开办了小学,但只办了一年级和二年级,且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孩子们就得自己走路或者骑车到布吉上学。
村里没有神庙,邬婆婆介绍说如果要拜神,需要去布吉,一般是去布吉牛岭下的英福庵,或者布吉鸡公头的观音庙拜神。村里虽然没有神庙,却有三座祠堂,分别是洪氏、邬氏和刘氏宗祠。这些祠堂的始建年份不详。上世纪五十年代土改时,祠堂被分给了村民,用来存放干柴或草,当做仓库等用途。因此,之后围绕祠堂的祭祖和相关礼仪活动都停止了。遇到譬如结婚等喜事的时候,并不需要到祠堂拜祖。邬婆婆说1970 年她嫁到村里来的时候,遇到“破四旧”,所以当时的结婚仪式,既没有炮仗,也没有点香,“什么都没有”。所以当她回想结婚时的场景,还略感遗憾。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深圳的发展,八十年代有港商在大芬村的周边建了诸如五金厂、蛇皮袋厂等工厂,给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不过,对于地处二线关外的大芬村,村民依然主要以务农为生,摆脱不了贫穷与落后的印记。直到油画产业进入,才逐渐改变大芬村的面貌。
二、油画产业带来的发展机遇
油画产业能够落户大芬村,并最终发展壮大成“中国油画第一村”,背后有机缘巧合的因素,也得益于政府的支持与推动。
后来被誉为“大芬油画村第一人”的香港画商黄江,1987 年原本在罗湖和朋友合作办油画厂。之后黄江出来单干,看中了关外便宜的租金,而且请来的画工办居住证就可以来工作,而不需要费工夫办理边防证。黄江起初是在布吉附近的村子租房绘画,由于绘画导致环境脏乱,那里的村民不大乐意租房给他。后经人介绍,黄江来到大芬村。大芬村的原居民也不喜欢画工把房子弄脏,但由于大芬村更落后,出于经济考虑也就接受了。于是黄江带着20 多个徒弟来大芬村办画厂,从事行画(即临摹画)的生产,然后通过香港外销欧美国家。[5]P74从此,油画产业在大芬村落地生根,并逐渐发展壮大。
不过,直到1997 年画工基本上都是关起门来画画,没有开店,绘画完工后装上货柜车就直接运往香港。虽然那年大芬油画产值已经达到3000 万,但与国内市场几乎没有多少交集。[9]而且,“村民们自建的楼房很不规范,街巷之间被乱搭建堵成死胡同,街巷路面残破,垃圾随处可见,污水到处横流。”整体环境显得脏乱差。[10]P42因此,可以说此时的大芬村没有多少独特的环境和基础设施优势。这种状况,在政府的介入后得以改变。
从1997 年底开始,布吉镇政府开始注意到大芬村的油画产业,并将其与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结合起来,加以宣传报道。同时,区政府和镇政府也推出一系列政策,扶持大芬油画产业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进行环境改造。2001 年底,大芬第一期环境改造工程完成,并建成三层高共三十间油画门市和绘画工场,形成“油画一条街”,吸引了北京、上海等地的画商前来开店。大芬村的油画门店从20 多家增加到近百家,形成了一个产业链比较完整的交易市场。油画产业链的聚集产生了良好的规模效应,使得大芬油画村的名声越来越响,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商直接来大芬油画村采购。[10]P42-48、108-111
2003 年,深圳市政府确定“文化立市”的发展战略。[11]油画作为文化产业,契合了深圳市的发展战略,大芬油画村得以成为首届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分会场。趁此机会,政府对大芬村进行第二次环境改造。“政府对大芬村进行了专业规划设计,对沿街的画廊和民房外墙进行包装,对广场和道路进行了改造。后来又出资1000多万元,进行了空中电缆电线入地、肉菜市场迁移等工作,在肉菜市场的原址上建立了油画展厅。”政府还把村口子上的几栋旧房子拆除,建起了“黄江油画艺术广场”。[5]P80凡此种种,使得大芬村的面貌上了一个档次,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画商、画家和画工入驻。
2004 年,首届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正式举办,大芬油画村作为分会场举办书画作品联展。与此同时,大芬油画村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在文博会举办期间正式揭牌,为大芬村赢得了巨大的国内和国际声誉。[10]P139-141大芬美术产业协会也在文博会举办期间成立,黄江当选第一任会长。[5]P80-81此后,大芬油画产业不仅在生产方面有大的增长,相关的展示和交易的规模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2005 年大芬村集艺源油画城和“大芬卢浮宫”等展销中心相继开业,提供创作、展览、销售乃至拍卖和培训等服务。行画的繁荣,以及整个油画产业链的建设,带动了原创性油画的发展,越来越多原创画家入驻大芬,包括已经成名的,也包括科班出身的毕业生。[10]P186-189、199-2062005 年左右,大芬油画村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画家、画师、画工2500 多人,成立了700 多间油画创作工作室,书画、工艺等经营门店达到243 家。[12]
大芬油画村在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遭到重创。由于行画主要以外销为主,金融危机使得国外订单锐减,导致许多画廊倒闭,大量画工离开大芬村。为此,大芬的画商与画家们加大对国内市场的开发,同时也加速转向原创。金融危机结束后,大芬村的油画内销、线上电子商务以及原创油画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2015 年,大芬油画村的成交量已增长到43 亿元,是金融危机前的两三倍。[13][14]
油画产业持续发展的同时,越来越多画商、画家和画工入驻大芬油画村,成为大芬村的“特殊村民”。[15]2019 年,大芬油画村共有大小画廊及门店1200 多家,知名企业60 多家,聚集油画从业人员约8000 人。[16]这些外来“特殊村民”的数量,已远远超过原居民的数量。不仅如此,2007 年以来多数原居民陆续搬进大芬新村,留在油画村里的原居民就更少了。
油画产业的发展,让大芬的原居民享受到了发展红利。首先是租金方面的收益。原来大芬村地处偏僻,分田盖房后,新建的房子乏人问津。随着油画产业的落地,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涌进大芬村,使得原居民的房子实现了其经济价值。原居民户均两栋楼,多的有五六栋。这些楼房多数租给了外来的画工和画商。房租是原居民的主要收入,并随着房租的上涨而增加。[17]P312不仅如此,随着油画产业的发展,周边的土地得到开发,大芬村也跟深圳其他村子一样成立公司来管理集体产业,集体土地和建筑所带来的收益和每年的分红,也为原居民提供了一份稳定的收入。从此,大芬由原来贫穷的小乡村一跃成为富裕的城中村。
三、重修祠堂与礼仪重建
在大芬油画村的油画产业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地人口住进来的时候,洪氏跟邬氏在2003 年重修了各自的祠堂,而刘氏则没能重修旧祠。因为建国初分祠堂的时候,洪氏和邬氏宗祠都各自分给同姓族人,而刘氏宗祠则分给钟姓人家。2003 年洪氏和邬氏顺利拿回旧祠建筑进行重修,而刘氏则因为房屋归属谈不妥而没法重修。这也与洪氏与邬氏是村里大姓,而刘氏是小姓有关系。刘氏不少人外迁,留在村里的只有十户左右。[17]P330[18]刘氏人数虽少,但也尝试修建宗祠,显示了在华南地区流行的宗族文化也影响到这个小乡村。[19]
洪氏宗祠跟邬氏宗祠的始建年份不详,祠内未见相关文字记载,原居民也说不清楚,可能建成于晚清或民国时期。不过相比深圳别的乡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重修祠堂[8]P68[20],为什么洪氏跟邬氏直到2003 年才重修呢?在访谈中,可以隐约地从村民的口中了解到这跟当时把修建宗祠与封建迷信相联系起来的认识有关系。随着深圳乃至全国修建宗祠案例的增多,这种认识也就淡化了。当然,2003 年两座祠堂得以重修,跟当时政府对大芬村的环境进行改造的背景或许也有关系。因为破旧的祠堂面貌,显然跟不上当时村貌焕新的要求。因此不仅族人出资,村里也拨了钱用于重修祠堂。[17]P314-315
2003 年农历四月重修完成后,邬氏刻了一通《邬氏历代源流》石碑,镶嵌在祠堂的墙壁里。《邬氏历代源流》列述了从先秦时期一直到清朝约十位邬姓名人的事迹。不过碑文并没有讲这些名人是自己的祖先。可见邬氏不清楚祖先的确切历史,因此将历史上的邬姓名人刻在祠堂里,表明自己与这些人多少有些关系,毕竟都是同一个姓氏。在《邬氏历代源流》的一侧是《邬氏宗祠贤孙捐款名单》,记载出资修祠的族人姓名。
同一时间,2003 年重修祠堂后,洪氏只是在祠堂里刻了一通《洪氏宗祠贤孙捐款名单》的碑刻,将捐款一千至一万的族人姓名刻在上面。可能参考邬氏的做法,2015 年,洪氏刻了一通《洪氏源流志》。不过,跟《邬氏历代源流》相比,《洪氏源流志》不是简单地罗列洪氏名人传,而是在叙述洪氏起源与历代名人的基础上,讲述了洪氏入住大芬的经过:“溯自上祖念九郎,原居潮州府海阳,行公同母始移大浦银溪及改程梅州古足迹也,今大清雍正十年壬子,复改为名曰嘉应,因明末扰乱他房迁居者,未悉何方,远则有江西等处,近则有新安等处。我必颂祖带父骸骨移居新安布吉洞,土名唐径。乾隆年间东兰公移民大芬村也。”“移民”一词是现代用语,显然是大芬洪氏加进去的。这大概是在2003 年重修祠堂后,大芬洪氏跟周边的洪氏取得联系的结果。洪氏祠堂里悬挂的照片显示,2003 年10 月,大芬洪氏族人曾赴梅州石坑,跟当地的洪氏取得联系,并参观作为洪氏祖屋的梅魁第。跟洪氏一样,邬氏也积极地与其他地方的邬氏取得联系。邬氏宗祠里挂着几块外地邬氏所赠牌匾。2003 年秋天,河源市龙川县紫市的邬氏用“祖德流芬”的匾额来祝贺大芬邬氏宗祠的重修;肇庆市怀集县的邬氏则赠送了“源远流长”的匾额。
洪氏与邬氏在修祠之际,积极联系外地同姓宗亲,主要目的是寻找祖源,进而书写自身的历史。约2009 年的采访记录表明,当时受访的邬先生只能大概地说“相传最早到深圳大芬村定居的是来自河南颍川郡(今河南省许昌市)的邬氏宗亲的一支,而在这之后,洪氏宗族的一支也来到大芬村附近定居。”[17]P315上述定居史没讲明确的时间。当2020 年笔者到大芬访问原居民时,受访者则说出大概的时间。60 多岁的邬先生带着不确定的口吻说:“总之一句话就是说,客家人就出现过大迁移,我们是中原来的,中原人就是呢,从河南(来的),迁到哪里,再迁到这里就找不到啦。迁到这里起码超过三百年。”这些认识,大概是他看了别的地方的族谱中所述客家人的来源,或所了解到的客家人来源,然后当做对自身的理解。2021 年,官方媒体到大芬油画村采访时,原居民讲述了这样一个版本:“清朝初年,河源龙川一群邬氏族人自龙川一路南迁,至大芬后停驻而居;时隔不久,广东嘉应州(今梅县)刘氏族人迁入;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嘉应州石坑堡洪氏族人亦成群迁至大芬。”[21]这里将大芬三个姓氏的入住时间与迁徙路线基本明确化,成为了现在对外宣传的官方版本。
祠堂重修后,几十年没有进行的宗族礼仪得以重建起来。现在正月初二、元宵节、除夕等节日,洪氏跟邬氏族人会在各自的宗祠集合拜祖。其中元宵节还会把上一年出生的男丁的名字记录到祠堂里。平时有结婚喜事,也会到祠堂拜祖。2020 年10 月我们到村里时,邬氏宗祠贴着新的对联:“今日完婚歌祖德,他年麟趾庆宗灯”,横批是“邬刘联婚”。后来通过采访知道有邬姓青年结婚,并在当天早上开祠堂拜祖。
2021 年2 月的除夕跟元宵节,笔者都曾到现场观察洪、邬二姓的祭祖活动。以洪氏为例,除夕的祭祖活动在当天下午1 点左右开始,三四十位洪氏族人聚集到洪氏宗祠祭祖。这些族人绝大多数是成年男性,还有三五位十岁左右的少年,同时也有一位年轻女子。他们先烧香祭祖,然后到祠堂外烧纸钱,之后燃烧炮竹。打完炮竹,洪氏在祠堂外放了一张桌子,把拜祭所用的烧猪放桌子上进行切分,然后族人就在桌子周围吃烧猪肉。大概下午两点半,族人陆续离开,祠堂门也关上,祭祖活动到此结束。
从烧香拜祭到分食猪肉,族人之间相互寒暄,彼此交谈。祭祖活动无疑有利于增强族人间的凝聚力。不仅如此,洪氏与邬氏聚集在一起,在宗祠里进行祭祖活动,住在油画村里的多数外来人也是知道的,有些还在祠堂外观看。只不过,虽然他们是住在村里的大多数,但在洪氏跟邬氏族人聚在宗祠外吃烧猪的时刻,我们才能明显看得出谁是原居民,谁是外来者。而在平时,村里从事油画职业的外来者并不能区分谁是原居民,他们很多时候唯一认识的原居民就是自己的房东。所以,对于现在已经基本上都从油画村里搬出,迁居到大芬新村居住的洪氏与邬氏来说,祠堂的重修与宗族礼仪的展演,是他们在通过宗族文化来宣示主权,彰显自己原居民的地位。
四、结语
从大芬油画村的案例来看,宗族文化的复兴,其中一大因素就是经济的发展。正是由于油画产业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收益,才使得村民有资金来重修旧祠堂,并复兴宗族文化。重修祠堂并重建宗族礼仪,既彰显了洪氏和邬氏在村里诸姓当中的地位,同时也向居住在油画村里的租客们展现了自己的主人翁地位。不仅如此,他们也将自己和几百年来的宗族传统联系到一起,展现自身的“悠久历史”,从而在现代语境中宣告自己文化的传统性,并最终重新书写了乡村的历史叙述。这就是在城中村复兴宗族文化的重要意义。上述大芬宗族文化的复兴过程,在其他城中村也能观察到类似的做法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