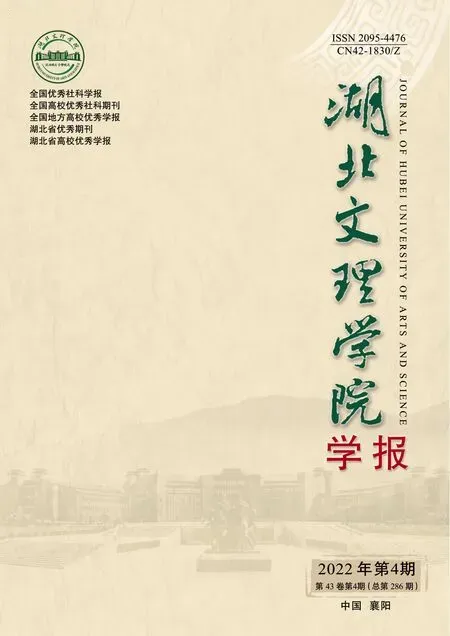从《汉宫秋》的文学改造看宋元易代时期的文人精神
2023-01-05江洁
江 洁
(天津外国语大学 国际传媒学院,天津 300204)
《汉宫秋》是马致远在昭君远赴匈奴和亲这一史实基础上改编而成的元代杂剧作品,该剧以汉元帝、王昭君的恋情故事为主线,主要写昭君拒赂画工受到中大夫毛延寿阻挠,不得相见元帝,后来因夜晚弹奏琵琶曲无意间得见元帝,二人相识、相恋,然而在胡强汉弱的背景下,却难以相守,昭君赴匈奴和亲,最后行在汉匈交界之处时,以身投黑江而死,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动人悲剧, 被焦循称为“绝调”。他在《剧说》中给予了《汉宫秋》一剧高度的评价,认同《元曲选》将其列为第一的编排,认为“良非虚美”。
一、昭君故事的历史记载及文学改造
在史传之中,有关昭君故事的记载大都比较简略,其中正史有《汉书》和《后汉书》,野史可参考的有晋代葛洪的《西京杂记》。在班固《汉书》中,关于昭君的记载主要集中在《汉书·元帝纪》和《汉书·匈奴传》之中。根据《汉书·元帝纪》中记:
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赐单于待诏披庭王樯为阏氏。[1]297
《汉书·匈奴传》则记载:
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1]3803
除此之外,《汉书·匈奴传》中还交代了昭君的结局:
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呼韩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呼韩邪死,雕陶莫皋立,为复株累若鞮单于。……复株累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1]3806-3807
在南朝范晔编撰的《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中,昭君故事有了进一步的具体和丰富:
昭君字嫱,南郡人也。……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2]
东晋葛洪则在《西京杂记》中记录了《画工弃市》一篇,《画工弃市》新增添了宫人贿赂画工的情节和毛延寿的人物形象:
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帝悔之……乃穷案其事,皆弃市。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宽……人形好丑,不逮延寿,……同日弃市。京师画工,于是差稀。[3]
对比《汉宫秋》与历史本事中的昭君故事,可以看出,较之历史,其文学改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其一,在故事背景上,《汉宫秋》改变了汉朝与匈奴的力量对比,变历史上“汉强胡弱”为剧中“胡强汉弱”,昭君和番这一事件也由汉王朝主动地展现包容友好的态度、保持两国和平关系转变为保全、挽救汉王朝基业的被迫之举。其二,在情节上,《汉宫秋》较历史本事增添了汉元帝遍行天下选女充盈后宫、毛延寿为呼韩邪单于献美人图、元帝昭君二人难舍难分、元帝深宫追思爱人等情节。其三,在人物形象上,《汉宫秋》改编了昭君的出身、地位、结局;以末本戏将元帝作为主人公,用大量的唱词细腻、真实地表现了汉元帝复杂、矛盾的心理,细化了汉元帝的人物形象;将毛延寿由无足轻重的画师变为中大夫,并以受贿刷选室女、献图单于等典型事件突出人物形象。其四,在人物关系上,《汉宫秋》着重突出了汉元帝与王昭君帝妃之间的恩爱情深;将王昭君命运与毛延寿一系列行为紧密关联,增强了二人的矛盾冲突。
昭君和亲从历史史实成为文学母题进行创作,在《汉宫秋》前就已经多有。《汉宫秋》在历史本事的基础上进行了与众不同的生发改造,在众多文学作品中脱颖而出,显示出别样的艺术风貌。而作家作为创作者生活在特定的时代,在作品改编重构的过程中,自然不可避免地展现出特定时代中社会的风貌和人的情绪心态,折射出宋元易代这一特殊时期文人的思想精神。
二、艰辛生活下敏锐的现实关照和大胆的批判精神
《汉宫秋》虽然将故事背景置于汉元帝时期,然而根据《汉书》真实的历史记载,剧作中“胡强汉弱”的故事背景并不符合历史真实,其实际正是对现实中蒙古族在华夏大地上建立强大政权的曲折反映。楔子中,呼韩邪单于一出场便迫不及待展示匈奴的强盛国势,夸耀其强大的军事实力能够“久居朔漠,独霸北方”,并且“有控弦甲士百万”。随后更是历数与前代和亲之事,“至惠帝、吕后以来,每代必循故事,以宗女归俺番家”,似乎在汉匈之争中汉朝孱弱由来已久。然而,在历史上,西汉初期“胡强汉弱”的局面在汉武帝时期发生了重大改变,武帝时期集结全国之力力抗匈奴,在汉朝将领卫青、霍去病的大规模出击下,再加上匈奴自己复杂的内部矛盾,到了元帝时期,匈奴的实力已无法与汉前期相提并论。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呼韩邪单于上书汉元帝“自言愿婚汉氏以自亲”,其行为中有臣服示好的意味,元帝于是才“赐单于待诏披庭王嫱为阏氏”。可见,《汉书》中王嫱和亲的目的更多是表明汉王朝对匈奴由军事斗争到和平共处的意愿,是汉王朝表现出的对于匈奴包容、友好、安抚的态度。此外,昭君本人也并非单于口中的“宗女”,而只是“待诏”。在这里,和亲政策某种程度上正是汉王朝强大实力的彰显。《汉宫秋》中一改“汉强弱胡”的背景,把昭君和番与江山社稷存亡紧密地关联起来,汉王朝处于“兵甲不利,又无猛将”的弱势地位,要用堂堂后妃“割恩与他”达成交换,才能“救一国生灵之命”,这种文学演绎不仅仅是为了在创作上加剧情节的矛盾冲突,同时也是为了展现元代蒙古族统治的背景下文人的生活状态和内心世界。
在元代,延续了多年的科举制度的突然改变给元初文人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蒙古族入主中华之后,汉人受到歧视、压迫、残害,华夏文明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千年来积累的民族优越感、自豪感荡然无存,元代初前八十年更是基本停止了科举考试,其后虽然重修科举,但是森严的等级制度和无理的民族歧视无处不在,这在诸如《选举志》“试蒙古生之法宜从宽,色目生宜稍加密,汉人生则全”的记载中可以充分得到见证。此时,文人在隋唐以来一贯形成的“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人生规划成为过往,残酷的现实断绝了进阶仕途的道路,他们失去的不仅是参与政治决策、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更现实的困境是,古代文人向来以读书为业,并无治理生产生活的经验和能力,一旦不能从读书中获得经济回报,就只能陷入生活贫困。然而,文人在长期儒家精神文化浸润下所养成的心忧万民、胸怀天下的道德原则,“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士人气节,“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进取精神,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早已植根于他们心中,在血液里流淌,给予了宋元易代时期文人保持自我操守的勇气、关注现实的社会责任感、参与感和嫉恶如仇的批判精神。
《汉宫秋》中昭君贫苦的家庭生活、出生时母亲不凡的梦境、坎坷的面君经历、不俗的才貌,造就了她一定的文人自我形象的象征意义。她出生在以“务农为业”的家庭,“家贫无凑”,出生时却有奇异之象,母亲“梦月光入怀”。“月光入怀”的梦境为昭君形象增添了纯洁、美好和神秘色彩,她受阻于毛延寿的小人行径,不得面见君主,却以超凡脱俗的容貌、高雅的琵琶曲打动元帝之心,成为御口亲封的明妃。这样的昭君形象,反映出文人创作中不可避免的“自叙传”色彩,折射出元初文人对自身艰难生存状态的真实感受。一方面,他们所认可的自身的才华和能力、对于实现自我价值的高度期许,在与残酷现实的交锋中屡屡受挫,带来了无尽的痛苦经历和苦闷情绪;另一方面,即使如此,他们也没有在复杂浑浊的世事中受到污染,或因迫害而折中妥协,以察察之身受汶汶之物,仍旧以自身强大的勇气和毅力坚持内心的道德律。昭君的经历是宋元易代时期文人生活的缩影,出生时“月光入怀”、不赂画工的纯美昭君形象更是易代文人的精神榜样和自我象征。
《汉宫秋》借用的是汉朝昭君和亲之事,真正写的却是元代社会现实生活,抒发文人胸中块垒。也正因如此,剧中大胆的批判精神显得更为可贵。汉元帝、毛延寿等人物形象在《汉宫秋》中都有了艺术性的再创造,作品对历史的反思深度和现实的批判力度均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
《汉宫秋》将矛头直指统治者和上层官吏,对于统治高层的贪图享乐、尸位素餐、懦弱无能有着清醒的认识、无情的揭露、辛辣的嘲讽,剧作对汉元帝和毛延寿形象的文学改造于此有充分体现。在作品中,元帝作为统治者,一方面,对国家局势缺乏起码的敏锐度和判断能力,认为“四海晏然,八方宁静”,同时,对于朝廷文武官员能力也没有基本认识,无识人、选贤之明,认为四海升平“皆赖众文武扶持”“忠臣皆有用,高枕已无忧”;另一方面,元帝耽于享乐,一味沉溺于“边塞久盟和议策,从今高枕已无忧”的满足之中沾沾自喜,对于匈奴虎视眈眈的危机局面也视若无睹,听信毛延寿之言遍行天下刷选秀女,“按图临幸”。宠爱王昭君后更是“如痴如醉,久不临朝”,因个人情爱而误社稷家国。除此之外,剧作创造性地增添了元帝被迫同意昭君和番的情节。他不但受到匈奴的威逼,甚至还受到群臣的“胁迫”,“都是些畏刀避箭的,恁不去出力,怎生教娘娘和番?”的话几乎是哀求式地控诉,最后不得不同意“先送明妃到驿中,交付番使”,自己“亲出灞陵桥,送饯一杯去”,即使做出妥协让步,还要受到臣子的阻拦,直到说出“卿等所言,我都依着。我的意思,如何不依?”这样的话才勉强得以送行,连元帝自己也感叹“我那里是大汉皇帝!”在这里,元帝面对外敌几乎是陷入束手无策、孤立无援的境地,他既无坚定的意见,也毫无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将社稷江山寄希望于贤臣名将,实在无计可施之时不得不以爱妻嫁与他人换取暂时的和平,他的“不自由”固然包含有作者的同情,却也不能掩盖作品中对汉元帝鲜明的批评态度。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汉宫秋》真正把作为君主的汉元帝请下了神坛,他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帝王,而是有着世俗缺点的平凡人物,这样的认识和批评是胆大而深刻的。剧作中元帝形象凝聚着文人批评和同情的复杂情感,借论古人古事实际包含着无尽的现实兴亡感叹,明确统治者对于国破负有责任,在深切反思中抒发了同情、追忆的情绪。
毛延寿在葛洪的《西京杂记》中是以画师身份出现的,他“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并且为同行所“不逮”,可见技艺颇高。在《画工弃市》中,他与宫人贿赂画工一事并无关系,也并非昭君不得面君的始作俑者。《汉宫秋》深化了这一人物形象,增加了他贪图贿赂点破美人图导致昭君不能面君的情节,又写是他献图呼韩邪单于,才导致昭君被迫和番,将其所做作为与昭君的悲剧命运紧密联系。他深谙官场规则、谄媚奸诈,“哄的皇帝老头儿十分欢喜,言听计从”,同时贪贿弄权,鲜廉寡耻,“生前只要有钱财,死后那管人唾骂”,一旦事发,便逃之夭夭,卖国求荣。毛延寿的身份在《汉宫秋》中由画工上升至“中大夫”,这样一来,毛延寿就成为处于政权高层官员的代表,对于他的刻画,就不再仅仅是对于画工受贿现象的揭露和昭君不得面君原因的解释,而是刻画了整个只为谋求个人私利、致国家利益于不顾的朝廷官员群体,而他与昭君的关系则更有忠奸对立斗争的意味,很容易将昭君不得见君的命运与忠臣能士受阻于奸臣弄权联系起来,在宋元易代的背景之下,反映出元代文人大胆的批判精神。
三、精神苦痛中强烈的民族意识和高扬的主体精神
异族的统治给宋元易代时期的文人不仅带来了物质生活上的贫困,而且给他们带来了更为沉重的精神痛苦。儒生被彻底排除在统治集团之外,使得他们一直以来追求的修齐治平的理想完全幻灭,高度的自我期待和无情的现实形成鲜明的对比;此外,在统治阶级所推行的民族歧视政策之下,儒生社会地位一落千丈,陷入“十儒九丐”的社会底层,成为“穷酸秀才”,这种“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的人格侮辱也令一向强调自尊自重的知识分子难以接受,正是由于元初文人对于社会黑暗、人情冷暖有着充分、深刻的体会,在作品中,往往表现出对美好事物向往、依恋、追思的怀旧心理。《汉宫秋》对于这对“所事儿相投”“五百载该拨下的配偶”帝妃的恩爱情深给予了细致动人的描摹,有研究者认为昭君的形象在剧中是人间的一切可拥有的美好的象征;[4]然而,美好事物终将逝去、不可追寻的苦闷又加剧了元初文人对于自我命运难以把握的浓重悲哀,这种无可奈何的心理和悲哀感伤的情绪充分表现在《汉宫秋》之中,作品加入元帝被迫同意昭君和亲的情节,又在第四折写元帝深夜独对孤月寒灯,睹物思人,悲情无限,渲染了浓重的悲剧氛围。袁行霈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认为:“环绕着汉元帝、王昭君的形象,他向人们揭示的,主要是对历史、对人生的体悟。他通过戏剧冲突,抒发自己无法主宰命运、只能任由播弄的悲哀。”[5]
然而,追忆美好的怀旧心理与无可奈何的命运之感并没有使元初文人的精神消沉下去,剧作在历史本事的基础上进行文学改造,不是局限在男女恋情的恩爱缠绵之中,一味抒发爱人之间离别的痛苦感伤,而是对历史上的昭君和番故事进行全面改写,昭君在社稷危急存亡之时顾全大局、挺身而出、舍己为国,慨然赴死,改造之后无私无畏的昭君形象充分反映出易代文人思想中强烈的民族意识和主体精神。正如孟称舜编《古今名剧合选·酹江集》中评说第三折:“全折俱极悲壮,不似喁喁小窗前语也。”
首先,在昭君和亲的原因上,《汉宫秋》将“为个人之怨”变为“为国为民之愿”。在历史上,昭君“求行”的原因是“入宫数岁,不得见御”,于是“积悲怨”,这里的悲怨,只是由于对自身处境不满而产生的个人情绪,昭君的求行,也只是为自身求取改变现状的机会。然而在《汉宫秋》中,在匈奴强于汉王朝的局势下,昭君主动地“求行”,是在忍受了与元帝难舍难分的夫妻之情的剧烈痛苦下做出的选择,昭君和番是为得息刀兵、国家安定,不惜抛却闱房之情的大义之举,昭君身上体现出的是拯救国家、民族、人民的自我奉献和自我牺牲精神。其次,在昭君和亲的结局上,《汉宫秋》也重新书写了其历史结局。剧作没有采用《汉书·匈奴传》中“生一男伊屠智牙师……呼韩邪死,……复株累单于复妻王昭君”的结局,也没有采用《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中“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的记载,而是写昭君“不肯入番,投江而死”。昭君在剧中有着鲜明的家国观念和民族意识,正如她自己所说,她和番是为“得息刀兵”“国家大计”,她离开汉土,唯一要求是“把我汉家衣服都留下者”,并早就抱着“蒙陛下厚恩,当效一死”的准备,最终在番汉交界的黑江投江而死。
此外,剧作还赋予了昭君鲜明的主体意识,与元帝的优柔寡断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在剧中,面对元帝与大臣的争执,她以国家为重,不惜“当效一死”,忍痛主动提出“情愿和番,得息刀兵”,在黑江水畔,她假说“借一杯酒望南浇奠,辞了汉字”,借机投江而死,可以看出早就做了以死全节的准备。她不再是历史上遵照朝廷命令嫁入匈奴的王昭君,也不再是历史上上书元帝请求归汉的王昭君,她和亲匈奴、投江赴死都是深思熟虑后主动的选择,这选择从人物所处客观环境、个人命运的角度看纵然有无可奈何的成分,但毫无疑问,真正支持昭君之愿的是家国之情、民族之义,是为国家计、为百姓计。昭君形象由“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的小儿女变为忠诚贞一、大义凛然的女英雄,反映出宋元易代时期文人的内心精神世界,忠于国家、忠于爱情,不事二君、不事二夫的昭君精神正是植根于他们思想深处的理想人格和不懈的精神追求。
法国批评家丹纳说:“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作为元初杂剧的代表作,《汉宫秋》以元帝与昭君的爱情为主线,细致地展现了美好事物艰难产生、逐步发展到最终消亡的全部过程,在这出淋漓尽致的爱情悲剧中,表现出元初文人在政策压迫、文化冲击下艰难的物质生活和在无法言说的精神痛苦下困惑、迷惘、幻灭的心态,以及对未来难以把握、无可奈何、进退失据的命运之惑。但同时也应当看到,这一时期的文人精神并未泯灭在现实的困顿中。艰辛生活下,他们仍具有敏锐的现实关照和大胆的批判精神,在精神苦痛中依旧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高扬的主体精神,即使处于社会底层,前途未卜,他们内心深处仍然没有放弃政治热情和关注现实的社会责任感,没有放弃民族大义和人格追求。这种精神闪烁着动人的光辉,历久弥新,也为《汉宫秋》在众多杂剧之中增添了与众不同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