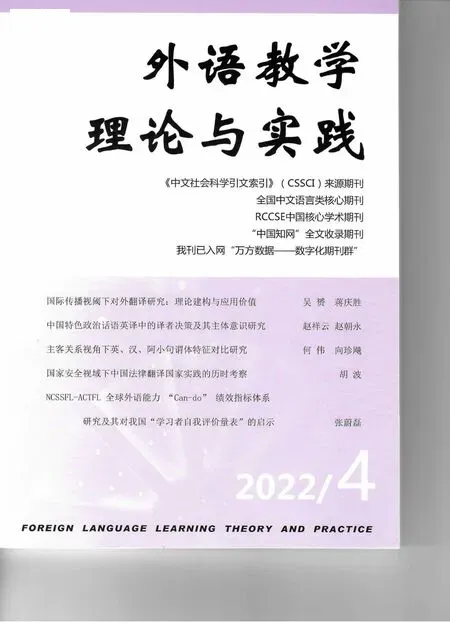江西诗法与文言翻译*
2023-01-05钟锦
钟 锦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提 要: 使用白话的诗歌翻译不断趋于成熟后,自身提出了更为严格的美学和格律要求,因此陷入传达的困难。无论是美感上的缺憾,还是格律上的制约,使用文言的翻译都可能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发。使用文言的诗歌翻译特别依赖文言诗歌自身的法则。江西诗法代表了旧体诗某些共有的法则,本文通过对其法则及在翻译中具体运用的论述,力图揭示其中蕴含的翻译学意义。以期有助于中国翻译学的建构,同时影响到翻译实践。
我国的翻译文学在新文化运动前后有着本质性的转变。从文体来说,文言向白话转变;从译法来说,意译向直译转变。两个转变之间是有联系的,这个事实让新文化运动之后的论者,轻率地将意译和文言、直译和白话笼统联系起来,同时使两组概念形成对立,从而将文言和意译看作翻译史上一个逐渐被超越的历史性过程。即使承认文言书写自身的辉煌成就,也仍然把文言翻译(本文特指用汉语文言进行的翻译)视作不完善的产物。在文言翻译里,诗歌除了表意的艰难,还增加了格律的束缚,就比散文具有更高的难度,因此更不容易取得成功。林纾和严复一直被看作文言散文翻译的代表性人物,而苏曼殊是公认的文言诗歌翻译的旗帜,但在翻译成就上,苏曼殊却很难和林、严比肩。随着白话文的不断成熟,以及它显示出来的对译写对象的强大适应能力,我们看到白话诗歌不仅在内容上能够完成直译要求,甚至在形式上也不难对应源语言的格律。这就使得文言诗歌翻译遭受的负面评价,更多也更严厉。郭延礼先生的说法,代表了一种普遍态度:“翻译外国诗歌用中国古典诗体,又用文言,很难成功”(郭延礼,2005: 101)。
同时面对异域文学输入的迫切需求和白话文运动的强劲势头,文言诗歌翻译似乎也没有做太多的努力。除了苏曼殊的译诗取得一定影响,几乎再没有重要的译者,马君武只能勉强算一个。笔者主持“中国旧体译诗文献纂集与研究”,经过爬梳文献,搜集到1949年之前合格的旧体译诗,尚不足15万字,可见惨淡。旧体诗翻译虽说一直不绝如缕,但总显得像过时的古董,只供小众消遣,没有实际的用途。然而经历了百年的翻译实践,我们今日的优势允许我们在历史的经验面前做从容、冷静的反思,既可以避免仓促地译写,也能够冷静地分析文言翻译的特长,从而为翻译学提供有益的经验。虽然文言和白话都是中文,但文体的背景、法则还是有着较大的差异,直接互相搬用显然并不现实。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之前有较为客观的认识,以待翻译家慢慢从中汲取有用的东西。
一、 诗歌翻译中白话和文言各自的优长和缺陷
用文言进行诗歌翻译,引起我们的重新重视,出乎意料的竟是因为白话诗歌翻译不断地趋向成熟反而陷入困境之中。困境首先表现在,译诗很难媲美源语言的美感,始终无法摆脱作为媒介的功能,成为独立的文学本体。这自然是白话日趋成熟后给自己树立了更高的标杆,但却使我们反思到文言诗歌翻译通过“雅”的原则,一直在争取独立文学本体的位置。我们甚至忽略了,其“信”恰是通过“雅”的原则在更深刻的美学意义上体现出来。思考旧体诗翻译在这方面的成就和潜力,实际出于白话译诗内在的要求。
其次,白话在形式上对应源语言的格律,也并非如期待的一样顺利,要求越高越觉得捉襟见肘。先说押韵。人类的诗歌多数是需要押韵的,尽管用韵方式有很多花样,但对于汉语白话诗来说,似乎由押韵走向不押韵成了趋势,而这个趋势也影响了译诗。白话词汇本身不够丰富,是造成押韵困难的直接原因。林语堂译《鲁拜集》第十五首,只是简单的四行诗,押三个韵。头两句:“And those who husbanded the Golden grain, /And those who flung it to the winds like Rain,”译作:“无论是那些守财如命吝啬的老太太, /或者是那些挥金似土慷慨的少奶奶”(林语堂,1926),为押韵凭添出“老太太”、“少奶奶”,真是让人瞠目结舌,即使旧体诗中也少见如此离谱的过度意译。像余光中这样特别讲究格律的译者,也因“跌跤重伤住院”,“出院后回家静养,不堪久坐用脑之重负,在遇见格律诗之韵尾有abab组合时,只能照顾到其bb之呼应,而置aa于不顾”(余光中,2019: 5)。放弃原作的押韵方式虽是无奈之举,也从侧面说明了白话诗押韵的困难。从这一点可见出旧体诗的优长,在旧体译者那里因为韵脚而窘迫的情况并不常见。同时,语汇结构差异造成源语言和目的语格律上的不协调,强以汉语的顿去符合源语言的音步,也使忠实传达原意陷入困难。黄杲炘先生坚持“以步代顿”,以每行12字5顿的格律,对译英文抑扬格五音步。但他自己翻译《鲁拜集》中最著名的第十二首,第一句:“A Book of Verses underneath the Bough,”受到格律的限制,加上中英文语汇结构不对等,译作:“开花结果的树枝下,一卷诗抄”(黄杲炘,1998: 25),增添了原文没有的“开花结果”。这些限制都使白话译诗陷入文言译诗类似的困难,被迫在不知不觉中使用一样的翻译策略。
但长期形成的偏见,使我们并未认真思考白话的缺陷和文言的特长,文言和白话翻译之间可能的互补长期处在翻译学的视野之外。
中国的文言从口语脱离,逐步形成自身的法则,这些法则带来了极强的秩序性,并且形成近于封闭的审美程式。法则和程式根基于对古典的追摹,从而保持与日常世俗的疏离,因此进行日常书写已经变得困难。一旦面对异域语言的翻译,又增加了和异域文化、语汇的疏离,书写困难更为严重,也就很难采取精确的直译方法了。为适应其审美程式的过度意译,往往会产生语言文化间的冲突。在佛典翻译时期,文言程式尚在建构之中,冲突显得缓和得多。但是,佛典翻译的语言始终和正统文言保持距离,形成一种独特的语言格调。这在文言程式建构完成之后,大概是很难想像的了。到了西学东渐时期,文言早已形成严格的程式,而所面临的西方文化也更为异质,距离世俗也更近,冲突逐渐激化起来,最终加速了文言被白话取代。但是文言的特长,恰是以法则的秩序性建构出严格的审美程式,从而成就一种“古雅”的美感。尽管程式的固化很容易扼杀天才的创造力,但如王国维所指出,“古雅之能力能由修养得之,故可为美育普及之津梁”(王国维,1996: 623)。长期处于“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明史·李梦阳传》)的熏染下,天才的创造也必须被这些程式所轨约。程式固化的体现,就是桐城文法和江西诗法,分别归纳了古文程式和旧体诗程式的“共法”。(1)关于桐城文法和文言翻译的论述,参看拙文《桐城文法与文言翻译》,见《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五十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尽管其极端的封闭性引起了很多批评,我们却不得不承认,唐宋以下几乎很难再被突破。而旧体诗的程式,显得更为严酷。
刘大櫆在《论文杂记》里强调了文法和诗法的不同,他说:“昔人谓‘杜诗韩文无一字无来历’。来历者,凡用一字二字,必有所本也,非直用其语也。况诗与古文不同,诗可用成语,古文则必不可用。故杜诗多用古人句,而韩于经史诸子之文,只用一字,或用两字而止。若直用四字,知为后人之文矣”(刘大櫆等,1998: 11)。同是根基于对古典的追摹,文法仅仅要求用字有所本,也就是说,必须使用大家所共同遵循的典范书面语,但并不主张直接使用现成语句,否则即违反了古文的大忌——“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所谓只用一二字而止,不得直用四字,就是这个道理。诗法却不一样,可以直接使用现成语句。为什么呢?因为诗歌讲究押韵和对仗。对仗需要两个句子,押韵需要两个以上的句子,如果这些句子都是现成语句,必然是不一致的,倘使它们之间产生出一致性,或是由统一的韵脚,或是由对仗的牵制,就造成一种类似惊异的美感。(2)这是康德讲过的美学原则:“当我们发现两个或多个异质的经验性自然规律,在一个将它们两者都包括起来的原则之下,具有某种一致性;这就成为一种十分明显的愉快的根据,甚至往往是一种惊奇的根据,这种惊奇乃至当我们对它的对象已经充分熟悉了时也不会停止”([德] 康德,2002: 22)。钱钟书从对仗角度讲了这个道理,他说:“律体之有对仗,乃撮合语言,配成眷属。愈能使不类为类,愈见诗人心手之妙。譬如秦晋世寻干戈,竟结婚姻;胡越天限南北,可为肝胆”(钱钟书,2007: 477-478)。如此,诗法和文法之间就有了不同,诗可以使用成语。在翻译中,诗法自然比文法显得更困难: 找到合适的成语表达出原意已是不易,还得直接使用现成语句,还要受制于押韵和对仗,无疑比古文的要求更高。因此,文言诗歌翻译很少采用格律严密的近体诗,多数是要求相对宽松的古体诗,这样就回避掉了平仄、对仗的麻烦,仅需在押韵的制约下遵守一般古文的用词规范。
大致了解了诗歌翻译中文言和白话各自的优长和缺陷,我们就江西诗法具体来看文言诗歌翻译的方法及其独特的美感。
二、 江西诗法基本原则在译诗中的运用
相对于桐城文法明确而系统的论述,江西诗法显得既含混又片段,但结合上述文法和诗法的差异性论述,仍然可能对江西诗法赋予旧体诗的法则有所认识。这里将结合具体的文言译诗,看看那些法则如何在译诗中运用。
我们先看最基本的原则,这以黄庭坚的一个著名论点为核心,就是所谓的“点铁成金”:“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答洪驹父书》)(黄庭坚,2001: 475)。首先我们需要了解,黄庭坚将这个方法上溯到杜甫和韩愈,事实未必如此,道理仍可一说。在文言程式完成的过程中,杜甫和韩愈无疑占据重要的位置,尽管他们不过是暗合程式,但在后来有意建立程式的黄庭坚眼里彼此并无二致。因此,黄庭坚的“点铁成金”其实是为诗的写作建立一个程式化的规范,强调利用古典学养灵活地袭取古人的现成字面,造成一种古雅的美感。这与借用典故的内在含义帮助我们进行凝炼地表达,实为不同的方法。看一下黄庭坚自己的例子,《寄黄几复》的第一句“我居北海君南海”,是他挺得意的句子。什么意思呢?任渊的注释说:“山谷尝有跋云: 几复在广州四会,予在德州德平镇,皆海滨也”(任渊,2003: 42)。不过是说我住在北方的海滨你住在南方的海滨,这么干巴巴的句子有什么好呢?好就好在“用经语”,用了经书上的语言——《左传·僖公四年》:“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这是大家通用的规范用语,典雅气派。可以说,黄庭坚的初衷,仅仅是把大家已经习惯的文言程式明白揭示出来,杜甫和韩愈作为诗歌、散文的代表,就自然地被他推向了前台。
这个写作程式到了翻译时,也不见丝毫改变。较早期的文言译者董恂,在译朗费罗《人生颂》的一句“Still, like muffled drums, are beat”时,直接用上了古典字面“一从薤露歌声起”(方浚师《蕉轩随录》卷十二),据《乐府诗集》引崔豹《古今注》:“《薤露》、《蒿里》,泣丧歌也”(郭茂倩,1998: 396)。丧鼓声换成了丧歌声,这在文言诗歌的语境里,就像黄庭坚自己的话换了经语一样平常。苏曼殊作为文言诗歌翻译最出名的人物,尽管旧学根柢并不扎实,但用旧体诗翻译时十分自觉地运用这个程式,并虚心向章太炎、黄侃等精通古文辞的大师请教。比如最著名的拜伦《哀希腊》,据说经过章、黄之一的润色,通篇类似的处理非常多。这里只举第一节:
巍巍希腊都,生长奢浮好。情文何斐亹,荼辐思灵保。征伐和亲策,陵夷不自葆。长夏尚滔滔,颓阳照空岛(苏曼殊,1933: 1)。
由于异域人名太多,希腊、奢浮(Sappho)、荼辐(Dolos),这些无疑使得文言语境过度异化,所以“Phoebus”就不再音译,把《楚辞·九歌》的《少司命》里“思灵保兮贤姱”那指称神巫的“灵保”用上了。大概因为福玻斯是神使,为神和人之间的沟通者,巫的角色与之类似。同时,福玻斯传说也掌管诗歌和音乐,“rose”和“sprung”译作“情文何斐亹”,虽然稍嫌不合,大体意思还是准确的。“斐亹”一词来自唐宋人用词恪守的经典《文选》,所谓“《文选》烂,秀才半”(陆游《老学庵笔记》),其选文中孙绰《游天台山赋》:“彤云斐亹以翼櫺。”李善注:“斐亹,文貌。”同时的旧体诗译者甚至经常直接使用古典成句,(3)参看汪莹、张子璇《异质的“归化”: 评莪默绝句百衲集的集句译诗策略》,《中国韵文学刊》,第32卷第2期。绝对不是在翻译里宽容剽窃,而是遵循着同样的写作程式。
“点铁成金”的方法还带来一种特别的美感,黄庭坚或许始料不及,但他确实有所体会。当古人的成句在与古人并不一致的意思来使用时,两种不一致的东西就通过相同的语词被置于一种一致之中,这样的一致性会使人不期而然地获得一种类似惊奇的美感。其实,这是审美里经常发生的经验,我们在前面讲诗法因押韵、对仗的需要允许使用成句时,也提到这一相同审美经验的不同体现。(4)前面的注释里也引述了康德表述的这个审美经验的原理,只是很多学者似乎并不理解。牟宗三就认为这个原理只“切合于‘目的论的判断’,而在这原则下所观的自然正是牧师传道之所赞美者,而这所赞美的世界之美好不必是‘审美判断’所品题之‘美’,而快乐之情亦不必是审美判断中之‘愉悦’”,因此以这种情况作为美感的依据,“正是第三批判关于审美判断之超越原则之最大的疑窦”(《以合目的性之原则为审美判断力之超越的原则之疑窦与商榷》,牟宗三,2008: 12-13)。这是非常遗憾的。大概在江西诗法里,这个原理得到了最明显地体现。即使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这些例子也层出不穷,比如,中日韩三国的围棋赛事可以称之为“三国演弈”,湘菜馆的名字可以叫“西湘记”。对于熟悉儒家经书的文人,看到“我居北海居南海”这样的句子,自然会产生类似的惊奇。而这样的惊奇往往和幽默很接近,宋人说“东坡长句波澜浩大,变化不测。如作杂剧,打猛诨入却打猛诨出也”(阮阅,1998: 194)。其实,江西派也与此一鼻孔出气,尤其学得了其“活法”的杨万里,更是专以幽默滑稽为诗,所谓“不笑不足以为诚斋之诗”(吴之振,1986: 2038)。但在翻译中,因为两种异质语言间的紧张性,在出乎意料取得一致性时,幽默并不突出,更多的是惊异。苏曼殊竭力使用古雅的辞藻,应该有这样的考虑在其中,就算他并未明确意识到,实际效果确实如此。比如《哀希腊》“You have the Pyrrhic dance as yet;”一句,庇瑞克舞尚存,而昔日辉煌竟沦,译为“王迹已陵夷,尚存羽衣舞”(苏曼殊,1933: 2),用词皆较为人所熟悉,惊异感更明显。(5)不过,庇瑞克舞是古希腊的战舞,译为“羽衣舞”不够贴切,或许译为“破阵舞”更好。不论曼殊他们是不假思索,还是仔细考虑,使用“羽衣舞”肯定是因其更熟知而易于造成惊异。相同的方法一定会带来相同的审美效果,只是在翻译中惊异显得更突出。揭示这一点,其意义即使不在翻译的方法,也在翻译的读法。当然在某些语境下,翻译仍然会出现幽默的趣味,比如一位英国主持人了解了中国的俗语“脱裤子放屁”后,脱口译作“butter on bacon”,很恰当,也很有趣。但在文言翻译里,类似的例子我尚未遇见。
三、 江西诗法的三个次生原则在译诗中的运用
江西诗法的基本原则无论在写作中,还是翻译中,履行起来都会出现困难,找到合适的成句绝难每发必中。于是出现了相对宽松的原则,可以看作次生的,比较重要的有三个。
(一) 句法
这是陈师道特别重视的。他有些取巧,用了最简便的办法,把工夫从用字转移到句法上。他本来对黄庭坚的理论和创作都很欣赏,也力图做到“无一字无来处”,但像钱钟书所说,他的“本钱似乎没有黄庭坚那样雄厚,学问没有他那样杂博,常常见得竭蹶寒窘”(钱钟书,1985: 116)。也许在尽力之后仍觉无奈,尤其发现自己的长处在于对杜甫的句法颇有心得,就连黄庭坚也赞赏他“作诗深得老杜之句法,今之诗人不能当也”,遂致力从句法中体现古雅的格调,成为一种新的方法。他指出:“今人爱杜甫诗,一句之内,至窃取数字以仿像之,非善学者。学诗之要,在乎立格、命意、用字而已”(张表臣,1982: 464)。在翻译中,这个方法给了很大的便捷,尤以马君武的译诗颇得其益。马君武也翻译了拜伦的《哀希腊歌》,我们看第一节:
希腊岛,希腊岛,诗人沙浮安在哉,爱国之诗传最早。战争平和万千术,其术皆自希腊出。德娄飞布两英雄,渊源皆是希腊族。吁嗟乎,漫说年年夏日长,万般消歇剩斜阳。(马君武,2020: 350)
他的英文似乎不及曼殊,把Sappho的“love and song”译成“爱国之诗”,或许是故意的改变,而“Dolos”和“Phoebus”并不是“两英雄”,前者是地名,后者是诞生在那儿的神福玻斯。这个不用管。他除了有意或无意的误译外,是尽力做了直译,但这样的译法很容易造成旧体诗丧失格调,成为类似“老干体”的恶札。马君武采取的就是陈师道的方法,从句法入手,他把七言古诗典型的句法运用得很娴熟,铺排的句式,开阔的气势,立住了古诗的格调。虽说难度相对较小,能够做到这一步亦非易易了。
(二) 换骨法
或许黄庭坚的长处还有风格都和陈师道不同,或许他觉得笼统谈句法不够精巧,并不特别重视陈师道的方法,而是自己提出两个很有创造性的方法,来解决寻找合适成句的困难,就是江西诗派里不少人讲的“换骨法”、“夺胎法”。这是由惠洪转述的:
山谷云: 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惠洪,2006: 34下引《冷斋夜话》语皆同)
这段话意义不是很明白,历来的解释各有分歧。因为“人之才有限”,就利用前人的“意”,难怪会被认作剽窃之黠。所以我很怀疑这是惠洪没有搞明白黄庭坚的意思,自己想当然地记成这样。依据黄庭坚的逻辑,这里所谓“人之才有限”,应该是说我们能够利用的前人成句有限,而要表达的意思无穷,这才出现困难。这是客观条件的限制,不是主观能力的不足,于是才提出新方法。
关于两个方法的说法也很纷纭,先看“换骨法”。按照惠洪的说法,诸如前人“意甚佳而病在气不长”的作品,给他把毛病改好了,就是换骨法。相比起来,我更相信钱钟书的说法:
《演雅》云:“络纬何尝省机织,布谷未应勤种播。”……按山谷词意实本《诗·大东》:“睆彼牵牛,不以服箱。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抱朴子》外篇《博喻》有“锯齿不能咀嚼,箕舌不能别味”一节,《金楼子·立言》篇九下全袭之,而更加铺比。山谷承人机杼,自成组织,所谓脱胎换骨者也。(钱钟书,2007: 9)
这其实是在无法承袭前人成句的情况下,通过“意”的一致,使词语的不一致产生一种一致感,因此既有了经典的背景,又保留了惊奇的审美效果。从原理来说,确是一脉相承,也和“不易其意而造其语”的表述吻合。这在文言诗歌翻译里,也是曾经被使用过的方法,比如黄克孙译本《鲁拜集》第31首。原作直译是:
从地心直上将第七门穿过
我飞升,稳踞在那土星宝座。
许多疑惑都已在路上解开;
除了人类命运的最大之惑。
黄克孙译作:“骑鹤神游阿母台,七重天阙拂云来。玉皇仙籍偷观尽,司命天书揭不开”(黄克孙,2012: 77)。原作带着很重的波斯意象,直接表现在旧体诗里肯定有龃龉之感,换作了道教的意象,就很适当顺畅。自然有人会批评,你这样一换骨,把波斯意象全损失了,失去了翻译的基本品质。可是意象虽然转换,原意具在,对于诗歌来说,意象是外在的,其作用是表现内在的思想,如果能以最符合中国语言的方式传达出其思想,不正符合了“意足不求颜色似”的中国诗歌精神吗?批评者还忽略了这里产生的惊奇审美效果,也许是在字面的直译里不可能有的。
(三) 夺胎法
“夺胎法”就更难理解了。“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这句话就很费解,所以《诗话总龟》引作“规摹其意而形容之”。大概黄庭坚自己也说不清楚,用了“窥入”这个词,旁人不明白意思,就跟上面的换骨法混淆了,改作“规摹”。仔细研究惠洪举出的例子,似乎可以窥出一些消息。白居易诗:“临风杪秋树,对酒长年身。醉貌如霜叶,虽红不是春。”苏轼则说:“儿童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醉红。”在豪迈里把“虽红不是春”的意思透出来,利用白诗翻进一层,似乎就是“窥入”的要义。不过,苏轼不如黄庭坚自己那样有意识、甚至是刻意地使用,还不够典型,最典型的得找黄庭坚自己的例子。还是那首《寄黄几复》,现在看第二句,第一句说他和黄几复离得遥远,这句说远到连封信都很难寄到。其实这个意思太普通了,你可以张嘴就来,像晏殊“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也可以有无限的前人成句。可就是因为太普通,不符合黄庭坚好奇的个性,他偏要表达得如此迂曲:“寄雁传书谢不能。”初看似乎这大雁太不讲人情,托你带个信你也推辞,然后你发现黄庭坚用了两个典故在里面,并且“窥入其意而形容之”。头一个据《汉书·苏武传》:“得雁,足有系帛书”,第二个据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旧说,鸿雁南翔不过衡山。”两个典故太熟知了,任渊都没有注出来,但黄庭坚这样一用就新奇了。我想让大雁替我寄个信,大雁推辞:“我飞不过衡山,怎么能带到广州四会呢?”上句的遥远,这句的信难到达,全在“窥入其意而形容之”里头了。“谢不能”,三字是点铁成金法,据任渊的注释:“《汉书·项籍传》‘陈婴谢不能’,则此诗所用之意。”这一句短短七个字,也没表达特别的意思,却用了三个故实、两种江西派的诗法,可谓刻意求精,难怪成了他的名作。
在翻译中碰到的情况,往往不是回避过于常见的表达,恰是用有限的成词去“追无穷之意”,不得不采用看似有些迂曲的夺胎法,算是基本法则外的一点宽容。我举一个自己翻译里的亲身经历。《鲁拜集》第59首,直译出来是:
葡萄酒能以逻辑的绝对真
辩破七十二家教派的纷纭:
那至尊的炼金术士顷刻间
就把生命的铅水变成黄金。
在中国的古典里,实在找不到炼金术士把生命的铅水变作黄金这样的表述,如果直译,难免过于异化,和旧体诗的格调不合。我从“生命的铅水”联想到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里“忆君清泪如铅水”的句子,就借用过来“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译作:“辩尽无涯辩有涯,不如全付酒仙家。能收君泪如铅水,炼作黄金买岁华”(钟锦,2020: 19)。
这三个江西诗派的次生原则,给了旧体诗译写稍稍宽松的尺度,如果没有受到时代外在环境的冲击,经过一定的发展,应该可能取得更好的成就。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文言诗歌翻译在苏曼殊后再未发生真正的影响,自身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甚至连江西诗法最基本的要求都未达到。比如,江西派讲究对仗的句子都用成句,使之在差异中产生一致,这样的例子在翻译中从未见到。文言诗歌翻译也一直更多地采用格律宽松的古体,近体也多用七言绝句,句子少,易表达,又不强求对仗。整体水平不高,即使出自名家的译笔也往往令人诧异。李霁野作为新文学的健将,旧体诗差一些,可以理解。他译《鲁拜集》第4首:“新年苏旧欲,灵魂乐幽居。枝上花如雪,群芳遍地苏”(李霁野,2004: 4),达意既不完整,又丝毫没有旧诗该有的格调,格律也出毛病,真就不如用白话了。五言绝句其实很难表达得妥帖,但我们看到,不少文言基础较差的译者很喜欢用,因为就凑字来说最简单。吴宓号称新学旧学都精通,他以《蝶恋花》译朗费罗的《伊万杰琳》:“苍茫松林千年老。败叶残蛩,满地鸣愁恼。陵谷规残人不到,高山流水哭昏晓。商妇弦绝伶工杳。片羽只麟,旧事传来少。今我重临蓬莱岛,原野凄迷空秋草”(吴宓,2005: 3)。虽达意和韵味都远好于李霁野,但水平仍是很普通,格律照样出毛病,就很让人诧异了。足见历史尚欠文言翻译发展的机运,尚缺乏更为出色的文言译作。
因此,在今天我们应该给予文言翻译更多的包容,这并不是说,要给它和白话翻译同等的地位。只是让它在小众中得以从容前行,将它可能达致的美感充分表现出来,供给中国翻译学有用的材料。我们相信,从中看到的问题,不仅有助于中国翻译学的建构,同时也会有益地影响中国翻译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