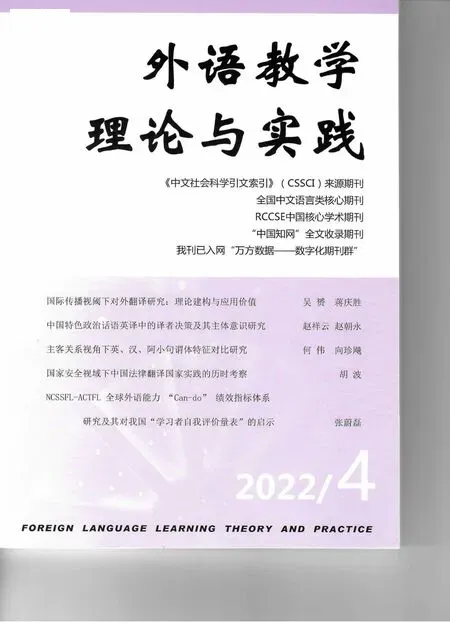译史框架下的译者群体研究:对象、意义和路径*
2023-01-05袁丽梅
袁丽梅
上海大学
提 要: 目前译者研究考察单个译者的居多,而译者群体研究成果偏少。本文针对这一现状,思考译史框架下译者群体研究的对象、意义和路径,尝试回答何为译者群体研究、译者群体研究为何以及如何进行译者群体研究三个问题。文章认为译者群体研究既涉及知名译家构成的译者群体,也不能忽视籍籍无名的译者;译者群体研究可为不同层面的译者研究提供参照系、填补译史研究空白、推动跨学科翻译研究;研究以个案为基础,借助比较的方法,构建译者个体间的联系,并始终围绕译者这一中心展开。译者群体研究具有不同于译者个体研究的价值与独特性,应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
一、 引言
历史研究离不开对人的研究,翻译史亦不例外,“翻译的全部过程必须依靠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去完成,否则便无所谓翻译行为”(宋以丰,2019: 171)。随着翻译研究的焦点由原文向译文再向译者的转移,译者在人类全部既往翻译活动中的中心地位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近年来相关成果踵出。其中,方梦之(2021: 11)撰文提倡拓展“翻译家研究的‘宽度’和‘厚度’”,希望研究者关注到在各个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翻译家,同时“重视翻译家道德精神的厚度”,揭示其“之所以成为翻译家的内在动力”;刘云虹、许钧(2020: 75)也指出亟需加强翻译家研究,“积极评价翻译家的历史贡献、深入探索翻译家的精神世界、切实关注并依据第一手资料考察翻译过程等”。译家译者研究俨然成为当前翻译研究,尤其是译史研究的一大热点。既然是对从事翻译活动的人的考察,那么就不只限于作为个体的人,也将涉及共同从事这一活动的一类人或一群人。然而,既有研究考察单个译者的居多,译者群体研究成果偏少,本文拟聚焦译者群体研究,廓清其研究对象、研究意义以及实施路径,以期引起学界对这一领域的兴趣与深入探讨。
二、 何为译者群体研究?
何为译者群体研究?其中指涉的关键问题便是译者群体研究的对象,也即研究什么?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译者群体研究自然研究的是译者群体。然而,且不论性情各异、风格参差的译者个人如何才能形成一个特定的译者群体,单就“译者”这个概念而言,也不是铁板一块。冯全功(2022)在“翻译家群体研究的总体路径——兼评许多的《江苏文学经典英译主体研究》”一文中较为集中地论述了译者研究对象的厘定、方法的选择、思路的推进与结论的归纳等。但不难看出,其中的译者仅涉及那些成就斐然、影响深远的翻译家,并不涵盖广泛意义上的所有从事过或正在从事翻译活动的人。不过,后者人数众多、不胜枚举,也不见得都有一定的研究价值,这就如同历史研究中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并不是所有发生过的历史事件都值得重新挖掘出来探究,“历史上的翻译家举不胜举,我们为什么要选择研究此一译家,而不研究彼一译家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研究此一译家,或研究某一译本,或某些翻译事件,会带出某种学术意义,所以我们才花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它”(邹振环 等,2020: 65)。学术意义的大小又往往取决于译者翻译成就的大小,因为我们研究某一译者并不只是为了回顾其翻译历程,展示其译介成果,更是为了探究其翻译策略 /思想,该策略 /思想形成的原因,在特定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下是否具有代表性,是否有助于总结某一阶段翻译活动的共性和规律,对不同文学、文化间的沟通交流有何影响等。译者译介成就的大小将直接回答代表性与影响力的问题,是评判学术意义最方便快捷的一项指标。正是基于这一点,译者研究,尤其是译史中的译者研究总是重点关注成就突出的翻译家,如在汉学家译者研究领域,蜚声中外的“中国文学的接生婆”葛浩文(H. Goldblatt)就吸引了绝大多数研究者的目光,自2000年以来以“葛浩文”作为主题词检索获得的期刊论文“已逾千篇”(朱振武,2020: 82)。
享有盛名的翻译家固然可以作为特定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下某一类文本翻译活动的典型代表,成为译史研究与译者研究中的焦点,但我们也不能忽视,除此之外还存在许许多多籍籍无名的译者。作为个体,他们很少为人所知,甚至在自己的译作中也不曾留下姓名,若按照“翻译成就的大小”进行排序,他们无疑处于金字塔的底端,这样的译者是否还具有“某种学术意义”?如果有,意义何在?2016年约翰·本雅明公司出版《口译史新洞察》(NewInsightsintheHistoryofInterpreting)一书,收录了“大发现时代的口译: 西班牙帝国在美洲的早期”与“口译之‘罪’: 作为二战战犯的台湾籍口译员”等文,前者考察了地理大发现与西班牙在美洲实行殖民统治期间,充当“中间人”的口译员的主要活动;后者则基于二战期间受日本征召的台湾籍口译员的翻译活动,“揭示口译员在极端环境下所面临的生存危机与道德困境”(覃江华,2019: 82)。香港中文大学的王宏志教授在自己的研究中也关注到了此类译者群体,他于2010年前后开始潜心研究翻译在近代中英外交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挖掘出大量珍贵史料,涉及李叶荣、鲍鹏、王韬等在这一时期从事翻译沟通工作的中国通。他正在撰写的《天朝的译者: 从李叶荣到张德彝》一书,将“以传统天朝思想下的蛮夷观作为整个研究的框架,贯串一系列个别译者或译者群”,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天朝思想对译者及翻译行为的制约,以及明末以来中西交往的译者怎样以一个文化现象作出集体性的回应”(王宏志,2021: 92)。上述研究实例表明,这些几乎湮灭于历史长河中的无人问津的译者事实上同样具有研究价值,值得深入的挖掘与探讨。
综上所述,译者群体研究不仅包括对译家群体的研究,也涉及对那些普通的、“无名的”译者群体的研究。而随着微观史学的发展,这些鲜为人知的边缘小人物正一步步走到历史的聚光灯下,“以其作为线索从多方面考量……(可)获得先前被忽略的因素并发觉历史现象新的意义”(包雨苗,2019: 96)。
三、 译者群体研究为何?
译者群体研究为何回答的是译者群体研究的意义问题。由知名译家组成的译者群体的研究意义与针对这些译家个体开展的研究一样,其价值不难论证。方梦之、庄智象(2016: 2)主编的《中国翻译家研究》(三卷本)选取古往今来最具影响力的翻译家,重塑以他们为代表的“我国译者的群体形象”,“弘扬他们对我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学、科技等方面的贡献”;周领顺等(2014: 101)指出:“译者群体行为研究,旨在寻求作为一个群体的译者其总的行为特征……”这种对群体特征的归纳与总结将突破地域、性别、流派等显而易见的共性,凸显其“对当下翻译实践的启发”(冯全功,2022: 158)。“无名”译者群体的研究意义当然也不乏丰富译者形象、挖掘历史贡献等维度,但如果只是着眼于这些方面,他们则既不典型也没有什么代表性,其翻译策略 /思想的指导意义也十分有限,并不是实现这类研究目的的理想对象。
本文认为,对于由普通译者构成的译者群体研究,其意义主要体现在: 1) 为译家研究提供必要的参照系;2) 弥补译史研究中的空白点;3) 拓展翻译研究的跨学科维度。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所有行为者的行为都受到了各种社会生产关系的制约”(王军平,2020: 56),译者也不例外。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之后,我们对翻译活动的考察总是离不开作者、译者、读者、赞助人、评论者等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然而,居于这一网络中心的是译作而非译者,其中的主体要素贯穿译作生成的全过程,译者不过是多个主体中的一个、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环。若将译者作为该网络的中心,则不难发现各中心,也即此译者与彼译者之间长期为我们所忽视的客观存在的联系。广义而言,一切从事翻译活动的行为人均隶属译者这一群体,而就某一具体的翻译实践来看,任何译者个体,不论他 /她多么特立独行、离群索居,其翻译行为总会在历史或现实的维度上与其他译者的翻译行为产生关联,无论如何都不是单枪匹马的行为。知名译家的翻译实践活动同样深嵌于这样的社会关系网中,他 /她在个人身份、教育背景、翻译思想、文化态度等方面总会归属于某一 /几个译者群体。无视译家个体与其他译者(包括其他知名译家),乃至其从属的某一译者群体之间的关系,译者(尤指译家)研究将难以摆脱“文本中心主义”的桎梏;孤立地考察某一译家也很容易使居于研究中心的译者“附置于其他翻译元素里,要说明的是这些其他的翻译元素”(王宏志,2021: 87),难以成为真正的译者研究。
译者群体的引入不仅是译家研究中的必要步骤,也将有助于拓宽后者的研究空间、深化其研究价值。既然要将一个个体放入群体的背景中进行考察,那么常见的问题无外乎找相似与找不同。如果某位译家的翻译行为特征与群体中的其他人趋同,研究者可在相似性的基础上提炼该群体的总体特质;如果差异性突出,则将引发一连串的话题——差异性表现在哪里?为何会发生?有何启发或揭示意义?……当然,成就突出的译家一般不会泯然众人,而通过同类比较的方式获得的差异性也将有助于凸显译家的独特风格与特殊贡献。葛浩文是汉学家译者研究的重要对象,但仅以他为中心的研究却远远不能反映当代汉学家译者的整体面貌、译介倾向和共同问题;同时,葛浩文翻译活动及其译介成就的独特性与重要性也只有在当代汉学家译者群像这一研究背景下才能获得更为准确的认识和把握。
此外,有的翻译事件中的译者主要以群体面貌示人,这些译者的翻译活动是译史研究中有待发掘的空白点,而要对他们进行研究就不得不将其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具体来说,这里存在两种情况。一是译者个体几乎全部隐匿,参与翻译活动的译者难以具体到个人。譬如张旭(2020: 69,76)对援越抗美期间中国翻译人员的史料挖掘,虽然提供了部分译员名单,也涉及个别译者的翻译事迹,如充当越语翻译的京族青年、“年仅20岁的罗周德牺牲在越南战场上”,来自华侨大学化学系的陈汇祥和洪南星、中文系的陈旺祺和苏昆平、物理系的陈江海等8人积极参军入伍。但更多的个人信息却无迹可寻,即使文中出现来自单个译者的引证,说话人自身也业已消弭在对群体行为的描述之中,焦点不在个人,而在于宏观展现译者群像,如译者之一的陈旺祺对参与军事翻译培训情况的回忆:“……学员的任务是学习政治、文化和军事知识,没有一定的学习期限,一有命令,就随时秘密出发,实质是在那里等候命令出国……”(同上)
史料阙如固然影响研究的推进,但有时将不同的译者归属于某一译者群体进行考察,并非仅受限于个人翻译活动史料的不易获取,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就某一话题而言,整体研究的意义明显大于对译者个体的专门研究。上文所举张旭与王宏志的研究皆有这方面的考量,后者对李叶荣、鲍鹏等中国通事的关注正是希望呈现身处中西交往浪潮中心的译者作为一个整体如何回应“天朝思想”。另有学者(喻锋平、唐媛,2021: 31)聚焦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份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的译者群体,其中涉及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袁振英、茅盾、沈泽民、杨明斋、李少穆、李震瀛等人,另有未署名译者2人。作为译者之一的茅盾,其翻译成就当然值得作为个案深入研讨,但这样的译家研究往往容易遮蔽其为《共产党》月刊所进行的一系列翻译实践,而如若剥离出来,单独对《共产党》月刊中茅盾的译介行为进行考察,甚而对沈泽民、李达、周佛海等人的相关翻译活动进行个案梳理,则不仅有重复研究的嫌疑,也无助于宏观勾勒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思想建党”的这一侧面。
译者群体研究意味着要在不同的译者个体间建立起联系,这种联系千差万别,从译者群体不同的划分标准中可见一斑,如依据地域划分的浙江籍翻译家或江苏籍翻译家研究、突显性别身份的女性译者群体研究、围绕共同的译介对象形成的《三国演义》译者群体或毛泽东诗词国外英译群体研究,以及具有共同的教育背景或相似的创作风格的大清留美幼童构成的译者群体与鸳鸯蝴蝶派译者群体研究等。不论依据何种标准,译者群体总是建立在一定的共性基础之上,共性的获得自然蕴含着比较的视野,从而有助于打破针对译者个体的传统的隔绝式研究,有力拓展译史框架下译者研究的横向维度,并进一步为翻译研究的跨学科融合创造更为广阔的空间。贺爱军(2020: 69-71)曾借助人文地理学视角对宋明时期的译者构成及其数量变化进行考察,获得该时期译者地理分布的相关数据,由此划分出丝路地带译者、译馆及译经院译者与文化中心区译者等不同译者群体。若要继续深入探讨其中某一译者群体,则首先应予以关注的便是上述在特定学科 /理论视角指导下形成的译者群体划分标准,这也是整个研究工作开展的前提与立足点。如对丝路地带译者群体的分析必然需要结合丝路地带“独特的交通位置”“频繁的贸易活动”(贺爱军、侯莹莹,2020: 70)以及多民族间的宗教文化交流,需要“应用于不同的学科相互吸取学科养分”(罗选民,2022: 1)的跨学科研究方法。翻译研究本身具有跨学科特征,译者群体研究则将凭借对一定数量上译者群体性行为特征的考察为翻译研究的跨学科融合提供研究素材与研究空间,其研究价值不容忽视。
四、 如何进行译者群体研究
译者群体研究的路径不一而足,本文重点强调以下几点: 首先,个案研究是译者群体研究的基础,这里的个案不仅指译者个体,在译者多以群体面貌示人的情况下也指某一具体的翻译活动或翻译事件。当前,译者研究的广度已经有了明显的拓展,文学翻译领域以外的译家译事受到了学界的普遍关注(韩子满,2019;方梦之、傅敬民,2018;单宇、范武邱、蔡万爽,2019;等)。以近十年的汉学家译者研究为例,越来越多小语种国家的汉学家译者正在进入我国学者的视野,如埃及汉学家穆赫森、娜希德,以色列汉学家柯阿米拉,韩国汉学家朴宰雨、宋载邵,意大利汉学家马丁·贝内迪克特等,大大丰富了汉学家译者研究的对象范围。有了对个体的关注,才有进一步考察群体共性与特征的基础和可能。古今中外,从事各类翻译活动的译者数量众多,译者研究个案俯拾皆是。单个译者的个案研究为译者群体研究的持续推进提供基础性材料,这类研究大多按照人类的整体认识规律,从对译者个人生平经历与翻译成就的概述,到对其翻译活动的简介,再逐渐深入至译介策略、翻译思想的解读等。如果没有越来越多的译者进入我们的视野,译者研究不论是在横向拓展,还是在纵向加深方面都将严重受阻;但如果只是一味追求新鲜的研究对象而对少人涉猎的译者译事进行浅层次挖掘,满足于对译者个体翻译行为与翻译成就的简单梳理,虽然个案研究的数量突飞猛进,但研究的整体价值却会遭到不断的削弱。单宇等(2019: 19-20)在统计了知网(CNKI)与Web of Science的相关数据后发现,目前国内“译家研究对译者生平、贡献和翻译活动等译家考古学研究明显多于理论化译家研究”,而在翻译家个体研究中,“介绍译家生平与主要成果的文献也相对较多”,似已形成一定的研究瓶颈。低水平、同质化的研究,不仅难以在译者研究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也将加剧微观史学的碎片化倾向。
因此,单个译者的个案研究虽然是译者群体研究的基础,却亟需打破各自为战的局面,通过比较的方法生成多样化的研究问题,真正实现译者群体研究。一方面,比较是形成译者群体的首要路径。如前所述,只有通过比较获得某方面的共性或联系,形形色色的译者个人才能依据一定的标准归属于不同的译者群体。因此也可以说,研究对象之间的可比性是开展译者群体研究的前提。但“在寻找翻译家群体研究划分依据的时候,不应简单地以性别、地域、国别、历史时期等为标准,还要看群体成员之间是否有其他共性”(冯全功,2022: 154)。性别、地域、国别、历史时期等在比较中都是一目了然的共性,可以成为译者群体研究的起点。然而,随着研究的推进,比较的范围需要不断扩大,比较的内容不断丰富,其他学科视角不断融入,群体划分标准相应调整,从而超越那些表面上的共性,获得深层次的“指向更广大问题”(... led to a much wider question that others had failed to ask)(Pym,2007: 21)的群体特征。
此外,在寻求共性的同时,对群体内部差异性的考察也是译者群体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无论如何划定标准,同一群体内部的个体之间既有相同也有不同,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译者群体研究虽然通过比较的方法,在共性基础上形成集合式研究对象,但其中个体间的相同或相似之处却不是译者群体研究的唯一目的。现有相关讨论多强调群体特征的归纳与总结,如周领顺(2014: 101)认为“译者群体行为研究,旨在寻求作为一个群体的译者其总的行为特征”,冯全功(2022: 158)也提出“保留差异、归纳共性是翻译家群体研究的核心任务之一”。但本文认为,译者群体研究并不只是为了将不同的译者分门别类,纳入对应的群体当中,提炼总结群体共性,同时也是为不同层面的译者研究提供横向与纵向的参照系,这里既包括了针对知名译家的研究(个中意义前文已有论述,在此不赘),对于那些本身就作为一个整体出现或只有作为整体时才具有特定研究价值的译者群体而言也同样适用。群体的规模可大可小,小群体可视作更大群体的组成部分,因而对其的考察应放入该更大群体的背景中进行。
覃江华于2011年发表论文“语言钢琴师——美国汉学家金凯筠的翻译观”,首次向国内学界系统介绍了美国汉学界“现当代中国文学翻译家,张爱玲研究专家”(覃江华,2011: 121)金凯筠(K. Kingsbury)。在论述过程中,研究者借助比较的视角,对金凯筠与葛浩文和蓝诗玲的翻译策略进行了对比,认为前者有所不同:“她大量采取直译(甚至是硬译)法,目的是传递汉语文化的特色,给英语文学注入新元素”(同上: 123)。研究者为何选择比较金凯筠与葛浩文,而不是比较金凯筠与沙博理,或者许渊冲?显然,与沙、许相比,金、葛之间有着更多的相似性: 他们同为美国当代汉学家(葛可以说是金的前辈),译研对象也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葛浩文早年是萧红研究专家,翻译过萧红、老舍、巴金、刘震云、苏童、莫言、毕飞宇等多位现当代小说家的作品;金凯筠师从王德威,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张爱玲,已发表 /出版多篇 /部张爱玲散文与小说的英译),在翻译过程中同样面临文化差异(人名、方言、典故等)带来的巨大挑战等。在相似性的基础上,二者之间的差异显得更为引人入胜: 金凯筠的翻译策略与葛浩文有何明显的区别?金大量采取直译(硬译)法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在目的语中的接受效果又如何?具体翻译策略的使用与读者接受是否与源语文本本身的语言特质或叙事形态有关?抑或取决于译者的文化态度?这种文化态度的形成与葛浩文等前辈译者是否有所关联?又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特定汉学家译者对美国当代汉学传统的承继和突破?继而是否能够预测目的语接受语境对待异质文化的包容度越来越大?遗憾的是,目前尚未有相关研究沿着这一比较的路径继续推进。经由比较不断区分差异正是获得事物本质的方法,法国当代哲学家、同时也是影响深远的汉学家弗朗索瓦·朱利安(Francois Jullien)(2013: 27)认为差异是为了抵达本质:“每一次将一种类型分为二,然后再把其中的一半分为二;如此继续下去,一直到无法再分的时候,就到达了所寻求的定义……从差异再到差异,一直到‘最终的差异’,此刻,事物的‘本质’便显露出来。”
最后,译者群体研究应始终围绕“译者”这个中心展开。值得注意的是,译者群体研究中涉及的“译者”并不是一个单数概念,既然包含了不同的行为主体,那么这些主体相互之间的关系就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研究内容。如前所述,译者与译者之间的联系既是形成特定译者群体的基础,也是彰显译者群体研究意义的关键所在。译者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研究开展多年,我们对于译者、读者、赞助人等行为主体间的互动关系并不陌生。周领顺(2014: 104)在以苏籍翻译家群体为例探讨译者群体行为研究的基本思路时指出,“一是要着重开展翻译内部研究……二是要开展翻译外部研究,即包括翻译家的翻译目的研究、影响译者翻译行为的外围因素(如译者心理因素、社会环境、时代因素、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等因素)研究……三是要开展内外批评研究……”。本文认为,文本与社会的确是进行包括译者群体在内的译者研究重要的内外维度,且此译者与彼译者(尤其是同属特定译者群体的其他译者)之间的互动关联本是外围社会因素中的应有之义,但这部分内容在目前研究中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使得冠以译者群体研究之名的成果有时难免给人以个案堆砌之感。当然,要探寻译者个体间的联系实非易事,这也是拓宽译者群体划分标准的意旨所在,需要在个案“广种”与“深耕”的基础上,借助比较的方法,寻找译者个体之间有形与无形的联系——有形联系多依赖史料发掘,如晚清留美幼童中的梁诚、容揆、谭耀勋、欧阳庚等人,他们“在清末民初的外交战场上互相提携,互相扶持,以翻译为国家作贡献”,然而大量史料仍有待系统的发掘(叶霭云,2014: 45)。
“译者本身是文化中的个人,即使最专业或职业化的译者,他 /她的活动不可能只限于翻译活动,而这些翻译活动跟其他各方面的活动是挂钩的、配合的,甚至互动的。文学译者的例子最易理解,他们的创作跟翻译是整体性的,不讨论他们的文学活动,不可能真正理解他们的翻译活动”(王宏志,2021: 90)。这是对译者作为“人”的主体性与社会性的强调,换句话说,仅仅局限于对译者翻译活动的考察最终无法完成真正的译者研究,对于译者群体研究而言也同样如此。事实上,前文所涉特定译者群体中个体间的联系有相当一部分便体现在翻译活动之外其他方面的活动中,对后者的关注与考察也因此具有构建译者群体内部联系的重要功能。与针对个别译者 /译家的研究相比,译者群体研究更需要从对译者翻译策略、具体翻译过程的讨论中突围出来,要实现对该群体全面、深入的了解必然需要将译者的社会生活纳入考察范围。
与此同时,译史框架下的译者群体研究自然蕴含着时间的维度。人的成长、发展、变化……无一不与时间要素息息相关。在不同时期,译者个人的翻译原则、方法、策略,文学、文化主张,政治观点,人生体悟……也不可能固定不变。一旦这些方面发生变化,译者群体的稳定性便会受到影响,由此导致的群体成员的退出、新成员的加入以及成员间联系的增强或削弱等均是译者群体研究过程中值得关注的话题。译者群体的形成、发展、解散是在时间维度上展开的一系列持续变化的结果,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译者群体研究的考察对象并不是一个定量,选取特定时间截面集中探讨或以时间为轴对其发展演变进行历时梳理,应是开展其他相关研究的前提。此外,表面看起来是由于个人自身的变化或个人与个人之间关系的改变而导致译者群体发生的演变,其实与外部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仍然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由此对译者群体兴衰演变的探讨可成为一扇新的窗口,基于群体研究数据反映出特定时期的翻译规范、翻译在整体社会生活中的价值以及翻译活动与社会变化之间的互动联系等。
五、 结语
本文围绕何为译者群体研究、译者群体研究为何以及如何进行译者群体研究三个问题,对译史框架下译者群体研究的对象、意义和路径展开思考与讨论。文章认为译者群体研究不仅旨在勾勒知名翻译家群像,更是为了挖掘几乎湮灭于历史长河中的籍籍无名的普通译者。后者虽然在翻译成就与社会影响力方面明显不及前者,却也是构成翻译行为主体的有机部分,对其进行系统考察有助于弥补译史研究中的空白点;同时为译家研究提供必要的参照系——在差异中凸显知名翻译家的独特贡献,在相似中探寻翻译思想的历史传承;并成为展示跨学科翻译研究的理想舞台。译者群体研究以个案研究为基础,通过比较的方法生成多样化的研究问题,从而推动研究向纵深发展。在比较过程中,特定译者群体的共性固然值得关注,其内部的差异也是重要的研究切入点。然而,不论采取何种路径,译者群体研究均需立足于译者这一中心,对译者群体中不同行为主体间的关系、译者除翻译活动以外的其他社会生活,以及群体形成、发展过程中的时间维度给予充分考量。译者群体是译史框架下译者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维度,与传统的针对个体的译者研究在诸多方面不完全一致,其中的相关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