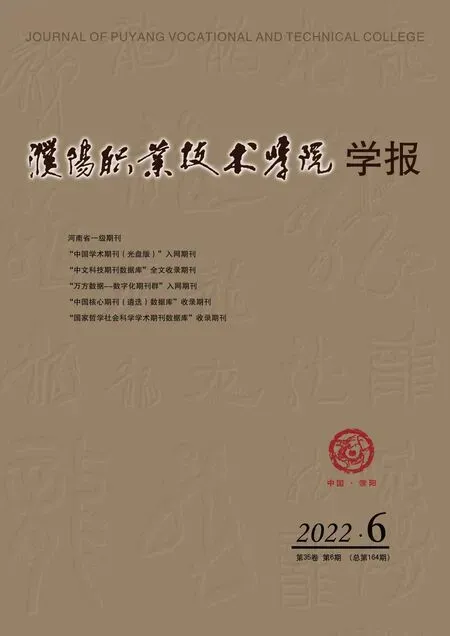花雅之争视阈下的“贵妃醉酒”①
——以北京、苏州两地为例
2023-01-05张聪
张 聪
(上海大学 上海电影学院 上海 静安 200040)
京剧《贵妃醉酒》作为梅兰芳大师的经典代表作品,其现有表演风格的形成经历了曲折、复杂的过程,在梅兰芳改革之前正如俞振飞所说的:“《贵妃醉酒》是一出花旦戏……这个戏经过梅先生多年的创作处理,终于使这出原来单纯卖弄技术、风骚的刀马、花旦戏而成富有一定思想内容的名剧……”[1]1这种“风骚”“低俗”的表演风格的形成与它的“母体”有关系,也与“花雅之争”时期的表演生态有关,同时与当时“小旦”行当的盛行也有关联。因此通过分析“花雅之争”视阈下的“贵妃醉酒”有利于还原乾、嘉年间的表演风格,帮助我们清楚的认识“贵妃醉酒”表演艺术的变化过程,也进一步体现出梅兰芳大师对于革新“贵妃醉酒”表演艺术的伟大之处。
一、“花雅之争”前的“贵妃醉酒”
最早出现“贵妃醉酒”这一故事的是明钮少雅的传奇《磨尘鉴》,但该传奇是否在舞台上演出过目前尚无证据。因此能见到的最早关于“贵妃醉酒”的演出本是《新选南北乐府时调青昆》(后文简称《时调青昆》)中的《杨妃醉酒》。陈多先生将《时调青昆》判断为“明末清初”辑录刊行的作品,而且“中华古籍资源库”将作者黄儒卿判定为明,出版时间判定为清初,也就是说《时调青昆》中所辑录的主要是晚明所流行的剧目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在《时调青昆》的二卷目录中剧名是《红娘请宴》,实际的内容却被替换成了《杨妃醉酒》。班友书认为这“是书商的把戏;他们在重印前乘机将《杨妃醉酒》塞了进去,请刻工另刻,抽掉了《红娘请宴》,但原刻本的目录却没有换”[2]271。这种现象的动机应该是书商们为了促进书籍的营销,而根据当时流行的演出剧目进行的调整,这也证明了《杨妃醉酒》作为青阳腔在清初的徽南地区是很流行、很受欢迎的。
从整本《时调青昆》来看,它的每一页被分为上、中、下三层,上、下两层是剧本,中层是土产歌谣、时兴笑话等通俗、低俗的内容,尤其是一、二两卷记录有“和尚宿娼”“僧淫”“僧道”“尼庵”等笑话故事,其内容以和尚、尼姑、娼妇、寡妇等的淫秽色情笑话为主体。这是书商的营销噱头,但也从侧面透露出底层的文艺审美风尚,这也为戏曲艺术中低俗“小戏”的形成提供了生存的土壤。《杨妃醉酒》就是在这样的审美氛围中形成的,作为青阳腔剧本其风格则也展现出了这种低俗特点。杨贵妃与高、裴二人的调情时的唱词,“你若不嫌我残花败柳枝,双双同入在宫帏里,颠鸾倒凤与你戏”[3],这种直白露骨的唱词在《纳书楹曲谱》的《醉杨妃》一出中进行了润色修改,删除了“颠鸾倒凤与你戏”这样的唱词,显然青阳腔的《杨妃醉酒》在唱词上更加贴近市民欣赏趣味。作为单出小戏,缺乏曲折的戏剧情节,也缺少传统剧目的艺术积累,其“卖点”只能在舞台表演上突出杨贵妃寂寞思春的情态和醉酒后与高、裴二人的“调情”上,并且在艺术风格上主动迎合市民低俗的审美趣味。
书商刊刻《时调青昆》的目的主要是面对戏班和演出市场的需求,这种商业化、通俗化、平民化的定位,也能窥测出《时调青昆》中《杨妃醉酒》并不高的艺术格调。玉环醉酒后的春情摇荡,小旦、小丑的行当设置,为向“花部小戏”表演风格的形成提供了故事题材的便利性和人物行当的契合性。后世“花雅之争”时期的“贵妃醉酒”的低俗表演从其母体中就已经携带了这种面对市场、迎合大众审美情趣的艺术基因和艺术风格。
二、“花雅之争”时期的“贵妃醉酒”
“花雅之争”是清代戏曲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张庚、郭汉城在《中国戏曲通史》中把“花雅之争”划分为三个阶段:“首先与昆曲争胜的是高腔。高腔,即弋腔,在北京亦称京腔。”“继之而起,代表花部在北京剧坛与京腔争胜的是秦腔。”“北京剧坛又出现了徽调与秦腔竞奏的局面”[4]884-887。以上三个阶段在时间上大致从康熙后期到乾、嘉朝,持续时间近百年之久,北京舞台上的“贵妃醉酒”故事就是在第三个阶段出现的。“北京‘乱弹’诸腔的称盛,及其在斗争中的胜利,反映了全国戏曲艺术发展的总趋势。”[4]887“花雅之争”在北京的剧坛上表现的更为显著。当然,从《扬州画舫录》,朝廷的禁令等资料来看,作为昆曲大本营的苏州地区也出现了“花雅之争”的现象,并且昆曲在该过程中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引起了自身表演艺术的变化。北京和苏、扬地区作为一北一南两个戏曲繁盛之地都成为“花雅之争”的重要舞台。因此,在“花雅之争”的背景下审视“贵妃醉酒”,需要注意北京和苏州两个地区的变化才能较为全面的了解流传途径。这一时期的中国戏曲处于急剧的碰撞、交流、变化之中,“贵妃醉酒”也正是在该时期的戏曲演出环境中形成了表演风格,而这种风格也反映了当时的戏曲艺术的发展方向和人们的审美风尚。
(一)苏州地区的“贵妃醉酒”
关于苏州地区“贵妃醉酒”的演出记录最早可见于清乾隆早期刊刻的《太古传宗·弦索调时剧新谱》,被称为《醉杨妃》。《太古传宗》“全书二函八册。下函后二册即为附刊朱廷锡、廷肆兄弟合编在《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中未采录的"诸腔"二十四套,定名为《弦索时剧新谱》。”[5]96而《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刊刻于乾隆11年,因此《弦索调时剧新谱》中搜集整理的剧目是流行于乾隆十一年之前的。《弦索调时剧新谱》凡例第一条“谱中俱系通行时曲,间有文义极其鄙俚者庸,或删改一二,与俗本稍有异同。”[6]可见其所辑录的曲谱是当时通行的“时曲”,文词庸俗鄙陋,却是流行于当时受群众欢迎的剧目。“弦索调时剧”就是用弦索调演唱的当时流行于苏州地区的比较时兴、流行的剧目。由于“早在十七世纪,北方的弦索调就已失传,南方的弦索曲受南曲声腔的影响,已‘渐近水磨’,使音乐具有了昆曲风格。不仅如此,它也受到俗曲的很大影响,选用俗曲的唱词,借用俗曲的曲牌”[7]136。弦索调《醉杨妃》进入苏州地区后进行了俗曲“昆化”并流传开来,但风格是“文义极其鄙俚”,却受到了当地群众的喜爱,也引起了当地曲家的关注,这也是昆曲曲谱《纳书楹曲谱》收录的原因之一。同时“弦索调时剧大都只分段落而无曲牌。这大概是弹唱时可以不受曲牌拘束比较自由地随腔就调”[8]329。弦索调《醉杨妃》除去开头和结尾两支曲牌外,中间大段唱词都是没有曲牌的长短句,中间没有曲牌的唱词是对俗曲唱词的直接借用,是俗曲的演唱方式,所以《醉杨妃》从曲文唱词到“随腔就调”的音乐风格都保留有自由随意的通俗的民间特性。这些特性为早期“贵妃醉酒”在南方不同艺术中流布提供了艺术变革的便利性。
苏州曲家叶堂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刊刻的《纳书楹曲谱》补遗卷中就辑录了《醉杨妃》,并把它列为了“时剧”。从分类上就表现了《醉杨妃》并非是昆曲的传统剧目。时剧《醉杨妃》从人物行当上来看是典型的“小旦、小丑、小生”的“三小戏”,并且唱词通俗易懂,这与昆曲从传奇剧目中挑选的精彩折子戏有着巨大差别。前者是是通俗易懂的民间性艺术的代表,其艺术审美是世俗化的平民观念;后者是经过文人不断打磨提炼的高雅戏曲艺术的代表,表现的是细腻、雅致的文人审美。昆曲这种表演风格的吸收与接纳也是应对“花雅之争”冲击性的体现。
“花雅之争”时期苏州地区的“贵妃醉酒”得到了文人曲家的关注,辑录到《弦索调时剧新谱》和《纳书楹曲谱》中的《醉杨妃》虽是经过修改润色的,但从舞台表演的记录来看依旧是带有民间审美的艺术风格和通俗的美学基调,反映的也是“花雅之争”背景下的大众的纯娱乐审美。市民艺术精神的觉醒赋予了“花部”戏曲强大艺术基因和生命力,并在交流碰撞中给了昆曲以新的艺术变革点。这种艺术生命力在北京舞台上体现的更加清晰和蓬勃。
(二)北京舞台上的“贵妃醉酒”
1.表演风格及审美特点。“花雅之争”时期北京舞台上关于“贵妃醉酒”演出的最早记录是乾隆五十年刊刻的《燕兰小谱》,“双喜官,‘保和部’姓徐氏,江苏长州人,亦隶贵邸,与四喜并宠,歌音清美,姿首娇艳。弱冠后,欣长堪憎,顾景自伤。尝演《玉环醉酒》,多作折腰步,非以取媚,实为藏拙。”[9]49这段记录了双喜官的表演风格和籍贯。双喜官是长州人,长州隶属于苏州府。虽然《燕兰小谱》记录的是北京舞台上的演出,由于康熙、乾隆年间宫廷内府在江南挑选技艺出色的艺人进入南府充当教习,同时“江南织造”也会在节日承应期间选送江南优秀的戏班进京。因此不管是从官方还是民间,不间断的有从江南流动到北京的艺人。作为苏州人的双喜官在这一时期把《玉环醉酒》带到了北京舞台上,也间接的反映出乾隆五十年之前的苏州地区就有“贵妃醉酒”的演出。因此成书于乾隆五十七年的《纳书楹曲谱》补遗卷辑录时剧《醉杨妃》也是对当时苏州地区流行剧目的客观真实反映,只不过经过文人润色修改在剧目名称和曲词上有了变化。
根据双喜官的演出风格可以看出《玉环醉酒》的表演艺术特点。《燕兰小谱》所记录的花部和雅部艺人均以小旦、花旦等行当为主,表演风格以妖艳妩媚为主。雅部双喜官的表演“姿首娇艳”,题诗为“婀娜多姿柳带牵,临风摇荡玉楼前”[9]49。由此可以看出《玉环醉酒》的艺术风格着重表现了杨贵妃醉酒后姿态缠绵、搔首弄姿的情态,从侧面也体现了当时剧坛对“男旦”在跨性别表演上描摹女性婀娜多姿的重“情色”的审美风尚。这一时期是“花雅之争”最为激烈的时期,也是《玉环醉酒》逐渐世俗化、通俗化,乃至低俗化的表演风格形成的时期。
《燕兰小谱》记载的雅部双喜官演出《玉环醉酒》相比于徽班的《醉酒》要稍微早一些。徽班演出《醉酒》最早记录是在乾隆五十六年,也就是四大徽班进京后携带到北京舞台上的。
王芷章编的 《中国京剧编年史》中记录的徽班《醉酒》是乾隆五十六年,“四庆徽班:董如意演《铁笼山》《蛮女》《佳期》《扯伞》《醉酒》”[10]17。 这一时期北京剧坛上徽班演绎的《醉酒》就是乾隆五十五年为庆祝皇帝万寿而携带过来的。成书于乾隆末年的《消寒新咏》记录有广庆部芳官演出《醉酒》。嘉庆八年也有对于徽班的记录,“三庆班:鲁龙官演《审录》《醉阁》,江金官演《审录》《醉阁》《打洞》《弑齐》《思春》。 ”[10]35通过《日下看花记》对于鲁龙官的记录,可以看出《醉阁》的故事内容也是“贵妃醉酒”的故事,“断红映颊,乍转星眸,细落歌珠,轻回舞袖。因忆玉环佳丽,未免肥婢贻讥。而云卿登场,即宠爱三千,何足销其一醉。”[9]168描写的就是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的杨玉环醉酒的故事。其剧目名称之所以改变,应该是为应对当时朝廷屡次颁布的演戏禁令,从剧目名称上规避审查。
关于徽班《醉酒》(《醉阁》)剧目的表演风格也有相关记录。《消寒新咏》中石坪居士评芳官:“观其演《戏凤》、演《醉酒》,不涉风骚,独饶妩媚……”[9]141虽然肯定了芳官在演出中“不涉风骚”,但间接反映了该剧目在其他人的通行的演出中却是以杨贵妃卖弄风骚、妩媚来博得观众眼球的。《日下看花记》对于三庆班演《醉阁》的江金官的表演留有评诗:“更喜身轻似绿珠,醉中争记侍儿扶。回身无力临风软,想见春胸腻欲酥。”[9]174江金官扮演杨玉环刻画了“酒后娇软无力”“春光外泄”“皮肤细腻光润”的形象。《日下看花记》形容鲁龙官演出《打番》《花鼓》等戏,“三庆部。已擅时名……衣块皆若多情也”[9]168,并放在品评的首位,可见受欢迎的程度。《花间笑语》称江金官“三庆部江金官,色艺皆优,若生在乾隆时,亦不在陈银官之下”[10]37。由此可见二人的表演技艺颇受欢迎,但作者以“陈银官”做比,可见二人的表演风格亦多涉及“娇艳”、“淫哇”等特点。这些已经不是表演技巧的描绘,而是对演员表演情态的书写。欣赏的着力点由戏曲声腔、表演技巧转向了如何塑造女性的柔软、抚媚,已偏离了戏曲艺术本身,过渡到了男旦演员对女性情态中风骚、妖冶、妩媚的刻画上。甚至出现了“春胸腻欲酥”的描写词汇,显然已经脱离了戏曲本身,滑向了“情色”“香艳”的娱乐取向。
《醉酒》(《醉阁》)这种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当时戏曲演出环境和大众审美偏向有着直接关系。“迨至五十五年,举行万寿,浙江盐务承办皇会。先大人,命带三庆班入京。自此继来者,又有四喜、启秀、霓翠、和春、春台等班。各班小旦,不下百人,大半见士大夫歌咏”[11]826。戏班中出现了大量的小旦行当,演出剧目有《借靴》、《磨房串戏》、《打面缸》、《小上坟》、《玉堂春》、《戏凤》、《思春》、《背娃娃》等,这些剧目以小旦为主体,载歌载舞、唱念并重,而且有些剧目在表演上雅俗共赏,宣教色彩淡化,娱乐性的强化使得大众的审美感情获得前所未有的宣泄,这是市民审美的解放和觉醒。市民阶层的审美觉醒与士大夫阶层不同,前者自身就缺少道德和礼制的约束,加之商业利益的刺激,“花部”一些剧目迎合、取媚于为他们提供经济利益的市民阶层的观众,戏曲剧目很快就走向了低俗淫秽的风格。而文人著的《燕兰小谱》《消寒新咏》《日下看花记》等书中都对这些男旦的表演特点、擅演剧目给予了品评,其品评集中于男旦的 “色”“艺”两方面,而且品评语汇偏向于“娇艳”“风韵”“妩媚”“放浪”等低级审美趣味,也很好的证明的戏曲审美的变化。
《醉酒》(《醉阁》)所处的戏曲生态是以“花雅之争”且“花部”完胜为背景而形成的,“花部”的胜利也宣扬了蓬勃昂扬的市民娱乐文化的崛起,同时戏曲作为文化产业进入到城市中开始参与商业的繁荣,处于这种戏曲生态中的《醉酒》(《醉阁》)为攫取经济利益最大化在表演上有意识的迎合市民审美,进一步强化了通俗、低俗、媚俗的表演特点。
2.剧目流变路径探析。北京舞台上“贵妃醉酒”故事演出的来源问题分两种:一是徽班《醉酒》,一是雅部双喜官的《玉环醉酒》。徽剧于明末清初在安徽南部的安庆、徽州一带发展形成。其声腔组成在不断变化之中得到了完善,“最初所用腔调为徽州腔、青阳腔……到了清初……首先是创造梆子腔、乱弹腔的唱法。以后……又和兴自枞阳的弦索调及由枞阳腔发展而成的石牌腔(俗称吹腔)混在一起,成为徽班的主要唱腔。”[10]2从形成的地域以及声腔的变化过程来看,形成并发展于安徽南部的徽剧继承了该地区的青阳腔,因此作为青阳腔剧目的《杨妃醉酒》自然被徽剧所继承,并随着徽剧声腔和审美风尚的变化而不断传承革新。“贵妃醉酒”故事一直存在于安徽南部声腔系统中,同时跟随戏班的流动而不断向外散,这也为苏、扬地区艺人学习“贵妃醉酒”提供了可能性。
雅部双喜官虽然是唱昆曲的,但他演出的《玉环醉酒》却不是继承自昆曲传统剧目。昆曲北上后的境遇并不理想,“雅旦非北人所喜。吴、时二伶兼习梆子等腔,列于部首,从时好也。”[9]21“昆曲非北人所喜,故无豪客,但为乡人作酒纠而已”[9]32,昆曲艺人为了改变这种境况,一是学习当时流行于京城舞台上的秦腔、京腔等的剧目;二是上演本就流行与江南地区受欢迎的时剧或花部戏。双喜官演出的《玉环醉酒》应是流行于江南地区的花部小戏,是徽班原有的戏曲剧目。首先,地缘因素导致戏曲的频繁交流。由于苏、扬地区与徽南地区距离较近,地水网密布,交通往来频繁,又同是戏曲演出的繁盛之地,该区域的戏曲存在交流的混杂性和必然性,因此也促进了不同声腔和剧种在该区域的迭代更新。李斗《扬州画舫录》就记载该区域戏班流动盛况,正是在这种交流的过程中安徽南部的各种声腔和剧目流布到了苏、扬,为赢得演出市场,苏、扬地区的伶人争相学习“花部”戏曲,并且遭到了江宁巡抚费淳的禁令。其次,表演艺术的一致。从上文《燕兰小谱》《花间笑语》《日下看花记》等记录的表演风格来看,双喜官的《玉环醉酒》与鲁龙官等徽班演员的表演风格、表演行当具有统一性和相似性。最后,剧目名称的承袭性。徽班戏曲剧目都有简称的习惯,例如《戏凤》《狐思》《打杠》等,《醉酒》应是对《杨妃醉酒》或《玉环醉酒》的简称。从最早的青阳腔称作《杨妃醉酒》到徽班的《醉酒》,再到双喜官演出称作《玉环醉酒》,剧目名称上有明显的继承痕迹。这与《弦索调时剧新谱》和《纳书楹曲谱》中的《醉杨妃》剧名有着明显区别。
所以说双喜官演出的《玉环醉酒》应该是承袭自安徽南部的徽剧,只不过双喜官进京的时间早于徽班,因此被较早的携带到了北京的舞台上,同时也证明在安徽南部和苏、扬地区在乾隆五十年之前就有“贵妃醉酒”的演出,且徽班的《醉酒》传承更加古老和明晰一些。
三、《醉酒》在北京舞台上的消失
(一)清政府政策的打压
由于男旦表演大多呈现了妖艳妩媚、淫秽放荡的特点,使得清政府提高了对于戏曲演出的约束,仅乾隆、嘉庆两朝就颁布了多次禁令。上文提到的《醉酒》改《醉阁》就是戏班应对这种戏曲禁令的一个缩影。
乾隆三十九年,魏长生进京演出,被称为“靡靡之音”的秦腔风靡京城,以一出《滚楼》“艳”压菊坛。也正是淫秽糜烂的风气招致了乾隆四十九年的戏曲禁令,秦腔因此被禁,魏长生被驱逐出京。随着乾隆末年花部戏曲的繁盛,以“男旦”为主体形成的淫哇、放荡的表演风格再次招致了政府的禁令。嘉庆三年颁布谕旨:
……乃近日倡有乱弹、梆子、弦索、秦腔等戏,声音既属淫靡,其所扮演者,非狭邪媟亵,即怪诞悖乱之事,于风俗人心,殊有关系。此等腔调,虽起自秦、皖,而各处辗转流传,竞相仿效,如苏州、扬州,向习昆腔,近有厌旧喜新,皆以乱弹等腔为新奇可喜,转将素习昆腔抛弃,流风日下,不可不严行禁止。嗣后除昆、弋两腔,仍照旧准其演唱,其外乱弹、梆子、弦索、秦腔等戏,概不准再行演唱。所有京城地方,着交和珅严查饬禁,如再有仍前演唱者,惟该巡抚、盐政、织造是问,钦此,钦遵。……今钦奉谕旨,饬禁森严,即应先令民间概行摈弃,不复演唱,则此种戏班无技可施,不致辗转流传,竟相仿效。除行司转饬查禁,如系外来之班,谕令作速回籍,毋许在境逗留。其原系本省之班,如能改习昆弋两腔,仍准演唱外,合亟出示晓谕。为此,示仰阖属军民人等及各戏馆知悉,嗣后民间演唱戏剧,止许扮演昆弋两腔,其有演乱弹等戏者,定将演戏之家及在班人等,均照违犯制律,一休拘罪,断不宽待,各宜凛遵毋违,特示。[12]295
以上文字分为两段,前半段是嘉庆皇帝的谕旨,后半段是江宁巡抚费淳采取的措施。通过这道谕旨可以看出京城和苏、扬两地是禁令的重点地区,由此也可见上述地区戏曲演出活跃,花部和雅部竞争激烈,朝廷鉴于对道德风化和社会风俗的影响,而颁布了禁演的谕旨。江宁巡抚遵照谕旨制定了实施措施:一是民间戏班自行摒弃,不复演唱;二是外省戏班驱逐出境;三是本省戏班改习昆弋两腔。同年苏州织造也颁布了类似的禁令。一南一北两大戏曲演出重镇都开始禁演或打压“花部”戏曲。加之于嘉庆四年乾隆皇帝驾崩,三年国丧禁止演戏等礼制的归束,徽班在京城难以生存,大部分南返或者解散,徽班的南返也使得演出剧目退出了京城舞台。
嘉庆四年谕旨,以八旗子弟流连于戏园,造成行为举止浮荡、生计困难为由,禁止在内城里开设戏园。谕旨不仅压缩了戏曲演出的场地,也约束了有“钱”、有“闲”的八旗观众,戏曲演出市场受到了挑战。嘉庆十二年谕旨,“凡遇斋戒和举行祭祀之日,要停止演戏”[10]46,又对戏曲演出的时令和节日作出了规定。嘉庆十八年颁布谕旨,禁止演出武打戏。从嘉庆朝的几道谕旨来看,虽然不再大规模禁演某一声腔,某一剧种,认可了“花部”戏曲在京城的存在,但对徽班的演出生态和演出市场都造成了影响,也对“花部”戏曲的表演风格、表演内容、表演场地等不断提出约束,“花部”整体的演出环境出现了收紧的状态,从侧面也催动了“花部”戏曲对演出剧目和表演风格的调整。
(二)演员个人因素
《醉酒》在京城舞台上的消失,除了上述政策导致的戏剧环境的变化外,演员的个人因素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条件。最后一次关于“贵妃醉酒”的演出就是嘉庆八年鲁龙官、江金官演出的《醉阁》,鲁龙官和江金官在嘉庆十一年之后就没有出现在京城的徽班中。成书于嘉庆八年的《日下看花记》记载“鲁郎以完姻暂归”[9]169,因成家而南返。根据当时结婚年龄也可以推测出鲁龙官到了变声期,生理变化不太适合舞台演出了。加之于清廷对花部戏曲的表演风格有所约束,而鲁龙官已经成婚,在演出环境变化、演员生理变化、个人家庭因素等影响下,再次南返回原籍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关于徽班表演《醉酒》(《醉阁》)的记载相比于其他剧目并不是特别多,呈现零星分布的特点,《醉酒》(《醉阁》)并不是徽班集中、主要上演的剧目,因此传承上就不会被作为首选剧目,所以说剧目随着演员的南返而消失于北京舞台上也是正常现象。
四、结语
从上述舞台演出的风格变化过程来看,“贵妃醉酒”故事在舞台上一直是保持着“花部”戏曲的艺术风貌。最早的青阳腔《杨妃醉酒》在受众群体上就面向广大民众阶层,曲牌运用、戏剧情节、行当设置都较为简单,而唱词也是通俗易懂,母体所携带的“基因”已经脱离了士大夫的艺术趣味和审美标准。进入“花雅之争”时期,随着戏曲艺术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当时戏曲小旦行当表演艺术的风靡,社会艺术环境进一步滋养了本就生发于民间的 “贵妃醉酒”。这种顺应当时戏曲演出风气,迎合市民审美意趣,维护戏班市场利益而形成的表演风格预示着戏曲作为文化商品的崛起。这一剧目表演风格的变化也是“花部小戏”风格的一个缩影,这种艺术风格一直维持到了梅兰芳改革京剧《贵妃醉酒》。因此针对“贵妃醉酒”表演艺术的溯源,有利于帮我们认识市民视野中的“贵妃醉酒”的审美焦点,同时可以看到“贵妃醉酒”面对早期演出市场的表演风格。
注释:
①因为“贵妃醉酒”的故事在演化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名字,所以本文以“贵妃醉酒”来指代这一故事,并不指代具体剧目名称。如论述在具体声腔、剧种中的变化,将以带有书名号的具体的剧目名称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