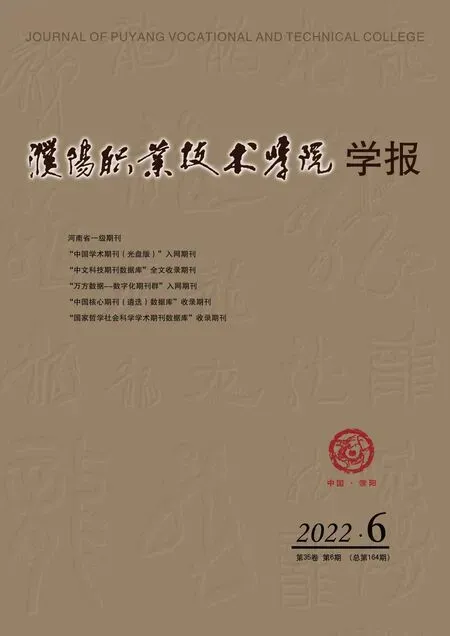陈思和“民间”理论的生成与实践
2023-01-05贺燕燕
贺燕燕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省 兰州市 730000)
陈思和1994年于《上海文学》发表《民间的沉浮——对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首次提出了“民间”概念。之后他在《民间的还原:“文化大革命”后文学史某种走向的解释》《理想主义与民间立场》《都市里的民间世界:〈倾城之恋〉》《莫言近年创作的民间叙述》等文章中先后阐释了“民间”概念的内涵并进行具体的批评实践。该概念作为批评范畴提出后,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改变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和方向,至今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陈思和后来提出的一系列颇有影响力的概念,如“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共名与无名”“潜在写作”等都或多或少地与“民间”有一定的联系,有些甚至是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对“民间”这一关键词的研究和理解,对分析近20年来现当代文学批评研究的路径变化有着莫大作用。“民间”一词的内涵不是确定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地调整、扩张,在文学批评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也产生了概念边界不明而过度泛化的问题。如何更好地发挥其批评实效,把握其使用的界限,是需要我们关注的重点。
一、“民间”理论的概念流变
“民间”概念的提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酝酿到成型的过程,通过梳理陈思和的学术研究史可管窥一二。1987年陈思和于“牛犊丛书”中出版了《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一书,他认为应该打破将重大政治事件作为划分文学分期标准的传统,建立新的现当代文学贯通的宏观视野。这为民间话语在文学史上的建构奠定了理论基础。陈思和在《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一文中具体探讨了知识分子庙堂意识、广场意识的失落及岗位意识的兴起,“民间”概念即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在剖析中国宏观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为建构民间话语提前做了准备。1994年,陈思和在《民间的浮沉》一文中首次提出“民间”这一概念,将其放在“民间文化形态”里理解,认为“是指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已经出现,以其自身的方式生存发展,并且孕育了某种文学史前景的文化空间”[1]68。这篇文章虽然强调了“民间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1]72,但是陈思和对此没有过多言说,只是重点挖掘抗战至文革文学史中取材于民间的民俗要素,即来自中国民间社会主体农民所固有的文化传统,强调民间文化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此时的民间文化形态含义比较简单,大体指现实农村社会的风土人情。
陈思和强调“民间”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在《民间的还原》一文中进行了具体的阐释。他认为“民间”包含着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是指根据民间自在的生活方式的向度,即来自中国传统农村的村落文化的方式和来自现代经济社会的世俗文化的方式来观察生活、表达生活、描述生活的文学创作视界。”[2]59这是他在早期批评实践中对民间着重强调的一点。“第二是指作家虽然站在知识分子的传统立场上说话,但所表现的却是民间自在的生活状态和民间审美趣味,由于作家注意到民间这一客体世界的存在,并采取尊重的平等对话而不是霸权态度,使这些文学创作充满了民间的意味。”这是后来对民间在物质实体层面上进行的形而上的延伸。他更倾向于认为民间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是一种创作的审美元素,一种当代知识分子的新的价值定位和价值取向。在《理想主义与民间立场》中,陈思和指出:“‘民间’不是专指传统农村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其意义也不在于具体的创作题材和创作方法。它是指一种非权力形态也非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形态的文化视界和空间,渗透在作家的写作立场、价值取向、审美风格等方面。”[3]1在《莫言近年创作的民间叙述》中,他赞同王光东把民间划分为三个层次,即“现实的自在的民间文化空间”“具有审美意义的民间文化空间”“知识分子的民间价值立场”[4]207。这三者在文学创作中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后者是将前两者联系起来的媒介,在现实民间的基础上经由作家的选择、体悟最后以文学的审美形态呈现出来。所以陈思和提出”民间”概念的重点还是在于知识分子立足于民间的审美取向和价值取向。他所推崇的从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开始的“新历史小说”即是在主流的意识形态之外重新建构的拥有一套新的价值标准的民间语境。他一再强调此“民间”离不开文学和文学史的范畴,是文学作品中的民间文化形态,是创作主体解构时代共名、立足于民间社会的精神结构而形成的审美心理和艺术思维,与此同时逐渐弱化了文学作品中作为创作题材和创作元素出现的农村民俗具体事项在“民间”批评范畴中的价值。
在《民间的浮沉》和《民间的还原》中,陈思和将“民间”限定在农村文化传统之中。到1995年撰写《民间和现代都市文化——兼论张爱玲现象》时,陈思和开始有意识地试图将“民间”概念向都市文化形态推演。都市的社会形态与农村相比有很大的差异性,它变化迅速,充满流动性、不稳定性,没有集体固守的文化传统,也缺乏代表民风民俗的历史遗物,民间在都市里更倾向于是人们对都市悠久历史的集体无意识,是一种记忆性的存在。所以陈思和认为都市民间的文化形态是“虚拟性”的,“现代都市文化这座金字塔的‘底’,只是一种呈现为‘虚拟’状态的价值立场”[5]62,这是一个纯粹的文化概念,没有固定的社会群体、历史传统,是处在都市的知识分子生于斯长于斯受传统和现代双重浸染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立场。陈思和认为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金锁记》、王安忆的《长恨歌》是都市民间文学的代表,对上海的生活、上海的人有细致的描写与刻画,在历史与现代的碰撞中保留着老上海的底色。陈思和的都市民间有一个本质特征,即个人主义的自由自在的生命形态,张爱玲的华丽传奇中的苍凉、王安忆琐碎日常中的真实,都带有独特的个人风格。都市没有固定的文化传统,各种破碎的民间碎片深藏于居民的记忆当中,必然是个性化的,残缺不全的,陈思和将这种非同质性的特征用虚拟性的文化记忆来表述。笔者认为“都市民间”这一概念的提出具有现实的基础,都市在日新月异地发展,但是城市的底色、历史的记忆仍会被保留下来,所以书写一个城市自有其独特的风味与传统文化特色。但用“虚拟性”将都市民间纳入“民间”的范畴,使农村与都市平行联系,实在牵强,二者之间的文化传统没有必然的联系,都市有独属于自己的一份历史底蕴,有自己特有的文化品格和地域传统,当然在每个人的体悟里有别样的风味,自由地言说比强加一个虚拟性可能更合理。
“民间”概念的提出是在新时期社会变革和学术转向的特殊历史文化语境中产生的,它敏锐地呼应了寻根文学的兴起,为重写文学史提供了内在的脉络线索。它自提出后,内涵日渐丰富,从创作元素到价值立场、审美取向,从农村到都市,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展现了较为宽广的理论阐释空间。
二、“民间”理论的批评实践
在文学批评实践中,“民间”理论具有较强的阐释能力,为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拓宽了学术发展的空间,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民间隐形结构、民间民俗形态和民间理想主义是“民间”理论作为批评范畴的三个关键阐释维度,厘清三者的内涵与批评路径对对文学作品的解读至关重要。
(一)民间隐形结构
“民间”话语在抗战至文革阶段文学史重读方面实现了具有现实意义的突破。“民间”概念最初直接针对的是抗战到文革阶段的文学创作,因而在这一阶段历史文本价值的重评上,“民间”概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陈思和“民间”理论提出之前,对于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有一个基本认识:即它们是国家意识形态、时代共名影响和约束下的产物,政治色彩浓厚、以歌功颂德为主,相比于审美价值来说,它们更关注功利价值。而民间隐形结构的提出,摆脱了这一枷锁,陈思和据此着力挖掘这些文本中潜藏的充满艺术魅力和生命活力的民间因素,别出心裁地找寻其吸引读者的深层次原因。在这个意义上,这一理论具有重大的价值。
陈思和的“民间隐形结构”主要针对的是文革时期样板戏和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这些创作在故事主题内容上鲜明地展现了政治意识形态的特征,但在隐形结构即艺术审美上还潜存着民间文化的样态,这也是它们能够长期流传的重要原因。比如《沙家浜》中的“智斗”,表现了中国民间传统文艺中“一女三男斗智”的隐形结构模式;《红灯记》中的“赴宴斗鸠山”这场戏中有“道魔斗法”的隐形结构模式。在这些主流意识形态完全控制的样板戏中,民间文化形态无法自在地展现出来,只能以民间隐形结构进行隐晦地表达。
在十七年文学创作中,民间因素碎片化地渗透在作品中,巧妙融合在时代主流和政治意识形态中,增强了作品的生命活力。如小说《林海雪原》中穿插的民谣:“奶头山/奶头山/坐落西北天/山腰有个洞/洞里住神仙/山顶有个泉/泉有九个眼/喝了泉里水/变老把童还。”在文本中穿插进民歌是“十七年”革命文学创作中的一种突出的艺术手段,《红日》《苦菜花》等作品中都有用到。除了使用民歌外,运用生动活泼的民间语言,也是十七年文学作品中民间审美因素的潜在体现。《山乡巨变》中多处使用了具有民间趣味的方言:“流水”表示常常,“黄竹筒”指黄鼠狼,“舞”是弄,“混”是聊天,“搞信河”指乱来,“裤包脑”指见不得世面的人,等等。此外,人物的塑造也是不容忽视的一点。《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和栾超家,前者是智勇双全的革命战士,是主流意识推崇的理想人物,栾超家身上带有民间的草莽气、粗俗性格,二人的性格互为补充,这样人物才更加真实,更加富有生命力。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吃不饱这些农妇形象塑造得比高大全的主角更加饱满、更富有艺术魅力,这就是民间因素存在的意义。民间文化形态以隐形结构渗透在文本中,在时代共名的强大压力下,变换面貌、化为碎片潜藏在字里行间,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作品在政治意识形态过度介入下形成的公式化、刻板化与肤浅化的文风,为文学作品增添了别样的魅力,吸引了读者阅读的兴趣,使其拥有了长久的艺术生命力。
(二)民间民俗形态
民俗形态阐释立足于现实的自在的乡土社会,是为了更加有针对性、学理性地解释新时期文学作品中书写特定地域的民俗文化的创作而在“民间”理论视域下形成的一种批评维度。民俗文化是最能展现民间风情世貌的,存在于民间大地上的包括习俗、伦理、传说、遗迹、语言、服饰、典章、制度等沉淀在集体无意识和与民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或具体或抽象的社会生活的沉淀物。透过文学作品所描写的存在于民间的民俗文化,往往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历史横截面,看到社会发展的年轮。新时期文学创作经历了拨乱反正后,寻根文学兴起、乡土文学复归,作家积极在乡土社会中寻找故事素材和创作资源,意图在对民俗事项、风土人情的描写中,更好地反映社会生活和历史面貌,这对于“表现民族精神、反映社会变迁、揭示民众心理、深化小说主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6]108。在新时期文学创作中,以汪曾祺、贾平凹、古华、韩少功等为代表的作家都深深植根于自己生长的故土,通过对自己故乡民风民俗的描写,来展现时代的变迁和历史的发展,体现了其对民间故土的深情厚谊。民风民俗是支撑乡土小说创作的重要文化资源。汪曾祺十分擅长描写民间淳朴、真切的民风民俗,在《大淖纪事》《受戒》等小说中,他悉心描绘了江南农村小镇美好的风土人情。他对风俗很感兴趣,他觉得那很美,它“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6]108。他描写乡土风俗的小说洋溢着和谐闲适之美,在诗情画意的生活下孕育了人性之美和人情之美,令人心向往之。在小说《大淖纪事》中,汪曾祺用平淡的语言勾画了如诗如画的山水风光,表现了淳朴善良的人情:“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夏天,茅草、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大淖这里,一年四季,风景旖旎秀丽,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淳朴善良,互帮互助。巧云遭遇强暴,没有惹来众人的非议与中伤,而是为她抱不平。为了促成巧云和十一子终成眷属,人们都给予帮助,最终还是美好善良的人性战胜了现实的邪恶力量。通过巧云与十一子的爱情故事,作者展现了一众大淖人的勤劳、质朴、爽直和真诚的美好人性。贾平凹在新时期陆续发表了商州系列小说,包括《商州初录》《商州》《浮躁》等,这些作品以商州特定的民情风俗表现该地古老的地域风情,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和历史文化色彩,同时展现了现代化进程中旧有的生活秩序和观念形态发生的变化,愚昧与文明、野蛮与进步的剧烈冲突,揭示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命运,在书写传统与历史时注入了当代生活的内涵。他的长篇小说《秦腔》将传统的民间戏剧艺术——秦腔贯穿在几代人的命运中,是小说的内在结构因素,大量唱词曲谱被引入小说中,具有象征意义。小说通过写人物面对秦腔的不同态度来展现其衰落再获得新生的命运。夏天智对秦腔充满热爱却仅停留于欣赏的水平,无助于秦腔的发展;夏中星作为剧团团长,将秦腔作为升官的工具,最终导致剧团的落败;白雪为了热爱的秦腔艺术放弃了家庭、爱情及大城市的优越条件,选择留在乡下,在村民的婚丧喜事上组织秦腔演出,使真正热爱秦腔艺术的引生一辈农民接受它传唱它,从而使秦腔艺术重新回到真正的普通民众当中,在民间重新获得生命活力。小说以强烈的态度折射了当下传统文化在流行文化的冲击下日渐式微的处境,讽刺了那些为振兴传统文化而采取的不合理的政策,指出了一条重回民间的路径,真正与民间社会结合,使得传统民间艺术重新焕发自由自在的精神活力。贾平凹是土生土长的商州人,当地的民风民俗、文化传统深深浸染在他的血液中,他将熟悉的民间传统文化作为自己写作的资源,同时与当下社会紧密结合,探索民间传统文化的命运及小说民族化的道路,将民间风俗文化融入到文学创作中,使作品具有了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民族特性,使读者从新奇丰富的民间风俗文化中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获得独特的美的感受,深刻理解作者深蕴其中的思想内涵及其流露出的民间情感和民间精神。
(三)民间理想主义
民间理想主义指涉的是一种新的叙事立场,这种理想主义不是传统的仁义道德,不是现实的人生理想,而是作家站在民间立场上对民间进行审美性解读,充分表现民间自在的生活状态、强劲的生命力以及丰盈的情感。这一概念的提出,针对的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一批歌颂民间理想的作家的创作现象,其中“以莫言、张炜为代表的作家,以他们对土地的特有理解和敏感而深厚的乡村生活经验,对乡土人生进行着诗性的解读。他们在小说中试图构筑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乡土世界,在大地、苦难、生命等关键词的运用和解读中昄依民间的诗性哲学,在探究人类生命本质和生命本原意义的过程中,实现对乡土的审美批判”[6]45。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及90年代,一部分作家摆脱时代共名的束缚,从五六十年代的狂热气氛中抽离出来,将视角转向民间立场,在民间大地上寻找具有生命活力的精神资源、确立人生的高贵理想。
莫言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具有开创性的一位作家,他以一部《红高粱家族》开创了民间写作。在高密东北乡那一片粗犷、野蛮的乡土大地上,余占鳌、九儿等人展现出了强悍的个性生命力,在苦难中坚韧地活着,他们无视世俗的法律和伦理道德,顺从自己的内心自由自在、无所畏惧、朴素坦荡地生活。我们无法使用善与恶、对与错的二元标准来评判他们的行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完全出于原始的生命渴求,他们鲜活的生命、自由的灵魂在民间社会得到了最真切的展现。正如九儿在临死之前所说:“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叫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已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7]451在九儿、余占鳌以及高密东北乡那一方土地上的乡亲们身上所流淌的就是这热烈奔放的血,这无拘无束的自由的生命精神。莫言在小说构造的民间空间中,把生命精神充分地张扬起来,而这种生命精神又具有民间文化精神的精华,与中国的民间现实和民间文化心理密不可分,从而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本土的、感性的、生命的审美文化空间。
张炜的《九月寓言》与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一样,都是探索在民间的乡土大地上关于生与死、爱与恨、精神与灵魂的感性命题的。但是与莫言所描绘的乡间现实的复杂与沉重相比,张炜的作品多了一份诗意和浪漫。张炜采用了寓言的写法,淡化了时间线索和具体的历史背景,小村完全成为了一个自在的民间社会。小说的结尾,小村故事到达了终点:地下煤矿塌方,肥和挺芳私奔,小村的人、事的结局没有被直接描写出来,最后一幅神奇的图景出现在眼前:“无边的绿蔓呼呼燃烧起来,大地成了一片火海,一匹健壮的宝驹甩动鬃毛,声声嘶鸣,尥起长腿在火海里奔驰。它的毛色与大火的颜色一样,与早晨的太阳也一样。天哩,一个……精灵。”[8]256小村历史可用“奔跑”和“停吧”的意象来涵盖。一旦由“奔跑”转化为“停吧”,便是善良渐退,邪恶滋生。于是有了男人摧残婆娘,恶婆杀媳妇,也有了男人间的自相残杀,而且人的生命力逐渐萎缩。小村的故事就是一个寓言,有流浪与还乡的冲突,有人性与兽性的搏斗,有善良与邪恶的冲突,也有保守与愚昧对社会进程的阻碍,一切冲突都可归结为“奔跑”与“停吧”的转换。小村最终在矿难中毁灭,同时是一场新生,宝驹腾飞喻示着小村人将在流浪中重新焕发蓬勃的生命力。张承志的《心灵史》赞颂了信奉伊斯兰教的哲合忍耶教派的回民的坚忍与纯真。不同的作家生活的地域不同,对民间的感知也是不一样的,所书写的民间也是多样的,表达的理想精神更是丰富多元的。从作家对民间的理想主义描写中,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坚韧,人性的力量。拨开外在的纷杂,书写蕴涵于民间的内在精神力量,激发生命的活力,是作家民间书写愈加深刻的表现。
在不同的时代,“民间”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从民间隐形结构到民间民俗文化到民间理想精神,“民间”首先是作为创作元素潜藏在文本中、然后成为一种现实文化空间、最后成为理想的价值立场,“民间”的涵义逐渐丰富,人们对“民间”的认识越来越全面、理解也愈加深刻。作家通过描写民间确立理想的生存方式和价值取向:这生存方式是与乡土民众在苦难的日常生活中所表现的积极乐观向上的心态紧密相连的;这价值取向中含有着真正的民间精神——即人们在与残忍的命运的抗争中所坚守的坚韧、善良以及追求自由的生命活力。
三、“民间”理论的含混及泛化
“民间”理论自提出后,因其内涵的开放性、包容性和丰富性有着广阔的文学批评空间,得到了研究者的普遍认可。但物极必反,宽广的阐释空间背后隐含的危机便是概念的矛盾性、笼统化与阐释效力的下降,所以该理论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时常伴随着质疑与争议。
“民间”概念自提出后,其内涵一直在不断延伸丰富,结果造成了概念前后的矛盾含混。通过梳理陈思和的“民间”理论内涵可以发现,它其实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现实的藏污纳垢的民间世俗形态;二是立足于民间的审美取向和价值立场。前者是形而下的客观世界,后者是形而上的主观世界。早期提出“民间”概念是针对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和样板戏的,这时的“民间”是指客观存在的民风民俗,是一种融入文学创作的元素。而到分析八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时,“民间”就成为一种当代知识分子的新的价值定位和价值取向。这两个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世俗的现实民间,一个是理想的审美空间,二者分别用在不同时期的文本阐释上,但陈思和却将其统一在整体的“民间”概念上,造成了概念的前后矛盾和混乱。陈思和面对争议也做过回应,“现实的自在的民间只是我们讨论的民间文化形态的背景与基础……我始终把关于民间的讨论限定在文学和文学史的范畴里进行。所谓现实中的民间文化空间与知识分子的民间价值立场,只有它们成为一种文学性的想象以后,才是我们讨论的对象。”[4]209他一直坚持自己的“民间”是文学形态的民间,是形而上的精神空间,是创作主体拥抱民间拒斥权力意识形态的审美立场,而不是现实的民间,但是不可否认前期的民间隐形结构对潜存在文革及“十七年”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民间审美因素的挖掘是建筑在现实民间基础上的,这文学的民间和现实的民间在陈思和批评实践与内涵阐释的前后不一中令人感到含混不清。
“民间”理论在文学批评实践中有着较为广泛的应用,但也因过度使用而泛化,特别是在当代文学作品的评论中,几乎只要是与政治意识形态、权力意志相偏离的文学题材和形象,都会被冠以“民间”之名。“民间”理论被纳入文学批评实践之后,逐渐演化出不同的阐释角度,前文提到的民间隐形结构、民间民俗形态、民间理想主义都属于这一范畴。当“民间”从一种农村文化形态,演变到都市话语再到知识分子主体的价值立场、审美取向时,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被囊括进这一批评体系,一个重要原因是陈思和对“民间”概念的不断调整和修正导致了理论的泛化。基于“民间”理论的批评文章在近20年来的学术产量是极为可观的,这些文章中存在着很多极具创新意义的学术见解和文学发现,尤其是关于抗战至文革时期的文学以及莫言、贾平凹等自觉以民间为写作立场的当代乡土作家的批评实践。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民间”作为批评话语过度使用而造成的泛化问题。出现在各种核心期刊上采用“民间”批评范畴的研究文章,囊括了20世纪中国相当规模的重要作家:周氏兄弟、老舍、萧红、叶圣陶、沈从文、张爱玲、赵树理、周立波、柳青、汪曾祺、张承志、莫言、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韩少功、尤凤伟、张炜、余华、刘震云、迟子建、阎连科、王安忆、池莉……这样大规模的学术生产,总体来说都是从价值立场、艺术风格、审美心理、主题类型、文化意蕴和精神内涵等角度切入来挖掘现当代作家作品中的“民间”元素,“民间”理论在相当意义上成为了一个超级能指,只要是不关涉宏大历史叙事、与主旋律相左、打破政治意识形态的作品,书写农村社会的乡土小说、描写小人物喜怒哀乐的底层写作、突出创作主体素朴的民间审美取向的新历史小说、武侠小说、网络小说等大众流行性文学都被纳入“民间”话语体系。
“民间”的含混、泛化使其成为一个很笼统的学术话语,这无疑会削弱理论阐释的独特性,明确该概念的边界应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根据笔者的思考,“民间”理论主要还是针对描写乡土社会的文学作品,无论是40年代以赵树理、丁玲为代表的解放区文学、新中国成立以后十七年的小说作品、文革时期的潜在文学创作,还是新时期颇具影响力的寻根文学、复归的乡土文学,都在“民间”的批评视域之内,这些作品都是以书写农村的风土人情、民俗物象为背景的,在此前提下运用“民间”理论对其进行分析,从具体的民间世俗生活升华到民间蕴含的内在精神力量、文化意蕴,由表及里,由外到内,形成了“民间”批评的常规路径。中国自古以来是个传统的农业社会,人们的骨子里传承着乡土世界的文化基因,对农村、农民、民俗文化有着天然的亲切感,文学创作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农村题材,“民间”理论的提出符合人们的心理期待与民族性的潜意识,在中国的社会现实与历史文化空间里有极大的适应性。提起 “民间”,一般就会下意识想到乡土农村,但不可否认都市也是民间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使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都市越来越同质化,然而每个城市依然保留着自己独有的文化品格,有着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市民阶层也展现出不同的精神面貌,这些在都市文学中也有所体现,可以将那些本真地书写都市文化风貌的作品纳入“民间”的批评范畴之内。无论农村还是城市题材的作品,只要真实地、原生态地、素朴地描写特定区域的民间世俗生活,便可以在“民间”理论视野下展开批评研究。其实不需要为“民间”持续追加复杂内容,大道至简,将其还原为最本真的、最原生态的民间生活,着眼于民间社会的具体文化样态,立足于现实的民间,再去延伸到人情风貌,也许这样的理论会更实在,更具清晰的边界感和更为实用的批评价值。
最后需要谈到的一点是,陈思和提出“民间”理论的初衷是为了打破政治意识形态的垄断,这造成了民间与官方二元对立的状态,使用“民间”话语进行文学批评时往往不涉及甚至有意识地遮蔽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其实随着时代的变迁,二者在新的历史时期、在特定的条件下有融合的可能性,尤其是在国家奋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乡村的当下,一系列反映新农村建设的文学作品正在相继面世。此时,“民间”理论面对着那些宏大历史叙事与乡土微观社会书写、弘扬社会主旋律与保持民间本色相结合的文学作品,可以与时俱进,进行理论更新,将官方与民间和谐地相融在一起,适应现实社会发展的要求和文学自身的发展状况,以更好地发挥批评实效。
陈思和在时代的转折期提出极具创新性的“民间”理论,表明他对文学发展中出现的新的创作因素极具审美的敏感性,这是一个知识分子保持主体性、坚持独立思考的结果。这一理论的提出是落实其“民间学术岗位”的具体实践,展现了一个人文学者对学术的高度责任感和对社会的深刻关切。“民间”理论的提出为构建中国理论批评话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重写文学史、建设新文学整体观提供了方法路径,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有重要的影响,它因为理论内涵的不断延伸有着强大的阐释空间,但同时也造成了概念的含混与泛化。应该明确这一理论的边界与批评实践的范围,将其还原到最本真的民间世俗风情也许是保持其解释效力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