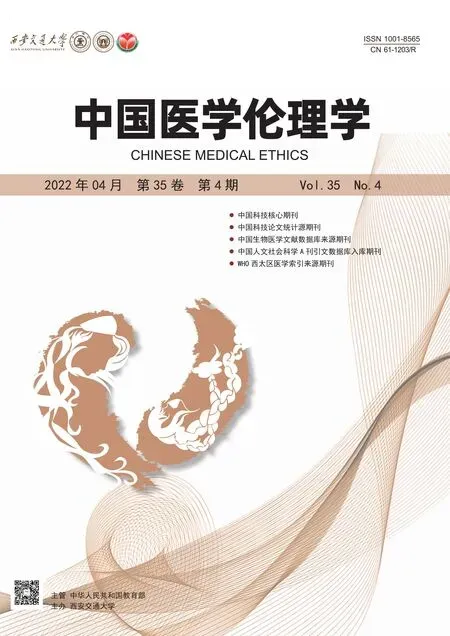关于扩大标准供者肾脏质量评估中的伦理学思考*
2023-01-04聂峰,黄晨,谭庆,胡赟
聂 峰,黄 晨,谭 庆,胡 赟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三医院器官移植伦理委员会,广西 南宁 530021,80958492@qq.com)
肾移植是目前治疗终末期肾病最理想的途径,但肾源匮乏,供求矛盾非常突出。公民心脏死亡后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成为我国移植器官的主流来源后,扩大标准供体(expanded criteria donor,ECD)器官也越来越多地用于移植。ECD由于年龄偏大或存在基础疾病,以及逝世前感染、缺血等常见病变,肾脏质量不同程度受损,而供肾的质量是决定肾移植效果最重要的因素之一[1]。由于DCD供肾质量评估国内外尚无明确统一的标准,目前供肾是否能用于移植仍然依赖于移植医师及其团队的经验[2],此决策主观性较强,且可能受专业以外的因素影响而出现偏差,一旦移植效果不佳或者失败,可能给受者带来巨大的身心伤害和经济损失,甚至使受者付出生命代价。因此,ECD供肾的评估使用不仅是专业领域研究的热点,也应作为器官移植伦理审查的重点。
1 ECD供肾评估
1.1 ECD供肾评估的专业背景
2012年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终末期肾病患者数量约200万[3],2018年,我国登记在册的血液透析人数约70万[4],且仍在逐年增加,对移植供肾的需求相当大。而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6月30日,我国施行器官捐献35 030例,捐献大器官包括心、肝、肺、肾、胰等在内仅103 923个[5]。2017年,美国92 685例等待肾移植的患者,仅33 891例可接受肾移植[6]。为增加捐献器官来源,移植医师不断尝试扩大标准,将年龄高于(含)60岁或年龄为50~59岁但有高血压病史,血清肌酐高于132.6μmol/L或死因为心脑血管意外的供者即ECD的供肾也应用于移植[7]。总体而言ECD供肾质量不够理想,移植后早期效果或长期存活率均不如标准供者(standard criteria donor,SCD)[8-10],一些早期的研究甚至发现ECD供肾移植术后移植物丢失风险比SCD供肾高出70%以上[11]。但与长期透析相比,ECD肾移植可获得较高的生存质量且费用较低[8,12-13]。因此,ECD是供肾严重短缺状态下可接受的选择。ECD供肾移植疗效的影响因素较多,但供肾质量是决定移植肾功能状态和肾移植受者能否长期存活的最重要因素之一[14]。为了最大限度地应用ECD缓解肾脏供求矛盾,又能合理选择ECD供肾获得良好的移植效果,不少学者都致力于ECD供肾质量评估及其标准制定的研究。
1.2 ECD供肾质量评估的方法和困难
现阶段供肾质量评估主要是排除绝对禁忌症以及供体存在多重耐药细菌、侵袭性真菌、部分病毒等可能引起严重不良事件的病原体感染后,再综合运用大体观察、穿刺活检、供肾危险评分、机械灌注参数、供肾分子标志物和分子诊断工具、活力评估等方法进行判断[1]。相对而言,供者高血压、血清肌酐评分与组织学评分的综合评分对于移植效果的预测最为准确[15]。然而,这些评估方法和工具的预测价值仍不理想[2]。以组织学检查对移植效果的预测效能为例,研究者对UNOS数据库2005—2014年22 006例肾脏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肾小球硬化比例10%以下的占58.0%,11%~20%的占13.5%,20%以上的占19.7%。虽然硬化比例10%以上移植失败风险增加,但患者5年存活率、1年急性排斥和功能延迟恢复的发病率无明显差异,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来确定边缘供肾的使用和改善预后的策略[16-20]。不难发现,将ECD供肾评估的初步印象和移植后的疗效作对比,并累积病例进行总结,再不断修正评估结论、最终建立评估标准,是供肾评估的大体思路和方法逻辑[17]。由于导致供肾质量受损的危险因素较多,临床上ECD常表现为不同危险因素的多样化组合,程度也轻重不一,因此质量评估标准的制订需要大样本和长时间的临床研究才能完成。在此过程中伦理风险客观存在,有的情况甚至较为突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三医院(以下称“我院”)移植团队与器官移植伦理委员会密切协作,探讨规避这些风险的方法。
2 供肾评估应用中存在的伦理风险
2.1 违背“不伤害原则”的风险
我院移植中心在过去10年中,ECD肾移植数量已经接近SCD供肾移植数量。随着我国对交通、施工、灾害等安全事故多发领域治理的持续完善,可以预见,未来DCD中ECD比例将会越来越高。虽然SCD肾移植也不能保证零风险,但移植手术及相关治疗的风险是蕴含于医疗实践之中的客观存在,带有一定必然性。ECD肾移植则不同,从定义上看,ECD的范围宽泛、情况多样,不同国家、不同移植中心之间的临床经验和认识差异决定了ECD标准扩大的尺度也不同[21]。比如来自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供者并双肾血管内血栓形成的供肾,移植成功的报道极少,有研究显示[22]高达33%的供肾移植后原发性无功能,但仍有移植中心将DIC供者且50%肾小球发现血栓,另有15%肾小管坏死的供肾应用于移植。在器官短缺背景下,为了尽可能利用可以利用的器官,供者标准扩大化的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科学合理地选择供者获取器官是成功进行器官移植的先决条件[2],研究者应清醒地认识到,供者标准扩大化的程度与受者承担的风险程度是成正比的,ECD肾移植并发症发生率、移植物失功率、死亡率等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受者及其家庭付出的健康和经济代价,甚至受者生命。医学伦理学中的“不伤害原则”是指在临床诊疗过程中不使患者受到不应有的伤害,移植医师在供肾质量评估中的标准越扩大,就越可能突破“不伤害”这根伦理红线。在评估标准还在研究的过程中,很难避免质量相对较差、在最终评估标准之外的供肾应用于移植,但随着临床经验的逐渐积累,相当多的风险已经可以被预见并避免,移植医师进行质量评估时需要始终努力将移植风险降至最低[23],防止器官移植对受者可能造成的伤害,并使效益大大超过可能的伤害[24]。绝不可出于增加移植数量、积累经验、经济利益等功利性动机,甚至为了满足好奇、博取关注而心存侥幸、放弃原则地滥用连移植医师都没有把握的器官,使受者受到本不应有的伤害。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要求移植医院成立人体器官移植技术应用与伦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伦理委员会”)并开展伦理审查工作[25]。但我国现阶段器官移植伦理审查多侧重于供者的权益保护、受者移植机会公平公正等方面,而忽视了供肾质量评估的伦理审查,而该漏洞则可能导致潜在受者遭受未经负责任的评估的供肾带来的极大伤害。
2.2 忽视“有益原则”的风险
“有益原则”是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之一,要求诊疗活动要促进人们的健康和福祉,有利于人的存在和完善。供肾评估时,移植医生将综合供者和肾脏的一系列临床数据和检查结果,根据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对供肾移植后的效果进行大致预判。那么,达到怎样的移植效果才能视为“有益”?例如,此例供肾移植后主要的肾功能指标血肌酐值下降到什么水平评估者将视其为“有益”或评估合格,200μmol/L还是300μmol/L甚至400μmol/L?再如,热缺血时间较长的供肾可能导致移植失败,那么多大概率会失败的情况下我们会选择移植,10%、15%还是20%?类似问题业内尚无明确答案,现阶段几乎完全由移植医生决定,其决策带有强烈的“医学家长主义”色彩,各种原因导致忽视“有益原则”的情况极易发生。对肝功能衰竭患者来说,“医学家长主义”不仅是有意义的更是必要的,因为如果不选择ECD供肝,患者将随时面临死亡威胁。与肝移植不同,肾移植大多数情况下并非抢救性的治疗手段,医疗决策的“家长主义”不仅要建立在“有益”的伦理原则基础之上,而且医务人员的经验和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现阶段ECD供肾的主观评估仍可能出现偏差,客观上并不能保证移植有益,况且是否有益的判断也多由移植团队作出,较少考虑受者和家属对移植疗效的期待。若移植后肾功能恢复未达到期望值,一方面受者需要频繁地随访检查、调整治疗,从而产生额外的经济支出、精力和时间的耗费;另一方面,还会引发受者失望、后悔、愧疚等不良情绪以及抑郁、焦虑等心理障碍,甚至对医院和医务人员产生怀疑和怨恨情绪。从这个意义上说,供肾质量评估或拟定评估标准必须充分理解和尊重受者对移植疗效的期待,并将其作为重要参考因素。
2.3 不自由的知情同意
伦理学中“尊重人”和“尊重自主性”这一基本原则要求医生贯彻知情同意原则,知情同意原则不仅是为了尊重患者、最大限度地保护患者,也是为了保护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本身。尊重移植受者的知情同意权在原国家卫生部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中已有明文规定。知情同意原则要求受者的知情是充分的、同意是自由的,要确保受者和家属充分了解治疗方案、可能存在的危险及移植费用等并取得其同意[26]。但受者群体由于个体病情、文化阅历、性格心理、家庭状况等条件的差异,对于移植的认知度和期望值也千差万别。而且,捐献案例的出现和手术机会的来临有一定突然性,即使ECD案例已经通过周密的临床论证和伦理审查,但是在考虑时间紧迫的特定环境下,受者作为个体往往会选择拒绝ECD供肾移植。因此,关于告知潜在受者与移植相关的一般风险和特定器官相关的特定风险,一直存在着争论[23]。
3 对策建议
3.1 避免违背“不伤害原则”
我国肾移植专家借鉴国际经验,总结归纳了供肾评估和保存等关键临床问题,通过了建立科学选择供体和合理评估供肾质量的共识[2]。但在公认的评估指南出台之前,落实“科学”“合理”的要求仅依靠移植团队还不够,必须充分发挥伦理委员会的作用,从观念上、制度上、流程上严格落实伦理审查才能保证。为此,移植中心应向伦理委员会全面、详细汇报ECD供肾移植的必要性、个案中特定情形对肾脏的影响及此类供肾应用概况、移植后可能出现的特殊并发症及其防治预案以及受者接受移植后的风险/受益比评估结论[27]。伦理委员会既要重视对器官获取和使用的伦理审查,也要督促医疗机构加强医疗质量管理和对ECD供肾移植受者的随访,还应定期审查ECD供肾移植术后情况的反馈汇报,并将历史案例中移植中心对伦理审查的态度、患者的疗效等作为今后伦理审查结论的重要依据,以此对移植中心进行伦理监督和约束。
3.2 避免忽视“有益原则”
《医师宪章》要求医师必须尊重患者的自主权,患者在了解病情的基础上有权对将要接受的治疗作出决定。只要患者的决定和伦理规范相符且不会导致不恰当的治疗,那么患者的这种决定就极为重要[28]。移植受者对ECD肾移植风险/受益比的期望值显然会高于移植团队,而移植团队面临ECD供肾及其移植效果的不确定性,在作选择时不可避免地包含有临床试验的动机,本身无可厚非,因为ECD肾移植本质上也属于临床人体试验的范畴[24]。因而,伦理委员会应在鼓励医学研究和保护受者权益二者中权衡。如果移植团队对捐献案例中肾脏质量及此类供肾应用概况不作详细评估,对移植后可能出现的特殊并发症及其防治不制定处置预案,对受者接受移植后的风险/受益比没有结论,这样的决策显然是草率和不负责任的,应当予以否决或者要求移植团队补充相应工作。
3.3 如何获得自由的知情同意
为了获得潜在受者自由充分的知情同意,本研究团队已提出了一些办法[27],再补充两点建议:一是将ECD供肾的相关缺陷和相应风险尽量用数据进行说明。由于专业知识有限,受者大多难以通过医生专业性的介绍充分了解ECD肾移植的利弊和风险,难免产生过多顾虑。如果将这些缺陷条件下获得的疗效和风险用治愈率、好转率、并发症发病率、死亡率等指标以数字形式表达出来,患者及家属将更容易理解并作出自主理性的决定。而这些疗效和风险指标既是ECD供肾质量标准确定后移植的结果,也是现阶段拟定ECD供肾质量评估标准的目标基础以及一切以制定标准为目标的临床研究的出发点。二是需要明确受者在群体宏观层面上对这些疗效和风险指标的接受程度,不但将其作为受者个体作出知情同意选择的参考指南,同时也是伦理委员会进行伦理审查的重要依据。知情同意原则的产生有法律背景,强调医务人员有责任和义务向患者揭示一系列核心信息,其中即包括具有现实重要性的和重大后果的风险。医生无法判断某个具体个人最大利益和生命预期的相关价值[29]。因此,研究团队认为应该组织多中心大宗样本的问卷调查来征求潜在受者群体的意愿,从受者整体层面上大致了解其可接受的疗效和风险指标的底线,再结合移植医师专业背景和评估实践,最终将ECD标准限制在某一目标区间。在进行问卷调查时,应对当前ECD器官来源、移植可行性、必要性和局限性向受者进行详细介绍,使之能以适当的心理状态和理性思维来对待调查。
4 结语
随着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和社会文明的协调发展,ECD供肾的评估和应用已成为移植医生以及受者共同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相应的伦理审查也在适应不断变化的伦理环境,采取措施努力规避前述以及其他可能发生的伦理风险。医患之间的关系由于医务人员的知识和权威而不对称,在肾移植领域由于供肾短缺则更为突出。移植受者的弱势决定了移植团队应该用医学专业知识和伦理道德来尽力维护患者的健康和生命,尊重和保障患者的权益,注重为患者提供医学人文关怀,进而实现医患同心合力的理想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