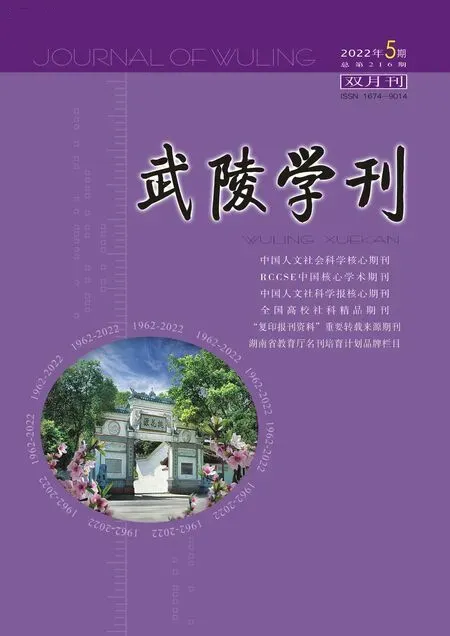北宋王朝对五溪南北两江少数民族的管治研究
2022-12-28王四莲
王四莲
(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宋朝的南方民族关系是民族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马力分别考证了北江羁縻州与南江羁縻州的名目及历史演变[1][2],分析了各大姓之间的利益关系,他还以具体案例解析了诚、徽羁縻州的设置沿革、地理位置及统辖范围[3]。陈曦通过诚、徽羁縻州的区划调整以及城寨置废,一针见血指出了宋朝治理理念中的摇摆性,认为宋廷没有制定长久稳固的方案进而导致边乱不止的局面[4],尤其在熙宁后,宋王朝对南江羁縻州消极的治理理念导致拓边失去主动性[5]。黄义军结合史籍与摩崖石刻剖析了宋初北江彭氏与宋王朝在政治、军事与经济方面的博弈关系[6]。段绪光则从官吏任免、民族关系、田业所有权和赋税、贡赐制度等层面剖析了宋代湘鄂西地区羁縻之制的具体内容[7]。吴永章、刘美嵩、伍新福多角度剖析了宋代羁縻政策与南方各民族关系的历史意义,立足点不同,涉及政治制度、赋税朝贡、军事法治等内容[8][9][10]。此外,刘复生考证了宋代羁縻州制度存在的不完善性[11],唐清明对宋朝处理湖南地区各民族的政策特点进行了总结[12]26。综上,宋代两江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史的研究成果较多,但主要集中于特定时间段或资料记载充足的领域,而宋朝对该地区管治的历史进程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概括。鉴于此,从北宋统治政策层面对南北两江少数民族进行研究,分析王朝与地方关系的具体表现及特点,总结历史上少数民族治理的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契合当前备受瞩目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热点。
一、南北两江少数民族的地理分布与其首领势力范围
北江指沅水最大支流酉水,南江指沅水自辰溪以上的支流。南北两江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现今湖南西部,这一地区地理位置复杂,地形地貌多样,作为宋王朝“南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虽然区域内分布着数量众多的少数民族,但彼此之间的文化特征又存在较大的相似性。“五溪”最早见于北魏郦道元所作《水经注·沅水》一书,后逐渐成为域名,特指湘鄂渝黔四省市边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后汉书》以“五溪蛮”统称东汉至宋代生活在沅水上游的少数民族。“苗、瑶、僚、僮、仡佬”等族群,由于溪谷、河沟众多,“不论生熟界,出观竞渡”[13]。唐宋之际,“五溪蛮”不断发展壮大,一些地方势力纷纷脱离中原王朝,“自署刺史”,形成一姓或以一宗族为主建立的小州县。
(一)北江少数民族
北江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沅陵县以西的酉水流域,最北至澧水上游一带,宋代属溪州,主要涵盖了今湘西州中北部地区。北江少数民族首领即历史上著名的溪州彭氏,古溪州彭氏宗族也是土家族大姓。彭氏不断适应该地区的物候环境,避免与地方土民发生冲突,保持发展,实现长达八百一十八年的稳定统治而巍然不倒。
从相关文献资料可知,五代十国动荡与鼎革的特殊时期,少数民族实力大幅增强,后梁初年溪州彭氏在当地已声名鹊起。当时以今长沙为中心建立的南楚政权是南方十国之一,楚王马殷采取“上奉天子、下抚土民,内靖乱军、外御强藩”的策略,势力不断强大,但在各方势力割据动荡的时局中,政权渐趋薄弱,未能完全控制湘、鄂、渝、黔交界地区的少数民族。其时,辰州西部的溪州一直为地方少数民族酋豪所控,并未归顺南楚政权。后梁开平四年(910),溪州少数民族首领吴著冲败走,彭瑊也因拓边有功被授以溪州刺史一职,经略湘西,逐步统一了酉水流域各部族,开创了彭氏世代经营溪州的基业,直至雍正六年(1728)彭氏土司彭肇槐献土归流才画上句号。后晋天福四年(939),“有彭士愁者出,寇辰、锦、奖,围澧州”[14]。最终彭士愁派其子及诸少数民族首领携锦、奖、溪三州的地图和印信向楚王马希范请降,双方议和缔结盟约、立铜柱铭誓,这便是现存的著名古文物遗存——溪州铜柱。铜柱铭文不仅记载了溪州刺史彭士愁与楚王马希范罢兵盟约的具体史实,而且以铜柱为界承认彭氏据有北江,确定了彭氏溪州刺史的世袭地位。据《永顺县志》记载,溪州彭氏全盛时期的势力范围“东抵荆湖,西通巴蜀,南近辰阳,北据归峡”[15]。
(二)南江少数民族
《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南江,本唐叙州,五代失守,群蛮擅其地……”[16]4872史料记述了后周湖南地方行政军事长官周行逢病死,领有龙标、潭阳、郎溪三县的叙州刺史钟存志奔逃,叙州部分地区则逐渐被地方豪酋舒氏、向氏和田氏割据。这些地区与原三大姓占有的锦州、富州共同为“南江诸蛮”地,而三姓氏族及各统辖区域内的少数民族被称为“南江蛮”。
南江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沅水南岸中游一带,即沅水支流儛水、辰水流域,大致在今湖南麻阳、黔阳、怀化、会同、芷江、通道、洪江和绥宁等地区,分属于不同的姓氏集团势力。谭其骧先生考证:“南江田氏在五季及宋世颇极一时之盛,与舒、向二族鼎足称雄,据有奖、锦、懿、晃四州。”[17]向氏、田氏、舒氏三足鼎立,基本维持着整体性安定,但也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部冲突。舒氏与向氏分别据有南江实力较强大的叙州、峡州以及麻阳富州。宋朝辰州布衣张翘上书:“南江诸蛮虽有十六州之地,惟富、峡、叙仅有千户,余不满百,土广无兵,加以荐饥。”[18]14180南江其余地区生存条件恶劣,人口分布较少。舒氏、向氏实力富强,二者势均力敌,存在众多利益纠葛,长期处在互相制衡与攻伐的不稳定关系中,也因此吸引了宋王朝对南江地区的关注。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中注重稽古求治,即“强调帝王稽考经史典籍与前代一切治世经验”[19],欲在南方地区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联动制衡不同势力。在宋王朝的纵横捭阖治政手段下南江少数民族三足鼎立的局面逐渐瓦解,而原本实力较弱的田氏却得以获得长足发展。可以说,南江田氏势力是一个不断“进阶”的过程,由弱到强发生了“质”的飞跃,传世最久。最终,舒氏、向氏归顺宋王朝,“独田氏有元猛者,颇桀骜难制,异时数侵夺舒、向二族地”[18]14181。
二、怀柔远人:松弛有度的羁縻之制
羁縻之制发端较早。自秦至元明之际,历代统治者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郡县,承认原少数民族首领的地位,“世长其民,世领其土”。羁縻政策涉及两个层面的内容:其一,用政治压力辅之以军事手段对少数民族进行控制;其二,对少数民族给予抚慰,在物质、经济等方面提供一些利益好处,以稳定少数民族、维系中央集权制度为目的,恩威并施、宽柔相济。唐高祖李渊以诏书的形式对羁縻政策进行了明确定义:“画野分疆,山川限其内外,遐荒绝域,行政殊于华夏,是以昔王御世,怀柔远人,义在羁縻。”[20]行政建制采用郡县制度,将某一大姓势力统辖的范围划为一州或者数州,“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洞”[21]。官吏经由朝廷任命,基本上由原部族首领任职,称都督或刺史。所任命的官职可由其家族或宗族内部世袭,形成集团势力,管理一切事务,是中央在地方上的“代理人”。
宋朝初建,为保障少数民族地区安稳,统治阶层更加关注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建隆元年(960),改置羁縻保静州,属荆湖北路。”[22]三年后,宋太祖派兵平定湖南,“得澧、郎、奖、辰、锦、溪、叙等十五州及桂阳监”[18]2093。宋承唐制,吸取各朝代的民族治理经验,笼络地方少数民族首领,完善并进一步发展了羁縻政策,使其成为治国安邦的统治策略,是宋朝统治南北两江少数民族的重要举措。宋朝借助少数民族首领实行统治,“州有刺史,县有县令,洞有洞官”,其下又有头目、小目,在这些地区实行羁縻州县峒制度[9]。
政务方面,职官设置基本类同于其他经制州,各溪峒还专设官员分管各项事务。《宋史》载:“北江蛮酋最大者曰彭氏,世有溪州,曰上、中、下溪……总二十州,皆置刺史。而以下溪州刺史兼都誓主,十九州皆隶焉,谓之誓下。”[18]14177-14178彭氏世据溪州,隶荆湖北路,治所在今永顺县东南旧司城。关于溪峒首领承袭程序与规范,宋王朝有明文规定:“州将承袭,都誓主帅群酋合议,子孙若弟、侄、亲党之当立者,具州名移辰州为保证,申钤辖司以闻,乃赐敕告、印符,受命者隔江北望拜谢。”[18]14178概言之,第一步继承者必须从其直系亲属或者旁系中选出,遵照子孙、兄弟、子侄、亲党的次序;第二步要在临近群酋的合议下推举合适的继承人;第三步经由上级官方审核并上报;第四步得到朝廷的认可,并颁赐敕告、印符等一系列凭证之后方可正式任命。
军事上允许羁縻州首领有自己的兵马。宋朝非常重视在羁縻州沿边地区修建寨、堡等军事据点,置保甲,不仅调派官军,还编练蕃兵、土丁、峒丁等,杂戍以“镇守封疆”。溪州铜柱铭文“本都兵士,亦不抽差”,高度概括了羁縻制度本质上是通过谋求局部安定以权衡并获取整体利益的主要特征。寓兵于农,不纳赋税,地方土丁平时身份为农民,参与耕种和军事训练,叛乱时则从中征调兵卒,从而能迅速有效解决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叛乱事件或军事冲突等。“外夷自相杀伤,有本土之法,苟以国法绳之,则必致生事,羁縻之道正在于此。”[23]宋朝得以集中精力对抗北方不同的强大政权,不至“左顾右盼”。
此外,大姓势力异地牵制也成为两江少数民族地区羁縻政策实施的主要内容之一,有两种主要的表现。其一,势力过盛的酋豪内迁供职。乾德五年(967)冬,“以溪州团练使允足为濮州牢城都指挥使。溪州义军都指挥使彭允贤为卫州牢城都指挥使,珍州录事参军田思晓为博州劳城都指挥使。”[18]14173因团练使彭允足、义军都指挥使彭允贤和录事参军田思晓等人“据山险、持两端”[18]14173,北宋为了防止这些较为强势的、具有军事号召力的溪峒大姓势力煽动地方民众滋扰事端,不间断使手握实权的少数民族豪强势力内迁任职,实际上是通过“调虎离山”尽可能规避潜在的安全隐患,维护地区安定,保障地方统治权益。其二,实施少数民族首领子弟为主的质子邦交。质子制度起源较早,春秋战国至清朝数千年的历史中都有相关的资料记载。北宋天禧(1017—1021)初,下溪州刺史(治今古丈县域东北)彭儒猛及其子彭仕汉纠集“辰州溪峒”各少数民族侵扰宋朝官民。天禧二年(1018),宋王朝第一次对北江地区用兵,最终武力镇压了辰州溪峒“蛮徭起事”,彭儒猛逃入山林,彭仕汉被俘,史称“白雾团之战”。北宋朝廷为牵制下溪州彭儒猛的政治势力,委任彭仕汉为西京右班殿直,实是宋朝控制彭氏的人质,以此避免彭氏诱唆地方民众叛乱,从而增加王朝管治的财力与驻防兵力的投入。北宋王朝借助历史上普遍存在的质子外交,将内地的官职与田业授予两江酋豪子弟或亲属,一则缓和了双方矛盾,再则通过人质实现有效管控地方势力的目的,总体上这一手段利大于弊,一度缓和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综观北宋时期的羁縻政策,它有利于改善南北两江地区大姓势力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减少内部摩擦和纷争,稳定了民族地区,必要的时候能在不分散中央军队力量的前提下削弱地方势力。更重要的是,羁縻制度打破了封闭的状态,促进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多重关系的连结,对推动“大一统”的历史进程起到了不可湮灭的效力。
三、止令和断:立竿见影的经制策略
宋代北部分布着数个实力卓然的政权,在武力攻伐的大环境中,宋王朝疲于应对北方强大军事力量的侵扰,因此在构筑国家安全体系及处理对外关系时主要向北倾斜,致力于加强北部的防卫力量。历任两宋要职的朱胜非曾言:“方今兵患有三:曰金人、曰土贼、曰游寇。”[24]宋廷多次将荆湖南路与荆湖北路的部分驻军调回,并暂停向南的扩张进程,造成区域内管制力量不继,加之少数民族长期受大姓宗族集团力量的管控,所受兵燹战祸相对较少。这就造成该区域内各族群有充足的发展空间,实力得以迅速增强,进而成为威胁宋朝统治的一方势力。雍熙北伐失败以后,宋朝统治者意识到王朝统治范围内政治失序、人心不和,民变频发,“治外必先安内”,而南北拓边方略密切关联、相互促进,切不可偏废,因此宋朝治政策略“向内化”。荆湖南路与荆湖北路作为王朝致力拓边和发展的“南疆”,是少数民族聚居地,长期祸事民乱不断。如何处理区域内各民族与中央王朝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成为宋朝避无可避的重要问题。
北宋天禧二年(1018),彭仕汉从西京潜逃回北江。新任刺史彭儒武状告彭仕汉出逃且在北江地区诱唆少数民族叛乱,彭儒武命其子追杀了彭仕汉,宋朝嘉奖彭儒武并升其职务。这一历史事件实际上反映出地方少数民族大姓内部对权力的争夺,彭儒武对宋王朝的效忠主要是出于谋求自身利益的考量,而宋王朝利用少数民族首领内部存在的不稳定因素,明面上维系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实则暗中支持内部相互斗争与攻伐,从中坐收渔翁之利。“蛮夷相攻,止令‘和断’,朝廷不介入。”[9]此后北江地区规模较小的动乱并未停息,但影响不大。至和二年(1055),北江地区再次因内部权位争斗而陷入动乱,彭仕羲率众数次反叛,边乱久未平息,宋廷一改羁縻抚绥的不介入、不掺和措施,嘉祐元年(1056)委派新官,对地方官员实施“大换血”,采取“招安为上,守御为下,攻取为失”的治边措施。但少数民族势力迅速壮大,忽视诏谕,不听命令。辰州布衣张翘上书:“蛮獠数入寇钞,边吏不能制。”[18]14179由此可见,南北江各少数民族的危害极大,有必要对这一区域进行经制。宋朝逐渐意识到南方地区的开拓和防御也深刻影响王朝的稳固,于是便派遣李参、窦舜卿、彭文思、王绰等人一同率兵讨伐。面对大兵压境,北江少数民族首领陈情力辩,“复贡奉内属”[18]14179,恢复了北江地区阶段性的秩序稳定,但由于彭仕羲为人狡诈,屡次侵扰边界,“边境不宁”现象并未发生根本改变。熙宁六年(1073),“宋廷诏谕北江下溪州刺史彭师晏内附”[16]6058,四年后辖域内的民户依照内地定期征纳赋税,正式成为宋廷的编户齐民。
南江少数民族内部斗争则一直威胁着宋朝“南疆”的安定和发展,北宋中叶朝廷对南江少数民族的管治力度出现强劲势头,“经制诸蛮”成为宋代开边目标之一,“熙宁中(1068—1077),天子方用兵以威四夷”[18]14180。宋神宗恢复对包括荆湖地区在内的南方地区的扩拓与开发,诏谕:“国家疆理四海,务在柔远。顷湖广诸蛮近汉者无所统一,因其请吏,量置城邑以抚治之。”[18]14181熙宁年间(1068—1077)章惇开边梅山,充分了解和认清不同少数民族势力的强弱,以武力征剿和屠杀等手段“经制”南江。他先遣人向懿州、恰州招抚,从实力富强的富、峡二州着手纳土,最后悉平南江诸峒,少数民族首领献土内附。章惇撤羁縻州,置沅州、诚州及卢阳、莳竹二县,派流官统治。宋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4),由于两江地区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风起潮涌,统治阶层内部达成共识,废弃荆湖所新开的道路和新置州县、堡寨等,借以缓和矛盾、维护稳定,自此,“五溪郡县弃而不问”[18]14179。至宋徽宗时期“开边拓土议复炽”[18]14180,羁縻之策得以更新,南江重新设置州县,少数民族纳入了经制州县的管辖,以避免出现地方少数民族首领过于强大的割据政治势力。
“章惇经制南、北江蛮,湖北提点刑狱李平招纳师晏,誓下州峒蛮张景谓、彭德儒、向永胜、覃文猛、覃彦霸各以其地归版籍……诏修筑下溪州城,并置砦于茶滩南岸,赐新城名会溪、新砦名黔安,戍以兵,隶辰州,出租赋如汉民。”[18]14179-14180章惇以武力先后平定了南北两江地区。熙宁六年(1073),彭师晏经由李平招纳而主动献其领地,由宋朝直接统治,并入京接受实权较小的礼宾副使京东州都监职位,此后彭氏所辖溪州一带“赋税如汉民”。忌惮于北宋的武力征服,各少数民族首领自愿内附,承认中央王朝的统治,“南江之舒氏、北江之彭氏、梅山之苏氏、诚州之杨氏相继纳土,创立城砦,使之比内地为王民”[18]14180。
从上述不同历史事件可以看出,两江少数民族地区羁縻制度的实施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统而不治”是本质。羁縻制度将少数民族地区纳入宋朝的统辖范围,但不直接统治,而继续任命少数民族首领管理辖境,尊重不同族群势力的差异,缓和了民族关系,维护了区域稳定。在一定阶段内,部分羁縻州县向经制州县转变,从而实现更有效的治理。另一方面,间接统治存在治理上的断层,中央与地方关系相对松弛,双方存在较多不和谐因素,矛盾极易激化,因而两江地区内部叛乱不止。
相对来说,经制州与朝廷的属隶关系更为紧密,它是由朝廷派遣官吏对地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层面实施直接管理。唐朝时期羁縻州、经制州和藩国已经并存,至宋代羁縻州与经制州出现互相转化的现象。具言之,物质基础积累到一定程度,且历史环境相对成熟时,羁縻州就可能向相对集权的经制州转变;而政局混乱或叛乱不断时,经制州可能降为羁縻州。
四、贡赐制度:正统仁恩的权宜牵制
正统问题既涉及朝代的承继,又牵涉华夷关系的处理问题。就横向历史关系看,朝贡体系往往成为正统性的外显形式,直接关系宋王朝的安全与稳固。宋廷通过不同的制度确立其政治话语体系,体现其“王朝”地位,构建宋朝的统治秩序[25]。
宋朝对地方少数民族政权入贡持谨慎心理。入贡必须按照特定的程序进行。首先,朝廷赐予部分少数民族政权入贡的资格,规定入贡的次数及人数上限,一旦确定后必须“岁奉职贡”[18]14179。其次,获得入贡资格的少数民族政权申请并登记造册,“南江诸蛮亦隶辰州,贡进则给以驿券”[18]14180。驿券作为沿途驿站的通行凭证,由兵部赐予,少数民族首领可持券入京纳贡。最后,少数民族政权向宋王朝纳贡,宋朝视贡物多寡给予回赐。在“统而不治”的羁縻政策下,少数民族地区仍负有一定的义务,如定期朝觐、入贡等[10]140。宋朝在贡赐上限制少数民族赴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贡赐是形式化象征。少数民族政权通过保持与宋朝的朝贡关系,可以在“厚往薄来”的贡赐贸易及商业贸易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26]。一般来说,中原王朝回赐的物资在数量上往往多于贡物,而宋朝也利用迎来送往的朝贡关系惠赐湘西边地少数民族部分稀缺的物质,如食盐等,借此笼络南北两江少数民族。《续资治通鉴长编》载:“上召回巡检使侯延赏曰:‘蛮人何欲?’延赏曰:‘蛮无他求,所欲唯盐耳。’上曰:‘此亦常人所须也,何以不与之?’乃诏谕谓。谓即取诏传告陬落,群蛮感悦,因相与盟约……”[16]1142其二,宋朝能通过回赐彰显实力与威严,既满足了强国虚荣,又维系了宋廷与边地的统治秩序与关系规范,达到“务在柔远”的目的。此外,朝廷常常回赐朝奉者相应的政治权益,或直接封官赐爵,或赐予红巾、锦袄、官服、腰带等代表身份地位的物品。
北宋推行贡赐政策,不断加强与少数民族首领、羁縻州土官之间的君臣关系。朝廷根据与朝贡方的亲疏关系确定不同的贡赐标准,“税上加以区别对待”[8],从侧面反映了朝贡体系下双方较为松弛的关系。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北宋王朝还将贡赐制度作为一种特殊的惩戒形式,《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盖自咸平以来,始听溪洞二十州贡献,岁有常赐,蛮人以为利,有罪即绝之。”[16]4077《宋史》亦载:“朝廷姑欲无事,闻遣吏谕旨,许以改过自归,裁损五七州贡奉岁赐。”[18]14179中央王朝与两江少数民族地区之间是一种动态的关系,利益勾连与矛盾冲突并存,此消彼长。
贡赐制度是宋朝维持整体安全机制的要素之一,不仅关涉王朝稳固基业,而且也关系少数民族地区的安定;不仅影响中央集权和大一统的发展,而且还关系少数民族势力的政治权益,是多向度利益牵制的反映。朝廷通过贡赐制度,昭示仁恩,宣谕政策,执行制裁,从而使少数民族自愿、主动归附宋王朝[12]26。中国古代朝贡体系以中原王朝为核心向四周辐射,遍及四海,维持了多方和谐关系,且通过物资反馈彰显王朝的统摄力。
中国北方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是中原王朝“天下”观与“华夏—四夷”结构在人文、政治层面上的中心。宋代外患集于北方,西夏、辽、金等彼此之间争锋博弈,纵横捭阖,形成错综复杂、相互牵制的多维关系。宋代是民族大对流的关键时期,宋王朝处在一个暗流涌动的历史大背景中。随着北方话语权的失却,北宋王朝调整开边战略,加强“江南”一带的管治。宋皇室南迁,经济重心实现南移,长江下游成为人口集中、经济富庶的区域,而统治者也致力于加强对长江中游的管制,以纵横捭阖之术周旋于南方少数民族中,在少数民族互斗中坐收渔翁之利。北宋王朝综合分析周边强权林立的大环境,力求在整体国家安全观念的基础上建立适用于五溪两江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羁縻制度。北宋王朝通过制定并实施贡赐规章律令,一则显示王朝统治的正统性,再则施仁布恩。此外,统治者还根据管治体系与管治能力的推进历程,适时适势转化羁縻州与经制州建制,羁縻州向经制州的转变是王朝“大一统”统治理念实施历程的具体表现。总而言之,北宋王朝对南北两江少数民族地区的管治表现出张弛有度的差异状态,朝廷因时而异、因地制宜地变化治理政策,保障王朝国家的统治秩序和安全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