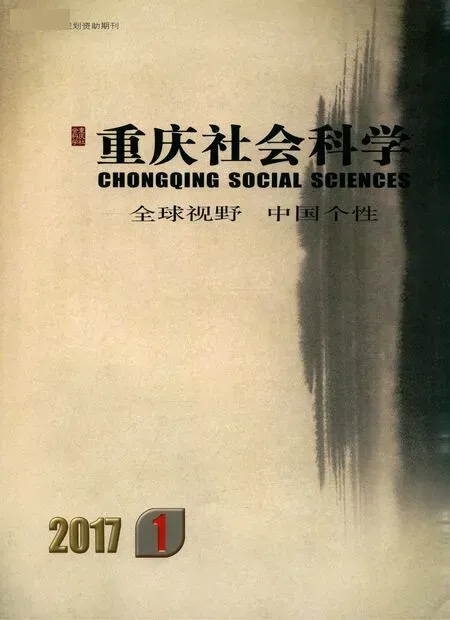土司宗祠的孝文化影响:湘省个案*
2017-03-28张登皓
张登皓
土司宗祠的孝文化影响:湘省个案*
张登皓
土司文化作为湖南湘西特有文化之一,有着较大的学术研究价值和社会研究价值。在湘西,土司文化中很大一部分的内容都直接反映在土司宗祠中。土司宗祠作为集结土司各种文化于一身的集合体,有着自身独特的发展路线,但土司宗祠文化的发展始终离不开“孝”这一主心骨。以孝文化一以贯之的土司宗祠在经过百年后仍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深入研究土司宗祠中孝文化的发展情况,合理分析土司宗祠中孝文化的时代内涵,辩证看待土司宗祠中孝文化的现实意义,对于构建良性土司宗祠的新型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
土司宗祠文化 孝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可称为“孝的文化”[1]。孝文化作为内化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积淀,是一种道德观念与伦理践行的复合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的性格养成、伦理观念、道德实践等方面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相应地,一定文化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物质载体,土司宗祠作为记载孝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对于保留孝文化的传统内容、记载孝文化的时代变迁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深入分析研究土司宗祠中孝文化的变化与发展,对构建具有时代价值的以孝文化为核心的新型土司宗祠文化是有所裨益的。
一、永顺土司宗祠中孝文化的起源及发展
湖南省永顺县老司城土司王城见证了八百年来土司家族的兴衰,是研究湘西土司文化的重要实地资料。老司城背靠太平山,太平山下又有三座山峰,它们好似手拉手般联系在一起,分别叫做“福德山、禄德山、寿德山,合称三星山,寓意太平盛世,三星照耀”[2]。老司城集生活、生产、军事、政治、文化、教育、医疗等于一体,具有一整套渗入个人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完整的治理模式。
永顺彭氏土司共历经了三十五世,历经五代。两宋、元明清时代。据记载,绍兴五年(1135年),彭福石在继承土司王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迁都老司城。[3]此后,便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土司王并没有修建宗祠,“孝”仅仅作为一种观念内化于彭氏个人的心中。元朝时,中央政府将地方土司制度纳入中央政治制度体系。直到明朝万历十九年 (公元1591年),第24代土司彭元锦时任宣慰使,主持修建彭氏宗祠。宗祠修建起初仅仅只是为敬奉祖先,使祖先的灵魂得以安放,届时彭氏后代可以享受祖先的荫蔽。由此可见,此时彭氏对于“孝”的观念开始外显,不再是隐藏在个人的心中。不过,尽管彭氏宗祠此时已经修建完成,但是对于“孝”来说仍旧是一种观念,尚未形成系统与体系,其影响力也仅仅只是从家庭走向宗族,尚未达到成为社会治理的一种实践性的文化手段。约于明末,彭氏土司宗祠在彭氏家族的几位长老共同努力下,实现了宗祠的文化意义上的回归,即几位长老用明确的文字,共同的契约形成以孝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并对以后发展的路线作出了一定的设计。至此,彭氏土司宗祠中的孝文化成文化、体系化,成为后期永顺彭氏土司宗祠的代名词。清雍正六年(1728年),中央政府对于永顺彭氏土司进行了改土归流。正因改土归流,永顺彭氏土司宗祠中的孝文化得以继续发展,吸收了以“顺”为内核的新内容。
近代以来,永顺彭氏土司宗祠中的孝文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进行着传承与发展,没有形成断点。面对外来入侵,以孝为根基的“忠”与“爱”成为鼓舞土家人坚决斗争的精神动力。随着现代对于湖南湘西等地的解放,土司制不再,但融进土家人特别是彭家人灵魂深处的关于“孝”的印记继续发挥着它的功能。改革开放后,受物质论的影响,永顺彭氏土司宗祠中孝文化的发展面临窘境。
二、永顺彭氏土司宗祠中孝文化的传统内容
孝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深刻的内涵之一,对于孝德的强调是传统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所在[4],深刻体现着中华民族的道德实践与伦理要求。为更好地了解永顺土司宗祠中的孝文化的发展历程,把握永顺土司宗祠中的孝文化的精神实质,应对永顺土司宗祠中孝文化的传统内容作出考究与解读。
(一)永顺彭氏土司宗祠中孝文化的传统特征
从整体上来看,孝与孝文化具有绝对普遍性,全国范围内的以“孝”为核心与养料形成的“孝文化”在内容、形式、特征上等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从局部来看,孝与孝文化具有相对的特殊性,尤其是在少数民族自我管理、自我治理的区域内,或多或少地带有地区民族色彩。在永顺老司城土司宗祠中所体现的孝文化便具有较强的地区民族性,突出表现为“三个相统一”,即政治性与生活性相统一、教育性与文化性相统一、继承性与强制性相统一。
1.政治性与生活性相统一
政治性是涉及国家治理的一些理论与观念、观点,具有鲜明的方向取向性。永顺土司宗祠建立之初就是为土司政治统治服务的,希望用一种内在的具有高度凝聚力的精神力量来辅助土司政治的长期有效统治。而这一力量就是传统文化,就是传统文化的本质,即孝文化。因此,永顺土司宗祠中的孝文化从发展之始便具有政治性的特征。生活性是孝文化的普遍特征,是作用于一个家庭、一个宗族的鲜明标识,有利于维护家庭、宗族的伦理秩序,有利于实现良好家风、族风培育,有利于和谐家庭建设。永顺土司宗祠中传统的孝文化代表的是彭氏一族对于族风、伦理、秩序等的现实建设,是彭氏土司王精神面貌的重要体现。所谓政治性与生活性相统一,是就永顺彭氏土司宗祠中传统的孝文化而言的,既服务于政治生活,又服务于日常生活。相对一般宗祠仅仅只是服务于日常生活所体现出的孝文化,永顺彭氏土司宗祠中传统的孝文化在内涵上显得更为厚实,在结构上显得更为完善,在特征上显得更为鲜明。
2.教育性与文化性相统一
“孝”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后天的教育来培养的。因此,“孝”是具有可教育性的,典型的例子就是“愚孝”。也正是由于“孝”具有可教育性,“孝的家教”才具有可能性。家教就是家庭教育,永顺彭氏土司宗祠中传统的孝文化教育是一个关于“大家庭”孝道的教育,首先是教育的彭氏一族,其次是所统治区的全部居民。在过去,永顺彭氏土司宗祠还承担着惩罚那些不尽孝道的外姓人的任务。据调查,在彭氏土司王统治的几百年里,因不尽孝道,违背家庭、宗族伦理秩序而受到处罚的彭姓人士约是6人,外姓人则多达10余人。此外,文化性亦是永顺彭氏土司宗祠中传统的孝文化的重要特征。“孝”从观念到文化的体现的是一种完整体系的形成,实现的是一种体系的跨越。永顺彭氏土司宗祠中传统的孝观念经过历代土司王的不断完善,逐步形成了一种以“孝”为统治秩序的文化制度,实现了从孝观念到孝文化的升华。因此,永顺彭氏土司宗祠中传统的孝文化表现出的教育性与文化性相统一就是“孝文化”作为文化的教育性,与“孝”作为教育方式与教育内容经体系化所具有的文化性的统一。
3.继承性与强制性相统一
继承性是文化发展的重要的内在属性,永顺彭氏土司宗祠中传统的孝文化在性质上是作为一种文化而存在的,在形式上通过口口相传、族规家训等方式流传下来,无论是从内在的文化特性来看还是外在的形式特征来看,永顺彭氏土司宗祠中传统的孝文化具有继承性是毋庸置疑的,这也是永顺彭氏土司宗祠中传统的孝文化为什么可以流传几百年仍旧生机盎然的原因之一。相对继承性,永顺彭氏土司宗祠中传统的孝文化的强制性特征主要表现为永顺彭氏土司宗祠中传统的孝文化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政治生活与家族生活。马克思说过,一个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也是在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因此,永顺彭氏土司宗祠中传统的孝文化需要服务的政治生活就是在思想观念上实现“占统治地位”,具体表现为彭氏土司宗祠中传统的孝文化上升为统治地区的思想观念发展的尺标,内化为人们内心信念,外化为人们行动的规则。此外,家族生活亦是体现永顺彭氏土司宗祠中传统的孝文化具有强制性的重要表现。家族生活,即集体生活,“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内,家族是最主要的集体或团体,在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生活中,主要的运作单位是家族。”[5]因此,按照孝文化教育的单向性特征,小一辈必须服从大一辈人的孝道传教,这是不可逆的。由此,永顺彭氏土司宗祠中传统的孝文化中的继承性与强制性可以看作同一过程中的两个不同方面,强制传授中进行着继承,在继承中使用强制性的手段。
(二)永顺土司宗祠中孝文化的具体内容
“孝”字,上面是“老”字的上半部分,下面是儿子的“子”,这就意味着所谓孝就是孝养父母。[6]的确,永顺彭氏土司宗祠中传统孝文化中的部分内容就是要孝养父母,这是一种情感,出于人对父母的爱,是仁德的根苗;也是一种实践,是对仁德初步的实践和对仁德根苗的培养[7],表现了永顺彭氏土司宗祠中传统的孝文化中对于孝养、仁德的看重,同时这也恰恰印证了西周时期的孝道观。此外,永顺彭氏土司宗祠中传统孝文化的具体内容可分为“爱、敬、忠、顺”。[8]
爱,在永顺彭氏土司宗祠中传统孝文化中指的不仅仅是爱父母,更指的是要“爱人”,广泛地去爱宗族中的其他人,爱受自己统治下的外姓人。这里的爱父母,不再是单一地要孝养父母,更增添了“敬”的意思,孝敬父母,不忤逆父母的意思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同时这种“敬”对应的就是秩序,如果说孝养父母的这种“爱”是一种家庭内部或家族内部的一种 “秩序”,那么“敬”这种“秩序”就是为社会统治立法,无论是外姓人还是本姓人都得按照“敬”的“孝”规范日常生活。此外,要求爱他人,一是为了更好地团结起来,二是为了壮大人口,这是一种民族情结的体现。因此,可以将这种具有广泛意义上“爱”的孝看作民族情结的体现。
敬,在永顺彭氏土司宗祠中传统孝文化中就是“敬爱”的意思,常常与“爱”连用。不过,除在“爱”中体现的所具有的“敬”的成分外,“敬”是一种恭敬,在其本质表现上应算作“礼”。这里所说的“礼”绝非一种秩序,相反,这种“礼”是一种处世态度。“对上恭敬,对下不傲,称为礼”,也就是永顺彭氏土司宗祠中传统孝文化中所体现的“敬”。
忠,是构成永顺彭氏土司宗祠中传统孝文化政治层面的重要内容。在“孝”中强调“忠”是永顺彭氏土司宗祠中传统孝文化的重要特征,为的就是尽可能地保障“忠孝两全”,尽最大可能避免自古以来的“忠孝难全”的难题。在永顺彭氏土司发展的历史中,统治内发生的冲突不多于5起,应中央政府的要求派遣土家族将领、士兵外出征战的不少于5起,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明朝时的抗击倭寇。无论是在内还是在外的冲突中,彭氏将领与土家族士兵都深受“孝、忠”传统文化的影响,尽可能地平安归来、孝养父母。
顺,就是孝顺,在永顺彭氏土司宗祠中传统孝文化中,“顺”是沟通“爱”、“忠”、“敬”的方法,能够有效地调节自己与父母、自己与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关系。在日常生活中,正是因为“顺”,才有力地将不同身份、不同角色、不同阶级的人群凝结在一起。“顺”所发挥的功能就是永顺彭氏土司宗祠中传统孝文化所有的稳定社会的功能。
三、永顺彭氏土司宗祠孝文化发展的时代变化
“时代变迁,移风易俗,这是历史的必然。”[9]世界是处于不断运动、发展的过程中的,永顺彭氏土司宗祠中孝文化的内涵历经几百年发展至今,经历了种种变化,主要包括形式上的、特征上的、内容上的与内涵上的变化。
(一)形式上的变化:由日常大礼到简化礼仪
在过去,关于如何表示自己是具有“孝”这一品质的在形式上永顺彭氏土司宗祠是有明确规定的,即要行日常大礼。永顺彭氏土司所用来表现“孝”的日常大礼绝不等同于皇家的日常大礼或者现代意义上所理解的日常大礼。这种日常大礼分为言与行两个方面,在“言”的方面主要表现为小辈对于长辈的“请安”。在传统的彭氏土司家族,辈分低的人无论年纪的大小必须在早上早饭前向长辈“请安”,主要包括帮助长辈洗漱、聆听长辈教诲、询问一天安排等,日日如此,不得断点,最为突出的就是儿子向父亲请安。当然,除去外出不在家的小辈。在“行”方面的日常大礼则主要是在特定的节日,小辈须向长辈行家族大礼,包括献礼、表演,其规模较为庞大,仪式较为隆重,参与表演的本姓人将载入族谱重大事件记录。
较之过去,现在永顺彭氏宗族显得简单了许多,既没有了过去中国式大家庭的集合居住,也没有了层层分严的宗族等级制度。过去用来表现“孝”的形式却保留了下来,但具体内容发生了较大变化。同样的“言”与“行”,但没有了过去的那般繁琐,变成了只是可能在路上遇到的互相问候,不过这种问候必须是由小辈先开口向长辈问好,一种日常简化的问候变成了孝在“言”上的表现。相应的节日大礼表演也变成了节日的拜访,“行”也随之简化了。
(二)特征上的变化:由刚性要求到柔性教化
传统上,永顺彭氏土司对于孝的要求是刚性的、硬性的,与之对应的是彭氏土司一整套的关于“孝”的教育系统。从娃娃抓起是彭氏土司关于“孝”的教育最为突出的特征。在永顺彭氏土司宗祠仍旧可见的陈列在祠堂的就是彭氏家训,分别从教子、教女、教媳三个主体出发,包含品德、行为、教育、卫生、生活、育子等在内的方面进行教育与规定。儿子、女儿、媳妇必须义务遵守家训,并且将之落实在日常生活中,否则就是“不孝”,需要接受家族内长辈的惩戒。然而,随着土司制度的土崩瓦解,这些家训、族训或早已被人遗忘,在对于彭氏家族进行调查时,年轻的一辈已然没有受这些祖先留下来的刚性的“孝”的规定性要求的训诫了。相应地,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思想不断解放,彭氏家族已悄然将这些刚性教化的内容变成了符合现代发展要求的柔性教育。这种柔性教育主要依靠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相结合,通过受教育者自我认识、自我反思、自我完善,达到自身的相对和谐,在这一过程中不借助任何强制性的手段或工具。
(三)内容上的变化:由权威“愚孝”到选择“孝养”
永顺彭氏土司宗祠孝文化由于在传统内容上原本便带有政治色彩,那么相应地对于权威的屈从是不可避免的。族权与孝道的相互加强,孝道被推向极端,出现了许多违背基本人性的愚孝行为,割肉疗亲就是在这种愚孝发展到登峰造极的一种表现。[10]据调查,在历史上彭氏宗族出现过约2起割肉疗亲的事件。无独有偶,除去割肉疗亲,彭氏宗族也出现过子代父之过接受残忍的惩罚的行为。诚然,不可否认,对于权威的崇拜与恐惧是造成这种愚孝的根本原因,这种愚孝面临的代价就是性命的威胁。现下,这种受权威威胁而产生的愚孝行为早已被人抛弃,取而代之的则是“孝养”。这种孝养无论在内容上、形式上还是特征上、内涵上都不仅仅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孝养”。现在所说的“孝养”多是基于自我和谐条件下的家庭孝养推进,为的是构建和谐家庭、共享人伦天道。
(四)内涵上的变化:由精神孝顺到物质孝顺
历史上,湖南湘西永顺就是一个蛮夷之地,生产力极度落后,物质生产相对落后,在此基础上,关于孝道的践行便停留在精神层面。彭氏土司作为湘西地区的最高统治者,拥有着湘西地区的最高物质财富,然而由于内在的质朴性,尽管是在“帝王之家”,尽孝也更多地表现在精神层面的慰藉,而非物质层面的享用。相反,在现代,孝观念的物质化却大行其道,即认为在物质上供养父母就行[11],而忽视了对于父母的精神层面的安慰,这直接表现为一种孝道危机。当在对彭氏家族成员进行调查时,不能陪同父母的原因大多数是没有时间,得去挣钱。在对其进行进一步询问如何孝养父母时,超过80%的人都表示等挣了钱多给父母一点钱。尽孝道由精神层面转向物质层面是彭氏宗族在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最为鲜明的标志。
四、永顺彭氏土司宗祠孝文化现存的问题及其原因
永顺彭氏土司宗祠孝文化作为展示土家土司文化的一支重要力量,同其他任何少数民族文化一样,由于其传统文化内在的复杂性及所处社会环境的时代性,对于永顺彭氏土司宗祠孝文化的传承与开发必然是各抒己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一)永顺彭氏土司宗祠孝文化存在的问题
社会总是处于“它现实是什么”与“人们希望它是什么”的张力之中。[12]这是问题出现的原因之一。永顺彭氏土司宗祠孝文化在时代变迁中由于社会的外在影响与土家人民内在情感变化,导致其在传承与发展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其中的突出代表就是孝文化下宗祠架子的出现、土司宗祠孝文化的内涵物质化、土司宗祠孝文化的意义流失、土司宗祠孝文化的精神需要满足能力弱化。
1.孝文化下宗祠架子形式的出现
架子,原指盛放东西的支撑物,是一种姿势或说一种形态;形式,则指的是某物的样子和构造,是物的外形。孝文化下的宗祠架子形式则指的是只剩下了宗祠的外形或是形态,没有了内在的“魂”。以孝文化为核心的永顺彭氏土司宗祠,综合涵盖了“物态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13],在时代的不断发展中剩下的就只是物态的架子了。综合表现为“孝”的固化,以及与固化的“孝”指导下的土司宗祠发展的物态化。
“孝”是动态发展的,而非静止不变的。这种发展不仅仅包含“孝”的内容、形式,也包括“孝”的创造、享用。有力的证明就是关于《孝经》的注疏,极大地丰富了“孝”的含义。而发展至今的永顺彭氏土司宗祠孝文化走上了静止之路,其内涵与精神享用功能仍旧停留在土司制度瓦解的阶段,没有对其进行时代性的丰富、加工与利用,以致其难以发挥出应有的功效与作用,这也是导致现代彭氏家族出现家庭养老困难、代际之间矛盾冲突大的内在原因。相应地,在这种固化了的“孝”指导下的宗祠建设,是没有灵魂的或者说灵魂是不完整的,纯粹成为了物态化的死气沉沉的建筑,不能彰显出强大的民族标识的作用,和引导彭氏家族甚至影响其他家庭或家族的和谐发展,实现代际间的“绿色发展”。
2.土司宗祠孝文化的内涵物质化
永顺彭氏土司宗祠中孝文化的物质化既是永顺彭氏土司宗祠发展出现的变化,也是永顺彭氏土司宗祠发展存在的问题。马克思说过,人所追求的首先是基本生存资料,其次是发展资料,最后是享受资料。由此来看,永顺彭氏土司宗祠孝文化由精神转变成物质是一种发展的倒退,是不符合发展要求的。然而,导致这种倒退发展的关键就在于永顺彭氏土司宗祠孝文化的内涵物质化了。
永顺彭氏土司宗祠孝文化的内涵物质化指的是在物质大爆炸的现代,彭氏家族过于受物质论的影响,简单地将能够满足长辈的物质需要,甚至超过长辈的物质需要当作孝的一切内容,抛弃了传统孝文化中对于精神享用作用的功能,这也直接导致了孝文化发展的固化和土司宗祠建设的空洞。此外,物质满足能力的大小在现代以来成为或长期成为衡量彭氏人是否“孝”的唯一标准。这一观念内化于彭氏人的头脑中。
3.土司宗祠孝文化的意义流失
永顺彭氏土司宗祠孝文化的意义有两个层面,从广义来看,永顺彭氏土司宗祠孝文化在实质上是一种“泛孝主义”[14],它广泛地应用于宗族、社会,分别作用于宗族的团结、和谐、协调,社会的有序、稳定、和善,发挥了孝文化在文化层面上转化而成的现实作用力,实现了人文目的与政治目的。从狭义来看,永顺彭氏土司宗祠孝文化是一种家庭文化,维护的是一个又一个家庭内的和谐有序,为的是家庭内的共享天伦,没有到达在广义上的“孝治天下”的意义范畴。
而在当代,永顺彭氏土司宗祠孝文化的意义流失恰恰也反映在这两方面上。首先,不得不直视的一个现实是永顺彭氏土司宗祠在当代的衰落,且不说影响到外姓人,连彭姓人几乎也没有几个踏足宗祠,感受祖先留下的文化教化。因此,永顺彭氏土司宗祠孝文化首先失去的就是发挥孝治天下的功能,失去了构建社会成员精神世界的意义,这与时代的发展是逆流的,若长期如此,面临的就是永顺彭氏土司宗祠孝文化的彻底消失。不仅如此,永顺彭氏土司宗祠孝文化在狭义上的意义也流之殆尽,据调查,2001~2016年,彭氏家族内部因养老问题、代际摩擦问题等发生口角,甚至暴力冲突的不下5起,直接造成了孝文化的调节作用失效。
4.土司宗祠孝文化的精神需要满足能力弱化
在兴建永顺彭氏土司宗祠之处,最原始的目的就是为先人建造一个安放灵魂之处,使后代能够享受祖先荫蔽。久而久之,发展出了作为教育、训诫、惩处之处的功效,极大满足了永顺彭氏的精神需要。伴随永顺彭氏土司王朝的建立,这种精神满足的功用作用于整个土家人们,使土家人们找到了根之所在,有着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获得了民族支撑力量。然而,随着土司王朝的瓦解,集体生活变成了单个家庭的生活,每个家庭为着自己的生计而不断忙碌,难以继续全身心为土司宗祠孝文化的丰富与发展作出必要的努力,这也是历史的原因。受物质论的影响,永顺彭氏人渐渐沉浸于物质的追逐上,而忘却了土司宗祠孝文化对于精神的洁净功能,没有对其进行时代性的发展,导致土司宗祠孝文化满足人精神需求的能力弱化。
(二)永顺彭氏宗祠孝文化式微的原因
原因,即某现象发生的根源、缘由。分析、寻找某现象发生的原因,即寻找该现象的根源所在,为更好地了解该现象的深层结构以及更好地对症下药地“治疗”该现象具有重大意义。
1.多元价值中个人价值取向的错位
永顺彭氏土司宗祠孝文化作为展现土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根植于土家人的精神世界,直接地对土家人的思维方式、价值判断、价值选择、行为方式产生重大影响。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的多元价值取向借助我国发展民族生产力、沟通国际经济的桥梁,或公然地或悄然地在社会中大肆宣传,误导、扭曲、荼毒了我国社会成员特别是偏远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导致了永顺彭氏土家人的价值取向错位,以致出现一种“继承断代、形式残缺、内涵缺失”的“现代性彭氏土司宗祠”,在一定程度上还成为了永顺土家人吸引外来消费的重要手段。
个人价值取向错位的延伸发展就是个人价值观错位。价值观作为指导人们更好地追求幸福生活的社会践行标尺,是决定人们行为的心理基础与思维起点。其中,构成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就是文化观。孝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而存在,对于孝文化的态度直接关系到个人价值观的形成。当下,永顺土家人对于土司宗祠孝文化的定位发生了偏差,使得原本作为精神依托的殿堂变成了世俗的挣钱房,直接忽视了土司宗祠孝文化在当代所具有的现实意义,成为制约、束缚永顺彭氏土司宗祠孝文化完成时代脱变的外在枷锁。
2.社会转型中物质论的误导
社会转型是每个国家都将面临的不可跨越的“卡夫丁峡谷”,在我国无论是从哲学的角度上看还是从社会的角度上看,都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重层面、多层意义上的变化与转型。而在现实社会活动中,社会转型越来越以人类最基本的经济活动形式而存在。[15]而对于永顺彭氏土司宗祠孝文化的发展来说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发展中的物质论的误导。
一定的经济政治决定一定的文化,永顺彭氏土司宗祠孝文化本身作为文化便具有相对于经济的相对独立性。在现实中,永顺彭氏土司宗祠孝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能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变成了土司宗祠孝文化的一切发展都是为经济服务的,要满足的应该是物质的需求,而不是精神的享用。因此,物质论是威胁永顺彭氏土司宗祠孝文化发展的最大阻碍。
3.现代发展中“破”与“立”的失衡
对于永顺彭氏土司宗祠孝文化进行盲目的“破”与“立”是导致彭氏土司宗祠孝文化发展停滞与畸形的根源。盲目地“破”,表现的是对永顺彭氏土司宗祠孝文化的文化底蕴的否定,追求的是现代物质的衡量。盲目地“立”,即不尊重自身文化演进的规律,不加思考地对永顺彭氏土司宗祠孝文化进行现代化的元素添加,导致永顺彭氏土司宗祠孝文化在现代生活中变成了畸形的时代产物,相对应地就反映在传承与发展这两者的失衡上。
传承与发展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彼此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不可分割。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任何文化、习俗都是在传承与发展中得以延续、丰富,一旦割裂开传承与发展的一脉性,就将导致该文化或习俗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永顺彭氏土司宗祠孝文化之所以在现代的现实生活中出现了大量的问题就在于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全盘否定了对于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内容的继承,割裂了继承与发展的一脉性,导致两者相失衡、相脱节。
4.土司宗祠建设的滞后性
近年来,永顺着力发展旅游业,这对于彭氏土司宗祠孝文化的发展可谓一个契机,但是永顺政府多开发自然风光,对于人文风景的开发、发展的力度不够,一度导致了土司宗祠建设的滞后性。此外,宗祠本身发展的后劲不足也成为制约土司宗祠孝文化发展的一大硬伤,主要表现为宗祠的发展能带来的经济价值有限、宗祠与人们所需的精神满足方面不同等。
土司宗祠建设的滞后性直接带来的影响一是土司宗祠孝文化在社会治理上的功能弱化,不能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作用,造成文化资源的浪费。二是导致土司宗祠孝文化自身的发展受限,难以实现与时代的接轨,完成时代的蜕变,为后续发展积累能量。与之相应的则是导致土司宗祠孝文化的意义流失与本质固化,没有鲜活力,长期下去,将面临着时代的淘汰。
五、“孝”视角下土司宗祠良性发展的策略
社会只有处于一种良性的发展中才能有秩序,保障人民的幸福生活。永顺彭氏土司宗祠孝文化也应当处于良性的发展中才能更好地成为民族的标识,树立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自豪感。而在现实中永顺彭氏土司宗祠孝文化发展出现了问题,如何使其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倡导个体“以孝为本”型宗祠新发展
孔子曾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16]也就是说,孝是一切品德的根本,一切教化都是根植于孝的基础上的。因此,倡导个体“以孝为本”也就是努力实现个体的各项品德培育,帮助个体实现全面自由可协调发展。诚然,永顺彭氏土司宗祠曾经扮演过承担着“孝的教化”的角色甚至具有这样的功能。而现代,土司制不再,凝结彭氏人于一体的政治强力不再;彭氏土司宗祠收归公有,凝结彭氏人于一体的精神殿堂被社会化,内含于中的文化内核难以继续发挥功效。这致使了彭氏个体的发展从小就是相对不完整的,甚至这片区域个体的发展都有待加强。因此,要重构永顺彭氏土司宗祠孝文化在时代上的价值指导,引导新型宗祠的建设,必须将个人的“以孝为本”的孝道观念与成套孝道文化加以重铸,深刻融入到永顺彭氏土司宗祠的新兴建设中去。
(二)实现社会转型中打破“唯物论”型宗祠新发展
我国当代社会面临的是多重转型的时期,回归文化意义上宗祠新发展应当成为实现永顺彭氏土司宗祠良性发展的关键,这就要求打破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唯物论”的禁锢。所谓回归文化意义指的就是要重构永顺彭氏土司宗祠的时代孝文化,在时代孝文化的指导下发展出文化性的彭氏宗祠。这要求理性协调好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三者的关系,使之更好地为实现永顺彭氏土司宗祠健康发展而服务。
协调政治制度,使得政治制度在实现永顺彭氏土司宗祠良性发展中平衡好自身显现的或潜在的矛盾,努力克服可能因政策的倾斜而潜伏的弊端,在政治制度上实现高度的逻辑严谨性、一脉相承性。协调经济制度,要注重解决实现永顺彭氏土司宗祠良性发展中存在的物质论误导,保障实际成效。协调文化制度,要给予土家人民民族文化定心丸、定音鼓,使之不再左右摇摆。协调三者关系,实现永顺彭氏土司宗祠在良性发展中以政治制度为保障,以经济制度为核心,以文化制度为导向的三者有机联合,更好地适应我国当下社会的多重转型,实现永顺彭氏土司宗祠中的孝文化的协调发展、绿色发展。
(三)平衡原则指导下宗祠孝文化的价值重构型宗祠新发展
平衡,就是要平衡协调好永顺彭氏土司宗祠中的孝文化在传承与发展中的连续性与速度性的问题,完成永顺彭氏土司宗祠孝文化的价值重构。
连续性,是一种文化得以存在、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改革开放之后,永顺彭氏土司宗祠因政治的原因收为公有,相应地彭氏人也就不再涉足祖宗宗祠,对于祖宗宗祠的孝文化的内涵、精神的传承力度越来越小,至今已有不少彭氏年轻人不知道自己祖宗宗祠的所在,更何谈对于宗祠中深厚的孝文化底蕴进行传承。因此,必须有计划有目的有科学方案地对永顺彭氏土司宗祠中的孝文化进行有效地继承,实现永顺彭氏土司宗祠在完成孝文化价值重构的基础上的新发展。
永顺彭氏土司宗祠中孝文化发展的速度与经济发展的速度不相协调。经济发展速度相对永顺彭氏土司宗祠中文化发展的速度而言较快,这也就直接导致了宗祠建设的滞后性。对于永顺彭氏土司宗祠中文化发展的速度相对缓慢必须要“加大马力”,使之适应经济发展的速度,才有可能借助经济发展的力量完成价值重构,更好地运用内涵文化来影响人。
(四)提升满足“孝”的精神需要能力建设型宗祠新发展
在谈及永顺彭氏土司宗祠中孝文化发展出现的问题时,很大一部分问题出现在自身,即永顺彭氏土司宗祠中“孝”文化对于现代人的精神满足力不足。这也印证了马克思所说的内因才是制约发展的根本。永顺彭氏土司宗祠中“孝”文化在解放永顺后便一直处于一种静止不前的状态,“孝”文化仍然处于传统模式,没有能够及时地进行更新,不能很好适应现代人对于精神发展的需要。这也意味着如果不加以改造、创新,永顺彭氏土司宗祠中孝文化将随着时间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将只是彭氏土司宗祠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对于社会具有一定指导意义的文化内涵将不复再见。因此,要提升彭氏宗祠中满足“孝”的精神需要能力的建设是势在必行的,继而提升满足“孝”的精神需要能力型宗祠新发展自然出现。
六、结语
永顺彭氏土司宗祠中的孝文化是展示土司精神面貌的重要标识,研究土司宗祠中的孝文化是窥探土司文化的重要步骤,对于重构土司宗祠文化的时代价值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发挥孝感天下、孝行天下的积极作用,有利于引导社会风气良性发展,有利于实现社会和谐、稳固社会结构。此外,未经创新的传统土司宗祠孝文化不能自动成为加速社会现代化、促进社会和谐的动力。因此,引导以孝贯之土司宗祠的新型发展,辩证地否定看待土司宗祠中的孝文化,创新土司宗祠中孝文化的时代发展是一项现实的要求。
[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90~391页
[2]柴焕波:《永顺老司城——八百年溪州土司的踪迹》,岳麓书社,2013年,第2页
[3]王禾芒:《司城春秋》,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46页
[4][10][11]李晶:《孝道文化与社会和谐》,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 年,第 1~2、9、89 页
[5][14]叶光辉 杨国枢:《中国人的孝道:心理学的分析》,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6、24页
[6]胡小林:《敬业三福 孝亲尊师》,岳麓书社,2013年,第10~11页
[7]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56~60页
[8]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0~76页
[9]乔继堂:《中国人生礼俗大全》,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0页
[12]陈万柏:《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5页
[13]陶嘉炜:《中国文化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页
[15]汪应曼:《经济转型与道德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第1~4页
[16]《孝经·开宗明义章》
Effect of Filial Piety Culture in Tusi Ancestral Temple:Case of Hunan
Zhang Denghao
Tusi culture,as one of the unique culture in West Hunan,has the value of academic research value and social research greatly.And a large part of the contents of the Tusi culture are directly reflected in the Tusi ancestral hall in a toast.Tusi ancestral hall,as the assembly of various cultural,has its own unique development path,but the development of Tusi ancestral culture always cannot do without"filial piety"which is the backbone.Tusi ancestral hall with filial piety culture making it one principle runs through it all still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future generations after hundred years later.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valu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enign Tusi ancestral hall.to do research on development of filial piety culture in Tusi ancestral hall,make reasonable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 of the filial piety culture in Tusi ancestral hall and have dialectical view on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filial piety culture.
Tusi Culture Hall,filial piety culture,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该标题为《重庆社会科学》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关于土司宗祠中孝文化发展的调查与研究——以湖南省永顺县老司城彭氏宗祠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