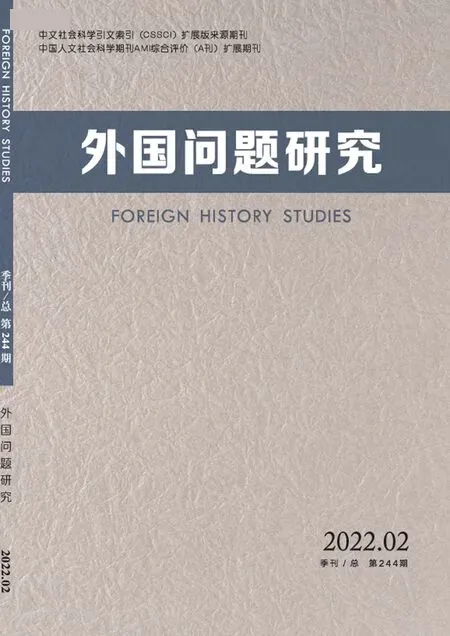1971年澳工党代表团访华与澳中民间交往
2022-12-28谢晓啸
谢晓啸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1972年12月,由澳大利亚政治家高夫·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领导的澳大利亚工党在国内大选中击败了自由党和乡村党联盟(Liberal-Country Coalition),在一举终结后者长达23年之久的执政纪录的同时,也宣告了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即将改辕易辙。此前,由于澳自由党和乡村党联盟政府始终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对华采取敌视和戒备的态度,中澳两国迟迟未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惠特拉姆在就任总理当天即宣布他已要求澳驻法大使阿兰·雷诺夫(Alan Renouf)与中方联系以便双方就建交事宜展开谈判,同年12月21日中澳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1970—1978》,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392—393页;Gough Whitlam, “Sino-Australian Diplomatic Relations 1972—2002,”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56, No.3, 2002, p.330.
澳中关系之所以能够在工党政府上台后迅速实现正常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惠特拉姆在前一年率领工党代表团访华时就已经与中方围绕相关问题达成了初步的共识。(2)在与中方举行会谈的过程中,惠特拉姆曾向周恩来总理坦言,如果由他率领的工党在次年的大选中获得胜利,新政府将立即寻求与中国建交。参见“Transcript of Discussions between Gough Whitlam and Zhou Enlai, 5 July 1971,” the Whitlam Institute, ed., For the Record: Gough Whitlam’s Mission to China 1971, Rydalmere, NSW: Whitlam Institute within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 2014, p.25.对于这一澳中关系的“破冰之旅”的前因后果,许多专家已有申论。国内学者中,汪诗明和张秋生曾分别撰文从不同角度对当时澳大利亚国内两大政党自由党和工党在对华政策上的不同之处做过剖析,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惠特拉姆此次中国之行的重要历史意义。(3)汪诗明:《论澳中关系正常化》,《世界历史》2003年第2期;张秋生:《试论澳中建交及其对澳亚关系的影响》,《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放眼国际学界,除了众多以澳中关系为研究对象的论著之外,还有两名学者,费思棻(Stephen Fitzgerald) 和比利·格里菲斯(Billy Griffiths)曾相继以专著的形式对这一事件的缘起及其深远影响进行过细致的历史学考察。(4)参见Stephen FitzGerald, Talking with China:The Australian Labor Party Visit and Peking’s Foreign Policy,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2;Billy Griffiths, The China Breakthrough: Whitlam in the Middle Kingdom, 1971, Clayton,Victoria: Monash University Publishing, 2012.
然而,无论是以澳中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分析性论著或是围绕工党这次出访展开的历史性叙事,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两国之间延续多年的民间交往为惠特拉姆等人此次访华之旅的成功创造的有利条件。事实上,在惠特拉姆以反对党领袖的身份到访中国之前,早已有数以百计的澳大利亚民间人士曾经来华访问。在这些澳中民间交流的先行者之中,有许多是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工会人士和议会议员,也正是通过他们在返澳后的积极宣传和“牵线搭桥”,才为澳中两国在缺乏稳定的官方沟通渠道的情况下,提供了一个相互了解和接触的机会,并由此在“润物细无声”之间为1971年工党代表团的历史性访问铺平了道路。(5)关于中澳建交前双方的民间往来,参见拙作《中澳建交之前两国民间往来初析——以1949—1965年间来沪的澳方人士为例》,《史林》2021年第3期。
值得一提的是,纵观新中国成立之后与西方各大主要国家的建交过程,“民间”因素无不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以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为代表的西欧各国都相继废除了名为“中国差别”(China Differential)的对华贸易禁运政策,同时开始积极重建对华民间贸易和人文交流的渠道,这些举措为上述国家日后与中国建交埋下了伏笔。(6)“中国差别”(China Differential)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以美国首的西方国家通过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China Committee)出台的对华贸易禁运政策的总称。参见崔丕:《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291—292页。关于20世纪50—60年代,英、法、西德、意等西欧国家与中国展开的具有半官方性质的经贸谈判和商贸往来,中外学界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参见吴浩、刘艳斐:《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与英国对华贸易政策的调整(1952—1957)》,《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11期;吴浩、刘艳斐:《1954年日内瓦会议与英国对华贸易政策的调整》,《当代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27卷第6期;李华:《新中国与意大利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27卷第1期。西方学界的研究成果可参见《现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近期刊发的一期专辑中的相关文章:Carla Meneguzzi Rostagni, “The China Question in Italian Foreign Policy,”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51, No.1 (January 2017), pp.107-132; Angela Romano, “Waiting for De Gaulle: France’s Ten-Year Warm-up to Recogniz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51, No.1 (January 2017), pp.44-77; Giovanni Bernardini, “Principled Pragmatism: The Eastern Committee of German Economy and West German-Chinese Relations During the Early Cold War, 1949—1958,”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51, No.1 (January 2017), pp.78-106.相较而言,目前学界对于澳中建交前双方在民间层面建立的联系,特别是围绕这种联系对两国关系的影响的探考仍尚付阙如。
作为一项个案研究,本文致力于将1971年澳工党代表团访华这一重要事件置于澳中建交之前的民间贸易和人员往来这一更大的历史脉络中加以考察,通过聚焦于迈克·杨(Mick Young)和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两人早年的访华经历以及他们在1971年惠特拉姆的中国之行中分别扮演的重要角色,深入揭示推动澳中关系走向正常化背后的民间助力因素。
一、工党访华提议出台的背景
1949年12月,由罗伯特·孟席斯(Robert Menzies)率领的澳自由党在选举中击败了执政的工党,由此开启了一个他本人连续担任总理长达16年之久的“孟席斯时代”(the Menzies Era)。孟席斯在担任总理期间,从未真正将与中国建交作为一个近期目标。(7)关于这一时期澳政府的对华政策,参见Edmund S. K. Fung and Colin Mackerras, From Fear to Friendship: Australia’s Policies Toward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66—1982,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85, pp.21-35.此后接替孟席斯担任澳总理的自由党领导人在大体上延续了由前者制订的对华政策基本方针。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同样反对发展对华民间贸易。
事实上,虽然孟席斯政府并未像上述提到的西欧各国一样在朝鲜战争之后径直废除“中国差别”的贸易禁运政策,但其在实际执行该政策的过程中却体现出一种不同于美国的灵活性。(8)参见Henry Stephen Albinski, Australian Policies and Attitudes Toward Chin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303-307.因此,在经历了朝鲜战争时期的贸易锐减之后,澳对华出口贸易自1956年起就呈现出一种持续增长的趋势,并最终发展成了一个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在两国建交之前的23年时间里,特别是在1956年之后,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了大量羊毛、小麦以及相当数量的各类矿石和金属材料,其中尤以小麦的出口最为重要,甚至一度占据了澳大利亚对华贸易出口总量的60%—80%。(9)参见Yi Wang, Australia-China Relations Post 1949: Sixty Years of Trade and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p.13. 关于这一时期澳中贸易的总体情况和相关数据,参见Australia Parliament: Senate Standing Committee on Industry and Trade and Australia, Australia-China trade: report from The Senate Standing Committee on Industry and Trade,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1984, pp.35-44.进入60年代之后,随着澳对华小麦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执政的澳大利亚自由党—乡村党联盟政府在发展对华贸易上所持的暧昧态度,开始频繁遭到反对党工党的攻讦,同时也引起了美国方面的担忧。(10)关于工党在澳对华贸易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变化,详见下文。关于60年代初澳对华小麦出口贸易引发的美方不满,参见Timothy P.Maga, “The Politics of Non‐Recognition: The United States, Australia, and China, 1961—1963,” Journal of Australian Studies, Vol.14, No.27, 1990, pp.10-11.尽管面临来自国内外各方的压力,但澳政府仍坚持未对澳中两国之间的贸易进行干预,而是采取了一种放任自流的做法。对此,A.W.斯塔加特(A.W.Stargardt)指出,这种将政治与经济区别对待的做法,反映了一种外交政策服务于国内政治需要的特点。具言之,他认为,执政的自由党和乡村党联盟政府并不希望对澳对华小麦出口横加干涉,因为这很可能会损害其在乡村地区的支持率。(11)参见A. W. Stargardt, Australia’s Asian Policies: The History of a Debate, 1839—1972,Hamburg: Institute of Asian Affairs in Hamburg, 1977, pp.229-230.
然而,澳对华小麦出口贸易在经历了近十年(1960—1970年)的稳定增长之后,却在1970年遭遇了一次重大挫折。同年,加拿大在与中国建交后不久即宣布同中方签订了一笔金额可观的小麦销售合同,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前一直负责澳对华小麦销售业务的澳大利亚小麦局却迟迟未能与中方续签合同。(12)参见“Canada to sell more wheat to China,” The Canberra Times, October 29, 1970, p.8. 关于澳小麦局未能与中方续签小麦销售合同的情况及其影响,参见Edmund S. K. Fung and Colin Mackerras, From Fear to Friendship: Australia’s Policies Toward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66—1982, pp.105-106.
更为火上浇油的是,当上述消息公之于众之后,澳政府采取了不甚明智的强硬立场,在被问到是否会为了发展对华小麦贸易而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澳大利亚副总理和乡村党的领袖道格·安东尼(Doug Anthony)公开表示:“我不会仅仅为了在贸易上获利,而出卖自己的灵魂。”(13)“Foreign Policies Not Changed for Trade,” The Canberra Times, February 08, 1971, p.7.安东尼的这一声明自然遭到了中方的抗议,同时也在澳大利亚国内引起了一片哗然。澳大利亚政府在对华建交问题上摆出的强硬姿态遭到了此时已经转变了立场的工党的公开反对,甚至在与自由党结盟的乡村党内都有人希望尽快与中国建交。(14)参见E. M. Andrews, Australia and China: The Ambiguous Relationship, Clayton,Victoria: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198-199.澳小麦种植业主作为对华小麦出口贸易的直接受益者,更是在中国与加拿大建交之前,就已经表态希望澳政府能够尽快同中国改善关系。(15)参见Edmund S. K. Fung and Colin Mackerras, From Fear to Friendship: Australia’s Policies Toward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66—1982, p.102.
在这一澳对华小麦出口贸易陷入危机的背景下,当时在野的澳工党的立场显得尤为引人注目。在1966年之前,澳工党主要领导人虽然并不希望在国际舞台上对中国实行外交孤立,但他们同孟席斯等人一样认为中国对于澳大利亚而言是一个“威胁”,这也是工党一度批评澳政府将政治和贸易区别对待的做法是“虚伪”的原因。(16)参见Edmund S. K. Fung and Colin Mackerras, From Fear to Friendship: Australia’s Policies Toward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66—1982, pp.37-38; 95-96.但在1969年惠特拉姆确立了其在工党党内的领导地位之后,工党在澳对华贸易出口问题上的口径开始发生变化,其不再把矛头指向执政党将贸易与政治分离的做法的虚伪性,而是转而呼吁澳政府改善对华关系以利于澳对华小麦出口贸易。因此,澳工党的主要领导人才会对安东尼的声明提出批评,甚至建议澳政府为后者和其他官员的过激言论向中国道歉。(17)参见Edmund S. K. Fung and Colin Mackerras, From Fear to Friendship: Australia’s Policies Toward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66—1982, pp.103-104, 107.工党在惠特拉姆成为其领袖之后摒弃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并不令人意外。早在1954年,惠特拉姆在澳大利亚政坛初露锋芒之时,他就曾在议会中对当时执政的孟席斯政府推行的反华政策进行过驳斥,并公开呼吁澳大利亚应当直面现状,基于现实主义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8)参见“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Hansard, August 12, 1954, p.274.更重要的是,在其后的十多年时间里,惠特拉姆从未改变过其上述立场。(19)参见Billy Griffiths, The China Breakthrough: Whitlam in the Middle Kingdom, 1971, p.13.
考虑到澳对华小麦出口贸易的重要性,工党在相关问题上会摆出与政府针锋相对的立场或许并不令人意外,但真正令许多时人侧目的是此后工党领导人做出的派遣高规格代表团访华的决定。1971年4月14日,惠特拉姆以工党领袖的名义向周恩来总理致电,表达了工党希望派遣代表团访华与中方就外交及贸易问题举行会谈的意愿。(20)惠特拉姆致电周恩来总理的电文原文详见Gough Whitlam, “Telegram from Gough Whitlam to Zhou Enlai, 14 April 1971,” For the Record: Gough Whitlam’s Mission to China 1971, p.7.
二、澳中民间往来与工党访华计划的提出
工党决定派遣代表团访华的消息曝光之后,立即在澳大利亚国内引起了舆论轰动。考虑到澳大利亚即将在一年之后迎来大选以及对华关系在澳国内政治中的敏感性,工党在当时提出访华的计划无疑是冒着一定政治风险的。(21)比利·格里菲斯指出,出于规避政治风险的考虑,惠特拉姆本人甚至一度犹豫是否要亲自率团出访中国。Billy Griffiths, The China Breakthrough: Whitlam in the Middle Kingdom, 1971, p.24.然而,惠特拉姆等工党领导人做出的这一看似出人意料的决定,实际上却并非是毫无先例的投机之举。在澳中建交之前的23年时间里,尽管反华的论调始终在澳大利亚国内占据着舆论的主流,但两国在民间层面仍然保持着一定的人员往来,并因此在潜移默化之间为1971年工党通过访华的方式推动澳中关系实现正常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早在1957年,也就是工党重新确立了其支持澳大利亚与中国建交的立场之后,就曾派遣过一支以党内议员莱斯利·海伦(Leslie Haylen)为首的代表团访问中国。(22)工党在1949年大选失利下台后曾一度在对华问题上持保守态度,直到1955年霍巴特会议后,工党才重新明确了其支持澳中建交的政策立场。参见Henry Stephen Albinski, Australian Policies and Attitudes Toward China, pp.113-118.海伦在华期间曾受到过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在会谈过程中,他介绍了工党在1955年举行的霍巴特会议之后明确的一系列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包括推动“发展不受限的对华贸易、在外交上承认中国以及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23)Leslie Haylen, Chinese Journey: the Republic Revisited. Sydney: Angus & Robertson, 1959, p.145.除了海伦之外,工党主席弗兰西斯·张伯伦(Francis Chamberlain)和议员托马斯·尤伦(Thomas Uren)等人亦曾在1958年和1960年分别到访过中国。(24)“A.C.T.U. SENDS 3 TO CHINA,” Tribune, February 26, 1958, p.1; Tom Uren, Straight left, Milsons Point, N.S.W: Random House, Australia, 1995, pp.117-118.
上述案例表明,在1971年惠特拉姆等人决定出访中国之前,工党方面就已经有过类似的尝试,只是由于彼时工党尚不具备获得赢得大选以推动澳中建交的条件,因此这些早期的访华人士未能获得像此后惠特拉姆等人一样的关注度。(25)费思棻指出,工党在当时并未切实地贯彻其支持澳大利亚与中国建交的宗旨的原因可能有两个,首先是其不得不顾及持反华立场的民主工党(Democratic Labor Party)在大选中的影响力,其次是因为“中国威胁论”的观点在工党内部仍有一定市场。Stephen FitzGerald, Talking with China: The Australian Labor Party Visit and Peking’s Foreign Policy, pp.6-7.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海伦等工党内的实力派人士的访华之旅毫无意义可言,相反,从他们在返回澳大利亚之后的一些言行来看,访华的经历不但给海伦等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强化了他们支持澳大利亚与中国建交的信念。海伦在返澳后不久就曾在时任工党领袖H.V.伊瓦特(H.V.Evatt)的支持下,公开致电美国驻澳大使W.J.塞巴尔德(W.J.Sebald),反驳其发表的反对澳大利亚与中国建交的言论。(26)参见“Mr. Sebald Attacked On Anti-China View,” The Canberra Times, 29 July, 1957, p.7.张伯伦则是对当时在澳大利亚国内以反共斗士著称的B.A.桑塔马利亚(B. A. Santamaria)发表的反华言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驳斥。(27)参见“ALP president’s China trip,” Tribune, July 2, 1958, p.5.尤伦同样曾在议会辩论中多次对新中国在社会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给予肯定,并且呼吁澳大利亚应当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28)参见“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Hansard, September 28, 1960, pp.1461-1463.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尤伦的上述言论绝非仅仅代表了他个人的观点,而是恰如冯兆基(Edmund S.K. Fung)和马克林(Colin Mackerras)所指出的那样,表达了工党党内许多人的心声。(29)参见Edmund S. K. Fung and Colin Mackerras, From Fear to Friendship: Australia’s Policies Toward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66—1982,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85, p.37.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海伦等人早期的访华之旅,为此后惠特拉姆等人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做了铺垫。
当然,在1972年澳中建交之前到访过中国的绝非仅仅只有工党人士。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曾迎接过不少澳大利亚知识分子或是和平人士。澳大利亚著名左翼记者威尔弗雷德·伯切特(Wilfred Burchett)即是为数不多的几名在50年代初就曾到过中国的民间人士,伯切特在1951年访华后撰写了《中国挣脱枷锁》(China’sFeetUnbound)一书,其中详细记录了他在北京、天津和淮河流域等地旅行的见闻,在其笔下,中国人民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呈现出一幅与此前截然不同、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同时也与他眼中物欲横流的西方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30)参见Wilfred G. Burchett, China’s Feet Unbound,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52.
尽管以伯切特为代表的这些早期访华人士对于新中国的正面叙述,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当时澳大利亚国内保守势力极力营造的反华浪潮所淹没,但他们的著作仍然在不经意间激发了少数澳大利亚的有识之士对于中国的兴趣,同时也对包括工党在内的澳大利亚各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事实上,在1971年工党的访华计划从最初提出到付诸行动的各个环节中,都可以观察到此前澳中民间往来留下的“蛛丝马迹”。
如上所述,1970年末澳对华小麦出口受挫是促使工党做出派出高规格代表团访华的直接诱因,但首先意识到“小麦危机”为工党提供了一个重要政治机遇的却恰恰是一名曾经熟读伯切特的著作并且有过早年亲身访华经历的工党领导人迈克·杨。在1971年4月于阿德雷德召开的工党联邦执委会会议上,杨提议工党派遣一支代表团访问中国,并获得了包括惠特拉姆在内的其他工党领导人的一致支持。(31)参见Gough Whitlam, The Road to China, Beijing: New Star Press, 2009, p.103; Stephen FitzGerald, Talking with China: The Australian Labor Party Visit and Peking’s Foreign Policy, p.10.杨之所以能够敢为人先,提出这一大胆倡议,一方面反映了他本人所具有的高度政治敏锐性,另一方面也与他早年的访华经历息息相关。(32)关于杨在捕捉政治机会方面的能力,参见Stephen FitzGerald and Garry Sturgess, “Stephen Fitzgerald Interviewed by Garry Sturgess in 2012 for Beyond the Cables-Australian Ambassadors to China Oral History Project,”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2012, Session 3, ORAL TRC 6440/3.
出生于草根阶层的杨在于1969年获选成为澳工党联邦书记之前,曾在新南威尔士州的布罗肯希尔(Broken Hill)从事过多年的剪羊毛工作并且担任过工会的干事。(33)关于杨的生平参见Stephen Guest, “Young’s Career Mirrors the Party’s Past 30 Years,” The Canberra Times, February 9, 1988, p.8; “The Rise, Fall, of Mick,” Sydney Morning Herald, July 29, 1984, p.4; Ross McMullin, The Light on the Hill: The Australian Labor Party, 1891—199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ustralia, 1991, p.324.在此期间,通过工友的介绍,杨接触到了由伯切特撰写的《中国挣脱枷锁》一书。(34)参见Stephen Guest, “Young’s Career Mirrors the Party’s Past 30 Years,” p.8.原文中提到伯切特的著作名为“China Freedom Bound”,应系笔误。伯切特在其书中所描绘的中国显然给杨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就在他读到前者的这本著作后不久,年仅21岁的杨便参加了由尤里卡青年团(Eureka Youth League)选派的代表团,先赴苏联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后又应邀前往中国进行访问。(35)参见“Keen Interest in Socialism,” Tribune, December 18, 1957, p.5. 尤里卡青年团是当时澳大利亚共产党的青年组织。
据杨在工党内的导师克莱德·卡梅隆(Clyde Cameron)回忆,这次访问苏联和中国的经历对杨起到了一种思想上的启蒙作用,使得他的政治立场更加趋向于“开明”和“进步”。(36)参见“The Rise, Fall, of Mick,” p.4.曾与杨同行共事的费思棻亦表示,虽然杨日后与左翼政治渐行渐远,但他始终对中国抱有浓厚的兴趣,并且坚信澳大利亚应当尽早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37)参见Stephen FitzGerald and Garry Sturgess, “Stephen Fitzgerald Interviewed by Garry Sturgess in 2013 for Beyond the Cables-Australian Ambassadors to China Oral History Project,” Session 3.惠特拉姆亦曾在回忆录中提到,每当忆起自己早年的访华经历时,杨常常满怀激情。(38)参见Gough Whitlam, The Whitlam Government, Ringwood, Victoria: Penguin Books, 1985, p.55.
杨早年的这次中国之行,显然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很深的触动,并且使得他坚信澳大利亚应当尽早与中国建交。也正是因为这一信念,杨才会在澳对华小麦销售受阻之时,大胆提议澳工党派遣代表团赴华,为澳中两国关系实现历史性的突破提供了可能。从一开始阅读伯切特的著作,到亲赴中国,再到日后提出工党派团访华的倡议,杨的上述经历看似偶然,实际上却恰恰体现了澳中建交前双方的民间往来对两国关系正常化起到的积极推动作用。
三、促成澳工党代表团访华的民间“先锋”
承上所述,工党领导人迈克·杨因为其早年的访华经历,成了促成1971年工党代表团出访中国的一个重要“幕后推手”。然而,工党方面在后续推进其访华计划时,却遭遇了一个无法与中方取得有效联系的尴尬局面,而惠特拉姆等人之所以能够最终顺利出访中国,还有赖于一名与中国渊源颇深的青年汉学家罗斯·特里尔的鼎力相助。
惠特拉姆在向周恩来总理致电表达了工党希望派遣代表团访华的意愿之后,并没有立刻收到中方的回应。考虑到若是中方不回复甚至直接拒绝己方提议的可能性以及由此将在政治上造成的负面效应,工党方面自然倍感焦虑,惠特拉姆本人甚至在同年4月21日(也就是电报发出7天之后)专门要求他的私人秘书理查德·豪尔(Richard Hall)向澳大利亚海外电讯委员会询问中方是否确实收到了来自工党方面的函电。(39)参见“F.A. Stanton’s letter to Gough Whitlam, 21 April, 1971”, Papers of Richard Hall, MS 8725,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Box 51, Series 15, File 2.
为了尽快敲定访华相关事宜,工党方面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探听中方对其来电的态度。当时负责工党农业事务的雷克斯·帕特森(Rex Patterson)就曾尝试联系他认识的“负责银行和小麦业务的中方技术人员”,希望后者能够助工党一臂之力,(40)Rex Patterson, “Letters to the Editor Solomon report,” The Canberra Times, 7 June, 1971, p.2.而惠特拉姆的私人秘书豪尔则是向特里尔发出了求助。
史料显示,在接到豪尔为工党访华一事向其求助的请求之后,特里尔曾多次联络他在世界各地的熟人朋友,包括彼时担任法国驻华大使的艾蒂安·马纳克(Étienne Manac’h),希望他们能够施以援手。(41)特里尔在与豪尔的通信中提及,他曾就工党访华一事求助过当时身在加拿大的林达光(Paul T.K. Lin)、马纳克以及香港《大公报》方面,参见“Ross Terrill’s letter to E. M. Manac’h, 28 April, 1971”; “Ross Terrill’s letter to Richard Hall,28 April, 1971”; “Ross Terrill’s Telegram to Lee Tsung-Ying, 26 April, 1971”, Papers of Richard Hall, all in Box 51, Series 15, File 2.其他佐证材料参见:Ross Terrill, “Australia and China,” Nation, August 7, 1971, pp.12-14;“How Labor group got to Peking,” Sydney Morning Herald, July 14, 1971, p.10, both in “China-Relations with Australia-Visits to China - ALP Delegation 1971,”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NAA): 3107/38/12/7 PART 2.在其于1971年4月28日寄给马纳克的求助信中,特里尔介绍了工党的访华计划出台的背景和惠特拉姆致电周恩来总理的情况,并且特别强调如果工党能够顺利赢得来年的大选,那么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将会迎来重大改变。(42)参见“Ross Terrill’s letter to E.M.Manac’h, 28 April, 1971”, Papers of Richard Hall, Box 51, Series 15, File 2.结合马纳克在5月27日给特里尔的电报,以及后者在其回忆录中的说法可知,马纳克是在5月7日接到了特里尔的信件,随后在第二天乘坐飞机时,遇见了时任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的韩叙,并请他向周恩来总理代为转达了工党方面的口信。后续的事态发展表明,马纳克这一打破外交惯例的举动应当是起到了效果,因为仅仅在两天之后,惠特拉姆就接到了来自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正式访华邀请。(43)参见“E.M.Manac’h’s telegram to Ross Terrill, 27 May, 1971”, Papers of Richard Hall, Box 51, Series 15, File 2; 罗斯·特里尔:《我与中国》,刘庆军、许道芝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6页;Gough Whitlam, The Whitlam Government, p.55;另外,关于韩叙当时与周恩来总理在工作上的联系情况,阮虹曾在其所著《韩叙传》中提道:“(韩旭)几乎天天都能见到周恩来。”阮虹:《韩叙传》,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125页。
如果没有特里尔通过马纳克在澳工党和中方之间牵线搭桥,惠特拉姆等人或许最终仍会收到中方同意他们访华的回信,但也很可能因为等待回信的时间过长而在政治上错失先机。事实上,在接到中方的电报之前,当时担任澳总理的威廉·麦克马洪(William McMahon)即抓住了工党方面“久候”中方回应未至的尴尬,对惠特拉姆致电周恩来总理的行为多有嘲讽。(44)参见“Uproar as Pm Plays His Hand on China,” The Canberra Times, April 21, 1971. p.1.更重要的是,即使工党的访华代表团最终能够顺利成行,如果他们未能在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宣布其访华决定之前抵达中国并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会谈,那么他们此番出访的政治意义亦将大打折扣。(45)关于工党代表团访华的时间节点所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参见Graham Freudenberg, “Introduction,” For the Record: Gough Whitlam’s Mission to China 1971, pp.4-6.因此,特里尔在确保工党代表能够顺利访华一事中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中间人”的作用,正是因为他通过马纳克向中方及时传达了工党方面的口信,才使得惠特拉姆等人不至于错失出访中国的最佳时机。
工党之所以会在当时寻求特里尔的帮助,很可能是因为后者是少数几名曾经有过亲身访华经历的中国问题专家。正像与他年纪相仿的杨一样,特里尔很早就萌生了对于中国的兴趣,并且同样受到过一名熟悉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影响。在墨尔本大学求学期间,特里尔曾受教于多名思想左倾的老师,其中就包括任教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知名汉学家费子智(C.P. Fitzgerald)。根据特里尔本人的回忆,费子智曾在重访中国后不久到过墨尔本大学给他和其他学生上过课,并且在课上介绍了当时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巨变。(46)罗斯·特里尔:《我与中国》,第6页。实际上,在这一时期访问过中国的澳大利亚知识分子之中,费子智或许是最具影响力的一人,由他发起创建并任首任主席的澳中协会(Australia China Society),是一个致力于推动澳中两国民间文化交流的组织。因此缘故,他与当时澳大利亚国内众多对中国抱有兴趣的各界人士都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并且曾经推荐他们中的部分人前往中国访问。(47)关于费子智当时与澳大利亚同情中国的各界人士保持的密切联系,参见C. P.(Charles Patrick) FitzGerald and Ann Turner, “C. P.FitzGerald Interviewed by Ann Turner,”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Session 2, ORAL TRC2797.费子智本人亦曾经于1956年率领澳大利亚文化代表团到访中国,并在返回澳大利亚后积极撰文分享他在华时的见闻。(48)参见C. P.FitzGerald, “The Changed Face of China,” Australian Cultural Delegation, ed., Report on China, Australia-China Society, Glebe: N.S.W. Branch, 1956. 关于费氏本人的著作和活动对澳大利亚公众眼中的中国形象和澳政府对华政策产生的影响,另可参见樊林:《汉学家费子智与澳大利亚公众中国观1949—1972》,《历史学教学问题》2013年第3期。除了撰写文章和讲学之外,他还频繁在澳大利亚各地举办公开演讲,向公众介绍他眼中的中国。(49)参见“CHINA MAY SOON MAKES DRIVE FOR MARKETS,” The Mercury, November 02, 1956, p.17; “Easier To See Red China Now, Says Professor,” The Mercury, November 06, 1956, p.2; “Professor claims that Red China has changed its attitude to the West,” Advocate, November 09,1956, p.4, all in “Charles Patrick FITZGERALD-Volume 2,” NAA: A6119, 675.
或许正是因为在大学期间就已经意识到中国对澳大利亚的重要性,特里尔才会参与创办了一个名为“承认中国”的学生团体,公开呼吁澳大利亚应当尽早承认新中国,并且在毕业后就决定亲赴中国旅行。(50)关于特里尔在大学期间参与创建“承认中国”团体并为其撰稿的情况,参见罗斯·特里尔:《我与中国》,第8—9页。在从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取得签证之后,特里尔于1964年取道莫斯科来华。在北京停留期间,特里尔对当地的市容市貌进行了细致的观察。他曾前往人民大会堂、天安门、颐和园参观,还去过北京市图书馆,并在米市大街教堂与赵复三牧师有过会面和交流。(51)罗斯·特里尔:《我与中国》,第18—21页。如同许多在这一时期到访过中国的西方人一样,特里尔注意到当时的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一整套基础社会保障制度,在其日后为《新共和国》(TheNewRepublic)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中他表示,北京的街头“并不总是永远干净或者没有任何异味,但却也未曾有明显恶化的迹象,亦没有像亚洲许多城市那样有着倒在路边的乞丐和病人。”(52)参见Ross Terrill, “A Trip to China II,” The New Republic, Vol.152, No.3, (January 16, 1965), p.14.在他的日记中,特里尔同样写道:“尽管小巷内比较拥挤,人们比较贫穷,但是没有一人衣衫褴褛,没有一人目光呆滞坐着或者躺着……尽管生活还很贫穷,但是整个社会井然有序,每个人都有尊严地活着。”(53)罗斯·特里尔:《我与中国》,第24页。
正如特里尔日后在《八亿人:真正的中国》(800,000,000:TheRealChina)一书中所提到的那样,尽管他的首次中国之旅只有短短两周时间,但这已经足以促使他下定决心“了解中国和学习中文。”(54)Ross Terrill, 800,000,000: The Real China, Boston: Little, Brown, 1972, p.9.也正是因为这一决心,在结束了其访华行程之后,特里尔旋即于1965年远赴美国就读哈佛大学,师从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攻读博士学位,由此正式踏上了中国研究之路。在攻读博士期间,特里尔曾基于自身的访华经历撰写了多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一举奠定了其作为一名青年汉学家的声名,为其之后参与到惠特拉姆的访华之行埋下了伏笔。(55)参见Ross Terrill, “A Trip to China,” The New Republic, Vol.152, No.1, (January 2, 1965), pp.9-11; “A Trip to China II,” pp.13-15; “A Trip to China III,” The New Republic, Vol.152, No.4, (January 23, 1965), pp.15-16.
正是由于特里尔是当时少数几名了解中国并拥有广泛人脉的澳大利亚人,澳工党方面才会在迟迟无法获知中方对其来电态度时向他求助,并最终通过他积极的“鸿雁往来”与中国方面取得了联系,确保了代表团能够顺利出行。作为澳工党代表团的“先锋”,特里尔本人则是在代表团抵达北京之前就已经事先应邀来华,并且在之后参与了周恩来总理与惠特拉姆的历史性会谈。(56)“先锋”一语为特里尔转述周恩来总理的说法,其意指前者为惠特拉姆等人的出访先行做了相关的准备工作,参见罗斯·特里尔:《我与中国》,第76—78页。
由特里尔上述的访华经历和他后续在工党代表团访华一事中发挥的作用可知,澳中建交之前双方的民间往来虽然看似雁过无声,实则在不经意间为两国关系的正常化铺平了道路。同时,我们也需注意到的一点是,相较于执政的自由党而言,工党在1955年霍巴特会议之后,对于发展对华关系这一点抱有更为积极的态度,因此才会在支持海伦等党内高层人士出访中国的同时,主动地与像特里尔这样的知识分子保持接触,确保了其能够在时机成熟之时采取果断的措施,从而推动了澳中关系的正常化。
结 语
作为一名以雷厉风行的施政风格而著称并因此备受争议的澳大利亚政治家,惠特拉姆生前曾多次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强调,早在1954年,也就是他所属的澳工党重新明确了其对华政策之前,他就曾基于现实主义的政治立场,公开呼吁澳大利亚应当尽早与中国建交。(57)参见Gough Whitlam, The Road to China, pp.5,9,30,46.澳中两国的关系之所以能够在1972年工党政府上台之后迎来历史性的突破,惠特拉姆在一众参与其中的澳方政治人物中自然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我们同样不应忽视的一点是此前两国之间存在的民间贸易往来和人文交流为此创造的有利条件。
这一“民间”因素的重要性在澳中建交的前奏曲即1971年由惠特拉姆率领的工党代表团对于中国的访问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首先,工党在当时做出的访华决策绝非仅仅是一种带有政治投机性质的草率之举,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叶,以海伦为代表的部分工党人士就曾以各种名义访问过中国。这些早期的访华尝试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强化了工党内部支持澳大利亚与中国尽早建交的信心。其次, 如果说澳大利亚对华小麦出口贸易在1970年遭遇到的危机,是促使惠特拉姆等工党领导人决定派出高规格代表团访华以寻求澳大利亚对华关系突破的一个重要契机,那么,迈克·杨和罗斯·特里尔则是确保了工党的这一大胆设想能够得以实现的关键。是杨首先意识到澳对华小麦销售危机对于工党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机遇并提出了访华的动议,而远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的特里尔,则是在惠特拉姆等人因迟迟无法与中方建立直接联系而一筹莫展之时,灵活运用了自己的人脉关系,在双方之间频繁牵线搭桥,一举敲定了澳工党的访华行程。
杨和特里尔之所以能够在促成工党代表团访华一事中发挥上述重要作用,无疑与他们早年的访华亲身经历息息相关。这一共同点的存在绝非偶然,而是恰恰印证了澳中建交前澳国内少数访华人士为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做出的努力,虽然时常被澳大利亚政坛弥漫的反共反华的言论所掩盖,却始终是一缕未曾间断的“执拗低音”。(58)“执拗低音”一词借用自王汎森所著《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但拙文中的“低音”并非意指遭受压抑的学术论述,而是指一种由部分澳访华人士建构的,更为广义的关于中国的叙事。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第1—2页。无论是以伯切特和费子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还是海伦等工党人士的访华之旅都表明,当时西方部分反共人士所极力渲染的“竹幕”(bamboo curtain)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其并未完全阻断澳中两国民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正是通过许多澳方访华人士在回国后的积极宣传,一种不同于当时澳国内主流的“中国威胁论”的中国形象才得以随着时局的变化日渐深入人心,并由此为工党最终在推动澳中关系正常化的道路上迈出关键性的一步奠定了民意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