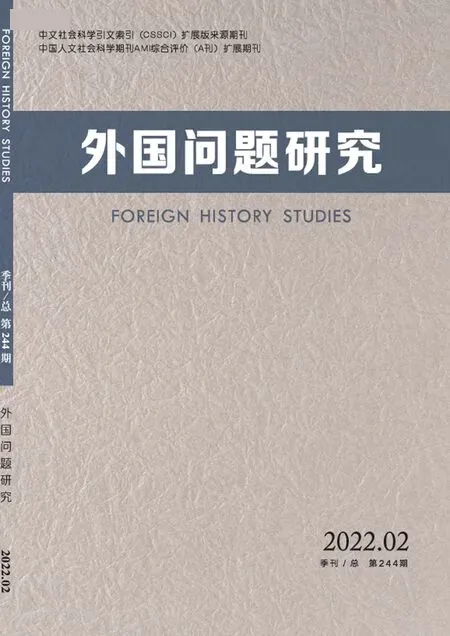近代早期英国的私生子问题与国家治理
2022-12-28初庆东
初庆东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作为非婚性行为的一个结果,私生子的数量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英国呈现爆炸式增长。彼得·拉斯莱特等学者以英国24个教区为样本,重新统计1561—1960年间私生子的数量,指出16世纪末17世纪初私生子数量达到第一个高峰。(1)Peter Laslett and Karla Oosterveen, “Long-Term Trends in Bastardy in England,” Population Studies, Vol.27, No.2 (Jul. 1973), p.283.拉斯莱特甚至认为,这一时期英国出现了一个“私生子成风的亚社会”(bastardy prone sub-society)。(2)Peter Laslett, “The Bastardy Prone Sub-Society,” Peter Laslett, Karla Oosterveen and Richard M. Smith, eds., Bastardy and Its Comparative History, London: Edward Arnold Ltd, 1980, pp.217-240.私生子数量的激增不仅加剧近代早期英国的贫困问题,而且不利于社会稳定,因而引起国家的高度关注。(3)史蒂夫·欣德尔认为“国家”不仅包括国王、大臣、王室官员以及中央政府的各机构,也包括郡、市镇、教区中的地方政府以及使其运转的低级官员,本文即在此意义上使用“国家”一词。参见Steve Hindle, The State and Social Chang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1550-1640,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0, p.21。
自20世纪70年代以降,随着英国“新社会史”研究的兴盛,私生子问题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相关研究不断涌现。以劳伦斯·斯通、基思·赖特森、马丁·英格拉姆为代表的学者围绕国家管控私生子的原因展开讨论,以安东尼·弗莱彻、沃尔特·金为代表的学者则考察国家管控私生子的具体举措。(4)Lawrence Stone, The Family, 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1800, London: Harper & Row, 1977, pp.483-648; Keith Wrightson, “The Nadir of English Illegitimac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eter Laslett, Karla Oosterveen and Richard M. Smith, eds., Bastardy and Its Comparative History, pp.158-191; Martin Ingram, “The Reform of Popular Culture? Sex and Marriag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Barry Reay, ed., Popular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London: Routledge, 1988, pp.129-165; Anthony Fletcher, Reform in the Provinces: The Government of Stuart England,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252-262; Walter J. King, “Punishment for Bastardy in Early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Albion, Vol.10, No.2 (Summer 1978), pp.130-151.约翰·维特从法律和宗教层面梳理私生子的法律规定,而帕特里夏·克劳福德和萨曼莎·威廉姆斯则聚焦私生子父母的境遇。(5)John Witte, Jr., The Sins of the Fathers: The Law and Theology of Illegitimacy Reconsider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atricia Crawford, Parents of Poor Children in England, 1580—18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Samantha Williams, Unmarried Motherhood in the Metropolis, 1700—1850, London: Macmillan, 2018.总体而言,国外学者对私生子问题的研究成果较为宏富,视角也比较多元,但未能凸显治安法官在私生子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也未能关照中央与地方在私生子问题治理过程中的互动。相较而言,国内学界对私生子问题的研究较为薄弱。(6)陈志坚探讨了中世纪英格兰教会对私生子权利的保护,参见陈志坚:《试析中世纪英格兰教会对私生子权利的保护》,《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黄薇薇考察了旧济贫法对私生子救济的问题,参见黄薇薇:《英国旧济贫法中私生子救济问题探析》,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15年。基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分析国家管控私生子的动因入手,聚焦治安法官应对私生子问题的司法实践,进而评析社会转型时期英国国家治理的特征与成效。
一、私生子问题的形成与国家管控的动因
私生子是合法婚姻之外的子女,“是私通、通奸、蓄妾、乱伦、狎妓或其他性犯罪的产物”。(7)约翰·维特:《西方法律和宗教传统中的非婚生子女》,钟瑞华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页。16—17世纪之交,英国私生子的数量急剧增加,出现“私生子爆炸”的现象。(8)Peter Laslett, “Introduction: Comparing Illegitimacy over Time and between Cultures,” Peter Laslett, Karla Oosterveen and Richard M. Smith, eds., Bastardy and Its Comparative History, p.24.拉斯莱特和欧斯特维指出,伊丽莎白一世晚期兰开夏和柴郡等地的一些教区中,私生子的出生率高达9%到10%,这一比例即使在工业革命时期工业化区域也难以企及。(9)Peter Laslett and Karla Oosterveen, “Long-Term Trends in Bastardy in England,” p.255.坎布里亚郡彭里斯村(Penrith)在1600—1649年私生子的出生率是3.2%,而在1650—1749年私生子的出生率仅为1.1%。(10)Susan Scott and C. J. Duncan, “Interacting Factors Affecting Illegitimacy in Preindustrial Northern England,” Journal of Biosocial Science, Vol.29, No.2, 1997, p.156.埃塞克斯郡特灵村在1570—1699年间共有82起私生子案件,其中有27起案件发生在1597—1607年间。(11)Keith Wrightson and David Levine, Poverty and Piety in an English Village: Terling, 1525—170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p.127.多切斯特在1597—1601年间私生子数量达到最高值,这一时期私生子的出生率为7%,随后锐减。(12)David Underdown, Fire from Heaven: Life in an English Tow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London: Fontana Press, 1992, p.107.麦克法兰认为,1560—1640年间私生子数量的峰值出现在1600—1627年。(13)Alan Macfarlane, “Illegitimacy and Illegitimates in English History,” Peter Laslett, Karla Oosterveen and Richard M. Smith, eds., Bastardy and Its Comparative History, p.82.在全国范围内,私生子的数量在1581—1640年达到第一个高峰。(14)Peter Laslett, Family Life and Illicit Love in Earlier Generations: Essays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133.1591—1600年全国私生子的出生率为4.6%,而1651—1660年全国私生子的出生率仅为0.5%。(15)Peter Laslett and Karla Oosterveen, “Long-Term Trends in Bastardy in England,” p.267.据此可知,16世纪末17世纪初英国私生子的数量达到高峰,而在1650年之后私生子的数量锐减。
“私生子爆炸”现象的出现是近代早期英国经济波动与婚姻习俗交互影响的结果。一方面,自16世纪“价格革命”以来,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这一经济危机不仅影响穷人,也对中上阶层的很多年轻人产生影响。(16)David Levine and Keith Wrightson, “The Social Context of Illegitimac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p.174-175.近代早期英国民众结婚的年龄一般较晚,因为大多数民众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来积聚结婚所需财产。(17)Martin Ingram, Carnal Knowledge: Regulating Sex in England, 1470—16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24-25, 57.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市镇和乡村中剩余大量未婚但已性成熟的年轻人,他们在舞会、狂欢和啤酒馆等场所亲身体验身体亲密接触的快感。(18)Ralph A. Houlbrooke, The English Family 1450—1700,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84, pp.72-73.这些场所为适婚之人发生非婚性行为提供了温床,随之而来的便是私生子数量的增多。(19)A. Lynn Martin, Alcohol, Sex, and Gender in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New York: Palgrave, 2001, chs.3-5.另一方面,近代早期英国的婚姻习俗是男女双方只要订立婚约,便确立婚姻关系,进而发生性行为,而婚约却常常因各种原因而未能兑现,这就造成私生子数量的激增。例如,在埃塞克斯郡和兰开夏的很多村落中,一些年轻人在16世纪90年代的饥荒过后,随着婚姻机会的增多,很多适龄男女订立婚约,并发生性行为。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些年轻人越来越难挣到钱以履行婚约,致使1597—1607年私生子案件猛增。(20)Keith Wrightson, “The Nadir of English Illegitimac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p.176-191.夏普教授也确认埃塞克斯郡私生子母亲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在发生性行为之前获得结婚的允诺,参见J. A. Sharpe, Crim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A County Stu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60。
私生子数量的急剧增加引起时人的高度关注,这与近代早期英国的人口增长、经济危机、社会分化及宗教改革等因素密切相关。首先,私生子数量的剧增不利于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这成为国家管控私生子数量的政治动因。近代早期英国是一个“家长制”社会,小到家庭,大到国家,都强调“服从”与“保护”,以此强化政府权威和维持社会秩序。(21)关于近代早期英国“家长制”的详细论述,参见初庆东、刘金源:《〈工匠法令〉与英国前工业化时期的劳资关系》,《安徽史学》2017年第1期。私生子作为非婚性行为的结果,是不为“家长”所允许的,因为“每一个女性都是其父亲或丈夫的财产,所以任何陌生人与之发生性关系,都得被视为一种盗窃,一种对其亲属的严重侮辱”。(22)法拉梅兹·达伯霍瓦拉:《性的起源》,杨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26页。而且私生子的降临“危害了继承权与父系的传承”,不利于家庭和谐。(23)法拉梅兹·达伯霍瓦拉:《性的起源》,第112页。一些私生子母亲又往往是妓女,更为社会所不容。例如,埃塞克斯郡一位居民在1623年被怀疑有私生子,随后又被控卖淫。(24)J. A. Sharpe, Crim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A County Study, p.58.家庭作为最基本的生产和消费单位,是社会秩序和政治权威最基本的机构。(25)Martin Ingram, Church Courts, 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70—16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25.家庭的稳定与否直接攸关国家稳定与社会秩序。而私生子数量的激增,严重威胁家庭和谐与国家稳定,故此国家积极管控私生子的数量。
其次,私生子数量的剧增加重对经济资源的压力,致使贫困问题愈发严峻,这成为国家管控私生子数量的经济动因。从16世纪中叶到内战前夕,英国人口基本呈现持续增长态势。据统计,除1561年因瘟疫与饥馑导致人口下降外,从1541年到1641年英国人口数量从2 773 851人增加到5 091 725人。在一个世纪中,英国人口增加近两倍。1641年之后,英国人口总数基本稳定,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8世纪。(26)E.A. Wrigley and R. S. Schofield, 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 1541—1871: A Reconstr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208-209, 402.与此同时,16世纪爆发的“价格革命”使得物价飞涨,穷人数量剧增且生活每况愈下。克拉克和斯莱克根据16世纪20年代的税收档案,揭示出英国城市中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在随后一个世纪里贫富鸿沟越来越大。(27)Peter Clark and Paul Slack, English Towns in Transition 1500—1700,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112-114.霍斯金斯认为,16世纪英国城市人口中穷人和劳工占三分之二,他们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或接近贫困线。(28)W. G. Hoskins, The Age of Plunder: King Henry’s England, 1500—1547, London: Longman, 1976, pp.96-100.在人口增长与物价飞涨的压力下,贫困问题更加凸显,而私生子的抚养问题又使贫困问题加剧。人们甚至认为私生子泛滥是贫困的根源,是无谋生能力与上年纪的穷人之骗局。(29)Joan Wake, ed., Quarter Sessions Records of the County of Northampton, Hertford: Northamptonshire Record Society, 1924, p.xxxi.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不仅要严格管控私生子的数量,而且需要解决私生子的抚养问题。
再次,私生子有违基督教的性道德教义,因而遭到清教徒的猛烈抨击,这成为国家管控私生子数量的宗教动因。教会反复强调婚姻是性行为和繁衍后代的唯一合法途径。(30)约翰·维特:《西方法律和宗教传统中的非婚生子女》,第4页。随着宗教改革的推进,清教徒猛烈抨击有违上帝的行为,认为非婚性行为是一种罪。(31)Patricia Crawford, Parents of Poor Children in England, 1580—1800, p.34.在清教徒看来,“性像睡眠和吃喝一样是生活的必要组成;如果能‘适当节制地’只在婚床上享受性,那么性是‘上帝的美好和无限甜蜜的标志’。然而,只有夫妻之间的性是美妙的,其他任何形式的性关系都是被诅咒的。”(32)埃里克·伯科威茨:《性审判史》,王一多、朱洪涛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44页。正如劳伦斯·斯通所言:“17世纪初英国相当高的性道德标准的主要肇因是清教组织及清教训诲的压力。”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一位绅士抗拒“婚前引诱他恋慕的年轻寡妇”的意念,因为“我们会挑起上帝的愤怒,因我们的邪恶而申斥我们”。(33)劳伦斯·斯通:《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1500—1800》,刁筱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405—406页。清教牧师也认为,私生子母亲的“放荡生活不仅会让上帝的怒火降临到我们这些小镇居民身上,她的邪恶还是个坏榜样,极可能腐蚀其他人”。(34)埃里克·伯科威茨:《性审判史》,第147页。私生子是非婚性行为的结果,而非婚性行为是被上帝诅咒的,会受到上帝的惩罚,因此在清教徒看来私生子是绝不会被允许的。
最后,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穷人与以“中等收入者”(middling sort)为主体的社会上层之间的分野愈发明朗,在此情况下“中等收入者”对穷人的态度发生显著变化。他们开始积极规训穷人的性行为,限制穷人缔结婚姻,严厉惩罚诞下私生子的穷人,这成为国家管控私生子数量的社会动因。“中等收入者”是“在中世纪等级制度瓦解之后从平民中分化出来的富裕社会阶层,包括城市市民和农村的‘约曼农’”,他们勤劳节俭、行为庄重。(35)向荣:《啤酒馆问题与近代早期英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冲突》,《世界历史》2005年第5期。在清教徒抨击非婚性行为的影响与自身经济利益的双重考量下,“中等收入者”积极规训穷人的非婚性行为和控制私生子的数量。从16世纪末开始,教区负担救济穷人的重任,而“中等收入者”是教区济贫税的主要承担者,所以穷人的私生子增加了“中等收入者”的济贫负担,有损他们的经济利益。例如,在一起诉讼案件中有如此陈述:“我们已经有太多可怜的私生子要养,压力太大。”(36)埃里克·伯科威茨:《性审判史》,第147页。随着“中等收入者”对穷人性行为观念的变化,到17世纪“中等收入者”很少成为私生子的父亲,而私生子日益成为穷人的“专利”。(37)Martin Ingram, “The Reform of Popular Culture? Sex and Marriag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156.赖特森通过对特灵村的案例分析认为,“尽管社会上层或中间阶层的一些家庭成员有私生子,但私生子主要还是穷人和名不见经传之人的罪行。”(38)Keith Wrightson and David Levine, Poverty and Piety in an English Village: Terling, 1525—1700, pp.128-130.“中等收入者”对非婚性行为与私生子态度的变化,促使国家管控私生子的数量。
二、国家立法与治安法官的司法实践
面对日益严重的私生子问题,国家授权治安法官承担私生子问题治理的主体责任,这与治安法官在近代早期的权力增长密切相关。从16世纪开始,治安法官渐次成为地方政府的权力中枢,掌握地方政府的行政与司法大权。治安法官的职责广泛,涉及地方社会的方方面面,为此梅特兰曾言:“律师已经放弃描述治安法官职责的尝试,或许字母表为这种尝试提供了一条线索。”(39)F. W. Maitland, Justice and Police, London: Macmillan, 1885, p.84.其中,惩罚私生子的父母与解决私生子的抚养问题,便成为治安法官的重要职责所在。
1576年,议会通过法令明确规定私生子的抚养权交由私生子降生的教区负担,授权两名治安法官经过调查后行使自由裁决权,惩罚私生子父母。治安法官有权要求私生子父母每周缴纳一定钱数,以抚养私生子。私生子父母如有违反,治安法官有权判处其监禁。(40)The Statutes of the Realm, Vol.4, London: Dawsons, 1963, p.610.但该法令规定的自由裁决权容易造成治安法官之间围绕判决结果而发生争执。例如,1578年的一天,埃塞克斯郡治安法官莫利勋爵(Lord Morley)和莱文索普(Leventhorpe)碰面以解决一起私生子案件,私生子父母是莫利勋爵辖区的史密斯和勋爵的女仆。史密斯打发那位女仆到莱文索普司法辖区的阿什威尔(Ashwell)教区,但遭到该教区居民的驱逐。于是莫利勋爵希望莱文索普接受“一份有良心的”私下协议,在该协议中史密斯愿意每周向女仆支付2镑作为生活费用,这个数目远远高于法律规定的数额,但遭到莱文索普的回绝。莱文索普认为:“犯罪与邪恶应该受到惩罚,犯法者按律当受鞭刑。”莫利勋爵宣称史密斯是他的租佃农,不受莱文索普的司法管辖。莱文索普则平静地答复:“那就让他带着他的女人离开我们的教区,让他不要把她丢在这里成为麻烦与负担……否则他将受到惩罚。”(41)Joel Samaha, Law and Order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Case of Elizabethan Essex, New York and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74, pp.67-69.因为阿什威尔是莱文索普的司法辖区,所以莫利勋爵只能屈从。
治安法官的自由裁决权在议会也引发激烈争论。早在1584—1585年,一些清教徒议员希望国家将私生子的出生定为犯罪而予以惩罚。一份“要求市镇对非婚生子不予负担”的法案坚持认为:单身孕妇“一经发现诞下子女”,便被送往教养院,予以鞭刑;私生子之父则被监禁一年,每月鞭打,并要求其保证下不为例。(42)David Dean, Law-Making and Society in Late Elizabethan England: The Parliament of England, 1584—160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85-186.尽管这一法案在议会未能通过,但随着私生子数量的急剧增加,议会最终在1610年颁布法令,明确要求如果“淫荡的妇女诞下私生子后,对教区造成负担”,那么治安法官应将她送往教养院监禁一年,使她在教养院接受惩罚与工作。如果再犯,则被监禁在教养院,直至她能够缴纳一笔不菲的保证金。(43)The Statutes of the Realm, Vol.4, pp.1160-1161.1610年法令明确要求治安法官惩罚那些对教区构成负担的私生子母亲,但没有提及私生子父亲的处置方式,而且对有能力抚养私生子的母亲免于惩罚。
在法令推行的过程中,各郡治安法官的政策存有差异。以柴郡、汉普郡和萨塞克斯郡为代表,治安法官在17世纪初并未惩罚私生子的父母。(44)Anthony Fletcher, Reform in the Provinces: The Government of Stuart England, p.256.相较而言,埃塞克斯郡治安法官严厉惩罚私生子的母亲,并且惩罚的力度逐渐加大:1580年之前,治安法官仅要求私生子母亲在原料仓库中工作几个小时;1580年之后,治安法官往往要求将私生子母亲绑在推车尾部进行鞭笞,但鞭笞的力度“适中”;1600年之后,治安法官要求鞭笞私生子母亲直到其背部血肉模糊;1610年之后,治安法官要求私生子母亲除接受鞭笞外,还需在教养院接受为期一年的惩罚。(45)William Hunt, The Puritan Moment: The Coming of Revolution in an English Coun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76.萨默塞特郡治安法官则通过强调惩罚的羞辱感以达到最大程度的威慑作用。治安法官通常在市镇繁忙时公开鞭笞私生子母亲,并押解她穿过市镇,往返持续一个小时。例如,一名私生子母亲在节庆活动日当民众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公开接受鞭笞,另一私生子母亲则在晚祷结束后被游街鞭笞。犯有非婚性行为前科的妇女,或丢下私生子不予抚养的妇女,再或错指私生子生父的妇女,将会受到在连续几天的市集上多次鞭笞的惩罚。(46)G. R. Quaife, Wanton Wenches and Wayward Wives: Peasants and Illicit Sex in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London: Croom Helm, 1979, pp.217-220.兰开夏治安法官在1600—1660年间惩罚私生子母亲共有90人,而私生子父亲有40人;拘禁29名私生子母亲,而私生子父亲只有2人;另外,在缴纳保证金后,治安法官允许接近一半的私生子父亲离开监狱,而私生子母亲离开监狱的比例仅有十三分之一。据此可知,兰开夏治安法官惩罚私生子母亲与父亲的方式有别。私生子母亲因为诞下私生子而被惩罚,而私生子父亲则因为不能提供抚养私生子的费用而被惩罚。(47)Walter J. King, “Punishment for Bastardy in Early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p.140.对私生子父母的区别对待,日益成为治安法官的共识。
一些郡的治安法官出于对私生子问题的担忧,积极推行1610年法令中关于教养院的规定。例如,埃塞克斯郡、兰开夏和沃里克郡在法令颁布之后便立即予以执行。(48)William Hunt, The Puritan Moment: The Coming of Revolution in an English County, p.76.威尔特郡治安法官在17世纪20年代往往通过教养院惩罚私生子的母亲。(49)Martin Ingram, Church Courts, 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70—1640, p.338.诺丁汉郡也积极执行对非婚性行为者监禁在教养院的处罚。例如,1653年1月治安法官判定一名私生子母亲监禁在教养院“劳动,并为她的罪行接受适当惩罚,在(教养院劳教)一年”。(50)H. Hampton Copnall, ed., Nottinghamshire County Records: Notes and Extracts from the Nottinghamshire County Records of the 17th Century, Nottingham: Henry B. Saxton, 1915, p.123.而萨默塞特郡治安法官直到17世纪30年代才放弃鞭笞,转而支持惩罚时间更长的教养院。(51)J. S. Cockburn, ed., Western Circuit Assize Orders 1629—1648: A Calendar, London: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1976, p.144.柴郡治安法官则对教养院的态度比较谨慎,1638年,柴郡治安法官规定教养院监禁仅适用于惯犯,而且要求对私生子父母的鞭笞需要证据充足。(52)J. S. Morrill, Cheshire 1630—1660: County Government and Society during the English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246.在17世纪的赫特福德郡、兰开夏、萨默塞特郡、沃里克郡,至少有203名私生子母亲受到治安法官的惩罚,其中有112名私生子母亲被监禁在教养院。(53)Steve Hindle, The State and Social Chang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1550-1640, p.186.由此可见,尽管治安法官运用教养院惩罚私生子母亲的情况在各地存有明显差异,但教养院仍不失为治安法官规训私生子母亲的有力工具。
治安法官积极惩罚私生子的父母,那么私生子如何处置呢?在中世纪与近代早期英国普通法的谱系中,私生子“不是任何人的子女”,所以要备受谴责和限制,但私生子又是“每一个人的子女”,所以理应得到抚养和保护,尤其是在年幼之时。(54)约翰·维特:《西方法律和宗教传统中的非婚生子女》,第130页。为解决私生子的抚养问题,治安法官往往要求私生子的母亲和被指认的私生子父亲向教区缴纳一定数额的抚养费用。如果私生子父母愿意自己抚养的话,便不用缴纳费用。例如,1657年北安普敦郡季审法庭受理一起私生子案件,治安法官判定私生子的父亲须在私生子7岁之前,每周向教堂执事和济贫管理员缴纳1先令6便士;在私生子7岁之后,其父须缴纳6镑13先令4便士以使私生子成为学徒,获得谋生技能。同时,治安法官要求私生子的父亲缴纳40镑保证金。另外,治安法官要求私生子的母亲每周缴纳6便士。(55)Joan Wake, ed., Quarter Sessions Records of the County of Northampton, p.166.
私生子父亲的指认成为治安法官解决私生子抚养问题的核心所在,因为只有确认私生子的父亲才有可能获得私生子的抚养费用,从而避免私生子成为教区的负担。例如,1616年一位怀有私生子的母亲在助产士和邻居的要挟下,被迫坦白那位私生子父亲的名字。(56)法拉梅兹·达伯霍瓦拉:《性的起源》,第28页。在一些案件中,私生子的父亲为逃避责任,唆使私生子的母亲误指私生子的父亲。例如,埃塞克斯郡一名男子与其14岁大的女仆发生性关系,并告诉她如果有孩子降生,就将孩子生父指认为在军队服役的士兵。另在两起案件中,私生子父亲用5镑收买私生子母亲,要求她们指认别的男子来承担责任。(57)J. A. Sharpe, Crim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A County Study, p.59.对于逃跑的私生子父亲,治安法官有权按照“养育和供养私生子”的实际需要,“占用和没收私生子父亲的物品和财产,在其土地上按年收取租金”。(58)The Statutes of the Realm, Vol.5, p.404.
由是观之,治安法官积极运用自由裁决权,通过鞭笞、羞辱性惩罚、教养院监禁等方式严厉惩罚私生子的母亲,并要求私生子父亲负担私生子的抚养费用,这表明治安法官的司法实践具有十分明显的实用主义风格。治安法官对私生子父亲的惩罚更多的是经济考量,而对私生子母亲的惩罚更多地缘于道德考量。治安法官对私生子父母的区别对待与国家法令基本一致,其目的是避免私生子成为教区负担,纾解教区的济贫负担,实现维护社会秩序的最终目的。同时,治安法官惩治私生子父母的司法实践也表明,近代早期英国的两性关系是不平等的。治安法官对私生子父母的区别对待在客观上强化了“双重的性标准”,即对女性贞洁的严格监管,同时也确认了男人对其妻子和女儿的所有权。(59)法拉梅兹·达伯霍瓦拉:《性的起源》,第112页。正是基于这种观念,治安法官更加积极地惩治私生子母亲,追查私生子父亲,严格监管非婚性行为。
三、治安法官与私生子问题治理机制的形塑
治安法官管控私生子的司法实践并非在权力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受到多重权力的制约,是多方妥协合作的结果。(60)Cynthia B. Herrup, The Common Peace: Participation and the Criminal Law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166-168.国王通过王室敕令要求治安法官管控私生子的数量。例如,1603年詹姆斯一世发布敕令指出,由于某些治安法官的懒惰与纵容,放荡之人充斥在王国的各个地方,这严重威胁整个王国的秩序。(61)James F. Larkin and Paul L. Hughes, eds., Stuart Royal Proclamations, Vol.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51-52.议会授予治安法官惩罚私生子父母的自由裁决权,从而使治安法官的司法实践获得法律权威。枢密院拥有治安法官的选任权,有权监督治安法官依法履职,并罢免不称职的治安法官。例如,1610年枢密院指责柴郡一些治安法官工作不力,谋取私利,并勒令他们依法行事。(62)T. C. Curtis, “Quarter Sessions Appearances and Their Background: A Seventeenth-Century Regional Study,” J. S. Cockburn, ed., Crime in England 1550—1800, London: Methuen, 1977, p.148.17世纪30年代,大法官考文垂勋爵罢免年龄过大与懒惰的治安法官。(63)Anthony Fletcher, Reform in the Provinces: The Government of Stuart England, p.9.为弥补枢密院的不足,国王选派王室法官担任巡回法官,每年两次巡回地方,监督治安法官的活动。例如,1617年弗朗西斯·培根爵士在巡回法官夏季巡回的指令中对巡回法官们说:“你们除日常的司法职责之外,还携带着国家的两面镜子。你们有义务将国王的荣光与关切传达给民众;在你们回来的时候,有义务向国王汇报民众的不满与悲伤。”(64)James Spedding, ed., The Letters and the Life of Francis Bacon, Vol.VI, London: Longmans, 1872, p.211.从国王、议会、枢密院到巡回法官,中央政府多渠道监督与敦促治安法官管控私生子,以使国家政令落到实处。
但治安法官不靠国家薪俸过活的特点,加之议会法令授予治安法官的自由裁决权,使得治安法官在管制私生子问题上具有较大独立性,他们有权决定是否执行中央政令以及执行的进度与程度,从而迫使“军事官僚国家机器比较薄弱”的中央政府必须依赖治安法官的合作。(65)王觉非主编:《近代英国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页。赖特森指出,秩序的形成过程“依赖多方对政府决策的赞同”,这在治安法官治理私生子问题的过程中获得集中体现。(66)Keith Wrightson, English Society 1580—1680, London: Routledge, 2002, p.153.中央与地方的合作关系成为私生子问题治理的重要保障,这也印证了史蒂夫·欣德尔的论断,即治理是“一个多方提议通过空间和社会秩序而达成的一系列协商谈判的过程”,“议会立法、枢密院法令或王室敕令绝非法律形成的结束而是开端……国家形成与其说是中央集权化,毋宁说是国家权力地方化的过程。”(67)Steve Hindle, The State and Social Chang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1550-1640, p.23.换言之,私生子问题的治理与其说是中央政府强力干预的结果,毋宁说是以治安法官为权力主体的地方政府积极参与的结果。治安法官不仅需要借助国家法令获取合法性权威,而且需要教区官员与民众的合作,由此形成广泛的社会参与和合作的局面,这成为治安法官治理私生子问题的第一个显著特征。
治安法官治理私生子问题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是治安法官在国家法令的基础上行使自由裁决权,这成为近代英国“法治”的一个真实写照。法律是秩序与权威的基石,而法律机构成为维护秩序与权威的强有力工具,但法律和法律机构的出现并不能保证“法治”的形成。“法治表达的是法律运行的状态、方式、程序和过程,”(68)陈晓律:《从习俗到法治——试析英国法治传统形成的历史渊源》,《世界历史》2005年第5期。而法律的运行仰赖广泛意义上的个人与公共道德。(69)Martin Ingram, “Reformation of Manner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aul Griffiths, Adam Fox and Steve Hindle, eds., The Experience of Authori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London: Macmillan, 1996, p.49.肯特郡治安法官威廉·兰巴德在1582年写道:“如果法律没有道德,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抱怨的错误如果不能通过严厉惩罚来矫正,那么我们还能得到什么?毫无疑问,罪恶的渊薮在于犯罪者的恶念,其次在于那些获得信任执行法律之人的怠慢。”(70)Conyers Read, ed., William Lambarde and Local Government,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68-69.治安法官作为执行法律之人,在遵循国家法令的基础上积极运用自由裁决权解决私生子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凸显了治安法官“法治”的两大特点,即个人性与合作性。一方面,治安法官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决定私生子父母的处罚力度;另一方面,从私生子父母的控告到判罚,都离不开教区官员与民众的合作。(71)初庆东:《近代早期英国治安法官与犯罪问题的治理》,《历史教学问题》2020年第5期。国家的正式官员(治安法官、警役等)与民众共享国家司法权力,使大多数民众参与到国家的“法庭之网”中。恰如詹姆斯·夏普所言,民众对政府和社会秩序的认知“根本上是由民众参与法律运作过程的法律体验决定的”,如此便扩展了政府权威和国家权力,从而推进国家治理向纵深扩展。(72)J. A. Sharpe, Crim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1550—1750,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84, pp.141-142.
治安法官治理私生子问题的第三个显著特征是世俗权威与宗教权威的结盟。由于私生子不仅有违基督教的教义,而且也是对社会秩序的威胁,所以宗教权威与世俗权威结成联盟共同治理私生子问题。从16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舆论不断强调世俗与宗教结盟的传统。(73)Steve Hindle, The State and Social Chang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1550-1640, p.179.例如,1586年爱德华·哈钦斯在切斯特巡回法庭的一次布道中说道:“我们的布道和著述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孤立地获得胜利”,“牧师用词,地方官用剑;前者通过爱,后者通过恐惧;前者和风细雨,后者狂风暴雨;前者通过劝说,后者通过惩罚,如果劝说不能奏效的话。”(74)Edward Hutchins, A Sermon Preached in West-Chester the viii. of October, 1586, Oxford: Joseph Barnes, 1586, p.B3.世俗的“司法之剑”(sword of justice)与宗教的“上帝之词”(word of God)的结盟,表明地方官员与牧师在一个有序的国家中功能互补,共同构成近代早期英国社会控制的有机系统。(75)Patrick Collinson, The Religion of Protestan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2, p.156; p.171.“剑与词”的修辞带来的实际效果在多切斯特、埃克塞特、格洛斯特、赫尔、伊普斯威奇、金斯林、拉伊和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等“上帝之城”中感受更为强烈。(76)Patrick Collinson, The Birthpangs of Protestant Englan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8, pp.28-59.以多切斯特为例,1600年之后私生子的数量急剧下降。(77)David Underdown, Fire from Heaven: Life in an English Tow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107.此外,很多治安法官自身便是清教徒,他们积极倡导治安法官与牧师合作,大力解决私生子问题,以创建一个虔诚的国家,这在诺福克郡治安法官纳撒尼尔·培根爵士身上获得集中呈现。例如,1602年10月15日培根爵士与其他两名治安法官判决私生子父母接受公开鞭笞,并对他们课以罚金。(78)Victor Morgan, Jane Key and Barry Taylor, eds., The Papers of Nathaniel Bacon of Stiffkey, Vol.IV, Norfolk: Norfolk Record Society, 2000, p.290.
尽管私生子数量的变化与城镇增长、工业化、婚姻年龄、人口的性别构成等多重因素相关,但政府和教会对私生子问题的联手管制,直接促使17世纪中叶英国私生子数量的锐减。(79)Peter Laslett and Karla Oosterveen, “Long-Term Trends in Bastardy in England,” p.257.例如,埃塞克斯郡特灵村在1630年之后私生子案件已比较少见。(80)Keith Wrightson and David Levine, Poverty and Piety in an English Village: Terling, 1525—1700, p.127.拉斯莱特等人的实证研究也表明英国私生子的出生率从17世纪初年开始下降,到1650年前后降至最低值。(81)Richard Adair, Courtship, Illegitimacy and Marriag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24.特别是随着17世纪晚期人口压力趋于平缓,同时民众的生活水平开始提高,人们对私生子的恐惧逐渐减弱,私生子问题不再是严重的社会问题。(82)法拉梅兹·达伯霍瓦拉:《性的起源》,第28页。
结 语
近代早期英国的私生子问题既是一个道德问题,又是一个经济问题。私生子问题所包含的非婚性行为与国家和教会的道德原则相悖,而私生子的降生致使贫困问题加剧。16世纪末17世纪初“私生子爆炸”现象的出现,引起了国家对社会失序与道德败坏的恐慌。私生子与犯罪、贫困、流民、酗酒、饥馑、瘟疫等问题一道,成为英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时期面临的严重社会问题。为有效应对这些社会问题,英国限于国家机器比较薄弱,必须依赖各社会阶层的合作。在此背景下,治安法官成为近代英国国家治理所倚重的社会力量。就私生子问题而言,以治安法官为权力主体的地方政府,积极回应中央政府管控私生子的国家政令。一方面,治安法官运用自由裁决权惩罚私生子的父母,以儆效尤;另一方面,治安法官要求私生子父母缴纳私生子的扶养费用,从而避免私生子成为教区济贫的负担。正是在中央与地方的通力合作下,才使私生子问题得到有效治理。治安法官作为中央与地方的连接枢纽,可谓功莫大焉。
作为道德问题的私生子问题,也是近代早期英国“风习改造”(reformation of manners)的重要内容。(83)国内学界对“风习改造”这一名词尚有不同译法,诸如“习俗改革”“移风易俗”“风俗改革”等。本文遵从向荣教授的最新译法,参见向荣:《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欧洲史研究的重要性及难度》,《光明日报》2012年6月7日,第11版。这一时期英国“风习改造”的核心内容是通过法庭对个人行为予以公开规训,对违反法律规定的个人予以适当惩罚,这些行为包括高利贷、服饰、赌博、流浪、盗窃、酗酒等,其矛头指向懒惰、浪费和过度消耗。(84)Martin Ingram, Carnal Knowledge: Regulating Sex in England, 1470—1600, pp.14-15.为有益于作为整体的国家和基督教社会,世俗权威与宗教权威结成联盟,规训民众行为,这在私生子问题的治理中获得验证。近代早期英国治安法官对私生子问题的治理,也凸显了这一时期“风习改造”的特点,即地方层面积极推行道德改革,强力干预民众的语言、宗教、性、劳作与休闲习惯;根据中世纪的标准,不道德行为者受到的惩罚更加严厉,频次更高。(85)Steve Hindle, The State and Social Chang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1550-1640, pp.176-177.私生子问题成为近代早期英国立法的主要对象,也是治安法官实践“风习改造”的重要场域。
私生子问题不仅关乎英国贫困问题的治理,也攸关英国“风习改造”的成功与否。治安法官作为中央在地方的“官僚”与地方社会的“家长”,形塑了中央与地方、世俗与宗教的合作关系,为私生子问题的有效治理提供了可能,从而为英国实现社会稳定转型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