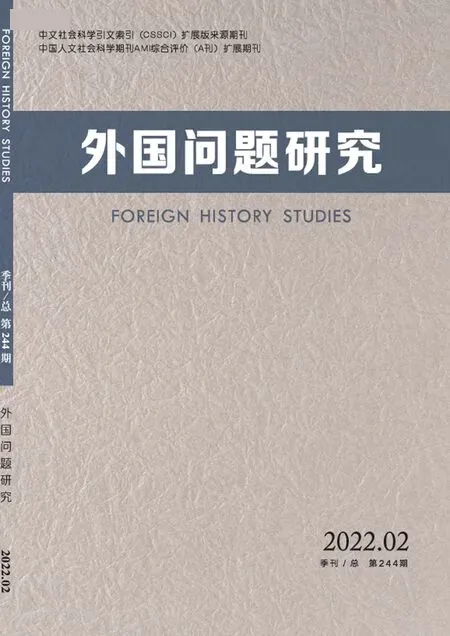罗马帝国晚期异教内部的衰弱
——以神庙和献祭仪式为中心
2022-12-28焦汉丰
焦汉丰
(复旦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433)
长期以来,西方古典学界认为希腊罗马传统宗教的衰弱是基督教压迫的结果,对此,彼得·布朗曾总结了“异教终结”的传统观点:“从爱德华·吉本到布克哈特再到现代的历史学家,在大多数学者的历史叙事中,一旦遭遇到基督教态度坚决的压迫,异教的终结似乎是不可避免的。”(1)Peter Brown, “Christianization and Religious Conflict,” Averil Cameron and Peter Garnsey, eds.,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ume XIII: The Late Empire, AD 337-42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633.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戴希曼(Friedrich Deichmann)和英国学者加斯·佛登(Garth Fowden)认为罗马帝国晚期的神庙遭遇了各种形式的暴力,它们的衰弱主要源于帝国当局的反异教法令和基督教系统的破坏运动(2)Friedrich Deichmann, “Frühchristliche Kirchen in antiken Heiligtümern,” Jahrbuch des (kaiserlich) Deutschen Archäologischen Instituts, Vol.54, 1939,S.105-136;Garth Fowden, “Bishops and Temples in the Eastern Roman Empire A. D. 320-435,” Journal of Theological Studies, Vol.29, Issue 1 (April 1978), pp.53-78.
然而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开始从长时段的角度来考察罗马帝国晚期异教的命运,他们试图逐步将政府和基督教对异教“压迫”的实际影响最小化,认为基督教崛起并成为国教后,在皇帝的法令下,异教仪式被禁,神庙遭到的破坏、关闭和转为教堂其实只是历史的一部分,这只是异教衰弱的原因之一。其实异教早在基督教崛起之前已经出现衰退的迹象(3)部分研究见Luke Lavan and Michael Mulryan, eds., The Archaeology of Late Antique ‘Paganism’, Leiden · Boston:Brill, 2011; Scott Bradbury, “Julian’s Pagan Revival and the Decline of Blood Sacrifice,” Phoenix, Vol.49, No.4, 1995, pp.331-356; Christophe J. Goddard, “The Evolution of Pagan Sanctuaries in Late Antique Italy (Fourth to Sixth Century A.D.): A New Administrative and Legal Framework, A Paradox,” Massimiliano Ghilardi, Christophe J. Goddard, Pierfrancesco Porena, eds., Les cités de l’Italie tardo-antique (IVe-VIe siècle): institutions, économie, société, culture et religion, Roma: 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2006, pp.281-308.比如在基督教合法化之前,埃及的一些神庙就面临着严重的财政问题,一些神庙在罗马帝国早期就已转为了世俗之用。(4)Roger Bagnall, Egypt in Late Antiqu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260-268.所以我们可以尝试拓宽研究视野,从当时的时代大背景中出发,考察异教的衰弱进程。本文试图结合文献和考古证据,从神庙和献祭仪式的视角来考察异教的衰弱进程。总的来说,当时异教自身的衰弱体现在两方面,其一,神庙修建活动的衰退,二是异教献祭仪式的衰弱,其中神庙建设活动的衰退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新建神庙数量的下降,第二个是新建神庙规模的缩小。
一、神庙修建活动的衰退
从公元3世纪开始,罗马帝国大部分地区修建新神庙的步伐大大放缓,而新建神庙中大部分是皇帝崇拜神庙。3世纪开始非洲的神庙建设就已经出现衰弱迹象,相关铭文显示,在3世纪末和4世纪初,虽然原来的一些神庙仍旧得到了维护和修葺,但几乎没有新建神庙的证据。有记录的只有两座,一座是公元283—284年修建的维列昆达(Verecunda)的神圣卡鲁斯神庙(Divus Carus),这是献给卡鲁斯的皇帝崇拜神庙,另一座神庙位于提格尼卡(Thignica),修建于四帝共治时期,但无法确定该神庙具体献给哪位神祇。(5)Gareth Sears, “The Fate of the Temples in North Africa,” Luke Lavan and Michael Mulryan, eds., The Archaeology of Late Antique ‘Paganism’, p.231.小亚地区的神庙建设活动相较前几个世纪也显得不值一提,无论是皇帝还是当地精英似乎不再热衷于为神庙及其相关仪式提供资金。目前已知的神庙中只有米利都的狄俄尼索斯神庙和爱奥尼亚沿海狄迪马的阿波罗神庙修建于3世纪,当时得到修复的神庙也只有以弗所的阿尔忒弥斯神庙。(6)Peter Talloen and Lies Vercauteren, “The Fate of the Temples in Late Antique Anatolia,” Luke Lavan and Michael Mulryan, eds., The Archaeology of Late Antique ‘Paganism’, pp.347-387.
同一时期罗马城的新建神庙也是屈指可数,虽然原有的旧神庙继续得到了维护,但根据文献记载,整个3世纪罗马城新建的神庙只有微不足道的3座。塞维鲁·亚历山大(Severus Alexander)时期的罗马城新建了2座神庙,分别是朱庇特·瑞度克斯(Iubbiter Redux)神庙和苏利亚女神(Dea Suria)(7)这里的苏利亚(Dea Suria)似乎是一位凯尔特女神,但是叙利亚女神(Dea Syria,即阿塔加提斯[Atargatis])有时也作Dea Suria,而考虑到赛维鲁·亚历山大和埃拉伽巴路斯(Elagabalus)一样的叙利亚出身,因此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庙,原来的复仇者朱庇特神庙(Iubbiter Ultor)和平原伊西斯神庙(Isis Campensis)也得到了修复。(8)Lawrence Richardson, A New Top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Ancient Rome,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p.456.奥勒里安(Aurelianus)也修建了一座新神庙。他在击败芝诺比娅后收复了帕尔米拉,公元273年,胜利归来的他在罗马兴建了一座神庙献给无敌太阳神(Sol Invictus)。(9)Zosimus, New History, 1.61.4世纪罗马城的新神庙可能也寥寥无几,有记录的只有一座。4世纪初,马克森提乌斯将他夭折的儿子封神,并于公元309年在神圣大道(Via Sacra)之旁为其修建了神圣罗慕路斯(Divus Romulus)神庙。(10)Lawrence Richardson, A New Top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Ancient Rome, p.458.
可见公元3—4世纪罗马帝国的新建神庙数量寥寥可数。学者们对其原因有着不同的解释,传统异教的逐步衰弱是其一。“整个世界似乎都在等待着基督教的到来。”萨奥尔这样说道,他认为神庙这方面的变化反映了罗马帝国公共工程模式的变化,当时新建公共建筑数量的下降是一种普遍趋势。不过从比例上来说,神庙建设活动的衰退程度显然要比新建公共建筑数量的总体下降趋势更为严重。(11)Eberhard Sauer, The Archaeology of Religious Hatred in the Roman and Early Medieval World, Stroud & Charleston (SC): Tempus, 2003, pp.114-130.北非地区铭文所提供的证据为我们充分展现了这一情况,当时涉及公共工程的铭文数量相较于前两个世纪呈下降趋势,而在所有建筑活动的铭文中,涉及神庙的铭文所占比例明显下降了。(12)Gareth Sears, “The Fate of the Temples in North Africa,” p.237.希腊和地中海东岸的黎凡特地区也有着相似的趋势,(13)Luke Lavan, “Political Talismans? Residual ‘Pagan’ Statues in Late Antique Public Space,” Luke Lavan and Michael Mulryan, eds., The Archaeology of Late Antique ‘Paganism’, pp.439-478.因此当时各个地区的神庙建设都存在着衰退的情况,当然这并不能说明异教本身无可挽回地衰弱了。
四帝共治时期公共工程的优先顺序更能说明神庙的处境。戴克里先力图恢复帝国的荣光,他自诩为朱比特,马克西米安则自称为赫拉克勒斯,但在他们治下,帝国各大城市并没有为这两位神灵修建宏伟的神庙,戴克里先只是在各地的行宫中修建了小型的神庙。按照约翰·马拉拉斯的记载,马克西米安在与波斯作战时,戴克里先则驻守在安条克,他在城市里修建了一座行宫,在城市近郊的达芙妮(14)这里的达芙妮是地名,位于安条克近郊,是阿波罗和达芙妮崇拜的圣地。则修建了一座体育场,并在其内部修建了一座奥林匹亚宙斯神庙和一座尼米西斯宙斯神庙(Temple of Nemesis Zeus),另外还修建了一座赫卡特的地下神庙。这些神庙规模都比较小,只是附属性质的建筑,马拉拉斯在叙述戴克里先的行宫时才顺便提及。(15)Malalas, Chronicle, 12.38.
这一时期帝国公共工程的重点在其他建筑上,四帝共治时期皇帝们选择优先在大城市里修建规模宏大的公共浴场。罗马、米兰、尼科米底亚和安条克在这一时期都兴建了新的大型公共浴场,(16)约翰·马拉拉斯在他的《编年史》中提到了戴克里先在安条克修建的浴场,详见John Malalas, Chronicle, 12.38;利巴尼乌斯提到了尼科米底亚的浴场,详见Libanius, Oration, 61.16-61.18.罗马的戴克里先大浴场是其中规模最大的,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中央大厅的面积达到了280米×160米,超过了赛维鲁王朝时期的卡拉卡拉大浴场。可见虽然戴克里先自诩为帝国的拯救者,力图恢复罗马帝国和异教诸神往日的荣光,但他对修建新神庙的热情并不高。(17)Roger Rees, Diocletian and the Tetrarch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57-71.
公元3—4世纪的异教皇帝似乎都对兴建新神庙失去了兴趣,甚至后来力图振兴和改革异教的背教者尤利安也是如此,这是值得深思的现象。尤利安发布法令逐步将基督徒从政府和教师队伍中清除出去,还打算模仿基督教会,为异教建立一个具有相似等级制度的“教会”,但他的关注点并不是神庙。虽然他重新开放了一些被基督徒皇帝勒令关闭的神庙,但并没有修建新神庙。按照利巴尼乌斯的说法,尤利安只在自己的宫殿中修建了小型神庙,“因为皇帝他不可能每天离开皇宫前往神庙,而与诸神的持续交流又是极其重要的事情,人们在皇宫的中心为他这位统治者兴建了一座神庙……”(18)Libanius, Oration, 18.126-127.
尤利安时期新建神庙的缺乏也许与他在位不到两年多少有些关系,毕竟神庙作为大型工程营建周期较长,两年不到的时间不足以让他的宗教政策在神庙建设上出现成果,但是时间短不足以完全解释这一现象。他振兴异教的重心在于宗教冲突严重的东部地区,特别是小亚、希腊和叙利亚地区,因此东部地区缺乏新建神庙的情况还是很能说明问题。另外,尤利安时期其实有不少新建的公共建筑。(19)尤利安时期部分工程见Lawrence Richardson, A New Top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Ancient Rome, p.457.尤利安还打算重建耶路撒冷的犹太圣殿,最后因为突然出现的大火不了了之。(20)圣殿地基附近持续喷出火球,因此重建工作无法继续进行,详见Ammianus, Res Gestae, 23.1.3.他同样修复了罗马元老院的胜利女神祭坛,并将其重新安置到了元老院,(21)Lawrence Richardson, A New Top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Ancient Rome, p.457.但是他似乎对修建新神庙缺乏热情。
总之,从3世纪开始,原先由神庙主导的古典城市布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共和国末期和帝国早期的神庙将城市中心位置让于广场和大型会堂等政治建筑,到了帝国中晚期则让位于皇宫和公共浴场。戴克里先在尼科米底亚的宏伟皇宫以及达尔马提亚行省的庞大行宫体现了这种转变,后者位于萨罗纳(Salona)附近,是戴克里先退位后的居所。考古学证据显示从公元4世纪70年代开始,城市的神庙和广场都已经丧失了其原来的中心地位,在很多城市中,大型浴场似乎成了城市生活的中心。(22)根据理查德森所列举的罗马城的公共建筑,可以发现在公元3—4世纪的公共工程中,浴场占了较高的比例,详见Lawrence Richardson, A New Top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Ancient Rome, pp.456-458.相关文献也证实了罗马帝国中晚期公共浴场在城市中的重要性。皇帝瓦勒里安(Valerianus)喜欢住在公共浴场建筑群中。(23)转引自Anna Leone, The End of the Pagan City: Religion, Economy, and Urbanism in Late Antique North Af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22.公共浴场也经常是举行正式会议的场所,公元411年,北非的多纳图派和罗马公教就在迦太基的伽尔基利阿纳(Thermae Gargilianae)浴场举行了宗教会议。愈来愈多的浴场成了城市的中心,也取代广场成了陈列雕像的重要场所。在北非提姆加德城的浴场遗址中,考古学家在一系列雕像的基座上发现了当时献给瓦勒里安和伽利埃努斯父子的铭文。(24)Anna Leone, The End of the Pagan City: Religion, Economy, and Urbanism in Late Antique North Africa, p.22.君士坦丁堡的宙克西帕斯浴场(Zeuxippus)也陈列着从各处收集而来的大量雕像。因此,罗马帝国城市公共空间发生了变化,帝国晚期公共浴场突出的地位也许与神庙修建活动的衰退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第二个衰弱的表现是神庙规模的缩小。从3世纪开始,不仅是新建神庙的数量大幅下降,而且相较于以前规模宏伟的希腊罗马神庙,当时神庙的规模明显缩水了。肯特大学的考古工作者在2009—2010年对罗马奥斯提亚港进行了挖掘,发现了一座帝国晚期的小型神庙。该神庙建于帝国早期一座蓄水池之上,只有3.6×3.8平方米的面积。(25)详细情况参阅此次考古发掘工作的官方网站https://lateantiqueostia.wordpress.com/。希腊地区也有相似的趋势,阿哥斯广场上的一座小型神庙也只有4.2×1.8平方米的面积。(26)Helen Saradi-Mendelovici, “Late Paganism and Christianisation in Greece,” Luke Lavan and Michael Mulryan, eds., The Archaeology of Late Antique ‘Paganism’,pp.263-310.4世纪的昔兰尼(Cyrene)也是如此,当地的竖琴演奏者阿波罗神庙(Apollo the Cithara Player)面积只有5×5平方米,公元365年大地震以后新落成的奥姆布里俄斯宙斯神庙(Temple of Zeus Ombrios)的面积也只有5×7平方米。(27)Gareth Sears, “The Fate of the Temples in North Africa,” p.237.
那些只出现在文献中的神庙也是如此,比如前文戴克里先修建的神庙,他下令在安条克的达芙妮体育场内修建了一座尼米西斯宙斯神庙和奥林匹亚宙斯神庙,这些神庙的结构也可能相对简单,所以能够融入体育场的整体建筑之中。(28)详见John Malalas, Chronicle, 12.38.尤利安皇帝也只在自己的皇宫内修建了小型神庙。(29)Libanius, Oration, 18.126-127.君士坦丁大帝在君士坦丁堡总共修建了三座神庙,其中两座是堤喀(Tyche)神庙和瑞亚(Rhea)神庙,(30)Zosimus, New History, 2.31.3.但这两座神庙都位于一座庭院之内,因此面积不会很大。第三座神庙是卡皮托利神庙(Capitolium),从神庙的考古报告来看该神庙似乎是供奉君士坦丁王朝皇帝雕像的神龛,具体规模目前无从得知。(31)Luke Lavan, “Political Talismans? Residual ‘Pagan’ Statues in Late Antique Public Space,” p.451.此外,还有位于希斯佩鲁姆(Hispellum)的君士坦丁王朝的皇帝崇拜神庙,目前还无法确定其规模。根据这一时期用来容纳皇帝雕像的神龛大小来推算,该神庙应该只是小型神庙。(32)Luke Lavan, “Political Talismans? Residual ‘Pagan’ Statues in Late Antique Public Space,” p.463.
二、血祭传统的衰弱
除了神庙修建活动的停滞外,罗马帝国传统的异教献祭仪式也逐渐衰弱了。尤利安个人已经体验到了这一时期罗马帝国异教自身的变化,有一个例子能生动地说明当时传统的献祭仪式所经历的变化。尤利安在安条克时准备向阿波罗进行献祭,但是神庙祭司并没有按传统提供牛羊等大型牲畜作为祭品,仅仅奉献了一只鹅。尤利安对此有着详细的描述:
……但是当我进入神庙,我看不到贡香,没有蛋糕,更没有献祭之用的动物。我愣了一会儿,还以为自己仍在神庙之外,以为你为了向我这个大祭司表示敬意,所以你还在等待我的信号。但是当我开始询问,为了荣耀阿波罗,城市打算在一年一度的节日上献祭什么动物,祭司这样回答道:“我从家里带了一只鹅过来作为献给神的贡品,但是城市这次没有做什么准备。”(33)Julian, Misopogon, 361d-362b.
可见当时就连安条克的异教民众也不认可这种血腥的仪式,在尤利安宗教政策重点针对的东部地区,民众对血祭的反应普遍比较冷淡,这其中包括小亚、叙利亚和希腊。(34)Scott Bradbury, “Julian’s Pagan Revival and the Decline of Blood Sacrifice,” pp.341-347.而在过往,传统上公开的献祭仪式比较隆重,祭司会精心挑选大型牲畜作为祭品,并提前几个月做好准备。(35)Alan Cameron, The Last Pagans of Rome, p.66.尤利安在安条克所遇到的情况也许反映了血祭的民众基础已然不再,就连尤利安原本的支持者阿米阿努斯·马赛林努斯也因此批判了他,马赛林努斯在书中表达了自己对奢侈的血祭仪式的厌恶:
他用了过多祭品的血去浸湿祭坛,有时候一次性要献祭上百头公牛,以及无数的其他动物,还有在陆上和海里被猎杀的白鸟,以至于几乎每天他的士兵都在贪婪地吃着大量的肉……(36)Ammianus, Res Gestae, 22.12.6.
利巴尼乌斯的演说中也体现了类似观念,他认为尤利安每天进行的献祭仪式不符合传统,明显过于奢侈了。(37)Libanius, Oration, 12.80.卡梅隆的《罗马最后的异教徒》涉及了帝国晚期献祭仪式的衰弱。卡梅隆认为一些异教仪式,比如曾经占主导的公共献祭仪式,在被政府禁止之前就已经衰弱了,这是异教自身演变的结果:
在完全缺少证据的情况下,没有什么能得到证实,但我怀疑在4世纪80年代(也许更早),西部和东部的公共仪式就已经不包含常规的动物祭品了……(38)Alan Cameron, The Last Pagans of Rome, p.67.
古代世界公开的献祭活动曾是各类崇拜的标志性仪式,但是这一仪式逐渐衰弱了。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之前,异教内部就已经出现了反对这种血腥仪式的声音,他们追求更高级的、纯洁的、精神性质的仪式。一些新柏拉图主义者对宗教仪式有新的观点,波菲利(Porphyry)就质疑了传统献祭仪式,他认为献祭是一种低级的仪式。波菲利厌恶血祭以及随后进行的无节制的宴会,他提倡崇拜的智力性和精神性,强调用精神的方式去荣耀和崇拜神灵,认为最高神灵理应得到信徒精神上的祭品。他甚至还声称远离肉食才能保持灵魂的纯洁性。(39)转引自Scott Bradbury, “Julian’s Pagan Revival and the Decline of Blood Sacrifice,” pp.332-333.一些新毕达哥拉斯主义者也持有类似的观念,他们同样认为血腥的动物献祭是最低级的崇拜方式,只是用来抚慰恶魔的低级仪式,因此应该尽量避免执行这类仪式。提阿纳的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 of Tyana)在实践中就只进行无血的宗教仪式,他甚至拒绝出现在献祭现场,并批评了雅典人对献祭的喜爱。(40)Scott Bradbury, “Julian’s Pagan Revival and the Decline of Blood Sacrifice,” pp.336.这一点与基督教类似,基督徒厌恶异教的献祭仪式,强调信仰的个人性和精神性,这可能也对当时的异教知识分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公元3世纪以来,异教仪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动物献祭不再是最主要的仪式,而焚香、点亮油灯和吟诵赞美诗等私下的崇拜行为在异教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突出。(41)Martin P.Nilsson, “Pagan Divine Service in Late Antiquity,” The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Vol.38, No.1 (Jan.1945), pp.63-69.考古发现和铭文都证明了当时油灯在祈愿中的重要性,(42)详见Richard Rothaus, Corinth, the First City of Greece: An Urban History of Late Antique Cult and Religion,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00, pp.32-63; 126-134.焚香也比以前更为流行,这些来自东方的异国情调的芳香更能凸显仪式的庄严性,在成本上也要比奢侈浪费的动物献祭要低,是比较受人推崇的精神化崇拜仪式。而歌颂神灵的赞美诗也是很好的精神献祭,爱奥尼亚沿海狄迪马和克拉罗斯(Claros)的铭文证实了当时流行神灵赞美诗。狄迪马的一份阿波罗神谕中,阿波罗自己也表达了对赞美诗的喜爱。(43)Scott Bradbury, “Julian’s Pagan Revival and the Decline of Blood Sacrifice,” pp.331-356.最重要的是,这些崇拜活动并不局限于神庙和神龛等崇拜中心,人们在私下也能通过这些方式表达自己对神的崇敬。
尤利安皇帝则受扬布利库斯(Iamblichus)和撒鲁斯提乌斯(Sallustius)等哲学家的影响,(44)详见Scott Bradbury, “Julian’s Pagan Revival and the Decline of Blood Sacrifice,” pp.338-339.依然十分重视传统的献祭仪式。对于血祭传统的逐渐衰弱,尤利安曾无可奈何地感叹道:“告诉我,卡帕多西亚还有哪些是真正的希腊人?据知,有些人拒绝献祭,另一些人尽管愿意,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如何去献祭。”(45)Julian, Epistula, 78.利巴尼乌斯也抱怨安条克的异教民众都把钱都花在了城市的赛马表演而非阿波罗的节日庆典上。(46)Libanius, Oration, 15.19.这些情况真实反映了传统的异教仪式正在经历的变化,也许与神庙的衰弱有着密切的关系。最迟从3世纪开始,传统异教的献祭仪式的确逐渐衰弱了。对于其中的原因,布拉德伯里指出这更多是源于祭司威望的下降和罗马城市中传统 “公益捐助(Euergetism)”(47)euergetism中文译名,详见刘津渝:《罗马史研究入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序言第5页。模式的变化,这一变化进一步推动了原本就已经出现的异教仪式上的变化,让献祭的衰弱成为现实。总的来说,神庙原先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市政府的宗教资金、公共资金和市民捐助,传统节日中的大多数献祭仪式由公共资金提供支持,(48)A. H. M. Jones, The Greek City from Alexander to Justini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0, pp.227-235.但宗教资金只限于包括神庙修建和维护等特定支出,公共资金又不足以应付庞大的献祭仪式和宗教游行等费用。因此富裕市民的捐助就成了城市宗教生活资金的重要来源,这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祭司阶层自身来承担,祭司职位因此是由那些富裕市民来担当,他们在承担财政义务的同时也享有部分特权。但3世纪危机无论对城市经济还是上层市民都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相关仪式因此也失去了原来的经济支柱,资金上的缩水导致异教仪式和节日在规模和数量上都有所减少,奢侈的献祭仪式因此衰弱了,而更迎合帝国政府的皇帝崇拜以及更受普通民众喜好的节日戏剧和赛马表演得以保留,这些活动比传统的献祭更具吸引力,民众生活也因此逐步世俗化了。
三、异教自身衰弱论
综上所述,可见异教自身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传统的血祭仪式衰弱了,异教徒的崇拜活动也转移到了宗教生活的其他方面,比如焚香、吟诵赞美诗和点灯祈愿等活动。(49)Scott Bradbury, “Julian’s Pagan Revival and the Decline of Blood Sacrifice,” pp.334-337.根据阿尔勒的恺撒略乌斯(Caesarius of Arles)的记述,异教徒会在草地上向神祇献上些物品,或者在水池旁点亮陶制油灯,或是向泉水投掷硬币抑或是为某棵圣树系上丝带,斯巴达和科林斯当地的一些圣地就出土了信徒留下的大量陶制油灯。(50)Béatrice Caseau, “Late Antique Paganism: Adaptation under Duress,” Luke Lavan and Michael Mulryan, eds., The Archaeology of Late Antique ‘Paganism’, p.130.虽然这些活动后来也被法令所禁止,(51)Codex Theodosianus, 16.10.12.但是法令在现实中的执行力度又是另一回事了,这类私下的供奉和崇拜活动通常很难得到有效的监督和控制,因此无法从根本上被禁止。
城市神庙和公共献祭仪式缓慢衰弱的现象有迹可循,特别是西部的少数城市为我们提供了相关证据,西部地区神庙被破坏的现象较少,神庙保存率相对较高。虽然帝国政府的法令要求关闭所有神庙,但是考古证据显示一些城市神庙在公元4世纪末仍然在正常运作。罗马大竞技场南部的花神弗洛拉(Flora)神庙在公元400年左右得到了修复,而每年4月花神节(Floralia)上围绕神庙的庆典活动仍在继续。(52)Michael Mulryan, “The Temple of Flora or Venus by the Circus Maximus and the New Christian Topography: The ‘Pagan Revival’ in Action?” Luke Lavan and Michael Mulryan, eds., The Archaeology of Late Antique ‘Paganism’, pp.209-228.位于奥斯提亚的大母神神庙状况也较好,附近两座修建于公元4世纪的新广场并未占用其领地。(53)Luke Lavan, “Public Space in Late Antique Ostia: Excavation and Survey in 2008—2011,”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Vol.116, No.4, 2012, pp.649-691.甚至到了5—6世纪也是如此,著名的朱比特·卡皮托利努斯神庙在东哥特的狄奥多里克时期得到了修复,维斯塔神庙于5世纪初得到了修复,罗马广场的农神庙也差不多是同一时间得到修复,元老院外的密涅瓦雕像则在公元472/473年得到了修复。(54)详见Christophe J. Goddard, “The Evolution of Pagan Sanctuaries in Late Antique Italy (Fourth-Sixth Centuries A.D.): A New Administrative and Legal Framework, A Paradox,” pp.303-304; Lawrence Richardson, A New Top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Ancient Rome, pp.457-458.而且这一时期乡村神庙仍然十分活跃,它们和西部的城市神庙是差不多的处境,很少遭到人们的暴力破坏。可见部分地区神庙的衰弱是没有暴力的过程,特别是罗马城所在的意大利本土地区。(55)Michael Mulryan, “The Temple of Flora or Venus by the Circus Maximus and the New Christian Topography: The ‘Pagan Revival’ in Action?” pp.209-228.因此就自然而然地有了这样的结论,从公元3世纪开始,似乎是异教自身仪式上的变化导致了神庙的衰弱,而非基督教和帝国政府的压迫性政策。
这种异教自身“衰弱”的理论也许还不够成熟,我们目前无法明确神庙的衰弱与异教仪式变化之间的具体关系,但是这一说法已经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这种“翻案”也存在着先例,这里可以回顾一下学术界古代晚期犹太人的研究情况,学者们的成果已经让我们对这一时期犹太人状况的认识大大改观。犹太人曾在罗马帝国内饱受歧视,以前的学者大都认为公元5—6世纪的犹太人大多处于贫穷之中,社会地位低下,因此没有能力在公共生活和建筑中展现自己的存在。但考古证据却否定了这一论点。地中海东岸当地犹太人的建筑显示了当时存在一个富裕的犹太社区。小亚阿佛洛狄西亚斯(Aphrodisias)的铭文显示犹太人在当地剧场拥有较好的固定位置,他们在推罗的竞技场也享有同样的待遇。萨迪斯的一座犹太会堂的面积达到了80米×20米,可容纳1500人集会,规模要明显大于当地的教堂。(56)Peter Brown, The Rise of Western Christendom, Chichester, West Sussex;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003, p.63.可见古代晚期的犹太人享有一定的宗教自由,犹太教是一种合法的宗教(religio licita)。
近几十年来的学术研究已经证明了戴希曼和佛登等学者异教终结和神庙转变理论的局限性。他们的研究也许适用于中东地区,但罗马帝国的其他地区并非如此。教会对待传统宗教的立场并不总是打压,双方还有共存和交流,很多古代神庙因其出众的艺术价值而被保留下来。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当时异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冲突也是确实存在的,但问题在于冲突是否对当时的宗教和社会变化有根本的影响,在彼得·布朗看来,这些宗教冲突的影响相对于当时庞大的日常社会生活而言就显得无足轻重了,“罗马帝国社会的活力、公共生活的节奏、向所有阶层都敞开的公民游戏,以及上层社会所共享的文化,这些都让基督教和异教的区别无足轻重”。(57)Peter Brown, “Pagans and Christians at the Warburg Institute in 1958,” Peter Brown and Rita Lizzi Testa, eds., Pagans and Christians in the Roman Empire: The Breaking of a Dialogue (IVth-VIth Century A.D), Zurich/Berlin: LIT Verlag, 2008, pp.21-22.宗教对于古代民众来说是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但并非仅有的内容。古代晚期的地中海世界是一个宗教和文化多元的社会,并非充斥着宗教暴力,以前基督教作家给读者留下了这种负面印象。当时异教的消亡以及基督教的扩张并不迅速,而是经历了一个长期且缓慢的过程。因此我们必须利用各种史料来重新研究古代晚期的宗教变化,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考古证据,异教自身“衰弱”的理论也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