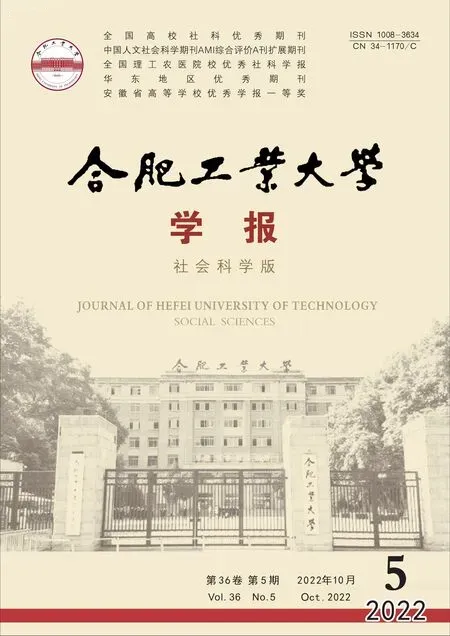明清时期寡居妇女的情感探微
2022-12-27李姣
李 姣
(安徽大学 历史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一、引 言
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情感是人类所特有,是人们在社会化生活条件下所形成的集体荣誉感、羞耻感、责任感等高级情感”[1],而“历史研究不仅要关注社会经济,而且要考察人的情绪气质和思维方式的变迁”[2]扉页。随着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心态史、情感史也逐渐进入史学研究者的视野,成为考察人类行为的一个角度。但就目前看来,国内学界对于传统社会的女性,尤其是寡居群体的女性情感问题,还是缺乏关注。本文从日常生活史的视角出发,探讨明清时期寡居妇女的生活,考察她们的情感变化动向及其原因,分析其生活形态与价值追求,以期能阐析清楚情感因素如何影响了妇女心理,从而为历史上较为普遍的妇女寡居行为提供较为合理的解释。
二、荣辱:从价值满足到道德恐惧
明清社会,妇女寡居现象突出,不仅有无数的丧偶独居者,还有大量守活寡之妇。“寡,少也。引申之凡倮然、单独皆曰寡。”(1)许慎.说文解字[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341.寡又可解释为“妇人无夫,妇人丧夫称寡”(2)王力.古汉语字典[M]. 北京:中华书局,2000:226.。“在不同文化中,潜在的情感是相似的,不同之处在于一种文化对一种情感的强调或重视程度是有差异的。”(3)情感人类学先驱人物罗伯特·列维(Robert Levy1973,1984)认为,每一种人类共有的情感或者是超认知的或者是若认知的,不同之处在于一种文化对一种文化的强调。Levy,Robert I.1973. Tahitians:Mind and Experience in the Society Islands.Chicago,I11.: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Levy,Robert I.1984.“Emotion,Knowing and Culture.” In Culture Theory:Essays on Mind,Self and Emotion.Edited by R.Shweder and R.LeVine,PP.214-237.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转引自威廉·雷迪.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48.明清时期,国家大力旌表守节义行,宗族则通过提高节妇在丧、祭礼俗中的地位开展教化。在官府及地方力量的双重引导下,寡居守节已然成为妇女的价值认同,并被赋予强烈的情感色彩,寡居至死的妇女群体数量达至历史高峰。叩问寡居女性群体的初心,情感变化是她们选择寡居生活的不可回避的重要因素。
传统社会,情感和道德密不可分。“赞许是最有疗效的安慰剂,谴责是最苦涩的毒液。”[3]道德通过善恶、褒贬的对立观念调控情感,改变人对事物的态度,并成为重要的文化情感。荣誉感与耻辱感是潜藏在人的心灵深处的重要道德情感文化,并以荣辱情结为基础形成了荣辱观念,对人的心理与行为方式具有持久、深远的影响。
1.恩荣之于家族及个人的价值满足
明清社会,寡居妇女群体普遍认为荣誉感的意义比爱情更为重大,妇名重如山。对于妇女及其家族来说,夫死守节获得旌表是沐浴皇恩、流芳百世之荣,是为家族光耀门楣的重要途径。这种至高至上的荣誉感足以成为寡居妇女一生的追求。
妇女贞节观念自宋代开始,并随着朝代更迭而不断地被加强。守节情感在妇女心中不仅是应尽的义务,更被作为一种高尚的情感道德被官方宣传。统治者利用旌表活动,给予妇人以精神表扬及物质奖励。明朝在建朝之初,就十分重视旌表问题。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即下诏:“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4]457。妇女守节二十年,不仅家族被旌表,本家艰苦的差役也可免除,自此以后,妇女寡居群体数量不断增加。“成化元年奏准,凡旌表贞洁孝行,里老呈告到官……妄将夫亡时年已三十以上,及寡居未及五十妇人,增减年甲举保者,被人首发或风宪官核勘得出,就将原保各该官吏里老人等通行治罪。”[4]457随着旌表条件的放宽,一些人为满足内心的荣誉感,开始弄虚作假,破坏旌表秩序,此现象也说明旌表所带来的恩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妇女的寡居守节。明嘉靖二年,朝廷扩大节妇受旌表的范围,由天下军民衙门而至天下文武衙门。除了已经竖坊表彰的贡举贤能和被封为命妇者不予旌表,“其余生员吏典一应人等,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卓异,足以激励风化表正乡闾者,官司仍具实迹以闻,一体旌表”[4]457。针对已经受旌表的节妇,“年及六十者,孝子冠带荣身,节妇照八十以上例,给赐绢帛米肉”[4]457。“绢帛米肉”正是寡居妇女急需的生存资料,物质奖励的实际效用增大了寡居守节对于妇人的吸引力。
清承明制。清朝的旌表活动在顺治时期就已经开始,且基本沿袭了明朝节妇的旌表制度。康熙十四年,“凡节妇已经核实到部者, 虽病故亦准汇题旌”[5]。到了雍正时期,尤其重视表彰妇女的守节行为。“至若妇人从一之义醮而不改,乃天下之正道”[6]。对于地处偏远山区的妇女,为避免遗漏,朝廷要求地方官员亲自走访,联系、复核妇人守节的实际情况,并制定新规,即“节妇年逾四十身故者,守节已历十五载以上,亦应予旌”[7]。将旌表守节时间减少至15年,道光时期更减为10年,而同治时期妇女守寡满 6年即有资格申请旌表,享受节妇身份和待遇[8]。
阖门荣誉、名垂青史足以让寡居妇女及其家族动心,具体到封官爵、赐食禄、恩荫子孙、免徭役、修建牌坊等物质嘉奖和荣誉表彰,则更使寡居守节理念在妇女心中根深蒂固并且外化成为一种社会行为准则。一言以蔽之,荣誉项目越丰富,则妇人追求荣誉的欲望就越强烈,寡居行为也就越普遍。
例如,徽州宗族在族规家法的制定中,就十分重视满足妇人内心的荣誉感。经济条件差、生活负担重、入不敷出,乃徽州寡居妇人的生活常态。为帮助寡居妇人解决实际问题,宗族在上谱条件、神主入祠、祭祀颁胙、宗族赈济等多方面给予节妇优待,大力褒奖她们的寡居行为。“妇人从一而终,以节为重,节而兼孝,尤堪励俗。凡有,请旌建坊,学宪给额,及年例已符、得载郡县志者,皆得书,妾之守节者,亦如之。”(4)孙家晖纂修.古筑孙氏家谱[Z].清嘉庆十七年刻本.徽州宗族紧紧抓住“青史留名”的吸引力,在全族中表彰寡居守节妇人,连小妾守节也能留名方志。妇人受此影响,对寡居生活的接受度有明显提高,尤其是表彰之余还有物质奖励。绩溪县南关许氏《惇叙堂宗谱·家政》中提到:“赈贫之用:凡家贫、孤儿、寡妇与疲癃、残疾,祠董拨祀产租以赈之。如祀租无余,于合族上户及其近房派送月米。节妇,则尤当加礼。其寡妇及疲癃、残疾,俱赈之终身”(5)许文源等纂修.绩溪县南关许氏惇叙堂宗谱[Z].清光绪十五年惇叙堂木活字本.。歙县东门许氏家谱中也提及“族中有志守节贤妇,及年老孤贫无依者,每名每月给以口粮五钱”(6)许登瀛纂修.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Z].清乾隆十年刻本.,“吾宗以忠厚传家,而立节、守义者亦多,今特疏名于簿籍,第其事势之难易,列为二等,剂量胙之厚薄,每祭必颁,示优待之意,抑亦表彰之义也”(7)同③。。由此,妇人们更愿意寡居家中守节直至老死。
由上可知,妇人坚守寡居生活多为表彰。表彰作为一种道德表扬,对寡居妇女至关重要。传统社会中,女性是男性的附属品,寡居守节使她们受到更多关注,其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对荣誉感的追求激发了寡居妇女这一社会群体的自我意识及生活热情,填补了她们的情感空白。但在今天看来,这类表彰对女性而言无疑是一种丧失人性的残酷压制,即所谓“礼法”迫害,“以理杀人”。
2.心理大坝之于个人的恐惧与自律
耻辱感与荣誉感相对,它往往给人带来焦虑、羞愧、压抑的情绪。为消除、避免这些负面情绪,一座无形的“心理大坝”(8)“心理大坝”这一比喻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他认为羞耻可以阻止欲望的涌动。参见 Robert Metcalf,2000,“The Truth of Shame-Conscious-ness in Freud and Phenomenology”,Journal of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Vol.31,No.1 ( 2000) ,pp.1-18.转引自王佳鹏.暧昧性、羞耻感与现代自我:弗洛伊德的羞耻思想及其社会意涵[J].山东社会科学.2021(2):136.牢固地构建在人们心中。寡居效应与耻辱感这座心理大坝息息相关。羞耻感的存在能够有效控制人的行为,培养人们的自律意识。例如,个体会因为“想到自己做了某些不得体的事,有可能使我们成为自己的同胞们的厌恶感与轻蔑感的正当且合适的对象”[3],而自觉拒绝发生该行为。
心理大坝利用个体的恐惧情绪进而拒绝那些可能使其感到耻辱的行为。在传统社会中,失节一直被视为道德低下的象征,是妇女低俗、放荡的行为。失节的妇女是整个社会鄙视和羞辱的对象,她们被视为丧失了礼义廉耻,与禽兽无异,因而被社会唾弃。在极端的舆论环境下,再嫁往往与失节无异。“彼再嫁者,必加之戮辱,出必不从正门,舆必勿令近宅。至穴墙乞路,跣足蒙头,儿群且鼓掌,掷瓦石随之。”(9)周溶修,汪韵珊纂.祁门县志[Z].清同治十二年刻本.再嫁妇女大多社会地位低下,社会舆论的压力使其心理上有很强的耻辱感,因此寡居妇女一般谨慎选择再嫁,而更多的是坚持寡居守节,以捍卫自身的道德尊严。不仅女性自身恐惧因失节、改嫁带来的耻辱感,宗族也恐惧族中妇女因罔顾“三纲五常”给家族带来耻辱,而倾向于鼓励妇女寡居守节,并因此将对失节、再嫁妇女的严惩措施逐渐地制度化,严格地贯彻在族规家法之中。“妇之再醮与女之再适,黜而不书,以示戒也”(10)程尚芳等纂修.新安休宁古城程氏宗谱[Z].明万历元年刻本.;“殁后而妻改志者,并不书其配,盖义已绝故也”(11)洪昌纂修.休宁江村洪氏宗谱[Z].清雍正八年刻本.;“妇人从一而终,倘不幸有夫故再醮者,其主不准入祠”(12)方树纂修.绩溪城南方氏宗谱[Z].民国八年恩诚堂活字本.;等等。
姓名不入家谱、神主不入祠堂,在家族中是极为严重的惩罚,意味着与其后人断绝关系,更不能享受后人祭祀。此种情形无疑为再嫁妇女本人,也为她的后人打上耻辱的标记。由此形成的耻辱观念如同一座心理大坝,时刻防御着妇女的出轨,避免其行为越矩。
在心理大坝长期、有效的拦截下,越轨行为不断地被警示和提醒,因此可以有效帮助社会不断维护和加强边界观念,耻辱感因此被限制在伦理道德范围内并成为正面积极的情感。妇女寡居由迫不得已逐渐演变成为一种自愿自觉的行为。《日知录》记载:“礼义, 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9]。心中有耻的人则能做到有所不为。“当外来强制转化为自我控制时,随着自我强制的环圈不断扩大,对于违犯社会禁律的惧怕就越是以羞耻感的性质呈现。”[2]497随着与耻辱事件相对的文明礼仪不断内化于心,羞耻感在寡居妇女心中的适应性越来越强,类似这样情感的强制性压抑以及由这些情感而引起的社会羞耻感已经变成了寡居妇女的个人的习惯,以至于即使她们在独自一人时,或在隐秘的场所里也不会去违反这一习惯。发展到最后,常常出现有的丧夫女子,即使家族劝其改嫁,其也宁守不嫁的现象。如徽州休宁张氏,“年二十一,嫁同邑许伯仁,未期,夫卒。事姑甚谨,明年,姑卒,遗腹生一子,亦卒。族据其业,毁其家,张氏无居,乃归母家,鬻簪珥买田,别筑一室,奉许氏祀,嫠居二十三年而殁”(13)黄应昀修,朱元理纂.婺源县志[Z].清道光六年刻本.。 张氏早年开始守寡,丈夫、婆婆、孩子相继去世,她不畏族中亲属的“占业毁家”,坚持“从一而终”,鬻簪买田,建屋寡居,直到老死。另有节妇者,“上山吴君孟希之妻。既嫁,甫六年而希卒。时姐适富溪程氏者,亦早寡。其父怜之,乃舁二女于家,将改嫁之。节妇曰:修短命也,一妇可事二夫耶?严命不敢从也。父强之,乃与其姊相持号泣于庭,以死自誓”[10]457。孤身嫠妇为避免耻辱感带来的情感不适,自觉自愿地开始了寡居生活。以上均说明耻辱感从隐于妇女心中到普遍为妇女所承认,逐渐成为道德意义上的自我保护性感受。以耻辱为核心的情感防御变得严格而细腻,并且规约着她们言行举止,使其朝着合乎当时社会公德要求的方向发展。
通过赞许和谴责形成的荣辱感,协调、促进寡居妇女的行为朝着更符合明清社会规范的方向发展,并且避免该群体出现与当时社会伦理秩序相悖的污名化行为。这是社会控制寡居妇女行为的重要手段,为巩固、维系传统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爱情:从情感效忠到香火延续
爱情作为人类情感的主要形式之一,有历史性也有社会性。明清时期,在以崇德尚礼为主体的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下,爱情的内容由单纯的两性情爱趋于积极地实践儒家传统礼仪及伦理道德规范。“在爱情的迷狂中,人仍然应该节制过一种心灵高尚部分占主导地位的生活。”[11]寡居妇女的生理和心理需求都被缩小,效忠和义务成为爱情的主旨。
1.效忠情感——不忘坚守忠贞的初心
寡居妇女的爱情始终贯穿着“效忠”情感,这一情感内在地加强妇女忠贞不渝的守节心理。《礼记·郊特牲》讲:“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12]。清代诗人季兰韵常作诗文悼念亡夫,“生已负前言,死祈早同穴,惨嘱续遗孤,奉命身苟活”[13]503。晚清才女左锡嘉在嫠居生活中,作诗以抒情:“十五东邻女,十六商人妇,上堂拜舅姑,下堂任井臼,欲别牵郎衣,语涩羞出口,三岁期不归,妾终为君守”[14]。贞固之志显于著述中。
明清时期,男子常因戍边、经商的原因远走他乡,长久不归。妇人则因受《朱子家礼》的熏陶,特别是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人性论思想影响下,效忠意识强烈。据徽州《歙县志》记载,“邑俗重商,商必远出,出恒数载一归,亦时有久客不归者。新婚之别,习为故常,然妇女类能崇尚廉贞,保持清白,盖礼俗渐摹为时久矣。”[15]159在效忠情感的影响下,妇人愿意承担由婚姻带来的分居或丧偶风险,常年独守空房。汪于鼎作《新安女史征》言:“吾乡昔有夫娶妇,甫三月即远贾,妇刺绣为生,每岁积余羡,易一珠以记岁月,曰此‘泪珠’也。夫还,妇殁已三载,启视其篋,积珠已二十余颗”[15]159。漫长的寡居生活期间,效忠情感是她战胜孤独、沮丧、失望、窘迫等负面情绪的重要因素。还有,“吴观献妻潘氏,白洋人,夫贾于苏渡,钱塘潮至坠水死。氏立志不嫁四十年如一日”[15]2278“鲍瑞璜妻方氏,堨田人,于归四十日,夫商于外而殁,氏终身奉佛茹素,四十余年”[15]1186。潘、方二氏新婚后,丈夫就外出经商,她们在迍邅万状、独守空房的生活中等来的是丈夫的丧讯,却依旧寡居守节,立志效忠丈夫,坚守初心,无怨无悔。
2.香火延续——坚守养老字幼的义务
明清时期,纲常伦理思想被要求实践为与忠君孝亲、男尊女卑、修祠续谱、建坊树碑等活动相关的社会行为。在此文化的影响下,履行家庭责任的义务感被塑造成为寡居妇女的重要情感之一。雍正在圣谕中强调妇人要增强责任情感,对殉夫妇人则严命给予处罚:“烈妇之殉节捐躯,其间情事亦有不同者……不知夫亡之后,妇职之当尽者更多。上有翁姑则当奉养以代为子之道,下有后嗣则当教育以代为父之道。他如修治频繁、经理家业,其事难以悉数,安得以一死毕其责乎?……倘训谕之后,仍有不爱躯命,蹈于危亡者,朕亦不概加旌表,以成闾阎激烈之风,长愚民轻生之习也”[6]。统治者要求丧夫妇女务必以代夫履职为第一要务,上孝翁姑,下育子孙,主持中馈。
在寡居妇女的诗文中,这种义务感多以寡居妻子对丈夫的爱为出发点,目的是完成丈夫临行或临终前的殷殷嘱托以维护家庭稳定。“儿承祭祀母衰年,付汝艰辛休负讬”[16]87“一闻此语魄魂惊,宛转哀思志不成;恸到情真难作语,此身何惜为君生。”[16]87。清代诗人季兰韵在婚后第二年,丈夫屈颂满病逝,她悲痛万分,守寡抚孤,将美好忠贞的爱情升级为孝亲抚孤的义务情感。丈夫临终时,“弥留一息尚神清,事事叮咛哽咽成”[13]505,再三以侍翁续孤为嘱咐。季兰韵在义务感的驱策之下,一边强忍着“不求同生但求同死的心愿”,一边寡居守节,养老字幼。“嫁君一年我即寡,与君恩义深,何不殉泉下,君有亲,君无子,我死亲伤无后矣。吞声忍泪娱亲情,欲亲加饭勤调羹,亲言妇能代子职,儿身虽死仍如生,柔肠断尽不敢哭,为君续孤偏求族,思君不独羊枣伤,残喘苟延惟侍粥,一年又一年,儿雏渐渐长,教儿读遗书,寸心常惘惘,幸儿聪明亲体安,九原料得君心欢。”[13]505丈夫病逝后,她遵循丈夫遗命,过继丈夫族兄懋修第三子为子承柱,延续香火。“珍重遗言议续孤,两房俱待第三雏,玉堦果报三芝秀,人愿天从信不诬。夫、子殁后,即议嗣,按宗支、昭穆应嗣……因议定三房内有先举第三子者,承嗣。今如所愿,懋修,惟豫子也。”[13]505她在诗文中对寡居生活无尽感慨,她的这一行为显然是受到了情感的支配,这是历史的进步,也是当时现实生活的反映。
为保障香火不断,避免祭祀资金短缺,一些相对富裕的寡居妇人还主动捐资给公祠,以保障祭祀事宜顺利开展。如江西奉新人甘立媃,其嫁入徐门后不久,丈夫不幸去世。“因闻祠堂向乏公项,近年冬至元日,祀事缺如。为官者清贫多累,苦无余俸,予用惄然焉。今将予手置田业,除分拨子媳外,尚有存。予养田十四亩零,献于公祠以助岁祀之资。”[17]475除了自己捐资公祠以供祀费外,甘立媃还倡议族人量力而捐,绵延祭祀。“想我族中必有好义君子,相率捐输,共成善举,俾岁时笾豆有供,永远弗废”[17]475。
寡居妇女承担的家庭任务繁重,有时候她们的角色比男子还重要,而维系这种关系最主要的情感,是妇人对丈夫基于义务感的爱情。在此情感的影响下,寡居守节已经成为她们的自律行为。同治元年,徽州地区留守家中的徽商妇人多写书信给外出的丈夫,字里行间表达内心的殷殷期待。为方便寡居妇女使用,有专人将书信的大概内容编辑成活套簿,如:“妻寄夫书:夫君别后,芙蓉两度开矣。行时万缕千言,妾慻慻在念。不敢有违。高堂中馈,妾身任之,弱女幼子,妾身抚之,家务一切,妾身理之,勿劳远虑,但我夫君客外风霜,举家念切。倘有羡余之利,即赐返驾,奉侍双亲,教诲子女,骨肉完聚,笑语一堂,庶免老亲有倚闾之望,贱妾有白头之叹也。室尔人遐,寸心千里,惟加餐自爱为嘱”[18]7343。从中亦可窥见常年留守家中的徽商妇人对自身在家庭中须承担的责任有了更深的认知,且已逐渐发展为自律行为。妇人在寡居生活中难免有哀死虑生、殚力苦心的情绪,但随着义务感一步步加深,她们的履职行为更加坚定,且有利于家庭的稳定。“程有仁妻罗氏,中丞应鹤之女,归临河程,年二十二,夫死。以遗孤在抱,忍死抚育,孤复殇,舅氏继殁,有仁并无兄弟,氏竭力奉姑二十余年,姑亡,三丧毕举。会有仁两从弟各举次子,氏请并立为嗣,叹曰:‘今可死矣!’绝粒八日,卒年五十五。”[16]罗氏的寡居生活极为艰难,历经舅姑、子嗣俱亡的伤痛,但她吞声忍泪,忍死尽责,过继子嗣以继承宗祧。待其完成使命后,她毅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明清时期,妇女心中的爱情多以对丈夫的效忠、对家庭尽责和教养子孙等情感体验及行为实践呈现。此类情感在妇女心中升级为一股思想道德力量,引导着寡居妇女自觉守节,一度成为维系家庭、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力量。
四、信仰:从心灵慰藉到精神寄托
信仰神祇是妇人重要的情感领域之一。“妇女与神祇之间存在天然的亲近感。”[19]妇女对信仰的对象自然地怀有某种敬爱与钦佩的情感,行为举止皆受其影响。明清时期,信仰神祇是寡居妇女情感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该群体常年过着禁欲的生活,陷溺于压抑、孤单的情绪中,因此对神祇的情感投入有利于她们缓解沮丧情绪、慰藉心灵。
1.解救苦难、增强信念
有人认为,宗教是阶级分化社会里大众逃离生活苦难的心灵天堂。明清时期,民间信仰、宗教文化发展速度快、影响深。僧道信仰一度出现不绝如缕、遍地开花的现象,女信徒数量尤其为多。“她们在家中设神座,供奉观音神像,朝夕焚香祈祷菩萨普济众生”[20]。
寡居妇女普遍地存在着恐惧疾病,祈求健康、平安的思想,宗教宣传的轮回转世说对她们很有情感吸引力,她们也常常为此日夜祷祝。“晨夕奉如来,瓣香志清旷,祝儿灾害除,祝亲寿无量”[13]589“侬只心清拜莲座,瓣香低祝赐平安”[13]542“生年二十似桃花,子结尤然脸晕霞,乞与娇儿添智慧,自携绣佛施僧伽”[21]。
寡居妇女通过信仰宗教获得心灵慰藉。马里诺夫斯基说:“宗教,不是产生于推测和沉思,更不是来自误解和幻觉,而是来源于人类生活中真正的悲剧,来自人们愿望和现实的冲突”[22]。寡居妇女常年过着禁欲生活,配偶离世或常年外出也加深了她们的孤独之感,却还要承担起家庭的内外事务。沮丧、孤单、压抑、无助等负面情绪占据了该群体重要的情感位置,使得她们转而信仰宗教神祇。她们相信浮屠之说可以带走人世间的苦难,更愿意以吃斋念佛这样一种相对温和、平静的方式释放内心的孤独与煎熬。季兰韵在丈夫和妹妹相继去世后,内心极为悲痛,转而信仰佛教,每日诵读佛经以求斩断烦恼。“纸钱心事共成灭,日对金经诵几回,君自双携娇妹去,孤妻我更胜泉台。”[13]505在诵经的过程中,季兰韵心中失去至亲后的痛苦与孤单情绪得到缓解,感情的缺口被填补。对宗教神祇的信仰成为寡居妇女的情绪稳定剂,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妇女心中忧伤、孤独的负面情绪。当愿望和现实发生冲突时,信仰感能使她们在孤单、禁欲的寡居生活中更有处理问题的勇气。
宗教神祇为寡居妇女提供希望与照拂。在许多场合,“我们依赖对来世的卑微希望与期盼,唯有此能够为人性照亮那不断逼近的难免一死的阴沉前景,并且在有时候由于尘世的混乱而使人性遭遇到的一切最严重的灾难中,维持人性的开朗”[3]。寡居的妇人们通过焚香、诵经、布施等方式苦修来世,向她们所信仰的神祇祈祷来世能够过上美好的生活。《歙县志》中说,“呈坎罗维信妻汪氏年十九,夫故。立侄懋绩为嗣,抚之成立,娶妇汪氏,年十八,夫故。姑妇相依,守节长斋奉佛,寿终俱至七十有余岁”[15]1935。汪氏及儿媳通过终生信佛,日日念经苦修来世,对神祇的信仰情感是慰藉二人情绪的良药。前文所提及的奉新人甘立媃,其寡居家中,虔诚地信仰佛教:“晨稽首而颂佛兮,暮默坐而理元,祛尘虑而消众魔兮,豁青眼以见天”[17]467。家乡每遇干旱,她就向观音祈雨:“官吏朝朝祷雨,我来稽首礼观音,杨枝一洒慈悲水,岂止人间十日霖”[17]467。不仅如此,她还经常在家中焚香祝祷:“旦夕焚香表志诚,对天跪祝诉衷情。只求四海臻仁寿,属望千邦颂太平。盗贼革心归正务,士农安业息纷争。官能清正民同乐,我自甘贫织五更”[17]445。季兰韵作《雨不止变成歉岁以记实》,文中提到“恒风先损木棉花”“九月以来雨不止,朝夕淋淋数旬矣,处处田忧稻未收,家家泪滴人愁死”“五百余钱米一斗,目观嘉禾难到手”。狂风吹毁棉花,导致以纺织为生计的贫农无所适从;暴雨冲击农田,导致农家颗粒无收,饿殍载道。“才闻城南数口殇(俱冻饿而死),又听城东一家殒(城东王氏一家七口因饥寒服毒自尽)”[13]564。雨灾结束后,疫情随之而来。“奇荒之后继大疫(辛卯水灾殊甚,壬辰时疫大行),辛卯壬辰事可哀,闺中无力饥寒救,一瓣心香求佛佑,愿得明年灾病无,丰登以保苍生寿。”[13]564季兰韵悲天悯人,感叹农民饥寒交迫的状况,日日焚香祷祝,期冀佛祖能消除天灾人祸,保佑民众早日迎来五谷丰登的好年成。正如费孝通所说:“我们对鬼神也很实际,供奉他们为的是风调雨顺,为的是免灾逃祸……我们的祈祷是许愿、哀乞”[23]。季兰韵不仅是虔诚的佛教徒,从她的诗文中可知,她还崇拜道教神祇。例如,“碧霞元君仙而神,驱斥百怪朝群真”[13]542。
另外,信仰民间本土神祇也是寡居妇女寻求心灵慰藉与情感寄托的重要途径。寡居妇人不仅向佛、道宗教神祇发愿,还向民间诸神祈祷,渴望借助其力量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实现心愿。华佗、织女、天花娘娘、紫姑等都是他们祈祷的对象。她们信仰华佗能带走疾病,织女能保佑生产。至于天花娘娘,现存的徽州文书中有《谢天花娘娘祝文》:“于维圣后,淑慎其躬,外和内裕,谊美恩隆,慈航普济,甘雨宏通,施予小子,惠我儿童”[24]。儿童多患痘疹,当地妇女多相信天花娘娘能治愈此病,所以每到重要节日,多向其祷告,以期能保佑幼子平安无疾。
2.从循规拘礼至违礼败伦
人类学家指出,“深刻的情感投入本质上来说是文化的产物,受其文化影响的深度超出了先前人类学家的认识”[25]48。随着宗教文化的宣传,妇人耳濡目染,久而久之,她们的信仰情感也发生了变化,自我意识逐渐替代了保守、安分、顺从的形象。尽管族规家法里对家族成员的僧道信仰有所规约,“凡葬祖、祭祖,儒家自有正礼,僧道邪说,概不可轻信”(14)许桂馨等纂修.绩溪涧洲许氏宗谱[Z].民国三年木活字本.,而据明代徽州休宁人汪循在其文集中记录,“府君不受符籙,母受之而不禁”[10]457,意即他的母亲不再是儒家家长制的附属品,而是多依从自己的情感需求行事。不仅如此,汪循的父亲要求江循“治丧悉遵《家礼》”,但是汪母提出了否定观点,并对自己的丧礼提出了不同想法。汪母认为,“《家礼》殓束手足,地下不得走动,今冥福自有,令汪循勿将布帛缠束其手足”[10]457。
在徽州社会,女性长期处于失声状态,从汪母的治丧态度中可见信仰感已经使妇人有意识地选择自己的追求,既不再悉遵《朱子家礼》,也对宗族治理提出了挑战。同时,随着寡居妇人信仰神祇群体的不断扩大,虔诚之心越来越重,各类迎神赛会活动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乃至“十五日迎神赛会,演剧进香者以千计,妇女跪拜焚纸箔者无数”[26]。
还以徽州地区的寡居妇人为例,随着信仰的时日越久,尤其是寡居的老妇人,她们越愿意为此花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吃素食、绣佛像、写心经、求冥福,鬼巫斋戒之风在程朱阙里的徽州社会大行其道,庭院闺阁内仿佛变为一座座僧道寺院,与此同时,三姑六婆穿街过巷,利用宗教文化诱惑、欺骗寡居妇人的行为也极为猖獗。如现存徽州文书即有以下记载:“我自到某处,倐经几时,本拟即回,因某事羁留,不能速回……但老太素奉神佛,须婉言劝慰,切不可放僧尼进门,此辈异流,常致误人不浅 。切记切记!老仆家禀小主,沐恩老奴某叩禀上……老太太茹素烧香,乃老人家情性,只好顺其心意,难以违逆,至于三姑六婆,先老爷在日,久已绝迹,老奴亦不敢轻放入门,……悬望,是禀。”[18]2359年少主人即使出门少许几日,也极为焦虑、急躁,生怕家中老母被僧道之流诓骗。徽州族规家法一再要求“妇女虽老,不许入寺烧香,不许借做法事,任僧道入室”(15)许文源等纂修.绩溪县南关许氏惇叙堂宗谱[Z].清光绪十五年惇叙堂木活字本.,宗族为禁止女子出家之行为,还特别在家谱中写道:“女子为尼者削之”(16)杜冠英等纂修.光绪仙源杜氏宗谱[Z].清光绪二十一年木活字本.,等等。但是徽州妇人僧道信仰乃至泛滥现象依旧屡禁不止。
人的思维和情感都会在潜移默化地随着宗教信仰的发展程度而改变。寡居妇女过于虔诚的信仰感随着迷信思想的加深而弊端渐露。晚清,寡居妇女频繁地接触僧人、道姑,极易受到她们的言语诱骗。 “妇人无子,诱云:某僧能干,可度一佛种,如磨脐过气之法,即元之所谓大布施法,以身布施之流也。”[27]佛教教徒利用寡居妇女求子以继承宗祧的心理编造谎言,使得妇女在佛寺的“礼佛”活动中丧失贞洁,败坏了社会风俗。“求佛信神之所,成为敛财宣淫之地,尼姑成为媒婆,寺庙成了淫窟,袈裟缁衣之内,包裹的是一颗颗贪淫的灵魂,礼义廉耻荡然,荒淫无耻遍地,通奸偷情屡见不鲜,卖淫嫖娼司空见惯”[28]。这说明,一些妇女只坚持名义上的贞洁,其真实行为却不受“礼仪”规范的控制。
信仰感是寡居禁欲妇女内心情感的重要部分。作为极具情感魅力的超自然神圣象征体系,妇女将其作为控制负面情绪、安心立命的精神支柱,自发地对其信仰、尊重,她们的精神观念与情感体验皆受此影响。晚清,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物质经济基础发生改变,涉及迷信、欺骗、旧习信仰的神圣信仰成为社会秩序退化的形态表现之一。师保巫觋、僧道姑婆利用寡居妇女对神祇的极端信仰对其坑蒙诱骗,引导她们的寡居行为从维持儒家伦理道德秩序蜕变为败坏伦常。今天看来,妇女的寡居情感对明清时期儒家伦理社会稳定、协调发展确有重要作用,但是并没有一以贯之。
五、结 语
近年来,情感被视为塑造历史文化的重要因素,史学研究面临着“情感转向”的趋势。格奥尔格·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等人在回顾21世纪初期的历史学时明确指出:“探究情感在历史中的作用”已构成历史写作的趋势和重点之一[29]。
在对明清时期的历史研究中,不少学者已经从情感文化角度切入,开始关注人的欲望需求及情感实态。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重视依靠“柔软的手”来轻易地触及和操纵民众以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其中最便捷的工具就是法律、舆论、道德、礼仪、习惯、信仰等,而这些工具对长期处于失语状态的女性情感影响较深。寡居妇女群体中的大部分人在此影响下,默认失节与再嫁是与社会主流价值和规范相违背的越轨行为,她们逐渐形成了生怕玷染污名的道德恐慌及日常生活中的顺从行为,寡居者甘心情愿度过踽踽独行、形影相吊的日子。
君主专制体制下,“礼仪”的情感常常被用来表达和规范部分政府、家庭、宗教的权威体系[25]194憧憬与约束的荣辱感、效忠与责任的爱情观、解救苦难与寻求寄托的信仰情绪,这些情感相互作用,在情感控制与自由之间、在社会控制与自我规训之间,建立起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的“心理空间”。荣辱观的建立使她们的道德情操不断升华,忠贞不渝的爱情成为协调家庭与社会稳定的纽带,对神祇极度虔诚使寡居妇人成为依赖“信仰生存”的群体。
漫漫长夜,寡居之途令人生畏,路上行人却有增无减。探索明清时期妇人内心的情感变化及其思维方式,不仅可为明清社会数以万计的贞洁牌坊提供更为合情合理的解释,而且有利于还原传统妇人“寡居生活”的情感实态,进一步地可以弥补心理历史学以往以群体情感为研究对象的缺憾,为历史研究提供新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