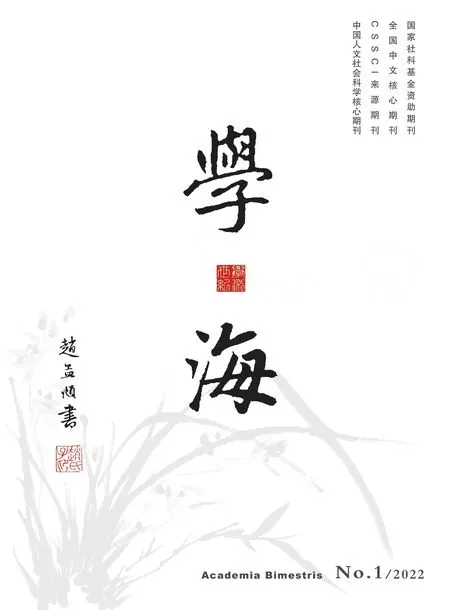转型与新生:澳门白话文学的兴起及文体变革*
2022-12-17赵海霞
赵海霞
内容提要 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进入大变革时代,因地理位置的偏离、人才的匮乏和内驱性的不足,白话文学在澳门几无自发产生的可能。同时,文化上与内地同根同源,文学发展与内地息息相通,又构成澳门白话文学产生的必然性。陈子褒在澳门倡导白话文、编写白话启蒙读本、推动启蒙教育,是晚清白话文运动在澳门的响应,为澳门白话文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1920年雪社成员冯秋雪发表澳门第一首新诗。20世纪30年代是澳门白话文学的初创期,澳门本土有白话诗、文、戏剧和小说的发表,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澳门白话文学全面兴起。澳门白话文学产生在澳门文学转型的大背景下,转型体现在“作家主体的转型”、“文学观念与作品形态的变化”及“文化下移与文体变革”等方面。知识分子的流动和市民对新思想的接受,对澳门新文学的产生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相比同时期的内地和台港,澳门新文学的产生有其特殊性。
近代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中西、古今文化交融汇通、碰撞冲突的时期,此时的文学也经历了内容、文体、观念和审美的巨大变革。从文体形态的角度来看,传统汉语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发生了显著变革,白话文学兴起,进而在五四之后获得了现代文学的合法地位。澳门虽地处岭南一隅,但与中国内地有着相同的民族学脉、文化传统和语言文字,其境内华文文学的创作和发展,一直与内地大体保持一致。明清时期,澳门文学以古典诗词为主体,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民初,直至20世纪20年代,澳门文坛上活跃的仍然是以旧体诗词创作为主的作家和文学团体,如以汪兆镛为代表的遗民诗人和雪社为代表的诗人社团。随着内地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澳门的白话文学何时兴起,背景如何,有哪些代表作品,发展状况如何,又有哪些特征?本文试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澳门白话文学产生的可能性
晚清民初的澳门,文坛上依然是古典文学尤其古典诗词一统天下。地理位置的偏离、人才的匮乏和内驱性的不足,使得白话文学产生的土壤十分贫瘠。在这贫瘠的土壤之上,白话文学自发产生几无可能。同时,澳门与内地在文化上同根同源,葡萄牙并未在这个小岛上有意识地进行文化移植,自晚清以来,澳门的文化运动和文学发展始终与内地息息相通,这又构成白话文学产生的可能性。
杜维明和李欧梵两位学者曾将香港文化的特性概括为“边缘性”,①这也同样适用于澳门。对于澳门来说,“边缘”体现在地理和学理两个方面。从地理上来说,澳门位于中国南部边陲,珠江口西岸,远离内地的文化中心,在交通尚不发达的古代,澳门很长时间是孤悬海中的一个小岛,仅有一道沙堤与内地相连,位置上可谓是边缘。从学理上来说,相对于内地中心源远流长、深厚博大的精英式文化,一度有“文化沙漠”之称的港澳,在一些学者和教材的研究领域中,一直处于“边缘”状态,澳门文学更是经常直接被忽略了。②同时,澳门本地人才相对匮乏。20世纪80年代东亚大学(澳门大学的前身)创办之前,澳门一直缺乏现代高等教育学校,本地人以渔业为主,受教育水平不高。就文学产生的动力来说,内地白话文运动兴起之初,本着一种反传统的内驱力,与之对立的是文言代表的正统文学观念和价值体系,白话文不仅是语言形式的变革,更寄寓着思想观念的革新,相比之下澳门缺少这种内驱力。不仅如此,由于长期与西方文化对抗并行,澳门文坛推崇以文言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学的态度是尊重、认同和延续,这意味着在葡澳政府的殖民统治下,华人身份的自我认同和对民族文化的坚守。自明朝到民初,澳门诗坛创作主体一直是以传统的知识分子为主,作品多是古典诗词,文学观念仍然以传统的儒、释、道为核心。从这些方面来看,晚清民初的澳门文坛,白话文运动和白话文学的自发产生几无可能。
然而,在风起云涌、新思潮乘时并起的近代,澳门白话文学的产生又是一种必然,细瞰晚清,已见端倪。首先,澳门与内地同根同源,就文学来说,拥有与内地时局密切相关的传统。澳门自16世纪中叶开始,即有零星的文学活动,真正形成规模的文学创作活动出现在晚明时期。避居澳门的明末遗民,如屈大均、释迹删等,留澳期间,记录所见,述志抒怀。后来清初派往澳门的官员如吴兴祚、印光任、张汝霖等人,创作了大量诗歌作品,掀起澳门诗歌创作的第一个小高峰。晚清民初,内地来澳门的迁客、塾师、爱国志士以及来澳避乱的粤籍士大夫,如郑观应、潘飞声、丘逢甲、汪兆镛、汪兆铨、吴道镕等,以诗歌寄情,形成澳门诗歌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可见,明末清初、晚清民初内地时局更迭动荡之际,同时也是澳门文学活动的高峰期。内地轰轰烈烈的白话文运动,势必给澳门带来影响,从而引发澳门本地白话文学的产生。
其次,内地白话文兴起之初,维新思想家们认识到,欲开启民智,在文学上必须实现语言的通俗化,必须通过教育、报刊、舆论等途径让大众接受熏陶和影响。澳门虽然是一个蕞尔小城,但开埠时间长,受西风熏染,较早拥有了报刊这一适宜白话文实践的阵地。自16世纪起,东西方贸易的发达,使澳门成为对外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商埠。澳门自19世纪便拥有了印刷所,1822年创办了中国境内第一份外文报纸——《蜜蜂华报》。1924年创办了《澳门报》,1834年至1836年间,《澳门钞报》和《帝国澳门人》先后创刊,这些都是澳门早期的报纸。1840年后,澳门不仅是西方在华办报的回旋地,也是国人办报的前哨和避风港。1897年,康有为在澳门创办《知新报》,成为维新派幸存的报刊,《知新报》发表了大量诗词,呈现出现代意识。③澳门报刊业的成熟,为澳门白话文学的兴起提供了现代化媒介。胡适的第一首白话诗发表于《新青年》杂志,澳门第一首白话诗产生于澳门文学刊物《诗声》,20世纪30年代后的报纸,更成为澳门白话文学蓬勃发展的主要园地。
再者,葡人在澳门的文化措施主要在于引进先进的工业,建造西式建筑如教堂、广场,推广西方医药以及传播宗教等,很少进行文化的软性渗透,故澳门人的语言习俗、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生活方式都还是“东方”的,澳门文化的“中华性”很独立。华人社会保持了高度的爱国热情,自觉向中华文化靠拢,一直保持与内地的交流并融入内地文学革新潮流的姿态。澳门是近代禁烟运动的主战场之一,1894年,郑观应在澳门完成了皇皇巨著《盛世危言》,对维新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世纪末,随着改良运动的开始,澳门成为康有为华南活动的基地,创办了舆论宣传阵地《知新报》。澳门也是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从事行医职业和开始革命事业的地方。“1890年前后,在澳门潜心著述的郑观应邂逅刚从香港大学毕业不久、正在镜湖医院行医的孙中山。”④20世纪初,同盟会在澳门成立澳门分会,澳门第一首新诗的作者冯秋雪,成为同盟会在澳门发展的最早会员,并在民国成立后与其他会员创办“雪堂诗社”。澳门虽是边陲小城,相对缺少文化底蕴,但精神上始终感受着中华本体脉搏的跳动,内地轰轰烈烈的白话文学思潮,必会在这里产生回应。
综上,笔者认为,澳门因地理位置偏离、人才匮乏和内驱性不足而无法自发萌生白话文学思潮,但澳门文学活动和内地息息相关,一直保持着融入新潮流的姿态,而先进的报业又提供了媒介支持,因此澳门白话文学的产生又是一种必然。澳门白话文学起自何时,发展脉络和特点如何?下文将细述之。
白话文运动“澳门化”与陈子褒启蒙读本
晚清白话文运动在澳门的响应,是陈子褒的倡导及其白话启蒙读本。陈子褒致力于启蒙教育,推动“言文合一”,不仅用白话编写启蒙课本,还在1904年主持编辑发行了白话报刊《妇孺报》《妇孺杂志》,陈子褒可以说是澳门推广白话文学的第一人,也是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为澳门白话文学的兴起吹响了前哨。
晚清白话文是晚清思想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五四白话文的基础。1903年,《宁波白话报》在上海创刊,该刊物主张实业救国,用白话文来移风易俗。同年《中国白话报》创办,次年,陈独秀在安徽创办《安徽俗话报》。1905年2月,安徽桐城人吴樾在直隶创办《直隶白话报》,1907年《吉林白话报》创办于吉林省城。白话报刊在晚清纷纷出现,办报宗旨皆是开通风气、开启民智,向同胞普及新思想。白话报刊的创办成为一股潮流,从南到北,范围几乎覆盖各省。这些报刊编印了大量的白话书籍,成为开启民智的重要措施,如梁启超主持的编译局,就有计划地编印白话书籍。
在澳门,陈子褒响应这场声势浩大的白话文运动,创办了蒙学书塾,编写了一批白话读本,并流行于华南一带。陈子褒,广东新会外海人,早年中举,1893年到广州万木草堂,翌年受业于康有为。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后,陈子褒先到日本,后到澳门办学。1899年,陈子褒在澳门组织香山、新会、新宁等地的20多位学塾教师成立“教育学会”,提倡初学启蒙,以推广改良白话课本为宗旨,先后推出了一系列白话教材。根据景堂图书馆所藏,蒙学课本举例如下:《改良妇孺须知》,分上下2卷,上卷是寻常科,下卷是高等科,全书把生字分为二十二类,每字下面注释一个短词,有时用粤语,力求通俗,如“留”字下面注释“留住佢(粤语意思:他)”;《三字书》,全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教礼节,如“早起身,下床去。先洒水,后扫地。开窗台,抹台椅。”⑤第二部分是《趣味三字书》,第三部分是《名物三字书》;《四字书》,仿照《千字文》编写的,书中宣传维新思想,反对吸鸦片和女子缠足,告诉学童要学习知识。还在列举所游历各国情况之后,列举旅行的好处,让学童可以开阔眼界,拥有广阔视野;《五字书》等,语句通俗,内容有趣。另有《妇孺八劝》《女儿书》《爱国书》,在《爱国书》中,充分体现了他的维新思想。自1895到1921年,陈子褒编写各种初级课本四十多种,这些读物被粤港澳的书塾和学堂采用,一版再版,声誉日高。
陈子褒在澳门推广白话文的特点和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陈子褒撰文立说,和晚清启蒙思潮紧密结合,积极倡导白话文运动。1900年,陈子褒在澳门《知新报》发表了《论报章宜改用浅说》一文,论述改文言为白话的重要性。他指出“大抵今日变法,以开民智为先,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不改文言,则四万九千九百分之人,日居黑暗世界中,是谓陆沉。若改文言,则四万九千九百分之人,日嬉游于玻璃世界中,是谓不夜。”⑥在该文中,陈子褒旗帜鲜明地提倡白话,阐明白话可以开启民智,有利于民气开放,国家进步,这是他推行白话文运动的纲领性文章。这篇文章与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几乎同时,一前一后,成为呼吁白话文运动的力作。陈子褒可以说是晚清澳门推广白话文学的第一人,是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其二,从实践上来看,陈子褒确定以妇孺作为白话文推广的主要对象,培育出一代新人。陈子褒在《知新报》连续发表《论训蒙宜先解字》《论训蒙宜用浅白新读本》两篇文章,阐述了他推广白话文的实践主张。在他看来,儿童是未来社会的栋梁,用白话读本开展训蒙教育,有利于儿童的成长。至于妇女,因长期在“无才便是德”的桎梏中,多不识字,陈子褒提倡妇女教育,认为这也是振兴中国的要务,如果女性掌握了知识学问,就可以把小学教育的权力归于女子。因此,陈子褒把学童和妇女作为推广白话文的主要对象,自号“妇孺之仆”,倡导女子教育和平民义学。他用浅白读本作为教材,亲自教授经史、国文、习字等学科,培养出一批优秀学生,比如岭南大学教授、广东学术界著名女学者冼玉清。其弟子陈德芸也曾撰文赞扬他对教育事业的执着:“先生设校授徒,提倡蒙学,屹屹不倦。口有道,道蒙学;目有视,视蒙学;耳有听,听蒙学;手有书,书蒙学。二十五年如一日,自刻其号曰妇孺之仆,信乎其毕生精力皆仆于妇孺也。”⑦
其三,虽然陈子褒身体力行,在澳门、香港推行白话文运动,然而随着内地白话文运动整体陷入低潮,他最终没有完成变革澳门文学语言的使命。1922年逝世之前,陈子褒未能看到澳门普及白话,也未能看到澳门文学语言完成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型。晚清的白话文运动,把语言变革和政治变革紧密结合,白话被视为一种开启民智的工具,然而语言有它的自身规律,书面语作为思想的承载,有一定的稳定性。正如裘廷梁等人所办白话报很多只是方言报,陈子褒的不少妇孺读物也是由粤方言写成,口语短时间无法代替书面语。但晚清白话文运动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陈子褒在澳门推行的白话文运动也是澳门白话文学兴起的先声。1920年,澳门第一首白话新诗出现,标志着澳门白话诗歌创作的开始。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白话诗、文、剧和小说
上文提到,1920年,澳门出现第一首新诗,作者冯秋雪和内地往来较频,而且深深肯定文学革新是“世界潮流之趋势”,他创作的澳门第一首新诗《纸鸢》,是对胡适倡导的新文学运动的切实回应。“据今所见,澳门最早的白话新诗应是冯秋雪的《纸鸢》(拟题)。它写于1920年1月,较闻一多《七子之歌》中的《澳门》最少早近五年。”⑧关于这首白话新诗,澳门大学邓骏捷教授已有详细考证,在此不赘述。但这首新诗之后,将近十到二十年,澳门的白话文学并没有形成风气,而是浅尝辄止。
与此同时,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内地新文学运动轰轰烈烈展开,早期白话诗人沈尹默、刘半农、俞平伯和傅斯年等紧随胡适进行白话新诗写作,并先后涌现出鲁迅、汪敬熙、罗家伦、杨振声、叶圣陶、冰心、俞平伯等一批白话小说作家。在此期间,澳门却相对沉寂了,除上文提到的零星白话文创作之外,白话文创作没有引领风气,也没有形成规模。承载着文学革新内涵思想的澳门白话文学的真正兴起,是在20世纪40年代。究其原因,如前文所说,澳门本地并无白话文学革新的驱动力,且人才相对匮乏,既缺乏文学革新的倡导者,也无足够的实践者,第一首新诗,只是新文化运动的一次响应,是作者本人的一次尝试而已。澳门白话文学的真正兴起要到20世纪30年代之后,随着抗战开始,广州、香港依次沦陷,大量难民中不乏学生、教师、文人墨客涌入澳门之后,澳门白话文学全面兴起,新文学随之起步了。
20世纪30年代是澳门白话文学的初创期。在这之前,澳门白话文学作品寥寥可数。1920年,澳门出现第一首新诗,1925年著名新月派诗人闻一多发表了《七子之歌·澳门》。1928年,收录了冯秋雪、冯印雪、赵连城三人共13题15首的新诗集《绿叶》发表。1927年,著名作家郁达夫的小说《过去》发表,这都是可见的较早关于澳门的白话文学。到了20世纪30年代,从事新诗创作的澳门诗人如华铃、德亢、蔚荫等陆续出现。澳门第一篇白话散文,据学者郑炜明考证,是1933年发表于《小齿轮》杂志上的《舱中之夜》,文章写了从香港到澳门的航程,总体“写得流畅有趣”。⑨笔者从《华侨报》中也发现了一些白话散文,如发表于1937年的《写白鸽巢公园》,发表于1938年的《西湾漫写》等。《写白鸽巢公园》通篇白话写作,优美流畅,全无文言痕迹。文中写道:“白鸽巢公园位在花王庙侧。这里的圣庙是所庄严巍丽底古剎,公园的前面。对有本澳唯一名胜的大三巴牌坊。后面隔了一条海道就是我们中山县的湾仔了。如果你去到这公园里。登临于这个所谓远眺台。青洲湾仔一带便可指数。每当晚霞斜影。鸟雀归林的时候。远眺海景。悠然生感。大有‘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之概。”⑩在戏剧方面,抗战时期,澳门戏剧界积极投入抗战救亡的运动中,《家》《雷雨》等作品都曾多次在澳门编排演出,也有一些原创的剧本和戏剧评论发表,如1939年8月“中旅”粤语部上演《武则天》后,报章上即发表了主演郑竹筠的文章《我对于武则天》,以及观众郑和安的评论《观“武则天”公演后之我评》。在剧本方面,笔者发现最早发表于澳门的白话剧本,是1938年4月发表于《华侨报》的剧本《鬼子进家之结果》,作者署名杨半狂,其语言风格,见第二幕如下:
布景堂中一切照前。
但是台上多了一个世杰的相。
雪云(很愁的坐在沙发上闲手抚着枕子)。
谭母(坐在留声机旁的椅上)。
……
(敲门声大大)开门。开门。
雪云妈妈——怎样(恐慌到极)矮…矮兵来了。
谭母(牙齿打冷战)无法了…开…开门罢。
可见,20世纪30年代,白话文的创作在澳门开启,从新诗到白话小说、白话散文均出现了一定数量的作品,这是澳门近代文学语言形式变革初期的体现。
20世纪40年代,澳门白话文学全面兴起。笔者通过考察澳门报刊发现,到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澳门文坛已普遍进行白话文创作,标志着现代白话取代文言文成为文坛创作的主要语言形式,白话新诗、白话散文、白话小说、白话剧本和剧评大量出现。以白话小说为例,澳门白话小说大量创作较晚,1937年《华侨报》创刊之时,发表的小说,其语言形式基本是文言和传统白话一统天下,1938年,《华侨报》连载第一篇现代白话长篇小说,到1947年,《华侨报》刊载的小说语体基本以现代白话为主了。1938年10月,《虎窟情花》在《华侨报》连载,这是笔者所见的澳门报载第一篇现代白话长篇小说。小说开篇:“戏行惯例,一到五月末一天便是散伙的期限,新班的开始时是在六月十九,但也有因着种种原故而延了这新班的开始期间的。不过无论怎样的情形,他们称呼这日脚也作‘开新’,和第一次上演就唤作‘头台’,今天是十七日,听公司的布告,头台是在台山县城哩。”可以看出,白话使用虽不太熟练,已经是欧化青年读的五四式白话了。这种白话文不同于晚清的启蒙白话文,它是一种新的语言体系,同时也是新的思想体系。它承连晚清,向民初延伸,把西方现代思想应用于社会文化领域,在思想层面具有现代性。
从陈子褒的白话启蒙教材,到冯秋雪的第一首新诗,再到20世纪40年代澳门报章白话文学的全面兴起,澳门白话文学经历了缓慢而曲折的发展过程。经过晚清民初的文学革命,在历经中西语言因子不断地互相渗透、变异、征服、妥协、归化之后,内地文学形成了一个新的白话语言系统。自1938年到1948年前后,因为战火的蔓延,内地和香港大批人士来澳,澳门和内地文化对接的同时也迅速地嫁接了这个白话系统并让它在澳门迅速成长,最终完成了澳门白话文的变革和文体转型。澳门文学在整个文体转型期,呈现出哪些特点?笔者试着进行总结。
澳门近代文体之全面转型
澳门近代文学的发展,自1840年到20世纪40年代末,与内地相比,虽然步履蹒跚,但实现了由文言到白话的语体转型,完成了它的使命。语体转型的大背景,整体呈现出“作家主体转型”“文学观念与作品形态的变化”“文化下移与文体变革”等系列特点。
第一,从作家主体来看,近代作家主体由官员代表的上层向乡绅、爱国志士、学生等中下层转移,同时出现了澳门本土作家群。自明朝到清朝中期,澳门文学的创作主体主要是两类人士:一是循迹避难的晚明遗民,如张穆、屈大均等;其二是宦旅澳门的官员,如印光任、张汝霖,以及妈阁刻诗的唱和者们。这两类人士中,官员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从《澳门诗词笺注》中选取的诗词来看,汤显祖留下四首早期吟咏澳门的作品,汤显祖作为明朝官吏,先在南京礼部主事后被贬为徐闻县典史,赴任途中,经过澳门。《由香山径入濠镜澳遍游天主寺》作者陈衍虞任番禺教谕,《佛郎机竹枝词》作者尤侗任永平府推官,《三巴堂》等诗的作者吴兴祚任两广总督,《香山澳》作者杜臻任职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澳门》《三八寺》《望洋台》《青洲山》作者刘世重曾任直隶行唐知县。成克大任内阁中书,转户部主事,迁员外郎,留下《望洋台》《仲冬赴澳》等作品。劳之辨任直隶、山东、广东等地方官,内擢大理寺卿、顺天府丞,写下《同满汉榷部巡历濠镜岙四首》。屈大均和释迹删作为晚明遗民,也曾任明朝官职。清代诗人作者中,印光任和张汝霖两位澳门同知尤其突出,作为澳门地方官,两人不仅编纂了第一部系统介绍澳门的著作《澳门记略》,还留下大量吟咏澳门的优秀诗篇。广东知府张道源、广东左翼镇总兵西密扬阿、户部主事兼泉州知府黄德峻等都在妈阁留下吟咏诗作。道光年间进士、香山籍鲍俊,曾任刑部主事,留下词作《行香子·澳门》。这一时期澳门文学作家主体中官员甚多,源于清朝前中期对地方管理的加强。1646年清占广州后,对澳门的管理一方面承继明制,一方面在军事、贸易、司法、行政体制方面设立机构,不断强化管辖权,不仅设立澳门县丞、澳门同知作为葡澳直接上司,高级官员如广州知府等也会不时前往澳门巡察。而1840年以后,清政府自顾不暇,葡国趁机排除清政府对澳门的管辖,中国官员不得以进入治下城市的方式进入澳门,此后澳门文学作家主体中官员大量减少,向中下层转移。在澳门留下诗作的晚清作家,如谭莹、蔡云湘、刘衍、张品桢、间朝亮、陈燮畴、张隽、何祖濂、杨增晖、赵天锡、梁鸾翔、梁乔汉等,他们或任职书院,或设馆授徒。又如,《澳门秋夜》作者易澜光为人掌记簿,郑观应为实业家,康有为是变法维新人士,潘飞声曾掌教德国柏林大学后主报刊笔政等。
第二,在文学观念和内容方面,由儒家正统思想转向中西文化对比和对传统的反思,相当一部分作品充满了爱国情志。明清时期,澳门文学作品的内容多为吟咏澳门风景名胜,抒情言志,或者以好奇和友好并处的态度,描写葡人的生活起居、风俗习惯和宗教习惯。在澳门的早期诗歌中,汤显祖的《香岙逢胡贾》便叙述了在澳门贩卖珍奇珠宝的葡商的情景。尤侗在《佛郎机竹枝词》中则描述了葡国人与中国迥然不同的婚礼习俗,“蜈蚣船橹海中驰,入寺还将红杖持。何事佛前交印去,订婚来乞比丘尼”。由于当时中国人对西方的知识极为有限,尤侗把天主教堂称为寺,把天主称为佛,修女称为比丘尼。在尤侗看来,葡国人在教堂内由神父主持婚礼,连同澳门主教手中的红藤杖,都非常新奇。吴历的诗词中,吟咏澳门风景、植物的较多,如三八寺景、荔枝、鲜花等。第一任澳门同知印光任吟咏澳门的诗词,艺术水平较高。《澳门记略》共刊载印光任“咏澳诗”11首,这些诗歌的空间描写恢弘旷远,语言雅丽精工,结尾往往意味深长。张汝霖的诗歌擅长描写风物,诗中多处描述了澳门优美的景色和华洋杂居的情景,如“窥牗曲通楼”和“家徒乌鬼多”,描写了澳门洋楼的外形和居住特色。1840年以后,政局的变化和时势的影响,使得澳门文学的内容和文学观念一改明清时期以山水景色风物民俗为主的特点,而是有了更多反映社会现实的内容。刘嘉谟作于1840年春的诗中提出,“夷肆扰澳门”“问道莲花澳,纷然肆犬羊”,诗中呈现了爱国之情。晚清的澳门文学中,有不少充满忧国伤时的悲慨、抒发爱国感情的作品。1885年实业家郑观应回澳门,1892年基本完成了《盛世危言》。这是一本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著作,本着“救国”的理念,郑观应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个成熟、完整的全面系统学习西方、改造中国社会的纲领。进入民国以后,澳门文学作品的数量大大增多,内容也更加丰富,与现实的关联感更强。在民初,避乱进入澳门的前清士大夫群体,以汪兆镛为代表,文学成就比较突出。进入到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又出现了一批反映国难、抒发抗战信念的文学作品。如培正中学语文老师李侯珠的《抗战诗集》,选取报上的新闻题材赋诗,诗中充满抗战必胜的信念和爱国精神。老同盟会会员廖平子手抄发行的诗刊《淹留》,收录数百首诗歌,“是一部抗战诗史”。《华侨报》《大众报》等报纸也刊载了反映抗战时事的纪实文学和爱国小说。
第三,在文学下移和文体变革方面,近代澳门文学语言形式发生了明显变革,小说、散文、戏剧大量涌现,打破了明清时期澳门文坛诗歌主导的局面,各文体发展趋向均衡,小说和戏剧创作增多。大众文化兴起,形成写作和文学的下移,以及本能欲望的扩大化、文学的感官化和多元化。首先,在语言的形式上,1920年之后出现了白话诗和白话散文。其次,散文、小说、戏剧创作增多,各文体的发展趋向平衡。在散文方面,除了20世纪40年代散文重要发表基地《艺峰》之外,散文的发表基地还有《华侨报》《大众报》等报刊,作品如1940年发表的《南湾月色》《翠微晚步》等。在小说方面,1937—1938年《华侨报》连载的小说有《曲线恋爱》《侯门样海深》《铁骑红尘录》《汉家飞将》等。在戏剧方面,抗战时期,澳门戏剧界积极投入抗战救亡的运动,发表了一些原创的剧本和戏剧评论。从小说的内容来看,澳门报刊连载的小说多为言情、狭艳、灵异、恐怖和猎奇题材,满足普通市民的阅读兴趣,追求文学的感官化,主要功能是娱乐和消遣,文学下移,娱乐至上。如1937年《华侨报》首载的《曲线恋爱》《铁骑红尘录》《侯门海样深》,《曲线恋爱》和《侯门海样深》可以看作是言情小说,《铁骑红尘录》标为“武侠爱国言情小说”。1937年11月26日开始连载的《汉家飞将》,题头标为“爱国侠艳小说”。此后,1938年连载的《恨绮愁罗》《御夫团秘史》《南国盘丝洞》、1939年的《苗宫艳骨》、1940年的《情海归槎》《铁血鸳鸯》《金城艳语》、1941年的《梵宫春色记》、1943年的《春色海棠红》、1944年的《粉侠》、1945年的《人约黄昏后》等,都是言情或武侠小说。1948年连载的《午夜尸声》《鬼恋》《粉面玄坛》《鬼姻缘》《神探记》《死城魔血》和1949年连载的《神探破奇案》《神探奇案》,都是以灵异、恐怖和侦探为题材,这部分小说受到市场的欢迎。
综上,晚清到民初,澳门文学完整承继了明清时期的文学特征,形式和内容都以古典诗词为主。内地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后,新诗的星星之火也传播到澳门,同时由于澳门地处偏僻,文学土壤也相对贫瘠,星星之火在很长时间内并未形成燎原之势。直到抗日战争爆发,纪实文学、小说、戏剧等各文体竞相发展起来,这意味着承载新题材、新语言、新理念的澳门新文学也在此时正式萌芽。
澳门新文学:知识分子的流动和新思想的接受
新文学代表着新观念、新题材、新形式,“处在‘自新’状态下的中国近代文学,完成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综上论述可以看出,澳门新文学的产生相当滞后,很长一段时间,澳门文学并未整体表现出“新民”“启蒙”“现代性”的特征,传统文学也未显现出主动求新求变的迹象。虽然报刊推动了澳门白话文学的发展和文学的通俗化,20世纪30年代传统文学依然具有强烈的延续性。直到抗战爆发,内地文人和知识分子大量来澳,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起到宣传、教育的作用,同时由于文化下移,市民文学兴起,市民阶层对新思想、新题材和新的文学形式的普遍接受,促进了新文学的萌生。澳门这个面积只有几十平方公里的小岛,曾是东西方交通和贸易的港口,也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更因二战时期的“中立”成为各界人士的避难港。知识分子的流动和市民对新思想的接受,对澳门新文学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新文学萌生之前,虽然澳门文学已表露出向现代转型的迹象,如语言的浅近化,诗歌体裁的尝试等,但整个文坛仍然保持超稳定的形态,如雪社社刊一直坚持刊载古典诗词创作。新文化运动前后激烈的新旧论争,在澳门从未出现,陈子褒的白话文运动,也未引起澳门本地的“文白之争”。澳门虽地处偏僻,但文化上是开放的,四百多年西风熏染,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一直和平友好地相处,文化的开放性与政治、地理环境的特殊性,使得澳门每每在易代之际,形成文学的创作高潮。根据章文钦教授的《澳门诗词笺注》及其对澳门文学史的考察,澳门文学数百年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明清易代之际,第二次是清末民初,第三次即抗战时期。1937年抗战爆发,1938年、1941年广州和香港先后沦陷,大批难民涌至未被战火波及的澳门,这一时期澳门的文学作品数量,超越了以往各个时期。尽管这一时期澳门文人来自不同地域、个人命运相异、政治主张也不一致,但在这片土地上同仇敌忾,团结一心,用文学创作共同表达民族抗战的正气心声。新文学杂志的出现(如《小齿轮》),一批华文文艺社团如文化协会、前锋剧社、晓钟剧社、呐喊文学研究社、怒吼社等应时而生。抗战时期的报刊如1937年11月创刊的《华侨报》,发表了大量散文和小说。在爱国热情激发下,澳门市民积极参与到各种抗战宣传和活动中来。男子身体力行,组织“义勇壮丁队”,练习实弹射击,女子则成立慰劳会,捐款、赶制衣服,青少年组织中小学战时教育先锋团,推动战时教育。市民们关心抗战进展,往往第一时间阅读报纸快讯,这些前线报道从形式、内容、观念、功能上都属于新文学。如1937年《华侨报》“侨声”版登载的《黑夜空袭》:“我们从平汉路归来,天色已经晚了,人是异常地疲乏。正当那些前来慰劳的人们,殷勤地劝我们进食的时候,而我们整个的身心却求片刻的休息,然而传令下来,是立刻再准备。从大队长那里听取了命令,我们的心又跟随了他的红笔在地图上翱翔了,十分钟之后,我们又一齐起飞。……然而为了国家,为了我们民族抗战的武器——重价的飞机的确保,我们决不愿任其轰炸。我们匆忙地仅能起飞四架,而敌人重磅炸弹已经掷下来了。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力量鼓动着,我们不但没有思想到死的恐怖,倒生着无限的民族的愤怒。”出于抗战的使命要求,更利于“表露真情”的白话诗,更易于被市民读者理解接受的白话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形式蓬勃发展,相比之下曲高和寡的古典诗词作品渐渐式微。报刊的采稿形式多样,发稿量大,有热爱文学的市民也参与到文学创作中,澳门的新文学伴随着抗日战火萌生并发展起来。这一时期,学校教育及校园刊物和社团的创办,培养了一批本地的青少年,作为本土新生力量,这批战火中成长起来的本土作家,承继并传播新文学的火种,使澳门新文学在20世纪50年代得以蓬勃发展,并迎来了20世纪80年代澳门文学创作的春天。 “三四十年代的澳门文学尽管尚处于萌芽状态,较稚嫩,但毕竟是一种开始、一种转机,是充满爱国爱民精神的,是属于全社会、全民的。它推动了澳门新文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和时代意义。”自1840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澳门完成了近代文学的过渡和转型,但此时新文学作品的数量还较少,新文学也不是真正的从澳门市民中、从澳门文学的根脉上萌发出来的,而是在外力压迫和推动之下,来自内地新文学火种的植入。相比同时期日据的台湾和受英殖民统治时期的香港,澳门新文学的产生既有与二者的相似性又有自身的独特性。相似性在于,其一,三地西学东渐的路线相同,由传教士揭开帷幕,转折在于“印刷书刊、新式学校及学会等传播媒介的涌现”,新文学的产生都伴随着晚清民初文学改良运动、五四风潮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其二,随着大众传播媒体的兴起,报刊的产生和发展,为三地旧文学的转型和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媒介和空间。在香港,20世纪20年代之后出现一大批中文文艺报刊和文学创作,如1922年《文学研究录》,1924年的《英华青年》和1928年的《伴侣》。台湾学者则以《崇文社文集》《台湾文艺丛志》为研究对象,还依据《台湾日日新报》《汉文台湾日日新报》等,分析新旧文学的关系。澳门的特殊性在于:首先是时间更晚,香港和台湾的白话文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澳门新文学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发展于20世纪40年代;其次,新文学产生前后,相比台湾的“文白之争”和20世纪30年代香港新文学的“倒退”,澳门本地没有新旧文学的论争,新文学产生伊始即是积极的姿态;再者,相比台湾和香港,澳门新文学并没有承担反殖民的功能,澳门本土并未出现类似闻一多的《七子之歌》之类型的反殖民作品。这归因于澳门开放性、人才局限及文化上可以保持独立的“中华性”。
研究一个地区的文学,理论性和史料性要兼具,随着澳门近代文学史料更多浮现和研究的深入,澳门文学的独立性、地域性及其与中华文学母体的关系会更为清晰,澳门文学的繁荣,也是中国文学的繁荣。澳门文学不仅是某地域的“地区文学”,它不僵化,更不孤立,它是20世纪民族新文学发展版图的一个部分,澳门文学发展的轨迹和时空梳理,会使得这个版图更加立体和充实。
①朱耀伟:《海外华人论述Ⅱ——杜维明与李欧梵》,见《当代西方批评论述中的中国图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4—129页。
②1986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四海》编辑委员会主编的《港台海外华文文学》,秦牧作序提出“当然高度关心香港、台湾的文学动向,因为他们实际上也是中国文学的一支。”2006年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黄万华:《中国现当代文学》第1卷(五四—1960年代),下编分为三章,第十章为“中国大陆文学”,第十一章为“台湾文学”,十二章为“香港文学”,澳门文学均未见踪影。陈思和在《学科命名的方式与意义——关于“跨区域华文文学”之我见》(《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中提出,“跨区域华文文学”应该是中国文学(含中国大陆文学、台湾文学、香港文学、澳门文学)和跨区域华文文学(中国以外地区的华人-华裔文学)的总称,而在其2014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行思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论稿》中,亦鲜见澳门文学的内容。
③赵海霞:《澳门近代报刊与文学演进脉络》,《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
④谢后和、邓开颂:《澳门沧桑500年》,广东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41页。
⑤新会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工作组:《新会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新会县政协文史组编印,1985年,第2页。
⑥陈子褒:《论报章宜改用浅说》,《知新报》1900年1月11日。
⑦黄柏军:《陈子褒、冼玉清〈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广东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广东史志》,广东史志编辑部,2018年,第234页。
⑧邓骏捷:《新文学运动的边缘回响——论澳门的早期新诗》,《中山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
⑨郑炜明:《澳门文学史》,齐鲁书社,2012年,第96页。
⑩径茜:《写白鸽巢公园》,《华侨报》1937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