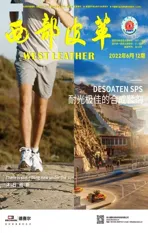儒家思想与冕服审美文化的内在联系
2022-12-14夏冰月
夏冰月
(1.重庆文理学院,重庆 402160;2.新纪元大学学院,马来西亚 加影 430000)
中国哲学丰富多彩,其中以儒家学说为主流。儒家学说因其历史久远,发展中吸收与同化各家学说,积淀了深厚的社会基础,构建了古代人的主要心理结构,成为华夏传统文化的根基。而儒家所推崇的中庸、人伦和谐观也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服饰文化。
本文将以李泽厚先生所著的《华夏美学》为引,结合书中建构的美学体系,深度探讨儒家思想与冕服审美文化的内在联系。
1 “礼乐”文化与冕服的内在联系
“远古图腾歌舞、巫术礼仪的进一步完备和分化,就是所谓‘礼’‘乐’。”[1]文中这样写道。原始时期的人类由于各种实践活动,例如图腾歌舞、巫术礼仪等,在感性与理性的融合中,逐渐被规范化、秩序化,也就是人内在的自然的人化与社会化。于是,渐渐启发了“智慧”,有了区别于动物的自我意识与社会属性。而原始时期那些以宗教为目的的活动,逐步发展成“礼乐”传统。从此之后,人的自我认知便从惧怕、崇拜神秘力量进化为“人定胜天”的高级生物。
“‘礼’既然是在行为活动中的一整套的秩序规范,也就存在着仪容、动作、程序等……这方面与‘美’有关。所谓‘习礼’,其中就包括对各种动作、行为、表情、言语、服饰、色彩等一系列感性秩序的建立和要求。”[1]“礼”通过各种形式制约、规范着人们的现实活动,其中就包括了服饰、色彩等与视觉“美”有直接关联的物质。“礼”通过这些活动或物质来实现其社会功能,也就是维护社会系统,促进人的自然人化,而这些活动和物质只有在具备“礼”的内容时,才能拥有致用、致美的意义。
冕服的等级制度就是“礼乐”文化政治思想的具体体现,是“礼乐”文化的物质表现。那些维系宗法制社会、政治秩序等的伦理内涵,最终发展为集体内部之间的等级之分,这些等级制度通过冕服的纹样、色彩、材质和冠帽等视觉上的区别,来显示穿戴者的等级身份。正如同前文所说,“礼”需要特定的活动和物质来实现社会功能。这便是“礼乐”文化与冕服的内在联系。
2 儒家思想与冕服审美文化的内在联系
孔子作为“礼乐”文化的维护者,他或亦是儒家学说的思想与冕服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呢?本文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2.1 “乐从和”的审美内涵
首先,“……与孔子引‘礼’归‘仁’的基本观点一致,儒家明显的发展了‘礼’与内在心理的重要关系……”[1],李先生强调了人的内在的情感与心理,而不是“礼”的外在理性与强制,是由感性的熏陶去制约外在的行为,通过对内在的引导,实现维护社会秩序和谐的目的。这个“和谐”,也是“礼乐”的基本目的。在孔子或儒家眼里,如何实现一种个体与个体、个体与他人(群体)以及个体与自然(宇宙)的和谐,在《华夏美学》能找到最直接明了的答案:“‘乐’只有直接诉诸人的内在‘心’‘情’,才能与‘礼’相辅相成。而‘乐’的特点在于‘和’,即‘乐从和’。”[1]很明显,儒家似乎将“礼乐”拆分,并且更加强调了“乐”的作用与意义。
因此,“乐从和”成了关键。简单地说,“乐”是一种拥有情感的艺术表现形式,它陶冶人的性情,追求生命关系的和谐;“和”,如孔子所言,“君子和而不同”。这里的“和”,是万物多样性的统一,是在相对矛盾中追求平衡与和谐,使宇宙生命生生不息;“和而不同”,因为“同”会带来生命的绝灭。因此,多样性、矛盾性是“和”的前提。
冕服中的十二章纹,蕴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给予冕服服饰背后的生命的多样性与矛盾性,足以能够作为“从和”思想的充分的艺术表现。其次,“乐从和”有它的现实形态的尺度,哲学范畴的理解便是“中庸”,便是“适度”。冕服中“视而不见”的冕旒,“充耳不闻”的充耳等,无不渗透着“乐从和”的中庸哲学。
冕旒,是冕冠前后边沿垂下,遮挡穿戴者视线的数串玉珠的装饰品。这看似并不便捷的设计却蕴藏着深刻的哲学内涵与审美心机。《淮南子》记载:“冕而旒,所以蔽明”。冕旒的设计目的主要有二:一是以“形而上”的形式区分贵贱尊卑,用旒的数量与质料的差异来表明冠戴者身份;二是“形而下”的哲学内涵,借以垂旒遮挡视线,示意冠戴者目不视非、目不视邪,不看不正之物。
《释名·释首饰》:“瑱,镇也。悬当耳旁,不欲使人妄听,自镇重也。或曰充耳,充塞其耳,亦所以止听也。”因此,“充塞其耳”是为了止听,如韩愈《原道》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这个道理放在“充耳不闻”或“视而不见”中,就是如不塞谗言,就不能明聪而进忠言;如不掩双目就不能明是非。
2.2 “比德”的物化形式
审美离不开想象,这毫无疑问,如果早期人类没有对大自然(宇宙)萌生想象的情感,没有将头脑里的疑问借助某种内在或外在的形式来寻求答案,那么就不会出现早期神秘的宗教观念,也不会产生任何的艺术形式了。
具有远古历史背景的“起兴”,是某种神话、巫术或宗教观念的现实形态,是将原始的情感、意念通过对自然物的比拟想象而对象化,这是审美文化发展的开端,它蕴含了人们的艺术想象力与创造力。“兴的起源即人们最初以他物起兴,既不是出于审美动机,也不是出于实用动机,而是出于一种深刻的宗教原因。”[2]如同巫术活动中的图腾或舞蹈一样,是具有特定且具体的本体含义的,被视为神秘含义的特定表现形式。
随着文明的前进,这种本具有特定本体含义和表现形式的“起兴”,经过重复模仿、借鉴,而逐渐失去其本身的特定情感,不再具有神话、巫术或宗教等神秘的观念或情感内容了,而变成一种对自然的普遍感受和一般的、自由的艺术形式。这种对自然的普遍感受,由于“礼乐”传统与儒家学说的影响与延续,它是从属于社会人事与伦理道德范围内的认知,这便从“起兴”发展到了“比德”阶段。
如果山在“起兴”阶段是具有特定的神秘内容,那么在“比德”阶段就被赋予可靠、坚韧、稳定等具有明确的道德内容,也就是所谓的伦理物象化,在审美范畴就是一种普遍的一般的审美表现。“把本是现实社会政治体制变而成意识形态中的伦常道德精神。”[3]“伦常道德”,这让我们立刻将儒家文化联系起来。“正如古代的巫术、神话、宗教为儒家所道德化伦理化一样,‘礼乐’传统中对‘乐’的解释论证便充满了‘比德’的内容,这也正好表现了具有巫术、宗教性能的礼乐传统向儒家伦理的过渡遗迹。”[1]将自然景物比拟成人的德行、品性的“比德”物化形式,在所有服装类型中,最具典型的莫不过为冕服了。
《书·益稷》孔疏:“天之数不过十二,故王者制作,皆以十二象天也。顾氏取先儒等说,以为日月星取其照临,山取其兴云雨,龙取变化无方,华取文章,难取耿介,藻取有文,火取炎上,粉取洁白,米取能养,棘取能断,做取善恶相背”。针对《周礼·春官·司服》有学者解释:日月星辰,“取其明也”;山,“取其人所仰”;龙,“取其能变化”等等。不管是哪位学者之说,都是以封建社会“比德”时期的认知出发去理解的“十二章纹”文化内涵。
例如,冕冠中冕板“前圆后方”寓意“天圆地方”的形状,有着突出的“比德”文化内涵。首先,是隐喻“天、地”的自然法则。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圆”为“规”,“方”为“矩”,“圆、方”又比喻这“天、地”,那么“天、地”的规矩就是世间的“圆、方”,自然生命生生不息的标准与尺度就是“圆满”与“方正”。人道从天道中映射了出来,此时的天道便是儒家的天道,因此引出了儒学经典的“知”与“行”的道德规范。
其次,是象征伦理道德“智(知)圆行方”的“比德”审美意蕴。所谓“智欲圆,行欲方。”就是行事要“方”,即为“道”“法”“常”等行为规范;知晓要“圆”,即为“智”者博学多才的内在精神。孔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这里的“智”通“知”,“智”与“仁”都是道德伦理范畴的含义。其中“仁者乐山”的“山”,通静止、稳固、安定之意,与“行方”的“方”内涵相互交融统一。孔子将“水”“山”的“动”“静”来状喻高尚道德精神人格美的“智”“仁”,也就是“知”与“行”,将人内在的道德品格与审美经验中的具体可见的形象特征相比,赋予这些内在情感道德以可视觉化的形式,这便是“比德”的审美内涵。
2.3 “天人合一”的艺术表现与政治目的
李泽厚先生反复提到“没有荀子,便没有汉儒;没有汉儒,就很难想象中国的文化是什么样子”[3]。荀子的观点可被视为孟子发展到《易传》的重要过渡,没有它,就没有后续的儒学,就没有“天人同构”或“天人合一”的儒家特色宇宙观。荀子的“天人相分”,除去了“天”的身形,彻底抹去了宗教神学成分,打破以天为大的传统思想,强调人作为宇宙主体的现实存在意义,“天”或整个世界是可被人征服的。如书中这段话:“这种力量不表现在道德主体或内在意志结构的建立上,而表现在对内在外在自然的现实征服和改造上。”[1]有了荀子对“天人”的拆分,才有了《易传》。《易传》便是在荀子的理论基础上进行反思与发展的。
“它的特色是保存和扩展了荀子那种向外开拓的物质性实践活动的刚健本色,同时又摒弃了‘制天命而用之’‘天人相分’的命题而回到‘天人合一’的心理情感的轨道上。”[1]不同于荀子的黑白分明,《易传》提倡顺应自然,而不是过分利用或隔离世界,它强调人要经过自我奋斗,不断强大内在,自我的情感、思想、德行才能得到升华,最终达到与天地同一、与宇宙同一,借助大自然(宇宙)的力量,在世俗中建功立业。这种思想加强了历代帝王在祭祀典礼中获取“君权神授”的政治决心,并在不同领域用各种美学形式实现“天人合一”或“天人感应”,以达到征服世界、统治国家的政治理想。
那么冕服,特别是汉代帝王冕服,由于时代的需要,它所蕴含的政治理想或曰建功立业的迫切感,通过图案、色彩、轮廓等艺术形式将“天人合一”的文化内涵表现出来。
早在远古时期的巫术活动,那些有资格举行巫术礼仪的巫师或首领,与寥寥众生不同,他们垄断了人与天的交流权利,在民众眼中被视为“上帝”般的存在,拥有着绝对的话语权与统治权。在奴隶社会与封建时期,“天子”与“天”的逻辑关系,蕴藏着深刻的佛教思想,“因果”之说:“因”,是天子是“天”或“上帝”的后代;“果”,是“天之子”在人间有着统治一切的权利,被作为“天神”的人间“代言人”。只有人类最高统治者才有资格与天感应,才会被“上帝”看到、认可。因此,作为“天选之子”,以“天”或曰“神”的名义统治、压迫劳动人民是中国历史文化长久以来的政治理想。那么,让人民相信“天选之子”、“君权神授”的可信性与权威性,使“上帝”能够认同“后代”,授予“天子”统治国家的权利,最终达到政治目的,是最高祭祀典礼以维护宗法制等级关系和政治秩序为目的的理性内容,亦是冕服审美文化的政治理想。
冕服“玄衣纁裳”的形制就是最明显的“天人合一”的艺术表现。“上衣、下裳”,对应的就是上“天”、下“地”的自然结构。“衣”在上,代表着象征“乾”“阳”的“天”,是宇宙中的主宰;“裳”在下,代表着象征“坤”“阴”的“地”。
“上玄下纁”的颜色,对应的正是天、地的颜色。《易·系辞》中言:“黄帝、尧、舜垂衣裳,盖取诸乾坤,干为天,其色玄,坤为地,其色黄,但土无正位,托于南方,火赤色,赤与黄即是纁色,故以纁为名也。”由此可见,天为玄、地为黄。但由于五行中“地”居中位,没有单独的方位,因此要托于居南方的赤色的火才能显现,因此下裳为赤色(纁)。由此可见,从冕服的形制到颜色,无不体现着儒家思想“天人合一”的哲学内涵。
穿戴冕服的君王,拥有了通天的本领,使得“天之子”的称号更加具备说服力,更加轻而易举地以“天子”的名义统治人民,统治世界。“这样一来,荀子所主张的‘天人相分’观点及其他的法家学说,不但没有脱离冕服审美文化的审美范畴,反而丰富和发展了冕服审美文化的深刻内蕴。”[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