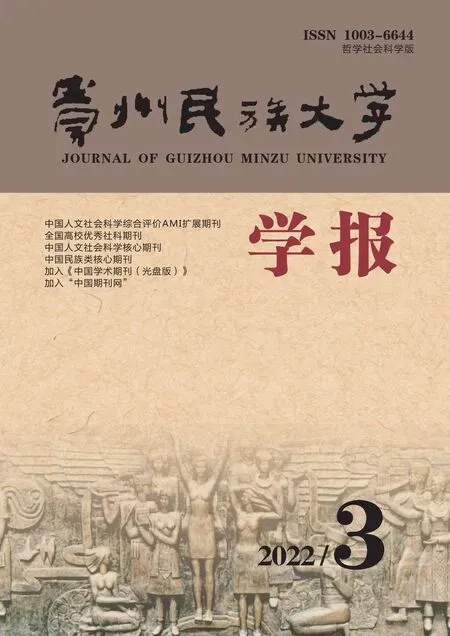有效辩护视域下的律师保密问题研究
2022-12-12廖常俊
廖 常 俊
一、引言
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下简称律师法)规定了律师保密规则,该规则一直沿袭至今。但是,在律师被定位为“国家法律工作者”的年代,一些地方的律师被要求协助打击犯罪,甚至被要求检举揭发犯罪,律师保密问题不被重视。随着我国《律师法》的修改,律师定位也发生了变化,从“国家法律工作者”转化为“社会法律工作者”和“当事人法律服务工作者”,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愈加强调,律师保密规则越来越引起重视。2012年我国刑诉法修改,增加了与《律师法》规定大致相同的内容。当前,随着我国律师队伍的不断壮大,在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和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的背景下,刑事诉讼对律师辩护和代理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效辩护和代理问题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辩护和代理质量的提高,要求律师遵守一定的职业规则,其中最重要的规则便是律师保密规则。①(1)① 2018年4月16日通过并于2018年11月1日生效的《德国律师职业规则》在第2条即规定了“保密规则”,该规则居于各规则之首,由此可见律师保密规则的重要性。虽然我国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均规定了律师保密内容②(2)② 《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辩护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有权予以保密。但是,辩护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应当及时告知司法机关。”《律师法》第38条规定:“律师应当保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有关情况和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但是,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事实和信息除外。”,但是该问题并未引起学界和实务部门的重视,有关律师保密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例如,律师保密在性质上是权利还是义务?中外普遍确立了律师保密规则,其理论基础何在?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值班律师是否应当遵守保密规则?当前律师出书成了一种时尚,涉及每一个案例的当事人,此种披露是否经过当事人的允许?人们关注的“章某某”在美遇害案件中,假设被告人的辩护律师知道章的尸体下落,能否向被害人家属和社会披露?假如辩护律师知道被告人欲在法庭上作伪证,他能否向法庭揭露?律师以发送微博、微信公众号、微信朋友圈等形式介绍自己办理的案件情况,其庭外言论是否应受到保密规则的规制?律师保密制度如何实现?我国有关律师保密例外情形的规定是否科学合理以及有无完善的必要?我国刑事诉讼法是否应当建立律师免证特权规则?等等。这些问题均需要从理论上作出回答。如果一个律师不知道如何保守职业秘密,就绝对不是一个称职的律师。最近,湖北省黄石市公安局下陆分局调取北京浩某某和(长沙)律师事务所郭某某律师办理案件的委托代理合同和授权委托书等相关业务手续,遭到该律师所的拒绝。除了此前的“李某某强奸案件”外,此事件将律师保密义务问题再一次推向了理论研究的视野。在美国,关于律师保守职业秘密的规则,体现在三个不同的规则实体中。首先,在证据法中规定有律师——委托人特权;其次,在程序法中,规定有律师的工作成果豁免原则;第三,在律师法中规定有律师的保密义务。律师的保密规则被美国一些学者称为律师职业行为的核心规则。①(3)① 参见王进喜:《美国律师职业行为规则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6页以下。“保密和忠诚对于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具有根本性,这是因为除非委托人有与其律师讨论其事务的很大程度的自由。否则,法律建议不能做出,正义不能实现。”②(4)② 王进喜译:《加拿大律师协会联合会职业行为示范守则》,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第63页。律师保密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问题,涉及被追诉人防御的有效性与惩治犯罪的关系。社会期望通过保守秘密来促进某种关系,社会极度重视某些关系,为捍卫保守秘密的本性,甚至不惜失去与案件结局关系重大的信息。很难想象有什么事情比律师保密规则更能阻碍真相的查明。③(5)③ 参见乔恩·R华尔兹:《刑事证据大全》,何家弘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56页。美国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学界和律师界围绕《职业行为示范规则》1.6条关于律师保密规则的设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我国,一些典型性案例中,律师泄露当事人秘密的情况比较严重。因此,对该问题的研究,应当引起学界和律师界的重视。律师遵守职业保密规则,有助于引领社会风尚。律师保密起到一个示范作用,能够培育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
二、律师保密系权利抑或义务
从中外已有的文献资料看,有的将律师保密作为权利看待,有的将律师保密视作义务,那么律师保密究竟是权利还是义务呢?这关涉律师保密的性质以及律师受制或者对抗的主体,不能不认真对待。之所以在性质上存在认识分歧,很大程度上与我国立法规范的表述有关。例如,刑诉法规定“辩护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有权予以保密”。从这一表述看,律师保密当是权利;但是,律师法规定“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有关情况和信息,应当予以保密”。用的是“应当”,似乎又成了律师的一项义务。这一问题,是研究律师保密规则不可回避的问题。
依笔者之见,律师保密具有相对性,针对不同的主体,它既可能是权利也可能是义务。相对于当事人而言,律师保密应当是一种义务,权利处分的主体是当事人,没有当事人的允诺,律师不得泄露有关情况和信息。例如,司法部《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13条规定:“律师未经委托人或者其他当事人的授权或者同意,在承办案件的过程中或者结束后,擅自披露、散布在执业中知悉的委托人或者其他当事人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或者其他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的,属于《律师法》第48条第四项规定的‘泄露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违法行为。”但是,这种义务又存在例外情形。例外情形的设置,完全是价值权衡的结果。律师法的立法目的在于规范律师的执业行为,特别强调律师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第38条“应当予以保密”就属于这一范畴。相对于当事人而言,律师保密应当是一种义务,权利处分的主体是当事人,没有当事人的承诺,律师不得泄露有关情况和信息。
相对于司法机关和第三人而言,律师保密又是一种权利,从域外刑事诉讼立法普遍确立的律师免证特权中即可得到明证。只有赋予律师保密以权利属性,才能有效对抗司法机关要求律师披露案件信息的无理要求,也才能保障当事人与律师之间的信赖关系。刑诉法中表述权利的词多用“可以”,但在为数不多的情况下采用了“有权”一词。①(6)① 例如,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第十四条诉讼参与人针对某些行为有权提出控告,第二十九条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要求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回避,第四十九条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诉控告,第五十八条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等等。这些“有权”的情况都是被追诉人及其辩护人面临强大的控诉机关,法律赋予的防御权,体现了强烈的权利属性。换言之,刑诉法的立法目的就在于限制公权,尊重和保障人权。因此,面对国家机关时,律师保密当然是一种权利。中华全国律协也认为“律师保密既有权利的属性,也有义务的属性。当我们强调其作为权利属性的时候,更多的是着眼于律师和司法机关的关系,主张律师可以根据保密特权而免去作证的义务,涉及的是诉讼法上证人作证义务问题;而当我们强调其作为义务属性的时候,则更多的是着眼于律师和委托人的关系,主张律师应尽到合理的注意,以保障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及委托人各种隐私和信息被不合理地公开”。②(7)②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职业伦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53页。2018年11月生效的《德国律师职业规则》第2条第1款规定:“律师有保密的义务和权利。”
关于律师保密问题,刑诉法采“权利说”,而律师法采“义务说”。对同一事项的不同规定,既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和统一实施,也反映了立法者的矛盾心态。但是,笔者试图理解这种立法上矛盾的合理性:是否出于保障当事人权利的考虑,刑诉法赋予了律师保密的权利属性;是否出于规范律师执业活动的考虑,律师法赋予了律师保密的义务属性。这恰恰说明在律师保密性质问题上,立法者针对律师所面临的不同情形,作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鉴于律师保密兼具权利义务性质,因此在立法完善时尽量避免使用“有权”“可以”“应当”等词汇。对此,可以借鉴美国律师协会《职业行为示范规则》1.6的规定,明确规定“未经委托人作出明智的同意,律师不得泄露在辩护、代理过程中了解的案件有关情况和信息”①。(8)① 参见王进喜译:《美国律师协会职业行为示范规则》,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页。同时规定一系列例外情形。
日本学界和实务上也持此种观点,认为律师守密义务具有双重性质。对咨询人和委托人来说是律师的义务,对国家机关和第三人来说是律师的权利。保密义务既是律师对咨询者或委托人的一项义务,律师对国家机关或第三人系其权利,不开示委托人秘密的权利。作为义务,可以获得咨询人或委托人的信赖以便执行职务,作为权利,可以对抗国家机关要求开示当事人秘密事项的请求。②(9)② 参见森际康友:《法曹伦理》,刘志鹏等译,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48页。正是基于此种认识,日本《律师法》第23条规定:“律师有保守职务上获得的秘密的权利,同时负担守密义务,但是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时候不在此限。”③(10)③⑥参见森际康友:《司法伦理》,于晓琪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3,64页。从律师守密规则的发展历史看,在17世纪以前,属于律师的一项基本权利,但到了19世纪,被认为是当事人的权利。④(11)④ 参见杰弗里C·哈泽德、安吉洛·冬迪:《比较法律伦理学》,李礼仲译,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227页。律师保密规则的性质不仅是律师之义务,且同时系律师之权利。由于其与委托人之间的信赖关系和契约义务,其义务性更为强烈。⑤(12)⑤ 参见姜世明:《律师伦理法》,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第172页以下。保密义务是律师义务,同时也是律师为取得咨询人或委托人信赖,籍以执行业务,进而保障律师业务之存立而承认的职务上权利。⑥
律师保密兼具权利和义务属性,有利于实现有效辩护和代理,更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维护公平正义的实施。具体如下:第一,有利于构建协商式的刑事诉讼模式。经过多年改革试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刑事速裁程序被写入刑诉法。这些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为前提的改革举措着眼于构建协商式诉讼模式。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施有赖于控诉方与辩护方之间的平等协商。辩护律师以保密为前提,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建立起来的委托关系,不可避免得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面对控诉机关的指控,律师基于辩护的立场“有权予以保密”,这是域外刑事诉讼立法中普遍确立律师免证特权的根据。只有赋予律师保密以权利属性,才能保障律师依法独立履行辩护、代理职责,而不是“唯司法机关的马首是瞻”,也才能保障当事人与律师之间的信赖关系。第二,有利于充分保障当事人的权利。律师与当事人之间形式上是一种委托关系,实质上是一种信任关系。基于这层信任关系,律师难免会得到一些控诉机关急于得知的事实和信息。而律师法要求律师“应当予以保密”。如此,被追诉人才可大胆放心的聘请律师,才可以吐露心中的秘密。律师掌握的信息越全面,越容易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其意见被当事人采纳的可能性更大。第三,有利于改善律师的执业环境。当前,律师执业活动面临着诸如“会见难”、司法机关听取律师意见不够充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律师作用发挥不够、律师控告申诉力度不够等情况。①(13)① 徐向春:《尊重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彰显现代司法文明》,《检察日报》2019年7月25日,第3版。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可以以披露证据的积极作为方式指控犯罪,而律师可以以保守秘密消极不作为方式进行防御,以此实现“平等武装”。律师绝对不能协助自己的对手“攻击”自己的当事人。尤其是保密的权利属性,可以使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成为独立的司法单元,提升其诉讼主体地位,这在目前律师执业环境有待改善的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
三、律师保密的理论基础
律师保密规则作为律师职业规则中的核心规则,其理论基础何在?亦即为什么中外各国普遍确立这一规则,且该规则在域外是一条历史悠久的规则,其价值何在?这是我们研究律师保密问题同样需要作出回答的问题。
(一)信赖保护理论
律师为当事人提供帮助,当事人必定希望律师能提供高质量的有效帮助。然而,高质量有效帮助的前提是律师能够全面了解案件信息,而案件信息主要来自当事人的吐露。当事人之所以自愿将案件信息向律师倾诉,是因为对律师保守秘密的信赖,亦即信赖保护理论。没有当事人对律师的信赖,律师了解的案件信息必定不全面甚至会受到当事人的误导,此种情况下,律师难以提出可以为当事人接受的合理建议。律师与当事人之间必须建立信任关系,这是有效辩护的前提。一些国家的律师规则甚至规定,当这种信任关系不存在时,律师可以终止辩护。例如加拿大律师协会联合会颁布的《职业行为示范守则》第3.7-2规定:“如果律师与委托人之间严重失去了信任,则律师可以退出代理。”①(14)① 王进喜译:《加拿大律师协会联合会职业行为示范守则》,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第157页。当事人对律师失去信任,成为律师退出辩护或者代理的正当理由。只有在律师了解他的委托人所知道的所有与案件相关事实后,律师才能有效地做好辩护工作。除非委托人能够被保证律师将会以最严格的保密措施来保护所有这些信息,否则,我们就无法期望委托人将所有潜在相关的信息——其中包括极有可能使其获罪的那些信息——透露给律师。委托人和其律师之间关系的目的和必要性要求委托人能最充分、最自由地表达其目标、动机及行为。如果破坏了当事人对保密性的“神圣信任”,那么委托人就无法自由地将秘密托付给期望能为其提供法律建议和帮助的律师。人们就不会冒险去咨询精于此道的人,或者只敢将案件的一部分告诉他的律师。②(15)② 参见门罗·弗里德曼:《对抗制下的法律职业伦理》,吴洪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7页。律师和当事人之间的信赖关系是对抗制和有效的律师帮助的基础,对于这种信赖关系的忠诚是“我们职业的光荣”。只有当事人愿意将那些可能牵连自己或使自己陷入困境的事实告知律师,并相信律师能为自己保密时,律师才能为其提供最有效的帮助。那些认为律师值得信赖的当事人也更容易接受律师的建议进行正确的行为。③(16)③ 参见蒙罗·H·弗里德曼、阿贝·史密斯:《律师职业道德的底线》,王卫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5页。例如,一位射杀了其丈夫的妇女,之后否认自己实施了射杀行为,她不太愿意告诉律师她的丈夫当时正在用一把匕首攻击她。她认为这样说会证实自己确实朝丈夫射击了,然而她并没有意识到她这样做其实是正当防卫,从而可以免于谋杀罪的指控。④(17)④ 参见戴维·鲁本:《律师与正义——一个伦理学研究》,戴锐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5页。日本学者也认为:“律师必须从委任人处得到所有的资讯才有可能进行有效的法律工作。”①(18)① 森际康友:《法曹伦理》,刘志鹏等译,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67页。可见,当事人对律师全面如实陈述是取得好的辩护效果的前提条件。律师保密义务与律师职业本质中之“高度信赖关系”密切相关。正是这一信赖关系的存在,委托人才能毫无保留地将家丑、社会交往、业务秘密以及个人不为人知的行为或心理状态等资讯告诉律师,而律师据此可作出周全、准确的法律判断。因此,在德国,有学者将律师守密义务视为律师职业之支柱。②(19)②③参见姜世明:《律师伦理法》,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第171页以下,146页。法官和律师都同意,保密对于确保当事人坦诚地公开那些可能令其陷入困境或存在潜在风险的事实的重要性。这一共识是基于最广泛的那种以经验为根据的证据,即法官和律师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世纪复世纪积累起来的经验。③当事人向辩护律师敞开的是心灵的深处,阐述的是自己的无辜、自己的堕落,不愿为他人所知的耻辱,连同私生活和家庭日常生活的所有细节也都向他倾诉。对此,司法女神不仅被蒙上了双眼,还应该耳朵发聋。④(20)④ 转引自尤·彼·加尔马耶夫:《俄罗斯刑事诉讼律师违法活动面面观》,刘鹏、从凤玲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94页;参见A·科尼:《刑事诉讼中的道德基础》(选集第4卷),莫斯科,1967年,第54页。然而,在我国,长期以来当事人与律师之间的信任关系以及律师保守职业秘密的问题不被重视,例如指定辩护或者通知辩护中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是“摊派”的,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中,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是“随机”的,上述两种情况下根本谈不上信任关系的建立。在值班律师制度中,由于值班律师并非辩护律师,没有值班律师保密的要求,这也是我国指定辩护和值班律师法律帮助质量不高的原因所在。
(二)尊严理论
律师披露案件秘密需经过当事人的同意,这是对当事人主体地位的确认和尊重。在律师保守的秘密中,有一些甚至是当事人不愿意让其配偶和其他家人知悉的个人隐私,而这些个人隐私是维护当事人尊严所不可或缺的。即便是作为被追诉人甚至罪犯的当事人也享有隐私权和人格尊严权。因此,律师保守秘密不仅能给当事人带来案件利益,也可以让其“体面”的生活,人格尊严得到维护。如此一来,尊严理论自然成为律师保守秘密的理论基础。在德国,律师守密义务来自于一般人格权的保护,强调任何人均有发展人格之自由,这一自由权包括资讯之自我决定权。如此,为了维护当事人人格尊严,律师对于委托人之资讯,当然不得任意散布,否则就侵害了委托人的资讯决定权。①(21)① 参见姜世明:《律师伦理法》,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第169页以下。美国学者马修提出的“尊严价值理论”一定程度上可以对此予以解释。“尊严理论”的核心内容是,评价法律程序正当性的主要标准是它使人的尊严、自尊得到维护和增强的程度,大体包括隐私、参与、平等、理性等方面。“尊严理论”是针对实证主义、工具主义甚至功利主义的程序价值观念而提出的。②(22)②④参见陈瑞华:《程序正义理论》,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第253页以下,257页。律师保密具有对抗公权力的权利性质,甚至可能阻碍事实的发现,这就避免该项程序设计沦为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危险。“在一个尊重个人尊严的社会中,我们赋予查明真相的重要价值并不是绝对的,在有些情况下可能得服从那些更高的价值。”③(23)③ 门罗·弗里德曼:《对抗制下的法律职业伦理》,吴洪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页。“只有尊重人的隐私,当事者才能真正成为独立的自治体,而不是被动承受官方处理的客体,其人格尊严也才能得到尊重。”④律师“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应当绝对忠诚于当事人,不能作背叛当事人的事情,尤其是未经当事人同意,不得将案件信息泄露出去,否则,当事人可能会背负沉重的“精神枷锁”,被施加可能重于刑法惩罚的“心理痛苦”。维护当事人的人格尊严,就是为了解除这些“枷锁”和痛苦。我国和域外刑诉法典普遍确立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试想一下,假如没有律师保密规则,被追诉人对律师陈述的而不想泄露的有罪事实,可能会借助律师的表达而成为控方证明有罪的证据,这其实违反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获得辩护的权利与反对自我归罪的权利的依据都在于对人格尊严的尊重(这体现在个人在面对国家时,对自我作出肯定)。”⑤(24)⑤ 戴维·鲁本:《律师与正义——一个伦理学研究》,戴锐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9页。
(三)独立辩护理论
独立辩护理论要求律师辩护,不仅要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当事人,更要求其独立于公权机关。律师协助打击犯罪往往是从放弃保密职责开始。典型的是律师充当警方的“线人”,这是最令人震撼的。由于刑事诉讼是个人与政府之间的一场纠纷,为了防止以强凌弱和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更为了实现律师独立辩护,使控辩审三方的诉讼构造能够良性运行,赋予律师保密义务具有必要性。律师保密义务的确立,其实是给予了弱小个体对抗强大公权力的有力防御手段。律师可以以此保持独立的品格,防范公权力的侵扰。“辩护职能的重要意义在于防止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形成‘一面倒’的局面,以确保诉讼结构的合理和诉讼结果的公正。”①(25)① 熊秋红:《刑事辩护论》,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10页。即使在非当事人主义的诉讼程序中,如果对辩护之进行不授予深广且独立的权利,则仍不免有损法治国家的理想。因此,即使被告私下对辩护人已为犯罪之自白,则该辩护人仍得据此证据不足之情况声请做成无罪之判决。如果辩护人违背其当事人意愿,向法院告知其自白时,则辩护人不仅严重忽略了其对被告之代求义务,也将受到刑法的处罚。②(26)② 参见克劳思·罗科信:《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48页以下。如果没有律师保密规则,检察官可能会随意地把辩护律师置于证人席上并且要求他透露当事人告诉他的有关案件的一切,那么就会出现比现在多得多的有罪判决。面对这种问题,诚实的辩护律师往往不得不回答说:“他告诉我那是他干的。”律师保密规则阻止公诉人采取这种捷径。③(27)③ 参见乔恩·R华尔兹:《刑事证据大全》,何家弘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58页以下。“律师执业独立于公共权力机构,包括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尤其是司法权力机构。律师职业系独立自由之职业。”④(28)④ 施鹏鹏:《法律改革,走向新的程序平衡?》,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40页。《德国律师职业规则》第1条第1、2款规定:“律师除应履行法律或职业规则对其特别规定的义务外,其执业是自由、自治和不受管制的。律师的自由权利是公民参与法治的保障。律师职业的作用是使法治国家成为现实。”
四、当前我国律师保密规则的缺陷
我国律师保密规则主要见诸于《律师法》《刑事诉讼法》之中,然而在性质上二者之间却存在冲突,这当属该规则之缺陷。除此之外,诸如保密主体、对象、范围、期限和例外情形的设置也有可讨论之处。以下分别作一探析。
(一)保密主体
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将保密主体限定为“辩护律师”,但是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其他律师、该律师的助理和实习人员其实也是守密主体。以下笔者拟着重分析“值班律师”和“实习律师”这两类主体。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和立法确认,“值班律师”这一新型的律师种类也为2018年修改的刑诉法所确立。根据刑诉法规定,值班律师并非辩护律师,行使的是“法律帮助”而非“辩护”职能,据此值班律师自然被排除在保密主体之外。然而,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提供法律咨询”,被追诉人其实就是法律咨询者。根据前述的信赖保护理论,为了使值班律师的法律帮助有效,也应当要求值班律师对咨询和交流的内容予以保密。大概是律师保密规则立法规定较早,而值班律师制度确立较晚,因此尚未来得及对保密规则内容进行修改。从域外立法和制度实践看,即便是咨询者,甚至是尚未与律师建立委托关系的“潜在客户”,其与律师交流的内容,律师也应当保密。“面对作为外人的律师,咨询人和委托人在刚开始的咨询阶段就要把所有的话和盘托出,对许多人而言都是勉为其难的。但是如果不能安心地提供信息或者委托律师取证,案件则不能得到很好的处理。”①(29)① 森际康友:《司法伦理》,于晓琪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3页。按照我国《律师法》保密规则的规定,保密的主体是“律师”,按照文义解释,值班律师显然应当包括其中。这不可避免与刑诉法的保密规则发生冲突。需要注意的是,对尚未正式执业的“准律师”,例如“实习律师”或者尚在律师事务所实习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学生,因其工作关系,也会接触到涉密事项,其同样负有守密义务。对此,法国《律师法》第12-2条规定:“接受培训的个人对于其在培训及实习期间在职业场所、法院及各种机构所了解的事实及行为均应严守职业秘密。律师学员进入培训后,即应在培训中心所在地的上诉法院宣誓,誓词如下:‘本人宣誓在此后的培训及实习期间,严守所获悉的一切事实及行为的秘密。’地区职业培训中心管理委员会主席应出席宣誓仪式。”②(30)② 施鹏鹏:《法律改革,走向新的程序平衡?》,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53页。为此,笔者建议在未来刑诉法修改时,应当删除“辩护”二字,并增加“欲成为律师的实习人员”。如此一来,该规则不仅适用于“值班律师”,也适用于“实习律师”。他们在从事辩护或者代理业务过程中,也有机会了解到委托人和第三人的信息,因此对其行为应当予以规制。既然保密规则是以保护委托人与律师之间的信赖关系为理论基础,律师保密是其对当事人的一项义务,那么在委托辩护(代理)合同中应当对保密事项作出约定,至少应规定“没有委托人、当事人同意,不得泄露与委托人、当事人有关的信息”。①(31)① 在实践中,因被追诉人被羁押,许多案件都是由其家属代为委托律师,这就出现了委托人与当事人不一致的情形。此外,该律师的雇员、同一律师事务所的同事,也应成为守密的主体。同一事务所人员会有机会接触其他办案律师所办理案件之秘密,例如相互切磋讨论案情、为办案参考需要而借阅卷宗、在案情资料及相关文件传递过程中被非承办人员接触到秘密资讯等,因而保密义务不仅约束承办案件的律师,同一事务所的其他律师亦受其约束。②(32)② 姜世明:《律师伦理法》,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第177页。德国《律师职业法》第二条第4项规定:律师应明示其共事者及其他对其执业协力之人尽保密义务及敦促为之。据此,律师在聘请雇员时应当在雇佣协议中载明保密义务条款。在雇佣期间,律师还应经常性地进行具体告示,以确保受雇人员能够坚守秘密。日本《律师职务基本规则》第19条规定:“律师应督导事务职员或司法研修生、其他使与职务相关者,就业务不得有违法或不当之行为,或泄露、利用法律事务所因执行职务所取得之秘密。”“与职务相关者”包含法律实习和校外研习制度下所指导的法科大学院学生。通过上述规定,明确课予律师指挥监督之义务。③(33)③ 参见森际康友:《法曹伦理》,刘志鹏等译,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50页。
(二)保密范围
保密范围是指对何人保密的问题。原则上应当是委托人或者咨询人以外的所有人。在此,委托人及其家属是需要着重分析的两类人员,也是实践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当事人作为律师法律帮助的对象,原则上享有阅卷权,但是考虑到我国的侦查利益和司法效益,基于对当事人翻供等的顾虑,阅卷权是赋予律师享有。但是,2012年刑诉法修改赋予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以后的“核实证据权”,在核实的范围和方式问题上,立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均未明确。④(34)④ 参见韩旭:《辩护律师核实证据问题研究》,《法学家》2016年第2期。司法实务部门的领导,甚至一些学者主张律师只能核实实物证据,对“人证”不能进行核实。理由有二:一是诱发翻供或者串供;二是对被害人、证人进行打击报复。并且“核实方法限于口头核实”,而不宜将卷宗材料交由当事人阅览。①(35)①②参见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职业伦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59页以下,160页。笔者认为,此种建议不妥。庭审实质化要求质证实质化,如果律师不能核实“人证”并据此做好庭前准备,那么庭审“一面倒”的格局将很难发生变化,这不利于宪法赋予被告人的辩护防御权的实现。至于向当事人家属透露案情的问题,律师应当以是否会引发当事人串供、案犯逃匿、证据毁灭或者证言发生变化为标准加以考量,而不能将卷宗材料、阅卷笔录、会见笔录和调查取证情况告知当事人家属。②有些涉及当事人隐私的信息,律师更不能泄露给其家属。③(36)③ 参见韩旭:《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及其家属证据知悉权研究》,《现代法学》2009年第5期。“对于律师保密义务之遵守,乃要求律师不可对委托人以外之人泄密,即使系委托人之亲属,原则上未得委托人同意,亦不能对之泄密。”④(37)④ 姜世明:《律师伦理法》,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第181页。
颇有争议的问题是,律师对委托人的守密义务与对法庭的真实义务发生冲突时该如何处理?例如,法官在庭审中要求律师回答被告人的涉密信息。因两种义务,律师都必须遵守,原则上应以律师的守密义务为优先,此时律师应该保持沉默。
(三)保密对象
依据我国律师法和刑诉法的规定,律师保密是对委托人的信息的保密,这在立法上是比较明确的,而对第三人的信息是否予以保护则语焉不详。保密对象包括已经签订委托协议的当事人自不待言,关键是尚未签订协议的咨询者。根据日本《律师职务基本规则》第23条之规定:委任人不限于在一定期间有继续委任关系之人或曾有委任关系之人,还包含未登载姓名而只有一次性的法律咨询之人,对于有可能成为委任人但最终并未成为委任人,因信赖关系而协议时,该协议内容的秘密也应予以保密。⑤(38)⑤ 参见森际康友:《法曹伦理》,刘志鹏等译,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57页。从《美国律师职业行为规则》1.6条(a)之规定内容看,律师保密是对“委托人”;德国联邦律师公会《律师职务规则》第2条(2)规定:“保密的权利和义务,及于一切职业遂行上所取得者。”法国律师公会2004年统一内规2.2之第3号指出:“律师在职务遂行中所收受之一切资讯及秘密。”欧洲律师公会协会欧洲联合律师职务基本规则2.3.2也规定:“律师必须守护其职务遂行上取得的一切资讯秘密。”从德国、法国和欧洲律师协会的律师规则看,“律师在履行职务时获得的所有信息”均应予以保密,没有特别限定保密的对象。①(39)① 参见森际康友:《司法伦理》,于晓琪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7页以下。法国《律师法》第66-5条规定:“不管是何类案件,无论是法律咨询还是法庭辩护,律师对客户所提供的法律咨询意见、律师针对客户所设计的法律咨询意见、客户与律师之间的通信往来、律师以及在特殊情况下其同事向客户所发送的带有‘正式’标志的函件、会谈记录以及在更一般情况下的所有案件材料均受职业秘密规则保护。”②(40)② 施鹏鹏:《法律改革,走向新的程序平衡?》,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69页。笔者认为,律师保密义务不应及于第三人。首先,保密义务属于律师忠诚义务的必然要求,具有忠诚义务的性质,而该项义务是对委托人而非第三人的;其次,律师从第三人处获得的资讯通常是通过调查取证程序获得,以“调查取证笔录”或“询问笔录”方式体现,以提供给法庭作为待证事实的证据为目的。如果将其作为律师保密对象,则第三人意志将决定律师不得向法庭公开,如此一来律师辛辛苦苦的调查取证行为将失去意义,相当一部分调查取证成果将不能在诉讼中使用。
我国律师保密范围是“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委托人不愿披露的其他信息”。“不打算把交流内容透露给除了有利于对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人或者沟通交流所必需的人如送信者以外的任何人。仅仅指出存在着律师与其当事人之间的交流是不够的,起码周围环境要求保密。”③(41)③ 乔恩·R华尔兹:《刑事证据大全》,何家弘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59页以下。通常保密信息需要以当事人明示的方式向律师提出,但有时也可根据“周围环境”进行推断。当事人在与律师交流时有第三人在场即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很多时候当事人在咨询时可能有家人或者亲戚朋友陪同,律师可能会有助理或者秘书在场记录,并不能以此为由否认交流的秘密性。我国立法上要求律师保密的范围是“有关情况和信息”,通常表现为“交流”秘密,主要是律师“听”到的情况和信息,那么律师“看”到的以及受当事人委托保管的物品能否作为保密标的纳入保密范围,尚不清楚。这就涉及何谓“秘密”的问题。“秘密”是委托人过去的犯罪行为、违反社会伦理的行为、疾病、身份、亲属关系、财产关系、遗言的存在与否、居所及其他构成委托人不利益事项等,包含了所有社会观念上内容不欲为人知晓的一切事情。①(42)① 参见森际康友:《法曹伦理》,刘志鹏等译,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51页。根据对美国律师协会《职业行为示范规则(2004)》1.6的“注释”,保密规则不但适用于委托人与律师秘密交流的事项,还适用于所有与代理或者辩护有关的信息,不论其来源如何?②(43)② 参见王进喜译:《美国律师协会职业行为示范规则》,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1页。有时可能来源于当事人以外的第三方,如果当事人不愿披露,则律师负有守密义务。律师保密范围不限于言词交流,还包括实物材料。例如,委托人基于信任委托律师代为保管的文件、物品,只要这些文件、物品与违法犯罪活动无关或者不含有违法犯罪内容,律师同样应当予以保密。未经委托人允许,不得交给公权机关,公安司法机关也不得予以扣押。域外刑事诉讼立法确立的律师免证特权中均有“禁止扣押”要求,其中对委托人基于对律师信任交给其保管或其持有的物品,律师有权拒绝交出,公权机关也不得随意扣押,除非具备例外情形。因此,在解释我国立法上的“有关情况和信息”时,应作广义解释,既包括言语交流的信息,也包括物品所包含的信息。
我国立法要求律师保密的信息是在“执业活动中”获知,域外要求“职务上取得”。无论是我国的“执业活动中”还是域外的“职务上取得”,二者虽表述不一,但内涵相同,均强调律师在处理法律事务过程中得知。如果是朋友间的私人对话、闲聊,律师在此过程中偶然得知的秘密,就不属于律师守密对象。
在此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诉讼相对人的信息可否公开?这需要视情况而定。有时从诉讼相对人的信息中可以间接获知当事人的信息,此时律师也不应泄露相对人的信息。因“其相对人资讯即形同系律师委托人状态之镜面反射”。如此,方能保证委托人之资讯的间接泄露。
(四)保密期限
我国《律师法》和《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将律师保密义务的期间限定在“执业活动中”,对起始和终止时间并未作出规定。事实上,律师保密不仅是在其与委托人关系存续期间,即所谓的”执业活动中”。即便是辩护或者代理活动结束,乃至律师退出辩护或者代理活动,甚至包括特殊情形下律师被停止执业或者吊销律师执业证之后,均应承担保密义务。根据日本律师《职业基本规则》的规定,即便是取消律师注册的人,或者在案件结束以后,仍然继续负有保密义务,该义务是没有时间限制的。①(44)① 参见森际康友:《司法伦理》,于晓琪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1页。直到该秘密已经为公众知悉,而无继续保护的必要。需要注意的是,辩护人或者代理人因各种原因而退出辩护或者代理活动,前任律师对于接任律师仍负有保密义务,未经委托人同意,也不得泄露案件秘密和信息。②(45)② 参见王进喜译:《加拿大律师协会联合会职业行为示范守则》,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第165页。律师保密除了辩护或者代理关系结束以后之外,在起点上并不以委托关系始,而是在向该律师正式咨询法律问题时起。否则,自认为涉嫌犯罪的公民就法律事宜可能不敢大胆请教律师。为了鼓励社会公众积极向法律专业人士寻求法律咨询,接受咨询的律师,无论是专职律师还是兼职律师,均有义务保守秘密。即使涉嫌犯罪的人表示欲潜逃,律师也不应向警察报告。在委托协议签订之前的咨询阶段,如果律师不能保证保守秘密,咨询人怎会敢向律师倾吐心声?而在交流不充分情况下律师提出的解决方案,又如何能保证质量和保护咨询人的最大利益?何况不排除会有一些律师恶意利用与咨询人交流的信息,“倒向”对方当事人,并利用之前所获取的信息为对方当事人服务。因此,美国律师协会制定的相关职业行为规范指出:保密义务,在律师同意考虑是否建立委托关系时就已经产生。③(46)③ 参见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职业伦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63页。
(五)例外情形
律师守密义务并非绝对性义务,“因为仍存在着其他更重要的价值,有时为了保全它们而必须解除该义务”④。(47)④ 森际康友:《法曹伦理》,刘志鹏等译,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59页。除了极少数国家对律师保密规则没有作出“例外情形”的规定外,大多数国家采用了“原则+例外”的立法体例,我国也采纳了大多数国家的做法。律师保密制度的例外,是价值权衡的结果。中外在建立律师保密制度时之所以普遍确立允许律师披露信息的例外情形,就是在律师保密所带来的利益与披露信息所产生的社会价值之间进行综合判断后作出的选择。综观中外立法中关于例外情形的设置,主要涉及三方面内容:一是预防或者避免未来重大案件的例外;二是律师自我保护的例外;三是犯罪或者欺诈的例外。例如,美国律师《职业行为示范规则(2004)》1.6(b)项规定:“在下列情况下,律师可以在其认为合理必要的范围内披露与代理委托人有关的信息:(1)为了防止合理确定的死亡或者重大身体伤害;(2)为了防止委托人从事对其他人的经济利益或者财产产生重大损害的,并且委托人已经利用或者正在利用律师的服务来加以促进的合理确定的犯罪或者欺诈;(3)为了防止、减轻或者纠正委托人利用律师的服务来促进的犯罪或者欺诈对他人的经济利益或者财产产生的合理确定的或者已经造成的重大损害;(4)为了就律师遵守本规则而获得法律建议;(5)在律师与委托人的争议中,律师为了自身利益起诉或者辩护的,或者为了在因与委托人有关的行为而对律师提起的刑事指控或者民事控告中进行辩护的,或者为了在任何与律师对委托人的代理有关的程序中针对有关主张作出反应;或者(6)为了遵守其他法律或者法庭命令。”①(48)① 王进喜译:《美国律师协会职业行为示范规则》,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页以下。中国留学生章某某在美国遇害案,至今尸体下落不明,被害人家属感情上确实无法接受。但是,根据上述的律师保密规则,律师违反委托人意志进行信息披露只能是为防止或避免即将发生的重大伤害,而非已经发生的事实,因此,即使委托人克里斯滕森的辩护律师知悉尸体下落,没有委托人的允许,他也不能对此信息向包括被害人家属在内的社会公众披露,否则将会遭到纪律惩戒。加拿大律师协会联合会《职业行为示范守则》3.3-3至3.3-7规定了律师保密的例外情形,即“当律师有合理根据认为存在迫在眉睫的死亡或者严重身体伤害风险,为防止该死亡或者伤害之必要,律师可以披露秘密信息,但是披露的信息不得超过所需”。“如果有人诉称律师或者律师的非合伙人或者雇员:(a)已经实施了涉及委托人事务的犯罪;(b)就涉及委托人事务的事项承担民事责任;(c)实施了职业过失行为;或者(d)从事了律师职业不端行为或者不检行为,律师可以为了就指控进行辩护而披露秘密信息,但是披露的信息不得超过所需。”“为了证明或者追讨律师费,律师可以披露秘密信息,但是披露的信息不得超过所需。”“为了就律师准备进行的行为获得法律或者道德建议,律师可以向其他律师披露秘密信息。”“为了查明和解决因律师雇佣关系变更或者律师事务所组成、所有权变更而产生的利益冲突,在合理必需的范围内,律师可以披露秘密信息,但是仅限于披露的信息不会损害事务律师——委托人特免权,或者以其他方式损害委托人。”②(49)② 参见王进喜译:《加拿大律师协会联合会职业行为示范守则》,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第66页以下。《德国律师职业规则》第2条第2、3款规定:“(2)法律要求或允许的例外,不属《联邦律师法》第43a条第2款所指的违背保密义务。(3)律师的下列行为不属对保密义务的违背:a)事先已获同意的行为;b)为该行为系维护正当利益所需,例如为了行使或反对因委托关系产生的请求权或为了本人事务中的防御;c)行为发生在《联邦律师法》第43e条适用范围以外的事务所工作运行范围之内,而且是客观上常见的和在社会生活中被普遍允许的(社会相当性)。”所谓律师的请求权,主要是指委托人欠律师报酬时,如果律师向法院起诉请求支付,那么律师就不受保密义务的约束。其理由是因委托人自招之危险,而导致其隐私维护与律师报酬间的冲突,因其自招行为,故不受优先性保护。所谓律师“防御”,系指委托人向律师请求损害赔偿时,律师为防卫其权利,可说明委托事件的细节。另在律师被委托人举发而成为刑事或职业惩戒之对象时,律师为维护自身权利,也可不受守密义务之约束。①(50)① 参见姜世明:《律师伦理法》,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第186页以下。我国台湾地区《律师伦理规范》第33条但书规定:“但委托人之未来犯罪意图及计划或已完成之犯罪行为之延续可能造成第三人生命或身体健康之危害者,不在此限。”
我国保密规则规定了三项例外: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事实和信息。这三项例外类似国外保密规则例外的第一项内容,即为了防止未来重大犯罪的例外,具有“急迫性”“可预防性”和“后果严重性”两项要件。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犯罪,分别是我国刑法分则第一章、第二章规定的犯罪,从逻辑顺序上可以看出其严重性。除此之外“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是常见多发犯罪,且危害后果严重。在律师保密价值与防止即将发生的严重伤亡后果的价值权衡中,前者作出让步,确有其必要性。这就排除了侵犯财产犯罪和妨害司法犯罪案件信息的披露。我国立法上之所以作此例外规定,主要是对特别严重犯罪进行预防和制止,从而避免或者尽可能降低其对社会的严重危害,从社会价值和利益上讲,要超过对辩护律师保密权利的维护。如果一般危险都要求予以披露的话,则显然忽略了保密规则的社会价值。只要损害法益具有严重性,律师即可免除保密义务,并不要求这种危险具有紧迫性。②(51)② 参见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职业伦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68页。当然,犯罪种类仅限于上述三种严重犯罪,对于其他危害较轻的犯罪,辩护律师仍享有保密的权利。③(52)③ 参见王爱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释义》,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年,第101页。即使律师知道被告人欲在法庭上作伪证或者撒谎,也不能向法庭进行披露。虽然律师对法庭有“真实义务”,但这是一种“消极的真实义务”。辩护人对法庭的真实责任,并不要求其积极向法庭提供“全部真相”。相反的,他如果告诉法庭他知道的全部事情就违反了他对当事人的责任。因而,诚实责任不能解释为强迫辩护人说话,而是要其保持沉默。①(53)① 参见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事诉讼程序》,岳礼玲、温小洁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2页。至少律师不能在辩护中援引明知是虚假的被告人陈述,以此来误导法庭。我国《律师法》第二条第2款规定:“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可见,“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是律师的首要职责。相较于法庭查明真实,维护委托人对律师的信赖关系进而实现律师制度的目的,可能更重要。“一个多世纪以前,对于当事人职责的重要性就开始超过了对法庭及对方律师的职责。”②(54)② 蒙罗·H·弗里德曼、阿贝·史密斯:《律师职业道德的底线》,王卫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7页。
在各种例外情形中,“律师自我保护”均作为保密规则的例外予以规定。遗憾的是,我国的保密规则遗漏了该项例外,体现出国家利益、公共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然而,在实践中律师被拖欠律师费或者遭受刑事控告、民事起诉和职业惩戒的案例不在少数,为了保护律师权益,应当允许律师披露其工作成果,即便这些工作成果涉及委托人秘密,也在所不惜。未来律师保密规则的改革完善,应当将律师“自我保护”情形作为例外予以设置。这不仅有利于调动律师工作的积极性,也可以促进我国律师制度的健康发展。
利益冲突是律师执业中必须关注的问题。对此,我国《律师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律师事务所应当建立健全执业管理、利益冲突审查、收费与财务管理、投诉查处、年度考核、档案管理等制度,对律师在执业活动中遵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的情况进行监督。”律师事务所如何进行审查?需要承办律师披露案件的相关信息。实践中,同一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不得为同一案件的双方提供法律服务,因为可能导致利益冲突。为避免冲突发生,承办律师有必要公开其承办案件的当事人和相对人的姓名、名称和案由。这是利益冲突审查的必然要求。
委托人同意,当然是律师可以对外披露秘密的例外情形。但有时因未能与委托人取得联系并且有迫切需要之时,即使没有委托人的明示同意,但为保护委托人的名誉和信用,律师认为必要时,可以推定委托人同意开示秘密。③(55)③ 参见森际康友:《法曹伦理》,刘志鹏等译,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60页。
在当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的背景下,应特别注意被追诉人虚假认罪认罚的问题。一个现实问题是,当律师得知当事人“替人顶罪”的事实后,能否予以披露?例如,律师从被追诉人口中得知其“替人顶罪”的事实,在律师明知其无辜时能否将其无辜的事实予以披露?对此,笔者认为律师应当予以披露,即使这种披露与被追诉人的意见相左,律师也不能继续保守秘密。既然守密义务设置的初衷是为了实现有效辩护或者代理,实现司法正义。此时要求律师继续守密会损害司法正义的实现。从价值考量出发,律师也不应继续保守秘密。俄罗斯《律师法》第六条第4款第3项规定:“律师无权在案件中采取违背委托人意志的立场,但是律师相信存在委托人虚假地自证有罪的情形除外。”所谓“虚假地自证有罪”,是指被告人承认自己实施犯罪的全部或者部分罪过,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实施犯罪。①(56)① 参见尤·彼·加尔马耶夫:《俄罗斯刑事诉讼律师违法活动面面观》,刘鹏、从凤玲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89页以下。如果保守当事人秘密会导致不公正,或者对无辜的一方造成实质性损害,那么就没有理由要保守秘密。②(57)② 参见戴维·鲁本:《律师与正义——一个伦理学研究》,戴锐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6页。
(六)披露的“度”
尽管各国均有律师保密的例外情形,但是在律师披露秘密信息时均有“度”的要求。例如,美国要求“在合理必要的范围内”予以披露,加拿大要求“披露的信息不得超过所需”。前者是对披露信息“范围”的限制,后者则是对披露信息“量”的限制。对此,我国立法虽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但律师在披露时也不能“广而告之”,仍然存在一个“度”的问题。一是“范围”度。我国刑诉法规定,对“三种例外情形”,律师应当及时告知司法机关。问题是,如果律师没有告知司法机关,而是告诉了潜在的被害人,使其及时躲避从而防止了危害结果的发生,那么律师是否应当遭受职业惩戒。对此,笔者查阅了域外关于律师保密规则,均未发现要求律师应当告知警察或者检察官的规定。首先,从诉讼立场上看,检察官是辩护律师的“天敌”,律师向其“天敌”告知当事人的秘密,可能会极大伤害当事人的感情;其次,律师若“告知司法机关”,自己的当事人可能会“罪加一等”,这将严重破坏当事人对律师的信任关系;最后,保密规则允许律师披露的目的是防止未来危害结果的发生,律师向潜在被害人的提前披露,完全可以达到此目的,也符合保密规则例外设置的初衷。鉴于以上三方面的理由,笔者认为对于律师向潜在被害人披露的,不应受到职业惩戒。同时,在我国保密规则修订时,对于“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应删除“告知司法机关”的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分别承担保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职责,律师及时向其告知,具有便利性。但是上述三种例外情形均要求律师“告知司法机关”,此规定显得过于“国家本位”和绝对化。此外,如果律师将此信息在微信、微博上发布,不符合“范围”度的要求,超过了披露的限度。二是“量”度。虽然在极特殊情形下允许律师对秘密信息的披露,但应以实现披露目的为限。否则,即为“过度披露”,律师可能会受到惩戒。例如,在利益冲突审查中,律师可能会向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或者其他律师披露案件信息,作为辩护律师,只需披露当事人的姓名、名称和案由即可,而无需披露当事人是否认罪认罚、是否取得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谅解以及双方沟通的辩护策略,等等。为了防止利益冲突的情况发生,必要的信息披露应当允许,但是“基本上仅限于委托人的姓名和案件名,多数情况下这些已经足够了”①。(58)① 森际康友:《司法伦理》,于晓琪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7页。
五、律师遵守保密规则的实践把握和制度完善
(一)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泄密情形
长期以来,我们对律师保密问题不够重视,很大程度上与我们的认识有关。传统观点认为律师保密在我国实践中不甚突出,亦无研究的必要。事实上,律师能否守密,事关委托人对律师的信赖关系,事关公众遇到法律纠纷后是否寻求律师帮助,从长远看事关律师制度的发展进步。律师泄密的情形在中外都存在,表现为故意和过失两种形态。律师泄露职业秘密,在实践中是如此之多样,被揭露却是如此之少。依违法行为的对象,也就是依据泄密的性质为标准,可将泄密行为划分为如下三种类型:一是泄露委托人实施犯罪和其他违法行为的信息材料;二是泄露委托人个人和家庭私生活的信息材料;三是泄露委托人基于律师提供法律帮助而告知律师的其他信息材料。例如关于被追诉人辩护立场的信息、有损于委托人名誉的信息。②(59)② 参见尤·彼·加尔马耶夫:《俄罗斯刑事诉讼律师违法活动面面观》,刘鹏、从凤玲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94页。其中,危害之烈、影响之大的当属律师故意向警方泄密。通常律师最严重、最没有道德感的泄露,是将被追诉人实施犯罪的情形报告给侦查人员,告知他们被追诉人个性中的弱点,他的疾病、恐惧和心境,他过去实施过哪些违法和不道德的行为。结果是,侦查人员将该秘密信息用作侦查的策略手法。或者使侦查人员相信,应当从被追诉人那里取得其他“有用的”供述,并提供寻找新的指控证据的方向。①(60)① 参见尤·彼·加尔马耶夫:《俄罗斯刑事诉讼律师违法活动面面观》,刘鹏、从凤玲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95页。《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8条规定:“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的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无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德国基于信赖保护原则,对辩护人适用特别规则,因为刑诉法第148条第1项保证其得与被告不受限制地任为言词上之交往联系。因此如果在对被告施行电话监听时,发现其乃在与辩护人通话时,则应将录音中断,或如已录音时,则需将之消除。如果辩护人同时也被监听,并且从监听结果中证实,该辩护人确有犯使刑罚无效罪之嫌疑时,则该所监听之结果不得作为不利辩护人之用。②(61)② 参见克劳思·罗科信:《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37页。我国刑诉法第39条第4款规定:“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上述规定,一方面是为了保障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交流秘密,另一方面是防止公权力对秘密的窃取,由此导致律师介入的失效。因此,即便是查明事实、控制犯罪,公权机关也不能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既然国际文件和内国法都禁止公权机关掌握、控制律师与当事人之间交流的内容,那么律师主动“投奔”控诉阵营,是对当事人利益的严重“背叛”,的确是“令人惊骇”的事情,是对守密规则最大的破坏。令人难以容忍和置信的是,辩护律师竟然充当警方“线人”,通过向警方提供当事人的“情报”领赏。2019年3月媒体披露澳大利亚一位资深的从事刑事辩护业务的女律师,长期为毒贩、黑帮代理案件,通过搜集自己当事人的犯罪证据,成功帮助警方破获了许多案件。③(62)③ 参见《女律师举报犯罪,为何竟成惊天丑闻?》,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EB82U BR20514C1JT.html,2019年12月23日。这在澳大利亚成了一件大“丑闻”,就是因为律师严重背叛了他(她)的当事人,他(她)不是在帮助自己的当事人,而是暗中帮助警察做事。不仅违背了律师保密规则,也有违律师的职责,令人产生“良心上的震撼”,这在任何一个宣称是“法治”的国家都不能容忍。难怪此事被披露出来后,澳大利亚将其视为举国“丑闻”。我国虽然没有发现上述律师泄密的极端案例,但是在前几年影响巨大、引发全社会关注的李某某等人强奸一案中,该案的辩护律师、代理律师共7人因泄露当事人隐私、不当披露案情而受到北京市律师协会的纪律惩戒。这说明加强律师职业伦理建设、增强律师保密意识,已经成为我国律师制度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一些律师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将自己办理的案件情况,甚至将作为工作成果集中体现的辩护词、代理词,通过发送微信、微博的形式公开出去,这不仅可能煽动社会舆情,形成“舆论审判”,而且有涉嫌泄露案件秘密之嫌。律师对此应当慎重。此外,近年来随着一股律师“出书热”潮流的涌现,律师在办结案件后以撰写辩护纪实、回忆录和自传形式出书,虽然可能隐去当事人的真实姓名、使用化名等进行撰写,但仍可能使读者“特定化”,从而泄露当事人的秘密。此外,随着微信等社交工具的流行,很多律师都有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律师通常将其办理案件情况甚至细节在此披露出来,这很有可能泄露当事人不愿意公开的秘密信息,这是当前律师庭外言论中必须注意的问题。由于我国比较高的羁押率,被追诉人大多被羁押,通常是由被追诉人的亲属代为委托律师。由于律师费是由亲属支付,律师将当事人秘密信息泄露给亲属的案例不在少数。辩护律师查阅、复制的证据材料中可能记载了当事人不愿为外人(包括亲属)所知悉的个人隐私内容,例如,房产、个人存款情况,甚至包括当事人背着家属在外面包养情妇、抚养私生子的情况,等等。如果辩护律师不经当事人同意擅自将涉及当事人隐私的证据材料泄露给当事人亲属将可能损害当事人的财产利益和名誉,甚至可能导致其婚姻家庭关系的破裂,也违反了律师对当事人的保密义务。①(63)① 参见韩旭:《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及其家属证据知悉权研究》,《现代法学》2009年第5期。
实践中发生的律师泄密情形大部分都是过失泄露。例如,与自己的配偶、子女和朋友谈及所办理案件的细节;在律师助理协助律师处理案件中,因监督管理不严,致使案件信息被泄露;案件办结以后,在归档过程中,案件信息外泄;律师在接受新闻媒体采访时披露有关案情;律师与其他律师同行谈论案情、寻求帮助时泄露案件信息;律师电脑加密不严,导致“黑客”侵入而泄密;等等。当前,很多律师事务所都实行重大疑难案件集体讨论制度,这种办案模式虽可以集思广益,提高办案质量,但也存在着泄露委托人隐私和案件信息的潜在风险。②(64)② 参见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职业伦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61页。上述泄密情形都是律师在不经意间进行,律师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稍加注意即可避免。例如,可以与律师助理、实习人员签订保密协议,隐去当事人、证人、被害人的姓名、住址等重要信息,会场上发放的案件材料不得带出会场和拍照、录像等,重要的案件材料尽量不通过发送电子邮件方式传送,等等。
(二)保守秘密规则对律师和公权机关提出的要求
既然律师保守秘密是一项基本的法律要求,那么律师应强化责任意识和保密意识,将保守秘密作为一项职业规则予以坚守。一是委托人在与律师签署委托书时,委托书中应当载有保密条款和例外情形,或者由律师签署专门的保密协议,将其作为委托书的附件。如此方能增强律师的守密责任。二是无论是律师接受采访,还是与家人、朋友谈及所辩护或者代理案件时,应当谨言慎行,避免言语不当泄露案件信息。律师应当避免关于委托人事务的轻率谈话和其他交流,律师直接的轻率谈话,如果被能够辨别出所讨论事项的第三方听到,也可能会给委托人带来损害。此外,聆听者对律师和法律职业的尊重也可能会降低。①(65)①②③参见王进喜译:《加拿大律师协会联合会职业行为示范守则》,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第59,63,119页。三是律师为获得合理建议,在与其他律师交谈时可能泄露与当事人有关的信息,对此其他律师也负有保密职责。四是律师在出版回忆录、自传或者辩护实录时,涉及案件信息的,应当事前征得当事人同意。“如果律师在从事文学工作,例如撰写回忆录或者自传,律师在披露秘密信息之前,需要获得委托人或者前委托人的同意。”②五是律师在聘用律师助理协助工作时,应当加强监督指导,提示其应注意保守秘密。一旦律师助理泄密,律师应当承担责任。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53条a之规定,律师辅助人等同于律师。加拿大律师《职业行为示范守则》3.4-23规定:律师或者律师事务所必须恪尽职守,以确保律师事务所的每个成员和雇员,以及律师或者律师事务所聘请其提供服务的每个其他人员不得披露关于律师事务所委托人的秘密信息或者该人曾工作过的任何其他律师事务所的委托人的秘密信息。③六是在律师办结案件归档时,应当加强保密工作,防止在该环节发生泄密事件。
当前应将法律援助律师和值班律师作为守密的最重要主体。与委托律师相比,法律援助辩护律师和值班律师更容易发生泄密情形,因为他们带有一定的“官方”色彩,更容易配合司法机关的工作,也较少取得被追诉人的信任。当前值班律师在犯罪嫌疑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时在场见证的做法,已经被众多学者质疑为“为检察机关背书”。律师一定不能基于与办案机关搞好关系,不惜以牺牲当事人的利益和秘密信息为代价换取信任。虽然我国立法上并未要求值班律师守密,一旦出现值班律师泄密情况,也无法追究其责任,这无疑会使其懈怠守密意识。但是,从防止利益冲突的角度考虑,假如值班律师在今后接受该案被害人或者共同被追诉人委托,就不应将其在向被追诉人提供法律帮助时获取的信息告知被害人或者共同被追诉人。这关涉值班律师制度能否健康长远发展的问题,不能不予重视。从律师业存在时起,就禁止做“背叛”客户的事情。根据俄罗斯《律师法》的规定,律师采取违背委托人意见的立场,是一种辩护违法行为。①(66)① 参见尤·彼·加尔马耶夫:《俄罗斯刑事诉讼律师违法活动面面观》,刘鹏、从凤玲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89页以下。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在深入实施,需要注意的是值班律师或者辩护人在与被追诉人进行“辩护协商”过程中了解到的认罚“底线”,在控辩协商过程中,如果未取得犯罪嫌疑人的同意,不得将此泄露给检察官。即便是值班律师或者辩护人为了达至合意的需要,也不能罔顾被追诉人意志而独立行事。
我国律师与当事人的信息交流主要是通过会见程序获得,在会见时律师通常会制作“会见笔录”。“会见笔录”记载的内容通常是律师与当事人交流的内容,对此未经当事人同意,律师不得作为证据向公安司法机关提交。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律师办案更多以电子化、数字化形式呈现,这为“黑客”攻击电脑系统,并因此泄密带来极大风险。为此,律师应采取严密的防护措施,避免电脑信息系统被“黑客”入侵和窃取秘密信息。《德国律师职业规则》第2条第4款规定:“保密义务要求律师采取必要的、与风险相当的和对律师职业为可期待的组织和技术措施以保护委托人的秘密。技术措施为已足够,如该措施在适用数据保护法时符合数据保护法的标准。其他的技术措施也应符合技术现状。”
律师保密规则,不仅仅是律师的一项义务,也是公权机关的一项义务,该项义务是对律师保密权利而言。这就要求公权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进行自我克制,以避免侵犯律师保密规则。一是对律师会见被羁押人员的会见笔录不得检查,律师会见“不被监听”的法律规定应当落到实处。江西南昌“熊某案”中办案警官偷听律师会见是严重侵犯交流秘密的权力滥用行为。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8条规定:“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的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无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二是被追诉人与律师之间的通信不被扣押、检查,除非涉嫌密谋犯罪。因为通信内容属于被追诉人的秘密事项,律师有权予以保密,公权机关有义务尊重律师的保密权利。
(三)促进保密规则实施的保障措施
目前对律师违反保密规则的处罚,只有律师法规定的“残缺不全”的“行政责任”。①(67)① 我国《律师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律师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给予停止执业三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的处罚:(四)泄露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从律师法的规定内容看,主要保护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而对“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是否能够解释为“个人隐私”,可能见仁见智。笔者认为,无论内涵还是外延,“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均比“个人隐私”要大。以“个人隐私”一词并不足以保护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即使律师泄露了上述信息,也难以追究泄密的行政责任。因为,该律师可能会以“情况和信息”并非“隐私”为由进行抗辩,从而使行政责任的追究变得困难。为此,在我国律师法修改时,应当将泄露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纳入行政处罚的范围,以保障保密规则的实施。但是,仅有律师法上的行政处罚还不够,还需要刑事诉讼法、刑法作出相应的修改,确立相关的制度和刑罚措施,才能有力保障律师保密规则的落实。一是在刑事诉讼法上应当确立律师——委托人拒绝作证权。域外刑诉法普遍确立了律师免证特权,不仅对于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秘密交流内容,包括会见和通信信息,律师有权拒绝披露,而且对于委托人基于信任关系委托律师代为保管的物品,律师有拒绝扣押的权利。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182条规定:“证人为医师、药师、助产士、宗教师、律师、辩护人、公证人、会计师或其业务上佐理人或曾任此等职务之人,就其因业务所知悉有关他人秘密之事项受讯问者,除经本人允许者外,得拒绝证言。”《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05条规定:“医师、牙科医师、助产士、护士、律师、代办人、公证人、宗教职业者或者曾经担任以上职务的人,对由于受业务上的委托而保管或者持有的有关他人秘密的物品,可以拒绝扣押。”②(68)② 宋英辉译:《日本刑事诉讼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6页以下。《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53条规定了律师基于职业原因的拒绝证言权。该法第97条规定了对拒绝证言权人的扣押禁止。③(69)③ 参见宗玉琨译注:《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第27页、第51页。在法国,如果律师与其顾客之间交换的信件涉及辩护的内容,则预审法官不得扣押这些信件。①(70)① 参见卡斯东·斯特法尼等:《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罗结珍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77页。该权利的理念基础在于,律师需要获得其客户的完全信任,而如果客户担心他们在未来的刑事诉讼程序中将被迫作出对其不利的证言,这种信任程度将会降低。而且,律师应当免受在法庭上讲述真相之义务与保守客户秘密之义务二者之间冲突的影响。②(71)② 参见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事诉讼程序》,岳礼玲、温小洁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8页。律师免证特权是保守当事人秘密的基本形式,也是最主要形式,目的是为了防止公权机关的披露要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2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律师,作为知道当事人情况和案件信息的人,也不例外。刑诉法和律师法上关于律师保密的规定并不能免除其“作证的义务”。因此,刑诉法需要就律师免证权问题作出特别规定。如此,方能保障律师保密义务落到实处,律师保密规则才能获得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二是刑法修改时建议对严重泄露当事人秘密的行为“入罪”。刑法增加“律师泄露案件秘密罪”或者对现在的“泄露案件信息罪”进行修改,将保护对象延展至所有案件中的秘密信息,从而以严厉的刑事责任促进律师履行守密规则。我国刑法修正案(九)规定了“泄露案件信息罪”。但该罪名保护的是“依法不公开审理案件中不应当公开的信息”,且系“结果犯”,要求造成信息公开传播或者其他严重后果。如果不是“依法不公开审理案件”,即使律师泄露了案件信息,也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放眼域外,日本《刑法》第134条第1项即规定了“泄露秘密罪”,该项规定:“律师或者曾经从事这些职业的人员,没有正当理由向他人泄露因业务获取的他人秘密,处六个月以下的拘役或者十万日元以下的罚金。”律师公开案件秘密也为刑法所禁止。③(72)③ 参见参见森际康友:《司法伦理》,于晓琪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3页。在德国,辩护人绝对不能泄露从当事人处获知的秘密甚至表面看起来无伤大雅的信息,否则他就不能有效地工作。违反这一义务即构成刑事犯罪(刑法典第203条)。④(73)④ 参见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事诉讼程序》,岳礼玲、温小洁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2页。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316条规定:“医师、药师、药商、助产士、心理师、宗教师、律师、辩护人、公证人、会计师或其他业务上佐理人,或曾任此等职务之人,无故泄露因业务知悉或持有他人秘密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万元以下罚金。”为了加强律师对保密规则的遵守,宜将我国公开审理案件中的秘密信息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律师泄密既可能有故意构成,也可能由于疏忽大意的过失所致。因此,在主观罪过方面,不应仅限于故意,还应包括过失。在行为形态方面,既可能是作为,也可能是不作为。
律师保密规则若要得到真正的遵守,需要改变传统的以查明真相为目的的“实体真实观”,代之以权利保障的“程序正义观”,否则律师有可能沦为公权机关查明事实真相的工具。
六、结语
律师保密义务具有相对性。对委托人而言,律师保密是义务,相对于国家公权力和第三人而言,律师保密具有权利属性。对委托人义务的履行,既需要律师严格遵守保密规则,也需要公权力的克制。律师保守秘密既是维护委托人对律师的信赖关系,也是保障委托人人格尊严和律师独立辩护的需要,特别是委托人对律师的信任,是律师有效辩护和代理的前提,也是委托人采纳律师建议的保证,更是法治国家实现的前提。因此,律师保密规则是律师职业规则中的核心规则。我国立法关于律师保密规则的规定,无论是保密主体、标的还是保密期限、例外设置均有可检讨之处。值班律师和代理律师也应当纳入保密主体之中;诸如被调查取证人员等第三人信息也应予以保密,而不是仅限于委托人的信息;保密范围中,除言词交流信息外,文件、资料等物品亦属于保密的范围;保密期限既包括在律师辩护、代理职责的过程中,也包括辩护、代理事务终结和签订委托协议之前的咨询阶段,在保密信息成为“公共信息”之前,律师均负有保密义务;例外设置中应当将“律师自我保护”作为对当事人义务的例外情形,允许律师对相关信息披露;在披露“度”的把握上,我国立法并未作出规定,应当从“范围”度和“量”度两个方面进行限制,防止超越披露目的的过度披露。我国保密例外规则中关于“告知司法机关”的规定,可以修改为既“可以告知司法机关”,也可以“告知潜在的被害人”。实践中律师泄密事件以过失形态为主,也有少量的故意泄密问题。例如,轰动一时的李某某等人强奸案中的辩护律师和代理律师违规披露当事人的隐私信息和其他秘密信息。如今律师出书成为一种时尚,律师在出版之前应当征得案件当事人的同意,否则有可能因泄露案件秘密而遭到惩戒。当前,守密的重点主体是值班律师和法律援助辩护律师,因为他们与当事人之间更缺乏信任关系,“官方”色彩较浓,更容易配合公安司法机关的工作。否则,法律帮助和法律援助质量不可能得到提高。为了促进律师遵守保密规则,应当通过修改律师法、刑事诉讼法和刑法,保障守密规则的落实。律师因泄露委托人和其他人的信息,是否应当进行职业惩戒,律师法语焉不详,可能导致追究行政责任的困难,对此,需要律师法修改时予以明确。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当增设律师免证特权规则,而不是当前“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借鉴德国、日本的立法例,在刑法中增设律师泄露案件信息罪,将刑法修正案(九)中泄露“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信息”扩大至所有案件秘密信息。以刑罚的严厉性保障律师保密规则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