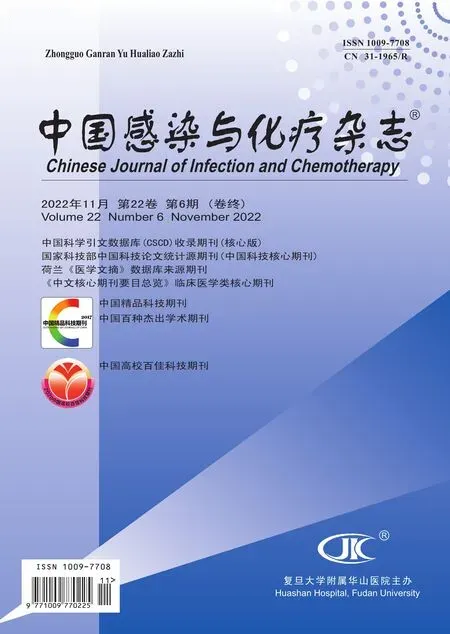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感染治疗进展
2022-12-08阿力米热艾买提伊思达徐晓刚
阿力米热·艾买提, 丁 丽, 伊思达, 徐晓刚
多重耐药细菌感染常导致患者住院时间延长,医疗费用增加,病死率上升,已成为全球重大公共卫生问题。CHINET中国细菌耐药监测网2021年监测数据显示,临床分离革兰阴性菌中肺炎克雷伯菌占比为14.12%,仅次于大肠埃希菌(18.96%)。近二十年来,革兰阴性菌对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耐药率持续上升,其中肺炎克雷伯菌对亚胺培南、美罗培南的耐药率从2005年的3.0%、2.9%上升至2021年的23.1%、24.4%[1]。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CRKP)可导致身体任何部位的感染,其中导管相关感染、血流感染、呼吸机相关肺炎和腹腔内脓肿最常见[2]。多数CRKP对常用抗菌药物耐药,使得治疗药物选择受限。研究显示CRKP感染组死亡率往往是碳青霉烯类敏感肺炎克雷伯菌(CSKP)感染组的2~3倍。在中国,CRKP感染患者平均年龄为60岁,重症监护室相关感染占54%,社区相关感染占35%。CRKP相关感染未调整30 d死亡率为12%,其中血流感染30 d未调整死亡率高达24%[3]。
虽部分CRKP(如产OXA-48酶菌株)可以被第三代或第四代头孢菌素单药治疗,但大多数对头孢菌素、氨曲南、喹诺酮类、庆大霉素、妥布霉素和甲氧苄啶-磺胺甲唑耐药[4],替加环素、多黏菌素、磷霉素成为了治疗首选[5]。十年来,头孢他啶-阿维巴坦(ceftazidime-avibatam)、头孢地尔(cefiderocol)、美罗培恩-韦博巴坦(meropenemvaborbactam)和亚胺培南-雷利巴坦(imipenemrelebactam),及新型氨基糖苷类药物普拉佐米星(plazomicin)等具有更好抗菌疗效、较低不良反应的抗生素相继问世,并批准用于临床。产碳青霉烯酶是CRKP主要耐药机制,且抗菌药物对产不同碳青霉烯酶菌株体外抗菌活性不同。因此,碳青霉烯酶的准确快速检测并分型有助于抗感染精准用药。故本文以CRKP碳青霉烯酶的实验室检测、抗菌药物选择及新药治疗为主题作一综述。
1 碳青霉烯酶实验室检测
目前将CRKP定义为:至少对一种碳青霉烯类耐药或产生碳青霉烯酶的肺炎克雷伯菌。产碳青霉烯酶是肺炎克雷伯菌对碳青霉烯类耐药的主要机制。按照Ambler分子分类方法,肺炎克雷伯菌中常见的碳青霉烯酶可以分为A、B和D三类。A类为丝氨酸碳青霉烯酶,以blaKPC(blaKPC-2、blaKPC-3)为主;B类为金属β内酰胺酶,以blaNDM(blaNDM-1)、blaIMP(blaIMP-1)、blaVIM(blaVIM-1)为主;D类OXA-48类丝氨酸碳青霉烯酶,以blaOXA-181和blaOXA-232为主;部分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blaCTX-M、blaSHV、blaAmpC)合并膜孔蛋白(OmpK35和OmpK36)缺失或者外排泵高表达亦可导致碳青霉烯类耐药[6]。Wang等[3]的国际多中心、前瞻性、多重耐药菌病例队列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94%的CRKP产blaKPC-2,而在美国和南美除产blaKPC-2外尚有较高比例的产blaKPC-3菌株;在中国同时合并产ESBL的CRKP比例明显高于美国和南美,主要以产blaCTX-M(81%)、blaSHV(45%)的菌株为主。
由于多种抗菌药物对产不同碳青霉烯酶的肺炎克雷伯菌体外抗菌活性不同,碳青霉烯酶的准确快速检测并分型对临床抗感染精准用药具有重要价值[7]。目前实验室检测碳青霉烯酶方法分为表型检测、免疫层析技术和基因型检测。表型检测利用3-氨基苯硼酸和EDTA可分别抑制A类丝氨酸碳青霉烯酶(blaKPC-2、blaKPC-3等)和B类金属β内酰胺酶(blaNDM、blaIMP、blaVIM等)活性为原理检测上述碳青霉烯酶;酶免疫层析技术和基因型检测技术,分别利用抗原抗体免疫层析技术和荧光定量PCR技术检测KPC、OXA-48、VIM、IMP和NDM等碳青霉烯酶型和基因型[8],为抗感染精准药物选择提供依据。
3 CRKP感染治疗药物选择
CHINET监测数据显示,CRKP对美罗培南、亚胺培南、头孢噻肟、头孢他啶、头孢吡肟耐药率为96.3%~99.6%;对阿米卡星、甲氧苄啶-磺胺甲唑、氯霉素、米诺环素、磷霉素耐药率为49.6%~64.6%;对头孢他啶-阿维巴坦、替加环素、多黏菌素B和黏菌素耐药率分别为11.1%、7.3%、5.9%和5.3%[1]。虽然阿米卡星、多黏菌素、替加环素和磷霉素等传统抗菌药物对部分CRKP感染仍然有效,但由于不良反应多,组织渗透差或需要联合用药等原因,临床使用受到限制[9]。目前CRKP感染治疗分为单药治疗和联合治疗。单药治疗可根据感染部位、抗菌药物浓度、抗菌药物特点及菌株药敏数据选择多黏菌素、替加环素、磷霉素、半合成四环素类、氨基糖苷类、碳青霉烯类及新型β内酰胺类及其酶抑制剂复方制剂等。但对多部位或严重感染,如血流感染或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推荐使用多黏菌素、替加环素或碳青霉烯类为基础的联合治疗方案[10]。CRKP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程度不一,当碳青霉烯类抗生素对CRKP的MIC≤8 mg/L时,含碳青霉烯类的两药或三药联合方案(如碳青霉烯类联合氨基糖苷类、替加环素、多黏菌素或磷霉素)采用大剂量、长时间输注使PK/PD达到可接受的药物暴露水平,也可以达到药效学目标[11]。
CRKP感染联合用药方案可能使重症感染患者有更多获益。有专家共识指出,多种体外具有协同或相加作用的抗菌药物联合,可快速控制感染和减少耐药的发生,可适当降低多黏菌素等毒性较高药物的剂量,以及减少其不良反应[10]。如一项产碳青霉烯酶肠杆菌科细菌 (carbapenemase producingEnterobacteriaceae, CPE)血流感染患者死亡率回顾性队列研究(INCREMENT),其纳入2004—2013年10个国家26家三级医院CPE导致血流感染437例,其中375例(86%)是肺炎克雷伯菌感染,产KPC型碳青霉烯酶最常见(329例),统计单药治疗组(黏菌素、美罗培南或亚胺培南、替加环素、氨基糖苷类、磷霉素等)和联合治疗组(替加环素联合、黏菌素联合、氨基糖苷类联合、碳青霉烯类联合、链霉素联合等)30 d死亡率,结果显示,与单药治疗组相比,联合治疗方案仅在INCREMENTAL-CPE死亡评分高分组(8~15分)减少了30 d死亡率,在低分组(0~7分)30 d死亡率无明显下降,故推荐CPE重症感染时使用联合用药方案[12]。然而,目前评估联合用药对CRKP感染有效性研究多为体外协同试验和回顾性临床研究,需要更多多中心大样本前瞻随机对照研究(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RCT)结果支持此推论。
使用广谱β内酰胺类与β内酰胺酶抑制剂复方制剂是治疗产广谱β内酰胺酶菌株感染的有效策略。老一代抑制剂,如他唑巴坦、舒巴坦和克拉维酸等,因无法抑制碳青霉烯酶对产KPC型碳青霉烯酶菌株,没有抗菌活性[13]。而新一代非β内酰胺环的β内酰胺酶抑制剂,如阿维巴坦、韦博巴坦和雷利巴坦,对产KPC型碳青霉烯酶菌株具有抗菌活性。KPC和OXA-48类丝氨酸碳青霉烯酶可被阿维巴坦抑制,因此抗菌新药头孢他啶-阿维巴坦对产KPC和OXA-48类丝氨酸碳青霉烯酶肺炎克雷伯菌具有抗菌活性,但对产金属β内酰胺酶菌株无抗菌活性[14]。目前处于临床研究阶段的亚胺培南-雷利巴坦和美罗培南-韦博巴坦[15]对产KPC型CPE具有抗菌活性,但对产金属β内酰胺酶和D类OXA-48类碳青霉烯酶菌株无抗菌活性。因此,实验室可根据碳青霉烯酶与抗菌药物间相互作用,如金属β内酰胺酶不能水解氨曲南,KPC型碳青霉烯酶的活性可被阿维巴坦、韦博巴坦或雷利巴坦抑制,青霉素酶和广谱酶及ESBL可被克拉维酸抑制,开展联合药敏试验为精准抗感染治疗方案制定提供依据(表1)[16-17]。

表1 常见肺炎克雷伯菌耐药相关碳青霉烯酶及治疗药物推荐[6, 8]
新型β内酰胺类及其酶抑制剂复方制剂的疗效评价也是抗感染临床研究热点。一项比较头孢他啶-阿维巴坦和美罗培南-韦博巴坦治疗效果与安全性的多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指出,其研究对象为2015年2月—2018年10月接受头孢他啶-阿维巴坦或美罗培南-韦博巴坦治疗≥72 h的碳青霉烯类耐药肠杆菌科细菌(carbapenem-resistantEnterobacteriaceae,CRE)感染的成人患者,共纳入131例(头孢他啶-阿维巴坦组 105例;美罗培南-韦博巴坦组 26例)。其中,40%的患者有菌血症,最常见的非血流感染为呼吸道感染,且两组CRE主要致病菌均为肺炎克雷伯菌。两组间临床治愈率无显著差异(62%对69%,P=0.49),而头孢他啶-阿维巴坦组比美罗培南-韦博巴坦组患者接受联合治疗的频率更高(61%对 15%,P<0.01)。30 d和90 d的死亡率以及住院时间和ICU住院时间在两组之间无差异,但在感染后90 d内,14.3% 的头孢他啶-阿维巴坦患者和11.5% 的美罗培南-韦博巴坦组患者CRE感染复发。头孢他啶-阿维巴坦组15例患者中20%(3/15)在90 d内分离菌出现耐药性,但美罗培南-韦博巴坦组分离菌未观察到耐药性的出现。此研究支持把美罗培南-韦博巴坦纳入CRE感染治疗的首选药物[18]。此外,近期也有专家共识指出,对肾功能正常患者美罗培南-韦博巴坦以每8小时1次 2 g-2 g(美罗培南-韦博巴坦)静脉滴注3 h为推荐剂量(低肌酐清除率需适应调整)可应用于急性肾盂肾炎在内的复杂性尿路感染(cUTI)、复杂腹腔内感染和医院获得性肺炎(包括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治疗[19]。
亚胺培南-雷利巴坦是新型碳青霉烯类与β内酰胺酶抑制剂复方制剂。其所含雷利巴坦是第二代β内酰胺酶抑制剂,属于二氮杂环辛烷类衍生物,虽具有与阿维巴坦相似的作用机制,但需要更多的分子去中和β内酰胺酶。肠杆菌目中,除了摩根菌科成员摩根菌属、变形菌属和普罗维登西亚菌属外,对亚胺培南-雷利巴坦也具有高的敏感率[9]。亚胺培南-雷利巴坦对产KPC菌株抗菌作用强,能够克服外排泵上调介导的耐药机制,但对产金属β内酰胺酶和OXA-48型丝氨酸碳青霉烯酶菌株的抗菌活性不强[20]。Lombardo等[21]2017—2021年收集13株头孢他啶-阿维巴坦和/或美罗培南-韦博巴坦敏感性降低产KPC肺炎克雷伯菌(KPC-KP)临床分离株检测体外药敏活性,有5株(38.5%)对头孢他啶-阿维巴坦耐药,3株(23.3%)对美罗培南-韦博巴坦耐药,但对亚胺培南-雷利巴坦具有较好的敏感率(84.6%,11/13)。所有耐头孢他啶-阿维巴坦(5/5)或耐美罗培南-韦博巴坦(3/3)的KPC-KP均对亚胺培南-雷利巴坦敏感,MIC50分别为0.25 mg/L(IQR为0.125~1 mg/L)和1 mg/L(IQR为0.5~2 mg/L)[21]。此研究虽样本有限,但结果显示亚胺培南-雷利巴坦对耐头孢他啶-阿维巴坦或美罗培南-韦博巴坦菌株有潜在的体外抗菌活性,需进一步大规模研究去探索亚胺培南-雷利巴坦治疗KPC-KP的临床疗效。
氨曲南-阿维巴坦是单环类β内酰胺类药物与β内酰胺酶抑制剂复方制剂,其中氨曲南对金属β内酰胺酶稳定,但可被丝氨酸β内酰胺酶如广谱β内酰胺酶、AmpC和KPC水解,而阿维巴坦可抑制A、C和一些D类β内酰胺酶。因此,氨曲南与阿维巴坦联合后对产A类、B类以及C类β内酰胺酶的肠杆菌科细菌均显示一定的抗菌活性[22]。目前,氨曲南-阿维巴坦的临床安全性和有效性已完成验证[23],也有Ⅲ期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24],但此复方制剂目前还没有得到上市批准。
新型抗菌药物头孢地尔有望成为CPE感染一线治疗药物。头孢地尔是一种含铁载体的头孢菌素,与头孢他啶或头孢吡肟相比,它对β内酰胺酶稳定性好,并可与游离铁结合,增加其在细菌周质浓度[25]。它对产A、B、C及D类β内酰胺酶菌株均有活性,对产KPC型碳青霉烯酶肠杆菌体外抗菌活性非劣效于头孢他啶-阿维巴坦[26]。2019年被FDA批准用于治疗cUTI,2020年被推荐为革兰阴性菌所致医院获得性肺炎(HABP)与机械通气相关细菌性肺炎(VABP)的治疗药物[27]。在一项比较头孢地尔与已有最佳方案治疗碳青霉烯类耐药革兰阴性菌引起的严重感染有效性和安全性评价(随机、开放、多中心、Ⅲ期)临床试验中,共纳入碳青霉烯类耐药的革兰阴性菌感染患者152例,2∶1比例分配至头孢地尔组(101例)和最佳方案组(51例)。其中最常见的碳青霉烯类耐药菌(carbapenem-resistant organisms,CRO)为鲍曼不动杆菌54株(46%)、肺炎克雷伯菌39株(33%)和铜绿假单胞菌22株(19%)。最佳治疗方案由研究者在随机化前预先指定,最多由三种药物组成,对于肺炎或血流感染或败血症患者,头孢地尔治疗可与一种辅助抗生素(不包括多黏菌素、头孢菌素和碳青霉烯类)联合使用。其中,医院获得性肺炎患者中头孢地尔组获得50%(20/40)的临床治愈率,最佳方案组获得53%(10/19)的临床治愈率。对于血流感染或脓毒症患者,头孢地尔组43%(10/23)的患者,最佳方案组43%(6/14)的患者获得临床治愈。对于cUTI的患者,头孢地尔组53%(9/17)的患者,最佳方案组20%(1/5)的患者实现了微生物清除。表明在这一耐碳青霉烯类革兰阴性菌感染的患者群体中,头孢地尔的临床和微生物学疗效与最佳方案相似[28]。此研究结果支持头孢地尔成为新的一种CRO感染治疗选择。然而,小样本量和异质性患者人群限制了分层随机化统计,增加了基线因素不平衡的可能性,需更大样本量的临床研究去证实头孢地尔在CRO感染治疗中的地位。
普拉佐米星(plazomicin)是一种半合成的氨基糖苷类抗菌药物,来自庆大霉素脱氢类似物(sisomicin),与其他氨基糖苷类类似,但对氨基糖苷类修饰酶(AME)稳定[29]。希腊一项全国性研究显示,普拉佐米星对产KPC、NDM和OXA-48型肺炎克雷伯菌敏感率分别为84.5%、100%和91.7%,相较于临床常用庆大霉素、阿米卡星、妥布霉素等氨基糖苷类显示了更强的体外抑制活性(不论是否产生AME)[30]。一项对抗耐药肠杆菌科细菌多中心、随机、开放临床试验中(CARE,ClinicalTrials.gov number, NCT01970371),对严重CRE血流感染或医院获得性肺炎(包含呼吸机相关性细菌性肺炎)患者进行了普拉佐米星与黏菌素疗效比较,主要终点是28 d全因死亡率和重大疾病相关并发症。37例CRE感染患者接受普拉佐米星或黏菌素(与美罗培南或替加环素联合)治疗7~14 d。其中,普拉佐米星组24%(4/17)的患者发生主要终点,黏菌素组50%(10/20)的患者发生了主要终点。普拉佐米星组的严重不良事件发生率低于黏菌素组[50%(9/18)对81%(17/21)]。此外,普拉佐米星组血清肌酐升高(≥0.5 mg/dL)比例明显低于黏菌素组[16.7%(2/12)对50%(8/16) ][31]。然而,目前尚缺乏大规模临床前瞻随机对照研究去评估普拉佐米星在CRE感染治疗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3 总结
具有高耐药、高死亡率的CRKP全球传播,以及有限的治疗选择,使CRKP感染成为了重大卫生保健问题。近几十年来,多种抗CRKP感染单药或联合用药方案在临床中不断实践,同时也有很多新型抗菌药物被开发并批准用于临床。依据分离菌株药物敏感性、碳青霉烯酶分型、感染部位和药物PK/PD特征及疾病严重程度与合并症选择单药或联合用药成为了CRKP感染个体化精准治疗的关键。虽大部分观察性及分析性临床研究结论支持CRKP感染联合治疗方案,部分学者认为单一用药也可取得较好的治疗效果,联合用药加速了耐药菌株的进化与传播[7]。不同药物及不同联合治疗方案在临床疗效、抗菌谱和不良反应等方面均有差异。现有可供选择的抗菌药物相关研究多为体外协同试验和回顾性临床研究,不同药物及不同联合治疗方案在临床疗效、抗菌谱和不良反应等方面均显示出明显差异[32],尚缺乏大规模临床前瞻随机对照研究结果去评估其安全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