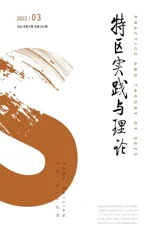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生成的天然土壤
2022-12-07殷文贵
殷文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更是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和实践深入发展的鲜明旗帜。在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的时代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离不开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更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和滋养。甚至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得以产生的最古老、最持久、最有力的历史渊源和价值支撑。这是因为,“在历史上的任何时刻,世界精神都处于某个特定的、具有这一精神、能对人类进步作出最大贡献的民族国家或文化中”。[1]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蕴含着浩若烟海、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血脉和基因,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命脉。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培育和塑造了诸多宝贵的精神品格和崇高的价值追求,比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博大胸襟,协和万邦、万国咸宁的和合追求,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智慧,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价值导向,利己达人、扶危济困的优良传统,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精神气质,义利并举、以义为先的道德品质等。其中,对中国处理与世界的关系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智慧,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博大胸襟,协和万邦、万国咸宁的和合追求。这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力量源泉,亦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然土壤。
一、哲学立场: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智慧
从哲学立场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智慧。“道法自然”出自老子的《道德经》(又称《老子》):“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这句话的大意是,在茫茫宇宙之中有四“大”,分别是天、地、人、道,其中人是以地的法则运行,地是以天的法则运行,天是以道的法则运行,道是以自然为法则运行。不难发现,这里老子以顶真的修辞手法把天、地、人最终都归结为一种“道”,而“道”的落实又需要以“自然”为本源和遵循。“道”其实就是道理、规律、道路、道德,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就是世间万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和最终归宿。“自然”则包括两层涵义:一方面,“自然”即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大自然”“有机界”“自然界”及其发展变化、根本规律;另一方面,“自然”即“自己的样子”,也就是“自然而然”“顺其自然”,意味着一种不为人为或者外力干涉的状态,象征着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行事风格。这就启示我们,所谓“道法自然”,就是要求人们在改造自然过程中,要懂得敬畏自然、尊重自然,向大自然学习,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做大自然的朋友而不是敌人,这即是真正的“天道”;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要善于把握学习和应用事物本身包含的发展条件和规律,真正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如此方能事半功倍、得偿所愿,这即是真正的“人道”。
与“道法自然”的哲学智慧相比,“天人合一”的哲学智慧并非道家学派的专属,崇尚“天人合一”、追求天与人的和谐统一始终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基调,儒、道、释等诸学派都对其有所提及。早在西周时期,中国哲学之源《周易》中的许多阐述就生动诠释了“天人合一”哲学理念。比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3]“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4]这是古人基于对天地运行稳健、气势厚实和顺的特点的观察而对君子提出的要求,即君子应该像天地一样拥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品格和胸怀。这是“人”向“天”学习之表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5]这里古人一方面把男人和女人视为天地万物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把相关的人及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限定在与生俱来的各种自然法则、社会秩序中。这是“人”顺应“天”之表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6]这里运用比拟的手法把“大人”的道德、圣明、施政、占卜等“人”所具有的属性与天地、日月、四时、鬼神等“天”所具有的属性进行形象联系和比较。这是“天”与“人”融合之表现。除此之外,《中庸》还提出:“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7]这其实是从个人品性的养成对天地万物演化发展的影响来凸显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庄子在《齐物论》中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思想,喻指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呼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提出“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理念,以更好地服务于其“独尊儒术”的政治理念。张载在《正蒙·乾称》提出“儒者则因明至诚,因诚至明,故天人合一”的命题,这标志着“天人合一”概念的正式诞生。在此之后,以程颢、程颐和朱熹为代表的宋儒程朱学派,明代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明末清初的王夫之等,都传承“天人合一”思想,并提出了有别于前人的“天人合一”理念。综合各学派有关“天人合一”的相关言论可以发现,尽管各时代、各学派对“天人合一”理解并未达成统一,但也存在一种主流观点:“‘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我们人类,天人关系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8]
总之,不论是“道法自然”思想还是“天人合一”理念,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智慧,并且主要是一种朴素的生态哲学智慧。它分析和总结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揭示了人与自然的本质关系,强调人与自然与生俱来就是统一的有机整体,并非相互孤立、相互排斥的关系;告诫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对自然要存敬畏之心、热爱之心,要懂得树立自然意识、顺应自然规律、保护自然环境,学会与自然和谐共处,做自然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引导人们要善于修身养性、宁静致远,丰富自身的知识,教化自身的德行,提高自身的觉悟,以此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统一,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的真正复归。在漫长岁月的洗礼中,这些朴素的哲学智慧对当代社会文化、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追求等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为世界各国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贡献了一套伟大智慧和科学方案。当今世界,由于各国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造成了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引发了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事件和自然灾害,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到了空前紧张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特别倡导构建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建设一个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正是对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智慧的一种传承和发展。
二、价值导向: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
从价值导向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博大胸襟。“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出自儒家经典著作《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9]这是孔子鉴于春秋末年礼崩乐坏、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而向学生言偃描绘的上古时期大道流行的社会景象。其中,“大道”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或者真理,意指政治上的最高理想;“天下”的意涵较为丰富,在春秋战国时期特指“天子统辖的区域”;“公”,根据东汉经学家郑玄的解释,即“共”,意指以天下为天下人所共有。所以,“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指的就是:在施行大道的时候,天下是天下人所共有的天下,而不是一家一姓的私有之物,如此,方能实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世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表达了孔子对周朝末年礼崩乐坏的社会乱象的痛心疾首和强烈抨击,寄托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崇高的政治理想和美好社会愿景。自此以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就深深熔铸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之中,成为中国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矢志不渝的价值追求和政治目标,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抱负和精神动力。正是基于这样的天下主义情怀,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民族,不论历经什么样的时代更替,不管面对什么样的政治动荡和社会磨难,都从来没有退缩过,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勇往直前、愈挫愈勇,不断汇聚起炎黄子孙和华夏儿女的磅礴之力,不断凝聚成一个中华大一统的共同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内外谈及治国理政和国际政治重大问题时,屡屡引用“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典故,充分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人执古御今、持经达变的思维方式和宏韬伟略,彰显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致力于实现人类社会公平正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情怀和博大胸襟。当然,21世纪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眼中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的“天下”与古人的理解是不同的。习近平总书记语境中的“天下”毫无疑问指的是生活在地球上的所有国家和民族,涵盖的是整个人类社会或者整个世界,中国仅仅是这个世界中的一员。而古代中国语境中的“天下”,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实际上我们理解到的世界只是中国汉族先民自古以来的民族地域概念——九州,或者说中国范围内的全部土地。这种理解固然有其实证科学意义,“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更重要的是一个人文政治社会概念,具有神圣的形上的超越的意义”,[10]它是一个物质概念,也是一个社会概念,还是一个精神概念和文化概念,既包含广袤无垠的空间,也包含延续不断的时间,还包含理想的秩序。因此,古代中国的“天下”其实是一个哲学视野中的世界,一个兼具人文含义和物理含义的世界,“世界”不仅是天下体系中的一个基本政治单位,而且是一个最大并且最高的政治单位,同时意味着思考所有社会生活问题的最大情景和解释框架,意味着一种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方法论。因为对西方国家而言,国家才是思考政治问题的最大政治单位,是思考和衡量各种问题的绝对根据和尺度,不论是城邦国家还是帝国,或者民族、国家,基本上包含的是“国”的理念,很少有“世界”的理念,“世界”通常只是个地理性空间概念而已。[11]这就决定了西方国家在思考问题时,总是仅仅考虑自己国家的利益而无视其他国家的利益,并且把自己国家的利益当成世界的利益,当成衡量世界事务的尺度。因此,如果说西方国家思考世界的逻辑是“以国家衡量世界”“属于国家利益的世界”,那么中国天下理念思考问题的逻辑就是“以世界衡量世界”“属于世界的利益”。
据此可知,不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念本身蕴含着鲜明的天下主义情怀,这种情怀体现出来的价值导向对中华优秀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华优秀文化中许多开放包容、宽宏深邃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都与其有着密切关系,比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担当精神,它们与其他优秀政治思想和价值理念,共同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政治智慧和伦理精义,共同构成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基础和文化土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着眼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前途命运指明了方向。
三、终极目标:协和万邦、万国咸宁的和合追求
从终极目标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协和万邦、万国咸宁的和合追求。“协和万邦”源自《尚书·尧典》,其原文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12]这是上古时期的部落联盟首领尧基于当时“天下万邦”的社会现实而提出的政治理念,其基本含义是:(帝尧)能够举用同族中德才兼备的人,使族人都亲密团结起来;族人团结和睦了,又考察百官中有善行者,加以表彰,以资鼓励;百官中的事务处理得当了,部落联盟的全体成员才能亲如一家、和睦相处。不难看出,这一政治理念是一个由近及远、由小到大的思想体系,其中象征天下太平的“协和万邦”正是这一思想体系的根本目标和最终指向。“万国咸宁”源自《周易·乾卦》,意在提倡各邦国之间要睦邻友好、相互团结、和平共处,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万邦安宁、天下大同。概言之,不论是“协和万邦”还是“万国咸宁”,都蕴含着一种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价值理念,这种价值理念可以概括为一种“和合”追求。但是,这里的“和合”不单单局限于某一个家庭、家族、民族的“和合”,而是存在于天地之间的所有邦国、群体、百姓之间的“和合”,是不同文明、种族、信仰、制度之间的“和合”,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天地万物之间的“和合”,是“对立中寻求统一”、“多样中寻求和谐”、“冲突中寻求合作”的“和合”。就此而言,中华文化中的“和合”,其实就是“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形相、无形相的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变易过程中诸多形相、无形相和合为新事物、新结构、新生命的总和”。[13]“和合”作为一种交往理念和处事原则,是中华文化的根与魂、经与脉、心与体,也是中华人文精神的核心和精髓,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本质、最典型、最完美的表现形式。
当然,在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要想把“和合”追求落到实处,真正实现协和万邦、万国咸宁的大同社会,无疑是不现实的。然而,“和合”追求毕竟是一种理想、圆融、超前的人类理性表达,一种契合人类本性和人类利益的崇高价值,拥有其他文化所没有的亲和力、包容力、凝聚力。因此,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赓续中,“和合”追求不断为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所传承和发展,不断展现出新的形式、传递出新的蕴涵。无论是“和衷共济”“礼之用,和为贵”“以和邦国”“化干戈为玉帛”“四海之内皆兄弟”等思想主张,还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羹之美,在于和异;上下之益,在能相济”“中也者,天地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天地和,则万物生;地道和,则万物兴”“合天道,则天府鉴临;合地道,则地府消愆;合人道,则民用和睦”等哲学智慧,抑或“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包容心态,都是“和合”追求的生动而深刻的体现,都蕴含着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追求和生、和气、和立、和处、和谐的社会愿景,人和、家和、国和、天下和的美好憧憬,以及人乐、地乐、天乐、人美、地美、天美的终极境界。在数千年的历史传承和发展中,“和合”价值追求延绵不断、推陈出新,塑造出中华民族“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文化传统和习惯,不断唤起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安全感,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得以出场和发展的重要历史底蕴和文化积淀,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实现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美好世界提供了基本遵循。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绝非空穴来风、无中生有,而是源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智慧,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协和万邦、万国咸宁的和合追求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在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传承和发展中,这些文化精髓世世延续、代代相传,早已深深融入华夏儿女的内心世界,成为炎黄子孙骨子里和思想上挥之不去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基因和精神食粮。正因如此,中华民族深谙“国虽大,好战必亡”的道理,即便历史上的中国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也从来没有过侵略和奴役他国的历史纪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强调的:“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14]过去的中国如此,今天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同样一如既往、初心不改。这是一种文化自觉,也是一种文化自信,更是一种文化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