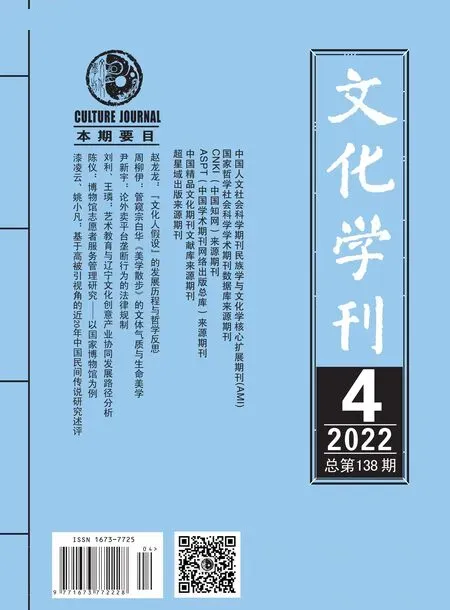马克思生态哲学视域下乡村环境治理研究
2022-12-07李海艳
李海艳
马克思、恩格斯本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马克思生态哲学”这一术语,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在探讨被资本逻辑笼罩下的社会现实时,其思想蕴含着深刻的生态哲学。辩证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人与自然内在统一是其生态观的主要内容,而实现二者间物质利益的转换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经之路。自然界作为人的无机身体,换言之,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人就不能进行物质生产,抛开人的实践活动,自然只是自在的自然。人与自然具有内在的同一性,这与中国“天人合一”观遥相呼应。就现实而言,它对于中国环境治理特别是农村环境改善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环境问题出现的最主要原因是在“人类中心论”与“商品经济”双重影响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而马克思生态哲学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作为其核心内容,这给予人们警醒与提示。此外,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物质生活虽然得到极大改善,但人们对优美宜居环境的愿望还未实现,部分地区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环境的现实困境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又再次将乡村环境治理问题推向人前。换言之,用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来研究中国乡村环境问题迫在眉睫。
一、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概述
(一)以感性—对象性活动原则为索引,实现人与自然的物质转换
理解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我们要理解“感性—对象性活动”原则,这是因为该原则不仅把人理解为感性的、活动的、对象性的存在,而且还要将活动原则贯彻到底。正如恩格斯所言,人们只有先解决吃穿等基本问题,才能够进行诸如政治、科学等更高层次的活动。换言之,人只有依靠自然界生活,依靠自由自觉的活动,满足并超越吃穿住等局限阶段,才能够从事更高层次的活动。自然界是人类存在的先决条件,人通过自身的生产实践活动从自然界中获取有关吃、喝、住、穿等物质资料,即自然界作为人的需要得以满足的对象。如果没有自然界,人既不是自然存在物,也不是对象性存在物,而离开了人的存在的自然只是自在的自然。换言之,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生存空间与物质资料。同时,人又作用于自然,赋予自然一定社会内涵,影响自然的自然进程,使自然人化。人通过劳动在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当中,实现物质转换。
然而,资本的无限制追求、人类中心主义生态观加剧了物质转化的失衡,不仅导致了环境的破坏,而且也破坏了人与自然和谐的共同体状态。现如今,随着一体化的进一步推进,这种失衡状态范围更广(波及乡村)、程度更深、影响更大。
(二)以超越单边价值为前提,构建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于环境的重大影响,恩格斯也通过对资本的批判来说明在资本影响下所产生的人的自身与无机身体间的隔阂,因此带来的一系列环境问题,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述了工业下的城市与周边地区,靠近黝黑发臭的小河的布莱得弗德肮脏不堪,即使是晴朗天气,也依旧笼罩着灰色的烟云,不适合人居住[1]。自然环境的破坏不单单影响到自然生态,也影响到人类的生产与生活,在这样的一种失衡对抗中,我们更应该构建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观已充分证明:如果不能超越人类自身的异化、不能超越自身单边利益、不能以整个生态系统的利益为最终目标,最终将无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总之,在劳动过程中通过劳动的结果、人化自然与自然化的人有机统一使人的有机身体(自我)不仅显现和生成为肉体与精神、感性和理性、受动与能动、存在与本质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且人的有机身体(自我)与无机身体(自然)共同构成有机统一的整体[2]。”换言之,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依赖自然获取自身所需要的物质资料与生存空间,人与自然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而实践或劳动成为这个有机整体的中介。
(三)以劳动为现实手段,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手段。现如今,这样的手段变成了破坏人的工具,这种破坏不仅体现在异化劳动下工人沦为不停机械运转的机器,因此工人感受到的不是幸福,而是痛苦,还体现在这种劳动导致的破旧肮脏的生产与生活环境。“此外,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3]。”资本主义为追求更高的利润而滥用科技最终所造成的对于人与土地的破坏,这样的情况在现代社会依旧存在,如滥用化肥所造成的土地破坏、食品安全、生态破坏等。
无论是物质资料生产实践、社会关系实践还是科学实践活动,都具有实践性,都是以劳动为中介的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一个方面。异化劳动虽然给工人带来了痛苦,但是本真劳动却让人们在劳动中享受到幸福感与成就感,马克思虽然批判科技对环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不否认科技所带来的重大推动作用。结合现如今的乡村生态问题与劳动问题,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想可以说是以人为基础,以劳动为手段,发挥科技的巨大作用,解决目前存在的乡村环境问题,让生态更宜居,以促进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
二、乡村环境问题的缘由
(一)逐利的资本逻辑,乡村资源不合理开发
当商品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范畴时,资本主义塑造了一个普遍物化或商品化的世界,伴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地域与民族界限被打破,资本逻辑的影响范围拓展到乡村。资本对于利润的无限的贪婪与自然资源本身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导致大量土地资源的丧失、资源的不当开发与生态环境的破坏。因而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生产关系导致乡村生态的不合理开发是乡村环境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马克思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致使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作为最先产生资本主义的城市内部,在“铁石心肠的利己主义”影响之下,不计其数的财富、“无法形容的贫困”与龌龊透顶的环境污染交织在一起,而作为被迫包裹进资本体系的乡村来说,情况更加危险,作为原料承担者的乡村并不是利润的最大受益者,反而成为环境当中最大的受害区。
现如今,国家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证乡村的建设,但是很多地区为寻求利益“最大化”谋求发展,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甚至以经济数字作为其发展的评判标准,从而忽视了生态的合理开发与保护,破坏了人与自然间合理的物质转换关系,从而走上了“先破坏,后治理”的错误道路。
(二)生产的空间转移,乡村自然沦为“承担者”
“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那些在北坡得到精心保护的枞树林砍光用尽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就把本地区的高山牧畜业的根基毁掉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来[4]560。”在马恩的文本中,我们不难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发展乡村的同时对乡村生态所造成的破坏。现在,同样的情况出现在部分地区,部分城市为了自身发展,将部分污染严重的工业逐渐迁徙向郊区乃至乡村,甚至出现大量“垃圾下乡”的情况,乡村单一的处理方式如填埋、露天堆积焚烧,极大地污染着空气、土地与水源,进而影响整个生态系统。
此外,随着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越来越多的乡村也开始被纳入到商业生产的范围之内,成为其人力、资源、空间乃至污染的重要承担者。一方面,生产要素向城市聚集,吸引了来自乡村的大量人力与资源,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乡村的发展,但人才流失、生产力低下、资源利用不充分等成为乡村振兴路上的难题。另一方面,与一体化相对的是,农村分散、生态破坏的局面也呈现日益严重的趋势。城市与乡村间开展劳动力与资源争夺,不断破坏着自然与人的可持续发展,也破坏着城市与乡村、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共同体关系。
(三)观念缺失与设施落后,乡村不合理的劳动方式
在商品化范畴与地域隔阂的背景下,城市先进的生态文明思想无法完全辐射到乡村,各种先进的生态、环保与治理观念无法充分发挥作用,村民长期受传统的生产生活习惯与观念影响。此外,乡村落后的基础设施是阻碍乡村环境整治的另一个客观现实。村民不仅对于自身产生的垃圾没有分类就直接采取就地焚烧等措施,而且对来自城市的大量垃圾大部分得不到很好的安置与循环使用,直接采取露天遗弃,不单单浪费资源、影响村容村貌,也更加破坏整个生态系统。
因此,产业兴旺、生活富裕不是乡村的全部,还因包括生态宜居、乡风文明与治理有效。我们对于自然的“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4]560。”我们以消耗自然环境为代价的劳动方式虽然可以取得短期的经济胜利,但是却是以生态与长期利益为代价,将反过来影响经济与人自身的发展。而“农业是生态产品的重要供给者,乡村是生态涵养的主体区,生态是乡村最大的发展优势区”[5]乡村作为我们生产生活资料的原产区,作为整个生态圈最重要的一环,不但事关人类的长期发展,也事关整个生态圈的和谐有序循环,因此,乡村生态保护迫在眉睫。
三、乡村环境整治的内在逻辑
(一)坚持合理“物质变换”,实现人与自然和解
人与自然关系失衡最核心的原因在于人需要的无限性与自然承载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人站在“上帝”的视角对自然进行无限制、违背自然规律的改造,致使环境遭受破坏,人也受到自然的报复。马克思曾经提到过两大革命,其中之一便是人与自然的和解,即人与自然打破对立的局面,重新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这种和解的实现需要合理控制和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物质转换是一个动态的相互过程,即人通过自由自觉地活动从自然界当中获取生活资料,而人又将生产生活的产生物释放到自然界中。如果人类为满足私欲无限制地开发利用自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获得相比于之前更加庞大的生产生活资料,但是随着污染的加重,部分地区因生态原因不再能给人类提供充足物质资料,甚至不再适合人类生存,因此,才会有越占有自然界越失去物质资料的内在矛盾的存在。在我国,乡村作为生产资料——农业的核心区,更应该坚持合理“物质变换”。根据其动态过程,乡村合理的物质转换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合理地利用开发自然与有足够的社会生产力为保护自然提供物质基础。
(二)坚持主体性原则,满足村民现实需要
在马克思看来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界。从生态方面而言,“主体”具有双重意蕴,其一是人们对于生态宜居的环境需求,其二是作为感性对象的实践存在,人在利用自然满足需求的同时还应当承担起保护自然的职责。
一方面,随着脱贫攻坚的顺利收官,村民已经实现了三不愁两保障,对于生活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建设更高质量的人居环境、进行生态合理开发与保护,不仅是马恩在分析资本生产给城市乡村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经验教训,也与目前我国以人为本的理念、主要矛盾、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人要坚持主体性,摆正自身在自然界的双重地位,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人类主导自然转为将人类贬低到与其他动物同等地位、提倡回归原始生活。在马克思看来,人不同于其他存在于人能够自由自觉地活动,既能使人自然化——人顺应于自然,又能使自然人化——人通过实践活动对自然进行改造。而在乡村建设与发展中,又要充分考虑村民多方面的需求,以实践不断调整改善人与自然、需求与实际之间的关系。
(三)坚持有原则高度批判,以劳动改善人居环境
要想真正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加强生态修复就需要进行有原则高度的批判,即不诉诸于浪漫主义的批判,既是借助科技的力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进行有建设性的劳动实践。
其一是必须抛弃浪漫主义的批判,既不要否定科技所带来的巨大推动作用与人的主观能动性,也不要诉诸于自然的放任状态与自主修复,像动物一样服从于自然的权利,放任自然与人的对立状态,那么人存在本身与人类社会将不会进一步发展,自然将会是纯粹的自在自然。在乡村,即使存在着垃圾处理基础设施,但村民依旧诉诸于河水的自净能力而向河里排放大量废水与垃圾;诉诸于山林的清洁能力将垃圾填埋或露天堆积;诉诸于土地的分解能力而滥用化肥农药,这不单是对自然的能力的高估、自身环保意识薄弱,也是对于现代科技的不自信与忽视。其二是反对只诉诸于人类的良知与精神而不把握于实践。我们不应只从“精神”层面把握实践,而且应该在社会活动中把握实践。自然界作为我们利用与改造的对象,我们不仅要对自然的价值与规律有着深刻的认识,还要在自由自觉的活动中获取所需物质的同时要顺应自然规律,采取自觉行动——合理的劳动生产方式保护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