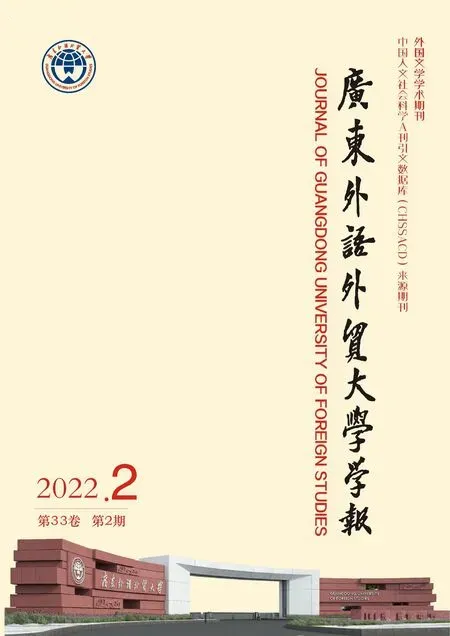若埃·布斯凯批评理论中的语言观
2022-12-01别致
别致
引 言
若埃·布斯凯(Jo⊇ Bousquet)是20世纪上半叶法国诗坛一个特殊的存在,他于一战中受到重创后终生瘫痪多病,但在写作中找到新生,发现语言带来的活力与存在空间。他不仅是法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实践者和批评者,也是诸多超现实主义诗人密友、超现实主义画作收藏家、画展赞助人;同时还是《新法兰西评论》和《南方笔记》固定撰稿人、阿尔托诗奖评委、二战抵抗者,荣誉军团勋章获得者。布斯凯生前发表多部小说和诗集,他的哲思文论作品与书信作品在1960-2010年间陆续被大量出版。以往的欧美作家和学者多关注其小说、诗作中的技艺和意象、或创伤与写作关系。其中,保尔·艾吕雅(P.Eluard)认为布斯凯揭示了现代文学的基本特征:想象使人真正接触到事物,并重组生活;罗伯-格里耶(A.Robbe-Grillet)认为他宣告了艺术的真正来临,将文学从转述和见证行为中解放出来;加斯东·巴什拉尔(G.Bachelard)认为布斯凯的批评性想象是对语言的超越,对现实的扩张。他的文论均为碎片式书写,文本结构松散,难觅主题脉络。借助不同文体和文本的比照阅读,本文旨在阐释作家对写作意义的反思方式,发掘研究文论中关于诗语言内在动力、及物能力、指涉存在问题之方式的思索。
19世纪末欧洲城市工业化、社会秩序与格局变动、宗教信仰没落、教育大幅改革、报刊和出版业勃发,诸多变化提出新的写作背景、问题与意义,促发多种文艺思潮和流派的涌现与更替。同时期的法国诗人普遍注重将创作观念理论化,为创作寻找理论支撑和抽象高度,讨论诗的本体价值或介绍诗技,通过多重介质更新诗的资源、内涵与形态,并通过新的语言秩序树立新的诗性和主客关系。这时期的诗语言节律松动、词义异化。摒弃理性表述、偏好直觉书写,不仅意味着西方工业资本主义文化危机中传统价值的失信,也意味着社会关系与公共空间多元化背景里个体地位的上升,这些转变无不呼吁新的写作视野与方法。
现代文学的问题、知见和技艺深受以下现象的影响:群体文学传统和个体断裂性经验、颠覆性价值取向。现代“艺术家不受理性或规则左右,任由感觉和情绪、直觉与想象来支配” (克里斯特勒,2008:248)事实上,自波德莱尔以降,诗就意味着新认知、新空间、新关系和新存在方式,“诗歌的本质在于致力于唤起一种新的关注, 以便在已知的世界中发现一个新的世界”(陈瑜明、杜志卿,2019: 105-112)兰波又将求新探索引向语言领域,此后的求新多以“新语言”为依托,拷问词与词、词与物、词与人的关系。20世纪上半叶的法国诗坛用直觉式认知、认知性想象、超现实或无意识写作等理念积极寻找词语获得意义的新方式,重新定义词语对存在的参与和揭示;发掘新的认知领域与方法, 思索个人语境、写作意义、写作对象的转变。
同许多20世纪上半叶法国诗人、思想家一样,布斯凯在中晚期文论里注重反思写作意义,将形而上问题重置进语言领域中,寻找能够解放思想、重建人与世界联系、证明存在整体性、并提供存在之地的全新语言。
个人化语言的纯净性
20世纪欧洲“迥异的流派平行发展,相互影响、斗争和渗透”,文艺界一方面“打破权威结构,探索全新艺术认识,一方面强调个体经验重要性,成就创作独行者”(帕驰,2016:9)。布斯凯认为法国20世纪20、30年代的“现代创作是一种极其个人化的探索。在探索中,感觉先于一切,并统领所有行动,它通过各种表达方式,绘画、音乐或诗引导我们走向自我超越。超越和嬗变意味着遗忘和急切感,要求我们毫不犹豫地抛弃和颠覆所有前人遗留的思想与认知,为创作清理出一片全新空间,让书写与自我和他者重逢” (Bousquet, 1980a: 49)。此论断重新定义创作的特征与目的,指涉一种富有内在张力、表达力、颠覆力的诗语言,能够重新定义诗的表述方式、认知和存在功能。语言中暗含着全新的挑战空间,诗人通过更新语言对现实进行认识、批判与重建,征服新的力量与存在之地。
布斯凯将语言创新视为文学创新的根本途径。传统诗意主要来自语言的形式、音乐性、具体语义或意象,从布斯凯的书写中,可发掘出两个主要诗意来源:语言的自身力量与内部碰撞,语言本身的形而上价值。创造总是意味着对规则的破坏(鲍曼,2018: 339)。语言创新首先要颠覆的是词语和意义的因果关系,这种颠覆使语言充满偶然性,成为拥有无限可能的世界,独立于思维和言说。
“文学改变和强化普通语言,系统地偏离日常语言”(伊格尔顿,2019:2)。布斯凯的小说和书信作品常呈现词语间的碰撞和意义相互侵染,他擅长将相去甚远的“异质词语叠加起来,让意群自我更新”(花瓶里的水裸了)(Guedj, 2000: 97-98)。比如 “vase où l’eau est nue”(里面的光线正在对理性进行荣誉惩罚)(Bousquet, 2008: 130), “la lumière y fait amende honorable à la raison” (Bousquet, 1999: 29)。语义在异质的词语间、在奇特的句法中被碰撞、被清洗;并在异质词语的距离中自我展开、蜕变,在不同本质的事物间流转并将它们联系起来,最终脱离理性秩序,变得不可预测、晦涩诱人。除了词语的大胆碰撞,布斯凯也常采用奇特的句法结构,比如“Reine transparente des images qui m’ont caché le temps, petite lumière dont mon regard est l’ombre enchantée” (众多意象的透明女王,它们把时间遮盖起来;小小的光,我的目光是它被蛊惑的影)(Bousquet, 1999: 38);这类句子打破隐喻和非隐喻两种语言间的区分、消解固定事物意象、使得事物之间相互侵浸。在这种语句面前,智性解读毫无用途,诗人和读者的思想被迫直接地、甚至于猝不及防地撞上事物,没有任何先在参考意义。读者只能跟从近乎直觉式的感知任由意象层层叠加,继而迷失在意象的交错或光影与事物间微妙的互动中。与此同时,“意识在诗内的语句中不断死去又重生。不是语句存在于意识中,而是意识被圈入语句中。而语句本身则在词语之间,在词语及其意象的爆发中自我滋生” (Bousquet, 1982: 24)。现代诗语言包含着对旧语言秩序与表达力的重思。诗语言对寻常词汇之用法和意义的偏移不仅体现作者本人对事物、空间和世界的态度,也投射作家本人的行动。这种语言摆脱日常语言的连续性,打破词汇间旧有关系,其目的并非使现实秩序与思想相对立,而是不断重构被理性语言塑型的意识,并揭示一种新的语言与思想互动模式:语言不仅表述思维、还可激发新思维,并展开一片全新行动空间。
在布斯凯文论中,诗语句并非现实之倒影或思维堆砌之果,而是词语碰撞所造成的意义迁移与更新的过程与场域。正如让·保朗(J.Paulhan)(1999: 19)所说,“布斯凯致力于消弭思想和语言之间的距离,并时刻注意着将思绪和表意的词语进行相互对照、相互拷问”。他眼中的诗是语言的冒险,对新语言的寻找又是诗人在感性领域和意识领域的冒险;诗人需要提高敏感度,密切观察语言内部的意义变动。词语只有通过不断更新、超越、升华、出常,才能真正地表达个人存在,同时保持自身独立性和无限可能性。事实上,摆脱理性和常识并追寻纯粹呈现的意象模糊而多义,是诗语言和诗性思维无限自新的物质依托。所以,新的语言是一种高度个人化并且拥有内在生命力的语言,可以映照诗人的思想;那是一种“更天然,更纯粹的思想,一种正在诞生的思想” (Bousquet, 2008: 301),在创作中不断褪去复杂的外壳,返璞归真,预告了纯粹而浑厚的诗性。
对于充满意象和碰撞的诗作而言,诗性的来源不是词语,而是某种不可言述,却又在意象互动中不断闪现的微妙存在。布斯凯(Bousquet,1999: 30)曾在一封私人书信中明确解释说他在寻找一种“晦涩而闪烁着意象的语言[……]。这种语言可以表达诗人所有的欲望,将生活变成一场介乎光和梦之间的游弋”。 诗人在寻找一种天然的语言,语句以印象为表,言说以感觉为体,让阅读的人不断在理性认识、直觉洞见、潜意识思维和想象之间穿梭游弋,突破现有认知内容与方式,走向自我的全新表达,让自我成为新的世界与谜题。语言在无限趋近感觉迸发和元表达之时才最接近事物的纯粹呈现 (pure présence)。菲利普·雅各泰(P.Jaccottet)(1994: 84)也曾描述这种存在“所有在纯粹中迸发并保持纯净的,以及所有的纯粹迸发运动都是谜”。微妙新意的根源在人本身,新意“进入我们内心,潜入其中最渊深的在处,同时已消逝无踪” (Rilke, 2006: 86)。
布斯凯(Bousquet, 1980a: 48)的诗歌、小说和文论都是上述探索的痕迹:“写作,是在构思新作品的同时学会蔑视刚完成的作品。成为自己的学生、孩子、敌人。一页散文、一首诗,是一段段痛苦追寻的痕迹,是和自己对战胜败的纪念。这才是现代的”。这种作品观意味着发现写作行为的内在逻辑:把创作行为定义成追寻新意的过程,不断用新作品去超越和取消已完成作品,不断在思想和语言中实现新碰撞与发现,始终用自我反思批判态度来保持作品的原创性、开放性与现时性。这种创作观把创作过程和反思过程紧密结合起来,前者承载想象与经验、追逐将现未现事物的过程,后者对语言规则进行整合,指出语言创新的动力、视野和方法,并对现有探索和书写结果进行批评,从而不断为写作提供新的基础和起点。通过打造契合直觉与思想动向脉络的语言,布斯凯将写作行为化作意识不断趋向自身和事物本质和整体的运动经验,对思想与世界之无限进行探索。
在充满反思和创新的视野中,诗语言和作品意味着一种激越的存在状态。诗人不仅需要指出语言是一个充满不确定的总体,更需不断为之创造新的内部秩序和外部资源。布斯凯(Bousquet,1980b: 47)认为,“诗歌不是思想的表述。当语句成为行动的源泉之时,诗就显现了”。作为行动之源的纯净语言具有新的形而上价值。正如布斯凯(Bousquet, 1980b: 84)所言,“诗不是众多语言中的一种,而是最大程度摆脱了回忆的一种语言,它让我们抓住纯粹的话语。纯粹的话语是一种完整的存在状态,我们只是跟随它”。换言之,全新语言诞生于高度批评的感性体验,保持迸发时刻的纯净,不被历史熏染,不被外界异化。这种诗论意味着语言不只是一种表现形式或认识工具:在全新诗语言的内部,意象与事物不断相互悖逆、消解、更新,从而造成意义的多重性和思维活动的延续性,并隐约勾勒出一个完全他异性的在所。
诗语言意味着一个独立完整的存在领域,“把语言视作认识自我的中介是荒诞的,因为语言的完美将我们排除在外,并展开另一个世界” (Bousquet, 1977: 42-43)。平常语言是思维活动的延伸,是与现实相对应的抽象符号;诗性语言则相对独立于现实,拥有特定内动力与结构,诗作中的事物与意象短暂易逝并始终指向别处,诗意则不断地在文本构思和思维闪现的时刻迸发,在意识与自我内在深度碰撞的瞬间自我彰显。
语言与物的统一性
对事物的关注是现代人将自我从现实生活碎片中解脱出来的一种方式,也是布斯凯诗作的永恒视野。他认为对事物本来面目的揭示是诗的主要目标之一,“当诗人纳粹而简单地引证真实的时候,真正的诗就诞生了” (Bousquet, 1980b: 48);“诗首先是语言的冒险,其次才是诗人的冒险。一篇优秀作品始于个人悲剧,终于对真实的客观表达” (Bousquet, 1980b: 50)。对许多法国现代诗人而言,诗承载并揭露现代人对自身和外在世界的不断探寻,将审美经验和认知经验合一。
现代诗人对外在世界的审美和认识在语言探索中进行。自兰波起,诗人们开始寻找“新语言”,意识到诗语言应反抗前人留下的文学意象,用新的方式去言说和思考世界。从布斯凯的文论中可窥见他对诗语言的双重要求:寻常语言是陈旧的,只能描绘事物外在并导致“词语熄灭”,“语言磨损”,而“精心雕琢的语言无法在诗歌之外存活” (Bousquet, 1980b: 50)。换言之,普通的书写与言说用精确度代替表达力,是对语言的异化,不能照亮言说对象,不能让我们真正经历想要命名的事件,也不能让我们靠近事物的本来面目;而精心雕砌的语言又缺乏生命力和适应性。布斯凯希望他的语言彻底超越现实和象征、主体与客体的分别与对立,“重新成为一切存在事物的灵魂”,成为“自然和自我之间的共同心跳,成为对生命的感知”(Bousquet, 1999: 29)。 新的诗语言必须言说一切并饱含真实,回应事物和人的存在:“用万物的声和动言说,也为之言说”(Bousquet, 1989:113)。布斯凯通过简单词汇的碰撞,将个体经验、想象和事物汇聚起来,并进行重构。认识与言说的过程是对事物的重新命名,意味着创造;诗对事物的认识试图让言说对象在诗人的精神世界中获得饱满、无限的生命。布斯凯对真实的关注和言说和对事物隐匿面的揭示实现了主观话语、主观感受、客观词语和客观映照之间的同一化尝试,指出诗人试图成为世界的中心和象征。
布斯凯文论对语言和真实之间隔阂的思索集中在语言和认识论两个层面。首要原因是西方语言的抽象性:“语言是藏洞、是帘幕、是气窗。它像身体一样揭示或掩藏;它用词汇去看、去听、去自我欺骗” (Bousquet, 1981: 85)。罗曼语是一种语音和语义并联的符号,符号和指称事物之间的关联高度抽象,思维与真实生活间始终存有距离。这种抽象关系在漫长的使用中逐渐僵化。布斯凯似乎认为西方人只是幻想了世界,而没能分享它的存在,正如维根斯坦(Wittgenstein)在《逻辑哲学论》中论述语言的遮蔽作用时所指出的,语言指称的对象并非事物的实在,使人远离现实。 “和语言结合的真实只是真实的表相” (Bousquet, 1982: 52)。因此现代诗人从前人手中继承的语言用陈旧的体系代替了鲜活的生命与思考,抹除了世人作为个体生命对世界的参与,并不断远离真实。
次要原因是认识方式和感知结果之间的内在差异:“任何事件都有象征性和实在性两种存在方式。对记忆而言,它是一个事件;对于思想而言,它是一副意象,而意象是对我们存在的表述” (Bousquet, 2008: 48)。语言表述的对象必须同时包含三重元素:思维、事件与感知。换言之,语言游移在两种不可分割的运动中,一是指称具体事件,二是揭示超越时间并具感性色彩的事件意义,却无法兼顾之,因而造成表述的不全面和意义的本源流失。
语言指向偏离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根本原因:理性认知方式的不足,外在表相与内在特性的二元对立。布斯凯(Bousquet,1999: 21)建议“不要被事物的表相所蒙蔽”。我们命名为真实的只是真正物质的表相、幻影,而非其本体自性。一方面,事物的本质深藏不露,唯有脱离了庸常陈旧的外在认知,才能在写作途中逐渐发现并靠近那游移言语之外,却又蕴含于个体生命之中的存在。“我们命名为真实的,不过是它的一种表相” (Bousquet, 1982: 19)。 真正的物质是不可见的,“物质只是难以触及的真正物质的影像,正是不可触及的物质构成了我们思想的幽深之处” (Bousquet, 1982: 20)。 另一方面,理性认识方式具有片面性或欺骗性,“只有想象能让我们认识周围的人,只有想象才能穿透他们用思维编织的面具”(Bousquet, 1980b: 40-41)。个体直觉感性的认识方式被视为打破内外、性相二元对立的根本方法。在主体的理解活动中,事物呈现出物质性存在;在感性觉察中事物则更像一种等待或冲动,能和人产生真正的联系。当诗人喜欢上一幅画面或意象,就是在进行一次憧憬与回应,挥散表相,走向匿藏在事物背后的真实。这种批评意味着认识论的更新:知识不是一系列理念之和,而是主体与现象世界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运动变化中。对于事物认识不足的直接表现是人丧失了自然而然为生命陶醉心悦的能力。“人都是迷醉不清醒的。自其降生就被接入一个充满奇迹的花园,却失去了惊异感叹的能力(……)我们只懂得欣赏万物的表象,而对于生活的诗性感知则教会我们发现事物暗藏的美” (Bousquet, 1977: 14)。人与物或世界的真正相遇会打破理性认识的冷静淡漠,充满惊叹、沉醉和热切。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不少法国诗人将诗视为革命性认识工具,布斯凯(Bousquet,1999: 47)同样认为“诗能打乱世界的现有秩序,揭露它惊人的内在结构,只有这种结构才真正和我们休戚相关”。 事实上,超越事物的表相和寻常认知并不意味着反驳或规避意义的生成,恰恰相反,诗性表述方式和想象始终以客观存在为表述对象和目的。在诗的自由空间里,物质与外形终于契合并相互指认。诗性意象与现实之间充满张力,意象是对现实表象的否定与隐匿,同时却揭示现实的深层本质,通过感官将人和事物真正联系起来。独立而活跃的诗语言不仅扩大艺术潜能、加深关于存在之物的认识,更为诗歌创作打开一种新的意义源泉:诗是对诗人本质的话语化,是现实的精要。
自康德起,想象被不少诗人视作理解事物整体和真正实在的能力。布斯凯将感觉与感性视作灵魂触手,对事物进行直觉感观式体验是诗人向事物倾注灵魂的表现,能揭示事物的本质与存在方式。如果说理性认识是间接而陈旧的,用集体记忆取代个人体验,想象对事物的认识则是直觉性、碎片式、理想化的,调动所有感官,意味着个人在具体场景中与事物的真正接触。所以“诗是某种现实的语言,我们的智性无法领会这种现实,但能在感性状态下开垦它”(Bousquet, 1980b: 49)。在布斯凯的作品中,诗性想象旨在描述人对真实的追寻,把存在的荒诞与绝望转换为意象,从而把沉重无尽的意义追求转化为一场感官狂欢,并蒙上梦幻般光芒:“死亡是不可接受的,可我们都被投进这终将成为埋骨之地的世界里。所以我们求助于想象,让想象为我们遮掩这残酷的法则,把我们化为土壤滋养无处安放的真实之萌芽。精神的世界歌唱着冰冷的现世,诗人终有一天会被遗忘”(Bousquet, 1977: 12)。加斯东·巴什拉尔(Bachelard,2004)也认为通过想象觉察事物,意味着碰触事物的灵魂,碰触尚未成型诞生却开始已经渴望生命的某种事物。对想象的运用使诗歌创造充满活力与不确定性。然而,想象创作的意象本身并不是诗作的最终目的。意象“放弃了类比功能,激发读者的想象力,但是并不给读者提供什么可表征的物或对象”(Ortel, 1961: 267-268)。布斯凯笔下的“意象正在想象中”(Nelli, 1961: 18),可以不断激发新的意义与意象,“想象创造意象,却一直在意象之外,是永不可及的他在”(Bachelard, 2004: 6)。文学意象不仅是虚构或经验材料的重组,也是精神和思想的框架。诗性语言不是简单的编码传输和解码对象,奇特的意象、异化的词语都暗含着面向真实的存在方式;在传统信仰与价值坍塌的时代中,在孤单、病痛、死亡、战争的威胁面前,诗性语言成为一种慰藉和导向,将个人与他者联系起来,打破个人独自承受的处境。
布斯凯文论中的诗性想象是对西方现代理性认识论和语言观的一种修补尝试。布斯凯(Bousquet, 1999: 61)认为诗语言越是个人化,就越是容易为他人所懂:“我想打造一个属于我的语言,但是所有人都能明白。用这种语言隐秘地倾诉,为人类所有的痛苦发声”。因为想象是个人化的、经验性的,而经验和感性是人与人之间的共通之处。因此,语言观中暗含着认识论维度:知识累积并不能保证思想和作品的客观性;认识对象的普遍性,对存在、语言等人类共同精神框架的关注才是作品和思想客观性的先决条件。 诗语言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凸显意识的作用和能动性。通过这种认识论,诗语言和诗作超脱了理性现实世界和梦幻想象世界之间的对立关系。
布斯凯通过诗语言寻找真实、言说事物隐匿真相的尝试却最终走向自我消解,因为他试图让语言成为真实本身,而非其符号象征。布斯凯希望建立起词语和事实之间的等效性,赋予词语外在现实的生命力、表现力、吸引力和影响力,“诗人都有一个共同目的:让念头与事实同一不可辨分,让言说念头的词语具有现实的维度,并与之不分彼此” (Bousquet, 1977: 43)。 布斯凯似乎认为在不断闪现的意象中,诗人通过直觉与感性与事物交融,并由此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此时语言就成为一种事实,与事实同质共性,不再是简单的表征或指称,成为可代替甚至取代事物的客观存在。“现代文学有自主的存在,把自己与其他所有语言分离开来,形成一条深不可测的鸿沟, 从语言的表象或指称功能回到语言的原始存在,即:语言首先存在与简单有形的书写行驶中,是事物上面的一个印痕,是散布在世界上的一个标记(这个标记是世界上最最不能抹去的形式的组成部分)”(福柯,2017:47,45)。至此,诗人对于真实的追求被扭转,介乎神学密语和游戏幻梦之间,布斯凯始终不断构建,而后推翻先前所有作品和理念,让无穷的诗性视野将诗人吞噬。
语言照亮存在
布斯凯对诗语言的探索代表了20世纪上半叶法国诗坛的一个重要诉求: 使语言包括多重内涵,兼容主观感受与客观反映、个体存在与客观真实,从而摒弃导致文化危机的思维传统,将形而上问题重置进语言探索中。“语言是人类活动的宿命性表达” (Bousquet, 1980a: 114),诗语言向人揭示事物的隐匿真相,将人重新和世界联系起来。 “万物皆在意识与语言中,又在其外。因为无论思考何物, 都首先必须能意识到该物,且必须将其表达出来, 并将我们封锁在语言或意识的内部。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意识和语言都是完全面向外部的,因为意识与语言只有在他们被外部世界所包含时,才反过来将世界封闭与自身之中”(Wolff,1997:11-12)。所以,现代“诗人的博弈对象,是一种属于所有人的语言” (Bousquet, 2008: 73)。新的诗语言试图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把被阶层、文化分割的人重新联系起来,让大家意识到面临着同样的命运。
诗语言不仅揭示诗人内在深度,贴近个人感觉印象,同时也富含外在现实,探索存在客观化,并试图魅惑读者,成为所有人的共有语言。“诗是人和人类命运之间紧密联系的产物”(Bousquet, 1980b: 49)。“世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异的人。对于诗语言的理解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相似性爆发出来,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动词,有着同样的血脉” (Bousquet, 1982: 29)。存在的自然规律在主观探索中被照亮,人与人的根本相似性在于我们面对同一个充满幻觉、谬误和分隔的荒诞世界;在于我们都需要重新认识自我、事物与他者。
“可感知物既非单纯以梦境一般的 存在与我之中,也非以内在属性的方式存在于事物之中:它是事物与我之间的关系,存在于我与事物的主观联系之中”(梅亚苏,2018:7)。诗人借助个体语言探寻和构造自身和世界,并照亮个体与存在的关联。在布斯凯的作品中,诗语言对于存在的探索包括两个层面:解析个体存在方式或者个人对自身处境和存在的知觉,超越个体存在去认知存在的普遍客观性。解析个体存在意味着诗人成为自己的他者、远方视野和无尽期望。认识生命意味着“在生命的运行过程中,发掘生命内在目的” (Bousquet, 1982: 14)。诗人在自己的生命中建立一个内在秩序,并用创作去践行。“我对事物无所期待,对人无所祈求。我所有的期待,都向自身讨要。我期待未来的转变,但并不执着于此。我所期待的,是指引后人为自己建立生命内在秩序,从而获得俯瞰主宰自己生命的能力” (Bousquet, 1973: 138)。 建立生命内在秩序的具体方式是通过创新与反思语言,将自我变为感觉,观察和思索的对象,发掘个体经验和所有作品的内在一致性与倾向。所以,当个体存在成为语言探索对象之时,诗人生命被展现成主动探寻和意义生成的动态过程。
让个体存在成为认识对象,也意味着诗人对自己生命的主动构建塑形,从而摆脱充满荒诞和偶然的被动命运。对于现有知识的反思性运用不仅是现代社会的活力来源之一,也是布斯凯创作的重要活力。“对语言的持续思考使我在每一日的寻常生活中意识到自我救赎” (Bousquet, 1977: 61)。诗人通过诗歌构建自我,并把自己的生命变成开放的空间和炽热的期待。 诗歌让诗人的生命自我觉醒,然而个人生命意义的浮现和重塑并不是诗歌创造活动的终点,对于存在的个人化书写才是创作的根本意图,它把个人的生命变为期待、变为一种渴望成为照亮存在的光。激发创作进化过程的生命冲动在布斯凯的作品世界呈现为趋向真实与无限的激情。
通过诗认识个体存在还意味着用语言探索、挑战意识边界,“人的思想中存在着一个不可言状的深度” (Bousquet, 1989: 88)。 布斯凯眼中的世界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承载意义的对象,另一部分是寻找对象与意义的主体。前者是显性的,而主体和他的追寻都是隐蔽的,在诗作中浮现。20世纪20、30年代的法国先锋诗人深受柏格森和弗洛伊德影响,注重讨论意象与直觉、想象、潜意识的关系;认为纯粹个人化的写作、潜入个人欲望深处,对个人化“潜世界”的表述是通向人性的有效途径。他们认为“在人的思想中有一种不可认知的深度,无论哪种表征方式都无法揭示它” (Bousquet, 1989: 88)。
现代主观性起统一作用,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形式上的统一之点(库尔珀,2019:383),“所有人都希望对自身存在的理解能成为照亮存在的高光” (Bousquet, 1973: 80)。布斯凯试图在个体生命中揭示存在,因为存在的根本特质是运动,它只能在具体的生命中彰显。换言之,诗人不仅思考人的存在意愿,也追问其存在潜能和事实,“人总在试图厘清他对个体存在内含潜力的认知与参与”(Beaufret, 1971:17),而 “诗是我们在相对性存在中唯一能够获得的关于绝对存在的看法” (Bousquet, 1977: 15)。在诗领域中,存在的潜力与可能性体现在语言的极致使用中;换言之,诗人可以通过不断加强发掘和展示美与真实的能力,借此扩张与丰富自己的存在,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存在是人的作品” (Bousquet, 1999: 217)。
然而,存在的客观性决定了诗人对存在的理解需要突破个体边界,摆脱现实的制约,达到“思维在时间之外,身体留在时间之中” (Bousquet, 1982: 39)。确切地说,诗人需要超越充满被动、偶然、碎片和矛盾的个人生命,打造一种连贯、能动、高度总结的整体生命观;从而俯瞰生活,重新赋予生命内在统一性,让人不再被生活所经历,而是主动创造意义,定义自我经历。加斯东·巴什拉尔也曾强调超越性反思对人的重要性:“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是对人的超越。我们要定义一个人,就必须考察他身上一切超越人类处境的倾向”(Margolin, 1974:121)。
诗语言是诗人打破个体经验,是个体和存在、世界各自彰显的结果。诗中语句是一种具体场域:在这个空间里,感觉和事实达到统一,个人和整体达到统一,个体存在的差异性和特点也得到包容与存续。只有通过创作不断扩大意识领域,让主体性和客观存在相互敞开,才能发现语言与生命是同质的,才能领悟语言包含着人的起源、归宿和存在之谜。正因为语言自身有无限可能性,才能够在创作中揭示生命的无限可能性。布斯凯笔下的诗语言具有高度批判性和反思性,不断自我突破、指向事物的隐匿真实,所以能够表述超越性的生命观。所以布斯凯认为诗人不是妄想家,他是寻找真实的人,寻找能指导俯瞰生活的真实。理想诗作中每一句言语都是对诗人的总结与超越。诗人通过对现实的超越,让思想和行动不断相互反映推进,由此趋向自由与常新。通过超越运动,诗语言承担起生命的整体性和延续性,并代表了生命趋向绝对和自我完满的本质运动。诗人在新的语言里逡巡,从言说自我和事物走向言说存在,并试图让自我言说成为对存在的言说。
结 语
布斯凯关于新语言的探索直指写作源头的思想、情感与冲动,也指明文学批评的任务之一:描述作品出现过程、揭示创作意图对语言的影响。相关批评文论中语言更新的动力可以归纳为三方面:词语之间的相互碰撞可产生新语言,诗人对事物的全新认识可产生新语言,对于个人内在的探索、对于个人生命体验的描述或对存在的探索也可产生新语言。诗人主动引导意识活动,运用种种手段主动建构人与自身、与事物关系,激起事物间关系秩序的持续变化过程。在不断趋向新奇、真实和无限语言观的统摄下,作为生命经验的诗便突破个体和虚构边界,成为认知的场域和见证。诗语言成为独立的意义体系和存在的意义空间,布斯凯用不断迸发的写作激情揭示事物隐匿真相,让个人主体性和世界客观性相遇,并从个体经验和个体超越两个方面照亮存在。创作行为就此成为存在的象征。当然,布斯凯清醒地认识到,诗人对于真实和存在的认识,是千万种认识中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