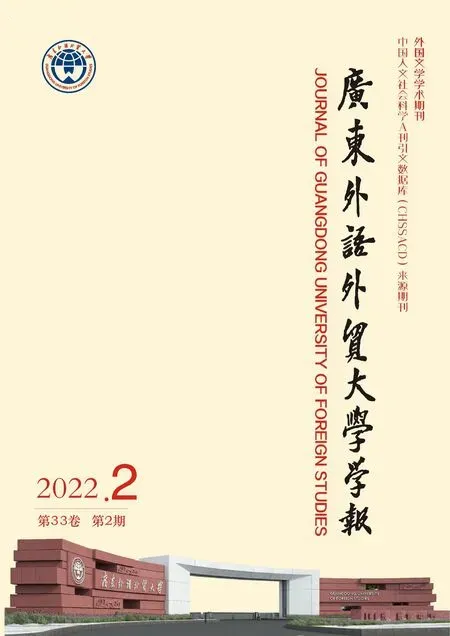阿里斯托芬谐剧对共同体危机的书写
2022-12-01李顺鹏
李顺鹏
阿里斯托芬('Aριστοφνης)在谐剧中通过歌队传达自己的观点,最具代表性的是在《马蜂》(Σφκες)中,他称自己为扫除城邦灾祸的清道夫,“他还在去年祛除了那使人发抖的寒热病(πιλοις, 又译‘噩梦’,即诡辩技艺)”(《马蜂》阿里斯托芬,2007:1038)①,与此相似,阿里斯托芬对谐剧崇高的社会作用深信不疑。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和诗人对现实的考量,阿里斯托芬在谐剧中构建了数种共同体,这些共同体都被置于分裂的概念之下,正是这种分裂使阿里斯托芬能够提出对政治现状的忧虑和可以取而代之的理想。对阿里斯托芬来说,在垂直的方向上,城邦处于家庭和泛希腊共同体的中间位置,既然城邦民主政治的危险难以根除,那么远离这种危险的家庭共同体就不失为一种良好的选择。然而,友爱的缺失导致的家庭分裂也同时存在,这在大多数情况下让城邦政治无路可退。而雅典城邦对政治的处理思路延伸至异邦时,垂直方向上的泛希腊共同体也被分解了。
古希腊语中的“共同体”一词是“κοινωνα”,这个词源自“κοινóς(共同的、共有的、公共的)”,其核心内涵是对共同的强调,如“κοινδιλεκτος”意为“希腊普通话”,又可译作“共同语”,意为希腊诸城邦的通用语言;索福克勒斯(Σοφοκλς)的《安提戈涅》('Aντιγóνη)中,安提戈涅著名的开场白也有“共同”一词:Ωκοινòνατδελφον’Iσμνηςκρα(啊,亲爱的伊斯墨涅,我同根生的亲妹妹;我自己的姐妹伊斯墨涅跟我连在一起;噢,亲妹妹、我至亲的妹妹伊斯墨涅的头)。安提戈涅这句呼唤强调了她与伊斯墨涅之间姐妹关系的共有性和她们所处的同一血缘共同体。“若某种集合体缺乏了这种内在的共同所有或分享,就不再是古希腊或亚里士多德语境中的‘共同体’概念了”(陶涛,2016:37)。除了强调内在的共同,亚里士多德(Αριστοτλης)还提到,一切共同体的形成都是因为对某种善的向往,这种善即只有借助共同体才能达到的某种目的。在阿里斯托芬对共同体的书写中,在确保共同体共有的目的得到保障之外,共同体的成员以其激进的爱欲冲破共同体,制造了共同体的危机。本文以具代表性的《阿卡奈人》和《云》为主要对象,分析谐剧中共同体的危机。
儿子打父亲:家庭共同体的危机
古希腊的“家庭”概念和现代意义上的“家庭”概念并不相同,古希腊语中指代“家庭”的词是“οκος”,包含了“房屋、宅子、住所、家产、家政”等内涵,根据成员构成,家庭可分为“核心家庭、拓展的家庭、家族(或氏族)”(孙晶晶,2016:81),一般来说,对古希腊家庭的提及限于对核心家庭的讨论。
亚里士多德(2003:268)曾言,“在每一种共同体中,都有某种公正,也有某种友爱”,友爱将家庭内部成员团结在一起,而家庭的联结和宗族的正常运作则进一步导向城邦的出现。在对柏拉图(Πλτων)的批评中,亚里士多德指出,《王制》(Πολιτεα)中那种对妇女、儿童和财产进行平均分配和共享的计划只会让城邦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巨大的家庭,看起来友爱的部分似乎是扩散了,其实这样的大家庭淡化了友爱,因为谁都可以是、同时谁都可以不是另外一个人的父母或儿女。所以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批评建立在后者对家庭共同体的扩建上,前者期望的是一种包含男人和女人、父母和子女、主人和奴隶在内的小型家庭共同体,城邦正是因为数百个这样的共同体聚集在一起互相帮助而逐渐形成。在阿里斯托芬的谐剧中,这种前政治式的小型家庭共同体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如《和平》(Ερνη)这种以结婚之喜收尾的谐剧和《吕西斯特拉特》(Λυσιστρτη)这类含有夫妻双方破镜重圆情节的谐剧,都反映出家庭在阿里斯托芬式期望中所占的巨大比重,而在家庭中,最重要的基础条件便是友爱。基于雅典城邦的现实境况——友爱的渐离,阿里斯托芬对家庭共同体的书写始终建立在其分裂——或几乎分裂的基础上。
《云》(Νφελαι)剧中儿子打父亲的情节或许会让剧场中的观众发笑,但也会让他们不解:为什么斐狄庇得斯殴打斯特瑞普西阿得斯的理由竟会让人无以反驳?谐剧开头就推出明显的家庭矛盾,儿子斐狄庇得斯为了赛马借了许多钱,还钱的期限马上就要到了,作为父亲,斯特瑞普西阿得斯为此感到焦虑,因此整晚睡不着觉,反倒是斐狄庇得斯睡得十分安稳,甚至梦里他都在赛马。在古典时期的希腊,“家庭”由人和财产组成,财产的内部流动主要是指儿子成年后对父亲财产的继承。在《云》剧中,显然儿子对父亲财产的“继承”过早了些,斯特瑞普西阿得斯在斐狄庇得斯的赛马消遣上花费了过量金钱,以至于仆人在换上粗灯芯时他都要呵斥一番。斐狄庇得斯将不得不负担起还债的责任,如斯特瑞普西阿得斯所说,“这些债务会完全落到你自己的头上”(《云》:40),但斐狄庇得斯似乎根本不在乎这些。《云》剧开头的这一幕制造了父子两人在财产问题上的矛盾,虽然这里的冲突并不激烈,却为之后两人在伦理层面更严重的冲突埋下了伏笔。紧接着父子对话的是斯特瑞普西阿得斯对婚姻的抱怨,这段话中没有任何关于友爱的因素。他说:
唉,但愿那媒婆,那劝我
娶了你母亲的媒婆,不得好死!
……
我是一个乡下人,她却是骄奢的
城市姑娘,一个十足的贵族女人。
新婚那天晚上,我躺在新床上,身上还有羊毛、酒渣和无花果的味儿,
她却满身是香膏和番红花,不住地和我亲嘴,
她就像爱神那样没有节制,那样大咬特咬(δαπνης,λαφυγμο,Κωλιδος,Γενετυλλδος.)。(《云》:41-52)
多数理论认为在古希腊家庭中,妇女或称妻子地位低下,她们服从于丈夫和儿子,如《公民大会妇女》(’Eκκλησιαζοσαι)中的丈夫对他们掌权的妻子愤怒不已,并叫嚣着要好好揍她们一顿;《奥德赛》(’Oδυσσεα)中奥德修斯的儿子忒勒马科斯在父亲离家时对母亲宣称自己主管家里的一切。但《云》剧中的妻子未受丈夫的管控,没有节制、骄奢的品性不但压过了丈夫的老实忠厚,还传给了儿子。在起名事件上,由于对以往老辈人所获荣耀的怀念,斯特瑞普西阿得斯的妻子要给儿子起个带“马(ππον)”的名字,希望后者能在以后的日子里重拾家族荣耀,而斯特瑞普西阿得斯则倾向于儿子祖父的名字——“俭德(Φειδωνδην)”,最后双方妥协的结果就是斐狄庇得斯这个名字,Φειδιππδην,意为“俭德马”。剧中斐狄庇得斯的赛马习性便源于此,如斯特瑞普西阿得斯所言,斐狄庇得斯继承了其母亲的习性,而父子之间友爱的缺失使斯特瑞普西阿得斯痛苦不堪。
在儿子斐狄庇得斯从思想所学成归来后,斯特瑞普西阿得斯让他为宴会上的宾客们唱一段西蒙尼得斯的歌,斐狄庇得斯不但拒绝了这个要求,还称西蒙尼得斯是个“很坏的(κακòν)诗人”(《云》:1363);斯特瑞普西阿得斯勉强忍耐,又叫斐狄庇得斯念一段埃斯库罗斯(Ασχλος)的诗,但斐狄庇得斯又反驳道,“我也把埃斯库罗斯当做头一个(πρτον)诗人吗”(《云》:1366);接着斐狄庇得斯念了一段他认为是最聪明的(σοφτατον)诗人欧里庇得斯(’Eυριπδης)的诗,内容是哥哥诱奸了同母的妹妹,这让斯特瑞普西阿得斯极为愤怒,于是父子二人便打了起来。《云》剧中的儿子打父亲式伦理混乱为思想所的修辞术提供了展示自己的机会,从而为那些如斯特瑞普西阿得斯和斐狄庇得斯那样不守城邦法律的人提供了用以摆脱困境的机巧。以这一伦理混乱为中心,《云》剧后边的部分都在暗示因债务——债务源于父子之间的互不体谅——而不能继续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时,家庭需要面对的严峻情形。斯特瑞普西阿得斯火烧思想所以及斐狄庇得斯对其冷眼旁观表明,家庭一度面临崩溃局面,学成的斐狄庇得斯不但会成为父亲和母亲的敌人,也将成为城邦的敌人。
如果说斐狄庇得斯口中为父亲好就可以打父亲这一理由是牵强片面的,那么《马蜂》中儿子对父亲的暴力则完全是能够被观众理解的。菲洛克里昂热衷于审判和判人有罪,“他总是怒气冲冲地划一条长线,判处每个罪人以重刑”(《马蜂》:106),这正是其时大多数雅典公民的真实写照,公民友爱因审判得严厉而退居一旁,雅典民主的政治环境因此变得严苛。菲洛克里昂的爱审判病(νóσον)祛除了公民友爱,同时也削弱了家庭内部的友爱,作为儿子的布得吕克里昂不得不把父亲关在房子里,时刻派人看守,并在必要时刻和父亲搏斗。通过菲洛克里昂和布得吕克里昂的冲突,阿里斯托芬表明,如果家庭不能治疗排挤公民友爱的政治爱欲病变,那么家庭和城邦的分裂一定不可避免。最终菲洛克里昂的爱审判病被治愈,家庭矛盾就此平息,友爱也得以回归。
直观来看,《鸟》(″Oρνθες)剧中的儿子形象比《云》剧和《马蜂》中的两位儿子要极端得多。这位逆子明目张胆地说,“热望掐死爸爸,得到他的一切(γχεινπιθυμτòνπατρακαπντ’χειν)”(《鸟》:1352)。和菲洛克里昂相似,他也患了爱欲病,“我成了爱鸟狂(ρνιθομαν),我想飞”(《鸟》:1344)。《鸟》剧中的鸟群隔开了诸神和人类,这位逆子希望和鸟一样,能够飞到天上,凭借自己的血气(θυμóς)和诸神比高,最终他被建议去边疆和色雷斯人战斗以疏泄怒气——对缺失友爱的弥补方案就是把取代友爱的怒气转移到敌人身上去,此举的方便之处还在于它很可能会拉近父子之间的关系,从而呼唤家庭内部友爱的回归。
阿里斯托芬谐剧中家庭共同体的分裂迹象不仅仅靠诗人对父子关系的书写来表达,如《云》剧所表明的,夫妻之间的不和也是导致家庭共同体分裂的原因之一。这集中体现在《吕西斯特拉特》和《公民大会妇女》中,两部谐剧的女主人公和她们的丈夫针锋相对,家庭矛盾得以激化,阿里斯托芬对这些情节的建构部分源于对古希腊一般妇女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思考。而如《吕西斯特拉特》所示,谐剧结局虽然是泛希腊式的,但家庭友爱也得到强调:“让妻子陪伴丈夫,丈夫也留在妻子身旁”(《吕西斯特拉特》:1275)。总的来说,家庭共同体分裂的根本原因是家庭内部友爱的消失和随之而来的各种爱欲病变——如爱马病、爱审判病和爱鸟病,其最终后果则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共同体的崩坏。
思想所:雅典城邦的危机
苏格拉底(Σωκρτης)之死被多数人认为是证明雅典民主制具有严重漏洞的重要证据,苏格拉底因“引入新神”和“败坏青年”两项罪名被处死,透露出雅典公民对看似遥远荒谬的真理的不解,苏格拉底被认为培养了分裂城邦的政治家,这从《云》剧也可见一斑。
《云》剧中的苏格拉底被施特劳斯(Leo Strauss)称为青年苏格拉底,原因在于这个时期的苏格拉底尚不够成熟,他专事自然科学研究,不顾生活事务。他和他的思想所(φροντιστριον)虽处在城邦之内,但平日里与外界隔绝,即使是在思想所内部,苏格拉底也高高地挂在吊篮里研究天上的事物,这让斯特瑞普西阿得斯感到既惊讶又迷惑,这正是雅典传统公民面对当时逐渐庞大的智者群体所表现出来的最真实的反应。也就是说,《云》剧中的苏格拉底不是那个被雅典民主审判的苏格拉底,《云》剧中的苏格拉底只是带上了后者的一点影子,阿里斯托芬更多的是想在雅典观众面前展示智者的样貌。
《云》剧中,当斯特瑞普西阿得斯劝儿子斐狄庇得斯前往苏格拉底的思想所求学时,他说,
“如果你关心爸爸的吃喝,
就抛开了你的车马,前去入学。”(《云》:106-107)
“前去入学”的古希腊语原文是“τοτωνγενομοι”,这和柏拉图在《王制》中的一段话产生了重叠。《王制》第六卷中苏格拉底说,“属于这个群体的极少数人(τοτωνδτνλγωνογενóμενοι)已经尝到了拥有哲学的甜头和幸福,已经充分理解了民众的疯狂”(《王制》:486c)。《云》剧中的“思想所(γενο)”和《王制》卷六上述“群体(γενóμενοι)”源于同一个词,这意味着《云》剧中的思想所可以被视为一个共同体,苏格拉底、凯瑞丰等思想所成员确实被描绘得像一个小的哲人共同体——一个关于哲学的帮会中的人。像其他许多帮会一样,斯特瑞普西阿得斯进入思想所学习之前需要举行入会仪式,“这个帮会像雅典的许多hetaireiai(同志会),其实践活动被看作背离宗教信仰、亵渎神明、不可知论或‘追求摩登’”(珂娄斯特,2005:126)。在阿里斯托芬和雅典城邦中的多数公民看来,正是这个帮会在雅典城邦的分裂过程中推波助澜。
促使雅典人判处苏格拉底死刑的主因是具体的政治事件和政治行为,比如雅典人对苏格拉底的两项指控,它们在阿里斯托芬的《云》剧中都有所体现:引入新神:云神;败坏青年:歪理代表的修辞术。对雅典人来说,“要弄清楚的问题通常不是被告是否真的犯了被指控的罪,而是在普通陪审团公民中的大多数看来,他的罪是否对共同体之善造成伤害”(卡特莱奇,2016:86)。苏格拉底被认为不虔敬,破坏了人神关系,因此威胁到城邦的传统根基,这样一种对城邦根基的公然违抗必然使得雅典公民对他痛下杀手,尤其是当大家回忆起克里底亚(推翻雅典民主的僭主之一)和阿尔喀比亚德(被怀疑于前415年摧毁赫尔墨斯神像,在雅典和斯巴达之间数次变换阵营)都曾受教于苏格拉底时,他们对审判的热情便更加高涨了。
但《云》剧并非完全是对现实中的苏格拉底的恶毒攻击,和克里底亚以及阿尔喀比亚德受教于苏格拉底相似的情节是斐狄庇得斯在思想所里被教授修辞术,但阿里斯托芬明智地让苏格拉底请出正理(τòνκρεττον)和歪理(τòνττονα)来自由辩论,至于斐狄庇得斯要不要学习修辞术,最后由他自己决定。《云》剧中的这一细节暗示,苏格拉底并非雅典公民认为的那样专事败坏青年之行,克里底亚和阿尔喀比亚德伤害共同体的行为完全是由他们自身的血气造成的,学习修辞术只是他们达到目的的便利手段之一。
由此引出来的便是阿里斯托芬对前5世纪雅典城邦民主政治的看法——智者群体的出现为雅典人日益扩张的帝国主义热情提供了便捷手段,“和平与富足的愿景与无限帝国欲望的统治相吻合”(Konstan, 1995:30)。在公民大会上,狂热的、充满血气的政治家可以凭借修辞术说服听众,从而为如西西里远征一类的军事扩张提供条件,如奥里根(O’Regan)(2010:1)所说,“言辞……日益成为政治权力的媒介”。更加荒谬的是,智者群体主要从事对富有的青年的修辞术教育,因为穷人没有能力支付学习费用,而这些富有的青年又大多是对扩张有着爱欲的个体,学成之后,他们在公民大会上的讲演毫无疑问会鼓动其他有着扩张激情的参会者。与此同时,更多传统的、保守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还在遥远的乡下耕种做工,他们在学习修辞术和参加大会上既没有金钱也没有时间。尤其是在斯巴达对雅典卫城周边地区进行扫荡之后,这些穷人不但失去了住所,还损失了辛辛苦苦耕种的庄稼,参加公民大会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奢求。这样一来,雅典城邦就出现了一种恶性循环,那些能够提出反对意见的群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忙于自救,而公民大会上的青年们则继续从事使前者备受煎熬的扩张。
正是《云》剧对这一幕进行了预告,继承了母亲骄奢习性的斐狄庇得斯拒绝其父亲式的节制,“渴望自由是他挥霍放纵的原因”(尼柯尔斯,2007:13),他对赛马的热情体现了其对自由的爱欲,和菲洛克里昂所患的爱审判病以及《鸟》剧中那位逆子所患的爱鸟病相似,斐狄庇得斯患的是爱马病,即“ππερóν”。这个词由“马”(ππος)和“爱欲”(ρος)组成,其中后缀“ερος”常用于表示疾病的词中,如“水肿病”(δερος),阿里斯托芬借“爱马病”这个词表明,斐狄庇得斯在进入思想所之前就已经患了爱欲病。后来斯特瑞普西阿得斯火烧思想所的时候,斐狄庇得斯离开思想所进入城邦,将他的爱马病和殴打父母的逻辑带入城邦,激进的爱欲将使他在公民大会上无所畏惧,而如他自己所说,
我懂得了这种美(δεξιος)语言新(καινος)技巧,
能够藐视既定的法律(καθεσττωννóμωνπερφρονεν)真是一件快事!
记得我以前只爱玩马的时候,
说不上三个字就要闹笑话……(《云》:1399-1402)
他的爱马病很可能会被治愈,但那种爱欲病的症状又将转移至他处——爱诡辩修辞的病。如施特劳斯(Leo Strauss)所说(2011:54),“苏格拉底还没有彻底收服他,让他心甘情愿地过那种极端自制和忍耐的生活。他从苏格拉底那里学到的是,他相信赛马生活能够获得的东西,可以凭借演说术轻易获得:他还没有学会用苏格拉底的目标取代自身的目标。苏格拉底的魅力只是把他转向歪理主张的生活方式”。斐狄庇得斯自认成功,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学成了可以使狂妄合理化的修辞术,事实上,他和柏拉图在《会饮》(Συμποσον)中描述的阿尔喀比亚德一样,在苏格拉底的教育中只走了一半的路,因此这两个人在城邦中扩展着他们的爱欲病。“形形色色的蛊惑人心的政客,赐地业主,自由民和帝国主义者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行为和他们本人的欲望完全一致,他们不受团体的约束。这种约束本可迫使他们掩饰自己的真实欲望”(路德维希,2013:7),后果就是城邦不得不忍受一大批这样的青年对它的破坏。
斐狄庇得斯不但证明自己能打父亲,还可以殴打母亲,这表明思想所代表的智者群体及其修辞术对城邦造成了巨大伤害,但阿里斯托芬并未止步于此,他让斐狄庇得斯悄悄退场,然后进入城邦,提醒观众城邦即将需要面对的灾难。换句话说,《云》剧的重点不在于谴责苏格拉底、思想所或者智者群体,而在于对患了各种各样爱欲病的年轻人的鞭挞。柏拉图笔下的高尔吉亚曾举了一个关于体育锻炼的例子,他说,一个人在摔跤学校和健身馆练就了打拳和摔跤的好本事,然后回家后用这身本事殴打自己的亲属好友,大家不会去谴责教给他们这身本事的老师,而是会谴责没有正当利用这本事的打人者,他对苏格拉底说,“相同的论证也可以用于修辞学……人们应当像对待体育才能一样适当地使用修辞学……是这个滥用修辞学的人应当受到厌恶、驱逐,乃至于处死”(《高尔吉亚》:457a-457c),高尔吉亚的类比并不一定恰当,但在阿里斯托芬的逻辑里,患了爱言辞病的雅典青年的确应当被净化,否则城邦一定会面临灭顶之灾。
追打“正义城邦”:泛希腊共同体的危机
“它真正是伟大的,你们应当热爱它”(修昔底德,1960:152),在前430年发表的纪念阵亡将士的葬礼演说中,伯里克利(Περικλς)将雅典人对母邦热爱的原因归结为雅典是伟大的,在他的逻辑里,雅典是伟大的,所以它值得雅典人热爱,由此城邦的自然属性——为了公民更好的生活——被抹除了。城邦的自然属性将雅典和其他城邦放置在同一种类型之下,雅典人则隐藏了这种自然性,因为“自然破坏了城邦希望了解自己的方式”(Mhire,2014:55),雅典人代之以卓越的外衣,并将其发展成激进的爱国主义,“爱雅典,是因为雅典卓越,而不是因为雅典属于自己。伯里克利这个选择在逻辑上导致雅典勇于和其他城邦竞争……具有爱欲特性的爱国主义意味着帝国主义”(路德维希,2013:419),于是雅典人因为热爱雅典而意欲使它更加伟大,而雅典更加伟大的前提就是使其他城邦虚弱,当时正值斯巴达同盟入侵阿提卡,雅典和比雷埃夫斯城又爆发了瘟疫,这些都使得雅典人的爱国主义和仇外主义联系在一起。“阿里斯托芬察觉到隐藏在表象之下的对和平普遍而深切的渴望,于是他独自把它公之于世”(Hugill, 1936:2)。
这便是《阿卡奈人》(’Aχαρνες)中由阿卡奈人组成的歌队追打狄凯奥波利斯的原因。狄凯奥波利斯对阿卡奈老人们说:
因为我知道
这些农民的脾气:有什么骗子
夸他们和他们的城邦,他们就非常
得意(χαροντας),不管夸得有没有道理(δκαια)。(《阿卡奈人》370-3)
这正是伯里克利讲演中那种虚荣自负的心理状态,狄凯奥波利斯指出这些来自雅典城邦、旧时的马拉松战士只愿意沉浸在雅典过去的光荣中,现在他们对城邦事务的参与也仅限于去公民大会上领发放的3个奥波尔,他们对雅典当前的处境只知大概——雅典受到斯巴达的威胁,这种状况被狄凯奥波利斯视为“没有道理”、不公正——即非δκαια。这呼应着在第三场对驳中狄凯奥波利斯作为阿里斯托芬代言人时所说的“正义(δκαιον)”,他向观众诉说:
我,一个穷鬼,写喜剧,
想对雅典人谈论国家大事。
因为喜剧也懂得正义(τòγρδκαιονοδεκατρυγδα)。
我的话会骇人听闻,但却正当(δκαιαδ)。(《阿卡奈人》:498-501)
借狄凯奥波利斯之口,阿里斯托芬表明,作为城邦的教育者,他有责任指出城邦的不义,这正是谐剧诗人的正义,即使这种正义曾使自己遭到克里昂的恶毒攻击。狄凯奥波利斯继续说,克里昂曾批评他当着外邦人的面诋毁(κακςλγω)自己的母邦,这同样呼应了深入雅典人心的伯里克利式爱国主义思想,狄凯奥波利斯对此感到绝望,所以才私下和斯巴达达成和平条约。事实上,狄凯奥波利斯并没有诋毁雅典,他对此给出解释:
我对斯巴达人满怀仇恨,
但愿波塞冬,泰那罗海角上的神明,
把房屋震塌到他们所有人的头上
……
这事情我们为什么要怪斯巴达人?
我们中间有些人,我不是说城邦(οχτνπóλινλγω)——
请你们千万记住,我不是说城邦(οχτνπóλινλγω)——
而是说一些坏分子,不务正业的
没有人格的造假的告密者。
他们一看见墨伽拉小斗篷就告密。(《阿卡奈人》:509-19)
狄凯奥波利斯为了区分城邦和城邦公民,在这里连用两个同样的否定,阿里斯托芬借此提醒观众,让城邦更加伟大的方式不止一种。狄凯奥波利斯提到前432年雅典对墨伽拉进行的经济封锁,这和之后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给阿卡奈人造成了难以言说的痛苦,据他说,这场战争起源于雅典城邦中一些喝醉了酒的年轻人,他们抢了墨伽拉的妓女西迈塔,墨伽拉人反过来又掳走了伯里克利的情妇阿斯帕西娅的两个女奴,于是伯里克利发布禁令,宣布对墨伽拉进行经济封锁。这一连串事件的后果就是作为墨伽拉盟友的斯巴达开始了对雅典的侵扰。狄凯奥波利斯据此断言,战争的主要源头是雅典而非斯巴达。结果一半阿卡奈人被他说服,就连随后赶到的、对从事战争具有极大热情的拉马科斯也被打败。
狄凯奥波利斯把阿卡奈人遭受的不幸归因于他们自己的虚荣和浅见,对雅典人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对雅典优越性的修辞性吹捧”(普拉多,2016:15),而雅典的这种优越性则部分源于希波战争,所以阿卡奈人歌队中这些参加过希波战争的老人感觉受到了狄凯奥波利斯的冒犯,他们看上去是因遭受斯巴达军队对他们生活的破坏而愤怒,其实他们愤怒的原因是不能容忍狄凯奥波利斯对雅典统治权及其以往荣誉的质疑。雅典曾在希波战争中带领希腊盟军战胜波斯,这一伟大时刻对任何一个雅典人来说都是不能忘记的,伯里克利在葬礼演说上鼓动雅典人让城邦更加伟大时利用的便是这种心理。这种心理发挥了实际作用,当时哪怕是雅典城内不同的利益团体,都默认雅典的伟大,也默认了雅典迈向帝国的合理性。
和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类似,柏拉图的《美涅克塞努》(Μενξενος)也是一篇演说词,苏格拉底复述了老师阿斯帕西娅的演说,巧合的是,这位苏格拉底声称是自己修辞术教师的阿斯帕西娅正是伯里克利的情人,伯里克利及其富有鼓动性的讲演除了受到普罗塔哥拉(Πρωταγóρας)等智者的影响,更直接受到阿斯帕西娅的影响。这两篇演说的相似性就在于它们都赞颂了雅典以往的功绩,表面上看苏格拉底历陈雅典城邦的丰功伟绩以显示其伟大,实际上从苏格拉底对这些事件的陈述顺序上看,整篇演讲词显示的不是雅典的伟大而是它的衰落。从单独对抗蛮族的、真正伟大的马拉松战役,到雅典和斯巴达联手战胜波斯的普拉提亚战役,再到由竞争压力和嫉妒引发的恩诺斐塔战役,最后到西西里远征,“雅典取得的胜利越来越微不足道……雅典自己正渐渐开始与整个希腊世界相对立”(普拉多,2016:21),雅典人固守着自以为是的正义感并将其发展到这样的地步:雅典人为了希腊的自由而反抗希腊。这一逻辑正是阿尔喀比亚德爱国的逻辑——为了雅典好就可以攻打雅典,这也是阿里斯托芬谐剧中经常出现的情节——为了父亲好,儿子就可以打父亲,到最后,雅典城邦树敌无数,“哪怕是整个世界都来攻打她都不能取胜”(《美涅克赛努》:243d)。
如《阿卡奈人》中狄凯奥波利斯(Δικαιοπολις)的名字所显示的,他代表着“正义的城邦(δκαιοςπóλις)”,阿里斯托芬借此说明,“在进行战争的城邦之中有和平之城、正义之城,其特点是其隐私和对家庭、地方以及节日的忠诚”(Edmunds,1980:32),在剧中的空间移动体现了他对城邦边界的漠视。“阿里斯托芬允许他抹去城墙,这是该剧明确的‘主要意见’的本质”(Nelson,2016:124),这一正义城邦的形象与其时大多数雅典人心中正义城邦的形象并不吻合,后者心中正义城邦的形象正是流传了许久的伟大雅典形象,他们不愿看见也不愿接受雅典民主与城邦正在衰落的事实,所以他们化身为年老的阿卡奈人追打狄凯奥波利斯这一“正义城邦”。和大多数濒临崩溃的共同体一样,阿卡奈人歌队未能意识到“强权政治给命运共同体带来的灾难甚至是文明的倒退”(周丽秋,2021:44)。阿里斯托芬借狄凯奥波利斯之口说出的劝告并没有将雅典人从疯狂的伯里克利式爱国主义的热情中拉回来,所以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继续创作关于雅典城邦和泛希腊共同体的谐剧,《和平》《吕西斯特拉特》和《公民大会妇女》更明显地构建了泛希腊共同体,在这3部剧作中,雅典人和异邦人通力合作,最终完成了对仇外主义的剪除和对泛希腊共同体的构建。
结 语
从家庭到城邦再到希腊,这构成了垂直方向上的共同体攀升运动,虽然亚里士多德强调家庭对城邦的重要作用,但阿里斯托芬对这种重要性着墨不多,在激进派主导下的民主政治体现出来的危害使诗人对城邦政治生活始终保持警惕,所以他让谐剧中的主人公们退回到前城邦时期的乡镇或家庭共同体中,以保守的姿态中和当时民主派的激进爱欲。《阿卡奈人》中的狄凯奥波利斯最后离开混乱的城邦回到乡间操办酒神节;《骑士》(Iππες)中的主人公德莫斯(Δμος,“乡村;民众”)最后也回到乡下,推翻并躲开了急进地克里昂。然而,对那些罹患爱欲病的雅典人来说,阿里斯托芬“徙民入乡”的决策及其带来的平凡的快乐缺乏吸引力,这是因为他们缺乏对公民友情的理解力和对历史变化的反思,也缺乏那种阿里斯托芬式的“智慧力量”和旧谐剧式的“文化力量”(Major,2006:133),这些人不但脱离了家庭,还将其爱欲病变扩展至城邦间的公共政治层面,他们热切地攻击、敲诈和占领雅典周边的弱小城邦,直到最后使雅典与斯巴达同盟对抗。在他们暴力的帝国主义思想中,没有体现出丝豪对阿里斯托芬喜剧中泛希腊共同体的怀念,雅典城邦及其民主衰落到无法挽回的地步时,他们才慌乱地将矛头对准雅典内外一切可以被责备的对象。
注释:
① 文中引用的古希腊戏剧皆出自阿里斯托芬. 2007. 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第六卷-第七卷)[M]. 张竹明,王焕生,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下文只标注剧名和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