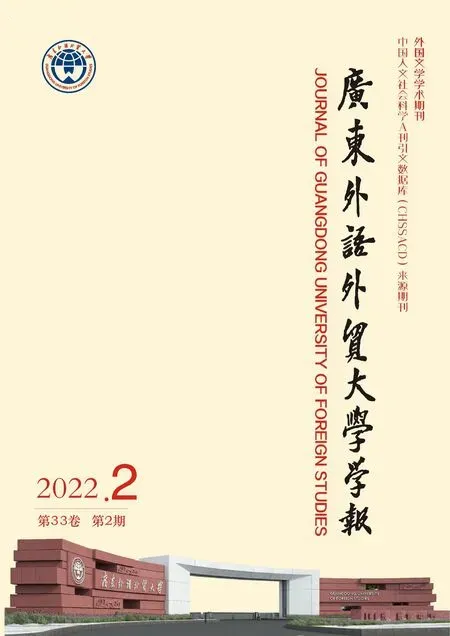《奥罗拉·李》:诗歌与女性身份
2022-12-01霍红丽
霍红丽
引 言
伊丽莎白·巴莱特·布朗宁 (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最著名的诗人之一。在19世纪中期已成为与丁尼生平起平坐的一流诗人,在1848年拉斐尔前派社评选的不朽诗人名单中,她是唯一的女诗人,更是当时桂冠诗人的有力角逐者(Stone,etal.,2006:391)。她的诗歌作品回应了当时的社会政治问题,并致力于探讨在男性诗歌传统中成为一个女诗人的含义。发表于1857年的著名小说体长诗《奥罗拉·李》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叙述女诗人成长的长篇巨作,进一步提升了布朗宁的国际盛誉(Stone,etal.,2006:392)。在这部诗作中诗人表达了对生活和艺术最为崇高的信念。作为一个成功的诗人和幸福的人妻及母亲,她的个人经历有效地论证了艺术和女性身份的兼容性。本诗主要讲述奥罗拉·李作为一个女诗人的成长过程,她对自己女性身份看法的改变是其成长的重要标志之一。
这部小说体长诗一经发表就得到同时代评论家的高度赞扬,但一些评论家认为这首诗的情节模糊,甚至有人指责诗中对女性角色的描绘太具有冒犯性。后来的评论家对诗歌形式和内容从比较研究、性别差异、艺术与政治的关系等多个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大多数评论家将这首长诗看作女性主义的名作,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部诗作一直是女性主义批评的重点文本。批评家关注布朗宁作为一名维多利亚中期女诗人的脆弱地位,从无法找到文学创作上的女前辈,到如何创作出新诗歌,从多个角度分析了女诗人的诗歌观点以及女主人公对自己女性身份的认可过程,认为这是女性主义自我发现和肯定的过程。
20世纪80年代以来,评论家重点关注诗中女主人公的成长过程,从多个角度分析对女性身份的接受过程。芭芭拉·盖尔皮(Gelpi,1981)通过深入分析诗中其他人物,揭示了奥罗拉如何逐渐改变对女性身份的看法。乔伊斯·佐纳纳(Zonana,1989)从如何逐渐成为她自己的尘世缪斯这一角度探讨了奥罗拉作为一个诗人的成长过程,奥罗拉之所以可以实现这样一个目标,正是在于她完全接受自己作为一名女性和一位艺术家的身份。艾莉森·凯斯(Case,1991)探讨诗人性别角色与叙事方式转变的关系。诗的后半部分自信和艺术能力的衰弱表明,除了诗歌成就,奥罗拉还有情感上的追求。情感满足的过程也是她对女性身份的理解逐渐成熟的过程。
2000年以来,评论家将《奥罗拉·李》置于诗人的创作历程中分析布朗宁的成长过程。近年来逐渐关注女性生活体验的核心作用和诗人的艺术观,比如探讨女主人公如何逐渐参与城市生活体验而符合自己的艺术观(Erbeznik,2014),但是未能从变化的观点理解《奥罗拉·李》中女主人公诗歌观点的发展过程。
在以上重要观点的启示下,本文基于奥罗拉的诗歌观点,分析了奥罗拉逐渐接受女性身份的成长过程。根据时间脉络,这一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奥罗拉认为诗人的性别是男性,诗歌是男性的专属,女性被排斥在这一传统之外,因而若要成为诗人,必须伪装自己的性别,拒绝女性身份;第二阶段,她提出诗人需具备双重视角,个人生活是必要条件,因而接受了自己的性别;最后一个阶段,奥罗拉结合斯韦登伯格关于物质和精神世界、今生和来世的学说,指出诗人实际上具有双重性别,情感生活也是极为重要的,因而终得完整身份。
消极的女性身份观
(一)诗歌是男性的艺术
这首诗的主要角色为女性,但对其描述多为消极的观点,尤其是在诗歌的前四卷。这与奥罗拉关于诗人性别的看法是紧密相连的。
父亲去世之后,姑妈获得奥罗拉的监护权,自此对她进行传统的女性教育,这个过程使她备受煎熬,只能从书中获得片刻慰藉。多年来通过阅读父亲收藏的书籍进行自我教育,“最终时机成熟/偶遇诗人”(Browning,1864:40)。接着奥罗拉表达了自己不成熟的观点。在第一卷诗行910-914,奥罗拉高度称赞诗人对人类的重要性,指出诗人是说真话者,拥有一种警醒的力量,可以赋予尘世生活庄严性。通过频繁使用第三人称“his” “he” “him”, 奥罗拉将诗人描述成一个男性;在第920行使用雷的意象来形容诗人的力量。地球象征女性的被动特性,而雷电则代表男性力量(Mermin,1989:51)。奥罗拉认为诗人是男性,作为一名女性她被排斥在诗歌传统之外。
此外,诗的开头通过呼应其他同时代作品,强化了女性不能成为诗人的观点。男权社会坚称女性属于家庭生活,她们应该接受和承担这样的天使角色。谈到姑妈对她的教育,奥罗拉提到她阅读了很多关于女性的书籍,那些书籍大胆宣称女性应该理解丈夫话语,永远不要驳斥他人或说“不”,应具有“天使般的美德”(Browning,1864:21)。对这些书籍内容的描述影射了维多利亚时期的多部流行作品,反映了男权社会中的女性地位。
仇小萌(2017:86)在描述维多利亚时期的两性关系时指出,女性终其一生被困守在花园和家庭中,其全部价值体现在对家庭的奉献中。莎拉·埃利斯(Ellis,1839:63-64)曾在书中哀叹女性品格的衰落,并表达了一种颇为普遍的观点,即女性的活动范围应该在自己的炉边。她进一步强调,一个女人最有价值、最令人钦佩和最受爱戴的是她无私的善良,而有学识和有成就的女人,如果没有道德上的伟大,就不能成为最令人钦佩的对象。此外,“天使般的美德”一词呼应了康文垂· 帕特莫尔(Conventry Patmore)发表于1854年的《房中天使》(“Angel in the House”)和布朗宁信件中的“她是天使”(“angelic she is”)。她在信中指出“(每个)男人都跪在拿着棉绒的女士之前,称她们为天使,而如果她们作为思想家或艺术家有所作为(涉及对普通人类的更多好处而不是涉及棉绒),同样的男人会谴责她们的无礼……”(Kenyon,1897:189)。当奥罗拉向罗姆尼宣布她的诗歌使命时,他戏弄并无情地否认她的写诗能力。罗姆尼深信关于女性家庭角色的惯例。此外,女性对事物的理解基于自己的生活体验,无法反映社会问题,因而缺乏社会价值(Barrow,2015:243)。当被奥罗拉拒绝时,罗姆尼妥协道:“写女人的诗句,做女人的梦 / 但让我在家中感受你的香味”(Browning,1864:95)。女性可以有所追求,但不可伤害传统的“房中天使”身份。这与其说是许可不如说是限制。科拉·卡普兰 (Kaplan,1978:9-15)认为这是对女性进入公共话语的偏见,尽管在19 世纪中叶女性作家的涌现打破了这种禁忌,但她们因敢于谈论不适合“房中天使”的话题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受指责。
布朗宁(1898:231-232)曾哀叹道,“在伊丽莎白时代以及之后,英国有许多博学的女性,不管是读者,还是博学的作家……然而,女诗人在哪里……我到处寻找前辈但一无所获”。同年的信件中她将女诗人的缺乏解释为:“女性在心灵上存在一种天生的不足——智力……而艺术史和天才史则证明了这一事实”(Browning, 1898:116)。然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Mill,1991:545-549)认为,女性从未在哲学、科学或艺术领域创作出一流作品,原因在于她们接受到的教育使其只能成为“业余艺术家”。
在成长的第一阶段,奥罗拉将诗人描绘成男性,通过频繁呼应其他作品,布朗宁强化了奥罗拉的这种想法,强调女性不应该拥有任何伤害她女性身份的艺术追求。
(二)拒绝女性身份
女性传统身份包括女性特征(womanliness)和性征(sexuality)两个方面(郑成英,等,2014a:93)。在作为诗人成长的早期阶段,奥罗拉将诗人描绘成男性,并通过影射同时代其他的作品,强调女性不可成为诗人。她认为只有将自己看作男性拒绝成为“房中天使”,方可实现诗歌创作的使命。男权社会中男性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上,更是在心理上压制女性(刘岩,2011:9)。布朗宁有着和诗中虚构的女诗人相似的心态,她曾极为排斥自己的女性身份。
奥罗拉将诗歌描绘成男性的艺术,为了追求诗歌使命,她唯有将自己伪装为男性并逃离传统的女性生活,似乎这样她才能成为一名诗人。芭芭拉·盖尔皮(Gelpi,1981:38)关注奥罗拉对诗中其他女性角色的看法,探索她对女性逐渐成熟的认识。她认为在奥罗拉成长的早期阶段,关于诗人的看法使她尽可能摆脱作为英国年轻女性的传统生活,并将自己视为男性。当谈到克服困难独自发展诗歌能力的勇气时,她将自己描绘成一头鹿,一头雄鹿而不是雌鹿;在第三卷,当瓦尔德玛夫人拜访奥罗拉时,她称自己为“lion-hunter” (Browning,1864:134)而不是“lioness-hunter”。除了使用隐喻,奥罗拉坦率地用“his”来形容自己,将自己看作男性诗歌前辈中的一员。
为了成为一名诗人,她必须“杀死”“屋子里的天使”,这种传统的完美女性是任何艺术追求的障碍。奥罗拉拒绝传统生活的第一个方面体现在她对教育的不同看法。自从母亲去世后,奥罗拉的父亲就承担了教育她的责任。忆起父亲教导自己希腊语和拉丁语时,奥罗拉通过与年轻的阿基里斯比较来描绘自己的处境。阿基里斯为了躲避特洛伊战争的征召被他的母亲藏在女装里,而她却被父亲披上男装, 接受了传统上认为不适合年轻女士的教育。
父亲教了奥罗拉古典语言,这为她的诗歌创作奠定了基础。父亲去世之后,姑妈让奥罗拉接受传统的女性教育比如音乐、舞蹈、绘画、女工。在她看来,姑妈的教育是一种折磨,并强调她并非例外,许多其他的年轻女性也忍受了极度的痛苦,只不过她的痛苦源于本性。姑妈对她的教育是为了培养她成为顺从丈夫的理想妻子(Dalley,2006:531)。虽然姑妈断然反对,奥罗拉继续阅读父亲留下的书籍,不考虑是否适合或对自己是否有益,以此抗争这种传统的女性教育。19世纪中期,很多中产阶级的知识女性关注女性社会价值,对这种取悦男性的教育十分反感。
诗歌传统上是男性的领域,女性的特征体现在爱情、婚姻和家庭(郑成英,等,2014b:22),这就是为何当奥罗拉拒绝罗姆尼的求婚时,她对传统生活的拒绝达到顶峰。罗姆尼认为,无私的服务是奥罗拉或任何女人唯一可以胜任的。闻言,奥罗拉反驳道,罗姆尼爱的不是女人而是事业,他要的不是妻子而是帮手;而且,他已经娶他的社会理论。她坚称“我也有自己的使命——工作要做”(Browning,1864:77)。值得注意的是,奥罗拉拒绝的不是婚姻本身,而是妻子在无爱婚姻中的从属角色。约翰·斯图尔特·密尔(Mill,1991:502-503)透露,婚姻是社会赋予女性的唯一命运,所有人都应该寻求婚姻;婚后他们被迫承担从属角色。罗姆尼让奥罗拉以妻子的身份为自己服务。奥罗拉拒绝他的求婚是意料之中的。瓦尔德玛夫人认为女性作家不同于普通女性,她们被剥夺了情感需求或传统的女性生活,以便她们能够超越普通女性并成为一名艺术家。
由于奥罗拉认为诗人是男性,女性身份是诗歌创作的障碍,在这首长诗的前四卷她对其他的女性角色表达了相当消极的看法。在第一卷,她使用天使和女巫、缪斯和美杜莎等一系列自相矛盾的意象来描绘母亲的画像。纵观全诗,这种描述可以看作奥罗拉对女性身份本身的看法:作为一名女子,如果想成为诗人,“社会所赋予的母亲角色是艺术追求的一把利剑,让其难以实现”(Gelpi,1981:35)。她的姑妈被称为母亲的仇人因而对奥罗拉也是相当冷漠;玛丽安·尔勒的母亲残忍无情;露西·格雷沙姆的祖母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极为冷酷的人;瓦尔德玛夫人是整首诗中最大的反派角色,在前四卷中,她已经被描绘成一个狡猾的女人。
自我性别认同
(一)诗人应具有双重视角和双重生活
第五卷是第二阶段的关键,在这卷中奥罗拉依然将诗人描绘成男性,仍持有这一根深蒂固的观点。然而,成长不可忽视,奥罗拉对诗歌的看法开始具有一定的女性特色。
在第五卷,奥罗拉表达了自己的艺术观,指出在当代创作史诗的可能性,安吉拉·雷顿(Leighton,1986:140)称之为“想象的当代性”来强调当代社会的史诗价值。奥罗拉的辩护有3个方面:首先认为当代社会亦可出经典;然后进一步指出任何时代都有产生英雄主义的可能性;最后强调诗人能意识到当代的英雄主义。诗歌应反映诗人自己的时代精神,有精神才有活力。奥罗拉运用“双重视角”“双重”等术语强调诗人具有识别当代社会英雄主义的责任,指出任何时代都能创作史诗。奥罗拉指出时代精神和力量可以通过女性意象“double-breasted”和“bosom”(Browning,1864:245)体现出来;而且诗人应聚焦当代的“客厅”来寻找诗歌主题。客厅是女性的专属领域,多萝西·梅尔曼(Mermin,1989:204-205)坚称这种看法暗示着真正的(更理想的)诗歌话题在于女性领域。在这首诗中客厅还是讨论政治的地方,这意味着传统意义上属于女性的领域可以触及家庭之外的话题。那么女性亦可承担家庭天使之外的角色。这一诗歌理论为女性参与诗歌创作提供了可能性。
“双重视角”是指看待问题的多个角度,比如当下和未来、个人和一般、诗歌和政治,强调了多个角度之间的差异和张力(Leighton,1986:109)。这可以解释女性和诗人的双重身份。诗人应具有双重视角和双重生活,诗人应具有从不同视角看待事物的能力,因此,女性的情感生活也具有诗性。诗人还应过着“双重生活”(Browning,1864:252)。这一概念意味着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艺术追求)相辅相成。诗人不能为了艺术追求而排斥生活经历,日常生活是诗歌创作的必要条件和创作源泉。在这首长诗的前四卷,奥罗拉认为自己的性别以及女性“房中天使”的身份是自己诗歌创作的一大障碍,因而伪装自己的性别,拒绝参与传统的女性生活;第五卷,她意识到生活体验是艺术创作的基础,虽然仍将诗人描述成男性,但此时奥罗拉意识到若要成为一名诗人,她应从不同角度看待自己的女性身份,接受自己的性别(be),才能够创作诗歌(do),取得成功。
(二)接受自己的性别,成为女诗人
奥罗拉对诗人和诗歌的观点逐渐成熟,强调双重视角和双重生活的必要性,成为一名诗人,不可能完全逃离自己的女性身份。在成长的第二阶段,奥罗拉不再将自己伪装成男性,她接受了女诗人的身份,用“我们女人”称呼自己,并意识到作为一名女诗人所具有的不足之处。在第二卷,罗姆尼认为女性不可以成为诗人的原因在于,女性太关注个性化的事物,无法像预言家一样口吐真言。第五卷奥罗拉开始意识到“我们女人”艺术创作的不足之处在于缺乏概括能力。
但是,当贺维勋爵提醒她“幸福的生活意味着谨慎的妥协”(Browning,1864:279)时,奥罗拉反驳道“为了艺术,不要多言”(Browning,1864:281)。再一次,奥罗拉拒绝参与传统生活的机会,不愿成为他人无私的妻子。艾莉森·凯斯(Case,1991:25-28)明确表示第五卷是一个过渡,自此诗歌的情节重点从艺术发展过渡到奥罗拉情感的实现,由于一直克制自己的情感需求和对罗姆尼的爱她成为不可靠的叙述者。到第五卷,奥罗拉历经挫折成为一名成功的诗人,创作出一部杰作,“看,最后,一本书”(Browning,1864:251)。但是,诗歌成就并不能带来充实的生活。社会压抑之下,女性即使冲破了家庭、婚姻等阻碍取得了成功,感受到的通常并非奋斗带来的喜悦,而是付出代价的苦痛(胡政敏,2003:58)。迪尔德丽·大卫(David,1985:132)在论及艺术对社会的服务时指出,奥罗拉通过比较女人猛烈的心跳和她诗歌的音步,暗示诗歌创作对于一名女诗人来说是不称心的,除非同时她也能得到爱。在第五卷,奥罗拉哀叹一个拒绝了传统“房中天使”身份的女诗人所承受的悲惨生活,书籍被世人称赞,而自己却无人所爱,远离了普通家庭生活的温馨,只能羡慕其他诗人享受的母亲般的甜蜜和家庭所给予的鼓励,“书籍获得成功,生活遭受失败”(Browning,1864:391)。奥罗拉在姑妈去世之后前往伦敦追求自己的诗歌事业,通过阅读报刊杂志等间接的生活体验创作出一部巨作,但是缺乏亲身的生活体验,不利于诗歌创作的进一步发展(Erbeznik,2014:623)。但是,作为一名成功的诗人,她逐渐能够完善自己的诗歌理论,并提升对自己女性身份的认识。
接受女性生活,获得完整身份
(一)诗人的双重性别
多萝西·梅尔曼(Mermin,1989:7-9,18-27,89,179) 指出布朗宁自孩童时就试图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诗歌传统中为女性谋得一席之地;少女时期对希腊有着不可遏制的狂热,后来基督教因有女性的参与取代了希腊神话在她心中的位置;19世纪50年代布朗宁热衷于斯韦登伯格主义和唯灵论,这一理论超越了国家、阶级、性别、甚至生死、人世和神灵。最终,她找到一个可以证明女性亦能创作诗歌的理论。
这首长诗的最后三卷是奥罗拉作为诗人成长的最后阶段,在这一阶段,布朗宁以奥罗拉之口提出了双重世界的观点。这一观点暗指斯韦登伯格关于物质和精神世界、今生和来世的学说。感性世界是精神世界的外衣,精神世界体现在物质世界中。换句话说物质世界总是与精神世界是对应的(Hawley,1937:205)。这样说来,感性生活是相当重要的,女诗人的情感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这首诗的主题是一位女诗人的成长,女性性别和传统的“房中天使”身份是诗歌创作的阻碍。在第五卷,奥罗拉已经成长为一名女诗人,但同时也强调拒绝传统女性生活所导致的悲惨境地。到第七卷,奥罗拉利用双重世界可以证明艺术追求和女性身份(尤其是感性生活)是兼容的;女艺术家不必逃离情感生活,过悲惨的生活;不仅人有双重的本性,诗人也有双重性别。
一方面,诗人的双重性别意味着诗歌能力不是男性专有的,女作家同样可以拥有,甚至在诗人创作的诗歌影响下,诗意人人可有。如果一个普通人可以通过感受到诗人的狂喜,认识到世界双重性,那么这个人就具备了诗性。比如,在这首诗的结尾处,罗姆尼在奥罗拉诗歌的影响下,意识到精神世界的重要性,并哀叹物质化的时代。罗姆尼也具有了诗人的觉察力。
另一方面,通过提出双重世界的哲学观点,奥罗拉不再将诗歌看作是男性的艺术,而是一种男性化的艺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男性化和女性化的特点。性别与性征的一致性,即性别二分法其实是人为的(丁少彦,2013:61)。奥罗拉同样进一步指出性别差异本身也是肤浅的,作为一个拒绝传统服务型女性生活的女诗人,她“不足以成为一名女子,也从来不是男子”(Browning,1864:404);“而男人/ 看呀!他们本性与女人无异/ 正如所有女子都是奥罗拉”(Browning,1864:405)。男子气概并非魔力,女子不可为诗人实际上是一种人为的偏见。诗人是双重性别,需要有双重生活,因此“女子的人生目标(或男子,我想)/ 都不是一本书”(Browning,1864:399)。作为一名成功的诗人,奥罗拉逐渐淡化对女性身体的描写,通过脱离实体(disembodiment)的方式逐渐超越(transcend)并升华女性身份,提出以女性为中心的诗歌观点(Barrow,2015:258)。从一个艺术家的视角来看,女性身份不再是一个讨论的重点,不再是诗歌创作的障碍,而是取得更大诗歌成就的必要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更具有优势。诗歌是一种双性文化,诗人应该超越自己的性别界限。
(二)拥抱传统生活
奥罗拉承认自己虽然取得了诗歌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但放弃传统的女性生活终究是错误的,牺牲女性生活而激情赞扬自己的艺术天性,忘却不完美的女性无法成为完美的艺术家。在第二阶段,奥罗拉强调诗人应具有双重生活,但她再次拒绝了倾慕者的求婚,因而并未达到这一标准。而此时奥罗拉意识到女性身份并不是障碍,无法接受自己的女性身份阻碍了她取得更大的诗歌成就,她成了过着悲惨生活的不完美艺术家。传统的女性身份是艺术发展的必要条件。若要成为更优秀的艺术家,奥罗拉必须接受自己的女性特征,同时作为一名成功的诗人,也逐渐意识到女性身份并不是诗歌追求的障碍。
在第九卷,奥罗拉承认并表达对罗姆尼的爱意时,最终成长为一名“完美的”女诗人(Zonana,1989:252)。奥罗拉对罗姆尼说“我爱你,罗姆尼”(Browning,1864:514),而且强调自己的爱不是同情,因为自己一直深爱着罗姆尼。值得注意的是,奥罗拉用了“一直”(always) (Browning,1864:514)来展示爱之深,同时也揭示了在之前的情节中她确实一直压抑自己的情感需求,欺骗自己两人之间并无爱意因而自己应全身心追求艺术。最终,二人携手走进婚姻。
奥罗拉逐渐意识到爱的重要性,这也改变了其对艺术的观点。在第二卷,奥罗拉坚定地认为没有诗人的影响,任何社会工作必定失败;在第七卷,她进一步指出艺术可以帮助改变世界;在诗的结尾,她表达了更为成熟的观念:“艺术重要,但爱更可贵……艺术象征天堂,但爱就是上帝”(Browning,1864:511)。这两句诗表面上通过赞美爱而贬低艺术的重要性。实际上奥罗拉认为,当人们内心可以直接感受到上帝时,艺术便成了多余的存在。同时,考虑到她一直改变关于诗人和诗歌的观点从而为女艺术家谋得一席之地,奥罗拉肯定不会有意破坏自己之前的努力。她意在证明爱的至高无上,从而强调只要不以牺牲人类的爱(情感体验)为代价,艺术追求本身不是错误(Hickok,1980:486)。最终,奥罗拉承认了自己的错误,重拾女性生活,并下定决心对自己的女性身份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日常生活不可或缺。在成长的第二阶段,她是一个女诗人;现在,奥罗拉是一名女子和女诗人,终得完整身份。
新颖但正统的诗歌观
(一)诗歌即生活
纵观全诗,奥罗拉作为诗人,其成长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最终证明女性身份和艺术追求是兼容的。而在整个成长过程中,有个观点一直未变,那就是,诗歌即生活。
布朗宁在1824-1826日记中指出生活对于诗人的重要性:“我越来越相信,平静的生活不是诗人的生活。他的思想应该永远像一棵年轻的树一样被移植。应让它在自由土壤中生根,而不是在角落里长草。看看我们伟大诗人的生活——莎士比亚的、弥尔顿的、拜伦的——并找出真相”(Mermin,1989:28)。结合布朗宁于1863年发表的随笔,可以看出诗歌即生活的观点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这一观点要求诗人应该有积极的令人兴奋的生活,因为“艺术需要完整的人”(Browning,1863:229);另一方面,这一观点强调艺术的活力,“诗歌应是诗人的生活,这是批判的真理而不是低级的看法”(Browning,1863:221)。论及希腊诗人和英国诗人时,布朗宁认为诗歌并未衰落,在书的结尾赞扬了华兹华斯的诗歌,认为他诗中的概念以及措辞生动有力,是诗人生活的见证(Browning,1863:228)。华兹华斯的诗歌就是生活,论其诗,必谈其人生。
对于诗歌与生活的认识体现了奥罗拉作为女诗人的成长过程。在诗歌的前3卷,奥罗拉将诗人描绘成男性,认为自己的女性身份是诗歌创作的障碍,因而将自己伪装成男性,为了支持自己这一论断,她强调诗歌就是生活,但艺术是“更大规模,更宏伟的生活”(Browning,1864:231)。在她看来,只要可以捕捉生活的本质,拒绝女性身份也是合理的。第四卷,罗姆尼提醒奥罗拉为了艺术把握人生,然而由于自己对诗歌的理解还不成熟,并不能意识到现实的情感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必要条件。第五卷,奥罗拉运用女性意象描写当下,因为当代的女性力量对艺术创作极为重要,后世定会钦佩不已并称为“活着的艺术/因而展示并记录了真实生活”(Browning,1864:245)。真正的诗歌必须饱含生活气息。然而,当贺维勋爵说道,对于女诗人,幸福人生需要在艺术和传统之间做出谨慎妥协,她失态大喊:“为了艺术,不要多言”(Browning,1864:281)。奥罗拉意识到诗歌即生活这一真理,但是自己却没有做到这点。在第七卷,她对诗人的看法已然完善,修正了最初关于艺术是更宏伟生活的论断,“艺术本身/ 我们称之为更高的生活,必须感受生活之精髓/ 经历生活”(Browning,1864:399)。这一观点既强调生活是艺术的条件,又指出艺术应有生命力。值得注意的是,第七卷之后,奥罗拉再也未提及诗歌即生活这一关系;一旦接受自己诗人与女子的完整身份,无须再提。
在这首诗中奥罗拉·李自始至终坚称诗歌就是生命,这一观点一方面强调诗歌创作不能以放弃常人的生活为代价,另一方面指出评价诗歌的一个标准就是看其是否表达了生命的活力。这可以看作她对诗歌诗人看法改变的基础。
(二)艺术即服务
奥罗拉作为一名诗人,其成长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最终为女性参与诗歌创作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这首长诗的结尾,她将艺术定义为一种服务,强调女性参与诗歌创作并不是惊世骇俗的举动,而是和“房中天使”的传统身份是兼容的。
在第三卷,奥罗拉列举了关于她作品的批评,有人警告她大众指责创新,好的作品应该“新颖但正统”(Browning,1864:120)。奥罗拉在诗歌创作中一直努力达到这一标准;在第五卷中她指出自己终于创作了一部得到大众普遍称赞的作品,包括之前低估诗歌重要性的罗姆尼。这意味着这部作品新颖但不脱离传统。奥罗拉通过强调艺术的服务性质突出自己的诗歌观点虽然将女性纳入诗歌创作领域,但这与女性“房中天使”的身份并不是背道而驰。艺术创作也是一种服务,服务上帝,服务社会。
纵观全诗,奥罗拉不断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在第二卷,她提出诗歌对社会主义者的项目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在第六卷,奥罗拉意识到诗人和慈善家之间存在互补关系;第八卷,罗姆尼承认自己的失败,意识到提升人们精神的重要性;在诗的结尾,论及男女角色时,罗姆尼指出“艺术即服务”,这表明两人达成了共识。艺术家可以打开认知之门,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建立联系。科拉·卡普兰 (Kaplan,1978:7-9)认为《奥罗拉·李》通过叙述女性经历,反抗当时文学创作中的父权思想,在19世纪女性作家创作传统的背景下,这首长诗非常具有革命性,在很多方面预示了激进的女权主义。
在迪尔德丽·大卫(David,1985:134)看来,在诗的结尾处将艺术定义为一种服务,暗示女性的艺术创作为男性的理想服务,布朗宁的性别政治因而是非常保守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定义是罗姆尼做出的,而且在承认奥罗拉的诗人身份之后,他将奥罗拉称为“我的米里亚姆”(Browning,1864:436)。辛西娅·施恩伯格(Scheinberg,1994:65-67)指出,米里亚姆被视为女诗人的权威先例,奥罗拉通过援引基督教中的诗歌权威来肯定和合法化女性的艺术体验;罗姆尼的占有欲修正了米里亚姆叙事的威胁,并将奥罗拉置于男性主导的希伯来历史中。这首长诗在很多方面都可看作激进和革命性的女性主义宣言;然而,在诗末,在奥罗拉已经获得完整身份之后,将艺术定义为服务的确发人深省。
奥罗拉为了证明女性也可以从事诗歌创作,不断改变自己关于诗人性别的观点,这一努力是非常新颖的。但是在诗歌结尾处将艺术定义为服务有效地解决了女诗人自我肯定和自我否定的矛盾,也就是说,这与女性“房中天使”的传统身份是兼容的。
结 语
布朗宁在长诗《奥罗拉·李》中记录了奥罗拉一名女诗人的成长过程。奥罗拉通过不断完善对诗歌诗人的看法,逐渐意识到诗歌创作和女性身份并不是不可调和的。这一成长过程大致可理解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奥罗拉将诗人看作是男性的领域,因而拒绝自己的女性身份;第二阶段,指出诗人应具有双重视角,过着双重生活,反映自己的时代,承认了自己的性征但否认女性特征,成为过着悲惨生活的女诗人;在第三阶段,结合斯韦登伯格主义关于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相辅相成的哲学观点,奥罗拉意识到不应将女性身份看作艺术创作的障碍,承认了自己的女性特征。在不同的阶段,奥罗拉·李都坚称诗歌就是生命,这一观点是她对诗歌诗人看法改变的基础。虽然这部诗作常被看作激进女性主义的重点文本,但结尾处以罗姆尼之口表达“艺术即服务”的观点,既强调了女性的社会价值,也突出了女性的服务本性。
本文结合布朗宁的生活信件,以及同时代作家的作品,试图理清女主人公诗歌观点的发展过程,以及如何相应地逐渐接受自己的女性身份。这一思路继承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批评,同时运用一种变化的观点理解女主人公的成长过程。但是由于参考文献有限,分析深度存在不足,此话题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比如结合布朗宁的生活经历,将这部诗作置于诗人整个诗歌创作历程之中,从传记分析的角度探讨诗歌观点的发展过程。随着国内对这部诗作的研究兴趣愈加浓厚,相信可以给与读者更多的生活启示,人生的多个角色相辅相成,相互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