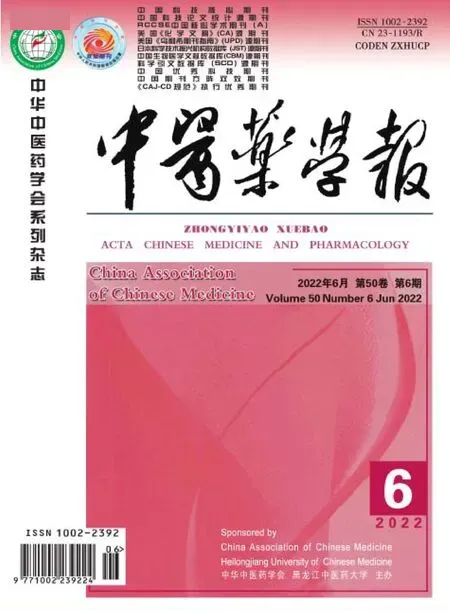从异病同治探讨肠道菌群对胆石症湿热病理的影响
2022-11-27王素英闵莉
王素英,闵莉*
(1.福建中医药大学中医证研究基地,福建 福州 350122;2.福建省中医健康状态辨识重点实验室,福建 福州 350122)
胆囊结石,中医称为胆石症,常被划分为中医学“胆胀”“胁痛”“黄疸”等病范畴,是消化系统临床常见疾病,其中大部分为胆固醇结石,现代医学研究证实,胆固醇代谢异常,致使肝脏分泌的胆汁内胆固醇过饱和是胆石症重要的发病机理[1]。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居民膳食结构、生活习惯等发生巨大变化,其发病率呈现逐年增多趋势[2]。近年来众多研究发现,肠道菌群通过发挥一系列作用在胆石症的形成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3],据临床治疗情况及相关调查结果得知,湿热蕴结是胆石症常见的临床证型和病理基础[4-6],湿热质、痰湿质也是胆石症人群最常见的体质[7-9]。湿热内蕴是多种疾病常见的发病机理,胆固醇结石湿热证的病理生物学机制尚不够明确,中医学“异病同治”理论讲究对证的核心把握,故根据其他疾病湿热证的发病机理共性可推测出胆石症湿热证的某些病理机制。课题组前期研究证实,胆固醇代谢相关因子的表达异常是其发病的分子生物学机制之一[10],因此,立足于“异病同治”理论,探讨肠道菌群对胆石症湿热病理的影响,大胆提出“肠道菌群可能通过影响胆固醇-胆汁酸代谢相关因子的表达导致胆石症湿热证发生”的想法,进一步丰富完善胆石症湿热证的病理机制,为其后续实验研究及临床诊疗提供新思路。
1 异病同治,“证”为之要
中医学认为,证是疾病发展某一阶段的病位、病因、病性、症状、体征、邪正盛衰状态等的综合病理概括,是病机与证候的统一体[11],也是疾病阶段性本质的体现。中医诊疗强调“辨证论治”,曹颖甫有言:“唯能识证者方能治病”,证辨识准确是后续临床疗效的重要保障。在此理论基础的指导下,即便是不同的疾病发展到同一阶段或有相同的病机表现出相似的证型,也可以采用相同的治法“异病同治”。病,指机体受到致病邪气影响,正气在与其抗争过程中脏腑、阴阳、气血等出现异常变化的动态生命过程,不同疾病间或某一疾病在发生发展过程中其病理状态更存在多种差异,若仅靠辨病达到治疗目的或明晰不同疾病间的联系存在太多易变和不确定因素。异病同治是中医辨证论治思想的延伸,其关键是立足于证的辨识,而不是局限于病的异同,核心在于抓住不同疾病的矛盾共性——同证。
异病同治从古至今都对临床治疗有重要指导意义。《金匮要略》在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脉证篇中提到曰:“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一斗,肾气丸主之。”消渴病的基本病机为阴津亏耗、燥热偏盛,下消病机以肾阳亏虚为主导,膀胱失约,故饮一溲一、小便量多。虚劳病病脉证篇也有记载曰:“虚劳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八味肾气丸主之。”肾阳不足,腰府易为寒邪所扰,常有腰痛、少腹拘急疼痛之症,肾阳亏虚,行气化水无力,则小便不利。二者虽不是同一种疾病,且小便量多少有明显差异,但其病机均为肾阳虚弱,而致膀胱气化失常,以肾阳虚为主证,因而两病治疗同用肾气丸以补肾助阳,均可取得良好疗效。张曼等[12]提出异病同治关键在于抓住疾病的主要病机,并认为可立足于气机郁滞这一病机,运用柴胡疏肝散达到对抑郁症、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乳腺增生等病异病同治的效果。临床证实,四妙勇安汤可通过解毒、活血、滋阴等作用,达到对动脉粥样硬化与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异病同治的良好效果[13];李艺博等[14]通过相关生信分析手段进一步预测了其异病同治的潜在分子生物学机制,为后续研究四妙勇安汤异病同治动脉粥样硬化与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开拓新思路。由此可见异病同治除了对临床治疗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科研发展中也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同证”的几种疾病间,依据已知的某病在这一“证”下的治疗方法与病理机制,可为该证的另外几种疾病治疗提供借鉴与经验,并推测其未知的病理机制。
2 肠道菌群与湿热蕴结型胆石症
2.1 从中医病因、病机角度对肠道菌群的认识
肠道菌群存在于胃肠道中,饮食结构的改变,如长久饮食不节、恣食肥甘厚腻等,会直接影响肠道微生态的平衡,进而导致部分代谢相关性疾病的发生发展[15-16]。相关动物实验研究发现,长期食用高脂饮食会导致大鼠肠道菌群结构紊乱增加结直肠癌的发病率[17]。“劳役过度,而损耗元气”(《内外伤辨惑论》),元气自肾中先天之精而生,赖脾胃运化之水谷精微而养,在中医学的论述中肠道菌群常被归为“脾胃学说”[18-19],故因劳倦过度而致病与肠道菌群失调引起脏腑功能紊乱之间有重要的联系。谭雅彬[20]经临床试验发现,与健康人相比,大肠癌术后脾肾阳虚证患者肠道菌群失衡,中药治疗脾肾阳虚证的机制与肠道微生态的改善相关。从中医瘟疫论角度来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乃因感受外在疫戾之气而致,患者除了表现出严重的呼吸道症状,也伴有明显的胃肠道不适现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中也建议使用肠道微生态调节剂,以维持肠道微生态平衡,预防继发感染[21]。肺与大肠相表里,调节肠道菌群可治疗外邪所致的肺结核、病毒性肺炎、哮喘等多种肺部疾病。张琳萄等[22]经动物实验证实,HIV感染后,猕猴肠道菌群改变,肠道微环境动态平衡也被破坏,且其AIDS发生发展状况与肠道菌群的改变紧密相关,由此可知,肠道微生态平衡失调是机体感受外邪的突出表现。
经研究证实,肠道菌群可通过影响神经系统造成精神障碍[23];从相关临床试验结果分析来看,重度抑郁症、精神分裂症、阿尔兹海默病等精神情志异常患者的肠道菌群和正常人相比均有明显差异[24-26],即中医学常讲的七情所伤、情志失调与肠道菌群的关系十分密切。
胆石症可归属于中医学“胆胀”“胁痛”“黄疸”等范畴,中医认为本病多是由于饮食不节、情志失调、劳倦过度、感受外邪等导致湿热蕴结、肝胆失疏、痰瘀交阻、肝失所养等多种因素相互影响,日久成石。综合以上肠道菌群与中医病因、病机关系的分析,映射了肠道菌群在胆石症疾病进程中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7-28],各证型的胆石症均可能会出现不尽相同的肠道菌群结构的变化。
2.2 肠道菌群与多类疾病湿热证相关
肠道菌群顾名思义存在于肠道中,随着胃肠道一起参与机体各类物质的消化吸收,与脾胃运化水谷精微的功能同出一辙,此外,若肠道菌群动态平衡遭到破坏,就会出现脘腹胀痛、便溏等脾胃运化失司的症状,故中医常将肠道菌群归论为“脾胃学说”[18-19]。加之章虚谷有言“湿热之邪始虽外受,终归脾胃”,且脾脏喜燥恶湿,便可知若脾胃为湿热所困,肠道微生态也会出现紊乱的现象。江月斐等[29]经临床试验发现,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的肠道菌群和正常人相比有明显区别,且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脾胃湿热证患者与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脾虚证患者的肠道微生态结构也存在不同。初旭等[30]经临床试验发现,与健康人相比,结肠癌湿热证患者肠道菌群丰度出现异常,提出大肠杆菌可能是促使结肠癌湿热证发病、发展的机制之一。
《素问·至真要大论》中载:“湿淫所胜”,若湿热之邪壅塞脾土太过会反侮肝木,导致肝胆疏泄失常,肠道菌群失调也会导致肝胆疾病湿热证候的发生。徐由立等[31]经临床试验发现,与健康人相比,慢性乙肝患者的肠道菌群明显失调,且慢性乙肝脾胃湿热证和肝郁脾虚证患者的肠道菌群结构也存在差异。除消化系统外,内分泌系统、呼吸系统甚至骨科、皮肤科等疾病的湿热证型均存在肠道微生态异常的表现。赵启菡[32]经临床研究发现,湿热证与非湿热证糖尿病肾脏病患者的部分肠道菌群组成上存在差异,某些菌属与湿热证的发生存在相关。邓力[33]通过观察比较正常环境下和湿热环境下的流感小鼠肠道微生态及黏膜免疫状况,证实湿热致病的本质是肠道菌群的紊乱引发肠道黏膜免疫功能下调。陈弋等[34]经动物实验发现,与正常小鼠相比,湿热型温病小鼠肠微生态结构紊乱。曹晔文[35]通过临床试验发现,类风湿关节炎各证型患者之间肠道菌群的结构存在差异,湿热型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的肠道菌群存在特异性改变。习婧[36]通过临床调查与实验研究发现,湿热型中重度痤疮患者肠道菌群中melaninogenica菌种丰度较高,非湿热型患者肠道内普雷沃菌属丰度偏低,肠道菌群的变化可能是湿热证诱发的关键。惠华英[37]通过动物实验发现,肠道湿热证泄泻小鼠肠道微生态失衡,通过中药治疗后小鼠肠道菌群失调状况得到改善。肠道菌群可作为中药治疗湿热证的作用靶点,为临床防治湿热证提供新思路。
以上大量临床与动物实验证明湿热证与肠道菌群之间存在相关性,肠道菌群的变化可能是湿热证的病理表现或诱发机制,某些特定肠道菌群可作为湿热证早期诊断的客观评价指标,总结众多相关文献得知,湿热蕴结在胆石症的发生、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5-9],据此推测胆石症湿热证的发病机制与肠道菌群相关,肠道菌群失衡可能是导致胆石症湿热蕴结的关键。
3 肠道菌群影响胆固醇-胆汁酸代谢诱发胆石症
肠道菌群在人体内可通过各种反应途径,参与物质及能量代谢,并在炎症、免疫防御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38-40]。现代医学研究证明,胆石症的发生受到肠道菌群的影响[27-28],吴韬等[41]经实验研究证明,胆结石患者存在肠道菌群结构失衡的状况且胆道菌群部分源于肠道菌群。胆固醇代谢异常是公认的胆石症发病机理之一[1],肠道菌群能通过相关酶促反应来调节胆汁酸的合成[42],进而影响胆固醇-胆汁酸代谢,造成胆结石的发生。
肠道菌群对胆汁酸代谢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介导法尼酯衍生物X受体(farnesoid X receptor,FXR)和G蛋白偶联胆汁酸受体1(G protein coupled bile acid receptor 1,GPBAR1,又称TGR5)的表达实现的。胆固醇在肝细胞内经过胆固醇7ɑ-羟化酶(cholesterol 7ɑ-hydroxylase,CYP7A1)或中甾醇 27ɑ-羟化酶(sterol 27ɑ-hydroxylase,CYP27A1)代谢形成结合型初级胆汁酸[43],经肠肝循环进入肠道后,肠道菌群中产胆汁酸盐水解酶(bile acid salt hydrolase,BSH)的细菌又将其修饰、催化为游离型胆汁酸[44],当回肠上皮细胞内游离胆汁酸浓度升高时,可激活肠道内FXR,进而促使肠上皮细胞分泌促进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19(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19,FGF19,在啮齿动物中以FGF15的形式存在),FGF19/15随着血液循环在肝细胞表面结合并激活FGF受体4(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receptor 4,FGFR4)及其辅助受体Klothoβ蛋白形成的FGFR4-Klothoβ复合物,从而促使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1/2(extracellular regulated protein kinase 1/2,ERK1/2)和 c-Jun 氨基末端蛋白激酶(C-Jun N-terminal protein kainse,JNK)磷酸化,抑制胆固醇7-羟化酶(cholesterol 7-alpha hydroxylase,CYP7A1)的表达,导致肝脏内胆固醇代谢为胆汁酸减少,即肝脏会分泌更多的胆固醇过饱和胆汁,促进胆结石的发生[40,45-46]。此外肠道中具有7ɑ-脱羟基酶活性的菌群可以将初级胆汁酸转化为次级胆汁酸,引发胆固醇结石[47]。次级胆汁酸石胆酸(DCA)和脱氧胆酸(LCA)增多,会进一步激活G蛋白偶联胆汁酸受体1(G protein coupled bile acid receptor 1,GPBAR1,又称TGR5),GPBAR1可通过进一步激活cAMP-PKA信号通路,介导Na+依赖性胆酸盐转运体(apical sodium dependent bile salt ranspor-ter,ASBT)调节控胆汁酸的重吸收,造成胆汁中胆固醇与胆汁酸的比例失衡,让胆汁维持过饱和状态,促发胆结石[48-52]。苗彬等[53]通过临床试验发现,胆石症患者胆汁内次级胆汁酸DCA比例较非胆石症患者升高,加之临床试验中也发现,胆石症患者肠道菌群的确发生明显的失调[27-28],更加证实了肠道菌群通过调控胆汁酸-胆固醇代谢参与胆石症的发生发展,并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4 小结
综上研究表明,肠道菌群失调与湿热证候的发生密切相关,胆石症与肠道菌群之间也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基于课题组前期的研究成果,胆固醇代谢相关因子的表达异常是胆石症湿热证的分子生物学机制之一[10],本文在异病同治理论的指导下,提出假说“肠道菌群紊乱导致胆汁酸-胆固醇代谢异常是胆石症湿热证的病理本质”,由此推测具有清热利湿作用的中药具有调节肠道菌群失衡的作用,进而影响胆石症的疾病进程,提示肠道菌群或可成为中医论治湿热蕴结型胆石症的新切入点,并为后续深入的实验研究提供新思路。本文虽提出肠道菌群对胆石症湿热病理影响的假说,但是缺乏实验验证,存在不足,为进一步验证该假说,课题组需要通过进行相关的动物实验或临床研究,明确肠道微菌群失调导致胆石症湿热证发生的相关微观机制,从宏观、中观、微观全面地探讨肠道菌群对胆石症湿热病理影响的中医本质,为中医药从调节肠道微生态防治湿热蕴结型胆石症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