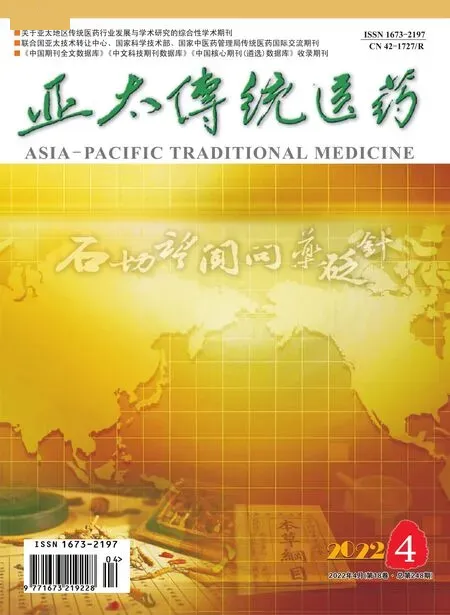国际传播视野下的《本草纲目》英译版本对比研究
2022-11-27罗瑞琪湛嘉欣王奕颖毛和荣
罗瑞琪,湛嘉欣,王奕颖,毛和荣
(湖北中医药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5)
中医药是世界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不仅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卓越贡献,而且对增进全人类身心健康和促进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当前,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国际传播迎来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暴发以来,中医药通过提前介入、全程参与等方式,不仅在治疗、康复、预防等环节彰显了独特疗效,而且为全球人类健康事业展示了“中国智慧”,贡献了“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精神,一定程度上也提升了中医药自身的国际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作为荆楚医家的主要代表,李时珍的不朽之作《本草纲目》蕴含着中国历代名医在防瘟疫方面的重要经验,尤其是该书中对各种常用药物的全面论述对当今中医用药仍有极为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中医药国际传播与中医药翻译紧密相依。近代以前,由于语言文化的壁垒,中医外宣主体多为西方人士,而中国本土学者则凤毛麟角。中医药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医药翻译主体常因文化背景差异、语言转换困难等问题使译文与原著内容大相径庭,错译、误译、漏译现象时有发生,从侧面反映了中医药翻译之于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海外传播的重要意义。除翻译外,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尚存在多重挑战。学者常馨月、张宗明、李海英指出,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过程中出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中医语言转换遇阻,文化差异问题突出;其二,中医药理论内涵传播难,应对负面新闻报道经验不足;其三,对社交媒体、新媒体等新型宣传介质利用不足[1]。中医药在国际上的接受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的准确性和适切性。本文尝试从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翻译技巧等视角对《本草纲目》两个代表性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旨在厘清中医药翻译与中医药国际传播的逻辑关联,借助外语翻译等手段不断提升中医药文化的国际认同。
1 《本草纲目》罗希文译本与文树德译本简介
1.1 《本草纲目》之罗希文译本
罗希文,早年毕业于对外经贸大学,被称为“中医典籍全英译本第一人”。他身兼中华典籍研究与英译专家、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等职[2]。世界上首部《本草纲目》全译本正是由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罗希文教授历时10年完成的。本书卷帙浩繁,罗教授曾花费半年时间来编写适合现代科学规范的索引,对每处深奥的词句都在查阅古籍的基础上作了大量的研究考据[3]。本书一方面完全按照原文内容和写作体例进行了全文编译,另一方面又以现代科学的研究态度,在注释与附录中对《本草纲目》中部分不适用于现代科学的内容进行了修订解释。例如,罗教授为了西方读者阅读研究的方便,在英译版书后梳理出八大索引,对中药名称、参考书目、方剂、参考地名、古代官职等内容逐项加以索引,全部采用汉语拼音、英文、拉丁文“三重法”同时标注,以适应现代科学的需要[4]。毫不夸张地说,这部600多万字的英译本的出版,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翻译和对外交流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
1.2 《本草纲目》之文树德译本
文树德,德国人,曾长期担任慕尼黑大学医史研究所所长,是世界著名中医医史文献学家和中医药翻译家,早年获得了哲学、药学、公共卫生学博士学位。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开始翻译《难经》《素问》等中医经典著作,同时编写了《本草史》《中医伦理学》《中国医学思想史》等中医药专著[5]。近20年来,文树德教授一直致力于做一件事情,即完成《本草纲目》全文的英译工作。文教授曾在接受《中国日报》记者的采访中阐述了自己翻译《本草纲目》的初衷:第一,《本草纲目》一书十分具备实用价值,翻译该书既能让全世界读者掌握古代植物知识,又能了解到中国传统医药知识的博大精深,为发展现代新型医药提供借鉴;第二,对《本草纲目》作者李时珍的敬佩,李时珍识多才广,儒释道三教兼通,《本草纲目》一书广征博引,为后人留下了不计其数的珍贵医案;第三,结合《本草纲目》中所代表的中医与西医以及现代科学,将有助于发展现代医学,造福全人类[6]。总之,在文教授看来,翻译《本草纲目》这样一部划时代的中医药学巨著,不仅能促进中医药文化在国际上的交流与传播,而且有利于增进人类健康福祉。
综上可见,译介传播最重要的主体是译者,其个人背景和职业素养直接影响了相关翻译策略的选择,进而决定了译文的质量和译本传播的深度与广度。在此,笔者将从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翻译风格三大方面对罗希文《本草纲目》的英译本(以下简称“罗本”)和文树德《本草纲目》的英译本(以下简称“文本”)进行对比分析。
2 《本草纲目》之“罗本”与“文本”对比分析
2.1 “罗本”与“文本”之翻译策略对比
“翻译策略”是指翻译中为达到一定的翻译目的所遵循的原则和所采纳方法的集合。根据译者翻译活动中取向的差异,翻译策略一般包括异化和归化两类[7]。
例1:[释名] [时珍曰]《战国策》云:长桑君饮扁鹊以上池之水,能洞见脏腑[8]。
“罗本”:[Explanation of Names] Li Shizhen:It is recorded inZhanguoCethat Doctor Changsang Jun fed his student,Doctor Bian Que,with Shangchishui (water from the upper pond).After that,Doctor Bian Que could see clearly the Five Viscera (Liver,Heart,Spleen,Lungs and Kidneys) and the Six Bowels (Gall Bladder,Stomach,Large Intestine,Small Intestine,Urinary Bladder and Sanjiao) of his patients[9].
“文本”:Explanation of Names.[Li] Shizhen:theZhanguocestates:“Chang Sangjun let Bian Que drink the ‘water from elevated ponds’ enabling him to clearly see the long-term depots and short-term repositories”[10].
根据《中医大辞典》的解释,“脏腑”为五脏六腑的统称[11]。因此,笔者认为此处“脏腑”指的就是“五脏”和“六腑”,其中“五脏”包括心、肝、脾、肺、肾,“六腑”则包括胃、胆、大肠、小肠、膀胱和三焦。显然,在译文中,“罗本”采用的是“归化法”,即站在读者的立场上,用目标语读者所惯用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涵,以使译文更通俗易懂。同时,“罗本”在翻译五脏六腑时,采用了首字母大写的处理方法,这样便于提醒读者,中医“脏腑”与西医解剖意义上的概念有着显著的区别。这一译法增强了中医古籍的可读性,彰显了中医药文化的独特性。就该段翻译整体而言,“罗本”运用了一个强调句式,明确了“长桑君”和“扁鹊”医家之身份,最后用补语成分“of his patients”,明确了“洞见脏腑”的对象,译文一气呵成。
对于“脏腑”一词,“文本”则采用异化策略,分别译为“long-term depots”和 “short-term repositories”。“脏”—depot(仓库)、“腑”—repository(贮藏室),虽然译出了中医术语的隐喻含义,体现了中医“取象类比”的特点,却也使得译文医学的味道大打折扣。这一译法相对生硬晦涩,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译文在目标语读者中的传播和接受。
当然,译者在翻译之前,就得清楚关键词“上池之水”究竟为何物。“上池之水”出自《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此前学者认为是“口中津液”[12]或是“未沾及地面的水”[13]。王轲认为“上池之水”是“助发挥最佳药效之水”[14]。就该词英译而言,“文本”又比“罗本”更胜一筹。“文本”意译为“water from elevated ponds”,选用“elevated”一词,显然是将其理解成 “未沾及地面的水”之意。即使原作与译者所处地域和时代截然不同,语言系统相去甚远,但是却能通过翻译将源语传达给读者。由此可见,中医药翻译的过程也是中西方文化相互沟通、彼此接纳、交流互鉴的过程。
2.2 “罗本”与“文本”之翻译方法对比
翻译方法是翻译中通过使用某翻译策略,为实现特定的翻译目的所采用特定的途径、步骤、手段[7]。
例2:[主治]瘟疫。五月一日,取土或砖石,入瓦器中,埋着门外阶下,合家不患时气。[8]-309
“罗本”:[Indications] Chen Cangqi:It is good for treating epidemic infectious diseases.On the first day of the fifth month,get earth or bricks and stones from a tomb and put them in a pottery container.Bury the container in front of the main gate of the house.This will prevent attacks of epidemic infectious diseases[9].
“文本”:Control.Warmth epidemics.On the first day of the fifth month acquire soil or bricks and stones [from a tomb] and give them into an earthenware container.Bury this below the stairs outside the front door,and this will prevent the entire household from suffering from [diseases caused by] seasonal qi[10].
“瘟疫”指因感受疫疠之气而发生的多种流行性急性传染病的总称[11]。首先,“罗本”用完整的句子补充解释了“冢上土”的主治功效,将“瘟疫”意译为 “epidemic infectious diseases”。其中,“epidemic”意为“传染病,流行病”,指的是在某地域广泛暴发的疾病。“infectious”一词点明了“瘟疫”具有强烈传染性之特点。可见,“罗本”在选词用字、句法结构等方面都较符合译语读者的习惯。这种译法在早期有利于促进西方受众对中医的初步了解,助力中医药顺利进入海外市场。相比,“文本”更忠实于原文形式,将该词直译为“Warmth epidemics”,接近中医“温病”——一般情况下是多种外感急性热病的总称[11]。同样的翻译方法也适用于“时气”一词。“时气”具有多义性,一是指疫病,又称疫疠、天行、时行、时疫;二是指病邪名,具有强烈传染性、流行性的病邪[11]。“罗本”同样沿用了“epidemic infectious diseases”,而“文本”则选用了“seasonal qi”。
相比之下,“罗本”对于例句的翻译更为详细,更有利于早期中医文化的对外传播,特别是在不甚熟悉中医的受众中传播。“文本”直译之法既保留了中医药的独特韵味,又兼具很强的回译性,更适合在对中医有所了解的受众中传播。这与译者本身不无关系。任何译者都不是独立于特定的文化背景而存在的,在每个译者的头脑中都深深打着自己所处的社会文化烙印[15]。“罗本” “文本”译文风格迥异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译者文化背景的差异。罗教授翻译的《本草纲目》是“大中华文库”项目的一部分,通俗易懂,交流传播是该项目的主要目的之一,故“罗本”在一些术语处理上采用了意译法。而文教授长期旅居于中、德两国之间,所接触的文化具有多元性,虽为外国人,医史文献功底深厚,故“文本”在一些术语处理上采用了直译法。应该说,两个译本各具特色。
2.3 “罗本”与“文本”之翻译技巧对比
翻译技巧是翻译中某种翻译方法在具体运用时所需的技术、技能或技艺。“翻译技巧”是局部的、微观层面的,是对文本在语言层面的操作和操控[7]。“罗本”与“文本”均使用了增译、分译及转换等翻译技巧。
例3:[主治]身体五脏百病,养精神,安魂魄,益气明目,杀精魅邪恶鬼。久服通神明不老。能化为汞。本经通血脉,止烦满消渴,益精神,悦泽人面,除中恶腹痛,毒气疥瘘诸疮。轻身神仙[8]。
“罗本”:[Indications] It is good for treating a hundred diseases of the five Viscera (Liver,Heart,Spleen,Lung and Kidney).It nourishes the Spirit and mind,pacifies the soul and boldness,reinforces the Vital Energy,and improves the eyesight.It kills devils and evils.Long-time consumption of the drug will enable the person to achieve great enlightenment and remain ever young.It can dissolve into Shuiyin/hydrargyrum/mercury.——ShenNo-ngBencaoJing(ShenNong’sGreatHerbal).It is good for facilitating the flow of blood and Channels,stop restlessness,fullness and thirst in diabetes.It reinforces one’s spirit and nourishes one’s complexion.It treats syncope due to attack of fright and noxious factors and abdominal pain.It is also effective to treat skin sores,scabies and fistula due to attack of noxious agents.Long-term consumption makes the person feel happy and enjoy long life.[9]-990
“文本”:Control.The hundreds of diseases affecting the [human] body and its five long-term depots.It nourishes essence and spirit.It pacifies thehun-soul and thepo-soul.It boosts the qi and clears the eyes.It kills spirit seduction-specters and evil as well as malign demons.Ingested over a long time it frees the passage of spirit brilliance and prevents aging.It can be transformed to mercury.Benjing.It frees the passage of blood through the vessels.It ends unrest,sensations of fullness and melting with thirst.It boosts essence and spirit.It makes one’s face appear happy and glossy.It ends abdominal pain resulting from being struck by the malign,and removes all types of sores,such as jie-illness and fistula,caused by poisonous qi.It takes the weight of the body and turns one into a spirit immortal[10].
在翻译“五脏”时“罗本”采用了直译加注法,仅仅把“五脏”译为“five Viscera”,读者不一定能够理解,因此在该词后增加了相关的背景信息,这是从文化层面考虑的增词。同样情况在翻译“汞”和“本经”处亦可见,既保证了译文表达的明确性,也减少了高语境与低语境之间的隔阂。在“魂魄”一词上,“罗本”和“文本”都采用了合译法,前者意译为“the soul and boldness”,后者直译为“thehun-soul and thepo-soul”。
“精魅”在西方医学文化中属于“文化缺省”。英汉文化差异显著,有些中医药术语在英语中存在词义上的空缺,因此找不到对等词。“罗本”采用了释义法和合译法,将“精魅邪恶鬼”三个术语译为“devils and evils”,行文更为简洁。中医术语所负载的中医文化内涵丰富,该译法是否能让西方读者理解仍有待商榷。“文本”将“精魅邪恶鬼”分译为“seduction-specters and evil as well as malign demons”。其中“精魅”,“seduction-specters”一词,为方便海内外读者阅读,在脚注处用音译加注法专门进行说明:“Jing mei精魅,‘spirit seduction-specter,’ a notion of demonic pathogenic agents。”可见,文教授注意到了汉英两种语言上的差异。文言文表述时惯用省略,故运用增译法使之补充完整并在翻译中统一术语十分有必要,如此有助于海外读者更好地理解掌握中医术语所涉及的概念群和语义场。
两位译者对“除中恶腹痛,毒气疥瘘诸疮”所采用的翻译技巧也大相径庭。“罗本”采用分译法将原文的一个句子切分成两个句子。在句式上用“It treats some diseases due to sth.”的排比结构,再现原文独到的语言风格,译文紧凑有力。“文本”则涉及语篇层面的转化,“中恶腹痛”译为“abdominal pain resulting from being struck by the malign”,由原文主动语态转换成被动语态,译文逻辑上更为缜密,最终使得读者能够领会该术语背后潜藏的因果关系,即因为有“中恶”,所以才有“腹痛”。
值得一提的是,两个译本都对副文本——“本经”进行了翻译。“副文本”指的是“在正文本和读者之间起着协调作用的、用于展示原著的一切言语和非言语的材料”。[16]此处“罗本”有别于“文本”,不是简单将“本经”音译,而是采用增译法,按照原版本格式要求,将漏译或不译的部分增译为“Shen Nong Bencao Jing (Shen Nong’s Great Herbal)”。《神农本草经》又称《本草经》或《本经》,如果没有这样的附加性信息,译文读者也许就无法理解“本经”此处指的是哪一部经典。译本虽有瑕疵,比如“罗本”将“本经”译为“Shen Nong’s Great Herbal”,但作为国内首部《本草纲目》英文全译本,仍不失为一部传播中医知识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典范之作。总之,“罗本”和“文本”这两个目前仅有的全译本所采用的策略、方法与技巧对当今中医典籍翻译仍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3 中医药典籍英译与国际传播之关联
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中医药文化传播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5年)》等文件都强调了中医药典籍文化整理与海内外传播的重要性。包括《本草纲目》在内的中医药典籍既是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也是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的源头活水。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一环。要提升《本草纲目》的国际影响力,不但要有真实新鲜的、丰富生动的内容,还要注意使用恰当的技巧,否则相关内容亦将无法得到有效的展示和宣传[17]。
有学者认为,翻译学属于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是传播学中一个具有相当特殊性质的研究范畴[18]。这个意义上,中医药英译的本质问题也可视作是传播问题。在中医英译中,要想做到尽量准确真实地传播中医文化,就应充分考虑受传者的文化背景、认知感受、思想习性和审美观念等,从而生成受传者欢迎的译本。英译典籍《本草纲目》能否被海内外读者认可和接受,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翻译策略、方法和技巧的选择。在此过程中,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并不互相排斥。例如,针对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医药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应以异化策略为主,一般采用音译、直译、直译音译结合或直译、音译加注释等翻译方法,把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和文化传向世界。在句型或语篇层面,则可借用中医的“加减化裁”进行归化法处理。具体方法如下:加,补充相应的背景知识和文化内涵;减,删减和简化一些重复的信息;化,对典籍中的某些语篇结构进行转化和重编,使译文更加符合现代读者的逻辑思维;裁,适当修改原文的语言风格,使译文更加符合国外受众的阅读习惯和审美追求。总之,中医药典籍英译在兼顾译文可读性和可接受性的同时,应尽可能保留和传播中国文化的特色[19]。
4 讨论
翻译与文化相辅相成。中医药典籍是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内容和载体,而翻译架通了中医药典籍对外传播的桥梁。推动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国际传播,就必须重视中医药典籍的翻译,尤其是像《本草纲目》这样有着广泛民意基础和重大医药学价值的典籍。《本草纲目》自明万历二十四年“金陵本”问世以来,陆续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版本,该书还广泛流传于亚洲、欧洲、美洲等地,并被翻译成日、英、法、德、俄、拉丁等多种文字。罗希文英译本多选用常见医学词汇,语言隽永、流畅易懂。由于多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意译的翻译方法,并采用大量的注解,有力推动了《本草纲目》和中医药文化的海外传播。文树德英译本多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直译的翻译方法,使用音译法来处理中医文化负载词以保留对仗句式,并使用大量的脚注,对推动《本草纲目》和中医药文化在世界传播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孜孜不倦的译者匠心精神是中医药文化典籍顺利走向世界的重要保障。中医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显著疗效正日益显现,并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和肯定。如何更好地借助翻译,将深藏于典籍中的中医药文化传向世界,造福全人类,是一项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学术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