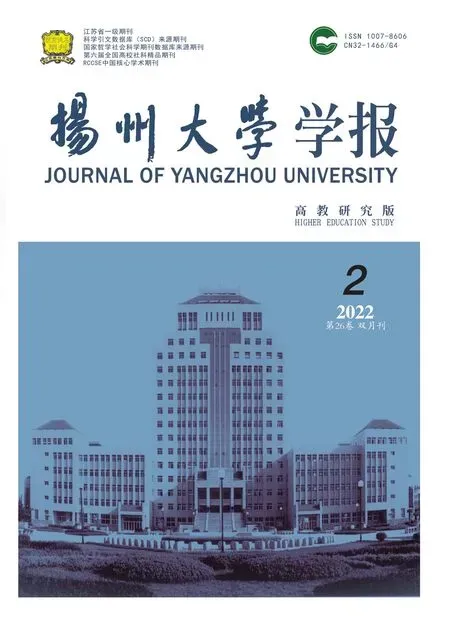“佛系青年”现象:因何而生与何以引导
2022-11-26欧庭宇
欧 庭 宇
(贵州师范大学,贵州 贵阳 550001)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网络空间有一群念着“都行”“可以”“没关系”等“佛系咒语”的青年,他们就是所谓的“佛系少女”“佛系员工”等“佛系青年”。“佛系青年”以新世相的方式在人民日报的文章《第一批90后已经出家了》中横空出世,甚至成为《咬文爵字》杂志社公布的2018年十大流行语之一,迅速成为学术界和社会各界所关注和回应的热点问题。然而,在“佛系青年”现象与“丧文化”的关系上,学术界依旧存在一定的争议。有学者从“延续论”的角度出发,认为“佛系青年”现象“所隐含的亚文化特质是‘丧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并成为当前青年群体亚文化的典型表现形式”[1]。有学者从“变异论”角度出发,认为其“表面上与佛教中的修行修为相似,实则与存在主义的基本精神诸如向死而生、消极遁世、生命悲观主义、绝对自由、快乐至上等更为贴近”[2]。相比之下,后者的观点更站得住脚,至少通过归纳总结其基本特征和本质,就会找到合理的依据。
1.“佛系青年”的基本表征。“佛系青年”的主体是90后和00后青年,常常被贴上“叛逆一代”“怪异群体”的标签。由于他们一出生便赶上了社会转型大剧变的时代,往往表现出“无所谓”“慵懒”“啥都可以”的生活状态,似乎跟缺少阳光和活力的“油腻中年”一样,表现出“无所谓”的人生态度、“无所求”的学习状态、“无所为”的生活哲学特征:“无所谓”的人生态度,即无任何欲望、无任何追求的人生态度,他们既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缺失奋斗精神、不在意结果好坏,又在人生目标和职业发展方面缺乏明确方向性、阶段性的规划;“无所求”的人生状态,即对学习和工作潇洒的、随意的人生状态,只追求短期的、及时性的自我满足;“无所为”的生活哲学,即将所有的出发点和注意力置于自身的兴趣消遣上,将所有的生活主题和日常重心都围绕在如何为自己减压减负上,尽可能地避免过度“为难自己”。
2.“佛系青年”现象是对“丧文化”的变异与进化。作为“丧文化”谱系中的“佛系青年”现象,就态度和行为而言,跟“丧文化”存在较大区别。“丧文化”是处于社会转型剧变的大部分青年面对生活压力,以娱乐和自嘲的方式主动污名化,来表达对自身标签的反抗和奋斗,表面上一无是处,实质上内蕴着强大的、澎湃的奋斗精神;而“佛系青年”现象恰好相反,它代表甘愿颓废、妥协,通过佛系心态、佛系话语、佛系文化去处理一切,特别是以潇洒自由、无欲无求来掩盖随波逐流的消极态度。区分“丧文化”与“佛系青年”现象的不同之处,并非是否定后者来源于前者,相反的正因为它们都有从自身贴标签出发这一共通之处,才有了“佛系青年”现象对“丧文化”的变异与进化。“丧文化”诞生的背景是人们面对巨大的经济压力、高居不下的房价、繁重的工作任务,一些人完成了从“丧文化”中的自我救赎;另一些人因为各方面的压力和不顺,选择追随“事事随大流、处处无所谓”的佛系文化,冠以自我减压的精神鸦片,以此缓解自身焦虑、自我恐惧。在近年来的“佛系青年”现象中形成了追捧“葛优躺”的网络热潮,这并非追求游手好闲、坐享其成的人生状态,而是对积极向上、创新创造、砥砺奋进的主流文化发出质疑和挑战,开启了顽主和废柴们“逆袭”正襟危坐正人君子的新纪元。进一步说,如今青年群体追捧和羡慕“丧文化”中所讽刺的“葛优躺”,不像“丧文化”的表面颓而内心不废,而是借助“佛系”标签掩盖内心的不思进取和甘愿慵懒,为自身面对压力时注入自我娱乐和精神缓解的“麻醉剂”。由此看来,“佛系青年”现象的产生,与其说是对“丧文化”的延续和补充,不如说是对“丧文化”的变异和进化。
透过现象看清本质,找准“佛系青年”的群体特征和该现象的内生根源还远远不够,深究该现象的形成原因,找到与主流价值思想融合的路径,帮助这些青年群体走出思想困境,引导他们走向青春正能量、成为担当中华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才是真正目的所在。
二、“佛系青年”现象因何而生?
1.利益分化带来青年人生前途的焦虑。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突飞猛进,我国的社会利益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多样,呈现出利益多元化、分层化趋势。按照“马太效应”原理来讲,社会资本的代际传递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固化,出现了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两极分化”,导致处于不利地位的青年群体愈加难以阶层上升。作为社会生活条件更加优厚的“佛系青年”,却面临着“收入停滞不前”“消费升级”的巨大压力,即便是部分较高学历的职业者也正经历着草根化、贫困化的残酷现状,面临着房贷、车贷、学历需求、教育经费、升职等各方面的压力与焦虑。伴随焦虑情绪叠加与积累,这些原本想朝着更高奋斗需求的青年群体开始主动降低目标和愿望,以淡泊名利、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麻痹自己,进而给予自己从焦虑中释放自我的空间。当青年群体处于焦虑、急躁的生活状态时,首先考虑到自我心理的安抚和缓冲。利益分化使他们找到符合内心“看淡一切”的价值观,使“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的价值导向遭到冲击,陷入“佛系青年”现象的“沼泽地”。
2.多元文化对青年个体价值的冲击。当主流文化受到其他文化和思潮的质疑、挑战和解构后,尤其是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文化冲击,社会转型必然带来社会思潮的变化。针对中国社会,费孝通先生曾提出过“差序格局”。与此相反,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提出的“团体格局”概念,指出了西方社会是个体本位,意味着西方文化思潮对我们主流文化的消解和重建,与互联网时代的去中心化、去权威化呈现高度关联。一旦青年群体在这种文化思潮的诱导下,极易走向强调自我、关注自我,进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主流文化意识提出质疑和反叛。如此一来,这部分青年群体便会追求个人思想和行为的解放,而不是通过坚守主流导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家国情怀、社会义务、道德责任融入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砥砺前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发图强的实际行动,实现“大我”的社会价值基础上成就“小我”的人生价值,摒弃远大的人生追求,注重个体的享受、为自身而活,对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变得漠不关心,对社会发展需求和世界动荡不安变得袖手旁观。
3.丰厚物质导致理想青年角色的退场。社会转型大剧变带来利益分层压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对精神世界追求的自由。有学者认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达,社会物质财富的丰富,人们对精神利益的需求必将日趋增长和重视。”[3]新时代的物质财富相对于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物质的丰富和发展给予了青年群体更加多样更加广阔的选择余地。在过去,青年往往以一些励志的人物作为人生奋斗的偶像,受到偶像们的艰苦创业、担当奉献精神激励,青年群体更加坚定理想、奋发努力。然而,物质选择的多样性助长了部分青年的享乐主义,制造了片面追求物质享受的空虚状态、浮躁体验,他们逐渐由理想青年蜕化为“佛系青年”,开始深陷理想弱化、激情不再的短视人生。显而易见,“佛系青年”现象就是隶属于后一种情况的典型例子,他们认为的“活在当下”看似是一种乐观的、物质的人生选择,实则是负面的生存体验与消极的人生追求。有学者借用海德格尔提出的“向死而生”概念来解释为什么青年一代要以“活在当下”作为人生态度,这就是“存在不是来自过去,而是来自未来,真正的存在是向未来的可能性中敞开的存在,只有死亡才可以将人交给自身、回到自身”[2]。换句话说,一些青年将此作为人生的一种选择,将“生命始终会走向终点”看成必然,既然如此,何不重视现在的人生体验、为自己而活,何必在乎遥远的未来?由此可见,“佛系青年”缺乏勇往直前、力争上游的勇气与魄力,若不能转变消极的存在主义生命观,将继续导致他们陷入不争不抢、沉迷颓废的泥潭,使“佛系青年”现象日渐盛行蔓延。
4.网络媒介加速健康青年心态的弱化。如果说前面的种种是导致“佛系青年”现象的社会原因,那么网络媒介的诱导与传播则是不可忽视的“网络社会原因”。网络媒介之所以能够对青年群体的思想行为发挥作用,是因为强大的网络用户带来的团体压力“使人从众、服从,在于它使成员感受到心理压力”[4],将其在移动网络软件的吸引下卷入群体交际、沟通的互联网空间,受到网络疯传的“佛系”这样的亚文化的冲击与碰撞,使他们由陌生到熟悉、由同化到认同。网络媒介具有对人们某种心态产生“聚光灯效应”的功能,当一部分人以淡然消逝的消极心态处世,容易使另一部分人相信“眼见为实”的思维逻辑。加上“青年一代生活阅历单薄,抗压能力降低,成长空间压缩,看不到生活的未来和希望,从而寻找佛系的生存哲学,这种选择一经网络传播,就像点赞和弹幕,既可以带来陪伴和认同,也可以带来颓废和逃避”[5]。当一些人通过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平台疯狂传播不求上进的“佛系”心态,青年很容易屈从于自身的从众心理,即便面对学历提升、职业发展、子女培养等方面的压力,只能选择掩饰内心焦虑的“低欲望心态”,从而导致整个网络空间弥漫着消极保守的亚健康心态。
三、“佛系青年”现象何以引导?
1.党和政府加强多渠道领导,为青年发展提供政治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指出:“关注青年愿望、帮助青年发展、支持青年创业,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6]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类似这样的讲话、演讲、批示、贺信、回信等重要文献达四五十篇,回答了“引导青年成为什么样的人”“谁是青年的引导者”“引导青年学习什么”“使用什么方法来引导青年”等重要问题,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青年成长的高度关注与亲切关怀,为促进青年群体健康、全面的成长提供了政治保障和思想指导。
首先,加强党对共青团的领导,发挥共青力在代表青年利益、引导青年成长中的关键作用。共青团作为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体组织,在联系各级党组织、政府和青年群体中发挥了纽带、桥梁的作用。团中央要从我国青年特点和国家实际出发,开展了百万青年创业计划、青年文明号、青年职业技能大赛、希望工程等全国性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年保持对远大理想和人生目标的执着追求,为民族复兴注入奉献青春的强大力量。同时,还要健全和完善团委干部联系青年制度,抓好各类学校、各企事业单位的团支部书记队伍建设,推动各级团干部积极联系青年、真正引导青年,帮助广大青年做有用之人、成有用之才,修立身之德、做追梦之人,做好广大青年的“朋友”、不做广大青年的“官员”。
其次,加强党和政府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科学管理,唤醒广大青年主动担当、自觉奉献的责任意识。习近平同志担任总书记以来,多次号召青年彰显青春力量,无论是2013年五四寄语“青春是用来奋斗的”还是2018年新年贺词“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均体现了奋斗与青春的高度关联,奋斗成为追求幸福、奉献青春的亮丽底色。为应对“佛系青年”现象的潜在危机,要建立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共同发力的协同机制,鼓励广大青年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将学校教育的“小课堂”与社会实践的“大课堂”相统一,推进道德、智力、健康、劳动、审美等方面的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尤其要重视他们在社会实践中增强工作能力、个人意志和担当精神,在职业发展中体会祖国发展带来的人生价值和社会责任,逐步引导他们养成谦和、自律、担当的良好品行。
最后,党和政府完善文件政策配套,满足广大青年的发展诉求。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 年)》,这是我国第一次专门面向广大青年制定的国家纲领性文件,帮助青年群体尤其是“佛系青年”渡过难关,引导青年群体突破健康发展瓶颈,为广大青年提供出彩的良好机会和支撑平台。高校应与企业、科研院所等机构协同共进,加强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打造一批平台载体、完善相应分配与激励机制,提升对广大青年参与创业创新、社会调研、科学研究、职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为他们提供各尽所能、各尽其才的服务平台,进一步满足他们健康发展、自我实现的发展诉求。
2.注重青年的教育引导,提升自身思想行为的调适能力。与20世纪末青年价值观“意识形态化”问题不同,如今“佛系青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空心病”,即青年价值观“社会问题化”尤其是“教育问题化”。面对多元价值取向的社会现实,广大青年的价值观、欲望、主体意识等方面的调适能力,显得尤为关键。
首先,提升广大青年的心理调适能力。面对房贷、延迟退休等压力,社会角色的转变使青年人难以适应,“佛系”文化成为他们自我安慰、自我保全、自我矮化的舒缓方式。为此,要从广大青年的心理层面实施引导教育,培养他们积极向上、健康阳光的心态。要在大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中加强健康教育组织的建设,针对各阶段、各方面的青年特点制定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譬如,课程教学引入心理疏导等元素,设置“一对一”心理应对档案,努力做好广大青年问题与解决方案的“案例库”,为青年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参考性、方向性。
其次,引导广大青年学会自我管理欲望。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无论处于什么阶段、什么阶层,都会有欲望的流露,青年群体也不例外。“佛系青年”现象就是一种关于“实现什么样的价值、怎样实现价值”的价值论问题。为了遏制“低欲望”现象,既要引导青年坚定理想信念,把个人理想与共同理想相统一,历练自强不息、砥砺奋进的精神,又要避免急功近利的“急欲望”,充分认识和把握人生所面对的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的重要价值,塑造青年群体的大情怀、大格局、大担当的思想境界,从而缓解青年群体在人生发展中的焦虑不安。
最后,要回归青年主体本身。中国梦的接力棒交到了青年手中,意味着提升广大青年的主体意识是他们肩负历史使命、时代重任的必然要求。一要从学校教育入手,结合每个青年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符合个人实际的理想,特别是职业理想、奋斗目标。二要从家庭教育入手,充分重视家庭环境对青年群体未来职业理想的树立与选择的重要影响,成为他们坚定理想信念的助手、监督者。三要从单位教育入手,针对不同的青年员工,给予不同专业的发展方向与专业特色的工作机会,并鼓励他们在专业相匹配的人生奋斗中实现自我价值。四要从公民教育入手,坚定中国梦全方位、全过程、全员育人理念,进一步提升他们对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体意识,驰而不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做党和人民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优秀接班人。
3.加强线上与线下协同发力,营造良好表达空间。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7]虽然说青年是每个时代最关键的晴雨表,其价值取向影响甚至决定未来社会的价值取向,但是社会环境弘扬或反对什么,对青年群体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取向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青年群体的健康成长,需要整个社会线上线下的协同治理,以主流文化涵育青年个人价值观的塑造,以加强网络空间舆论治理构筑青年群体的精神家园,为他们的成长与发展创造健康向上的社会环境。
一方面,优化主流文化传播方式。在主流文化传播渠道上下功夫,才能有优化传播方式带来的效果。作为对“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思考与回答,各类学校、企事业单位不仅要重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挖掘党课、专业技术课堂、文化讲座的“思政元素”,使“思政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守好“第一课堂”的主渠道,而且也要重视社会实践“第二课堂”,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主流文化及书法文化、绘画文化等校园文化活动,发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作用。同时,要充分了解、调研他们的群体特点,注重语言表达的创新,将他们所热衷的网络热词与主流文化的精髓相结合,在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中增加文化产品供给,提升主流传播力。为提升青年群体的主观能动性,可邀请一些优秀的青年代表为他们讲述创业创新的成功经验、科学研究的心路历程,让更多青年群体感受同辈的敬业奉献、艰苦奋斗的青春正能量,促使他们明白自身的社会责任、家国使命的角色定位。针对“佛系青年”群体走出亚文化的心理困境,我们要强调广大青年个体努力奋斗,不仅可以得到社会尊重、物质的回报,而且所作的每一份努力都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贡献,使青年群体收获奋斗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另一方面,牢牢把握网络空间舆论治理这个重点。要从产生“佛系”文化的网络源头抓起,加强QQ、微博、微信公众号、论坛等新媒体的舆论治理,为广大青年提供一个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网络环境。从舆论引导来讲,要将做好网上舆论工作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8]。其中,政府既要加强对占主要渠道的“草根性网络平台”的网络监管,对亚文化的传播进行适度限制,制止现实伦理和网络伦理错位,又要鼓励和支持运营者开发正能量充沛的网络文化产品,将网络平台作为宣传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渠道,如为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穿上时尚外衣,增加其内在吸引力,使广大青年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神,增强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当然,也要强化广大青年对网络空间充斥着的亚文化、反主流意识形态等文化现象的辨识力,通过更有营养、质感、活力的文化传播方式提升其文化素养,反对和抵制负能量文化,在网络空间营造相互鼓励、相互呐喊的良好氛围,帮助广大青年以拼搏精神替代所有消极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