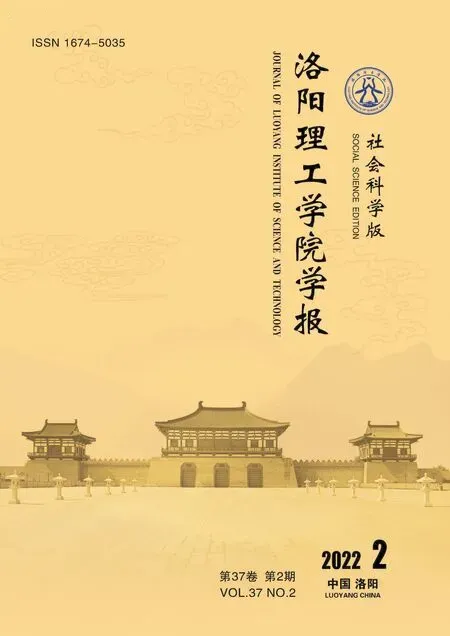郭绍虞赋论发微
——兼论其对现代赋体批评格局的开拓
2022-11-26韩叶林
韩 叶 林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贵州贵阳550025)
民国时期,西学东渐达到高峰。时代交汇点上的中国学者一方面引进西方现代学术理念,一方面进行本土化应用。与“人”学思想相并行涌入中国的是西方现代语言学、现代史学观、进化论等观点,这些观点在传统古典文学研究中逐渐发挥作用,由此形成的现代文艺批评新观念也波及赋学领域。此时期的学者多在报刊、文学史及文学批评史著作上发表赋学观点,丰富了这一时期的赋体评论,正所谓“民国时期的古典文学研究既承继了传统学术研究的理论特征与写作样式,又广泛吸收了西方学术著作的写作范式,并逐步转型,形成了中西融会的理论品格”[1]。
郭绍虞,20世纪著名的文学批评史家、语言学家,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等领域造诣颇深,有《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等著作存世。观其一生,虽未留下较系统的赋体批评文本,且他的赋论仅散见于《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汉赋之史的研究〉序》等文章以及《中国文学批评史》等著作中,然郭绍虞在其中灌注了较为独特的赋学观念。将郭绍虞的赋学思想放在新的历史语境下观照,就可以发现其中已涉及赋体源流演变、诗赋关系、赋体文学性、赋的文学史地位等重要赋学问题;并且,郭绍虞的赋学观点已带有现代文艺批评之色彩,总体特征为融贯中西,客观上促成了现代赋体批评格局的初步建构,并深刻影响了民国以降近一个世纪的赋体文学研究,后来的学者论赋多承其绪。许结说:“郭绍虞是较早地用现代研究眼光对赋的文学性及文学史地位做出中肯评价者。”[2]郭绍虞赋论在20世纪赋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一席,考察其中蕴含的赋学思想对于重新把握20世纪赋学史的发展演变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一、进化史观影响下的赋体源流观
关于赋体源流问题,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看法,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一是源于《诗经》说。如东汉班固《两都赋序》“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3]1,认为赋源于《诗经》,此种说法贯穿赋论史始终,论其根源则是自汉代递延下来的尊经传统,即认为赋体最初是诗体的附庸。二是源于《诗经》《楚辞》说。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言:“然赋也者,而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4]134此为二元说。三是源于纵横家说。章太炎《国故论衡·辨诗》认为:“纵横者,赋之本。”[5]128章太炎认为赋源于纵横家之文。四是多源说。章学诚《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第十五》认为:“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6]967此观点主张赋既源于《诗经》《楚辞》,又出于战国诸子之文。除以上四种主要观点外,关于赋源问题的看法还有“俳词说”“隐语说”等观点。
对于赋源,郭绍虞认为:“诗赋在后世虽有区别,在古代却是同源的。就其最初而言,赋本是诗的一种创作方法。所以班固《两都赋序》说:‘赋者,古诗之流也’,早已说明赋从诗出。到后来赋家云起,体构严密,遂与诗划境,而由‘六艺附庸,蔚成大国’了。所以赋之源是合于诗,而其末却不同于诗。”[7]80可见,郭绍虞认为诗赋同源,赋本是“六诗”之一,即赋从诗出,而后独成一体。自西方传入的进化史观在20世纪初大行其道,梁启超等人由此倡导“史界革命”,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向前的,呈现为不断进化的样貌。梁启超论史:“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8]7由此可见,与传统史学观念有别的是现代史学观倡导进化概念,讲求事物发展演变背后的前后因果关联。赋体批评在当时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郭绍虞关于赋体演变问题的探讨,带有明显的现代学术视野。郭绍虞将赋的发展演变概括为短赋、骚赋、辞赋、骈赋、律赋、文赋的线性演进历程,这符合历史不可逆的单线发展理念。
章学诚曾说:“六经皆史也。”[6]1文史之间的关联性早已确立,自始存有交融、互渗机制,无法彻底将其对立分割开来。一方面,文学作为抒写历史文本的必不可少的手段,是用来记录、还原历史真实的重要途径之一,且文学文本具有反映、记录历史的功能。如现实主义文学家巴尔扎克作为法国社会的“书记员”,其作品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真实再现了法国社会历史。另一方面,按照马克思的划分,文学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存在的。历史环境可以通过政治等因素影响文学的演进,如魏晋时期政局混乱,玄学兴盛,文人尤好老庄,玄言诗风靡一时。在宋代,从苏东坡等人散文与赋体的创作中可以看出,这两类文体的界限已不明显,这种当时的文学新现象昭示了赋体在朝着散文化的方向迈进。若论其背后的本质,郭绍虞说道:“宋代文坛上,散文战胜骈文;韩、柳虽创古文于先,而古文的势力实至宋代而始盛。所以宋人改用散文的方法以作赋,遂能别创一格,成为文赋了。”[7]85宋代的散文家多兼赋家身份,因此该时期的赋格多受文格左右。郭绍虞将文赋置于古文运动的背景下进行思考,注意到宋代古文运动对于赋体文学创作的波及与渗透,揭示了散文与赋两种文体间的动态关联与影响作用。将赋体发展演变与历史演进相结合考察,在史学维度上窥探影响赋体演变的文化环境,揭示赋体发展演变与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之间的关联,以探清其背后的本质问题,是郭绍虞论赋体源流的灼见。郭绍虞关于以上问题的视角与观点,为现当代学者所普遍接受。
郭维森、许结在此基础上,结合每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发展状貌,对赋的演变问题作了更细致地梳理。他们认为:“中唐以后伴随古文运动出现的类文之赋,是唐人辞赋创作过分诗化的自赎,这种自赎延至北宋新文赋体的出现,构成辞赋艺术继汉以降又一次以文为赋之创作高峰。”[9]29郭维森、许结将文赋置于古文运动中考察,认为宋人创作文赋是潜意识里对唐赋过分诗化的拨正。叶幼明将赋分为:诗体赋、骚体赋、散体赋。以散体赋为例,叶幼明又将散体赋的发展流变划为4个主要时期,继而又于此种发展演变当中归纳出散体赋的4个体式。叶幼明认为,“汉代是散体大赋时代。汉代是我国散文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魏晋南北朝是骈赋时期……魏晋时期,骈文正式形成,骈赋也随之出现”[10]62,“唐宋是律赋时期。在唐代,诗歌随着声律对偶的讲求而出现律诗,并成为唐代科举考试的重要科目。赋也随着律诗的形成而在逐渐格律化,并且也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科目”[10]63,“唐宋又是文赋时期,韩愈、柳宗元掀起古文运动,反对骈文,要求用三代两汉时期那种句式长短随宜的散文写作……随着古文的盛行,赋也重新趋向散文化而出现一种新的赋体——文赋”[10]64。显然,叶幼明以每个时代的文史背景为视域,将着力点放在赋与诗、文等其他文体的关联影响与文人的多重身份上,并看到了科举体制对文体发展的影响,而后分述每种赋的嬗变历程。这种研究方法在郭绍虞的研究视角上又有所推进,进而丰富了赋学的发展。
可见,郭绍虞在进化史观影响下所形成的赋体源流观,不仅在当时属于新观念,而且对后来的学者讨论赋体源流演变问题也具有启发意义。
二、现代语言学视角下的赋体文学性
汉代以来的学者,从多个角度对赋的文体本质进行过论述。自东汉班固《两都赋序》始,后人多从赋与诗文的关系出发,探讨赋的文体本质问题。南朝梁文学理论家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言:“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4]134是从赋的文体特色出发来区别赋与其他文体的代表性论赋之语。此后,在漫长的赋学发展史中,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也不乏精辟见解。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兴起,西方传入的“人”学观念在学界蔓延。至此,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学形式受到极大冲击,而作为历史性文本的赋体文学则首当其冲。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赋被一些学人贴上了“贵族之文”“山林文学”等标签。这就使赋体的文学性在当时受到普遍质疑,赋学发展也蒙上一层时代阴影。与此同时,现代语言学也随着西学东渐传入中国,并逐渐融入传统的古典文学研究中,从而形成新的研究格局。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与语言学具有复杂的纵横交错关系。就本质来看,一方面,语言、文字是构成文学作品的基本元素,是外在形式。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文字对文学作品来讲必不可少。另一方面,文学研究尤其是文学文本研究又离不开语言学这门工具,两者联系极为紧密。韦勒克认为:“语言是文学艺术的材料。我们可以说,每一件文学作品都只是在一种特定语言中文字语汇的选择。”[11]163从语言学视角研究文学是将现代语言学原理应用于文学研究的一种范式,可以理清诸多文学现象背后的本质问题。郭绍虞对此有足够认识,认为“文学的基础总是建筑在语言文字的特性上的”[7]497。在郭绍虞所处的时代,语言学正由传统向现代过渡,并且,现代语言学开始被应用于文学研究中。汉语具有有别于西方语言的一套独特语言体系,因此,从民族语言文化视角出发来对待由汉语构成的独特文体现象——赋,具有十分重要的民族文化意义,这也是文学文体上的中、西之别。从这种意义上来理解五四时期赋体文学性所遭受的否定,不过是当时的学人没有认清文化壁垒下的西学理论盲区的存在,而直接将西学理论武断地应用于本民族文化遗产的阐释之中所造成的。
基于以上认识,郭绍虞论赋时说道:“赋之为体,非诗非文,亦诗亦文,所以中国文学中之诸种文体,其性质最不明确者即是赋。”[12]1赋体由于汉语的独特造语结构而形成的“非诗非文,亦诗亦文”的特征,正是该文体特有的民族色彩。郭绍虞在论中国语词之“弹性作用”时讲到,汉语的弹性作用在文学作品中有着明确表现,中国古代文人,“在骈文与诗歌中间,往往利用文字之单音,使成为文辞上单音步的音节,利用语词之复音,遂又成为文辞上二音步的音节。单复相合,短长相配,于是整齐中含铿锵,参差中合自然,而文章掷地真可作金石声了”[13]74,由此就形成了中国文学中的特殊韵律。实际上,不仅是骈文、诗歌,赋也是常将汉语单复音融合变换的典型文体,如赋语中联绵字的使用[14]。有鉴于此,郭绍虞点明了赋体的独特民族文学性:“赋法最能发挥中国语言文字之特性,又最适合中国人思想之范畴。”[12]3短短的论赋之语,却极具启发意义。郭绍虞将现代语言学引入传统的文体研究中,再与其他民族语言进行比较,从而解剖出赋体的语言学本质。郭绍虞将浓厚的本土意识与民族意识寓含于赋体的阐释之中,点明了赋体的民族文学特质,一语道出这种西方文学所不具备的文体之于中国语言文学的独特意义,从正面肯定了赋体的文学性,也坚定了后来学者探究赋体的信心。在《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一文中,郭绍虞主张赋体的创作应当在现代文学中延续下去,可称其为“白话赋”。郭绍虞赋论成为从现代意义上评价赋体文学性的开端,后来承继者不胜枚举,且多有所发展,开始了现代意义上对赋体文学性的新探索。
龚克昌认为:“汉赋是较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的。千百年来强加在它身上的一些鄙薄之词是到了可以推翻的时日了。我们应该给它恢复名誉,把它提高到应有的高度来评价,作为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加以批判地继承。”[15]1龚克昌从现代性的辩证眼光出发,重新审视赋这种传统的古代文体,合理地肯定了汉赋的文学性与艺术性,在明辨赋体文学性的基础上,呼吁新时代的学者关注赋这种历史性文本并客观地发掘其文学价值以及传统文化意义。万光治认为:“文学的艺术归根结底,是语言的艺术;赋作为一代之文学,如果在当时并无所谓语言的魅力,显然不可能激发起一大批作家的创作激情并吸引为数更多的读者。”[16]295万光治以语言学、文学创作学、传播学、接受学作为切入角度,肯定了汉赋的语言艺术,探寻了赋体创作、传播与接受之兴盛局面背后的本质问题,认为这种现象正是汉赋文学性的光环所引发的外在效应。曹道衡的观点明显承继郭绍虞的观点:“赋这种界于诗和散文之间的文体,也许是我国古代所特有的一种文学现象。”[17]1曹道衡从赋的独特文体特征出发,将这种文体理解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言下之意,赋作为中国古代所特有的民族文学形式,不能以对待诗、文等其他文体的常理度之,应当对它的文体特征及文学性给与特殊关照。马积高也有相似观点:“在我国古代丰富的文化遗产中,赋是一种最有民族特色的文学体裁。”[18]1康金声从美学角度出发,认为:“赋又是最能展示汉语文学独特审美情趣的一种重要体式。”[19]3文学具有审美特征,且“审美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的多样种类之一。文学正是这样一种审美意识形态”[20]58,一语点出了作为汉语文学之赋体所独有的文学审美特质。这些现当代学者的论赋之语,与郭绍虞观点如出一辙,同时又有新的开拓。
三、对赋体文学史地位的承认
赋体形成较早,产生于战国时期,至汉代达到创作上的鼎盛,被后人誉为“一代之文学”,其文学史地位得到确立。汉赋彰显了汉王朝的大气,铺叙体物极具文学性,是时代风格的体现。至唐,科举试赋,文人作律赋,时代赋予这种文体正统的文学地位。降至晚清,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21]1。王国维明确将汉赋与唐诗、宋词并列提及,肯定了汉赋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就作品的后世传播与影响来看,或许汉赋的成就不及唐诗、宋词,但它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学之代表的文学史地位不容否定。
郭绍虞能出脱时代苑囿,在进化史观的视域下阐释赋体的体式流变,不仅明晰了赋体独具特色的发展脉络,还展现了这种文体仅次于诗文的漫长生命力。他在语言学视角下发掘出的赋体的民族文学特质,也证实了这种文体在某种意义上的独特文学性。郭绍虞以上论述足以使赋体的文学史地位得到证明。具体来看,基于对赋体源流演变及文学性的认识,郭绍虞将赋体与其他古代文体等同观之,肯定了赋体文学应有的文学史地位。他反对“有些讲文学史的人,因为反对旧时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之说,而以为汉赋在文学史上为最无价值,或且不认之为文学”[7]86-87。郭绍虞认为,赋作为一种文体,在历史上一度存在过,既有独特的文体渊源、嬗变路径及文学性,那么就自有文学史意义,应当在漫长的文学史上占据一定地位。郭绍虞对赋体文学史地位的肯定坚定了后来学者对赋体文学价值与重要意义认识的信心。
在后来的赋体批评中,现当代的多数学者对赋的文学史地位持肯定态度。马积高认为“否定汉赋价值的意见是站不住脚的”[18]10,且“赋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既有其自身的独立发展过程,又以其优秀的篇章丰富了文学遗产的宝库”[18]14,从而对历代赋家创作出的优秀赋篇予以赞扬。龚克昌在论及汉赋时曾言:“我越发感到汉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巨大价值和不可替代的地位。”[22]48龚克昌意识到赋对于中国文学的巨大价值,肯定了赋独一无二的地位。万光治也曾说:“在中国文化史上,赋是作家第一次自觉地把文学与学术区别开来进行创作所取得的成果。它以其作家的广泛性和作品的丰富性成为一代之文学,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6]183-184万光治从文学发生说以及作家与作品创作的角度来解构赋体的文化史地位,并给予肯定,具有独特的视野。康金声则从文体学角度肯定了汉赋的一代文学之地位以及赋体的重要性:“汉赋是一代文学的正宗,且创成了两千多年相沿不绝的一种重要文体。”[19]1
以上诸位学者的论赋之语皆与郭绍虞的观点一脉相承。可见,郭绍虞赋论对于后来的学者开展现代赋体批评实有导先路之功。
四、结 语
综上所论,郭绍虞将西学视野融入古典文学的研究传统中,既持守了传统文体批评的递延脉络,又在进化史观、现代语言学思想下试图建构新的研究范式。郭绍虞不仅就赋体的源流演变问题提出一家之言,还着力阐释了赋体作为汉语文学自身所独有的民族文学性,继而肯定了赋的文学史地位。总之,郭绍虞的赋学观念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特征,在捍卫民族文化本位的同时,又有所拓展,为中国赋论由古典传统迈入现代化历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