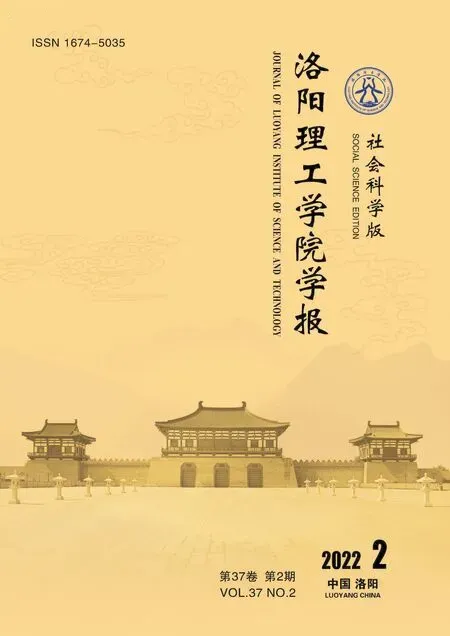论小说对李贺诗歌创作的影响
2022-11-26李昌平
李 昌 平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安徽芜湖241000)
诗歌在盛唐已臻巅峰,到贞元、元和时面临着创新发展任务。“制从长庆辞高古,诗到元和体变新”(白居易《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这使得诗人将眼光放到诗歌之外的诸种文体。古文运动使散文创作取得一定的成功,传奇也进入创作高潮,“以文为诗”被引入诗歌,使得诗歌抒情与叙事并重,引起诗歌体式的变革。唐传奇及唐以前的野史、笔记等也影响诗歌创作,胡应麟说:“唐人小说如柳毅传书洞庭事,极鄙诞不根,文士亟当唾去,诗人往往好用之。”[1]370这说明吸收小说入诗在唐代成为一种风尚。
余恕诚说:“从李贺等滥觞,到李商隐深入推进,大量吸收偏记杂录、志怪小说、神鬼故事、野史传奇内容,吸收传奇小说的艺术经验与笔趣,其变化则是更为深入的。”[2]李贺、李商隐、温庭筠等人,在诗歌中援引奇闻逸事、野史杂记、传奇小说,征事用典隐僻猎奇,情思超出常理,难以捉摸,使诗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纪昀将其视为唐诗的“升降大关”[3]609。这里的“小说”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它既包括先唐的稗史、杂记、笔记,也包括唐代新兴的传奇。李贺是较早将小说融入诗歌的诗人之一,其诗歌在内容、风格以及手法等方面与小说有深厚的渊源,在诗歌的变革过程中有着重要影响。
一、采撷小说意象和典故入诗
杜牧为李贺诗集作序:“贺能探寻前事,所以深叹恨古今未尝经道者。”[4]8李维祯提到:“会稽曾谦氏取长吉诗为之注释,自六经子史、六朝汉魏稗官小说,无所不攟摭。”[4]198可以看出,李贺诗歌中运用的小说意象和典故来源广泛。遍览李贺诗集,采用的典故既有正史中的人物和事件,也有稗史杂记收录的逸闻逸事及古往今来的神话故事和风俗传说。
李贺运用正史中的典故不少。《咏怀二首》其一“长卿怀茂陵”[5]63写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以辞赋闻名,先后受到梁孝王与汉武帝的赏识,人们却只识其文采而不察其治国大才。王琦谓:“此篇盖借司马长卿以自况也……谓己在时,上之人皆弃而不用,至身没之时,见其遗书,而反思之以施用于世也。”[6]42此诗作于李贺不得举进士而回归昌谷之后,李贺以司马相如自比,在轻描淡写之中透露出满腹牢骚和希望有慧眼之人给予自己施展才华的机会。如《南园十三首》其十“边让今朝忆蔡邕”[5]520,用蔡邕举荐边让典故;《南园十三首》其十二“谁遣虞卿裁道帔”[5]524,写战国时期赵国虞卿;《绿章封事》中“扬雄秋室无俗声”[5]306,是西汉扬雄的典故。李贺仕途不顺又多愁善感,只能在这些与自己有着相同经历的文人名士中寻求心理上的自我安慰,感叹明珠埋尘的无奈,渴望伯乐赏识以助自己实现人生抱负。安史之乱后,唐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况,李贺痛心疾首,在诗中运用史书中的典故加以揭露和抨击。姚文燮说:“故贺之为诗,其命辞、命意、命题,皆深刺当世之弊,切中当世之隐,倘不深自弢晦,则必至焚身。”[6]192《汉唐姬饮酒歌》中李贺借“董卓鸩杀汉少帝”的典故影射永贞政变。李贺用典故中人物的遭遇抒己之怀,有着浓厚的家国情怀。
除正史中的典故外,李贺对野史逸闻、笔记小说有浓厚的兴趣。王思任曰:“(贺诗)有典谟训诰之正,则必有竹坟石鼓之奇。”[4]200这种“奇”体现在李贺的诗歌中便是稗史杂记、风闻传说入诗。采自稗史杂记者,如《河阳歌》“颜郎身已老”[5]549用《汉武故事》中汉武帝拜颜驷为会稽都尉的故事,《猛虎行》“东海黄公,愁见夜行”[5]151用刘歆《西京杂记》中东海黄公的故事。采自志怪小说者,如《始为奉礼忆昌谷山居》“犬书曾去洛”[5]138中的“犬书”出自《述异记》,《嘲雪》“久别辽城鹤”[5]747用《搜神后记》中“丁令威化鹤归辽”的故事。采自志人小说者,多出刘义庆《世说新语》。如《后园凿井歌》“情若何,荀奉倩”[5]545,语出《惑溺篇》:“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7]918《苦昼短》“飞光,飞光,劝尔一杯酒”[5]207,语出《雅量篇》:“太元末,长星见,孝武心甚恶之。夜,华林园中饮,举杯属星曰:‘长星,劝尔一杯酒,自古亦何时有万岁天子。’”[7]378
李贺还对神话传说、风俗纪闻有浓厚的兴趣。《瑶华乐》“穆天子,走龙媒”[5]216用《穆天子传》周穆王驾八骏游昆仑山拜会西王母的故事。《兰香神女庙》用“杜兰香神女”的传说,描绘了神女庙的环境,“借兰香以表己之贞素,是故备言其人境之洁”[4]253。《贝宫夫人》用民间海神的传说,《苏小小墓》用鬼妓苏小小的传说。《苦昼短》中“谁是任公子,云中骑白驴”[5]207用民间传说“仙人骑白驴”,又融合《庄子》中“任公子投竿东海”的传说。采择资料入诗不限单一来源,而是糅合多种材料,塑造出看似耳熟能详的人和事,但细究起来又难寻踪迹。
李贺巧妙地将稗史杂记、神话传说熔铸诗歌中,以此表达身世之感或现实批判。《河阳歌》中的颜驷年少时未得重用,到年老才为汉武帝拔擢,其经历触动了李贺。元和八年(812)六月,李贺去潞州谋求仕途,取道河阳,作此诗。姚文燮注曰:“言当春盛,正及花繁,而我仅为奉礼,如颜驷为郎之日,不复少矣。”[6]253昔日踌躇满志,希冀一举中第,如今又遇故人,自己却没有功成名就,反而投靠朋友谋求出路。颜驷年老,尚得汉武帝拔擢,自己年岁尚轻,却暮气沉沉,前途渺茫。或用典故隐喻一些难以明说的事情,如《猛虎行》。古乐府《猛虎行》主题为“不以艰险改节也”[8]676,而李贺此诗紧扣“猛虎”为题,用了“东海黄公”“道逢驺虞”“泰山妇人”三个与虎有关的典故,言虎之凶恶。钱仲联云:“《猛虎行》,刺成德军之叛乱。”[9]44叶葱奇说:“这首诗讽刺当时的藩镇强据一方,子孙相承,肆为凶恶,而中央一时姑息畏葸,不能任用贤才,加以征讨。”[10]264中唐时期,朝廷处理藩镇不力,藩镇势力坐大,将势力渗透到朝廷内部,甚至暗杀朝廷官员,人心惶惶。李贺有感于此,用隐晦的方式表达自己对藩镇的痛恨。
李贺将史书中的典故、奇闻逸事和稗史小说融入诗歌,不仅是个人创作倾向,也是当时的文学风尚使然。中晚唐诗歌相对于盛唐最大的特点就是昂扬向上的理想主义与浪漫精神的退却,诗歌的现实性与世俗性加强,诗人将目光投向社会底层,诗风由庄重变为戏谑。稗史小说不仅为诗人采撷入诗,文人创作小说也成为风尚,诗歌在这种环境下必定受小说影响,“诗歌适应社会文化环境变化特别是世俗审美趣味变化做出的积极反应,使中晚唐诗歌从一些方面展现出传统所从未曾有的面貌,对于诗歌艺术是重要的开拓和丰富”[11]283。
二、借鉴传奇小说手法创作诗歌
李贺善于将小说中常用的场景设计和氛围渲染用于诗歌,并将人物塑造与之结合起来。如《公莫舞歌》,本是《史记》“鸿门宴”的故事,记述项伯在鸿门宴上保护刘邦。李贺诗前有小序:“公莫舞歌者,咏项伯翼蔽刘沛公也,会中壮士,灼灼于人,故无复书,且南北乐府率有歌引。贺陋诸家,今重作公莫舞歌云。”[5]699李贺诗意在翻新,改为赞颂刘邦。此诗起笔不同凡响,一连用了“刺豹淋血”“长刀”“无桐竹”“割鸣筝”等意象,这种视觉和听觉的感官冲击,给人一种恐怖阴森的感觉,营造了紧张骇人、杀气四伏的氛围,暗示了刘邦的困境。这种环境描写与场面设计在小说中被广泛运用,对于故事的推进及人物的塑造有重要的作用。接下来描写项羽的勇猛、范增三次示玦的焦急以及项庄舞剑的咄咄逼人,李贺在描写这些人物时选取人物典型的动作,节奏紧凑、急促。之后转入樊哙的视角,怒斥项羽,掩护刘邦,塑造樊哙赤胆忠心、奋勇救主的形象。整首诗描写有声有色,场面宏大逼真,氛围渲染到位,人物描写传神,用极短的篇幅将鸿门宴最精彩的部分呈现出来。
李贺用诗歌演绎一些典故时,没有按照故事原本的发展来叙述,而是用小说笔法虚构情节,让诗歌在叙事的外壳下抒情。如《金铜仙人辞汉歌》,诗前有序:“魏明帝青龙元年八月,诏宫官牵车西取汉孝武捧露盘仙人,欲立置前殿。宫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唐诸王孙李长吉遂作《金铜仙人辞汉歌》。”[5]159裴松之《三国志》注引《汉晋春秋》记载,魏明帝拆取铜仙人并没有成功,因为太重就留在霸城,但李贺虚构了铜仙人从长安运往洛阳途中的情节。诗用拟人的手法,时而从正面描写铜仙人在途中的感受,时而转入对途中环境的描写,整首诗弥漫着一种忧伤的情绪。铜仙人寄托了汉武帝渴望长生的愿望,同时也象征国力昌盛的大汉帝国,然而帝国盛世就像汉武帝希望长生一样早已虚无缥缈。送别自己的只有咸阳道边的“衰兰”,陪伴自己的只有承露盘以及对故国的追忆。李贺虚构铜仙人被运往洛阳的情节,同时也将自己的情感投射在铜仙人身上。关于此诗的创作年份,钱仲联认为作于贞元二十一年(805),“贺以同情王叔文诸人政治革新之立场,伤其遭遇,作《金铜仙人辞汉歌》《还自会稽歌》,皆托古寓事,反映永贞朝政变”[9]20。吴企明认为此歌作于李贺长安任职期间,认为李贺在长安获知宫闱秘事,更亲眼见到统治阶层对藩镇政策的失误以及贵族们的骄奢享乐,而唐宪宗迷恋丹药,致使大好的中兴局面付之东流。感于此,李贺不禁陡生家国之痛,统治上层不图恢复,那些希望通过变法改革以再造盛世的有志之士却被贬杀,已见亡国之兆。李贺不拘泥于已有的史实和传说演义一些故事,并通过想象的方式虚构情节,在诗歌中运用小说笔法,这在诗歌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李贺借传奇小说中人物心理描写方法创作诗歌。其组诗《谢秀才有妾缟练,改从于人,秀才引留之不得,后生感忆,座人制诗嘲诮,贺复继四首》,如下:
谁知云忆泥,望断梨花春。荷丝制机练,竹叶剪花裙。月明啼阿姐,灯暗会良人。也识君夫婿,金鱼挂在身。[5]415
铜镜立青鸾,燕脂拂紫绵。腮花弄暗粉,眼尾泪侵寒。碧玉破不复,瑶琴重拨弦。今日非昔日,何人敢正看。[5]417
洞房思不禁,蜂子作花心。灰暖残香炷,发冷青虫簪。夜遥灯焰短,睡熟小屏深。好作鸳鸯梦,南城罢捣砧。[5]419.420
寻常轻宋玉,今日嫁文鸯。戟干横龙簴,刀环倚桂窗。邀人裁半袖,端坐据胡床。泪湿红轮重,栖乌上井梁。[5]421
从诗题可以得知,李贺这组诗是有事件来源的。在写这组诗时,李贺并没有平铺直叙,以缟练的心理变化为线索串联起整个事件。方扶南《李长吉诗集批注》[6]312中对这组诗做了批注,第一首言“初去”,缟练弃谢秀才而去,又心生悔意。第二首言“去后初景”,缟练对镜饰容,浓艳的妆也难以掩盖眼角的泪痕,她现在的感情生活并不如意。第三首言“去后浓情”,“洞房”句点明缟练感忆之情不能自禁,李贺嘲笑她虽有新人,仍饱受寂寞之苦,即使自己盛妆艳饰,却无人欣赏自己,只得独守空房,而一切的美好只能从梦中去回忆了。第四首言“感忆”,缟练直言自己遇人不淑,“戟干横龙簴,刀环倚桂窗。邀人裁半袖,端坐据胡床”,活脱脱一个莽夫,又怎会怜香惜玉呢?李贺展现了人物心理的变化,讥诮缟练对感情有始无终。
在诗歌写作中借鉴传奇小说手法,在李贺的诗中已现端倪,晚唐李商隐、温庭筠等人更是发扬光大。尤其是李商隐的诗歌创作,采集小说中的故事,运用小说笔法,并与诗的整体构思融为一体,形成了浑融的艺术特色。李贺在诗歌中融入小说的创作手法,新颖生动,让诗歌自身获得丰富和提高,使其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
三、荒诞奇异、诙谐滑稽的艺术特色
关于李贺诗歌的艺术特色,有诸多评论。唐代杜牧曰:“鲸吸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荒诞虚幻也。”[4]8宋代周紫芝言:“李长吉语奇而入怪。”[6]24元代范梈说:“长吉虚妄,不可效为。”[4]83明代王世贞认为:“李长吉师心,故尔作怪,亦有出人意表者。”[4]118明代焦竑评价:“(长吉、义山二家)摆落常诠,务为奇崛。”[4]199对于李贺诗歌的艺术特色大体不过“奇”“怪”“奇崛”“虚妄”等,这与李贺爱采撷志怪小说中的神鬼仙怪等入诗有很大的关系。
李贺诗歌常有描写鬼怪神仙的。如“呼星召鬼歆杯盘,山魅食时人森寒”(《神弦》)[5]398写鬼吃人,“百年老鸮成木魅,笑声碧火巢中起”(《神弦曲》)[5]395写鬼火,“嗷嗷鬼母秋郊哭”(《春坊正字剑子歌》)[5]193和“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秋来》)[5]688写坟墓。李贺写鬼怪与唐前的志怪小说如出一辙,阴气森森,让人如临其境,不寒而栗。李贺不仅将笔触伸向鬼域,而且也描写仙界,如《罗浮山人与葛篇》《天上谣》等。鬼域与仙界是两种极端,李贺用超出常规的思维,描写凄冷恐怖的鬼域以及令人向往的仙界,不仅是受了唐人传奇中爱写鬼怪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李贺自身抒情的需要。“生命”一词对李贺而言是非常敏感的,鬼和仙是生命的两种不同的存在形式,李贺体弱多病,对于生命的思考常会出现在诗歌中。但李贺并不沉迷对长生的追求,在诗中多次写秦始皇和汉武帝,他们企图长生不老,可最后都成了冢中枯骨,并借此讽刺唐宪宗沉迷丹药。人生短暂,现实不公,以及怀才不遇的痛苦,让李贺对现实世界充满了悲观与失望。李贺反对神仙迷信,但却没有否定神鬼世界。于是李贺便将对现实世界的悲观与失望寄情于神鬼,更加关注那些怪异、阴森、凄冷的意象。李贺在诗中用大量的神鬼意象寄托情思,使得诗歌具有“奇怪”“虚妄”的艺术特色。
李贺的诗歌还具有诙谐戏谑的艺术特色。如《昌谷读书示巴童》言:“虫响灯光薄,宵寒药气浓。君怜垂翅客,辛苦尚相从。”[5]68“虫响”句言环境幽静以衬自己的愁绪,“宵寒”句则言自己病体缠身。用《后汉书·冯异传》“垂翅”的典故,来比喻自己前途失意。前途渺茫,病体难愈,小巴童对自己不离不弃,李贺以“君”称之,足见喜爱。姚文燮曰:“长夜抱疴,遭时蹭蹬,而巴童犹然恋恋,深足嘉已。”[6]246第二首是《巴童答》:“巨鼻宜山褐,庞眉入苦吟。非君唱乐府,谁识怨秋深。”[5]69这是诗人代巴童回答,“巨鼻宜山褐,庞眉入苦吟”这句是李贺自嘲。李贺貌质丑陋,自怀大才,却前途失意,顿生一种自卑感,而小巴童知道自己深于吟咏,并非苦吟,必有寄托,巴童已经是李贺的知己了。李贺通过自嘲,在这一示一答中,展现出一种谐趣。
李贺诗歌的荒诞特色体现在一些游仙诗中,往往突破时空局限,随意驰骋。如《梦天》一诗,黄周星在《唐诗快》中评曰:“命题奇创。诗中句句是天,亦句句是梦,正不知梦在天中耶,天在梦中耶?”[4]233姚文燮评曰:“滓淄既尽,太虚可游,故托梦以诡世也。蓬莱仙境,尚忧陵陆;何况尘土,不沧桑乎?末二句分明说置身霄汉,俯视天下皆小。”[6]214此诗驰骋想象,前四句写月宫,月宫在雨雾的掩映下有种朦胧迷离之美。诗人被月宫的美景吸引,仿佛融入其中,世俗的烦恼都抛诸脑后。“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出自葛洪《神仙传》,言时光飞逝。最后两句是写下望所见,诗人感觉九州如烟尘般渺小。整首诗节奏跳跃,任意驰骋,寄寓了李贺对人世沧桑变化的深切感悟,表现了他对于时光飞逝的时间观念,这种时间观念同样受唐前志怪小说的影响,如《幽冥录》中“刘晨阮肇”的故事,《神仙传》中“壶公”的传说等都是人入仙界,时光飞逝,世殊时异,与李贺梦入月宫有异曲同工之妙。
李贺体弱多病,对于生命的体悟十分深刻。钱锺书说:“其于光阴之速,年命之短,世变无涯,人生有尽,每感怆低徊,长言咏叹。”[12]58他的很多诗歌都具有跳跃式的荒诞感,穿古越今。如《古悠悠行》:“海沙变成石,鱼沫吹秦桥。空光远流浪,铜柱从年消。”[5]205这首诗亦感时伤逝,海中的沙子在岁月的锻造下变成石头,当年秦始皇造的石桥如今只有鱼儿在嬉戏,汉武帝造的铜柱在岁月的侵蚀下早已销灭不存。整首诗不言生死,而言时光流转匆匆,那些渴望长生的帝王,早被岁月淹没,哪有一个长生?相比《梦天》,《古悠悠行》更具讽刺意味。这两首诗皆表达岁月变换与生命短促之间的矛盾,在其他诗中李贺用更荒诞的笔触和逆向思维写了神仙同凡人一样也会死亡,如《浩歌》“彭祖巫咸几回死”[5]127、《官街鼓》“几回天上葬神仙”[5]198,超出人的一般思维,虽然荒诞无稽,但对于生命的感悟却是铿锵有力。面对时间的折磨,李贺不是坐以待毙,而以更荒诞的行为企图摆脱时间的束缚。《苦昼短》展现了李贺大胆的想法,诗中写道:“天东有若木,下置衔烛龙。吾将斩龙足,嚼龙肉,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伏。自然老者不死,少者不哭。”[5]207李贺借神话中“若木”“烛龙”,倾诉了对生命的美好愿望。但是李贺有一个荒诞、大胆的想法:斩断烛龙四足,大嚼龙肉,让它早上不得巡回,夜晚不得伏息。如此太阳就没有东升西落,时间不再流逝,人们不会因衰老而焦虑。这是他的幻想,虽然荒诞,却充满浪漫与激情,此时的诗人成为时间的主宰,把时间的公平带给每一个人。钱锺书《谈艺录》将此诗与李白《日出入行》比较:“(太白)自天运立言,不及人事兴亡,与长吉差类。然乘化顺时,视长吉感流年而欲驻急景,背道以趣。”[12]59尽管是借神话形式,虽然荒诞,却能打动人心,闪耀着理想与智慧光芒,使艺术得到升华。
潘德舆《养一斋诗话》中评论李贺诗歌:“以极艳之辞,写极惨之色,宛如小说中古殿荒园,红妆女魅,冷气逼人。”[13]2080李贺诗歌尚奇、尚怪、荒诞的艺术特色,很明显是受了志怪小说的影响。
四、结 语
一种文体不可能单独发展,必然会受其他文体的影响,多种文体相伴生长,相互交融借鉴,实现文体的创新发展。中唐以后诗歌面临着求新求变的任务,必须吸收各种文体为诗歌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活水。李贺的诗歌在用典方面择取小说中的意象入诗。在诗歌创作方面借鉴小说笔法,虚构情节,营造氛围,铺演故事,让诗歌的叙事性加强,抒发情感更加深刻。在艺术特色方面,李贺爱用志怪小说中鬼怪神仙的意象,形成鬼魅骇人、奇崛荒诞的艺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