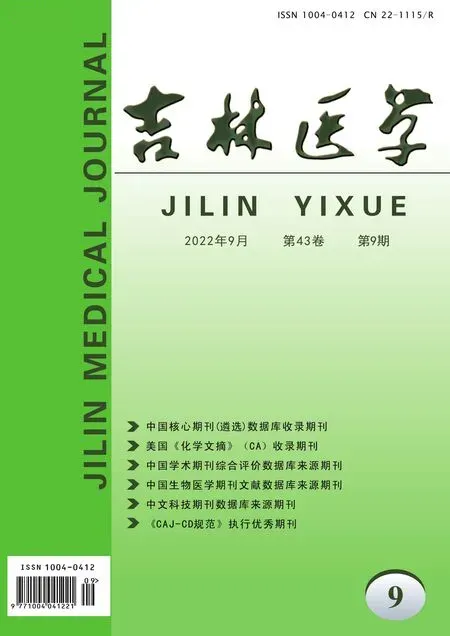生前预嘱问卷调查与尊严死亡研究
——生命末期管理模式探索
2022-11-26王灵强
袁 月,王灵强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四医院,吉林 长春 130000)
生前预嘱是指人们在健康或者意识清楚时,先行考虑在濒临死亡或处于不可逆转的昏迷状态下,谁来替自己做哪些方式的医疗决定,从而签署的相应文件[1]。通过生前预嘱给予患者更多医疗自主权,对生命尽头的治疗方式进行自主选择,最大限度减少患者承受的病痛煎熬和“过度的”创伤性治疗,让患者自然又有尊严地走完生命旅程,不仅有利于减少患者在临终前的焦虑不安,对医患纠纷的减少、消失和营造良好的就医环境也起到一定推动作用[2]。生前预嘱为老龄化社会下老年人生命末期健康管理模式提供新方向。我国第一个生前预嘱协会于2013年6月在北京成立,通过“选择与尊严”公益网站[3],为人们提供自愿填写生前预嘱的平台,截至目前已有注册会员5万多人,逐渐引发了一系列生前预嘱话题的讨论,探讨其实行的有效性。生前预嘱在我国仍是较新概念,且在现有社会经济和法律规定下仍存在使用困惑[4],为进一步探究人们对生前预嘱相关问题的真实看法,本文对此进行问卷调查。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课题组制作了包含22道问题的《生前预嘱问卷调查》,从“对死亡的看法”“临终的计划”“对不可治愈的伤病生命末期的医疗选择”“医疗自主权”和“生前预嘱的认知态度”等五个方面进行提问。同时,问卷也分别对填写者的性别、年龄、婚配情况、居住地、受教育程度、职业、医疗付费方式和宗教信仰等8个方面进行提问,以进行进一步数据统计。本研究经过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同意。
1.2方法:此次问卷共成功收集1 063份有效问卷。其中,男430名,女633名;填写者年龄主要集中在21~60岁,其中41~60岁共659名,占61.99%;从婚配情况看,已婚人士947名,未婚人士116名。共有来自21个省、4个直辖市、4个自治区和1个特别行政区的人填写问卷,辐射面广,其中,参与程度最高的是福建省和吉林省。从教育程度看,问卷填写者涵盖了自高中及以下至博士的所有教育阶段。问卷填写者涉及行业广泛,人数比例较高的五大职业分别为公务员、企业职员、医务人员、教师和自由职业者。从医疗付费方式看,选择医保的有751名,选择公费医疗226名,自费86名。从宗教信仰看,737名无宗教信仰,224名有佛教信仰,102名有基督教信仰。个人特征在一些选择中具有趋向性。
2 结果
2.1对“死亡”的看法:生前预嘱的最基本前提在于,能正确地面对“死亡”这个概念。问卷问题“您是否愿意在需要时与人谈论死亡?”的选择结果显示,有88.05%选择“在需要时与人谈论死亡”。受访者普遍对“死亡”话题的包容度高,根据个人特征分析发现以下几个特点:
年龄与谈论死亡的意愿呈反比,自20~80岁以上5个年龄段愿意谈论死亡的比例分别为100.00%,88.36%,89.23%,77.03%,75.00%;受教育程度与谈论死亡的意愿呈正比,本科及以上的受访者愿意谈论死亡的比例均在85.00%以上,大专、高中及以下学历的意愿程度均低于82.00%;医务人员谈论死亡的意愿未高于其他职业,在五大职业中,其他四个职业的选择均高于86.73%,而医务人员只有84.51%。一些个人特征未有较明显的选择区别。
2.2对临终的计划:生前预嘱实质上是对自己的临终安排作提前计划,问卷共设计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您是否思考过自己的临终?是否通过任何方式安排过自己的临终?”问卷结果显示,有 93人(8.75%)选择了“思考过,安排过”,有605人(56.91%)选择了“思考过,未安排过”,有365人(34.34%)选择了“未思考过”。第二个问题,“生命最后一程您希望在哪里告别?”有55.13%的人选择了“家里”。第三个问题“您希望亲人朋友实现您最后什么愿望?”,有405人(38.10%)选择了“我希望尽可能有亲朋好友陪伴”,553人(52.02%)选择了“我希望告别仪式从简”,有879人(82.69%)选择了“我希望我的亲朋好友在我去世后能尽快恢复正常生活”。整体上看,目前整体上对临终安排的重视程度不高。
根据个人特征分析发现以下几个特点:从性别看,女性思考临终的比例高于男性,男性思考并做出临终计划的比例高于女性,男性未思考过临终计划的比例也高于女性;从年龄看,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临终思考和临终安排的人数比例都逐渐增加;从受教育程度看,思考过临终但并未安排的人数比例随着学历的增高逐渐降低,未思考过临终的人数比例则逐渐增加;从职业看,工作稳定程度越高,对临终的安排越少,但思考临终的比例越高;婚配情况和宗教信仰的不同对选择未有较大影响。
2.3对不可治愈的伤病生命末期的医疗选择:共设计了三个问题,主体分别假设为“我”“我的亲人”和“一个人”“在处于不可治愈伤病生命末期时,是否应该选择使用生命维持疗法来维持无质量、无尊严的生命?”,选择的比例分别为90.59%,56.63%和82.97%,在主体为亲人时,对生命维持疗法的依赖程度明显高于其他两项选择。
从性别看,女性选择不使用生命维持疗法的比例更高,尤其以“我的亲人”为主体时男女比例差距最大;从年龄看,年龄层越高越降低对生命维持疗法的依赖性,尤其在为“我的亲人”选择时比例差距最明显;从婚配情况看,未婚者与年龄低者重合率高,因此选择生命维持疗法的人多;从职业看,各种职业在三个问题的选择上比例相似,但医务人员在“我的亲人”为主体时,选择不使用生命维持疗法的人数远高于其他职业。有趣的是,以“我的亲人”为主体时,“不会”选择使用生命维持疗法的硕士人数为108人(52.43%),博士人数为65人(67.01%),比例差距最大。
2.4对医疗自主权的看法:共设计三个问题。问题“您认为,在不可治愈的伤病生命末期,相比延长生命,更应最大限度尊重、符合并实现本人意愿,尽量有尊严地告别人生吗?”,近96.00%的选择为“是”。第二个问题“您认为当一个人意识清楚时,谁应该成为临终要不要生命维持疗法的决定者? ”,有超过92.00%的选择为“自己”。第三个问题假设处于不可治愈伤病生命末期时,有533人(50.14%)选择了“我不要疼痛”,有519人(48.82%)选择了“我不要任何形式的痛苦,如呕吐、痉挛、抽搐、恐惧等”,有65.00%以上的人选择不增加痛苦的治疗,包括各种生命维持疗法,只有71人(6.68%)选择了“我宁愿忍受痛苦,也坚持使用生命维持疗法延续生命”。
从性别看,女性选择“自己”、男性选择“医生”为决定者的比例更高。女性选择生命末期“不增加痛苦的疗法”的比例也普遍高于男性;从年龄看,年龄的增加与选择“自己”为决定者的比例呈反比,对“医生”的依赖程度逐渐增加,另外,年龄在61~80岁间选择“我宁愿忍受痛苦,也坚持使用生命维持疗法延续生命”的比例高于其他组别;从受教育程度看,大专组选择“自己”的比例最低,选择“亲属和家人”的比例最高,而博士组别在选择形式时,对“我不要疼痛”等形式的选择都低于其他组别;从职业上看,医务人员选择放弃心肺复苏等维持疗法的比例高达76.00%;从医疗付费方式看,所有选择“医生”作为决定者的人均来自公费医疗和医保组别。
数据结果显示,绝大多数人都倾向于选择有尊严地告别人生,且大部分人对临终有较强的自我决定意识,有较强的医疗自主权,在面对生命末期的具体医疗手段时,选择非疼痛的治疗手段的人数比例基本都超过半数。
2.5对生前预嘱的认知态度:共设计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您是否了解生前预嘱”中“是”的比例只占34.81%。第二个问题“您认为推行”生前预嘱“是生命末期患者尊严死亡的重要途径吗?”,有89.65%选择了“是”。第三个问题有88.90%选择了“愿意填写生前预嘱”。第四个问题则对生前预嘱的建议作多项选择,有67.73%的选择关注了生前预嘱的法律效力,有51.74%的选择倾向于“在民间大力试行推广,待条件成熟时再上升到法律层面”,有71.87%的选择认为要“保证生前预嘱文件的公信力和有效性”。
从性别看,男性更了解生前预嘱概念,相较于其公信力和有效性,也更关注生前预嘱的法律效力;从年龄看,年龄越大对生前预嘱的了解程度越高,但填写生前预嘱的意愿反而降低了;从受教育程度看,填写生前预嘱的意愿也随受教育程度提高而提高,更关注生前预嘱的法律效力和公信力;从职业看,医务人员和公益组织对生前预嘱概念的了解程度高于其他职业,但也只有45.00%左右。医务人员更关注生前预嘱的公信力和有效性,公务员则更关注其法律效力;从医疗付费方式看,自费组对生前预嘱的作用认知和填写意愿都低于其他组别;另外,有宗教信仰者对填写生前预嘱的意愿也低于无宗教信仰者。
生前预嘱的认知程度仅有三成,且更多集中在相关从业群体。虽然它作为生命末期患者尊严死亡的意义获得了普遍认可,也有较高的填写意愿,但其法律效力和社会公信力仍有提升的空间。
3 讨论
3.1加强死亡教育:《最好的告别》书中提到,医患双方都要学习的任务是,在人的必死性方面谋求共识,并以生命尊严和保持有意义生活作为生存追求[5]。死亡教育的目的就是帮助人们正确面对死亡,树立科学、健康的死亡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同时,学习和探讨死亡心理过程,为处理死亡做好心理准备[6]。最终目的,是落实到每个人对生命的尊重和自主。
人口老龄化为代表的现实问题,也推动着社会开始正视和思考死亡问题[7]。但结果显示,在年长者和受教育程度偏低者身上,对“死亡”话题的包容性更低,近四成人从未思考过临终安排,都反映出死亡教育的不足。中国传统文化对死亡话题讳莫如深,“死亡”话题总与禁忌、伦理相联系,对年长者影响尤甚,导致他们无法正确面对和处理“死亡”话题。
然而,死亡教育是针对每个生命的基本教育、普遍教育和全民教育[8],开展死亡教育是帮助人们开启生命价值观的思考,通过各种方式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生老病死是生命的自然规律,珍视自己生命的价值,减轻临终患者的心理负担,提高对死亡的认识[9]。这是需要各级政府部门、学术团体、社会组织机构等社会各界的重视和支持的。提高老年人生命末期的生活质量,应将死亡教育应用于生命各阶段,在全社会、全民覆盖,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帮助他们用更平静的态度去面对死亡。
3.2加强生前预嘱研究体系建设:问卷中对生前预嘱概念知晓率只有34.81%,与其他针对不同群体的调查研究结果相似。例如何萍等对社区居民调查发现,对生前预嘱概念的知晓率为40%[10],Kang等对患者及家属的调查结果为38.3%的知晓率[11]。通过张蓉蓉等和王毅欣等对老年人以及晚期肿瘤患者的调查发现,调查对象不仅对生前预嘱理念认知水平低,对生前预嘱的认同度也相对较低[12-14]。对生前预嘱法律地位的探讨也需加强。生前预嘱的合法性研究具有必要性[15],生前预嘱可得合宪性考验,具有民法基础,并无法理上障碍[16]。
但目前而言,生前预嘱概念的认知程度整体偏低,作为新兴概念,其相关理论的研究缺乏连续统一的体系性成果,我国也未作进一步立法要求[17]。包括生前预嘱的概念解析,与相似概念的有效区分,适用对象、适用时间、适用环境等内容,也都未有统一可参照的文件标准。患者自主权包括了有放弃或者拒绝接受医疗救治的权利[18]。生前预嘱合法性的研究,既保障了患者的自主决策权,也保护医务人员治疗的合法性和权益。
以问卷为例,个人特征所影响的个人选择就为未来研究提供方向,从而有针对性地加强生前预嘱概念的体系研究,为其执行与实施制定行之有效的标准文件,提升其公信力和社会认可度,为其“合法”推广提供保障平台和文件参照。
3.3解决生前预嘱的伦理问题:生命维持技术主要用于自主呼吸、循环、消化等维持生命的重要器官衰竭的患者[19]。患者对这些技术依赖性强,也需要承担这些技术使用时对身体产生的伤害,在处于不可治愈伤病生命末期时,这样的治疗方式往往只能维持没有质量的生命状态。生前预嘱就为患者提供不选择生命维持技术的医疗自主权。但这种避免临终无效延长生命的理念是与中国的传统观念相互矛盾的。正如问卷中显示,大部分人仍然无法遵从亲人选择“放弃”生命维持技术的决定。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影响就表现在,当生与死被赋予道德意义时,尤其在患者家庭的决策权实际上高于患者本人的环境下,无论是患者家属,或者医生,都将“保持患者生命”置于最高追求,从而忽略了患者自身的意愿、尊严或者决定权[20]。中国人讲求孝道伦理,面对亲人选择“不救”,则会被定义为“不忠不孝没有人性”,成为亲人的困扰。生前预嘱本身具备预设性和提前性,也与传统文化中的“运势”“坏兆头”相关联,阻碍了人们接触此概念的积极性[21]。应解决生前预嘱所包含的伦理道德问题,加强正面、积极、科学的宣传方式,通过医务工作者的临床渠道加强引导,引入相关机构进行生前预嘱工作的推进,与患者及家属进行讨论、访谈和周期性沟通,辅助患者及家属作出适合的决定。
3.4做好医学行业人员培训工作:医务工作者是生前预嘱的见证者和实施者,他们的支持能使生前预嘱更加顺利地被推广和普及。目前研究却发现,医务人员对生前预嘱的概念并不熟悉。许琢等对护士生前预嘱的认知率调查发现,虽然对相关概念的认知程度中等偏上,但专业性不高,更多依靠的是自学理解[22]。董晗等对实习医学生的调查同样显示,对生前预嘱的认知程度超过了70%,但主要知识来源并非课堂教学,而是报纸期刊的自学过程[23]。针对某高校医学研究生的研究发现,对生前预嘱不了解的比例甚至高达79%[24]。吴梦华等也表示,医务人员的概念认识水平低也导致了生前预嘱实施困境[25]。问卷中义务人员的了解程度甚至不到50%。
应加强医学教育对生前预嘱知识的普及和推广,将相关内容加入课堂教学和医学类研究生培养计划中,推动相关专业对生前预嘱概念的掌握。应加强相关系统对生前预嘱法规和概念进行有效推广,通过各种讲座、研讨会和学术研究,增加医学行业人员对生前预嘱在法律法规制定、规则标准健全、社会推广和实践方面的参与程度,加强对生前预嘱的宣传与主题活动开展,增强医务工作者对生前预嘱的讨论与交流,并在临床工作中积极推广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