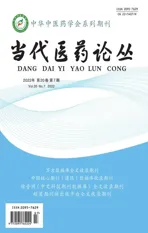新型冠状病毒对心血管系统损伤中西医机制的研究进展
2022-11-25陆依雯王振兴
陆依雯,王振兴
(1. 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苏 南京 210023 ;2. 江苏省中医院,江苏 南京 210029)
新型冠状病毒是一类具有极高传染性的冠状病毒。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是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而导致的肺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自2019 年年末被发现以来,迅速在国内外蔓延。截至2021 年7 月16 日19:21,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已达1.8 亿,其中有超过400 万人死亡[1],给全球的公共卫生安全及经济带来极大的挑战。目前来看,国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控工作卓有成效,但其他一些国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控工作仍面临着严峻挑战。新型冠状病毒的原名为2019 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2],后WHO宣布将其正式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新型冠状病毒虽然与SARS 病毒及MERS 病毒同属于β 冠状病毒,但它与这两种冠状病毒并非为完全相同,其主要累及呼吸系统,但也可对心血管系统造成损伤,部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甚至以心血管系统症状为首发症状[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常见的心血管系统损害包括心律失常、心力衰竭、急性心肌损伤及静脉血栓栓塞等[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属于中西医中“湿毒疫”的范畴。湿毒疫致心血管系统损害的过程在中医理论中早有记载。外感疫疠,邪犯心包,可耗气、动血、扰神,症见神昏、心悸、烦躁甚则厥逆[5]。临床研究表明,合并有心血管基础疾病或出现心血管系统损害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往往病情较重,病死率较高[6]。Zheng 等[7]研究指出,既往有心血管基础疾病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预后不良。故对于新型冠状病毒对心血管系统造成损伤的中西医机制亟待深入研究,以期完善中西医结合治疗的理论基础,降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重症率和病死率。
1 新型冠状病毒的概述
新型冠状病毒是一类有包膜的单股正链RNA病毒,其有5 个必需基因,分别编码翻译核蛋白(N)、病毒包膜(E)、基质蛋白(M)、刺突蛋白(S)4 种结构蛋白及RNA 依赖性的RNA 聚合酶(RdRp)。研究发现,SARS-CoV-2 与SARSCoV 基因组序列的相似度可达到79.5%[2]。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的潜伏期为1 ~14 天,多为3 ~7 天,其主要经呼吸道飞沫传播和密切接触传播,接触被病毒污染的物品也可造成感染(也可经气溶胶传播)。所有人群都普遍易感新型冠状病毒,其具有很强的传染性。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ACE2)已被证实是新型冠状病毒入侵机体的膜受体[8]。该病毒的刺突蛋白可通过结合细胞表面的ACE2 受体进入细胞,引发一系列病理改变。由于ACE2 受体主要在人体的呼吸道上皮细胞中表达,因此患者在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后易出现呼吸系统症状。此外,ACE2 也广泛存在于心血管系统、泌尿系统、消化系统、中枢神经系统、免疫系统和生殖系统内,故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后可造成多系统不同程度的损伤。
中医理论认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属于“疫病”“疫疠病邪”等范畴。《说文解字》中说:“疫者,民皆疾也。”《黄帝内经》中有如下记载:“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 疫疠病邪在中医文献中又被称疠气、疫气、戾气、异气、毒气等,是指具有传染性的一类外感病邪,其所致病证被称为疫病,又称疫疠病、瘟病等。疠气致病,传染性强,易于流行,又兼发病急骤,病性危笃,正如吴又可在《温疫论》中所言:“此一日之间而有三变,缓者朝发夕死,急者顷刻而亡。”导致疠气产生和流行的因素较多,主要包括气候因素、环境因素、预防措施因素和社会条件因素等。具体来说,气候反常、环境卫生不良、预防措施不力、社会动荡不安都可为疠气的出现与流行创造条件。诸多中医学者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证候特点,并结合前人著作,为本病进行中医学命名,出现了“湿热疫毒”“寒湿疫”“温热浊毒”“湿毒疫”“肺疫病”等名称[9]。可见,本病的发生与湿、毒密切相关。研究表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临床症状以低热、乏力、咳嗽、纳呆为主,其舌苔厚腻,脉象以滑脉为主,兼病程缠绵,故病因属性以“湿”为主[10]。综合气候地域、致病特点及临床表现等,本病应属于“湿毒疫”的范畴。
2 新型冠状病毒对心血管系统造成损害的表现
2.1 病理表现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八版)》中阐明了新型冠状病毒可对心血管系统造成不同程度的病理改变[11],包括:部分心肌细胞变性、坏死,间质充血、水肿,少数单核细胞、淋巴细胞和(或)中性粒细胞浸润。除此以外,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全身主要部位的小血管还可见内皮细胞脱落、内膜或全层炎症、血管内混合血栓形成、血栓栓塞及相应部位梗死,且其主要脏器的微血管可见透明血栓形成。
2.2 临床表现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除了会出现发热、咳嗽、气促、乏力等呼吸系统症状外,还可出现心慌、胸闷、胸痛等心血管疾病的症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可直接或间接引起一系列的心脏并发症,包括急性心肌损伤、心肌炎、心力衰竭、心脏骤停、心律失常、急性心肌梗死、心源性休克、凝血异常等[12]。Wang 等[13]对138 例住院治疗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进行分析发现,其心律失常的发生率为16.7%,急性心肌损伤的发生率为7.2%。谢丹等[14]研究显示,在118 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中有34 例患者发生心力衰竭。
3 新型冠状病毒造成心血管系统损伤的机制
3.1 西医机制
3.1.1 病毒直接损伤 新型冠状病毒对心血管系统造成损伤的机制与柯萨奇病毒等引起直接心肌损伤的机制类似,主要是因为心肌细胞中广泛存在ACE2 受体,当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病毒表面大量的刺突蛋白经跨膜丝氨酸蛋白酶2 激活后会与ACE2 受体相结合,入侵心肌细胞并在细胞内复制,导致心肌细胞变性、坏死及功能丧失,引起心肌损伤[15-16]。
3.1.2 ACE2 水平的下调 肾素- 血管紧张素(ACE)- 醛固酮(RAAS)系统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其中ACE 可作用于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血管紧张素Ⅱ- 血管紧张素受体1(ACE-Ang Ⅱ-AT1)轴,引起血管收缩、血压上升和炎症反应。ACE2 虽然是ACE 的同系物,但其介导的ACE2-Ang(1-7)-Mas 轴可拮抗以上效应,起到抑制心肌重构、舒张血管、降低血压、减轻氧化应激、抗纤心肌维化等作用,是心血管系统的保护因子[17]。而新型冠状病毒与靶细胞结合后可导致ACE2 内化并下调其在细胞表面的活性,诱导ACE2 脱落[18]。ACE2 水平的下调,可促使Ang Ⅱ的水平升高,从而导致心血管系统疾病的发生或发展。
3.1.3 免疫损伤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可诱发过度免疫反应,促进大量细胞因子和炎症介质的释放,引起细胞因子风暴[19],表现为血浆促炎细胞因子的水平升高[20]。促炎细胞因子包括干扰素-γ(IFN-γ)、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1β(IL-1β)、IL-6、IL-8、IL-12 等。Chen等[21]研究发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多存在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增多、T 淋巴细胞减少的情况,且其血清中降钙素原、IL-6、C 反应蛋白的水平可明显升高,这提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体内存在由过度免疫反应引起的细胞因子风暴。大量细胞因子释放入血后可随着血流到达心脏,引起血管内皮损伤、血液高凝状态、心肌炎症等。若细胞因子侵蚀冠状动脉斑块,可引起急性心肌梗死和心室功能障碍[22]。研究指出,TNF-α、IL-6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血栓形成的机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3]。血清TNF-α 水平的升高会抑制心肌的收缩功能,减少心肌供血[24]。
3.1.4 氧供需失衡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可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13],导致其机体缺氧,引起低氧血症。心脏本身就是一个高耗能器官,且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后机体的代谢速率会显著增加,因此可进一步加重心肌负荷,导致心肌氧供需失衡,使心肌细胞能量供应不足,引起内环境紊乱及毒性代谢产物堆积,导致心肌损伤。此外,机体处于低氧状态还可造成炎性细胞浸润和细胞因子的释放,导致心肌损伤进一步加重。
3.1.5 凝血功能障碍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血液多处于高凝状态,可引起血栓性并发症,包括深静脉血栓栓塞、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及肢端小血管闭塞等[25]。新型冠状病毒引起凝血功能障碍与多种因素相关,其具体机制尚未完全阐明,目前可用血管内皮功能障碍、细胞因子风暴及非炎症因素等解释[26]。细胞因子风暴可损伤血管内皮细胞,激活凝血系统,抑制纤溶系统和抗凝系统,导致血栓形成[27-28]。此外,非炎症因素如发热、呕吐等造成的血液浓缩、接受激素治疗、静脉输注免疫球蛋白、长时间卧床等,都可导致血液呈高凝状态,诱发血栓形成[29],最终导致血栓性事件的发生。
3.1.6 抗病毒治疗药物的影响 α- 干扰素、利巴韦林、磷酸氯喹、阿比多尔、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等作为有效的抗病毒治疗药物已被纳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八版)》[11]中,而上述抗病毒药物对心血管系统均有一定的不良影响。α- 干扰素是由白细胞产生的一种广谱抗病毒低分子蛋白,具有心脏毒性,可引起高血压、心律失常、心肌梗死等心血管事件。利巴韦林是嘌呤核苷酸类似物,大剂量使用此药可导致心肌损伤、心律失常等心脏毒性反应。若合并有心血管疾病的贫血患者应用利巴韦林,可能会出现心肌梗死等严重的心血管不良反应[30]。磷酸氯喹是一种病毒蛋白酶抑制剂,可引起低血压、房室传导阻滞、心电图改变(如QRS 和QT 间期延长)、室性心动过速、室颤、阿- 斯综合征、心源性猝死等心血管事件[31]。阿比多尔是一种血凝素抑制剂,为非核苷类广谱抗病毒药物,可引起心动过缓,故在用药期间应密切监测患者的心电图[32]。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属于抗逆转录病毒蛋白酶抑制剂,可引起高胆固醇血症和高三酰甘油血症,因血脂异常是引起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故在使用此药时应注意监测患者血脂的水平[33]。
3.1.7 应激反应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尤其是重症患者)的生理和心理均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创伤,可导致其机体处于应激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患者的交感神经系统会过度兴奋,导致儿茶酚胺大量释放,而儿茶酚胺对心脏具有强烈的毒性作用和缩血管作用[34],可引起心肌顿抑、血管痉挛、恶性心律失常等,导致应激性心肌病的发生。
3.2 中医病机
在中医理论中,新型冠状病毒属于“湿毒疫”的范畴,其病位在肺脾[35]。外感疫疠之邪,兼夹湿、毒、寒、热、痰、瘀等病邪,邪犯心包,加之七情变化、劳逸过度、先天禀赋不足、所处环境不适宜及用药遣方不当等,可使病邪在体内从阳化火、从阴化寒,亦可由实转虚、虚实夹杂,此为湿毒疫的关键病机。其中最主要的病理因素是湿、毒,二者既是病因,又是继发的病理产物。湿毒蕴结,随之产生的其他病理产物(如痰瘀等)可进一步加重湿毒,导致湿毒流注,病势难以遏制而传变少阴、损及厥阴,最终可牵涉心、肾等多个器官。
从温病的卫气营血与三焦辨证论,叶天士在《温热论》中说:“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古代医家认为心为君主之官,不得受邪,心包络于心外,当代心受邪。如《黄帝内经·灵枢·邪客》中说:“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脏坚固,邪弗能容也。容之则心伤,心伤则神去,神去则死矣。故诸邪之在于心者,皆在于心之包络。”且心主神明,而心包代心行令,故外感热病中的神志失常多责之于心包,归于上焦证之热闭心包证。结合卫气营血辨证,心包的感邪途径可分为逆传、渐传和直中三种,概括为:其一,心肺同居上焦,有肺卫之邪逆传至心包者,可越过气分直传心营,称之为“逆传心包”;其二,有邪经气分,渐入营血,犯于心包者;其三,有外邪直中心包者。邪犯心包者症见神昏谵语、身灼热而肢厥、舌蹇、舌降、脉细数等。若夹痰,可见喉间痰鸣有声、舌绛苔垢等;若兼瘀,可见神志如狂、爪甲青黑、舌质紫晦等。
从脏腑病机论,湿毒内犯,最易困脾,脾失健运,运化水谷及水液功能失常,脾气受损,不能升清,则症见倦怠乏力、腹胀腹泻、纳呆肢重等。根据五行母子相及理论,心火生脾土,脾为心之子,心为脾之母,子病及母,脾虚湿困,则心气受损,出现心动悸等心系症状。此外,疫毒犯肺,肺失宣肃,通调水道功能失常,可使水湿更盛,进一步损伤脾土。脾为气血生化之源、后天之本,脾虚则正气虚损,无力驱邪外出,疫邪鸱张,进一步耗伤心气,导致心肌受损。
4 小结与讨论
综上所述,新型冠状病毒主要是通过ACE2受体入侵心肌细胞,引起细胞因子风暴,攻击血管内皮细胞,造成血管内皮细胞功能障碍,引起凝血功能异常、血栓栓塞,导致心肌细胞变性、坏死,使心肌组织及冠状动脉内出现不同程度的炎性细胞浸润及血栓形成,从而导致患者出现胸痛、胸闷、心慌等心肌损伤的症状。新型冠状病毒的中医病机主要是湿毒疫疠之邪内侵,在体内攻窜流走,或化热炼液成痰,或从寒凝血成瘀,痰瘀阻滞心脉,损及心气,发为胸痹、心悸等,甚则厥逆。可见,无论是西医病机中病毒介导的炎性因子浸润及血栓栓塞引起的心肌损伤,还是中医理论中湿毒蕴结、化生痰瘀而导致的心脉痹阻、心气受损,都会引起一些类似的心系症状。虽则西医理论旨在直观描述心血管受损的病理变化过程,中医病机更强调多种病理因素的消长转化,最终牵涉至心,但二者都能解释本病发生发展的共同趋势,即对心系造成损伤。因此我们可以互参互用,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充分发挥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优势,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大众。总而言之,新型冠状病毒所致心血管系统损伤患者往往病情较重,因此需重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心血管系统并发症的预防和治疗。此外,应进一步完善中医理论关于本病发生发展的系统阐述,为中西医结合治疗本病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