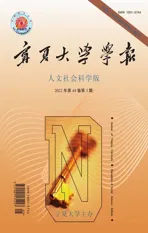科学技术与文学的对话:从思想到形式的演变
2022-11-23李洁
李 洁
(宁夏大学 外国语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的演变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关系,每一种艺术形式的构成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科学或者文化看待现实的方式,是认识论的隐喻。科技的惊人发展、准确度和适应力以及所造就的想法和习性,必定给传统艺术带来深远的改变。物质和时空的维度变化造就的伟大革新足以改变整个艺术技巧,进而影响艺术创造,甚至给艺术观念带来蜕变。[1]
一 理性主义科学方法主导下的线性文学思维
近代科学革命不仅是少数才能卓越的科学大师对旧思想与旧传统的突破,也是对古代异常思想中合理因素的继承和发展。自古以来人们便相信世界以一定的规则、秩序和规律存在。这种信念推动古往今来的科学家去探索和把握那些决定世间万物之联系的普遍法则,因此16 世纪至18 世纪中叶充满了理性主义光芒的科学和哲学思想。科学史上的第一次奠基式革命发生在15 世纪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它包含了从主导的地心说向哥白尼世界观的转变,也相当于对地球和人类的拆解运动,歌德的《浮士德》(Faust)就演绎了其中的许多思想。16 世纪到17 世纪间笛卡尔掀起的理性主义思潮已突破了哲学,成为科学革命的理论基础。18 世纪的理性主义者将宇宙视为钟表,上帝则是钟表制造者,暗指世界是由环环相扣的零部件组成的,零件可以相互脱离,一个智慧的观察者从零件的工作方式就能推断出它的作用。世界像一部机器那样有固定和静止的形式,一旦它被发动起来就会自行运转而无需神的干涉,但前提是它的工作是理性的,并且演绎和归纳这两种线性链式的方法是最合适的探究方法。据此,时间顺序和因果转承就成了最自然和直接的线性叙事方法。
时间的概念源于日夜交替、四季轮回等自然过程。为了尝试控制时间,传统思想给出一种井然有序、等级明晰的时间再现。虽然不断有人怀疑把时间当作外部世界的组成部分是否正确,但人们仍旧按照时间来调节自己的生活。一个与外部世界的所有感知割裂开的人大抵仍然会继续体验他自己思想与感觉的连续性。传统上的文本时间注定趋向一个方向并且不可逆转,因为语言预先规定了一个符号的线性形式,比如逐字、逐句、逐章节阅读,所以呈现出的信息也是线性的。尽管人们想方设法逃离传统模式,但它却历久弥坚。托多洛夫指出,故事的时间概念包含了一个约定俗成的惯例,它将自己等同于理想的时间顺序,或称自然年表顺序。事实上,严格的承继行为只有在一条故事线索或一个人物的故事中才能找到。但凡多余一个人物,事件就可能变为同时性的,并且故事往往呈现出多线性,而非单线性。严格的线性时序既不是自然,也不是大多数故事的实际特点。不过,传统的“标准”仍被广泛地接受,最终代替了故事实际的多线性时间性,获得了“伪自然”(pseudo-natural)的地位。
而“事出有因”是现实主义叙事作品的基本特征。笛卡尔认为宇宙受一种普遍但抽象的规律决定和约束,周而复始并且恒久不变。如霍尔巴赫在《自然的体系》中提到,“在这个自然之中,没有偶然,没有属于意外的事物,也决无没有充分原因的结果,一切原因都遵循着固定的、一定的法则而活动。”[2]亚里士多德早在《诗学》中就确定了开头、中间和结尾的一体化,以及内在的根据、情理或者真理的叙事概念。解构主义学家希利斯·米勒(Hillis Miller)则称,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人物是按照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所特有的一套有关起源和终结、因果性、统一性的共享假设来行动的[3]。但事实上,许多生活事件缺少清晰可辨的原因,而理解的惯性却引导人们做出种种根本不可能的解释,那就是将传统的开端、结局、目标等概念强加于那些本会暗中破坏这些概念的文本之上。米勒还说,不管出现的东西多么杂乱无章,人们都可能会采用因果链或者有机生长的模式来描述叙事之合乎人意的连贯性,人们将线性连贯性视为理所当然。[4]
传统的科学方法对一批文学思想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T.S.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一文中赞扬了创造力的增殖方法,将文学的线性置于神圣的地位。他认为诗人都是用过去的材料来成就自己的传统,也因此为文学打上了进化模式的印记,线性是这种模式的主要特征,是理解艺术过程的重要依据。通过艾略特的复原法,被现代主义文学视为典范的《荒原》中那些多样的典故,事实上展示的是作品与体现在作品中一脉相承的线性发展,因为它从占主导地位的艺术传统中得到了统一和方向。
二 相对论与现代主义小说
科学史上的第二次革命开始于19 世纪,其动力源自热动力学理论、相对论和量子力学。20 世纪末,技术和物理理论的变化激发了文化总体态度的变化,艺术回应并且塑造了科学假想。场论、相对论等概念对传统小说形式的改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主义小说可以说是宇宙爆炸、多元主义、相对主义和不确定性的必然结果。
爱克纳(Hans Eichner)指出,如果世界是一个动态的、生机勃勃的整体,那么单凭理性认识就不能全面地理解它。生命的神秘本质要求理解那些引起共鸣的想象[5]。这种观点在人文科学中得到了回应。尼采、弗洛伊德、荣格、齐美尔、怀特海绘制的人类影像都集中于攻击人类作为静止和自主生物的传统观点上。人类不断地被看作可以在物理领域被辨识的、趋向不断进化的动态互动中不可缺少的部分。20 世纪文学深受柏格森的“绵延”(duration)理论和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对时间概念的启示,柏格森的时间是弹性的,因为它与以非机械方式感知的生命力相联系,比如沃尔夫(Virginia Woolf)《达洛卫夫人》(Mrs. Dalloway)中的大本钟不仅仅是在强调物理时间,还揭示着人类系统的时间与个人主观体验时间的方式之间的紧张关系。文学创作的终极目标不再是表现现实的镜像,而是研究和再现时空的概念和人类纷繁复杂的大脑活动,以及强调现实动态、流动的本质。[6]
美国现代诗人威廉姆斯(W.C. Williams)1948年的演讲“作为行动场的诗歌”(Poetry as a Field of Action)指出,尽管文学还要延续模仿,但人类对现实本身的概念因为近来的技术发展已经改变了。虽然此番言论发表时现代主义已到了中期,但仍然指出了美国文坛自庞德提出“make it new”以来的变化。他说,诗歌如果要跟上对心智研究的发现和人类感知力、知识和理解能力不断前进的步伐,就应该在新物理的基础上反映现实。“伴随工业革命,一种新的精神,新的时代精神已经稳固地掌握了世界,结果,新的价值观取代了旧的、贵族化概念”[7]。新的表现应该反映世界科学、社会和经济的复杂性,同时挑战传统的诗歌形式。威廉姆斯说,如果不能把相对论的基本事实——测量的相对性纳入我们的活动(诗歌)中,那我们何以接受爱因斯坦那影响了我们对天体概念理解的相对论。我们认为自己置身于宇宙之外吗?或许英国国教是如此?相对论适用于一切,比如爱情。[8]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以下简称《追忆》)就响应了这样的召唤。美国著名的评论家和作家威尔逊(Edmund Wilson) 在《阿克瑟尔的城堡》(Axel’s Castle)中就指出,普鲁斯特很早就将新科学和技术的规则纳入自己的小说中了。
其一,表现在人物塑造上。威尔逊说,对于现代物理而言,我们对于所有宇宙活动的观察都是相对的,它们取决于我们所处的位置、观察的世界、我们移动的速度和方向、以及周遭的环境、时刻与情绪等。[9]《追忆》中的人物并非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中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那样非黑即白、棱角分明。他们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以不同的角度,在不同人的视野里出现。因此,这些人物是圆形的,是多重影像和印象叠加而形成的,好似毕加索立体主义画像中呈现的多棱体面庞。不过,普鲁斯特每一次也只描绘人物的一个面,使人物的个性更加不明朗、不确定。如同威尔逊所说,尽管普鲁斯特的全部观察看似相对,但他像爱因斯坦一样为自己的表象世界建造了一个绝对的结构。他的人物也许在变化……好像爱因斯坦那个能收缩和伸长的测量棒,他的钟表可快可慢[10],将这个概念应用到文学方法中就会去除客观性和稳定性的假象,反而将注意力引入善变的主体性行为上。
其二,表现在文本结构上。根据普鲁斯特自己的说法,对文本的设计是用来说明某些定律的,譬如场论(field theory)。场论最基本的概念是,事物是相互关联的。牛顿原子论思想认为现实中的物体都是离散的,各事件能够独立于其他事件和它的观察者。与此截然不同的是,场论将现实描绘为物体、事件和观察者,他们都难分难解地归属于一个场。据此而论,每一事物的性状,有时剧烈地,有时微妙地,但无一例外地都深受其他事物性状的影响。普鲁斯特在《追忆》的结尾处也表明了相同的观点:
如果我们不能把自己生活中那些连续的场景记录下来,也就无法讲述我们与一个知之甚少的人之间的故事,因此,每一个人——而我自己就是其中之一——的生命的存续期都是由他在自己和别人之间所完成的回旋来衡量的,特别是由他在与我的关系中所占据的地位来衡量的。[11]
场论要修正的思想之一就是被称作“原因”和“结果”的单程连锁反应。作为意识流小说的扛鼎之作,《追忆》没有波澜起伏的矛盾纠葛,甚至没有中心人物和完整的故事。它大体以叙述者“我”的生活经历和回忆为线索,将大量或长或短的人物与事件串联起来,伴随梦呓、呢喃、沉思、冥想和独白在其中恣意蔓延。如作者所言,“生活不断地把它们编织在不同的人之间,不同的事件之间,在我们的过去和其他所有的点点滴滴之间储存了如此丰富的记忆,它穿过这些线,让它们延长,使它们加厚。”[12]
《追忆》就是一个文学的场域,如同盘根错节的大树,更似纵横交织的网络,网络上的每个节点就是个体生活轨迹交汇的痕迹。普鲁斯特通过故事与故事的嵌套、交叉和重叠,组合成了一个互相牵扯、参映的巨大网络。在此意义上,科学模型影响着文学,好比文学也同样影响了科学模型一样,两者都影响了我们在整体上对相对论和场论的理解。
三 混沌学与非线性文学
美国后现代文学批评家海尔斯(N. Katherine Hayles)认为,科学和艺术出自相同的文化背景,“后现代主义语境提供了一套文化和技术环境,这其中的零散部分聚集起来,互相加强,直至不再是孤立的项目,而是紧急地意识到无序、非线性和噪音在复杂系统中所起到的构建作用,从而催化了新科学的产生。”[13]
20 世纪末,技术和物理学的概念始终在变化。物理学从决定论一统天下走向决定论、随机论、混沌论三分天下的局面,这是人类认识自然规律的又一次重大飞跃。笛卡尔式分析方法遵循的是线性因果决定论,虽然几百年来在特定的范围内行之有效,但它只适用于认识较为简单的事物,不能如实地说明事物的整体性,也不能反映事物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因此当面临关系错综、规模巨大、参数不定的复杂问题时,传统分析方法束手无策。当现代科学所面临的简单性思想和方法无法处理复杂对象时,一系列以复杂系统为研究对象的新科学相继诞生。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混沌学是针对复杂系统的,包括了非线性动力学、不可逆过程热力学、气象学和认知学等领域的跨学科研究。
第一,“混沌”与不规则运动、偶然性和可能性相关,它暗示着几种矛盾状态的存在:(一)不规则运动也可能构建某种范式;(二)无序与有序相链接;(三)无序中暗含着有序;(四)有序以某种无法预测但确定的方式从无序中抽离出来。
第二,混沌学重视非线性问题的研究。混沌是非线性动力系统固有的特性,也是非线性系统普遍存在的现象。混沌理论的优越性在于它尽量从整体性上理解非线性系统。线性系统大多是由非线性系统简化而来的,而不是偏离线性轨道,因此它们在同样的系统中并非相互排斥。法国最伟大的数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庞加莱(Henri Poincaré)早就对保持自然界稳定性的假设提出了质疑。他相信在“系统”或“多体”(many-bodied phenomena)现象中,“线性”和“正常”状态事实上总是被不完美、纷扰和错位打断[14]。
文学中同样存在混沌现象,因为一部作品就好似一个复杂和混沌的系统——一个包含总体的秩序,但其零部件却是以看似不可预测的方式运行着的实体。两种叙事模式恰如其分地论证了这种现象:“马赛克叙事”和“任意路径”小说。
“马赛克叙事”(mosaic narrative)含蓄地表现混沌。在这一类作品中,正常的叙述被碎片化了。逻辑上的一致性与因探索多视角而呈现出了非逻辑和非线性的共栖。过去和现在并置,第一人称叙事的线性结构由于第三人称声音的插入而间断。莫里森(Toni Morrison)《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示范了第一人称有限视角与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的交替,暗示了连贯系统的限制和约束,以及对更多样复杂形式的需要。杜瑞思(Michael Dorris)《蓝水上的黄筏》(A Yellow Raft in Blue Water)从三代美国妇女的叙述视角构建了一个多视角和多声部的观点,过去的声音和经历根植于当前的世界,创造出历史的马赛克。它试图说明,更加接近精确的现实图景有可能来自互相补充的和多维度的视角,而非单一的视角。在这些语境中,第一人称独白性话语的连贯性总是被另外一种“非系统”暗中破坏。所谓“非系统”(nonsystem),就是“一堆碎片”或“拼凑之物”,它与系统中的“任何表达盘根错节地缠为一体”,是“由互不相容的裂片连接而成的一个裂片系统。”[15]
“任意路径”(random-access)小说将混沌理论内化为自身的结构。库恩(Thomas Kuhn)提出,科学是依靠模型或范式来建构和表现自己的,范式通过假设、步骤、惯例和文化视角来建构意义。[16]20 世纪的小说也趋于强调模式、模型和范式的作用,“任意路径”小说皆由或长或短的若干片段组成,读者可以不按照章节顺序从任何一个片段进入阅读。不同的阅读顺序会“生产”出不同的故事,而人物、情节之间的关联则任由读者自行揣摩,《暴行展览》(The Atrocity Exhibition)、《跳房子》(Hopscotch)、《赤裸的早餐》(Naked Lunch)、《保姆》(The Babysitter)、《亚 历 山 大 四 重 奏》(The Alexandria Quartet) 皆 属 此 类。巴 拉 德(James Graham Ballard)在《暴行展览》的前言中写到:
读者会被《暴行展览》陌生的叙事方式所挫败,但事实上,只要你尝试采用不同的阅读方法,就会发现它比最初看上去的要容易得多。你可以打破从第一页开始阅读的惯常做法,信手随翻直至碰上那个吸引你眼球的段落。如果某个想法或是图像还比较有意思的话,那就扫视一下附近的段落,看是否有什么能引起共鸣的话语。很快,我希望,你就能感到云开雾散,隐藏的叙述将会自己现身。实际上,你读的方式也就是我书写的方式。[17]
这种程式恰恰与当今网络超文本无始、无终、无中心、非线性、多入口的“根茎”式特点不谋而合。每个片段既可独立成篇,也可以任意顺序与其他片段关联起来阅读。选择的对象与顺序的不同都会导致故事在时间、地点甚至人物命运的变换。只要读者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力反复阅读,就会组合出新的文本,产生新的意义。伯尔特(Jay D. Bolter)将这种意义的不确定性称为“悬置”(hyperbaton),它违背了传统线性小说所秉持的“熟悉化”(familiarization)策略。熟悉化为读者明确了一个视角,一个审视叙事的位置;而随机阅读造成的意义悬置、间断性和分支却不停地将读者拽出舒适或熟悉的位置。[18]
在这种创作模式中,无序或混沌穿插于有序的各层次之间,侵扰或颠覆了既定顺序的随机元素也许会创造另一种顺序。“有序”是由小说的物质载体——平面印刷文本而决定的,因为阅读印刷小说的惯常做法就是按照线性方式从头至尾阅读。“无序”是因为“任意路径”鼓励读者突破印刷页码的藩篱,任意组合出一个片段序列,从而形成“故事”。但正如“混沌”概念所示,在一个系统中,无序和有序并非相排斥的非此即彼,而是蕴含与被蕴含、此强彼弱和此弱彼强的关系。这颇似物理学中的“波粒二象性”(wave-particle duality),即一切物质都同时具有波动性和粒子性的双重性质,只是在不同条件下一种性质显著,而另一种微弱。读者被传统和惯性驱使去追求连贯性,这种追求如此执着,无论那是多么支离破碎、杂乱无章的叙事片断,他们都能够构建出一种令自己信服的连贯性。
四 新媒体技术与文学数字化
与科学革命同样重要的是技术革命。科学革命的成果被文学创作所吸收,内化为文学文本的思想、理念和结构,而技术革命直接影响了文学的载体、表达和传播方式。从1040 年中国宋代人毕昇发明胶泥活字印刷术,到1500 年德国人古登堡整合多项技术推进了印刷工业的形成,人们在印刷文化中浸染了五百多年,白纸黑墨早已被默认为文学的外部形态了。但是,“在今天这个数字化时代,印刷书籍绝对再也不是一个清白之物”[19],没有什么比技术,尤其是新媒体技术更能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文学的内涵与风貌了。
数字技术是新旧媒体的分野。新媒体是以数字、网络、无线电、卫星等技术支持的媒体形态而存在,也被称作“数字化新媒体”。它将传统媒体上的内容转换成电脑可处理的数据资料后呈现在各种媒体终端上。由于对科学发展的敏锐洞察力和技术上的先动优势,美国在传统文学数字化和新媒体文学方面的成就令世人瞩目。1971 年,由美国人哈特(Michael S. Hart)发起并延续至今的“古登堡工程”(Gutenberg Project)是世界上最早的数字图书馆。2004 年谷歌宣布要对1500 万册书籍数字化,纵观当今世界,各种工程相继展开,数字化步伐据估计将以每年一百万本的速度迈进。不过,这些都属于文学数字化的初级阶段,是文本从纸面到电脑屏幕的“搬家”,好像从印刷书上撕下每页重新安排后摆在读者眼前。事实上,数字技术为文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开辟了更加广袤和深邃的空间。
(一)超链接技术使得既定的印刷文本得以优化
1987 年,由美国计算机学会主办的第一次国际超文本技术研讨大会召开,超文本的核心是电子超链接(hyperlink)技术,它通过关键词在文字、声音、图像等不同格式的文本间建立关联,使当下的阅读引发或触及到其他文本的内容,因而更符合人类多线性、交叉性和由此及彼扩展性联想的思维模式。传统文学的电子版本呈现出的是印刷文本的提升和优化,它起到了两方面的作用。
其一,超链接扩展了文本的外延。在电子版的小说作品四周嵌入相关资源链接是目前作家作品网站惯常的做法。电子文本有两层空间:显示文本的电脑屏幕和存放文本的电子存储器。电子空间是活跃的,视觉上是复杂的,并且在作者和读者的手中有令人惊叹的延展性。这种延展性是指电脑书写空间里文本内容的调整、版本的修订与增补、检索、外部链接等各种功能。这些功能所展现的速度与自由度是平面的印刷文本所缺乏的,以福克纳《喧哗与骚动》(Sound and Fury)为例,原著是一部复杂的,融意识流、多线性、多人称叙事为一体的文本,遍布全书的用典更是增加了作品的厚重感,使其成为复杂叙事的经典。而它的电子超文本版[20]可谓研究此小说的语料库,本质上就是把一部小说里各种零散的资料和其他小说以及学科的资料有机地结合起来。换言之,超链接能将单一文本和与其相关的各种资源整合起来创建一个认知环境,它使得支撑独立文本的各种资料比其在传统技术条件下更紧密地被关联起来,体现出学科之间的局部可通约性。
其二,超链接简化了阅读印刷作品的“劳碌”。譬如字典、百科全书一类的读本都含有大量条目、注解、索引等关联指涉和相互参照的成分,在印刷版中只有依靠眼球和手指的“翻山越岭”才可到达目标位置。然而当它们被数字化后的版本不仅能够提供文本和图像,还附带音频和视频,并且,只需点击超链接就可在顷刻间定位目标,源文件的大小并不构成搜索的障碍。
(二)媒体融合技术使传统的平面语句获得了视觉提升和动态维度
“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的概念是20世纪80 年代麻省理工大学的浦尔(Ithiel de Sola Pool)教授提出的,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自最早的家用机Apple II 问世以来,电脑的绘图、算法和互动性促进了文学作品形式上的改观。作家们都热切地进行新媒体实验,没有把电脑当成节省劳动力的工具,而是当成创新和加料的手段。
印刷文化用很长时间才使人们意识到语言在视觉表达方面的潜质。美国诗人从庞德、威廉姆斯到黑山派和语言诗派都力图脱离传统,探索诗学话语的新形式,比如e.e.卡明斯等具象派诗人始终在挖掘印刷文本中白纸黑字间的互动所产生的效果。麦克黑尔(Brian McHale)也谈到,后现代作家采用一系列手段来强调本体划分:空间利用(字体、空白页、页边)、具象散文和插图、脚注、多栏、多路径阅读等。[21]20 世纪90 年代中期,计算机图形界面的革新不可否认地促进了印刷排版实验中图形元素的发展。尽管过去的诗人用打字机和印刷机也能创作出精美的视觉作品,但计算机却使这些文本操作简单便捷了。“多模态小说”(multimodal novel)应运而生,它们不再是单一的文字文本,而是在叙事话语中包含了广泛的视觉元素。图画等符号的增殖改变了传统上基于文字的小说风格,挑战了语言在文学和研究中的历史主导地位,尤其是印刷中的书面文字。[22]
技术的发展瞬息万变。20 世纪末期,多媒体软件,如Flash、Dreamweaver 和quicktime 等将文字文本和图表、图画、动画和音乐以日臻娴熟的技巧结合起来,形成了融思想、技术和观影体验为一体的视频诗歌(video poetry)。此时的诗歌语言已不是图像和文字的简单并置,也不再停留于固定和沉默的纸页上,而是通过附带链接、复杂的图形组件、音轨等功效的计算机语言将思想、技术和观影体验融为一体的动态作品,它展现的是思维的过程和感官体验的共时性。
(三)互联网技术改变了文学作品单一的传播模式
互联网是全世界最大的有效运转的无政府组织。互联网络去中心化、互动、高互文性、虚拟聚群等特征突破了人类在真实空间交流中受时间与空间限制的藩篱。进入2003 年后的“Web2.0”时代,互联网模式发生了革命性的改观,内容更加丰富、联系和沟通性更强、应用门槛更低。网络成了发布平台和交流渠道,一些用户提供信息,另一些用户则获取信息,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如论坛、博客、微信、Facebook、Twitter 一类的社交媒体平台。
这些技术工具也成就了“跨媒体叙事”(transmedia storytelling),即一部虚构作品的完整性元素沿多个输出渠道(包括小说、电影、社交媒体、漫画书、网页、虚拟现实游戏等)被系统地分散开来,旨在创造一次统一、和谐的娱乐体验,每一个媒体都贡献出自己独特的力量来展开故事。这些虚构作品可以是独立的,也可与其他媒体联手共同营造一个故事世界。新的传播形式不仅为扩展叙事宇宙开辟了广泛的路径,同时也获取了良好的商业回报。2013 年获得艾美奖,改编自《傲慢与偏见》的YouTube 短视频系列剧“丽奇·班纳特日记”(Lizzie Bennet Diaries)就是非常成功的跨媒体作品。短剧保留了原著的主要人物和故事线索,但却以现代人的生活模式延伸了叙事,在Facebook、Twitter 上设有主人公的账号,方便观众与人物的对话。观众可在官方网站上给制作方留言,参与后续剧情发展的讨论。随后又出版了印刷小说《丽奇·班纳特的秘密日记》(The Secret Diary of Lizzie Bennet),以满足深陷剧情而又无法满足于短视频的观众对细节阅读的需要。另外,观众还可以在iTunes 上听小说音频。
此外,文学名著的跨媒体改编多集中于游戏方面。例如《贸易风之奥德赛》(Tradewinds Odyssey)是玩家在航行中利用智慧毁灭敌人,通过建设、加强和升级自己的船来称霸爱琴海,最后把货物运到新大陆——与荷马史诗《奥德赛》历尽艰辛的海上诗篇形成互文。再以菲兹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为例,除电影、戏剧、歌剧、芭蕾等输出方式之外,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美国游戏巨头Oberon Media 出品的电脑游戏《经典冒险:了不起的盖茨比》(Classical Adventure: Great Gatsby)。玩家身份是原小说的叙述者尼克,以他找寻盖茨比的历程为主线,期间的对话和文字全部来自原著。游戏包括字谜、寻宝等经典的冒险游戏项目。艺术混溶性和审美流动性被这类游戏设计发挥到了更高的层次。
结 语
每一次革命都迫使科学界推翻一种主导和权威的科学理论,以支持另一种与之不相容的理论;每一次革命都彻底改变了科学的形象,也根本改变了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那个世界。文学与科学虽然以不同的方式追寻和探索真理,但它们本质上都是在洞察宇宙和人心的奥秘。科学为文学提供了思维的范式、结构和模型,而文学,正如现代著名的数学家和哲学家怀特海(A.N. Whitehead)所言,“人性的具体外貌唯有在文学中才能体现出来。如果要理解一个世界的内在思想,就必须谈谈文学,尤其是诗歌和戏剧等较具体的文学形式。”[23]在此意义上,文学与科学是相辅相成的,它们的对话始终在进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