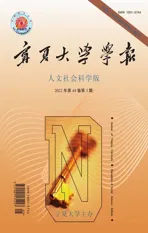宋诗中的种植书写与士大夫精神内蕴
2022-11-23梁思诗
梁思诗
(浙江大学 中文系,浙江 杭州 310012)
随着种植经验与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社会草木观赏风气的时兴,种植成为了宋诗常见的题材之一。宋诗题材比之宋前更加注重对文人近身事物的体察、对私人生活的记录。对宋代咏物文学的研究已有不少,但种植诗与一般的咏物诗不同,除了对物的关注外,还加入了人的参与,歌颂人力的作用,以及表现人与物之间长期相处的情感互融。宋代文人如欧阳修、梅尧臣、苏辙、张耒、杨万里、陆游、方岳等都作有不少种植诗。文人士大夫在种植诗中详细记录栽种过程、体认物理,融入个人情怀、实现物与人的精神交流。随着种植文化的发展,由北宋至南宋入诗的植物愈加丰富。种植诗的繁兴也体现了宋诗日常化的一面,诗人们脱离了咏物文学对物本身的细致描摹、对文辞修饰的精雕细刻,注重记录种植的日常行为书写,把诗歌当作类似种植日记的体裁。宋代种植诗古体多于近体,这是出于律诗绝句的篇幅限制,诗人们更多地选用较长的古体来记录他们的栽种过程、植物的生长过程、欣赏过程等。种植诗不仅记录了宋代士大夫的生活,具有古代种植方法的文献价值,还体现着士大夫的精神内蕴和价值追求。
一 无用之用:寓物之乐与生命珍视
栽种在宋代蔚然成风,社会上不仅兴起了观赏花木的风气,还流行亲手栽种,文人对种植的方法十分熟稔,不仅在诗歌中详细记述种植的方法和过程,还亲自撰写花谱树谱。宋代植物谱录繁多,已形成时代潮流,现存有名目的花谱就有41 种,其中牡丹21 种,菊花9 种,还有芍药、兰、海棠、梅等[1]。著名文人如欧阳修写过《洛阳牡丹记》,范成大有《范村菊谱》《范村梅谱》,陆游有《天彭牡丹记》,这些文人有切实的栽种经验,还时常在诗歌中记录种植心得体会。宋人笔记如莫君陈《月河所闻集》、沈括《梦溪笔谈》、王辟之《渑水燕谈录》等皆记载了一些植物的种类和栽种方法。栽种方法和经验在文人圈内流传,例如苏东坡栽种竹子的方法就常在南宋诗歌中被提及。介绍栽种方法的诗如周紫芝《南窗植竹数百竿后数日蔚然俱青客问种竹法作四言以告之》等,还有详细记录栽种过程的诗如李复《种菜》《种罂粟》等。
欧阳修《伐树记》对树木之“用”进行了一番探讨:“彼杏之有华实也,以有生之具而庇其根,幸矣。若桂、漆之不能逃乎斤斧者,盖有利之者在死,势不得以生也,与乎杏实异矣。今樗之臃肿不材,而以壮大害物,其见伐,诚宜尔,与夫才者死、不才者生之说又异矣。凡物幸之与不幸,视其处之而已。”[2]对“用”的定义,被赋予存在意义的物都是有用之物。那么,植物对于文人之“用”在何?欧阳修云:“不寓心于物者,真所谓至人也;寓于有益者,君子也;寓于伐性汩情而为害者,愚惑之人也。”[3]欧阳修所谓有益者指的是读书学习,认为人不应过度耽溺于外物玩乐,有害性情。那么种植看来应是无益之事了。文人将种植视为余事,他们既不把植物用于商业贸易,又不指望这些果实饱腹,种植对于以读书从政忧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而言,只是“闲事”,所谓“用”的意义主要在宽慰身心和观赏解闷。
宋人种养植物首先是出于一种文人雅趣和娱乐心态,他们将种物、赏物视作生活的调剂品,如赵孟坚《种石菖蒲》将种植作为政务读书后调节心情、放松心态的方式:“少年眼力健观书,卷里千言一览无。官事簿书昏惘惘,效尤石上种菖蒲。”[4]美国学者艾朗诺曾经探讨过宋代士人对于种花赏花的道德焦虑问题,宋人一方面着迷于艳丽花朵的感官吸引,一方面又对这种诱惑进行谴责和批判。在宋诗中,种植牡丹等冶艳花物的作品较少,大部分集中在梅、竹二物。诗人们毫不掩饰自己对花物外在美的着迷,大肆描写其生动形象,其本质上体现的是文人对生命体的珍视与眷恋。如司马光《独乐园》云:“志倦体疲,则投竿取鱼,执衽采药,决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热盥手,临高纵目,逍遥徜徉,唯意所适。明月时至,清风自来,行无所牵,止无所柅,耳目肺肠,悉为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间,复有何乐可以代此也?”[5]植物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当美的事物参与文人的生活,就为他们增添了净化心灵、除忧解闷的工具,文人暂时躲进美好事物所营构的审美世界中,逃离了公务、琐事等烦扰。宋代大部分种植诗都抒写了作者愉悦畅快的心境,诗风明净轻快,诗人把对物的描写降到次要地位,而将自身赏物的欢乐提升到主要位置,体现了亲手栽种、自享其成的乐趣。华岳《舍后丈地令人植花种竹闷则邀清风明月尽醉而倒》:“有地都来一丈余,垦锄元不费工夫。匝墙先种竹三本,绕槛却栽花数株。风伯唤来烦解佩,月娥邀得醉携壶。凭君试向蓬莱问,还有神仙似我无。”[6]诗中除了写及种植经验外,还用更多篇幅表现了诗人种完之后在花木底下乘兴醉酒的惬意之情,他全然不觉得锄地栽花辛苦,反而说自己胜似神仙。类似的还有如欧阳修《谢判官幽谷种花》:“浅深红白宜相间,先后仍须次第栽。我欲四时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开。”[7]许多文人所种之花盛开之际,还会邀上三五好友前来共赏,共赋次韵诗以庆祝植物的长成。如马永卿《嬾真子录》载:“富郑公留守西京日,因府园牡丹盛开,召文潞公、司马端明、楚建中、刘几、邵先生同会。”[8]植物把文人汇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小范围的文人圈子,于是种植就不仅体现着文人雅趣,以植物为圆心辐射,形成一个具有社交性的文学圈子,种植一事也从私人领域延伸到公共领域。
在宋人眼中,草木应是自然生长,由天而生。王安石曰:“道有本有末。本者万物之所以生也;末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万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后万物以成也。”[9]张载曰:“天以直养万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尽道矣。”[10]王观《扬州芍药谱》曰:“余尝论天下之物,悉受天地之气以生,其小大短长、辛酸甘苦与夫颜色之异,计非人力之可容致巧于其间也。”[11]但栽种一事本质是人为,宋代诗文中常见“手植”一语,“手”表示的就是人为的力量。宋代士大夫所鄙夷的人为指的是如嫁接、修剪等害物的行为,正如程颐所指的“养物而不伤也”,他们将单纯的栽种视为顺应自然规律、因势利导而为。他们一方面否定人为的介入,另一方面又不厌其烦地在诗歌中表达自己亲手栽种花木时的喜悦之情。如周紫芝《甘菊数本旧植之地沮洳湫隘颇有悴色十一月二十三日移植墙下明日小雨数刻欣然便有生意》诗云:“小草偷微生,崛强沮洳间。托根倘失所,憔悴无好颜。嗟哉一大地,宁无尺寸闲。造物惜不与,无乃亦太悭。”[12]造物主让甘菊憔悴无所托,诗人怜悯之,于是“我移东篱栽,往近九畹兰。天心固有在,生理似可还”。诗的末尾还写道:“物微自有知,报君以长年。”诗人把自己视作甘菊的救命恩人,他用人力的介入让本已奄奄一息的植物重新活过来,其本质上歌颂的也是人为的力量。诗人们甚至无形中将花木视为人的产物,种植诗里缺少了咏物诗中对自然天工的赞叹,而更强调人力的介入,在诗中,植物成长的每一步都含带着作者的辛劳付出,作者也没少在诗中歌咏自己的勤勉,直白地表露种植的喜悦和成就感。如林希逸《小盆新种水芝方有生意》:“买石殷勤种水芝,主人欲速讶渠迟。朝来喜见芽如粟,点点青青上下枝。”[13]
栽种的过程即孕育生命的过程,诗人们怀着如母亲生养孩子一般的心态对种苗悉心呵护照顾。种植诗并非单纯的咏物之作,其中还有诗人自我的参与,他们不仅在诗中描写种成后开花结果的景象,还热衷于将自己如何从种子开始培育、发芽、长枝、结苞等过程细致有序地记录。如赵孟坚《种水芭蕉》诗云:“石上芭蕉手自移,黄梅便得雨如期。水根联络银丝漾,风叶纷抽羽扇攲。日验发生疑有准,心加爱护每忘疲。犹如老大初生子,及见成人长立时。”[14]诗人在诗中毫不掩饰自己对芭蕉的喜爱之情,他一心一意将其呵护,不辞辛劳。诗人站在一个母亲的视角将芭蕉视作自己的孩子,更表达了自己看其成长壮大时的慈爱之心。作者与植物的关系不同于一般咏物诗中的观赏与被观赏的关系,还掺入了孕育与被孕育、爱护与被爱护的亲子般互动关系。如此,诗歌中的关注焦点不再仅限于植物本身,还有作者的主体能动性,作者在整个种植过程中的心态感受,以及种植的辛劳与不易。诗歌充当了一种日记的功能,记录着诗人在种植中独一无二的私人体验。如果说咏物诗描绘了某一物种的普遍特色,书写了共有的文化内涵,那么种植诗的文本和物都被作者私有化、独特化了。
种植诗表现了文人士大夫对生命的珍爱,对悠然意趣的偏爱。朱熹曾云:“在天地则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15]朱熹还曾讲述自己观察植物的体验:“动物有血气,故能知。植物虽不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默见。若戕贼之,便枯悴不复悦怿,亦似有知者。”[16]又如其《杂记草木九首》其七诗云:“西窗萱草丛,昔是何人种?移向北堂前,诸孙时绕弄。”[17]移室外野物入自家来种是宋人常见的行为,这不仅体现了诗人对植物的怜爱,“诸孙时绕弄”一语指出了如孩童一样的爱物之心。种植行为包含着诗人对生命长成的期待,诗人常善于捕捉生命变化的细节,通过生命的力量带来物的诗性和感动,原本普通的物在文人笔下得到了诗意的提升和净化。郑刚中《窗前种小梅树今年未著花但春来绿阴乱眼每过之必徘徊注视冀叶间或青圆如豆也成二十八言》:“水边移得竹边栽,树小条新花未开。绿叶参差须细看,尚疑低处有青梅。”[18]诗人对自栽的梅花满怀期待,因此时时观察其变化,此诗描写的是梅花未开花结果时的状态,明明尚未长成,但作者内心已急不可待,绿叶间青梅若有似无,诗人捕捉到了梅树正在生长、生命正在孕育的细微变化,那种生命的悸动给诗人带来了殷切、愉悦的心理体验。
二 物吾与也:物与精神主体的双向互动
前文已述,种植诗中存在着物与作者双向互动的关系。在种植的过程中,植物是诗人的孩子,种成以后它更多地充当了诗人亲密伴侣的角色。植物并非死物,因其生长变化,能让人感受到活力与生命力,其兴衰变换和人相似,文人总能从植物身上获得共鸣,而植物也像个无声的“人”和诗人相处。植物不再像一般咏物文学中那样,是一个被观赏物,而是一个具有主动性、自主性的有机生命体,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超离了客体的物的本质,其生命本质被凸显出来。邵雍《接花吟》云:“物为万民生,人为万物灵。人非物不活,物待人而兴。”[19]人与物是平等共生的关系,二者之间相互倚仗、彼此成就。宋代文人怀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心态,将人与植物视为天地间平等的生命体,二者可以达到“同情”的心灵对接。他们认为植物是“有情”的。司马光《种竹》诗云:“乃知就阳意,草木皆有情。”[20]他们把客观事物说成是有“心”者,之所以会有情和心等说法,皆是因为草木都是生命体,文人敬畏自然生命生长变化的力量,他们抬升了物在宇宙中的地位的同时,也把它们视作与自己平等共生的存在,是可以与自己进行心与情交流互动的存在。如潘玙《移种菖蒲》诗云:“得此伴闲身,凡花何足惜。呼童汛净室,寘彼芝兰侧。如参物外人,利名念俱释。如亲诗中仙,冷澹趣相得。人物本一体,清浊霄壤隔。物以类而聚,人于交贵择。人为物之灵,讵可乏真识。”[21]种植赏物可以让文人净化心灵,他们把目光从繁杂的人间俗世转移到纯净天然的植物身上,消融名利杂念,重要的是人在观物过程中并未感到自己与物之间格格不入的间隔感,反而生出“人物本一体”的亲近感。欧阳修《希真堂东手种菊花十月始开》诗云:“高人避喧守幽独,淑女静容修窈窕。方当摇落看转佳,慰我寂寥何以报。时携一樽相就饮,如得贫交论久要。我从多难壮心衰,迹与世人殊静躁。种花勿种儿女花,老大安能逐年少!”[22]菊花对诗人盛放,诗人举杯与之对饮,诗人与花的精神交接点在于,菊花的清静独守,不在春日与万花争艳,象征诗人为人处世的态度。此诗书写诗人的老年境况,唯有植物与之相伴,不仅表现了其内心的孤寂与荒芜,也似不再对人生充满热情和希冀。又如《至喜堂新开北轩手植楠木两株走笔呈元珍表臣》:“为怜碧砌宜佳树,自斸苍苔选绿丛。不向芳菲趁开落,直须霜雪见青葱。披条泫转清晨露,响叶萧骚半夜风。时扫浓阴北窗下,一枰闲且伴衰翁。”[23]此诗从栽种的过程写起,诗人参与了树木从出生到繁茂的整个过程,而树也参与到诗人的人生中来,与其日夜为伴,成为了诗人重要的伙伴。风刮树叶发出声响,就如同树木在与诗人对话,它落在诗人窗台上的阴影就像偎依在诗人身旁的友人,紧密地陪伴着他。罗泌曾评欧阳修:“公性至刚,而与物有情,盖尝致意于诗,为之本义,温柔宽厚,所得深矣。”[24]欧阳修的诗、文、词都写到自己的种植体验,诗人对生命有机体的衷爱并将其视作与自己等同的个体,体现了他的爱物怜悯之心,以及内在性情中柔和中正的特质。
张耒作为苏门文人因苏轼遭贬而受牵连,于绍圣四年(1097 年)被贬为黄州酒税监督,后又贬为复州监竟陵郡酒税,元符二年(1099 年)起为黄州通判。张耒曾三次被贬黄州,共在黄州生活了七八年之久,期间他曾创作不少种植诗,把各种植物当作与自己心灵交流的对象、偏居谪地的伴侣。他在《柯山赋》中写及此间的生活:“吾不加物以一毫兮,亦莫受人之燠寒。悟纷华之多虞兮,幸寂寞之至安。饮我薄酒欢有余,啜我豆羹甘而腴,隐几而休读我书。”[25]他在《理东堂隙地自种菜》一诗中说自己“幽居无一事,隙地自畦蔬。”其目的在于“邂逅无事时,弛弓曾把锄。矧我放逐者,终年守敝庐。谅非勤四体,寓意以为娱。”[26]下面看张耒的《问双棠赋》:
寓舍之壤,既膏且腴。手植两棠,于堂之隅。风来自东,冰雪融液。兴视吾棠,既葩而泽。乃沽我酒,又命我人。期一醉于树间,聊快酬于芳春。夹钟之初,谪书在门。陆走千里,止于江滨。天星一周,穆然旧春。想见吾棠,粲然含姿。俯睨旧堂,今居者谁?婉如怨而有待,淡无言其若思。嗟乎!始种自我,其享将获。盈我旨酒,会我宾客。一酌未举,俯仰而失。事至而惊,其初孰测?惟得与失,相寻无极,则亦安知夫此棠不忽然一日复在余侧也?且夫棠得其居,愈久愈敷,无有斤斧斲伤之虞。我行世间,浮云飞蓬。惟所使之,何有南东?夫以不移,俟彼靡常。久近衡从,其志必偿。歌以讯之,用著不忘[27]。
此赋作于元符元年(1098 年)被贬黄州之时。诗人亲手种下的海棠,尚未得以与之共处多少时日,诗人就远赴天涯,宛如在思念一位故人一位旧友,诗人对海棠的思念本质上亦是对旧日安闲时光的怀恋,对贬谪漂泊生涯的无助与无奈。诗人由此生发出得失、聚分等矛盾辩证的思考,任何相对的观念都是随时可转化的。他无法把握命运走向,感叹人生无常,宛若浮云飞蓬漂泊无定。凭树的生命力,只要不伤凿斧,会一直生长在原地,而诗人却四处飘零。海棠就如一位故人时时在故地、在脑海中呼唤着他,牵引着他。
其种植诗有如《秬移宛丘牡丹植圭窦斋前作二绝示秬秸和》二首:
共我辞家似旅人,栽培莫怪倍殷勤。明年太昊城中色,来作齐安江上春。
千里相逢如故人,故栽庭下要相亲。明年一笑东风里,山杏江桃不当春[28]。
诗人在诗中直言牡丹是自己的故人、伴随自己辞家的旅人,还表达了诗人如何殷勤栽培,诗人与牡丹亲密无间、朝夕相伴,诗人似把牡丹视作自己离家漂泊后唯一的伴侣,其中万般无奈都只有牡丹能明了,二诗都寄寓了诗人对来年牡丹盛开的殷切企盼,当花开繁盛,也像是牡丹对诗人的回馈,诗人寂寥的心多少能得到些宽慰和欣愉。
苏辙也同样经历过几度贬谪,他在贬谪时期所作的种植诗,也将植物当作自己的精神伴侣,在漂泊穷处之际成为自己极少可贵的依靠。如《予初到筠即于酒务庭中种竹四丛杉二本及今三年二物皆茂秋八月洗竹培杉偶赋短篇呈同官》:
种竹成丛杉出檐,三年慰我病厌厌。剪除乱叶风初好,封植孤根笋自添。高节不知尘土辱,坚姿试待雪霜沾。属君留取障斜日,仍记当年此滞淹[29]。
此诗作于元丰六年(1083 年)八月,元丰二年(1079 年)苏辙因牵连乌台诗案被贬为监筠州盐酒税,按诗题推算,诗人于元丰三年(1080 年)刚被贬至筠州时种杉竹,可想当时心情如何低沉寥落,因而种杉竹以为伴,诗人在诗中直言杉竹“三年慰我病厌厌”,诗人对其悉心照料,杉竹也日益生长繁盛。诗人取法竹子的生存之姿,也要置身尘土而自持高节。诗人是筠州的过客,杉竹见证了他被贬于此的经历,他日诗人离去后,杉竹似还留在此向人诉说诗人曾经的酸楚。
又如《庭中种花》:
空庭一无有,初种六株花。青桐绿杨柳,相映成田家。春雨散膏油,朝暾发萌牙。造物知我心,初来尽枯槎。开花已可贵,结子成益佳。百事尽如此,一生复何嗟。我生本穷陋,中年旅朝衙。失脚堕南海,生还梦荒遐。筑室虽不多,于我则已奢。松筠伴衰老,已矣无复加[30]。
从诗中提及的“南海”和“中年”推断,苏辙曾于绍圣四年(1097 年)被贬为化州别驾,安置雷州处分,元符元年(1098 年)又移至循州安置,此诗当作于其被贬广东以后。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苏辙连遭贬谪,人生中的大部分坎坷皆已经历过了,他此时的心态不免消极哀愁。家中所种的花柳生机勃勃,俨然如农家乐园,这是他贬谪生涯中难能可贵的慰藉,让他在异乡的生活显得不那么孤独。
其他诗人诗作还有如王禹偁《种菜了雨下》:“菜助三餐急,园愁五月枯。废畦添粪壤,胼手捽荒芜。前日种子下,今朝雨点粗。吟诗深自慰,天似悯穷途。”[31]前日刚撒种今朝就下起雨来,好像老天怜悯身处穷途的诗人,让蔬菜快些长大与他为伴。不仅植物是能与诗人共通的存在,整个自然界也似能听得懂诗人的心声,能看到诗人的精神世界。陈与义《得长春两株植之窗前》:“乡邑已无路,僧庐今是家。聊乘数点雨,自种两丛花。篱落失秋序,风烟添岁华。衰翁病不饮,独立到栖鸦。”[32]此诗作于诗人晚年,绍兴八年(1138 年)七月,陈与义因病提举临安府洞霄宫,此诗作于九月。全诗渲染了一种空漠无所依傍的无归属感。诗中只有两个生命体,一是诗人手种的花朵,二是在诗末树立的孤独自怜的诗人形象。漂泊的诗人因为孤独而寻求陪伴,因无聊而寻找闲事,于是花便成了与他在异乡相互偎依的伴侣,为他灰白的生活添上一抹亮色,花朵似乎也能抚慰他失意寥落的心情。
三 格物之理:时间尺度与宇宙意识
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云:“夫中与和者,有常之气,其推于物也,亦宜为有常之形。”[33]张载也认为万物由天地间的气而生。宋代文人认为,草木皆由大自然,或者说是“天”孕育而生,阴阳相生,遵循宇宙循环往复的生死规律。欧阳修《易问童子》卷一云:“天地之心见乎动,《复》也,一阳初动于下矣。天地所以生育万物者本于此,故曰‘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34]对于宇宙万物运行之规律,欧阳修有这样的认识:“天形如车轮,昼夜常不息。三辰随出没,曾不差分刻。北辰居其所,帝座严尊极。众星拱而环,大小各有职。不动以临之,任德不任力。天辰主下土,万物由生殖。一动与一静,同功而异域。惟王知法此,所以治万国。”[35]王安石《即事三首》其三:“日月随天旋,疾迟与天侔。寒暑自有常,不顾万物求。蜉蝣蔽朝夕,蟪蛄疑春秋。眇眇万古历,回环今几周。”[36]张耒《鸣蜩》:“阴阳且战争,微物何所竞。化工执其机,开阖惟所命。”[37]宇宙与时间都是无限的,生长与凋落,存在与消亡,是不可逆转或更改的永恒的运行机制,一切皆不由人力可控。而人也和草木一样是宇宙中臣服于天道常规的存在之一。晁说之《晁氏客语》:“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当与天地齐毕。天地未尝老,而人自老。”[38]种植作为一种需要时间长度的事时常能引起文人对物理、时间以及宇宙人生的深刻思考,文人常将植物视为一个时间的标尺,种植诗的文本中也时常出现表示时间的词。诗人总是惯于将植物与人作对比,他们通过表述从物身上看到的理,来抒发自己对生命万物的情。诗人的时间意识主要产生在几个阶段:首先是栽种之初,想象日后还需多长时间植物长成;其次是植物长成时,意识到它盛放之短暂,凋零之日近;最后是植物生长的整体时间长度时常被诗人拿来与自己人生的时长作对比。如刘克庄《留山间种艺十绝》其三:“一生着数落人先,白发栽松故可怜。待得伏菟堪采掘,此翁久已作飞仙。”[39]文人通过对植物生长变化的体察,感受到时间的不可把控性,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短促,进而感受到命运的不堪托付。
欧阳修在其诗文中时常流露出时间生命意识,如《寄圣俞》:“古来磊落材与知,穷达有命理莫齐。悠悠百年一瞬息,俯仰天地身醯鸡。其间得失何足校,况与凫鹜争稗稊……壮心销尽忆闲处,生计易足才蔬畦。优游琴酒逐渔钓,上下林壑相攀跻。及身强健始为乐,莫待衰病须扶携。”[40]《述怀》:“物理固如此,人生宁久盛……偷闲就朋友,笑语杂嘲咏。欢情虽索莫,得酒犹豪横。”[41]《采桑子》:“十年一别流光速,白首相逢。莫语衰翁,但斗尊前语笑同。”[42]人与草木一样,在天地之间皆渺小如丝,宇宙浩瀚无垠,俯仰之间,瞬息万变,物理永恒,那么人又做得了什么呢?索性趁着短暂的欢愉,把握当前尚能把握住的时光。欧阳修的种植诗同样流露出了类似的生命无力感。如《西斋手植菊花过节始开偶书奉呈圣俞》诗云:“好色岂能常,得时仍不早。文章损精神,何用觑天巧。四时悲代谢,万物世凋槁。岂知寒监中,两鬓甚秋草……为君发朱颜,可以却君老。”[43]花虽开了,但并不能持久,花开给诗人带来的不是对生命的礼赞,而是反观年迈日衰的自己,反而产生出对时间流逝与生命善变的悲观之意。所幸花开还是为生活带来了一丝生意,让消沉的诗人不至于孤独寂寥。《去思堂手植双柳今已成阴而有感》:“曲栏高柳拂层檐,却忆初栽映碧潭。人昔共游今孰在,树犹如此我何堪!壮心无复身从老,世事都销酒半酣。后日更来知有几,攀条莫惜驻征骖。”[44]诗人把初栽小绿到如栏般高的柳比作曾经壮年而今衰老的自己。从植物的变化感到时间的挪移,进而产生物是人非之感,而人事变迁比植物的变化还快,令人措手不及。
其他诗人的诗作同样以植物为时间尺度,讨论物理的同时也渗透着诗人对宇宙人生的消极悲观之情。如寇准《判都省怀感》:“昔为学士掌三铨,屈指年光三十年。秋雨滴阶桐已老,白头重到倍依然。”[45]其自注云:“余顷年手植桐树在省,有朽者。”三十年这个时光概念成为了全诗的核心,它联系着衰朽的桐树与白头的诗人,诗人不禁油然生出光阴荏苒的时变之叹。陈舜俞《种梅》诗云:“绕径一百树,抚视如婴儿。古来横斜影,老去乃崛奇。嗟尔生也晚,笑我行且衰。世人非金石,或作千年资。转眼共零落,较此不更痴。有情且寓赏,勿着嘉与悲。”[46]植物的生命长度与诗人的生命长度是不一致的,诗人只能在短暂的与植物生命相交的时间里与之共处。诗人将新生的梅与行将就木的自己作对照,梅的生命周期短,也许会与诗人“共零落”。梅从新生到零落的过程犹如诗人自己的生命缩影。所以诗人说有情暂且赏乐,勿要把关于生命生死的浓重悲喜寄托于此。强至《野园移植小松》:“落落岩涧姿,相对永朝夕。如言千载后,其长可千尺。人生虽百年,相期眇无极。且结无情游,汝固予何易。岂待百年外,人松两殊迹。人为松下土,松化土上石。我生始逾壮,足以伴寒碧。”[47]松虽是长寿之物,但也如人一样,百年寿命看似长实则转瞬即逝,诗人为了逃避这种对时间无限、生命有度的无力把握之感与困惑,索性说“无情游”。诗人没有从植物身上看到对生命的希冀,反而说物与我殊途同归,百年之后“人为松下土,松化土上石”,诗人自我的生命长度虽与植物的生命长度有千载与百年之别,但在存在与消亡的意义层面上实则是等同的。蔡襄《福州堂下小栏花卉多是手栽今已繁盛因赏花有所感悼》:“爱花尽日傍花台,点检当年手自栽。前事已随朝暮变,旧丛空见浅深开。山禽忽下还飞去,溪雨才收又复来。只有春醪能遣恨,无人栏畔共持杯。”[48]花从当年新栽到现今盛放,对应着前事的存与亡,诗人接着又写了飞来又飞去的山禽,停了又下的雨,这些都是表现诗人时间意识的意象,它们都和植物一样代表着时空的变迁,在诗人所能感知的世界中,一切都是变化无常的,而在这无边的无常中,只有当下手中的酒是诗人能把握住的,他只能在醉意中消解世事无常带来的茫然和空虚感。范成大《两木》其一:“枇杷昔所嗜,不问甘与酸。黄泥裹馀核,散掷篱落间。春风拆勾萌,朴 如榛菅。一株独成长,苍然齐屋山。去年小试花,珑珑犯冰寒。化成黄金弹,同登桃李盘。大钧播群物,斡旋不作难。树老人何堪,挽镜觅朱颜。颔髭尔许长,大笑欹巾冠。”诗序云:“壬申五月,卧病北窗,惟庭柯相对。手植绿橘枇杷,森然出屋,枇杷已着子,橘独十年不花,各赋一诗。”[49]诗人在诗中记录了枇杷从随意洒落篱间的种子,到长成齐屋大树的过程,这种奇妙的物质变化让诗人感受到了独特的生命体验,对天地自然产生了敬畏之心,他不禁揽镜自照,只见自己脸上长出的胡须,使他一再感受到生命的力量、时间的变化体现在自己身上。序中提及诗人此时正卧病,他从植物身上感受的生命变化与自己身上的变化有兴衰之别,“大钧播群物,斡旋不作难”既指大自然对草木的孕育,也体现了诗人对任何生命在宇宙天道面前无法抗拒、只能任其兴衰的无力感。
四 人格空间:身份标志与价值取向
宋诗中的种植以大片栽种为主,主要用于装饰庭院,这实质是文人在为自己构筑一个理想的闲居生活环境,创造一个清逸宁静的空间。植物成为屋舍的一隅,整个空间都被染上了植物的特性,或者说是诗人赋予了它文化性格。宋人将种花植树称为“幽事”,种植者则自称为“幽人”,把观赏植物称为“幽赏”。“幽”有隐蔽、深远、清静、闲适的意思,种植这件事情本身就被视作是处幽自静、避世独守的表现,且文人选择栽种的物种以竹、梅、柳等为多,这些物种本就被赋予了清静脱俗的文化内涵,文人种植花木实则是在树立一种与世无争、宁静致远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是一种喜静性格的自我标榜。诗人种植花木邀人观赏,或自己作诗予人,在诗中将植物的性格等同于自我的性格,将自栽的花木视作自我的化身和精神外现,因此种植也是诗人自我存在的身份标志、自我与世界相处方式的昭示。文人在种植与观赏中获得内心的平静与精神的自由,这是他们选择由外转向内,选择幽独自守的原因之一。如陈宓在《跋族子惟孝蒲严记》中记录自己种菖蒲的体悟:“心犹火也,必有所丽,然后不失其正。上焉者丽于道,其次丽于物之不为病者,凡书画草木皆是也……手植而时溉之,不瘠不腴,长不过寸,畅茂之意,四时有常度,风雨晦明,晨朝莫夜,心无他系,率寓于是,恬清怡愉,气因以平,与世之好尤物而外鹜者有间矣。”[50]
宋人有不少以植物命名厅堂的例子,如陈著在《延清堂记》中记载,友人家中自种桧木两棵,因而为之起名“延清堂”,只因桧木“与松柏同清,苍然秀楚,嚣俗不得而亲,故独静”,宅院主人“若而能对越旧物,切已体认以自玉,则名斯称”[51]。《中吴纪闻》载:“双莲堂在木兰堂东,旧芙蓉堂是也。至和初,光禄吕大卿济叔以双莲花开,故易此名。”[52]建筑的名称因植物而起,而植物的特质也与主人的人品相联系,由此形成了植物、园圃、主人三位一体的关系。就如起名一样,诗人作诗描写自己的居所和植物,是一个向外人彰显自己的过程,诗歌本身也成为了他们的自我标榜,一种自我表达。
还有一种自我标榜的方式是在诗歌中模仿古代名士,树立文化偶像,张贴文化符号。在家中种植以营造隐居环境是长久以来形成的文化传统。由于植物具有所属者的身份意义,因此宋诗中的种植之物大都为具有文化内涵、能体现士人身份的雅物,瓜果等农作物为少数,种竹、松、柳、菊为多,选择这些植物是基于其内在的文化基因。如“吾爱王子猷,借宅亦种竹”(司马光《见山台种竹斋》);“子猷借宅亦种竹,渊明荒径犹存菊”(喻良能《种菊》)。文人如此称引先贤是为了借文化偶像来标榜自己的品德。
种植成为了隐逸的代名词,种植的空间如农圃、庭院等空间名词在诗歌中成了隐逸的符号。罗大经《鹤林玉露》曰:“士岂能长守山林,长亲蓑笠,但居市朝轩冕时,要使山林蓑笠之念不忘,乃为胜耳。”[53]文人在自家栽种就是要自行建构一个隐居的空间,使其虽身处闹市亦得以心宁自守,留住一片清静的园地。《渑水燕谈录》载:“野(魏野)于东郊凿土室方丈,荫以修竹,泉流其前,曰‘乐天洞’;渎(李渎)结茅斋中条之阴,曰‘浮云堂’,皆有潇洒之趣。每乘兴相过,赋诗饮酒,累日乃去。”[54]苏轼曾云:“筑室艺园于汴泗之间……使其子孙开门而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闭门而归隐,则俯仰山林之下。”[55]刘方指出:“士大夫的入世与入仕,往往容易导致对于皇权的依附,从而失去了士大夫人格的独立与自由……只有建构起士大夫独立与自由的人格,才能保证以道抗势的人格精神、终极信仰与审美理想,而基于自由原则的隐士,恰恰能够提供人格的独立与自由。”[56]隐逸是士大夫对自我存在、人格与精神自由的追求。但归隐绝不是士大夫绝对的终极目标。曾巩《南轩记》云:“得邻之茀地蕃之,树竹木灌蔬于其间,结茅以自休,嚣然而乐。世固有处廊庙之贵,抗万乘之富,吾不愿易也。人之性不同,于是知伏闲隐奥,吾性所最宜。驱之就烦,非其器所长,况使之争于势利、爱恶、毁誉之间邪?”又:“得其时则行,守深山长谷而不出者,非也。不得其时则止,仆仆然求行其道者,亦非也。”[57]身居陋室,清静自守是顺应了诗人天然性情之事,可实现其精神之自由。而对于出仕与静守的矛盾,曾巩则用“得其时”来作判断的标尺,人要在适当的时机做适当的事,既不应违背性情、也不应违背时态,进退得宜。葛胜仲《维心以诗送花果栽次韵》诗云:“奉乞花栽旋旋移,退师老圃自安时……庭柯只作怡颜具,肯比侯封逐利宜。”[58]诗人用“退师老圃”来指代退隐,又将退隐与“侯封逐利”相对立,表示自己宁肯与庭柯作伴,自得其乐,也不愿到庙堂之中陷于追名逐利中。晁补之《栽花招泗州叔父》:“春园移春栽,芽孽粳粒大。东风日日吹,喷吐不暇裹。杨梢青犹未,桃萼红尚可。田蔬美已最,村醑醇亦颇。少年慕立事,幸得能几个。艰难合归来,茅屋聊共佐。”[59]诗人把“立事”和在茅屋中赏花饮酒相对立,对功名利禄淡然处之,只愿关心花木蔬植。文人士大夫生活在草木环绕的茅舍中,就是生活在一个审美的、已被净化的、无忧的世界,他们选择遗忘人世,只关心自己身边的日常生活,回归舒适区。陆游《种秫》:“种秫供留客,移花待探春。愁边开乐国,闹里作闲身。鬓发今如此,头颅莫问人。白鸥非避俗,野性自难驯。”[60]种植代表“野性”,被视为一种与功利性相对立的价值观。诗人种植不为达到任何具有实质性的目的,只为愉悦心灵,实现精神的自由。
诗人们对于自己几经栽种修饰幽美的宅院的描绘,总是致力于雅致清幽意境的营造:
西垣种竹满庭隅,正值天街小雨初。渐近凉风侵梦觉,已留清露滴吟馀。卜邻近喜苍苔满,托迹方惊上苑疏。昨夜青藜光照席,绿阴相对小除书[61]。(孔平仲《和子瞻西掖种竹二首 其一》)
临砌复临流,栽初尚未稠。长因带风雨,远似在汀洲。静间宜红蓼,闲栖称白鸥。前春应更好,江上梦潜休[62]。(魏野《新栽苇》)
栽梅沿屋角,幽趣少人知。雪后月明夜,孤芳吐几枝[63]。(金朋说《种梅吟》)
植物犹如一道屏障,把诗人与外部尘世阻隔开来;宅院经装饰后,也变得悠然宁静,好似在深山野外的桃源之中。文人栽种植物,亲手为自己建构了一个诗意的乐园,诗人在植物的包围中,肉体和心灵都被植物的生命力浸染着,暂时忘却了尘俗烦扰。
种植诗不仅具有栽种的史料文献价值,反映了宋代士人阶层种植、观赏的社会风气,扩大了宋代诗歌的题材范围,更在思想层面上,折射出宋代文人士大夫广袤深厚的精神内蕴。诗人们在仔细体察植物生长过程中,将自己对宇宙天地的哲学思考融入诗歌书写中,将物与人摆放在同等齐平地位,进行物我对话,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与植物互相依偎。植物不再如在一般咏物文学中那样,是一个被观赏物,而是一个具有主动性、自主性的生命有机体,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超离了物的本质,其生命本质被凸显出来。士大夫在闹市中种植,实现了不踏入山林亦能隐居避世的目的,把自己与尘俗烦扰隔离开,选择与肩天下之大任相反的价值取向。种植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诗理性化、哲学化、日常化、雅化等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