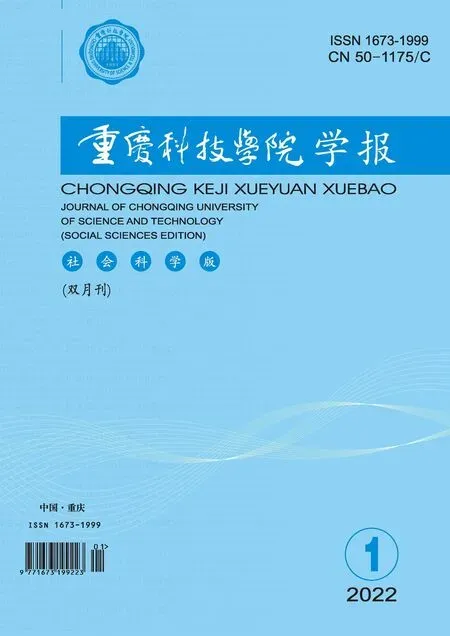以业立世:《颜氏家训》的家庭劳动教育思想及其启示
2022-11-21孙海霞张德学
孙海霞 张德学
(黄山学院,安徽 黄山 245041)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家训作为家庭对子孙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教诲,往往包含着丰富的劳动教育思想。古人尤其看重家训,那些被记录下来的训导展现着中国传统的劳动价值观和劳动精神。北齐著名学者颜之推(531—约594)所撰《颜氏家训》是一部系统完整的家庭教育教科书,享有“古今家训,以此为祖”(王三聘《古今事物考》二)的美誉,其“勉学”篇中明确提出“人生在世,会当有业”的训导,形成了以“以业立世”为核心价值观的家庭劳动教育理念,对后世影响深远,至今仍具有启发意义。
一、自力更生、积极担当的人生追求:《颜氏家训》谈劳动的意义
颜之推一生坎坷,“三经世变,身仕四朝”,其晚年所作的《颜氏家训》[1]成书于隋朝初期。当时,国家分裂,战乱频仍,朝代更替频繁,士族衰落。动荡的时局令他清醒地意识到,必须以家庭教育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颜氏家训·序致》,以下引此书只注篇名)。他在《勉学》中深刻阐释了劳动的意义,提出以“人生在世,会当有业”为核心价值的家庭劳动教育理念,以期培养子孙勤学立业、勤俭向善的劳动精神和品格,引导子孙树立自力更生、积极担当的人生价值追求。
颜之推善于通过身边的人和事点明劳动的意义。“多见士大夫耻涉农商,差务工伎,射则不能穿札,笔则才记姓名,饱食醉酒,忽忽无事,以此销日,以此终年”(《勉学》)。他看到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大多终日无所事事、浑噩度日,不禁长叹:“何惜数年勤学,长受一生愧辱哉!”(《勉学》)这些表面光鲜的士大夫们,平常不注意勤学立业,到了关键时刻难免丢丑受辱。于是,他告诫子孙“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切不可虚度年华,要有以“业”立世的志向,勤于学习,读好书、学好技能,争取“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勉学》)。
颜之推也常通过历史的经验教训指出劳动的意义,来劝导子孙。他注意到,梁朝在全盛之时,社会上奢侈安逸之风盛行,贵族子弟们大多不学无术。他这样描述当时贵族子弟的生活状态:“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勉学》)他告诫子孙,这些日常涂脂抹粉、好逸恶劳、过着“神仙”般生活的贵族子弟,一旦遇到世道离乱,往往“求诸身而无所得,施之世而无所用”,最后只能落个颠沛流离、无处安身的下场,成了实实在在的蠢材。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有学识和掌握一定技艺的人则可以 “触地而安”(《勉学》),有着很强的适应社会的能力,到哪里都能安居。
自力更生、积极担当一直都是传统儒家文化尊崇和倡导的精神。在儒家看来,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积极担当,是人法天道应有的一种品格。孔子在回忆自己一生时讲到“三十而立”(《论语·为政》),朱熹对此解读道:“有以自立,则守之固而无所事志矣。”(《四书集注》)他认为一个人一旦实现了自立,就意味着把志向落实到了行动,就有了较强的行动能力。颜之推提出的“人生在世,会当有业”的主张,蕴含着古人这种依靠劳动实现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自由精神,也彰显着古人“以业立家、以业立国”的责任和担当。“一个健康向上的民族,就应该鼓励劳动、鼓励就业,鼓励靠自己的努力养活家庭、服务社会、贡献国家。 ”[2]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乱,政治斗争极其惨烈,人们在个体与整体剧烈冲突的矛盾处境中……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的淡化与对个体生命存在的重视结合起来,很自然地衍生出了及时行乐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3]39。因此,颜之推这种从实现个体自力更生和积极担当两个方面突出以“业”立身的主张,是针砭时弊、行之有效的。他所强调的劳动意义兼顾了劳动的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两个层面。以业立世,实现自力更生,是劳动的外在价值,强调的是劳动作为人们维持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工具意义。以业立世,积极担当,是劳动的内在价值,突显的是劳动对实现人的尊严和自由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指向了人的本质实现问题,“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4]。
二、以业立世:《颜氏家训》中劳动教育的主要内容
“以业立世”是颜之推家庭劳动教育的核心价值精神。那么,一个人该立何“业”,如何立业?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对这些问题所做的解答,便是其家庭劳动教育的具体内容。
(一)皆有先达,可为师表:业无尊卑的劳动观念
“人生在世,会当有业:民则计量耕稼,商贾则讨论货贿,工巧则致精器用,伎艺则沉思法术,武夫则惯习弓马,文士则讲议经书。”(《勉学》)颜之推劝导子孙以“业”立世,要求子孙应该学习并掌握一定的专业技能。他认为,一个人只有掌握相应的职业技能,有自己的职业和事业,才能立定自身,维持家庭的运作,也才能保证国家的安定有序。
在颜之推看来,职业虽然分工不同,但都有各自的专属技能和技术要求。每个职业所涉及的专业技能是需要全面地悉心学习和深入钻研的。只有这样,才能胜任其职。例如在讲到地方官员的“治民”之术时,他说:“但知私财不入,公事夙办,便云我能治民;不知诚己刑物,执辔如组,反风灭火,化鸱为风之术也。”(《勉学》)颜之推指出,作为一个地方官员,想要治理好一方百姓,除了要有“夙夜在公”的无私品格,还要做到诚心待人、为人楷模,要具备变恶为善的能力。当然,不仅仅“士”阶层的职业需要专业的技能,农商工贾也有其专门的技术要求。“爰及农商工贾,厮役奴隶,钓鱼屠肉,饭牛牧羊,皆有先达,可为师表,博学求之,无不利于事也。”(《勉学》)就算是农民、商贩、劳役、渔夫、屠夫、养牛放羊者,也都有成就突出的人,应该广泛地向他们学习,以便增益事业。
颜之推这一“皆有先达,可为师表”的观点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其中包含着一定的劳动平等观念。这个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元末明初的徽州名门望族太平杜氏家训也有言道:“人无一定之业,则无以生,故士农工商皆恒业也。凡为父兄者,须量子弟材质之高下,身体之强弱,各治一业,不可听其游惰,陷入下流。”[5]这是说,每个人立于当世,都应当谋求一份职业,掌握必备的知识和技能,以此来满足个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求,才能承担起家庭和社会给予的责任。至于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根据个人的具体资质来决定就好。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一个人只要踏实肯干、勤于钻研,无论从事什么样的职业,都能做出卓越的成绩,都能成为能人。
(二)贵能有益于物耳:实干务实的劳动精神
颜之推教导子孙,为人处世要有务实精神,要做有益于他人的事,不可高谈阔论、虚度人生。他说:“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涉务》)在他看来,一个士君子如果不能在自己的公职岗位上做到尽职尽责敬业,那是令人羞耻的。“入帷幄之中,参庙堂之上,不能为主尽规以谋社稷,君子所耻也。”(《诫兵》)他劝导子孙应勤苦修德、勇敢担当:“又君子处事,贵能克己复礼,济时益物。治家者欲一家之庆,治国者欲一国之良,仆妾臣民,与身竟何亲也,而为勤苦修德乎?亦是尧、舜、周、孔虚失愉乐耳。一人修道,济度几许苍生?免脱几身罪累?幸熟思之!”(《归心》)
有了务实之精神,还应有实干之能力。颜之推主张通过广泛接触社会,增加劳动体验尤其是农业劳动体验,来提升应世经务的能力。“吾见世中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陈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以应世经务也。”(《涉务》)他认为,只有通过劳动才能提升个人对社会不同阶层的了解,才能提高个体处世办事的能力;否则,不仅难以应付时事和处理政务,甚至还可能闹出笑话。例如梁朝的王复,生活奢侈浮华、孤陋寡闻,最后连马和老虎都分不清楚。“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喷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涉务》)
(三)施而不奢,俭而不吝:勤俭向善的劳动品格
勤劳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可以让生活变得富足,也是对劳动成果的尊重和珍惜。这是向善人格塑造中的重要内容。早在《尚书》中就有“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的劝导。《左传·宣公十二年》也指出:“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勤俭是古代劳动观念中的应有之义,是齐家治国的基础。中国古代家训中普遍重视勤俭美德。《国语·鲁语下》记载了春秋时鲁大夫公父文伯的母亲敬姜对儿子的名训:“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这是说,人民勤劳就会想到节俭,想到节俭就会产生善心;相反,安逸会带来纵欲放荡,纵欲放荡就会忘记善良,忘记了善良就会生出坏心肠。颜之推遵从儒家经典的教诲,告诫子孙一定要勤俭敬业:“生民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爰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植之物也。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但家无盐井耳。”(《治家》)在他看来,一个人的职业才是生存之本,若能守业敬业、勤俭节用,那基本上就可以自足而安了。
针对生活中时常存在的“施则奢,俭则吝”现象,颜之推劝导子孙应该做到“施而不奢,俭而不吝”(《治家》)。他认为,在践行节俭美德时要注意把握“度”,既不能丢弃节俭美德去奢侈,也不能节俭过度成吝啬。为此,他讲到梁朝一个“中书舍人”由于治家过于严苛,最后这个人的妻妾联合买通刺客,趁他喝醉时把他杀了。这是节俭过度的吝啬招致的恶果。颜之推说:“俭者,省约为礼之谓也;吝者,穷急不恤之谓也。”(《治家》)节俭是合乎礼制的节省,是珍惜劳动成果、克制内心贪欲的一种行为选择,是一种美德;而吝啬则意味着对穷困急难的人也不加救助,是为了保全自己的财产,对他人疾苦无动于衷的一种表现。二者是完全不同的。《左传》亦云:“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可见,他对勤俭的推崇,不仅是出于对治家之方考虑,也是在表达对子孙美德养成的期待,鼓励子孙养成一种勤俭向善的劳动品格。
(四)学之所知,施无不达:知行合一的读书理念
与传统儒家将“成圣成贤”视为读书目的不同,颜之推秉持“以业立世”的核心价值观念,提出读书是一种职业技艺的观点。“夫明《六经》之指,涉百家之书,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厉风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勉学》)这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将读书看作一种生存技能和谋生路径,不仅反映了个人以“业”立世的现实需求,也反映了身处动荡时代的士君子们谋求自保、安身立命的迫切愿望,因而更能被普通大众理解和接受。在他看来,相较于其他技艺,读书是一种更易掌握且更受尊敬的谋生方式。“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世人不问愚智,皆欲识人之多,见事之广,而不肯读书,是犹求饱而懒营馔,欲暖而惰裁衣也。”(《勉学》)一个有天资但不愿读书,仅仅依靠日常经验来生存的人是懒惰的。
不似某些贵族士大夫把读书视作闲谈消遣,颜之推强调读书是为了开心明目、增益行动。“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勉学》)。他主张“学之所知,施无不达”,学习与实践应该统一起来,实现知行合一。实际生活中,许多读书人“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勉学》),能空谈但不能身体力行。“加以断一条讼,不必得其理;宰千户县,不必理其民;问其造屋,不必知楣横而梲竖也;问其为田,不必知稷早而黍迟也”(《勉学》),遇事往往一知半解,办不好事。在颜之推看来,这些只知吟咏歌唱、写诗作赋的人,只会做些迂阔荒诞的事情,对治军治国没有丝毫用处。要弥补这种不足,应该通过读书学习古人的做法。比如在不知如何孝养父母时,“欲其观古人之先意承颜,怡声下气,不惮劬劳”;在不知如何侍奉君主时,“欲其观古人之守职无侵,见危授命,不忘诚谏,以利社稷,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勉学》),做到真正地学以致用。颜之推又举“孝”德为例,指出孝的真谛就体现在日常侍奉父母的劳务中。
现代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谈到:“世界上有四种人:一种是劳心的人;一种是劳力的人;一种是劳心兼劳力的人;一种是在劳力上劳心的人。单单劳力,单单劳心,都不能算是真正之做。真正之做须在劳力上劳心。”[6]104陶先生强调“做”,并指出真正的“做”是要用心思去指导并指挥“做”,由此强调劳力和劳心的合一性,消除劳动和职业上的歧视。可见,颜之推在其家训中提倡的“学之所知,施无不达”已是非常先进的教育理念。
三、《颜氏家训》中开展家庭劳动教育的方法
从劳动教育的视角审视《颜氏家训》,我们会发现其中包含着丰富而有价值的家庭劳动教育方法。
(一)重立业之志的确立
儒家一贯重视立志教育。孔子十五岁便“志于学”,成为后人楷模。王阳明在与弟子的对话中,曾经专门讲到“立志”的意义:“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则自然心中凝聚。犹道家所谓结圣胎也。”(《传习录》上)颜之推遵循儒家教义,以“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劝导子孙,应从小立下要成就一番事业的志向,不要无所事事、不学无术、奢侈安逸地虚度年华。他认为:“有志尚者,遂能磨砺,以就素业,无履立者,自兹堕慢,便为凡人。”(《勉学》)那些有志气的人能够经受磨炼,成就一番大的事业,而那些没有操守的人,容易懒散懈怠,只能成为平庸之辈。在他看来,只要肯努力,任何人都可以在自己的领域成就一番事业的。“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就是他对自己子孙志向的勉励和期待。
颜之推主张积极入世、博施济众,反对当时因盲目、片面追逐道家教义,而把儒家主张的济世成俗之业“弃之度外”(《勉学》)的社会风气。他指出,道家主张“全真养性,不肯以物累己”(《勉学》),把追求本真、不为外物所牵绊的逍遥自在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目标,不过是“直取其清谈雅论,剖玄析微,宾主往复,娱心悦耳,非济世成俗之要也”(《勉学》)。那些以清谈为务、追求个人享乐、不问政事的道士,都是缺乏自觉担当精神的人。据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上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玄学的兴起,一些人试图用老庄思想来解释儒家经典。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儒家思想逐渐被道家思想所改造,随之而来的,则是士大夫在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方面的变化,其价值取向由传统的士所遵循的兼济天下向独善其身转变,因此,纵情声色,追求个体自由,不拘礼法成了这个时代的时尚”[3]16。然而,颜之推坚持以强调责任担当的儒家道义来引导子孙确立自己的事业志向。在他看来,若从小立下“会当有业”的志向,便可以凝心聚力,把握好人生前进的方向,就能够保持一种自力更生、勤学克俭、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最终成就一番事业,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
(二)重劳动习惯的养成
提倡通过“早教”来养成好的德行,是《颜氏家训》的一个特色。这种“早教”就是在强调家庭劳动教育中劳动习惯养成的重要性。“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使为则为,使止则止。”(《教子》)颜之推认为,在子女能看懂大人的脸色,知道大人喜怒的时候,就要开始进行劳动教育。要尽早让孩子养成大人允许做的事情才做,不允许做的事情就不能做的习惯。如果父母对子女不加教育,甚至一味溺爱,任其为所欲为,就会养成孩子骄横的习性。“骄慢已习,方复制之,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教子》)坏的习性一旦养成,那父母的教诲、管束就只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甚至遭到子女的怨恨,其最终恶果可能会让孩子成为道德败坏、懒惰成性的人。他甚至以自己为例告诫道:“年十八九,少知砥砺,习若自然,卒难洗荡。”(《序致》)在他看来,正是由于自己当时缺少好的“早教”,所以在成长过程中走了不少弯路。
家庭劳动教育的日常化,对良好劳动习惯的养成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后来《朱子家训》中也有“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和“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等训条,体现着对劳动习惯养成的重视。
(三)重榜样示范的引导
颜之推十分推崇榜样在家庭劳动教育中的示范引导作用。“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肄,久而自臭也。”(《慕贤》)他认为,人在年少的时候,很容易受周边人和环境的影响,因此好的榜样可以引人向善,坏的榜样却会让人误入歧途。模范对规导个人行为、引导社会风尚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且劝一伯夷,而千万人立清风矣;劝一季札,而千万人立仁风矣;劝一柳下惠,而千万人立贞风矣;劝一史鱼,而千万人立直风矣。”(《名实》)颜之推指出,人在本性上都是仰慕善、追求善的,好的榜样可以起到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这也正是孔子所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的道理。
因此,颜之推一方面强调父母应该言传身教,努力营造好的家庭劳动氛围;一方面教导子孙要向周边的贤人学习,向古代先贤学习,向普通从业者学习。他尤其擅长通过对比正反两方面的人物例证来引导子孙养成相应的劳动观念和品格。比如在《治家》篇中讲到“施而不奢,俭而不吝”时,他不仅提到那位因治家过于严苛而最后被妻妾共谋杀害的“中书舍人”,还列举了当时的一些名士,由于治家过于宽仁最后被家人克扣馈赠的故事。讲到一位叫房文烈的官员,因治家不严,任由其家中奴婢把房子当柴烧了的惨事时,他还将虽然生活清贫但乐于助人的南朝裴子野和贪得无厌又十分吝啬的邺下将军做了对比。这种对比强烈的叙述方式,在颜炳罡教授看来,是“以理统事,以事明理,理事圆融”[7]。颜教授认为《颜氏家训》通过人物故事来说理,通俗易懂,能在劳动实践教育中产生更好的育人效果。
(四)重亲身劳动的体验
颜之推主张,通过亲身参加劳动尤其是农业劳动的方法,养成相应的劳动观念及品格。“古人欲知稼穑之艰难,斯盖贵谷务本之道也。”(《涉务》)他认为,只有亲自体验过耕种和农作的艰辛,才能使人真正地珍惜粮食,形成重视农业生产的意识。他告诫道:“未尝目观一坺土,耘一株田;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故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皆优闲之过也。”(《涉务》)农业是国民经济之本,而一个缺少必要农业劳动体验和农业生产知识的人,是不可能做好官、当好家的。“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涉务》)没有农作经历的人,是不可能理解普通劳动者的艰辛和劳苦的,也难以处理好社会事务。只有那些体验过耕种辛劳的人,才会尊重农民并由此尊重他人。因为劳动本身就具有育人的功能,亲历劳动过程,有助于涵养人的同情心、理解力、审美力和行动力,帮助个人实现全面的发展。
对此,陶行知先生也有相似的主张。他认为学习者一定要亲历劳动,特别是农业劳动。他说:“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6]158,实践对形成知识和观念作用巨大。他倡导“教育与农业携手”,他在谈到当时的乡村教育时说:“倘有好的乡村学校,深知选种调肥,预防虫害之种种科学农业,做个中心机关,农业推广就有了根据地、大本营,一切进行,必有一日千里之势。”[6]82陶先生当年的这句话是针砭时弊的。今天重新审视颜之推提倡的亲身体验式劳动教育方法,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其特定的农耕文明的社会背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其中的重要启示,那就是:通过亲历劳动,尤其是应通过加强对农业劳动的亲身体验,拓宽人生体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让更多的青年学生了解农村、农业和农民,吸引更多的青年投身到乡村振兴的事业中去。
四、《颜氏家训》的家庭劳动教育思想对新时代高校劳动育人实践的启示
“《颜氏家训》的出现,开始把自汉代以来处于上层经学和精英文化层面的儒学引向了世俗社会的深层,为儒家文化世俗化或民间化创造了一种有效的形式。”[8]可以说,颜之推用《颜氏家训》将传统儒家文化所蕴含的劳动教育理念,进行了一次民间生活化的展示,其意义超越了家庭劳动教育范畴,对新时代我国高校的劳动育人实践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2020年2月至3月,我们曾围绕“大学生劳动价值观现状”问题,对当时宅家战疫的大学生做了一次线上问卷调研,收回有效问卷1 788份。在问及大学生们宅家经常会做哪些事情时,“常常帮父母分担家务”的占比只有47.15%,而“经常玩手机”的比例则达到56.43%。由此可见,当今大学生的劳动观念还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大学阶段是现代社会青年价值观塑造的重要时期,结合《颜氏家训》中有关劳动教育的启示,我们认为,高校应该承担起对新时代大学生进行劳动教育的主导性作用。
第一,高校应重视和引导大学生树立专业志向和职业志向。“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大学的学习是专业性的学习,大学生在校通过接受系统的专业训练,学习掌握系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由此获得将来回报社会、贡献社会的一技之长。高校要重视对大学生专业志向的培养。在新生进校时就开展专题讲座,不仅要介绍专业课程体系和培养目标,也要介绍该领域的专业领军人物及杰出毕业生的典型事迹,培养他们的专业认同感,帮助其逐步确立专业志向和职业志向,做好学习规划和职业规划,激发其内在学习动力,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争取未来在专业领域实现卓越。
第二,高校应充分利用课堂这个主渠道,将劳动价值观教育融入其中。劳动教育的核心是劳动价值观教育[9]。根据调查,大学生在被问及对“干得好不如嫁(娶)得好”这一观点的看法时,明确表示不太赞同和不赞同的占比是42.34%,另有43.29%表示“中立”。可见,大学生群体确实存在着劳动价值观上的偏差和认知误区。利用课堂这一主渠道重塑大学生的劳动价值观:一是利用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辟专题,引导大学生学习有关职业道德、劳动法规、唯物史观、劳动价值论和劳动幸福观等相关知识,学会洞察时代特征,领会和把握劳动的本质和意义;二是适时地把劳动价值观教育和专业教学结合起来,通过实验、专业实训、技能竞赛、见习和实习等环节,将专业学习与实践统一起来,实现知行合一,鼓励大学生努力提高本领,勇于创新、不断求真、勇敢担当。高校的劳动价值观教育应着重于引导大学生热爱劳动、热爱创造,自觉“通过劳动和创造播种希望、收获果实,也通过劳动和创造磨炼意志、提高自己”[10],最终成长为全面自由发展的人。
第三,高校应注重在校园文化建设中打造劳动文化元素,营造崇尚劳动的校园环境。首先,充分利用墙体、橱窗、展览厅、横幅等做好劳动文化的宣传工作,通过组织演讲、讲座、文艺演出等活动,讴歌和弘扬劳动精神,包括解读相关政策法规,宣传劳模事迹、工匠精神,展示身边先进人物事迹。其次,通过社团开展志愿者活动,在校园内外掀起志愿劳动服务的气氛;最后,优化一些考核评价机制,对勤学肯干、乐于助人的同学进行适当的褒奖。
第四,高校应创新劳动平台,多渠道引导大学生参与劳动实践。学校要发挥寝室、班级、社团和社会多层平台的作用,引导大学生积极参加劳动。比如通过开展寝室内务检查与评比活动,促进学生养成日常内务管理的习惯;通过教室卫生保洁等日常性工作的安排,形成大学生都能主动积极关注班级事务的氛围;通过学校这个劳动平台,开展校园绿化管理、公共区域清洁、勤工助学等活动,让大学生参与到校园文化建设中来,提高主人翁意识;通过联系校外企业、社区或农村,开展观摩、调研和体验活动,让大学生与普通劳动者一起经历劳动过程,加深劳动体验。根据调查,大学生们在被问及毕业后“准备在哪些地方就业”这个问题时,明确表示愿意去农村就业的占比只有6.66%,74.05%的调研对象表示要到城市就业,这样的调研结果值得关注。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是需要大批各类优秀青年人才自愿投身到乡村振兴事业中去的。但目前,我们的学校教育基本上是远离乡村的教育,甚至那些来自农村的学生都未必了解农事。《颜氏家训》指出,不知“耕稼之苦”“劳役之勤”,则很难应世经务。一个人如果缺少对农业劳动、农事活动的体验,缺少对农村、农业的热情,是不会有投身乡村振兴事业的强烈意愿的。
第五,高校应重视家校社联合,打造协同劳动的育人机制。在家校协同上,高校要主动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充分发挥家庭在劳动教育中的基础性作用,引导家长关心并关注大学生日常的劳动习惯、劳动品格的养成问题,同时做到以身作则,督促大学生在家也能保持良好的劳动习惯,积极帮助父母分担家务,承担家庭责任。在与社会的协同上,高校要加强与地方政府、企业和社区的联系,获得他们的支持和保障。同时,高校也要注意配合社会治理的需求,开展有针对性的劳动教育教学活动,广泛传播劳动精神,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炫富攀比、不劳而获等不良现象,共同营造崇尚劳动的社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