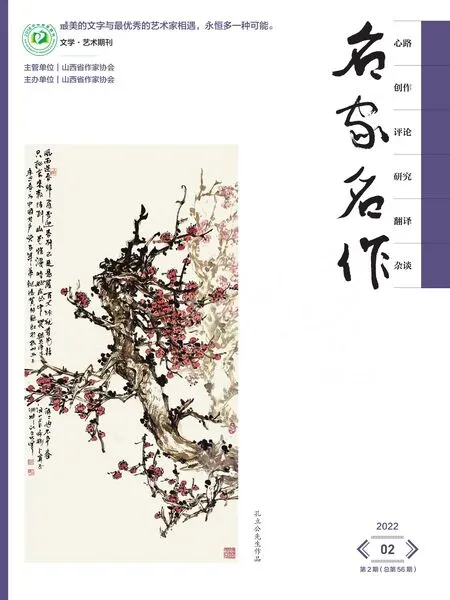《眉语》中的图像对都市新女性形象的建构
2022-11-11唐先菊
唐先菊
晚清时期,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中国部分知识分子把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作为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尺度。1914年,陷入一战泥潭的西方列强自顾不暇,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发展,报刊业也得到发展,此时国内时局动乱,人们对政治感到失望,沉迷于享乐之中。在这种环境中,一大批以商业盈利为目的的女性杂志诞生,《眉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本文主要以《眉语》中的都市新女性为研究对象,通过图像与文本的结合,考察当时都市新女性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状况。
一、时尚的服饰与身份的焦虑
《眉语》在第一卷第二号的《本杂志编撰部诸女士像》中刊登了五位编辑的照片。高剑华身穿小凤仙装,佩戴着当时作为流行饰物的眼镜。柳珮瑜身穿西式衬衫和大衣,头戴西方圆顶礼帽,手拄着西式文明棍。由照片可见,这些处在新旧交替时代的知识女性对时尚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西方的影响。清末民初,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一部分在城市生活的知识女性率先觉醒,产生了自由解放的念头。时尚对她们而言,是新女性身份的标识。《眉语》第一卷第二号《美人睐》刊登了女子身穿男装的照片:图中女性头戴男士瓜皮帽,身穿男士马褂套装。儒家思想强调男女不通衣裳,女扮男装无疑是对传统秩序的破坏。民初时期女穿男装的现象并不少见,徐坷的《清稗类钞》中提到,当时青楼中的妓女们身着男装的很多,“徒步而行,杂稠人中,几不辨其为女矣”。清末民初,秋瑾以身穿男装的女英雄形象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秋瑾本人曾说过自己喜欢穿男装的原因:“在中国,通行着男子强女子弱的观念来压迫妇女,我实在想具有男子那样的坚强意志,为此,我想首先把外形扮作男子,然后直到心灵都变成男子。”在当时,社会期待的女性特质是柔弱、温顺的,“坚强”被认为是只有男人才拥有的品质,女性想要获得这样的品质,就需要摆脱身上的女性特征,从内到外变成男人。只有这样,女人才能作为“坚强”的人得到社会的认可。
清末民初,一些有机会进入新式学校学习的女性开始觉醒,这些女性选择走出家庭,自力更生。但当时社会可以为她们提供的职业太少,她们在经济上得不到保障,又不甘心回到家庭之中,只能选择从事社会服务型行业。一方面,沦为社会服务型的摩登女郎无疑意味着女性的堕落和沉沦;另一方面,她们堕落的起因和目的是为了解救自己。从这个角度来看,导致这些女性堕落和沉沦的原因正是她们解救自身的渴望。她们一旦堕落和沉沦,便会被社会抛弃,成为社会的边缘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她们自己才可以自我解救,对这部分女性来说,时尚是她们自我解救的工具。
二、女性身体的解放和女性身体的商品化
《眉语》第一卷第一号、第五号、第六号和第十四号封面上的半裸美人图均出自郑曼佗之手。《眉语》第一卷第一号封面中的女性上身皆未着寸缕,仅靠一条薄纱遮掩身体,其大胆开放的程度是传统中国美人图中没有的,图中女子的五官和神态则充满了东方韵致。除了郑曼佗创作的半裸美人封面图为东方女性之外,《眉语》中刊登的全裸美人图都是西方女性。刘海粟在《二十年代围绕着模特儿问题的一场斗争》中提到,1914年,上海美专不仅无法聘用到女模特,连男性也不愿意做模特。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之下,《眉语》编辑在刊载全裸女性画的时候,只能选择西方女性。
除了总发行所在上海,《眉语》在全国21个省及南洋各地都设分所。从销量上看,《眉语》第一卷第三号称其发行量已经达到5000多册,“而民初一般杂志同类杂志每期只有一两千份”,可见《眉语》的读者数量多且杂。《眉语》编辑在选择西方裸体美人画的时候,要考虑大部分读者的文化知识水平和审美鉴赏能力。对当时大部分人而言,还没有能力纯粹从艺术角度出发去欣赏这些画作。《眉语》编辑在登载这些西方裸体女性画像时,没有对其背景做详细解释,而是在图中配上与中华传统文化相关联的文字来保持图片的趣味性。如第一卷第三号有一组《采莲图》:这组画中有三幅图,分别是“临风”“汤桨”和“散花”。中国古代诗词中素有描写美人采莲的传统,南朝乐府民歌《西洲曲》就以女子采莲来寄托对爱人的思念和忠贞,《眉语》编辑把这幅西方美人图命名为《采莲图》,再配以“散花”“汤桨”和“临风”,很容易把读者带入对传统文化的想象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对西方文化并无了解的中国人也能从中获得想象空间,从而体会到图片的趣味性。编辑借助这些西方裸体美人图来满足读者对女性裸体的窥探欲,通过搭配与中华传统文化有关的文字或者诗词来维持图片的趣味性,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隔阂,即使是对西方艺术不了解的读者,也可以通过图片上的文字拥有自由想象的空间。
三 、虚幻的婚恋自由和现实的困境
《眉语》上刊登了大量以爱情为主题的组图。其图像分为东、西方两种,西方图像在情感表达上更为大胆直接,东方图像则较为含蓄内敛。第一卷第五号有两张分别名为《女儿羞》和《女儿娇》的照片,前者是一对西方恋人在黄包车内对视,他们举止亲密,紧紧依偎在一起;后者是一对东方恋人,女子在假山之上向男子伸出双手似乎要扑向男子,男子在下方握着女子的手。在《眉语》女编辑看来,男女之间的情爱应该是坦荡、热烈的,男女之间的情欲是合理的,然而当图片中的情侣为中国人时,编辑却选择了更为含蓄的方式展示情侣之间情感的流动,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中华传统文化中,未婚嫁前,男女之间几乎没有接触的机会。清末民初,女性可以入学读书,但是男女交往十分受限。一些因师资不足不得不招聘男老师的女子学校在招聘男老师的时候态度极为谨慎。首先,在年龄方面要求60岁以上。其次,为避免男老师和女学生有直接的交流和接触,有些学校规定:男老师讲课的时候不能看女学生。五四运动之后,随着社会对男女同校问题的讨论,男女同校的学校越来越多。“五四以后,婚姻自由的观念在智识阶级里似乎已经普遍化了,大多数人已经觉得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可是纯粹恋爱的结合总还只有少数人敢去尝试。”在这种环境中,《眉语》编辑选择西方人来完成情侣中亲密关系的想象似乎更为合理。
《眉语》正大光明地在期刊上刊登了大量以男女爱情为主题的照片,除了为了商业盈利的目的,还有鼓励婚恋自由的意图。《眉语》第六号《女子之求婚》一文中,作者提到俄国有一个叫厄克冷的地方,婚配事务全凭女性做主。《眉语》编辑试图给读者传达这样的信息:俄国女性不但能够自主择偶,而且她们在与男性相处的时候处于支配地位。实际上真实的俄国社会并非如此,在俄国颁布《公民婚姻法》之前,俄国妇女结婚必须征得父母的同意,一旦嫁人,她们便要追随丈夫的姓氏。由此可见,外国女性拥有绝对的婚恋自主权只是来自作者的想象。当时的女性认为只要获得了婚恋自主权,自己就可以摆脱父权的统治。事实上并非如此,当时的社会可供女性选择的职业极少,即使部分女性获得了职业,其薪资相比于男性也少得可怜。即使少数女性毕业后可以找到工作,也难以平衡家庭和工作。“女教员们,一周担任二三十小时功课,回家还要带小孩子,烧饭洗衣,晚上还要改卷子,预备功课”,这种繁忙的生活状态导致当时的女性无法兼顾家庭和工作,于是出现了两种极端的现象:一是专注于事业而失去青春,导致晚婚甚至不婚;另一种情况是渴望快速找一个家产丰厚的男性嫁人,在经济上继续依附男性。
可见,在当时的社会,女性并没有真正的婚恋自主权,即使女性可以自由地选择婚恋对象,在结婚后仍然不能获得独立自主,她们依然是男子的附属物和男权文化的牺牲品。男性一方面倡导女性的自由解放,另一方面又对自己主权的丧失感到恐惧和焦虑。《眉语》编辑通过刊登这些以爱情为主题的图像,给当时的都市新女性提供了一个幻想的空间,这个幻想的空间可以让她们暂时逃离当时的社会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