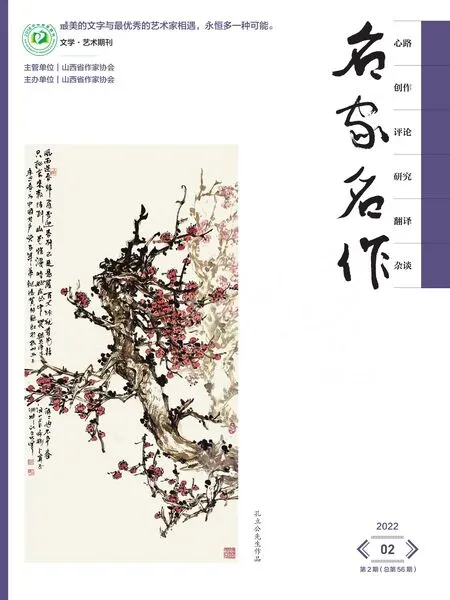《西游记》在英国的文化传播
2022-11-11杨娟
杨 娟
一、《西游记》的译介与传播
《西游记》在西方世界最早以片段的形式传播,早在1895年,上海华北捷报社出版了美籍在华传教士吴板桥的《金角龙王或唐皇游地府》。该通行本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但也是《西游记》进入英美世界的初步尝试。1942年,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的译本Monkey(《猴》)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该译本因通俗易懂的情节而受到读者的青睐,成为《西游记》译介传播的典范。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转向”直接推动了《西游记》的译介活动及相关研究领域的繁荣,根据《西游记》译本改编的影视剧等层出不穷。至今受到学界广泛认同的《西游记》全译本有两部,一部是华裔学者余国潘的译本,另一部是英国汉学家詹纳尔的译本。其中,余氏译本又是当前在西方传播最广的文化译本。翻译并非单纯的言语活动,也是一种复杂的文化交往行为。译者作为文化的传播者,译者本人的翻译策略和思想意识等在各自的译文中得到彰显,并且直接影响到译文的传播效果。英国作家亚瑟·韦利作为以英语为母语的翻译家,他对小说阅读的目标群体的认知能力有深刻的了解,将《西游记》中的冒险、勇敢、机智等大众喜闻乐见的价值观精准地对接到西方的价值体系中。如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情节,亚瑟·韦利采用了归化的翻译方式,凸显了孙悟空的个人形象,来表达一种大无畏的反抗精神,这与西方价值观念中的个人主义与英雄崇拜相契合。亚瑟·韦利的译文显然是故事传播,而不是文化传播。其对原文中大量的诗词进行了删减,只保留了思想内涵和西方民众价值观念相符合的部分,这也是该译文受众广、传播广的原因所在。余国潘先生是美籍华裔作家和学者,一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宗教方面的研究,基于自身的人文学者的立场,以学术交流为立场,倾向忠实翻译,采用了异化翻译策略。如“悟空”二字的翻译,使用音译法,又对此进行了简单的注释,深入浅出,极大地尊重了原著的思想性、文学性和艺术性,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意味着放弃了很多非学术目的的普通读者,使得余译本的流传度远不如亚瑟·韦利的译本。詹纳尔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英国人,在翻译策略上,归化为主,异化为辅。如对于“阎王”一词的翻译,詹纳尔先生的译文是“King of Hell”,“hell”指的是基督教义中的“地狱”,虽然符合目标读者的宗教背景,但两者的宗教含义不同,相比之下,余译的“YamKing of the underword”更加符合原文的思想。
总的来说,余译本的受众程度远远不如亚瑟·韦利的《猴》,但余译本极大地尊重原著。而亚瑟·韦利的译文,为了满足欧美读者的需求,经过了较大程度的改写,大大降低了原文的艺术价值。而詹纳尔的译文对于英语读者来说,更多地对文化、文体、语言进行了转换,尽量引导两种语言、文化调和共融。詹纳尔的译文纳入了“大中华文库”和“汉英经典文库”出版,在中英两方的认可度较高。
二、《西游记》在英国的传播形式
《西游记》在海外传播中,无论其译本的数量,还是在跨文化改编形式的多样性上,堪称中国故事“走出去”的典范。而《西游记》在海外传播主要有文本和非文本两种形式。 对于文本形式的传播来说,伦敦英国博物院很早就藏有小型刻本形式的《绣像西游真诠》。直到1901年,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编写的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国文学史》)在纽约和伦敦同期刊印,首次提及《西游记》书名以及介绍了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故事。1905年上海华北捷报社在East of Asia Magazine(《亚东杂志》)第四卷发表了英国汉学家韦尔的论文The Fairyland of China(《中国的仙境》)。大英博物馆检索系统出现次数最多的是亚瑟·韦利的《猴》,该译文以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排印本兼标点本《西游记》为底本,只选取了其中的一些章节,着力塑造主人公的形象,展示其故事性和世俗意味,所以该译本一直畅销。与此同时,《西游记》的故事逐渐成为儿童读物的常见题材。亚马逊(英国)在售的《西游记》读物有80多种,绝大多数为中文版,英语版本有十余种。进入20世纪,媒介类型更加丰富多样,西游故事、神魔趣事、历险题材和各色原型人物广泛受到西方影视界和现代媒体的垂青,取材于《西游记》的影视剧、动画片、舞台剧、音乐剧、电子游戏在英国持续引发反响。如英国团队研发的科幻网游《奴役:西游记》(Enslaves:Odyssey to the West)。2007年,中西方联手合作的歌剧《美猴王:西游记》在英国曼彻斯特国际艺术节上大放异彩。2008年,英国广播公司为了迎接当年的北京奥运会,在其官方网站上正式推出了一部时长两分钟的动画宣传片《猴子:西游记》(Monkey,Journey to the West),反响热烈。从该片的动漫造型来看,具有浓厚的欧美典型意味,孙悟空多了妖邪气,少了中国人的内敛沉稳;猪八戒也一改以往憨态可掬的形态,变成一个其貌不扬的田径运动员;沙僧更是蓝面长耳,咄咄逼人,完全失去了原著里面老实巴交的气质。人们对这部短片褒贬不一,甚至产生了一些针锋相对的言论,但从客观上显示了《西游记》在西方世界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也表明欧美人开始对美猴王的故事有理性的思考,开始探索将中华文化更好地植入西方个人主创的作品中的路径。
三、《西游记》文化传播的困境与启示
《西游记》作为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对话的载体,无论是文本形式还是非文本形式的传播,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变异。尤其是对话关系的框架中,民族话语进行转译,不可能实现完全的对等。《西游记》的译者在面对文本中高超的语言艺术、精妙的叙事结构、丰富的修辞手法时,往往举步维艰。因此,注重传播效果的译者,如亚瑟·韦利便放弃了原文中的诗歌部分,选取了里面故事性强的部分,而不是文本的全面性;忠实于《西游记》原著的译者,如余国藩力图让西方话语与东方话语对等,效果甚微。由于中国诗歌中的修辞和典故,对西方读者来说实在无法理解,也难以找到恰当的翻译方式。即使是西方的汉学家,在面对《西游记》时,也会找寻本民族的文化参照物。例如,余国藩本人就十分关心《西游记》的文化标杆问题,李奭学也提出,从一个西式的角度来看《西游记》,“《西游记》的内容,其实诗歌‘取经’或‘朝圣’的‘历险旅程’,所以和荷马的《奥德赛》……尤其是但丁的《神曲》……的确有许多可以相互呼应的地方”。这为中国的文化传播工作者提供了翻译思路和传播方向,即找到一个容易被西方接受的故事线,并以此为主线进行编译。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思路。第一,中西译介合作。《西游记》的众多版本中,取得成功的译文都不是目的语文化方译者单独实现的。如余国潘的译文,就参考了陈士斌、张书绅等对《西游记》的诠释资料。中外译者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在把中国传统古典小说的高语境的表达方式向低语境的表达转换时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第二,充分利用传播媒介的互补性。跨文化传播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其有效实现和文本构成、传播方式、情感价值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是一个交互的过程,单一的探索路径难以取得成功,研究者必须综合考量不同路径的相互作用。2020年8月份《黑神话:悟空》在国外也引发了强烈的反响,至今已经收获了600多万的播放量,其传播的范围和效果远远大于文学文本。第三,构建本民族文化话语传播体系。文化冲突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愈演愈烈,翻译问题已成为一个文化问题,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就是语言,如今全球化的发展给“语言”蒙上了一层意识形态色彩,《西游记》这个经典文本中的诸多文化价值在西方话语中被掩盖。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解构主义思潮启迪了翻译界,文化传播应该肩负起解构话语权力的任务,深入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历史脉络,应对具备跨文化传播潜能的中国古典小说进行系统的整理,构建一个平等的而非规训的文化话语传播体系。
四、结语
《西游记》已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代表。为了满足不同的需求和顺应全球化的潮流,五花八门的改编应运而生,这些改编虽然扩大了《西游记》的传播范围,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文化误读或是文化的缺失。从翻译入手,中西译者各取所长,利用传播媒介的多元性,最重要的是要有充分的自觉性,对中华文化进行创意编码,才能准确地传递中国符号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