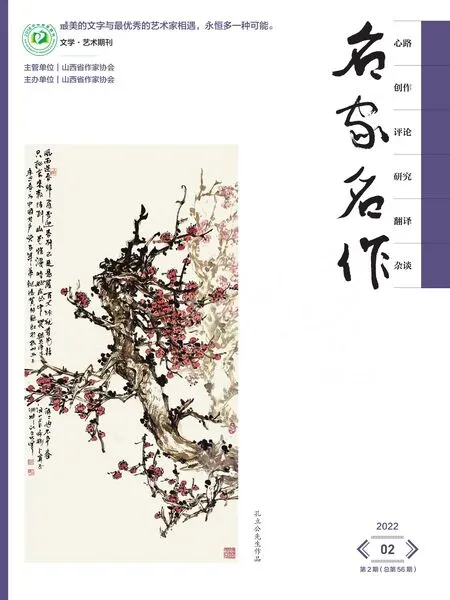多重叙事视角下的《巴黎圣母院》
——以克洛德的人物塑造为例
2022-11-11康颖
康 颖
一、引言
维克多·雨果是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最杰出的代表,《巴黎圣母院》是雨果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国内对《巴黎圣母院》的研究多集中在美丑对照原则、复杂的人物形象、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以及艺术手法等方面,从叙事学角度探讨雨果创作的内容相对比较少。克洛德一直是书中备受争议的人物形象,本文试图通过对《巴黎圣母院》进行文本细读,分析在多重叙事的视角下,作者是怎样塑造克洛德这个充满矛盾的角色的。
“叙事视角”即“叙述聚焦”,指作者观察事件或事物的角度。叙述聚焦最初是由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在《修辞格》一文中提出的,在《叙述话语》一书中,他将叙事聚焦分为零聚焦、内聚焦和外聚焦。热奈特提出“聚焦”这个术语,主要是为了厘清叙事学中“谁说”和“谁看”的混乱,“即谁是叙事文中观察者的问题和完全不同的谁是叙述者的问题之间的混淆”。“谁看”和“谁说”的问题,实际上两者一个代表了观察的视角,一个代表了叙述的视角,观察者是“谁看”的问题,是以谁的视角去展开故事的;而叙述者则是“谁说”的问题,也就是研究声音的问题,指叙述者传达给读者的语言是如何展开的。叙述者和观察者的关系是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两者时而是一致的,时而是不一致的。
二、全知叙述视角——克洛德的成长
热奈特理论中的零聚焦叙述视角也被称为“全知视角”。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不仅可以说、可以看,还可以全面掌握人物的内心世界,达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效果,叙述者仿佛“上帝”,知道书中每个人物的发展变化、情感思绪,知道故事发展的脉络和全局,作品中的任何人物都没有叙述者了解得多,叙述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任意的时空来叙事,也可以从某个人物的细节处入手。
就作品中对克洛德的人物塑造而言,对克洛德的描述最初采用的就是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集中在小说第四卷的第二章和第四章,这两个章节集中对克洛德的身世和成长经历进行了叙述式的描述,同时在作品其他章节也通过他人的视角对克洛德进行描述。
克洛德出生在一个中等阶级家庭,他从小就听从父母的安排去神学院学习,在学院里一直勤奋刻苦,是神学院里苦修博学的优等生。在16岁时,克洛德博览群书,在各方面已经具备了成为一名优秀的神甫的条件。克洛德的学习不仅限于神学方面,还学习了医学、天文、语言和其他知识。但是在他19岁的时候,突如其来的瘟疫使得克洛德成为孤儿,他独自抚养幼小的弟弟长大,甚至还出于怜悯收养了弃儿弗比斯,并教他读书、写字。由此可见,成为主教之前的克洛德是一个勤劳好学的学生,是若望和弗比斯的守护者,是一位科学知识的追寻者,闪烁着内在美的特质。但是若望成年后的无知和懒惰,让克洛德十分失望,他又一次投入了科学的怀抱,在偏执中迷失了人性和信仰,成为一位严厉的、阴沉的神甫,变得倍加严肃、不近人情、异常冷漠。
雨果用全知全能的视角向读者客观地介绍了克洛德的成长经历,掌握了人物的发展变化,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将克洛德年少时到成为副主教的经历通过大段地叙述展现给读者,最初的克洛德还是有人情味儿的、虔诚的,随着其曲折的成长,最终成为人人害怕的、阴沉的副主教,使读者理解他性格的双重性产生的原因,展现出克洛德身上的悲剧性色彩。
三、内聚焦视角——克洛德的内心世界
内聚焦经常被称为内视角,即叙述者和观察者的视角合二为一,两者都集中在一个特定的人物身上。内聚焦视角不同于全知视角,叙述者只能聚焦于自我,只知道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整个故事的完整脉络并没有提供给叙述者,可以得到与全知视角不一样的叙述结果,叙述者能更深入地展现角色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感情。
克洛德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杂的角色,雨果在塑造这个具有双重性的角色时,采取内视角,站在克洛德的视角上,用主人公的内心独白,揭示他内心的所思所想。当克洛德看到爱斯梅拉达跳舞时,他长期被压抑的人性被唤醒了,面对这样年轻美丽的女子,副主教立马爱上了爱斯梅拉达。但这种热烈的情感明显违背了他恪守的禁欲主义,这浓烈的爱让他失去了分寸,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是一个神甫,却把弥撒书当做淫欲的枕头。”克洛德作为副主教,恪守教义、崇尚科学,但爱上爱斯梅拉达后,并不再是从前那个严格的禁欲者,面对被唤醒的人性,他同样有欲望,内心矛盾不已。
小说中还有一处,用内聚焦叙事揭示了他在遇到爱斯梅拉达以后内心的躁动和挣扎。对爱斯梅拉达的追逐和迫害,让克洛德更加疯狂,在将爱斯梅拉达送上绞刑架前,克洛德深情告白,苦苦哀求爱斯梅拉达接受他的爱,却遭到爱斯梅拉达的严词拒绝,甚至是对他恨恨地唾弃。克洛德的爱而不得让他内心愈发痛苦,一次次的拒绝也让克洛德的爱逐渐转变成了恨,爱与恨、善与恶多重复杂的情绪萦绕在他的心中。雨果用克洛德大量的内心独白来表现他的挣扎和痛苦,也展现了教会对克洛德的束缚。事实上克洛德对爱斯梅拉达的爱,是一种被压抑的、被扭曲的、变态的、疯狂的爱,是充满矛盾和挣扎的。通过内聚焦对克洛德内心世界的叙述,我们可以窥探到他内心的激烈斗争。克洛德不仅仅是宗教伪善的代表,同时也是它的受害者,是在宗教禁锢下被扼杀了人性的牺牲品。雨果正是用这样的叙述视角描述克洛德内心隐秘的感受,体现了克洛德的双重性,由此表现教会对人性的扭曲和摧残。
四、多重视角的转换——克洛德的挣扎
多重视角,是指从多角度出发,采用不同的方式观察同一个事件或人物,这种对同一对象的多角度、多侧面的聚焦,构成了一种复合式的、相互呼应的叙述特色,多重视角增强了人物的深度和厚度。同时,多个叙述视角的灵活转换,弥补了单纯使用某个叙述视角造成的不足,从多个视角阐释故事,使得人物的言行与心理更加饱满,描写的主题对象更加突出,丰富了故事的层次和内涵。
在《巴黎圣母院》中,雨果的叙述视角切换频繁多变,有时雨果会采用全知的视角介绍巴黎的建筑特色、人物的成长经历,甚至是一些宏大的场面描写;有时雨果会采用内聚焦视角,从不同的人物视角出发,去解读同一个事件在不同人物的视角下是如何观察的。克洛德的人物形象在这种叙述方式下,无论是言行还是内在都显得更加饱满和立体,同时也实现了多种视角运用的灵活转换。
最典型的例子是在小说第九卷第一章《昏热》中,一开始雨果采用了零聚焦的全知全能叙述视角,叙述克洛德在爱斯梅拉达被弗比斯救走的时候的一系列动作,回到更衣室,他先是脱掉自己的衣服、围巾,扔给了仆役,急忙从便门就逃了出去,钻进了崎岖的街道里。接着很自然地转入了内聚焦的视角,刻画了他复杂的心理活动,对爱斯梅拉达的向往,对弗比斯的嫉妒,对自己的嘲讽,展现了克洛德内心的躁动不安。他想象着假若爱斯梅拉达与自己的身份变换,自己不再是神甫,也许两人可以一起逃跑,彼此相爱,可这份夹杂着信仰与人性的矛盾的爱,让他变成了魔鬼。他不断地逃跑,夕阳也落下,同时叙述视角又转变为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描写了克洛德碰上了他的弟弟的情景,他害怕被弟弟发现这狼狈的样子,于是顺势躺在地上装醉。两种不同视角的灵活转换和运用,不仅克服了零聚焦的全知全能视角的分散性,同时也弥补了内聚焦的第三人称视角的片面性。尤其是内聚焦视角中克洛德的内心独白,将克洛德备受挣扎的内心展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他不能停下对爱斯梅拉达的美好幻想和向往,渴求爱斯梅拉达能接受他的求爱;另一方面,爱斯梅拉达对他求爱的一次次拒绝,对“生死未卜”的弗比斯的关心,以及宗教传统对克洛德的压迫束缚,让克洛德的灵魂彻底倾覆、破碎、撕裂,可见他的内心是十分挣扎和痛苦的。
在《巴黎圣母院》中,两种视角交替使用的情况十分普遍,或从客观的零聚焦描述事实,或从不同的人物视角出发,对克洛德的内心世界进行了深入分析,构成了互相映照、互相补充的交响乐般的叙述效果,有助于多侧面理解克洛德复杂的人物形象,探寻克洛德内心的挣扎和发生转变的原因。
五、结论
雨果是一位具有很强的叙事意识的作家,他不同于同时期的其他作家,他将塑造的重点放在人的复杂性上,雨果笔下的人物往往是复杂的、生动的,具有一定的多面性,带有立体的、浑圆的人物的性质。克洛德具有十分复杂、立体的性格,两种叙述视角相结合产生了多声部、多层次交响乐般的叙述效果。雨果使用这种叙事手法,让读者窥见克洛德内心苦闷的叹息和在求爱过程中犯下的罪恶,但同时也意识到他是宗教禁欲主义的受害者和牺牲品,从而对他感同身受,进一步丰富了克洛德这个善与恶相统一的立体的人物形象。